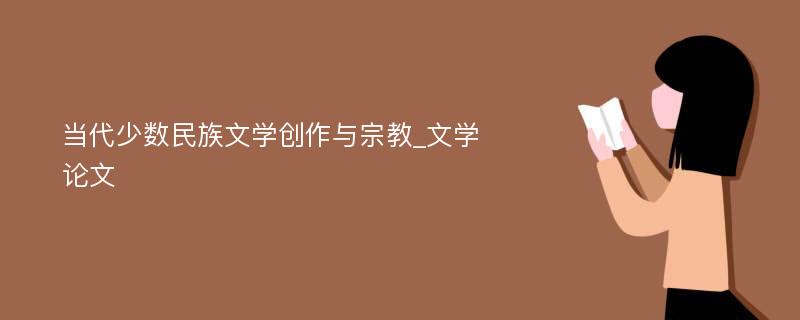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宗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当代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I19 B93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里的“当代”一语,在这里是一个特指的时间概念。也就是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指的是建国以来由我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作者们所创作的所有作品,包括用汉语汉文和本民族语言文字所创作的所有体裁的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因语言的障碍,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所创作的作品,本文不拟涉及它的价值判断。
我们的前辈文论家们在对少数民族文学与宗教的研究时,大多滞留于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的研究,或宗教经典与文学的研究,而忽略了建国以来由我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作者们所创作的文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为了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推向深入,拓宽其研究领域,特写拙文以作尝试与探索。
一
宗教与各少数民族的现代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各少数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各种节日和禁忌、风俗人情、婚丧嫁娶,乃至农牧业生产及收获等,都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已渗入到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诸领域,并积淀为稳定或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隐含于各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之中,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下,以各种形式展现出它颇具能量的作用。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要历史地、真实地、生动地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全部面貌、表现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和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内核以及本民族的心理结构,不可能不对本民族宗教文化现象作认真的考察和描述。宗教反映、渗透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自古以来,文学便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中国而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的《周颂》既是宗教,又是文学;楚辞《九歌》也既是文学,又是宗教。因此,宗教与文学都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两种评说和把握方式,二者同属上层建筑,都是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复杂反映。它们同源而异流,如象两股溪流,都发自于社会生活之源,而又各自沿着自己特有的渠道奔腾向前,以自己的波涛与喧闹,尽情地显示着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与文学,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既有先天的血缘联系,也有后天的性格差异。
由于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并早已渗透到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诸方面,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和生活习俗等,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留下了各种宗教印迹,尤其是全民信仰宗教的民族,整个社会诸领域无一不受宗教的浸染。因此,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其笔端总是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本民族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宗教现象,作品内容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宗教的影响或带有宗教与宗教习俗色彩;少数民族作家们在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时,如果有意无意地回避宗教现象,反倒是一种失真。
二
纵观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历程,关于宗教题材与宗教人物的描写,经过了一个不同的演进变化过程。
从50年代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的近30年,少数民族文学是以歌颂为主调的歌颂型文学。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反映宗教这一题材时的基本倾向是对宗教的完全否定。由于宗教文化中有摧残人性等消级因素,因此,大多作家以宗教作为反面对象进行描述无情批判,政治上予以否定。除个别作家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宗教现象外,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把宗教当作封建迷信或完全反动的意识形态加以揭露和批判,这是事实。有的作家甚至把宗教与政治相提并论,即:宗教即政治,政治即宗教,如政治是反动的,宗教也是反动的,二者有机的统一。有的作家尽管把思想较开明的宗教上层人士从宗教中脱离出来予以肯定,但事实上取得这一肯定是对宗教的反叛,目的也是对宗教的进一步否定,如《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玛拉沁夫)、《草原雾》(扎拉嗄胡)、《欢笑的金山江》(李乔)。到了三中全会后的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们正处于中外文化相互影响之大潮中,这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民族自省,在对待宗教这一问题时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完全否定宗教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老一辈作家和中年作家的作品中,如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等等;一种是表现在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他们在寻找自己文学创作之“根”的同时,将笔端渗入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领域,正面描写宗教现象,他们既看到了宗教的消极因素,也发现了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审美观照,如孙健忠的《死街》、朱春雨的《雪菩提》、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朝佛》、马知遥的《古尔邦节》、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棕色的熊》以及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和《一个彝人的梦想》,等等;另一种情况是完全肯定宗教文化的,如张承志。他是一位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现代宗教意识和肯定宗教文化在其小说《黄泥小屋》、《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宗教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份。因此,以形象表现和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与历史发展为己任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可能避免对少数民族宗教的描述。我们主张少数民族作家们要尊重客观现实,尊重艺术规律,不夸饰,也不回避予盾。宗教以及与宗教有关的习俗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得到公正的反映,歪曲、回避或忽略或完全肯定或否定这一文化现象都是不科学的。既要看到宗教的消极因素,又要看到并承认宗教的积极作用。
三
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初步形成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群,产生了具有一定质量和有影响的作品,如彝族作家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山江》、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的长篇小说《红路》和《草原雾》、壮族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等等。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是由当时的中国历史所决定的,因此,他们是时代的产儿。既是一代人,也是一代作家。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大多来自本民族地区,在党的关怀下,亲自参加了革命,亲自投身于火热的斗争,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这个时期初露头角的少数民族作家或后来才步入文坛的作家,在接受汉语汉文的同时,竭力学习和模仿汉族作家和外国作家(当时主要是苏俄作家)的写作(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因熟悉本民族的本土文化,受到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而成为作家,这也是事实)走上创作道路的,所以他们的创作风格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的汉族作家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无论受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还是受汉族作家的创作影响,他们均处于一个不断模仿的创作过程,属于一代具有一定成就的效仿型作家。
正是由于效仿别民族(主要是汉族)作家,加上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教育时,只是单频道(纯粹实用性)地接受唯物论思想的教育,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宗教现象,包括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民风民情,便在50—70年代末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一直受到了无神论思想的冲击。作家们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不假思索、不加研究地一概反传统,宗教理所当然第一个受到冷遇和致命的批判。那一时段几乎所有作家都在唱颂歌,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歌颂党的民族政策,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歌颂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歌颂各民族的翻身解放等上面。当然,我们不反对这种颂扬,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这对中国少数民族来说,确是雨后晴天、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值得大书而特书。但是,我们也认为,体现着每个民族历史文化深刻内涵的民俗民情包括宗教信仰等,同样应该是不应被蔑视的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从50年代初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尽管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反映了本民族生活,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在创作思想上、审美趣味上浓厚地带上中国当代政治变迁的历史风尘,甚至在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了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注:《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的超越》,尹虎彬著,见《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6期。)宗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禁区,或不敢涉入, 或有意无意地忽略、回避。当然,基于这一时期的客观现实,作家们不可能在创作上独辟蹊径,哲学上的归属性思维必然导致:归属于统一的政治模式而形成一种统一的创作模式。这个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多数是寻找一种与汉族、或与这一时期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现,而缺乏从本民族生活、本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本民族心理素质的角度去反映和描述生活。宗教,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自然要受到批判或否定,或扬弃。
中国历史如此悠久,传统文化如此绚丽多姿、如此雄厚,中国并非是无宗教的国家,儒道不就是中国的吗?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习俗,乃至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各种宗教现象,我们的作家们应采取审慎态度。当我们还不完全认识它、了解它时就拒之于创作之门外一概斥之,全盘否定,这未免太过分了。要承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宗教,现实生活中也有宗教,若把它完全看成是人民的敌人并将其进行无情地批判和扬弃,视其为“鸦片”(消极因素),欲在旦夕之际全部铲除,这办得到吗?也行得通吗?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注意表现本民族的宗教信仰等习俗。挖掘本民族独特的心理特征。彝族老一辈作家李乔在其《欢笑的金山江》等作品里对凉山彝民族的宗教有所涉及,但李乔对彝人所崇奉的原始宗教以及宗教人士苏尼和毕摩也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认为他们都是“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的主持者,应坚决制止。我们认为原始宗教并非完全迷信或反动,有其积极的一面和合理的因素。当然,我们知道,李乔是个彻底的无神论作家,在无神论思想的指导下,理应对宗教进行否定。但由于李乔本身不是凉山彝人,更不懂彝语,他对凉山这块神秘的地方并不很了解,很难知道凉山彝人的历史文化以及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习俗现象。我们在这里并不否定李乔具有一定的本民族感情,但有感情并不等于对待本民族文化现象以及其他事物都正确。他认为存在于彝人们生活中的原始宗教以及有关带有宗教色彩的习俗都是陈腐落后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阻碍着当地彝人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应当统统去掉,这个“度”就未必把握得完全正确。
四
到了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可否认地处于世界文化大潮之中。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也就在这样宏大的中外文化相互发生作用的背景下崛起了,并取得了很大成就。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仍是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同样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有的直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有的通过汉族作家受到间接影响。八十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文学所反映的生活,不是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的生活,而是在与中外文化发生交感和对流的世界性格局中的生活。广博的外国文化一旦与优厚的中国文化结合,便产生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坛充满了勃勃生机。
外国文化中的文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所发生的作用尤为深刻,英法美等国文学、苏俄文学、拉美文学都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拉美文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则更大,如藏族青年作家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等作品,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等作品,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和《一个彝人的梦想》等诗集,都可以从中看出拉美文学对他们创作的启迪,还有青年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等作品,我们也不难发现其所受艾特玛托夫和海明威等的影响。
新时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在八十年代初,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创作实践陡然转向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作家们打破了以往的禁区,有了新的觉悟,重新神视脚下的国土,回顾自己民族的昨天。在这样的文学大潮中,少数民族作家也进行着寻“根”实践。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说:“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他的文学创作之“根”就是在那古老而纯朴的凉山。藏族青年作家扎西达娃的“根”不也就在雪域高原吗?这两位青年作家的“根”都在祖国西南边陲各自民族文化的沃土上。回族青年作家张承志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影响巨大的作家之一。他与鄂温克民族作家乌热尔图的“根”都在北国。这四位作家和诗人,北南相应,大胆探索、创新,是五十年代乃至三中全会以来的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们是新的一代,而又是在新的时期崛起的。他们在中外文化的影响下寻觅着自己的“根”也寻到了“根”,于是发现了自己的“根”越理越深,简直是深得不可探,因而以公正的创作态度去认识事物、描写事件、塑造形象。置于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纵深广阔的文化背景,少数民族作家有意识地向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的掘进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来自本民族,又回到本民族,立足于本民族。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真诚感受,基于胸中流淌着的民族血质而赋予的真诚意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基本的和首要的标志。少数民族作家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而投入文学创作之中。他们把文化价值取向深入地指向了本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德,极力维护本民族文化中属于美好的东西,以严峻的审视态度来描写本民族的风俗人情,其笔端有意无意地触及传统文化中的宗教现象,既展现了良俗中的美德,揭示它在民族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又挖掘出陋俗中的劣根性,指出它扭曲人性、阻碍生产、不利团结、不适应人类生存和时代前进的落后性,从而较深刻地展示出少数民族社会各个文化层次的特殊风貌。当然,由于宗教本身的复杂性,所以涉及宗教题材的作品,其主旨是复杂交错的;作家对宗教的感情,也是复杂微妙的。
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冥》、《丧钟为谁而鸣》和《朝佛》等作品便典型地体现出复杂却又很正常的心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开篇就是:“现在很少能听见那首唱得很迟钝、淳朴的秘鲁民歌《山鹰》。我在自己的录音带里保存了下来。每次播放出来,我眼前便看见高原的山谷,乱石缝里窜出的羊群,山脚下被分割成小块的田地,稀疏的庄稼,溪水边的水磨房,石头砌成的低矮的农舍,负重的山民,系在牛劲上的铜铃,寂寞的小旋风,耀眼的眼光。”然而,“这些景致并非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而是在西藏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扎西达娃从心灵的深处流露出了对这种原始生活图景的留恋和欣赏。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琼跟一个过路的汉子走了,“她根本不想去打听汉子会把她带向何处,她只知道她要永远离开这片毫无生气的土地了。”那汉子是要去“理想国”的——一个虚幻的世界。女子(琼)就跟着他——永远跟着他,这就心满意足了。荒原、苍茫的天色、孤零不靠的矮屋、深沉的黑夜,没有任何顾虑和障碍的结合,漫无目标的流浪,宗教,扎西达娃画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对原始生活,他没有进行冷酷的一刀砍的否定,恰恰相反,而是对愚昧中的人类精神和旧有价值作了诗一般的赞美。男主人公塔贝在死亡之前,进入了幻觉。他将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的英语广播,说成是‘神开始说话了’”。(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曹文轩著,第184页。)这里, 宗教迷信在作家笔下已失去了原有的反动性,当然,作家的用心也不在于宣扬宗教迷信,而仅仅将它看成是一种经验式的、用以说明人类追求一种目标时的那种坚不可摧的意志。扎西达娃在其另一部作品《朝佛》中,既肯定了宗教的巨大的凝聚作用,也着力表现了虔诚固守的宗教信仰以及现代愚昧对人性的再度摧残,突出了人们的现代化要求与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陈旧观念意识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强烈的批判色彩。
当代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表现鄂温克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时也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那些老猎人对自然、动物的畏惧心理是与他们善良纯朴的美德情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作家笔下的猎人与大森林的关系是在表现着人对大自然的征服。这种征服充满着艰辛和苦难,也充满着欢乐和幸福。人在“矛盾重重的大自然里接受难以想象的磨炼与启蒙。”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许多时候,他们和解了,在其作品《七岔犄角的公鹿》里的“我”不就是放走了美丽而强壮的七岔犄角的公鹿吗?吉狄马加对彝民族原始宗教的表现时的感情更是浓郁的。诗人描绘了大凉山和森林中彝人古老而美丽的灵魂。他看到了自己民族灵魂的美。这里有爱、有友情、也有死亡的安祥和生的哀伤,而在这一感情的深处,诗人透视了彝人灵魂最宝贵的质素:“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要是在活着的日子,就能请毕摩为自己送魂”到毕摩告诉“我”的白色世界,因为“我”的祖先在那里幸福地流浪。一条白色的道路,通向永恒的向往。这说明诗人与所有彝人一样崇拜自然、崇拜灵魂。
回族青年作家张承志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作家,也是一位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系伊斯兰教最朴实的哲合忍耶教派的作家。他浓烈的现代人的现代宗教意识在其《黄泥小屋》、《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心灵史》描述的是“世世代代举红旗”,用自己的生命义无反顾地殉教以捍卫自己的心灵自由的哲合忍耶教派的两百年间牺牲如流放、剿灭等写就的历史,它既是一部艺术作品,也是一部回族人民的“宗教史”。
五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们以真诚、真实、慎重而严肃的态度来表现宗教题材与宗教人物,应当充分肯定这种极富现实意义的文学探索。但因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宗教与其陈旧的观念意识的顽固性和不可泯没性与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现实生活以及民族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任何理论先行的简单化否定和肯定认识都不可能触及其本质,因而是不足取的。可以这样说,宗教现象可以和贫穷落后的民族紧密相联,也可以和繁荣富强的先进民族相并存;可以成为消极的力量,对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起着阻碍作用;也可以化为积极因素,成为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或时期的精神支柱。
马克思说:“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上还有某些理由受到人的尊重,只有意识到,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2 页。)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要创造出神秘的艺术氛围,揭示民族心理中的奥旨,就得知晓本民族宗教文化和宗教哲学,对本民族的文化积淀要作更深层的探研。
收稿日期:1997—12—20
标签:文学论文; 宗教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