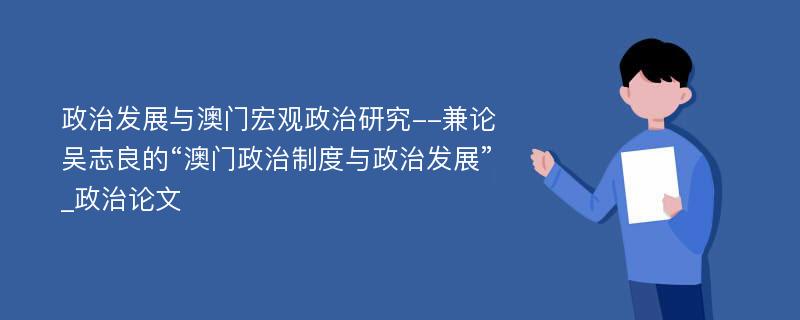
澳门政治发展与宏观政治研究——评吴志良《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政治论文,政治制度论文,吴志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志良所著的《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乃是一部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架构出发探讨澳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专著。由于该书的叙事方式是历史的,而且辅之以大量详实的档案馆材料和其他论者的研究文献,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的最大特点往往被认为是历史材料的丰富以及作者经由这些材料而表现出来的说服力。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历史材料本身并不是志良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他所要回答的的理论问题,而且由这些历史材料勾连而成的澳门政治制度史也只是志良在其知识支援下对历史材料进行选择和归类的结果。据此,个人以为,解读《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这部著作的重要之处,在于把握作者所试图回答的理论问题,洞见支配作者选择材料和处理材料的研究路径或分析框架,以及作者经由此一研究所可能具有的理论贡献。毋庸置疑,对志良这部著作可能具有的理论贡献的分析,当包括对其间所存在的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的揭示。
一、以澳门本身为主体的研究路径
大凡学术研究工作,都是在学术传统中展开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展开相关的研究之前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研究而对这一学术传统做出自己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学术传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学术研究也在其间获得了它自身的意义。依据此一道理,志良的《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首先展开的就是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反思,并通过分析和反思进而确定了他研究澳门的路径。众所周知,自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以来的四个半世纪期间,有关澳门的研究层出不穷,一如《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所附“参考书目”所示,仅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有关澳门历史的专著和资料集,中文版的就有近20种,葡文版的有近30种,英文版的有五六种。但是在这些研究论著中,套用志良的话说,“时至今日,仍缺乏一部获中葡双方和澳门居民基本认同且在学术界具起码共识的《澳门历史》”。
澳门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境况,学者们各有论说,然而我个人以为,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论者的研究路径所致。具体来讲,也就是志良在《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澳门史研究与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一样,存在着明显的双轨……,中葡学者对‘澳门史’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国学者一般将澳门史视为中国地方史,虽有其特殊性,但本质不变;而葡萄牙学者也向来把澳门史作为海外殖民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如人们所知,中国自鸦片战争始的发展趋向主要就是美籍政治学者邹谠教授所言的从权威政治系统向全能政治系统的发展,因此采取那种将澳门史视作中国地方史的研究路径,就无从解释澳门自身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非全能政治的发展取向;而葡萄牙的相应发展趋向则表现为全能政治的发展和海外殖民统治的扩张,因此采取那种将澳门史简单视为葡萄牙海外殖民史的组成部分的研究路径,也无法解释澳门自身发展中的所谓“分而治之”的现象。正是立基于此的思考,志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澳门史研究虽不可避免地以中葡两国作为重要的参照系,大量涉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必须力求以澳门为主体,真实反映中葡(包括其他民族)居民在澳门地区共同生存发展各个方面的历史,华洋不可排斥偏废,双轨定要交汇合一。”这就是志良在其专著中所确立的以中葡两国发展为参照系但却以澳门自身发展为主体的研究路径;显而易见,这一努力不仅一方面为澳门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而且在另一方面也为志良自己真切地洞见和把握澳门的“内部”发展进程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渠道。
二、“和谐共存”抑或“文明冲突”
研究路径的确立,只是志良洞见和把握澳门发展历史的一种可能渠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研究,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这是因为纯粹“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似不可能,而且即使可能,也无从反映出论者的当代理论关怀。因此,对于一项历史研究来讲,在研究路径确立的前提下,还需要对研究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加以确定。从这一角度来看,确定具体理论问题,便是志良所著《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所做的第二项努力:当然,一如我们所知,志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恰如他所言,澳门“奇特的发展演变过程不单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形下,葡萄牙人如何神话般地在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土地上据居下来的?明清政府为何让他们‘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自治长达300多年, 直到1887年才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初步确定澳门的政治法律地位?中葡两国不同时期对澳门这个特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向和政策有什么不同?澳门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葡关系史上作用如何,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扮演着什么角色?中葡民族怎样克服思想文化差异而和平共处分治?更令人深思的是,澳门又怎样面对外来压力和威胁,自强不息,屡度难关,在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摇摆漂流,避免搁浅触礁而到达今天, 并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城市?这些一直是史学界极感兴趣的题目”。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问题只是志良认为澳门发展中所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这些问题视为是志良的专著所要回答和解决的理论问题。综观《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个人以为,志良所要挑战或论辩的,一方面乃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晚近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亦即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撞与世界秩序的重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一书中指出的,在冷战以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必然替代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甚至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则是西方以现代化理论为依凭的“西方文明普遍论”,这种论点在否定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主张西方的价值和制度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普世性;毋庸置疑,志良所要批判的还有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体认西方文明过程中的非理性观点,而这种非理性观点的两极便是“全盘西化”论和“全盘反西化”论。正是志良所具有的这种对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论关怀,促使他在以澳门为主体的政治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理论观点,即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存”论。这就是志良所明确指出的,“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乃因为澳门不仅‘实为泰西通市之始’,还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典范。……这难道不值得当今世界或因经济、或因宗教、或因种族而大动干戈的国家或地区效仿”?
志良依据澳门历史经验而提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是许多其他论者所关注的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理论问题。然而,志良与其他论者不同,他在回答其所确定的理论问题时,采取的方法并不是一般论著所采取的那种只对中葡居民在澳门社会和平共处做事实描述的方法,或者那种对不同文明间和谐共存的理想做应然建构的方法,相反,他所采取的乃是对中葡居民如何在澳门社会和平共处进行探究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追究“如何”,而非追问“实然”或“应然”。正是这种讨论“如何”而非追问“实然”或“应然”的方法,决定了志良在《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中不满足于对澳门历史事实做简单的描述,而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对这些历史事实如何形成的原因加以追究,并在此一追究的基础上推论说,“只要西方文明抛弃其向来所表现的政治、军事或宗教、文化优越性,是可以与非西方文明和平共处的,葡萄牙人可以长期在天朝的土地上生存,根本的原因是面对强大的中国,只求经济互利共荣,不刻意也难以表现其政治、军事或宗教、文化的优越性。”
三、宏观历史分析与微观行动理论
姜义华先生在评论志良的《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时指出,“坚实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对澳门和世界未来深切的普遍关怀,使吴志良先生这部著作具有比之一般澳门政治史远为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内涵。作者没有仅就政治制度谈论政治制度,本书作者深入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有力地证明了澳门特殊生存发展过程,完全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变化及中西文化碰撞角力使然”;而在我看来,从分析框架的角度言,志良这一努力所凸显的则是他所采用的宏观政治发展理论框架,也就是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西方政治学界研究政治制度史的主流理论取向;这种宏观政治发展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归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套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A.Przeworski的话说,也就是“宏观历史比较社会学”(macro —historicalcomparative sociology)的一部分。 志良通过采用这种“宏观政治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强调了中葡两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以及两种文明讨价还价的过程对澳门政治制度发展的制约性,并且通过此一宏观政治发展框架的引入,揭示了澳门研究脉络中的一个新的维度,从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推进了澳门的既有研究。
当然,志良所著的《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所讨论的乃是关于澳门政治制度的理论问题;这种学术讨论的特点在于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真理性质的讨论,因此任何学者都可以对其间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甚至展开学术意义上的批判。个人以为,志良这部著作,一如其他理论著作,都存在着自身的理论限度,而志良这部著作所存在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澳门研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乃是他所引进的“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本身。然而,即使我们通过对“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的质疑而能够指出志良研究的不足之处,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恰恰是志良这部著作的贡献所在,因为正是志良将这一分析框架引入到澳门史的研究之中,为我们深入检讨这一分析框架本身提供了一个切实的文本,也为我们有可能在试图解决其间所存在的问题并推进澳门研究之前厘定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一如前述,“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大体上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然而众所周知,自本世纪80年代初以降,这种宏观研究取向遭到了大体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学术界对60年代以后的社会政治发展所展开的经验研究和统计分析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或现代化的进展与政治发展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化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复杂,而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促使论者们开始对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的缺失面展开检讨和批判。另一挑战主要来自于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当时以“博弈论”、“常人方法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等方法论的发展为基础,西方社会研究的重心日益转向个体和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亦即研究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偏好”和“选择机制”对人的行动以及制度性安排的影响。
这种微观策略分析取向所强调的,乃是这些由个人和集体所做的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决定会产生不同的政治结果,同时也是由他们做出的这些选择和决定会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和他们自己的命运,从而也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本身。正是这种从宏观向微观研究的转向,对宏观研究取向的一个核心命题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这个核心命题就是:给定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条件,个体和集体不论怎样行动,都只会产生同样的政治结果。显而易见,从这种微观取向研究的角度看,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的主要弱点就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太强的决定论品格。因此,这种微观取向的理论转向,便开始在政治制度研究中强调关注在微观且具体的历史情景下,作为政治行动者的个人和集体会选择什么行动方式和策略,以及这些行动方式和策略在各种互动过程中所可能形成的政治制度安排。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指出宏观向微观研究的转向,主要的目的并不在于由此完全否定宏观政治发展研究的分析框架,也不只在于简单地主张以当下的微观政治研究分析框架替代宏观政治发展分析框架,并动用这种微观分析框架来研究澳门的政治发展,因为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只会使我们跌入另一个陷阱,即以同样的方式忽视微观政治分析框架自身在解释力方面所具有的缺陷。因此,我们在这里指出宏观向微观框架的转向,主要的目的便在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在澳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能打通宏观政治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微观政治分析框架,也就是既从宏观的角度强调中葡两国及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澳门政治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同时也从微观的角度关注澳门的政治行动者根据他们的知识所做出的策略选择与确定的目标取向对于澳门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观制约性。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首先需要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意识,而且更需要我们进入澳门的生活实践之中,并经由具体的澳门研究活动而对它做出回答。
(本文原是作者为《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所作的序,发表时略有删节——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