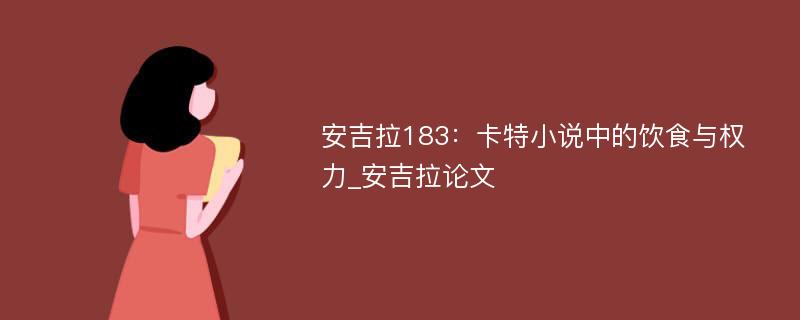
安吉拉#183;卡特小说中的吃与权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特论文,权力论文,安吉拉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是当代英国文坛的一颗璀璨之星。阅读卡特的作品总有一种让人不安的感觉,这部分是因为卡特“总是在反叛‘高雅品味的暴政’(tyranny of good taste)”(Lee 316)。作为道德色情文学(moral pornography)的拥护者,以及敢于贬低莎士比亚的文化异端,卡特激怒了很多人。尽管如此,这丝毫无损于卡特在西方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目前国内外对卡特作品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视角和手法也日益多元化,但少有学者评论卡特对吃与权力关系的描述,尽管这是她小说中被反复论及的母题。考虑到食物与吃在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类的卡特作品中所占据的重要作用,这种评论的盲点是违反直觉的,也是值得评论界重视的。与食物相关的议题下有一个潜文本,食物不仅给身体提供给养,而且女性什么时候吃、吃什么、怎么吃、跟谁一起吃等问题本质上与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信念与哲学紧密相连。并且卡特曾是一个长期的厌食症患者,鉴于她早年经历中与食物的复杂纠葛关系,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食物情结就更加值得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卡特曾援引法国人类主义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生的与熟的》(The Raw and the Cooked,1981)中的观点来为她的一本烹饪评论书《被删除的感叹词》(Expletives Deleted,1992)题词。她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认为,一种文化可以通过它的食物神话与食物隐喻来加以理解,饮食提供了通往社会最深层的无意识领域的途径。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生物性,而在于其象征性,它对人的自我认同非常关键。卡特认为吃象征了权力的编码形式,女性的饮食模式与父权行为有紧密的关系,食物与吃已经成为性别权力斗争的场所(Cline 1-3)。本文将透过食物与吃的多棱镜来审视卡特作品中性别与权力的运作机制,分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来分析其小说中对吃与权力关系的不同认识及再现,从而揭示出卡特女性主义思想的转变与提升过程。 一、吃与被吃:二元对立的角色关系 在卡特的早期小说中,吃意味着权力,隐含着权力斗争,体现着二元对立的角色关系:即男性与女性,猎食者与被猎食者,消费者与被消费者。卡特在论文集《萨德式女人:文化历史批评练笔》(The Sadeian Woman: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1979)中清楚地写道:“萨德说,强者虐待、剥削弱者,并使弱者食物化(meatify the weak)。他们必须也意在吞食他们的猎物。不管怎么样,人类的原初状态不能被改变,那就是吃与被吃”(140)。作为一种沉默的表达方式,吃的行为可以让隐性的东西显性化,并且暴露出父权社会试图掩盖的权力机制以及无形中施加在女性身体上的身体政治。 卡特无疑了解食物与食欲在二元对立的性别角色关系中所体现的重要作用。这个从小因自卑而节食甚至得了厌食症的女人,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与食物的纠葛关系出发,写了不少关于“食物主义”(foodism)和“食物崇拜”(food fetishes)的新闻评论,收录在《快手快脚:新闻与写作》(Shaking a Leg:Journalism and Writings)一书中。卡特在青春期后期得了厌食症,她认为自己“从婴儿时期就很肥胖……认为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男人会被这样的胖安吉所吸引”(Shaking 57-8),在某一时期她甚至把自己饿到35公斤。这个细节在卡特的早期小说《魔幻玩具铺》(The Magic Toyshop,1967)中有生动的再现:15岁的女主人公梅拉尼(Melanie)“害怕吃太多的面包布丁会发胖,会没人爱她,她会到死都是处女。她经常汗水淋淋地在同一个噩梦中惊醒,她梦到一个庞大的梅拉尼,趴在面包布丁上就像一具泡肿的浮尸”(4)。34岁那年,卡特最终这样自嘲地写道,“我曾有十年没有吃面包,正是那段时间让我习惯自己骨瘦如柴;我现在已经有17年没有碰过白糖、甜腻的蛋糕或者那样的东西”(Shaking 57)。显然,卡特与食物的关系占据了她年轻时代的重要部分。然而,让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卡特坚定不移地认为女性应该接受她们是自己受压迫的合谋犯的事实,而她自己却饱受这样一种本质上是文化造就的女性气质的疾病的折磨。卡特的评论者莎拉·斯基茨(Sarah Sceats)指出,“食欲就跟性欲一样由文化建构,受外界制约和势力的影响”(102)。确实,这不是巧合,历史上食欲与饮食在建构女性气质的模式上起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自19世纪开始,关于女性吃什么、吃多少的兴趣已经反映出对于女性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一种焦虑。卡特在1974年指出,“厌食症显然将成为70年代流行的疾病之一”(Shaking 56)。正如歇斯底里症之于早期的妇女,对于20世纪晚期的妇女来说,神经性厌食症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性疾病:两者都以病态的方式体现了广为接受的文化成见。① 卡特的早期小说常展示食欲缺乏、瘦骨嶙峋、虚弱无力的女性形象,受男权社会压迫,而男性则展现野兽般的食欲,他们对权力的欲望隐喻性地体现在吃的能力中。在《魔幻玩具铺》中,梅拉尼在父母死后被送去与菲利普舅舅一起居住,她发现他是一个可怕而又贪婪的人物,专制地统治着这个房子。梅拉尼把他描绘成嗜血的蓝胡子以及渴望权力的萨坦。菲利普舅舅有着巨大的食欲,而他顺从又胆小的妻子玛格丽特仅有“熊宝宝的饭量”(77)。他们之间的权力分配不仅反映在食物的分配上,也反映在体型的差异上。菲利普舅舅是一个体型硕大的男人,他的重量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他的权威使人窒息,而玛格丽特是如此之瘦以至于她看起来像“饥谨圣母的肖像”(119)。面对男性对社会空间的决定性占领,消瘦带有脆弱和缺乏权力的内涵。菲利普舅舅送给妻子一个恐怖的项圈作为结婚礼物,不容置疑地让她每周日下午茶时佩戴。戴上紧箍咒般项圈的玛格丽特不得不高昂着头,呈现出亚述王后的傲慢,但她的眼神里没有自豪,只有悲伤和忧虑。项圈直接抑制了玛格丽特的进食能力,而她的痛苦似乎更刺激了丈夫的食欲: 戴着项圈,玛格丽特舅妈的进食就变得非常困难。周日下午茶是固定的。总是虾、面包和黄油,一碗芥菜和水芹,还有一个富有营养的明亮的金色松蛋糕,蛋糕是早晨就放进炉内和星期日烧烤一起烘焙的,所以它还带有一丝肉脂的焦香味。餐桌上堆满了虾须壳,松蛋糕已经被吞食了,只余下一点残渣——但她能做的,只是疼痛地吸一口寡淡的茶,玩耍般挑起几根芥菜和水芹,尽管是她做出如此丰盛的美食的。菲利普舅舅敲开了足有一个营的粉红虾的壳,不紧不慢地吃掉了它们,吞掉了抹了半磅奶油的一整条面包,然后又随心所欲地吃光了最大的一份松蛋糕,他注视着她,一种面无表情的满意,很显然是从她的不适里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快感,或许他甚至发现她的这个样子促进了他的食欲。(119) 女性的食欲——更准确地说是食欲缺乏——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的关键所指。菲利普舅舅正是着迷于妻子身上这种女性气质所指,并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与快感。几乎卡特所有早期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都如菲利普舅舅那样展示了男性欲望的吃人(cannibalistic)本质,强大的男性不仅展现巨大的食欲,而且弱肉强食,而女性总是“被吃”的对象,体现着“吃与被吃”的二元对立。卡特对男性饕餮食欲的含蓄控诉体现出她对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蔑视。卡特最后走出了厌食症的阴影,认为那段饱受厌食症困扰的日子是一种“由自恋引起的长期尝试的自杀……一种英雄主义的疯狂展示,却充满讽刺性地凸显了她与之斗争的无能”(Shaking 57)。卡特把自己的恢复归功于她女性主义意识的激进化:“我不会说是妇女解放运动给我提供了最后的治疗力量来对付我残留的厌食症,但那确实有帮助”(Shaking 57)。可见,食物必须放置在政治领域,并把女性与食物充满纠葛的联系解读为权力被剥夺的产物以及对父权制的抗议。 二、角色的易变性:超越二元对立 随着卡特女性主义思想的日益提升,她在中期小说《新夏娃受难记》(The Passion of New Eve,1977)中避开了吃与被吃的简单角色颠覆,而是超越了二元对立,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彰显了卡特对吃与权力关系的重新认识。 小说《新夏娃受难记》刚开始时似乎延续了卡特早期小说的套路,女性气质依旧与清瘦且食欲缺乏联系在一起。但不同的是,生理性别(sex)却不必然与女性气质所对应的社会性别(gender)挂钩,因为小说中作为女性气质缩影的主人公特丽思岱莎事实上是一个异装癖者,即生理性别是男性,社会性别是女性。特丽思岱莎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她如死尸般苍白,消瘦憔悴的肉体像幽灵。叙述者想知道,“特丽思岱莎吃些什么?位于地下室的厨房不比游艇的厨房大,在那里,他们只找到许多罐可以加水变成液体食物的某种粉末,一玻璃瓶又一玻璃瓶的维他命丸”(130)。正如特丽思岱莎的社会性别,她的食欲也是文化造就的,也就是说,女性食欲的压抑绝不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她的食欲缺乏是模式化的女性气质的产物。虽然特丽思岱莎在生理上是男性,但她对女性气质的表演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这有效地使她成为了一个女人,体现出女性气质的本质内涵。伊弗林反问道:“真正的女人怎可能跟你一样有女人味?”(128-29)母神也拒绝为特丽思岱莎做变性手术,因为她已经太像个女人。根据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理论,身份不存在一个预先设定的生物本质,生理性别也是被建构的,所谓性别本质是靠人不断重复某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而产生的: 生理性别范畴先于所有对性差异的范畴化,它本身就是通过某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性模式所建构的。把生理性别建构为分立、二元这样的生产手段,通过假定“生理性别”是性经验、行为和欲望的“原因”,而隐藏了这个生产机制本身的策略目的。(32)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区分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性别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而卡特试图超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她认为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具有易变性的。女性气质是由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社会势力所建构,与生物性别无涉。卡特关注并揭示出女性气质的文化生成属性,而不是其自然属性,这在她35年创作生涯中的小说与非小说中有清晰的再现。 卡特在《新夏娃受难记》中旨在塑造女性气质的新形象——正如小说标题中的“新夏娃”所示。这个重塑过程不仅涉及对基督教创世神话的修正,也包括对该神话中的女性消费态度的重新评估。自从夏娃给亚当吃了禁果,女性的食欲便被烙上危险和罪恶的印记。于是,在小说创作中,卡特把女性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节食行为表现为男权社会对女性施加的霸权话语的产物,并且卡特致力于冲破这种话语的牢笼,塑造一种颠覆性的新夏娃形象——变性人(transsexual)。“卡特通过母神作为阉割者将伊弗林变性为新夏娃,实现对阳具中心宇宙的阉割”(冯海青86)。在该小说标题中,卡特用“passion”这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字眼来形容夏娃:在暗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考验时,“passion”一词表明救赎可能诞生于受难;同时,在基督教概念中的“passion”一词包含痛苦与狂喜并置的双重含义——痛苦是因为耶稣的受难与死亡,狂喜是因为他的死保证了人类的救赎;卡特把夏娃因变性所经受的苦难以及灵魂的重生与耶稣相提并论,这表明了卡特意在消解二元对立的思想。② 伊夫林[伊弗林]由男性变成了女性,他的男性中心意识、霸权意识得到了有效地消解;特里丝特莎[特丽思岱莎]在心理上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女性,但她在生理上则是个男性,也就是说,两者身上的男性中心意识、女性中心意识均得到了消解。在社会意识上是个中性人。换言之,理想的两性关系并非是男女二元对立,而是超二元对立,即男女霸权话语均得到消解后两性完美的融合。(欧阳美和、徐崇亮76)因此,特丽思岱莎和夏娃都已超越了吃与被吃的二元对立,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她们既是消费者也是被消费者。小说中卡特匠心别具地描绘了这样一个细节:当她们被困于沙漠时,她们“把彼此的嘴当作水瓶吸吮,因为别无他物可饮”(Passion 149)。这里相互依存的关系取代了支配关系,营造了一种不再建立在否定基础上的滋养形式,指向了一种比以往更加复杂的、超越简单的二元主义的消费类型。该小说以重生和新的可能性结尾:夏娃航行在海上驶向“他处”(elsewhere)(205),一个游离于男性权力话语之外的乌托邦所在。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分析卡特小说中消费的性别模式时指出: 这是卡特的论断,如果一个女人要实现一种独立的而不是依赖性的存在,某种程度的虎性(tigerishness)是必须的;如果她们想避免——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下——成为肉。……但卡特没有把男人的本质限定为不可避免的猎食性,女性是他们“天生”的猎物。羊性与虎性可见于任一性别,甚至同一个体的不同时刻。(121)不同于其早期小说,卡特创作中期的小说不仅挑战了角色二元对立的属性,而且模糊了男性与女性、猎食者与被猎食者之间的界限,提供了整合与流通的可能。 三、女性食欲的狂欢:和谐的二元共生 在后期小说《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1984)中,卡特开始关注女性经由食物媒介获得的权力与快感,呈现了食物叙事中的食欲演示与女性狂欢的主题,象征了女性内在的对公共权力、独立自主和性满足的欲望。女性的象征地位从被消费的对象转为消费者,而且,主动的消费行为使卡特小说中的女性获得独立自主、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和驾驭男性社会的权力。当女性被认同为消费主体,消费的本质也就发生变化:消费成为一种愉悦而不是恐怖的体验,从中体现了卡特从聚焦于女性痛苦的女权主义转向强调女性快感的政治。 对食欲的嬉戏是卡特在创作后期对权力与欲望的复杂再现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她对食物与吃的描绘通常具有敏锐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讽刺意味。《马戏团之夜》中,卡特将长久以来压抑的食欲以及所有对吃的想象都投射在飞飞这个夸张的、颇具戏谑意味的新女性形象上,塑造了一个食欲惊人、自我放纵的享乐者。不同于卡特早期小说中食欲缺乏、沉默无语、瘦骨嶙峋的女性,飞飞胃口巨大,说话滔滔不绝,体型超常,光脚就有6.2英尺。她是拉伯雷式的女主人公,有《巨人传》中卡冈都亚那样的胃口。飞飞的食欲对其人物刻画起到关键作用: 她正以不输巨人卡冈都亚的狂热,对着这种最粗鄙土气的马车夫伙食大快朵颐,所以嘴巴塞得太满,没办法立刻还击。她狼吞虎咽,她拼命把食物填进肚子里,她把酱汁泼溅在自己身上,她吸吮刀子上的土豆泥;她有个与身材尺寸颇成比例的大喉咙,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餐桌礼仪。大开眼界的华尔斯,秉持其专业的温顺,坚持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她终于满足了巨大无比的胃口,她用袖子擦擦嘴唇,打了一个饱嗝。她又投给他一个怪异的眼神,仿佛心里有一半希望自己这副贪婪的吃相会把他逼走。(28) 在卡特的创作中,食物与吃的行为常常伴随着性与权力的斗争,而食欲与性欲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流通,两者有着深刻而又含混的关联。在一篇写于1985年的书评中,卡特甚至有意混淆食欲与性欲这两种欲望(Noovs' Hoovs 22-23)。如果食物是欲望的焦点,那么吃就是一种情色行为。当飞飞啃着面包而眼睛好色地游移在华尔斯身上时,他把这个举动视为性挑逗而不具有虐待狂般的危险:“华尔斯感到饥饿的眼神在他身上,这在他看来好像她的牙齿一点也没有伤害地咬在他的肌肉上”(204)。斯基茨指出,在卡特的小说中,“食物的准备或吃的行为可能涉及性唤起、性满足、自恋的自我观照、堕落、施虐受虐狂等等”(25)。正如性动力(sexual dynamic)在经验上可能类似满足饥饿的欲望,《马戏团之夜》中的性动力可以被编码为一种食物性的消费。飞飞公然不顾及女性的合宜与得体,她期望自己对食欲的演示,就像她作为空中超人的马戏演出,会受到观者的注目。飞飞希望所有围观她的人知道她在满足她的巨大食欲时的快感,而她攻击食物时所体现的动物般的快感则象征了她的性欲。华尔斯对飞飞的巨大食欲印象深刻,他甚至觉得飞飞很性感:“一种有如地震般的、满含情欲的不安撼动了他”(76)。华尔斯对飞飞的欣赏与爱慕颠覆了传统男性对女性美的刻板印象。 飞飞肥硕怪诞的身体与厌食症患者骨瘦如柴的身体形成强烈的反差,也与理想的具有典型女性气质的苗条身体相去甚远。她是一切“可悲的女人”、柔弱的以及病态的维多利亚理想女性模式的对立面,有意识地挑战了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气质的界定与认知。飞飞的超常体型不仅反映出她的巨大食欲,也体现了女性自足的狂欢。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狂欢是颠覆秩序的有力手段,并且狂欢常与饮食联系在一起,它消除了差异。与巴赫金一样,卡特也认为吃是跨越和转化文化秩序的关键力量。尽管飞飞贪吃,但不同于卡特早期小说中食欲巨大的男性,她并不野蛮,也并不具有攻击性。飞飞矛盾性地既虚荣又仁慈,不仅贪吃而且喂养别人,不仅消费而且生产,就如巴赫金提到《堂吉诃德》中桑丘的人物性格,“他的食欲与饥渴传递了一种强有力的狂欢精神。他对富足与财富的热爱体现出一点也不是私人的、自我的、疏离的特征”(22)。这个特征也概括了飞飞迥异于卡特早期小说中男性的食欲精髓:她绝不否认自己的食欲,但不会以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巨大的食欲,她拯救而不是毁灭他人,她慷慨帮助弱者,包括女性与男性,如受伤挨饿的迷娘(Mignon)和处于困境中的华尔斯。飞飞经由吃而获取的权力是仁慈的而不是邪恶的、攻击性的。在卡特后期小说中,权力不再是负面的、压制性的;相反,卡特采用福柯谱系的权力观,即权力是潜在性的正面的、具有生产性的。③可见卡特超越了早期小说中两性对立、对抗的局面,走向了一个女性狂欢的世界,体现出卡特重构和谐两性关系的女性主义目标。 卡特在小说中展示了吃是权力关系可以被研究并加以重新配置的一个场所,她小说中吃的主题因卡特观念的转变而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早期小说中,人物处于一种“吃或被吃”的辩证关系,女性总是“被吃”的目标,体现了男权的压迫性;在中期作品中,人物超越了“吃或被吃”的二元对立,体现了角色的易变性;在后期文本中,吃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潜在的重要途径以获取权力和快感。最终,卡特的作品变成了对权力的正面颂扬,而不再是建立在统治与从属的地位基础之上。尽管食物奴役了女性,成为了她们的敌人,但是“食物具有象征性再现和扮演有意义的角色的潜力”(Chernin 114)。这种与食物的新型关系是一种转变的社会象征秩序的产物。 注释: ①对于神经性厌食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参见Susan Borde,"Anorexia Nervosa:Psychopathology 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ulture." ②故本文把小说标题中的“Passion”一词译为“受难”,而不同于一般翻译的“激情”,如严韵的译本《新夏娃的激情》。 ③有学者指出卡特对福柯的权力概念非常熟悉,卡特在20世纪70年代阅读福柯,而且卡特也熟读文学、文化和政治理论。参见Lorna Sage,ed.Flesh and Mirror:Essays on the Art of Angela Carter; Aidan Day,Angela Carter:The Rationed Class,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