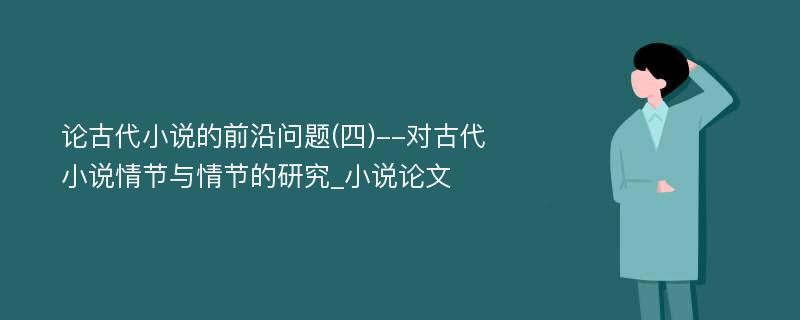
古代小说前沿问题丛谈(之四)——古代小说的情节与情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丛谈论文,情节论文,古代论文,小说论文,之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
2007年开始,我们在《北京大学学报》开辟了《古代小说前沿问题丛谈》的专栏,轮流主持,现在已是第四回合了。从一开始,我们就设定了一个思路,希望借此清理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问题,回顾已往研究的得失,探寻今后发展的思路。目前已讨论的有文体、语言、人物等,这些问题都与古代小说研究的全局有关,这次讨论的情节问题也是小说创作与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
小说研究者们对情节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没有人否认情节对于小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分析与评价时,情节又往往让位于主题、人物、心理等等小说的其他构成诸要素。最显著的例子是,上个世纪初,西方小说理论刚刚传入中国时,就有人提出了“小说之美,在于意义”的观点(成之《小说丛话》,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2页),而中国古代小说则因所谓片面重视故事情节,忽视人物、环境等屡受非议。实际上,很多时候,研究者并没有特别在意“情节”的基本内涵;也没有在意“情节”是否重要,其实更多地取决于如何设置、展开情节。鹏飞先生的文章力图在这方面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
情节问题的复杂性或理论意义不限于某一特定的文本,对于有着漫长历史的中国古代小说来说,情节的继承与衍变既可能是某一具体作品不断改进、臻于完善的过程,也可能是这一作品在广泛传播中迎合市场需要或适应接受者心理的一种变通性调整,当然,还可能是小说艺术整体发展成熟的表现。建国先生的文章和拙作就是从小说史的全局着眼,讨论有关情节的衍变与类型化问题的。
我们相信,情节研究如果不只限于对故事起承转合的描述,也不被当下叙事学研究有关叙述方式、角度等的分析所替代,而是真正结合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及其历史的实际,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刘勇强
“情节”一语乃英文词“plot”之转译,本是一个舶来语。但这个术语的确切含义究竟为何,在西方叙事学中也是一笔糊涂账,其含义随着时代思潮的演变也在不断地变化,而难以定于一尊。因此,大致了解其含义的变迁及其与小说研究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廓清“情节”这一批评术语与批评角度长期运用所造成的迷雾,从而给历史悠久、渊源深厚的小说情节研究带来一些“松动”。
关于“情节”一词,最权威的定义出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该书指出“情节”是“对行动的模仿”与“对事件的安排”。所谓“安排”指的是作者对故事事件本身的构造。而“事件”应是一个完整的,具备开端、发展、结局的统一体,事件组成要素之间应具备因果关系,其发展应符合或然律(可能性)或必然律。这一经典的“情节”定义对后来西方叙事学的“情节”观发生了很深影响。比如,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爱·摩·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专门对“故事”和“情节”加以区分,指出“故事”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事情,而“情节”虽然也是叙述事情,不过重点是放在因果关系上。这一区分原则的确立显然受到亚里斯多德的启示(参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二章“叙述学的情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以及《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小说面面观》第五节“情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福斯特的这一区分对后来的情节研究发生过重大影响,但这一区分方法也备受非议,比如里蒙-凯南即认为时间顺序也可以含蓄地表示出因果关系,并获得自己明确的地位;她还顺带指出因果关系这一概念有时会包含不同的含义,会导致不同的理解(参见张锦清等译《叙事虚构作品》第二章第四节“结合的原则”,三联书店1989年版)。相对于福斯特的上述区分,俄国形式主义者则把“故事”视为作品所叙述的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全部事件,“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进行的艺术处理或形式上的加工,尤指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欧美结构主义叙述学则认为叙事作品由“故事”和“话语”两部分构成:“故事”乃作品的内容,“话语”即表达方式或叙述内容的手法,并把形式主义所谓“情节”归入“话语”层次,是对故事事件的重新组合、重新安排,“每一种组合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情节,而很多不同的情节可源于同一故事”。而从研究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结构主义叙述学家以及某些俄国形式主义者所研究的“情节”并非处于“话语”这一层次,而是处于“故事”这一层次。但有一些极端的形式主义者(如什克洛夫斯基)则仅注重话语技巧而排斥故事事件,这种过于注重形式的情节观无论相对于传统情节研究还是现代情节研究都是一种偏离,在分析以故事事件为中心的传统小说时极易导致偏差。因此,有中国学者提出:最好把“情节”保留在故事事件这一层次,把各种形式技巧都看作在“话语”这一层次上对故事事件进行的加工处理。如果一部作品话语技巧特别重要而事件并不重要,就可集中研究其话语技巧,但没有必要称之为“情节”(参见前揭申丹书同一章节)。
可以看到,在西方叙事学中实际上出现过“故事”、“情节”与“话语”这三个互相关联的术语,这些术语都与小说叙事有密切关系:“故事”强调时间性,指按照自然时序所发生并被讲述的事件,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不可能存在只包含纯粹时间性的事件,时间性总是难免要包含因果关系,即使我们只用“然后”、“以后”之类的连接词来概括小说的事件,也无法完全消除其中所隐含的因果关系。因此,这一术语与强调故事要素之间因果联系的“情节”一词确实难以被截然区分,所以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我们便往往会看到将这两个术语混为一谈的情况。在笔者看来,我们自然还是可以根据小说所包含事件因果性的强弱或者作者着重所表达的意图来决定究竟使用哪一术语,以及决定应该从哪一角度进行讨论。而“话语”这一包含小说形式技巧研究意识的术语在西方则出现得比较晚,似乎跟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关系不大。但这一研究角度恰恰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首先,光是从故事或者情节角度去研究小说,其实深入的余地都不是很大,如果要涉及小说的叙事艺术,最终都会要落实到形式技巧的层面。以往的“情节”研究其实往往会要归结到形式技巧的层面,只不过我们仍然打着“情节”的旗号罢了。其次,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实践来看,形式技巧乃是被特别加以重视的,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金瓶梅》、《红楼梦》这一类并非以所谓“情节”取胜的作品,而情节性比较强的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之类,也包含复杂精妙的形式技巧。中国古代的评点家(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所特别关注的也正是这些形式技巧(可参看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不过,因为“话语”一词近年被过于滥用,为避免不必要的混乱以及古代小说研究界对这类西方术语的心理排斥,可以直接运用“叙事形式”或“形式技巧”这样的词来替代“话语”,但一定不要继续将这一研究归入情节层面,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技巧大都具备纯粹的形式性,跟时间性、因果性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主要是小说结构或空间安排的艺术。
其次,西方关于“情节”与“故事”以及小说的关系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因果关系对于情节的重要性虽然被强调,但他并没有把缺乏因果关系的事件排除到情节范畴之外。福斯特则特别重视因果关系对于情节构成的意义,将因果关系之有无视为“情节”与“故事”的根本差异。里蒙-凯南则认为时间顺序足以成为构造故事或者小说的基本条件,故事或者小说可以不必包含明确的因果关系,有的小说作者甚至避免故事中出现明确的因果表达。有的结构主义者(如查特曼)则指出“一个叙事作品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没有情节”,并因此区分出“结局性情节”和“展示性情节”。前者主要指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它的特点是有一个以结局为目的的基于因果关系之上的发展过程;后者则主要指“情节淡化”或者“无情节”的现代叙事作品的“情节”。如果涉及情节与小说的关系,则爱·缪尔的《小说结构》从这一角度将小说大致分为人物小说、情节小说、戏剧性小说等类型,并指出:一般而言,人物小说的情节比较散漫、随意,情节为表现人物而设;情节小说则主要表现生动有力的事件,人物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是附带的,而且总是有助于情节的发展,人物常常是按照情节的需要而具备哪些性格以及具备何种深度的性格;戏剧性小说则是人物与情节结合最为紧密的类型,人物就是情节,情节就是人物,情节的发展过程既出于自然,又合乎发展的逻辑性。但此后又有学者提出可以按照作品主人公的主要演变区分出“有关行动的情节”、“有关性格的情节”、“有关思想的情节”等三种情节类型(以上分别参见前揭申丹书以及《叙事虚构作品》、《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小说结构》)。但在笔者看来,以上这些类别并不足以全部涵括西方以及中国古代小说情节的各类复杂情况,比如《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无论归入哪一类都不合适,因为其包含的乃是人生、命运乃至生活的全部,自然也包括情节的各种类型,因此它是涵括情节本身而不是被情节所涵括的。这一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能多论。
从以上所述,我们大概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西方叙事学所谓的“情节”原本是以具备因果关系的故事为其主要内涵的。但在后来又发展出极端形式化的情节观念,视“情节”为纯粹叙事手法与形式技巧,但对于这一观念,中、西方学者都有人加以反对,认为“情节”还是应该局限于故事层面。而对于作为“情节”主要特征的因果关系,也有人提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至于“情节”与故事、小说之关系,则有人认为故事、小说可以包含情节,也可以不包含或者不明确表达具备因果关系的情节。如果根据“情节”来对小说进行分类,则可以分出多种类型。这些情况都说明:首先,“情节”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复杂概念;其次,小说的情节具备丰富的形态;第三,“情节”或许并非小说的必要因素,也未必是衡量小说的恒定标准;第四,作为“情节”基本内涵的因果关系也具备复杂性与历史性。因此,当我们运用这一概念来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时,必须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概念的上述特性,并根据中国古代小说的具体特点来灵活地加以运用。
而除此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情况则在于:“情节”这一概念完全是西方叙事学的术语,自从进入汉语学术语境之后,成为极为重要、运用极其频繁的批评手段,这在无形中导致中国的小说研究者都是用西方的“情节”标准在衡量中国小说的情节,因此我们便会看到有人提出中国小说(以及小说评点)不如西方小说那么重视情节、令人感觉不到情节的因果特性、感觉不到时间在故事组织中的作用这类略显偏颇的看法。当然,这一说法并非完全不合理,但是其立论基点则主要是西方小说的情节理论。而如果要对中、西方小说进行真正有效的比较,或者说对中国小说的叙事特点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至少需要搞清楚这样一些问题:西方的“情节”这一术语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有没有大致对应的概念?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一概念所反映的中国小说的“情节”(暂且借用这个词语)观念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中国小说如何组织故事、如何表达因果关系?等等。而根据笔者浅陋的了解,似乎并未看到有人对以上问题进行透彻论述。但事实上,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便会立刻想到中国古代小说以及小说批评中原本也有一些用以描述小说所叙述的事件以及叙述手法的用语:比如关目、筋节、事理、筋、事等(笔者注意到,日语正是用“筋”这个汉字来对应英文的“plot”,这一对应是否完全合适暂且不论)。在此仅对“关目”一词略作讨论:这个词语最初很可能来自江南某些地区的方言,后来成为元杂剧的用语。有学者认为其本意为关键、眼目,即紧要部分之意,最初指只记曲文的剧本,后来则指剧作家在完整剧情的基础上,基于传达剧情与表演效果二者的衡量而决定的剧本内容。总之,这个词既包括戏剧情节,又包括表演方面的设计(参见许子汉《戏曲“关目”义涵之探讨》,载于《东华人文学报》第2期)。到明清时代的小说以及小说批点中,这一原本用于戏曲理论的术语的出现频率就变得很高了,比如《水浒传》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云:“因此权记下这两打祝家庄的话头,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的人乘机会的话,下来接着关目。”第一百一十四回“宁海军宋江吊孝涌金门张顺归神”云:“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演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云:“只因一个富翁,也犯着无儿的病症,岂知也系有儿,被人藏过。后来一旦识认,喜出非常,关着许多骨肉亲疏的关目在里头,听小子从容的表白出来。”另外,《续西游记》第七回总批中也有“龙马衔经出池,关目最妙”之语(此处承井玉贵兄赐告若干资料出处,谨致谢忱)。这些地方所见“关目”一词,可以肯定包含故事或事件之类含义,有的也类似于包含因果关系之“情节”。如果古代小说对“关目”一词的运用在含义上大致接近戏曲的“关目”,那么其至少还应包括这样一些意思:既指重要故事段落,又指具备穿插联络功能的重要事件(参见《汉语大词典》之“关目”词条)。虽然对这一术语在古代小说批评中的精确含义还有待深入研究,但还是可以看出其跟西方叙事学的“情节”这一术语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果再联系其他几个术语如“筋”、“筋节”等一并考虑的话,则不妨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原本也有一套描述故事事件以及叙事手法的专门用语,可以跟西方的“情节”概念大致对应,但又可能体现出与之不太一样的“情节”观念,比如:注重事件的结构功能、关键段落的重要意义等,而同时又并不忽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对因果关系的看法可能也与西方不太一样。总之,“关目”这样的术语可能具备比“情节”更为宽泛的含义,如果对其意义能够加以比较明确的界定,仍然可以运用于古代小说的批评实践。不过,在此笔者还是不得不谨慎地借用“情节”这一术语来继续进行古代小说“情节”问题的讨论。
既然借用这一术语,就无法忽视其所包含的“因果关系”这一最重要的因素。而所谓“因果关系”主要涉及人们对自然与人事发展演变动因的认识与体验。这类认识与体验在叙事文学中如何被表现,自然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孕育“情节”这一术语的古希腊史诗和戏剧中,人类的悲喜剧往往由命运或者天意所决定,在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类似情况。但与西方文学不太相同的是,中国叙事文学最早成熟于史传叙事,史传叙事崇尚实录,对人事变迁尽量加以如实记载,而不大进行人为的解释。如果要作解释,也同样是立足于天意或者命数这样的角度,这从《左传》中大量的“占梦”与“梦验”类记载可以获得深刻印象:“梦”暗示着天意或者命运,蕴含着推动人事演变的动因。这种十分简朴的情节包含着当时的人对历史变迁的认识。这种以天命来解释人事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曾发展到十分细致的程度,举凡人的生死、婚恋、饮啄,无不出于命数,人力完全无法与之相抗。唐代传奇便十分热衷于表现此类情节和主题,比如著名的《定婚店》(见《太平广记》卷159“定数十四”),讲述杜陵韦固从月下老人处得知自己未来的妻子乃是一卖菜老妪的三岁女儿,便命仆人去行刺,仆人惊慌之中只刺中幼女眉心。十四年之后,韦固娶了自己的上司郡守之侄女,此女正是当年卖菜老妪之养女。夫妻尽知前因,更加恩爱。小说讲述韦固不听月下老人劝阻,决意要反抗自己的命运,结果发现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乃“知阴骘之定,不可变也”。此类情节最为奇特的还是表现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观念,比如唐代的《逸史》讲述某官吏被预言吃不上自己家正要用来宴请客人的鲙,此官吏与占卜者为此还打了赌,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官吏果然没有吃上自己家的鲙(见《太平广记》卷153“定数八”之“李公”)。这类情节所包含的观念与《左传》乃是一脉相承的,但其叙述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左传》所表现的天意乃是暗中起作用,没有人会有意进行对抗,所以其中事件所包含的因与果之间没有太多的悬念,也没有什么过渡因素。但唐传奇的这类作品则使命运的存在以及对命运的反抗都明朗化,主要展示人类如何反抗这一命运以及反抗如何失败,也就是说,在此“因”与“果”都已经确定无疑,需要讲述的乃是这一“因”如何具体地导致那个“果”。这一过程被展示得越具体、越曲折,就越充满悬念,而不是一般所猜想的:既然因果关系都已经被揭示,就不会再有悬念了。此外,在这类小说中,除了天意本身这个“因”与其所注定的“果”之外,其实也包含着人事内部的因果关系:可见天意终究还是要假手于人事,才能实现其目的(但小说家在“天命”与“人事”之间,更偏重于“天命”)。而从主题来看,这一特殊的情节类型除了表现命定观念之外,还表达出独特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对于命运的体验),这一点也值得反复体会,不应被忽略。这一表现命定观念的情节模式在后来的白话小说中也被反复运用,比如宋元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可参见《警世通言》卷十三)开头即通过算卦先生断言孙押司“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点子时当死”造成极为强烈的悬念,然后借助天意与人事的双手去推动结果的实现,表现出十分巧妙奇特的意味。这样的情节设计对于吸引听众或读者显然是非常有效的。
与西方文学的命运观念颇为异趣的一点还在于:中国古代的命数观到汉魏以后又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相结合。此二者的结合使天命观与因果观念都被大大地强化了,而在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中,人类自身的道德因素也被加以强调。这样一种复合的因果观念也很快进入小说的情节结构,比如唐传奇有很多作品表现前世恩仇、今生相报的内容,并逐步演变成新的情节类型。运用这一情节类型的古代小说可谓不胜枚举,仅就长篇小说而言,便至少可以举出《水浒传》、《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姑妄言》、《红楼梦》等重要作品。这些作品的开头、结尾互相呼应,成为一个外加的因果框架,不仅仅表现一种文化观念,更成为小说的结构技巧。对此已有学者专门予以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请参看刘勇强《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刊于《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
关于小说情节的有无或者情节性强弱的不同看法在前述对西方叙事学的讨论中也已涉及。一般认为,情节性越强的小说越吸引人,但这一想法包含着以情节作为衡量标准的立场,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没有什么情节性的小说就不吸引人或者没有什么价值。殊不知,过于紧凑、集中的情节其实反倒是不自然的、更违反生活真实的。其次,没有情节的小说还可以具备故事性,如果故事性强的话,也可以吸引人。其实,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的小说倒是有大量不具备明显情节性的“故事”,比如大量志怪传奇类作品即属此类:唐传奇的很多作品就是表现书生在荒野遇到精怪,与精怪清谈、吟诗唱和,或者一夜绸缪,天明精怪恢复原形,书生失魂落魄而去。这样的故事被人们饶有兴致地不断重复,但其实并不包含什么因果关系或者说情节之类。在这类故事中,实际上包含着最令人困惑的成分:精怪的变形。好端端的动植物竟然变成人,跟人类称兄道弟或者卿卿我我,这绝不会有任何人经历过,但这样的成分进入小说之后,却没有原因能加以解释,即使有人加以解释,也不可能有人相信。但读者照样会去兴致勃勃地阅读这类故事,可见对于原因的追寻并不是读小说或听故事的唯一动力。在笔者看来,表现没有强烈情节的故事,并且将其表现得有趣味、有情致、自然而然,或许是更高级的叙事能力。毕竟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紧张、激烈、集中的事件。或许有人会秉承某些艺术原则,认为紧张激烈的情节来自于对生活事件的提炼和浓缩,是高于生活的,这对于时间、篇幅有限的创作或者叙述而言,自然是必要的选择。但过分执着于这些原则也会让我们忽略:精确地描绘生活事件的自然状态,或者自然地表现生活事件的本真面目,乃是一种更难的艺术。而这种艺术,恰恰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直所具备的重要能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比如,在喜欢表现各类奇闻逸事的唐传奇里,也有不少表现普通日常生活场景的作品,至于描绘生活琐事、没有任何情节性的故事段落就更常见了。比如《奚陟》一文(见《太平广记》卷277“梦二”,注出《逸史》):讲述梦验的故事,但描述的却主要是日常生活中官吏与同僚喝茶的场景,极其琐细,却反而从这琐细之中显出奇异。又比如温庭筠的《曹朗》(见《太平广记》卷366“妖怪八”)一文,本是表现妖怪扰人的异事,但开头却用很多文字描写唐代官吏秩满移居、新居的布局以及屋内的陈设。再比如《李宗回》一文写到县令家七岁的小女儿嚷嚷着要“勾当家事”,县令着恼,便让小姑娘安排正旦饭食。结果小姑娘不知道该煮五种馄饨中哪一种招待客人,仍要向父亲请示(《太平广记》卷153“定数八”)。这样的生活琐事描写在唐、宋文言小说中屡见不鲜,但并未能如情节一样被当作小说的相对独立因素被注意。到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或话本集如《金瓶梅》、《欢喜冤家》、《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红楼梦》、《鼓掌绝尘》等作品中,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才真正成为小说最重要的成分,而所谓的情节就溶化在这些细节之中,变得很不明显,正跟生活的本然状态相似。这样就让情节变成复杂、混沌的状态,人们对其中故事情节或者因果关系的理解也获得多样性,带来小说艺术的多元与民主,从而避免明显情节所造成的主观和独断。
在世界范围内,小说或者叙事性文学作品其实都存在情节与非情节、现实情节与虚幻情节的结合形态(当然,这类概念的运用只能局限于相对的意义,进行这些区分只是为了讨论的便利,而不应成为教条与标准)。情节与非情节的问题在此暂且不作讨论。现实情节与虚幻情节两类形态的结合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极为普遍,但学界对其表现技巧、艺术原理以及艺术价值的探讨似乎并不深入(已有的有益的研究可以参看钱锺书《管锥编》、刘勇强《幻想的魅力》、鲁德才《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以及一些关于《聊斋志异》的研究论著)。首先,具备幻想性情节的小说的现实合理性应该如何去解释?那些狐鬼花妖、神仙异人的千变万化,终究还是具备现实的心理基础或者文化动因的,这些原因从小说内部大概无法获得充分透彻的解释,而必须从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去进行探索。其次,幻想情节与现实情节的结合如何获得内在的连续性、完整性与逻辑性?《聊斋志异》的人物频频地“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语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却并不令人觉得情节断裂、结构支离,其奥妙何在?《西游记》描写神魔妖怪的变化并不让人觉得牵强生硬,而《封神演义》的神魔变化却令人觉得突兀、孤立、不自然,其原因又何在?再次,幻想性情节表达功能的历史演变如何?比如某人梦入异界偷看人类命运簿册的情节因素在唐代传奇中就出现了,在《红楼梦》中也仍然在运用,其含义和功能已经发生很大改变,至少已从比较单纯的民间信仰变成重要的文学结构手段。此外,幻想性情节在具体表现手法上有无特殊的原则?等等。这些问题也许看上去并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中国古代小说中这类故事情节实在太多了,长期以来,人们司空见惯,已经当成“现实”而接受了。但或许,中国古典叙事学的很多重要奥秘就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
小说的情节研究还涉及太多其他的问题,比如情节与主题的关系、情节与人物的关系、情节与偶然性或巧合的关系等等,这些在传统情节研究中都曾被广泛讨论过。但是,相对于西方传统叙事学对于情节问题的众多经典研究成果而言,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理论框架的束缚,也没有提出有影响力的重要情节理论。笔者以为,要改变这一状况,不妨尝试着先把现成的情节理论甚至术语搁置起来,采取一种还原的思路,让我们直接面对中国古代小说活生生的实践,去认真地想一想中国古人对于故事或者事件的固有处理方式以及固有观念,这时候,一种具备某些独特性的“情节”理论也许就会逐渐浮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