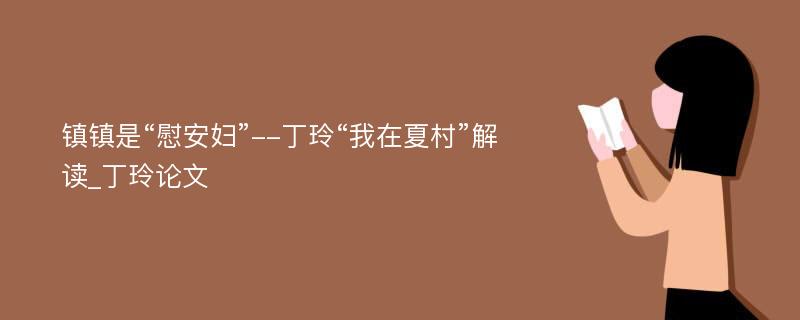
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个论文,我在论文,慰安妇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短篇小说中的名篇。研究者在论及这篇小说的时候,大都把主人公——十八岁的农村少女贞贞称作(看作)“军妓”或者“随营妓女”。但这种表达(也是一种认识)并不确切。因为贞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军妓”或者“随营妓女”,而是一位被日军掳去作为性工具的中国女性、一位“慰安妇”。“军妓”一词表达的仅仅是妓女与军人的关系,只有“慰安妇”这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词,才能表达韩、日、中三国的某些女性与日本侵略军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妓女与军人、女性与男性的关系,而且包含着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慰安妇问题是性问题与国家问题、民族问题的混合物。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将贞贞称作(看作)“慰安妇”的仅有日本学者中岛碧一人。她在《丁玲论》一文中这样说:“女主人公贞贞,过去曾被日本军拉走,强行做过‘慰安妇’。后来却利用这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注:原载日本《飙风》1981年第13期。中文译文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丁玲研究资料》。)这显然是因为,中岛碧作为日本学者、作为一位女性,更容易以慰安妇问题为背景来阅读《我在霞村的时候》。
在确认了贞贞的“慰安妇”身份之后,能够发现,《我在霞村的时候》有可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一篇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将贞贞作为慰安妇置于与日军、与边区政府的特殊关系中来理解,作品的某些隐秘才能被揭示出来。
慰安妇之所以称其为慰安妇,取决于被充作性工具的女性接受了日军强加给她们的性角色——无论是自愿接受还是被迫接受。1940年前后,丁玲创作了两篇以遭受日军强暴的中国女性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一篇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另一篇是1939年春写于延安马列学院的《新的信念》。在《新的信念》中,遭受日军强暴的中国女性陈老太太等人拒绝、抵抗那种屈辱的生活,或者选择死亡,或者逃出虎口控诉日军罪恶以激发同胞的抗日斗志,因此她们虽然受辱却并未成为慰安妇。而贞贞不同。她没有反抗,没有逃走,因此她成了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也变得暧昧。虽然得了性病,但在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与日本兵相处的过程中,贞贞甚至学会了日语——即“鬼子话”。她对“我”说的那段话包含着更多的信息:“日本的女人也都会念很多很多的书,那些鬼子兵都藏得有几封写得漂亮的信:有的是他们的婆姨来的,有的是相好来的,也有不认识的姑娘们写信给他们,还夹上一张照片,写了好些肉麻的话,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心的,总哄得那些鬼子当宝贝似的揣在怀里。”学日语、一起欣赏来自日本的照片和情书(这些照片和情书显然是战争中日本的“国防妇人会”为鼓舞日军士气而让日本女性邮寄的,丁玲的描写具有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生活并非那么残酷。尽管在村民的想象中贞贞“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但事实上从日军炮楼回村的贞贞却是“更标致了”。活泼、洒脱,脸色红润,目光安详。村民们虽然蔑视她——所谓“不干净”、“比破鞋还不如”,但蔑视之中又有几分艳羡——即所谓“更标致了”,所谓“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所谓“说是还到大同去过,很远的,见过一些世面,鬼子话也会说哪。”
在小说的这类描写中,贞贞不像是自魔窟中归来,倒像是从与乡村生活不同的新生活中归来。她与日军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交战国国民之间的关系,而是接受了“慰安妇角色”的中国女性与日本兵的妥协关系(妥协之中似乎还有几分温情)。在这种关系中,日本兵亦不再仅仅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反而有了几分人性。至于那些有机会“念很多很多的书”、能写信的日本女人,甚至是值得中国北方乡村的女性羡慕的了。简言之,对于侮辱自己的日本兵,贞贞显然缺乏陈老太太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
《我在霞村的时候》问世近六十年,研究界对于贞贞这一形象的评价以肯定与赞扬为主。较早并且较有代表性的当为冯雪峰的观点,所谓“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出了她的丰富的有光芒的伟大”(注:《从〈梦珂〉到〈夜〉》。原载1948年1月《中国作家》1卷2期。)。近年依然有人认为:“《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被泼上那么多污水,心身经受了那么深的摧残,但却在传统的阴霾中放射出圣洁的光辉,在人生逆境中表现出解放区新人的独立意识、自觉精神和峻洁人格”。(注:张大雷《要做一支白色花——论丁玲的创作个性》。收入《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这类评价显然漠视了贞贞与日本兵的关系中暧昧的一面。认为与日军苟且的贞贞有着“峻洁人格”,总有些勉强。类似的评价如果是送给自日军魔爪中逃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的屈辱激发出村民斗志的陈老太太,也许更恰当。
耐人寻味的是,在50年代后期批判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时候,某些批判文章倒是注意到了那些赞美贞贞的评论家们所忽视的贞贞作为慰安妇与日军的暧昧关系。不妨举陆耀东与华夫的文章为例。陆耀东1957年底发表的《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注:《文艺报》1957年第38期。)一文谈及贞贞的时候这样说:“日本法西斯军队突然来了,把她捉了去。这时候,她却一点也不反抗,屈辱地跟着日本人跑,让日本强盗任意侮辱,与许许多多日本人发生关系,以致染上了性病”,“顺从地与日本人一块儿生活,像日本法西斯的军营里的妓女一样。”华夫1958年2月发表的《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注:《文艺报》1958年第3期。)一文认同了陆耀东的观点,对贞贞与日军暧昧关系的把握也更细致。他说:“她在敌人那里当了一年多的军妓,‘当时倒也马马虎虎的过去了’;还学会了一口日本话;在和敌人鬼混的时候,还兴致勃勃地欣赏‘那些鬼子当宝贝似的揣在怀里’的照片和情书,拿肉麻当有趣;回来以后,‘说起鬼子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一点也不害臊’。”——因此陆耀东在其文章中对前述冯雪峰的观点进行了合理的否定。陆耀东认为贞贞在日军那里的表现“是严重地丧失节操”,“不仅是一个女人的贞节,更重要的,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民族敌人面前应有的气节”。这种看法至少适合成为情报员之前的贞贞。贞贞确实曾经是一个“双重失节者”。
不过,“双重失节者”并非贞贞的全部。因为她在成为慰安妇之后又成为边区政府的情报员,而“慰安妇”身份正是做情报员的前提。贞贞不止一次为边区政府送情报,有一次甚至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个人在夜里走了三十多里路。于是,作品中同时并存着两个贞贞:一个是“双重失节者”的贞贞,另一个是为抗日力量送情报的贞贞。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这两个贞贞的并存有些不和谐,边区政府利用女同胞的肉体搞情报的做法也不太光彩。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不和谐和不光彩,因此陆耀东和华夫两位在前面提及的文章中才竭力否定小说中关于贞贞为抗日力量送情报的描写的真实性。不幸的是,这种否定一方面暴露了他们的意识中潜存着的传统的父权、夫权意识,同时也使他们在接近小说本义的道路上中途而返。
毋宁说,边区政府利用贞贞这样一个慰安妇、一个可怜的弱女子搞情报,才是这篇小说的要害所在。由于有了这个情节,边区政府便和日军一样,成为贞贞的利用者。虽然他们是对立着、厮杀着的双方。确如美籍华人学者梅仪慈70年代在《不断变化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注:中文译文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丁玲研究资料》。)一文中已经指出的:“她的肉体被战争双方野兽般地糟踏过,一方利用她的肉体;而另一方则把这作为搞到对方情报的手段。”贞贞本来是有机会逃出虎口的,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她接受边区政府的指示重回虎口。显然,贞贞的第一次失节是日军造成的,第二次失节则是为边区政府做出牺牲。她的性病既是日军奸污的结果,又是边区政府利用的结果。小说后半部分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贞贞在蒙受村民的误解与蔑视之后“恨不得早一天离开这家”,并且真的即将奉命离开,这时她对“我”说:“他们叫我回……去治病。”从下文的描写来看,贞贞到延安治病是她本人的要求,而且她从未去过延安。那么,她话中的“回”只能理解为“回日军炮楼”。只是由于某种担心,她才中途改变了话题。由此可见边区政府对她身体的利用并没有结束。无疑,边区政府利用贞贞是为了抗日救亡的崇高目的,是为了正义,这一点与日军用贞贞的身体发泄兽欲完全不同,但是,对于贞贞个人来说,无论哪一种利用都是以她肉体和人格的受伤害为代价的。作为一个为了抗日救国贡献出自己身体的女性,回到故乡却要遭受村人的白眼和非议。于是,在来自双方的利用中,贞贞陷于空前的孤独——孤独于祖国之敌人的日本兵之外,并且孤独于祖国和同胞之外。身为弱国子民,她才惨遭异族男子的强暴,而在她的继续失节变为对祖国的奉献的时候,她依然未能摆脱那种受歧视的命运。
因此,研究者们仅仅依据小说的部分情节、在国家与民族的层面上将贞贞视为“变节者”或“英雄”,都偏离了作品的本意。在本质上,《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表现女性之孤独与女性之困境的小说,是一篇“纯粹为女性”的作品。虽然它是创作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并且是创作于革命圣地延安。在这里,女性问题超越了国家、民族问题,被还原为纯粹的女性问题。换言之,性别的悲剧在小说中被用超国家、超民族这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作品中“女人真作孽”、“女人真倒霉”之类的议论,才是主题所在。写于1942年3月初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对女性问题的关心,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对战争状态下女性命运的探讨是一脉相承的。
确如蓝棣之所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出自一位革命作家之手,的确让人惊讶。”(注:《女性的愤懑和挣扎》。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4期。)值得惊讶的不仅仅是革命作家关注女性问题,更主要的是:丁玲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她的民族意识,于是,在处理中国女子被日军强暴这一最适合宣传日本军之暴虐、激发民族抗日情绪的题材的时候,丁玲反而解构了国家的神圣性、表现了革命对个人的残酷,甚至无意中展示了那些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兵的人性。这解构与展示具有内在的相通。这种对国家神圣性的解构与几乎是同时创作的《在医院中》对革命的怀疑完全一致。《在医院中》表现了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不平等,主人公陆萍甚至怀疑:“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我在霞村的时候》曾被看作反党作品(陆耀东在前面提及的文章中就把这篇小说看作“1941年丁玲反党思想高涨时期的‘著名’的作品之一”),成为丁玲本人反党、变节的证据,恰恰是因为它包含着类似可以被解释为“反党”的内在机制。遗憾的是,仅仅根据《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失节”判断小说作者丁玲反党的人,完全忽视了同一时期丁玲还创作了《新的信念》这种揭露日军的兽性、残忍,号召人们起来抗日的充满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品。
《新的信念》中的中国女性以死或逃走来保持自己作为女人与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却因为妥协而变成“双重失节者”并游离于“国家”之外。这两篇同一时期创作的小说题材相同,而处理方法与作品内涵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是基于丁玲心理结构的二重性:一方面她是一位革命的中国作家,同时她又是一位女性作家。如果我们意识到丁玲曾经是一位自觉的女性作家,将《我在霞村的时候》与丁玲10年代的小说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这篇小说被创作出来的必然性。将一位忍辱负重、患了性病的弱女子命名为“贞贞”,一方面表现了丁玲对贞贞“为国捐躯”行为的肯定,同时也表现了丁玲对传统贞操观的亵渎。这种亵渎与她早期的《暑假中》、《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等作品所表现的对于“贞节”的蔑视、对于卖淫的宽容正是一脉相承的。在50年代末的丁玲批判中,有人将贞贞与沙菲相提并论,并非没有道理。《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创作可以看作20年代丁玲个人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丁玲决绝地向一切压迫女性的社会、文化势力“复仇”,以至于淡化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精神。这是丁玲女性意识的极致。王德威在《做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注:收入《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文中对《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了独到的分析,但他认为“丁玲欲藉小说渲染一种福音式政治讯息的动机,不言而喻”,认为小说“很意外地透露了她(丁玲)对妇女问题的深切体验”,则是低估了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的自觉性。事实也许正相反。《我在霞村的时候》不是在“渲染”、而是在解构“福音式政治讯息”。不是“很意外地”、而是“很自觉地”表现出了丁玲“对妇女问题的深切体验”。不过,与此同时,身处延安的丁玲正在努力抛弃那种个人主义的“女性立场”也是事实。在《三八节有感》一文发表后不久的整风运动中,她进行自我批判,说《三八节有感》是一篇“坏文章”,“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丁玲研究资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等作品的创作,也说明她思想意识中的“国家”、“革命”层面正在日益变得丰厚。
从新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我在霞村的时候》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五四时期“娜拉”的出走标志着中国新女性追求“自我”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在胡适的剧本《终身大事》(1919)中被田亚梅小姐表达为“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在鲁迅的小说《伤逝》(1925)中被子君表达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五四之后中国女性并未完全获得对于自己身体的权利,《伤逝》所期待的对于中国女性的“辉煌的曙色”迟迟没有出现。相反,女性们继续承受着多种外在力量的“干涉”。鲁迅的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1925),本质上就是在表现生存与道德的冲突对于女性身体的异化。而《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为同样以女性身体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冒着违反“政治正确性”的风险,展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身体更为特殊的存在方式,以及这种存在方式中女性自身的价值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冲突。在该作品中,女性的身体作为女性自身的符号与作为国家、民族的符号以统一而又对立的多重关系纠缠在一起。如果系统探讨新文学作品中女性身体的存在方式及其所负载的意义,《我在霞村的时候》无疑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篇。它延续并且丰富了丁玲本人以及胡适、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五四以来对同一主题的思考与表现。
80年代以来,慰安妇问题引起了广泛注意,相关研究也由国家、民族的层面延伸到“纯粹女性”的层面。日本女性问题研究专家上野千鹤子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在《民族主义与社会性别》一书中,她将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对于慰安妇的犯罪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战时强奸罪,二是漠视、忘却罪,三是把慰安妇的起诉说成是想要钱(可以称之曰诽谤罪)。确实如她分析的,韩国慰安妇以“个人身份”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她们的已经从视慰安妇问题为民族之耻(这种认识的背后是父权、夫权意识)、企图将慰安妇问题掩盖的“韩国”独立出来。不过,上野千鹤子的“日本学者”身份使其超国家、超民族的分析方法容易被看作为日本侵略者辩解。据她介绍,在1995年召开于北京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当她提出日韩两国的女性主义应当超越国界这一主张的时候,立即受到美籍韩裔女性的质疑:“我们的国境遭到了你们国家军队的侵略。没有理由这样简单地说‘忘记国境’。所谓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无关这种观点,与欧美女性主义者那种以自己的民族为中心的思考方法有什么区别?”(注:青土社1998版,194页。)然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却证明了上野千鹤子的观点成立的可能性。丁玲的超前性与现代性亦由此见出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