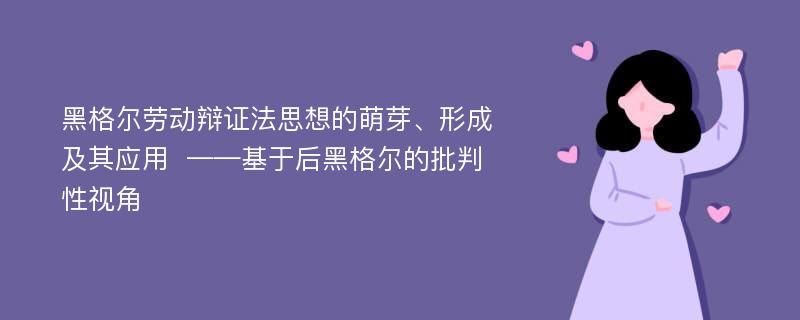
哲学研究
·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专题·
[摘 要]在黑格尔哲学中,劳动辩证法同样是沿着现象(耶拿时期)—本质(《精神现象学》)—现实(《法哲学原理》)的逻辑展开的。黑格尔在耶拿时期观察到了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所导致的“劳动异化”现象,打破了学界的一般结论,并对劳动辩证法的理解表现出存在主义的倾向,如劳动作为对外部世界塑形、破坏和肯定的否定性行动,以及货币作为精神劳动的抽象化符号。但这在《现象学》和《法哲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自我继承和展开,而是一方面从自我意识哲学出发,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讨论了劳动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劳动改造和创造了历史以及劳动开辟了人类解放而获得自由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晚年则彻底简化和退守为实现市民社会中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满足的“中介性”劳动。黑格尔之所以从早年的激进走向晚年的保守,主要源自对“抽象的精神劳动”的信仰,对劳动的内在矛盾和否定的轻视,并坚信从其之中能够获得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统一。这一理论就走向为劳动本身并不能获得解放,劳动只是人获得自由或解放的一个中介和环节。
[关键词]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否定性辩证法;主奴辩证法
对于黑格尔劳动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学界一般都顺着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批判路子展开对黑格尔劳动或劳动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这样的缺陷在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以下简称《现象学》)中对劳动的极其“抽象”和突兀的论述使读者难以理解:(1)为什么马克思说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消极方面;(2)由此而来的,难道黑格尔对于他那个时代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劳动异化现象视而不见?以至于在《现象学》中只字不提,人们看到的顶多只是晚年发表的《法哲学原理》(以下简称《法哲学》)关于劳动异化现象的肯定性描述,即仍然是从积极的满足需要以及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满足的层面理解劳动,其劳动辩证法思想也被表达为劳动的异化现象在更高的“国家”阶段被扬弃。
一是对假物现场的勘验。假货、假币、假发票等假物现场,包括假物的加工现场、假物的仓储现场和假物的交易现场等。这些现场必然遗留有大量的与假物犯罪有关的物证书证。这些物证书证是认定涉案物品的种类、数量、制假过程、售假网络、用假范围、涉案物品与嫌疑人关系等的重要证据,需要通过认真仔细的实地勘验才能尽可能地全面获取。对此类案件的现场勘验也可以使侦查人员通过一个犯罪现场(如仓储现场)发现其他现场(如制假现场)。通过勘验假物现场,侦查人员还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制假犯罪的全过程,进而切断此类犯罪原材料的供应链,摸清假物的集散网络和制假售假用假人员关系网,对进一步扩线侦查和防范该类犯罪都有积极的意义。
但如果将比较的视野拓宽至黑格尔早期,将“整全的黑格尔”置于其思想史来看,问题的视域会变得更宽阔和清晰。按照洛维特的说法,黑格尔至少有三次关于“劳动问题”的讨论,分别是:耶拿讲演、《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1]358-365因此,对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的理解和阐释,只有从其对劳动的这三次讨论入手才能被实在性的把握。
春光这样明媚,花儿万紫千红,这一切居然无人欣赏,没人理会,她伤感了,难道自己就像无人爱惜的春天,悄悄流逝,年华虚度吗?“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中,杜丽娘做了个梦,在梦中她见到手持柳枝的少年书生,大胆地和他幽会了。《惊梦》之后,家教已锁不住她,她不顾母亲的教训,第二天又去后花园寻梦。
一、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在“耶拿时期”[注]但黑格尔早期讨论到劳动的著作并不只是洛维特所指认的《耶拿实在哲学》第1卷(1803—1804年),至少还包括《伦理体系》(1802—1803年)和《实在哲学》第2卷(1805—1806年)。因此,笔者将1802—1806年这一时期统称为黑格尔的“耶拿时期”。的萌芽
在“耶拿时期”,黑格尔首先是第一个对劳动作哲学讨论的哲学家,打破了国民经济学对劳动解释的霸权,将劳动看作为对自然具有塑造性和肯定性的否定性行动。第二,黑格尔同样是看到“劳动的异化”并对其作哲学批判的第一个哲学家,但仍然是从“机器”(工具)的视角分析这种劳动者-劳动对象分离的异化。第三,从作为满足需要的中介理解劳动。这一点既贯穿于黑格尔劳动辩证法思想史,同时在晚年也得到了完整的发挥,即从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社会结构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第四,在黑格尔这里,作为“物质实存概念”的“货币”本质上就是精神劳动或抽象劳动的代名词。
首先,奴隶通过主人而意识到的“自由”。主奴的生死搏斗是为了得到对方的“承认”,奴隶的生命活动即劳动中还蕴涵了一种超越于物质和承认欲望的价值和力量使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就是“自由”。奴隶在体验到死亡恐惧的时候,也体验到了对其自由的双重否定:一是主人对他的自由的否定;二是死亡对他的自由(生命)的绝对否定。所以,奴隶意识到的仅仅是另一个人的自由,而不是劳动的自由价值。科耶夫表述为:“否定性=死亡=个体性=自由=历史;人是终有一死的,有限的,自由的,历史的个体。”[11]55
劳动成为赞颂的主题并不是古往有之,在中古基督教时代,劳动本身被赋予了“原罪”性质。劳动是一种上帝对罪恶的惩罚,劳动被赋予了“诅咒”的消极属性,“劳动就是毁坏或者诅咒世界”[2]。
10q23微缺失综合征是较少见的染色体缺失综合征之一,临床表型涉及多个系统,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由于10q23包含较多基因,基因型-表型间的联系尚未完全明确。
与这种消极的理解不同,黑格尔一开始就是从“精神特征”对劳动作出规定的。人不同于动物,劳动不是人的本能活动,相反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理性活动”,黑格尔称为“精神的方式”。从而在黑格尔这里,劳动就被设定为一种相对于自然的“否定性行动”,是“对象的消灭”和“有目的地消灭客体”等。[3]这种否定性行动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动物并不会同人一样“劳动”,它只是通过与自然建立直接性关系使得本能需要得以满足,“与此相反,人的杰出之处在于他间接地自己生产自己的面包,把自然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1]358。因此,劳动在这里被表达为调节人与世界关系以满足人的需要的“中间环节”。不过,黑格尔认为作为中介的调和运动,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否定性行动,不是简单的消灭。与动物的本能不同,“人借助工具的精神性劳动是构成性的,是借助塑造来造成持久的东西的,也就是说,是造成独立自主的东西的”[1]359。这清晰地表现出了黑格尔与以往哲学(宗教)对劳动的完全消极的评价有着质的不同,可看作黑格尔对劳动进行哲学化(去宗教的神秘化)的早期尝试。
因此,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表现为对“否定性”“破坏性”以及“塑形性”的强调。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一“否定性”行动所包含的“肯定性质”,在劳动的过程中,这种包含“肯定的否定性”应当被理解为对现存世界的改造加工,它给予劳动主体的对象世界的一个全新存在形态。[注]值得思考的是,马克思对劳动的否定性理解为劳动的内在否定,一是大家熟知的“异化劳动”,二是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否定。可见黑格尔仍是从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理解劳动的否定性,即主体改造客体(自然)。但笔者以为,此时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主要展现在客体的维度,即对自然的改造和塑形。这与《现象学》中所强调的不同,劳动不仅对外部世界有塑形能力,劳动尤其创造人本身,因而包含了劳动对主体的创造与反向塑形。
2.中介性劳动:作为需要及其满足的劳动体系
黑格尔最早在1802—1803年写作的《伦理体系》中就阐述了劳动在需要体系中的三一式辩证法,即需要—劳动—享受。从这个式子中可以看出,黑格尔此时将劳动看作需要和满足(享受)的中介。与劳动对自然的否定性一样,黑格尔将劳动的中介性视作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因为动物与欲望的关系是单纯的直接性关系,所以其满足也是直接性的,不像人必须通过劳动这个中介来获得物质需要上的满足,因而对于动物而言,“单纯满足欲望就是纯粹消灭对象”[4]171。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已经涉及后来在历史哲学中的重要思想——理性的狡计,劳动只是满足需要的中介环节和工具。
黑格尔并不仅仅停留在单个人的需要和满足的关系理解劳动的本质,而是将劳动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理解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这一讨论在《法哲学》中得到了展开,同样表现了耶拿时期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及认同。在传统社会中,劳动所扮演的是个人的中介和工具,即人为了满足当前一时的需要而进行劳作所收获的“物质财富”,这个财富并不是“货币”,而是具体的“物”。所以,这种满足仍然是从个人出发,而又立即回到了个人。但是现代社会的劳动所满足的对象不囿于个人层面,而是为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即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互为中介关系。黑格尔认为,“每个人的工作按其内容来说是普遍的劳动,既看到一切人的需要,也能够去满足一个个人的需要。……每个人虽然是具有需要的个人,却变成为一个普遍的东西”[5]。这个“普遍的东西”就是“抽象劳动”,这是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一般”的哲学指认。黑格尔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在需要及其满足中构成的抽象劳动体系对现代人的支配和统治。这与国民经济学完全乐观理解现代劳动体系(“看不见的手”)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黑格尔在晚年证明,这种异化仍然会在下一个更高的“国家环节”得到扬弃,所以这一点上仍然没有脱离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其次,这种“普遍劳动”的异化形式还体现于劳动体系化所导致的专门化,而这意味着多样化的丧失。“劳动这样普遍化为劳动体系,其辩证的另一面就是其专门化,就像劳动简单化为每一特殊的劳动导致其多样化一样。”[1]361劳动的单调化、特殊化以及简单化使得本身也更“复杂化”。这种复杂化和多样化使得人越是从自然的具体化中解放出来,就越变得屈服和依赖于自然。
按照贺麟的研究,在构成需要与劳动的相互依赖的体系中,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体现在两个方面[注]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贺麟将其图式化为:(一)主体辩证法:需要—劳动—享受;(二)客体辩证法:占有物质资料—劳动活动本身—占有产品。:一是劳动在客体中的辩证法,即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本身占有产品的过程;二是劳动在主体中的辩证法,即体现在人的需要的满足方面。马克思显然继承了劳动的主客体辩证法思想(尽管不一定读了黑格尔早期著作),劳动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才能摆脱自然的必然性,“认识到劳动的本质,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所以是真实的人——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98。而且,劳动在主体的辩证法过程隐含了后来在卢卡奇哲学中的“物化”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并没有发展出来,因为黑格尔仍然是就“辩证法”的积极和肯定意义谈劳动对人的需要满足作用。
为营造良好创业环境,有效整合社会服务资源,为创业者不同发展阶段提供质优价惠的创业服务支撑。2013年,省工信委制定出台了《云南省省级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截至2017年,全省已分五批共40家服务机构通过省级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认定,入驻示范基地企业达5237户,带动就业人员69858人。
3.异化的劳动:第一次从“机器生产”讨论劳动的异化
第三,黑格尔从人的生存境况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的使用所造成的劳动异化现象以及给劳动者带来的巨大伤害。这是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异化”最精彩的部分。随着机器作为人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工具,虽然是为人服务的,是人征服机器或自然的表现,但是同样给人产生了负面作用。黑格尔认为,虽然随着机器的使用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是“劳动绝对地变成越来越僵死,它成为机器劳动,个人自己的技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工厂工人的意识则下降到极端愚钝”[4]177。并且,“由于劳动的抽象化,工人变得更加机械、更加呆板和缺乏灵活性。……他能把某些劳动交付给机器,他自己的动作就越趋向形式化”[4]243。显然,黑格尔的这种批判仍然只是存在主义的,而没有继续探索异化的根源。
可以说,对“机器”造成的劳动异化的批判和分析是黑格尔早期经济思想中最为精彩而耀眼的环节。这一点打破了一般学者对黑格尔的教条主义理解,以为只有马克思看到了“劳动的异化”,似乎黑格尔只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研究表明,这一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在劳动辩证法的问题上,黑格尔对机器的讨论分为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
第一,黑格尔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机器的运用对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劳动产品价值的影响。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专门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灭了个体劳动的多样性,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却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黑格尔生活在一个机器运用和机械化的社会进程中,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看到了机器的这种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进步意义。他认为,“由于劳动的个别化,任何个人的单一劳动的技能直接增大了”,“劳动的个别化增加了产量”。[4]177
第二,黑格尔还洞察了机器化生产体系下,“劳动的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的价值规律。因此,黑格尔从抽象的普遍的劳动中洞察出了“劳动”具有价值。他说:“被加工物的等同性即价值,在价值中,被加工物都是同一的,这个价值本身作为物是金钱。”[4]225这里的“等同性”其实就是“抽象的普遍的劳动”,从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一般劳动”,这表明黑格尔深谙国民经济学,尤其是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但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看,黑格尔“犯了两个错误”:(1)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这里的“劳动具有价值”所指实则是“劳动力”。劳动无价值,具有价值的是劳动力。(2)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随着大机器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运用以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单个商品所包含的价值会随之下降。黑格尔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而是对价值认识上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模糊认识,把价值看成了对“事物的意见”。
在正常情况下,静脉瓣膜能控制静脉血流量和血流方向,而当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时,则会出现静脉瓣膜关闭不全导致静脉血液反流。下肢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为最常见的静脉瓣膜功能疾病之一,能导致下肢出现皮肤萎缩、色素沉着、皮下硬结、湿疹等皮肤营养性病变,严重者甚至出现淤血性渗液、难愈性溃疡等严重并发症。有研究对57例下肢静脉性溃疡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原发性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继发性皮肤溃疡45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继发性溃疡仅12例[10]。
同样,机器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天然亲和关系的疏离,因为正是机器的使用使得自然界被人欺骗了,这种对自然欺骗行为的后果则是自然反过来报复人类,欺骗者反而在在这种借助机器奴役和剥夺自然的过程中将人类自身趋向更卑微和渺小。“由于他让使用……机器加工自然,他并没有扬弃自己劳动的必要性,而是仅仅推移了劳动,使它远离了自然,不把自然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自然而以有生命的方式对待;而是逃避这种否定性的有生命性,而他所剩下的劳动也就变得甚至更为用机器进行了。”[1]360因为劳动越是依赖于机器,劳动就越没有价值,劳动者也就越依赖机器。在黑格尔看来,机器会造成劳动的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批判了“机器生产”会将人丢进无法救助的贫困深渊之中。因为人们总是寻求对劳动的简化以及对新机器的疯狂追求,从而导致“现在个人的生存已屈从于整体的癫狂的偶然性,因此,大量人被驱赶到车间、工厂和矿厂中去从事完全残酷、有害而又完全没有保障的劳动……整个阶层都被丢进了无法救助的贫困的深渊之中。我们看到了巨富与赤贫之间的对立”[7]。黑格尔看到了,当社会财富分配出现两极分化时,这种依赖机器体系的劳动会使得社会有可能堕入“极度野蛮”的不正常状态。更甚,这种巨富与巨贫之间的极度不平等关系也必然造成人们意志的极度分裂和内心的愤恨。由此可知,黑格尔对英国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真实状况有着具体而深刻的研究,对“巨富”和“巨贫”的研究延续至了《法哲学》。
综上所述,黑格尔并非没有看到劳动消极的一面。相反,他对劳动的这种异化现象有着独到的理解,充满了激进的批判精神。我们已能清晰见到黑格尔对劳动分析的两种影子,一是哲学存在论的,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但只是零星闪烁、若隐若现,并没有被继续发挥和充分发展出来。他没有认识到,实际上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抽象劳动对人的具体劳动的统治(“抽象对人的统治”),而是从机器作为工具的角度批判了劳动与工人的异化现象。这仍然属于人类学和现象学的讨论范式,而不是从哲学存在论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核中来分析“异化劳动”。
4.精神性劳动:货币作为普遍的精神劳动或抽象劳动的“代名词”
我们发现,黑格尔的讨论呈现出一种模糊的指认,即“抽象的精神劳动”。这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对黑格尔《现象学》中劳动辩证法思想的概括。但在耶拿时期,黑格尔主要是从“货币”指认“抽象的精神劳动”。越发抽象和精神化的劳动,就物的实在性而言指的是货币,货币实则是精神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代名词。“货币拥有一切需要的意义,它是所有特殊性的一种抽象,因为它借助自己的精神统一性和普遍性绝对造成了平均化。”[1]362除了马克思和G.齐美尔对货币进行过哲学分析以外,就只有黑格尔这么做了。
黑格尔按照劳动的方式区分了由不同教养组成的三种阶层,即农民阶级、手工业劳动者阶层和商人阶层。黑格尔认为,(1)农民的劳动还不是抽象性的精神劳动,因为它沉浸于具体的事物之中;(2)手工业的劳动实际上是“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过渡;(3)与“物”离得最远的是商人,他们根本不塑造任何东西,因此在商人通过抽象的货币与商品的交换之中,劳动的精神性的东西被最为纯粹地表达出来了。所谓“精神劳动”指的是货币作为“理性的形式原则”,作为“精神性”的实体内容。因为抽象普遍的本质是“精神”,所以它(意识)能够抽象掉作为感性的东西,包括自身的存在。其实,如黑格尔再往前走一步就和马克思达成了默契,即抽象劳动其实就是“价值”和“资本”的代名词,仅仅从货币理解,仍然停留在“物”层面讨论“抽象劳动”,而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机制中理解“抽象劳动”的存在论含义。所以黑格尔所说的具体劳动指的是传统劳动,如与物质直接打交道,抽象劳动也只是被简化为现代劳动形式,即机器生产下的劳动。这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及其关系的理解有着质的差异。
二、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在《精神现象学》主奴关系中的形成
《现象学》是黑格尔于1807年发表的第一本哲学著作。《现象学》出版之后并未如预期反响那样大,以至于黑格尔一度沮丧而未曾作过一次修订。但在今天看来,这本书毫无疑问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最核心的部分之一,马克思对它推崇备至,称之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6]94。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有两次提到“劳动”,第一次是众所周知的第四章(自我意识章)的“主人-奴隶”部分,第二次是在第五章(理性章)的“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其自身的活动而实现”部分。本文首先沿着文本自身的展开方式阐明“主奴辩证法”的原初内涵,进而探明蕴涵在主奴关系中的劳动辩证法思想及其内在机理。
1.主人-奴隶关系的确认:双重自我意识及其斗争
李志勇笑着说:“我们不生产食品,我们只是云南大山里的搬运工。我们把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美食转交给热爱天然食材的全球朋友,让健康和长寿赋予每个食客快乐和吉祥。”
在黑格尔看来,主人并不是天生就是主人,同样也没有天生的奴隶。这就是说,主人-奴隶的关系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之中形成的。问题在于,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27不同,黑格尔这里所指认的历史载体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主-奴斗争”。“阶级”之间是为“生存的经济条件”而斗争,“主-奴”之间却完全不同:他们为了崇高的尊严、荣誉,为了“承认”而斗争,归根结底是为“自由”而斗争。因此,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也就形成了两种解读模式:第一种解读模式是以科耶夫为代表的“为承认而斗争”,也就是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模式在今天看来广为学界诟病,因此产生了类似“回到黑格尔”的第二种解读模式,即主张将主奴关系置放在黑格尔哲学的文本以及哲学体系中讨论,主人-奴隶之间的生死斗争以及奴隶的劳动实际上是人类自由意识的实现过程,也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一个环节。这种解读反对科耶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反对一味从奴隶的卑微地位讨论主奴关系,尤其反对从“阶级斗争”,即“支配论”“统治论”“平衡论”等角度过度诠释黑格尔哲学。[8]笔者认为,既要全面展现黑格尔主-奴关系或劳动辩证法思想全貌,但也完全可以从现代的视角对其展开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如此才具有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现象学》包含了五个环节,即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最后走向的是绝对知识。主奴关系属于自我意识的第一个本质形态,也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而主奴辩证法正是揭示了自然向人的转向过程。
那么,主人是如何实现对奴隶的权力支配关系的呢?在斗争中,主人证明了其存在对于奴隶的否定作用,因此主人支配着奴隶的存在。“主人既然有力量支配他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又有力量支配它的对方[奴隶],所以在这个推移过程中,主人就把他的对方放在自己权力支配下。”[10]186所以仍然是“承认关系”决定了主人与奴隶的行动的主次,也就是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权力高下关系。但承认的关系是两方面的,一是奴隶否定了其“自为存在”,他的一切行为(包括劳动)正是主人对他所要做的事情。因为主人对奴隶是一种支配的权力关系,支配就是“命令”,但这种命令的有效性体现在“承认”的关系中,因此主人对奴隶的支配也可以说是奴隶在支配自己去行动;二是奴隶做的事情正是主人要去做的,所以仍然是“主人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势下,主人是主要的行动,奴隶是次要的行动。但黑格尔指出,这种承认的关系仍然是“不平等”,这是一种片面和不平衡的承认关系。
其次,主-奴权力关系的确立源自双重自我意识的斗争。两种自我意识的斗争是一个双重的行动:(1)对方的行动,“每一方都想要消灭对方,致对方于死命”;(2)通过自身的行动,“它们自己和彼此间都通过生死的斗争来证明它们的存在”[10]184;它们必须通过这样的行动来证明和确证自己的真理性,并将这种真理性提高到客观的即现实的地位。这里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双方的斗争是源于“自我意识”的确证和提升,那些为“物质利益”的斗争只是偶然性而不具备真理性;但马克思以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根源于为现实利益的真实斗争,固然包含着自我意识(证明自己)的一方面,但“现实利益”更为根本。两者共同性的一面是,“只有通过冒生命的危险才可以获得自由”[10]184,这种危险的考验是奴隶获得自由的必要且必然的环节。
至于如何走出这种困局,黑格尔提供的方案仍然充满着“思辨的逻辑体系”的痕迹。黑格尔明确表示,没有节制和尺度的特殊性所导致的贫困和匮乏的“这种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和”[16]228。因此,尽管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中的矛盾和特殊利益的优先性,但他并未放弃追求“普遍利益”的希望。首先,特殊性只有在普遍性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理念不仅赋予特殊性以伸张和发展的权利,更“赋予普遍性以证明自己既是特殊性的基础和必要形式、又是特殊性的控制力量和最后目的的权利”[16]225。其次,特殊性的真理存在于普遍性之中。“特殊性的原则,正是随着它自为地发展为整体而推移到普遍性之中,并且只有在普遍性中才达到它的真理以及它的肯定现实性所应有的权利。”[16]228
在经历了生死斗争之后,这种你死我活的环节就结束了。因而,他们的关系就转向了单纯存在而不对立(斗争)的两个极端,也就是后面出现的主人和奴隶。由此可知,主人和奴隶是经历了生死斗争后被确立下来的“非等同性”的“和平关系”。黑格尔指出这种否定关系是一种“抽象的否定”,而不是意识的否定。在抽象的否定中,相互之间是没有“肯定”的因素,而只是简单粗暴的否定。“意识的扬弃是这样的:它保存并且保持住那被扬弃者,因而它自己也可以经得住它的被扬弃而仍能活下去。”[10]185“活下去”是指扬弃的运动建立在两者生命保存的前提下,不然没有了“生命”,要么主奴关系不复存在;要么陷入重复的战斗。这意味着主奴辩证法的扬弃仍然属于意识的范围内。
2.主人-奴隶辩证法的展开过程:作为“否定”力量的统治与恐惧
主奴关系确定之后经历了三个阶段(逻辑的而非历史的),即主人对奴隶统治、奴隶对绝对主人的恐惧以及奴隶的劳动(陶冶事物)。
第一,主人方面:统治阶段。这是就主人对奴隶的单向关系而言,但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建立在主奴的生死斗争而获得了相互承认的基础之上。首先,奴隶的本质是作为主人的物性存在。与主人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一个物相关系,这物是欲望的对象,另一方面又与意识相关联,而这个意识的本质是物或物性。”[10]186所以这里的确隐藏了卢卡奇所提出的“物化”思想,主人对物的欲望必须通过奴隶来得到满足,因此奴隶对于主人来说其本质上是为满足欲望的“工具”,即物性。这与亚里士多德时代是一致的,奴隶只不过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语)。奴隶与物打交道,在这里也被表达为物与物打交道。黑格尔指出,“主人通过独立存在间接地使自身与奴隶相关联,因为正是在这种关系里,奴隶才成为奴隶”[10]186。
在这里,可以与马克思作个比较。马克思所谈的关系是劳动者-资本家的关系,与黑格尔主奴关系的本质差异在于:其一,劳动者或奴隶都是被主人设定为“工具”,在这种关系中被降格为物-物关系,被“物化”了;其二,但对于主人和资本家有着质的差异,奴隶的劳动所得是为了满足主人的直接需要,劳动产品成为主人直接享用的对象,资本家却不同,作为它所购买得来的“商品”(劳动力)所使用生产得来的产品不是为了资本家自己享用,而是为了他人(消费者),这个他人更根本的意义上就是劳动阶级自身;其三,资本家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商品”,商品不仅不是他直接享用的对象,而且和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所有存在都成了资本增殖的中介。
再看一看主人与物关系的本质。奴隶对于物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否定的运动的关系,奴隶虽然加工改造物,但并不直接消灭掉。因此,主人需要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直接消灭物的是主人,也就是“享受了物”。相对动物的直接性(不需加工)而言,人(主人)则必须通过“陶冶”之后才可以享用,但这个“陶冶”的工作交给了他者,也就是奴隶。这也是主人对物始终存在的显隐关系,即一方面是通过奴隶与物发生的间接关系,另一方面又是对物的直接性享受。无论哪种关系,都决定了主人必须依赖奴隶才能完成“吃喝”这种生命活动,并得到满足。“这样一来,他就只把他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的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10]187主人将劳动的独立性让渡给了奴隶,因此在主人这方面包含了两个矛盾:一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斗争是为了被承认有尊严和价值,但主奴关系一旦确立后,又倒退为自然存在物,即仅为了自然欲望的满足;二是,斗争目的在于另一个他者的承认,但最后承认他的却是一个作为“物性”的存在——奴隶。所以科耶夫认为,“主人的态度是一条存在的绝路”[11]59,这就意味着他必将走向自我灭亡。科耶夫称之为“主人的辩证法”。
1)对原相似岩石试件、掺加微胶囊的相似岩石试件和预压损伤修复后的相似岩石试件进行抗压强度试验,计算强度修复率,记录应力-应变曲线, 研究微胶囊为围岩裂隙的修复情况。
首先,黑格尔指出自我意识的运动必须是双重的,也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黑格尔认为,“单方面的行动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事情的发生只有通过双方面才会促成的”[9]。这就隐含了后面讨论的两种自我意识即主人和奴隶的斗争。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发生”在主奴关系中完全可以理解为“主奴关系的逆转”,或者在马克思哲学的语境下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通过双向的运动才得以发生,仅靠一方面消灭另一方面或单方面的极端运动(如极端暴力革命),是办不成功的。但在黑格尔哲学中,所谓双重的自我意识,本质上是同一个意识的双重化,而运动本身也只是被解释为自我意识的运动,而不是社会现实的运动。黑格尔认为,双重自我意识之间并没有达到“等同性”地位,“一方只是被承认者,而另一方只是承认者”[10]183,这就必然会导致两种自我意识的对抗和斗争。
只有在马克思哲学视野里才能解释支配者何以能够支配被支配者,这种力量不是来源于他们已经存在的支配关系,而是来源于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如果更进一步,权力关系来源于对“资本”的支配,不一定是“拥有”货币,而是将资本运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之中。所以说,资本不是“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象征的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正是在支配与被支配以及奴隶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翻转,这就是主奴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一种形式上的转变,也就是从人类学角度(与动物的区别)所谈到的转变,而不是真实权力关系的转变及其消失。
第二,奴隶这方面:恐惧阶段。黑格尔认为,奴隶虽然没有这种独立的自为存在着的意识,但实际上奴隶在本质上却内在包含这种纯粹的否定性和真理,因为他曾在对自身生命中体验到这一本质。“这种奴隶的意识并不是在这一或那一瞬间害怕这个或那个灾难,而是对于他的整个存在怀着恐惧,因为他曾经感受过死的恐惧、对绝对主人的恐惧。死的恐惧在他的经验中曾经浸透进他的内在灵魂,曾经震撼过他整个躯体,并且一切固定规章命令都使得他发抖。”[10]188绝对主人即指“死亡”。奴隶的一切行动都是在这种死亡意识中完成的,主人也是将“死亡意识”作为他的控制对象,进而实现对奴隶的支配。
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在这里略微表现,即他认为奴隶对死亡的意识并不能完成“普遍的转化”,而必须“在服务中现实地完成这种转化的”[10]188。这个服务的现实过程就是奴隶为主人劳动的过程,所以死亡恐惧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扬弃对自然存在的依赖,转而用“劳动”取消自然的存在,也就是改造和加工自然物。如果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意识,也就没有主人对奴隶的“权力”支配关系,更不会有“陶冶事物”的机会。所以黑格尔下一个环节必然绕不开对奴隶“劳动过程”的讨论,并且暗示了在这一过程实现对“死亡意识”的扬弃以及主奴关系(认识形式上)的逆转。在《现象学》中,“死亡”与对死亡的“恐惧”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它使得奴隶失去了本质,从属于自然;另一方面,它又把本质还给奴隶,使它优越于主人。[12]156
3.主奴关系中的劳动辩证法思想
劳动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是作为主奴辩证法展开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在主奴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中包含了四个本质的环节:为承认而发生的斗争、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奴隶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奴隶的劳动。这四个环节在逻辑上一个比一个更高、更深刻,同样是一个扬弃一个。主奴关系的所有本质都全部聚之于最后的劳动辩证法阶段。在《现象学》中,劳动不仅使得奴隶重获“自我意识”,从而成为自为之存在;甚至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一切。正如马克思评价的,“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6]98。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用SPSS 17.0软件进行,以α=0.05为检验水准,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第一,劳动逆转了主人-奴隶之间的权力关系,使奴隶成为人之存在。这是黑格尔《现象学》中劳动辩证法的最主要方面。对于奴隶来说,在恐惧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他所意识到的是“自为的存在”。只有通过劳动,奴隶的意识才能回到它自身。对于主人来说,他的欲望的满足只是对对象的纯粹否定,而不能像奴隶一样与物直接打交道,也就是缺乏劳动的环节,所以这是主人的缺陷。“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10]189奴隶对事物的否定说明了奴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黑格尔认为,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表明了奴隶的自为存在,“因此那劳动着的意识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10]189黑格尔认为通过外在化的结果都是直观自身,每一次返回都是一次进步。
主奴关系的逆转源自“劳动陶冶事物”。劳动对事物的陶冶包含双重含义:一是肯定性的意义:“使服役的意识通过这种过程成为事实上存在着的纯粹的自为存在”[10]189,也就是奴隶获得 “自我意识”;二是否定性的意义:劳动是对前一个环节(恐惧)的否定。在劳动过程中,“服役的意识”意识到它自身具有的否定能力,自为存在则成为其意识的对象。黑格尔将功劳归之于“劳动”,因为奴隶意识实现了对“独立存在形式”(物)的否定,即成了他的“劳动对象”。这个被奴隶所否定的对象曾经正是他所恐惧的对象,“在这个异己的存在面前它曾经发抖过”,但现在它摧毁了即否定了这个异己的存在者。所以马尔库塞认为,劳动不仅是主奴关系的中项,而且是改变这种关系的手段。[13]109
但奴隶的“自为存在”或自我意识并不是在“劳动”阶段突然生成,在黑格尔看来,它经历了“统治”“恐惧”“劳动”三个过程。在主人面前,奴隶感觉到的自为存在仍然只是外在的,但到了恐惧阶段,这种自为存在就转变为潜在的了。最后,“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10]189。奴隶必须经历恐惧、一般服务和陶冶事物的环节,这两个环节并且是以普遍的形式存在的,即奴隶的劳动成为抽象和普遍的社会劳动。
第二,劳动改造了世界,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劳动创造了历史过程,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在奴隶的劳动中,包含了三重含义。1.奴隶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奴隶自身的自然需要和欲望,而是为了一个超越性的目标。2.奴隶的劳动之所超越了自然的本能需要,是因为奴隶在劳动中始终保持着对绝对主人即死亡的恐惧。3.劳动是奴隶生命的对象化和外在化过程,在对象性的关系中奴隶获得了对自身的直观。因此,“劳动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12]171。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理性所固有的,人的理性的外化便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劳动对外在世界的改造正好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裂。但也正是通过劳动,人与自然在更高阶段获得了统一性。在《现象学》中,奴隶的劳动和主人对物的绝对否定和消灭不同,它是一种赋形的活动。劳动陶冶事物的原始形式,赋予的是人类的价值和审美。所以,劳动产品正是人与自然关系达到统一的象征。
中南半岛各国相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中小国家,但各国的文化影响力却存在显著差异。譬如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18年全球文化影响力排名,泰国在80个参评国家中名列第19位(略高于中国的第21位),越南则名列第52位。 [18]以下我们对越、泰、柬三国的文化影响力及同中国之间的文化流动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当然,如果没有主人,也不可能有历史”[11]211。因为只有奴隶的劳动才能真正完成历史的进步,所以在奴隶的劳动过程中蕴涵了社会转型的可能性。这种转型的可能性来自主人与奴隶的权力关系之中,“一旦奴隶或任何人在劳动中并且通过劳动而意识到自我”[14],那么主奴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被转化了。这一点的发挥实际上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完成的,即当这种关系中的被支配者意识到这种关系时,这种阶级意识将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变革。
第三,劳动获得了普遍性的形式,造就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奴隶的劳动在黑格尔看来仍然不是普遍的抽象的一般劳动,因此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我们知道,不论马克思或海德格尔都指出了黑格尔《现象学》劳动的抽象性质或形而上学本质。从文本来看,《现象学》在“理性”章也对劳动作了简短的分析,在黑格尔那里,主奴在自我意识中的对立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对立,而没有进入到现实的伦理社会之中。当自我意识发展到理性环节,社会关系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抽象的,它达到了社会意义上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仍然是通过劳动完成的。因此,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并没有放弃“耶拿时期”通过劳动实现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意义的统一的愿望。他认为,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劳动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欲望,更是为满足每一个他者的需要和欲望。并且,每个“小我”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大我”才能实现。黑格尔指认了劳动的抽象本质,“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那么同样,他另外也还当作他自己的有意识的对象来完成着普遍的劳动”[10]297。因此这是一个在劳动体系中完成的个人为整体献身的总体社会,并且这是通过普遍的“抽象劳动”才得以完成的。同样,个人的具体劳动只有在社会的普遍劳动之中才能获得其真正的意义。“既是通过我而存在的,也是通过别人自己而存在的……我直观到,他们为我,我为他们。”[10]298这种具体劳动的意义必须要到普遍劳动中去寻找的价值取向,正表现出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立场。
第四,劳动开辟了人类自由与自我解放的道路。当奴隶从劳动之中获得了自我意识之后就开始进入它诸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这也是奴隶或人类获得自由意识的三个发展阶段: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因此,奴隶的劳动开辟了人类自由与自我解放的艰苦卓绝而漫长的道路。
1.否定性行动:劳动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塑造性和肯定性的破坏
其次,奴隶从普遍的劳动中陶冶出的“自由”。奴隶的劳动与那种个别性的劳动不同,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而劳动,所以他将自己理解为一种能够从事普遍劳动的存在。因此,奴隶发现自己同主人一样也具有否定和陶冶任何事物自由与力量。所以霍尔盖特认为,正因为奴隶劳动害怕死亡,因此他可以将任何特殊活动视作为摆脱周遭给定的和特定的东西的普遍自由的特殊表达,即普遍的赋形活动。[15]科耶夫甚至认为奴隶的劳动开辟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之路。因为奴隶的劳动并不完全依赖于某种给定的生存环境和条件,而是依循奴隶自身的想法去利用甚至改造被给予的东西,因而他意识到了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劳动是奴隶实现自由和自我解放的一个必然途径,就像马克思那里的异化劳动是自由劳动必经之路一样。“自由”是奴隶或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通过劳动曾经潜藏于生命之中的自由目的得到了实现,所以“劳动是自由的基础,自由是劳动的灵魂”[12]173。但这种也只是意识到了的抽象自由,奴隶仍然是奴隶,他的劳动仍然是强迫的不自由的劳动。
到此为止,奴隶的自由意识进入到第一个形态:抽象的自由意识——斯多葛主义,往后便是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和苦恼的(基督教)意识。这都是劳动所开辟出来的自由所经历的三个逻辑阶段。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是自由实现的中项和工具,不只满足需要还是生产自我意识或是创造人的中介;但马克思则相反,劳动是人的本质而不是中介,自由-劳动本身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生活方式。因此,黑格尔的自由仍然是一种精神的抽象的自由,将自由和劳动耦合是马克思对以往劳动观和自由观发起的一次成功的革命。
“拥有自由观念而没有人身自由”[11]208,这是科耶夫所看到的奴隶的自由状态。但在马克思看来,拥有人身自由,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解放,因为这种劳动获得了普遍的形式,成为每一个人每天必须为生存而烦恼和担忧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这种自由仍然是虚幻的,现代人只是有自由选择某种特定的不自由的权利而已。因此黑格尔的自由与劳动都带有抽象的精神性质。马尔库塞评价道,“纯粹思维再次吞噬了活的自由”,“哲学认识世界的自我信心战胜了实践改变世界”。[13]113
综上所述,黑格尔《现象学》中的劳动辩证法思想特征呈现出“否定”和“精神”(抽象)的二元结构。首先,奴隶的劳动经历了两次否定:第一次是奴隶通过劳动对物的“否定”,这种否定同时是一种赋形的活动;第二次是在劳动过程中,奴隶实现对自己作为“奴隶”的否定,从而获得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因此,劳动的否定性质为奴隶的自由解放指明了精神上的道路。其次,同时这种劳动在黑格尔这里仍然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语)。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劳动必须获得纯粹的形式,这个纯粹形式就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另一方面,继续着“耶拿时期”的想法,黑格尔企图能够在具体的劳动中抽象出满足所有人的普遍劳动,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黑格尔的这种“国民经济学”的愿望最终是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完全的展开。
三、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在《法哲学原理》中的应用
《法哲学原理》(以下简称《法哲学》,1921年)是黑格尔最后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一本著作。但就其中的劳动辩证法思想来说,笔者以为并不具有根本性的变化,黑格尔无非是延续了“耶拿时期”和《现象学》对“劳动”的“中介性”和“精神性”的讨论。在《法哲学》中,对劳动的讨论着重置于“伦理”中的“市民社会”部分。在黑格尔的哲学里,“伦理”是高于“抽象法”和“道德”的环节,也是前两者在社会现实的统一。而“伦理”又包含“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阶段。“市民社会”就属于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
因此,对“市民社会”的准确把握成为理解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关键。黑格尔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内在矛盾并对其作了深刻的哲学批判。市民社会的首要原则是“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特殊性原则,这一原则是市民社会的起点,也是“劳动”的起点,但个人的满足必须经由他人劳动才能得到满足,因此“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16]224,这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第二原则。简而言之,市民社会就是以特殊利益为起点和终点的,因此“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16]224。所以,普遍性中的特殊性成为社会福利的唯一尺度,所有人都成为个人达到目的的手段和中介,因此在社会中活跃的一定是充满着偶然性和任性,整个市民社会成为中介的基地,在其中,“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16]225。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作了辩证分析,既看到了市民社会的起点是“个人的特殊利益”,但同时个人必须依赖于社会,必须通过普遍性原则才能满足“一己之私”。普遍利益就是在这种私人利益战场之中得到满足的。因此黑格尔看到了潜藏在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并指认了二者的“不可分性”。他认为,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看似相互分离,实际上是互相束缚和制约的。在实际中,“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都只是相互依赖、各为他方而存在的,并且又是相互转化的”[16]226。正是市民社会内部包含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黑格尔认为其必然会导致“荒淫”和“贫困”的现象,同时市民社会中的人也会出现生理和伦理上的蜕化景象。
显而易见,黑格尔仍然将自我意识转变成了“历史运动”的主体。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行将消逝的环节”[10]184,反过来说,自我意识才是永恒的,建立其上的自由也才是永恒的。显然,早在这里黑格尔的历史观就已经表现出了“唯心主义”性质。
黑格尔的理论目的和旨归清楚地再现在《法哲学》之中,他一方面既承认市民社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切特殊性的真理都不在自身之中,试图寻求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现实统一。笔者认为,“劳动”及其辩证法就是在这样的文本语境中再一次被黑格尔重新设置进他的体系之中的。
第一,作为“中介性”的劳动。《法哲学》继续发挥“耶拿时期”的思想,劳动不仅是满足个人需要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是作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个人与社会的“中介”。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分析了作为满足需要的劳动体系,模糊地指认了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相互关系。在《法哲学》中,黑格尔更为明晰地显示出了他的劳动辩证法的价值关怀,即作为特殊需要与普遍需要之间之中介的劳动。黑格尔认为,“通过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16]232。从主观出发的特殊需要,正是通过普遍性在满足他人需要和自由的关系中肯定了自己。黑格尔仍然从区分人与动物的角度谈论人的需要,人不直接享用食物,也不像动物一样“随遇而安”。所以人的共同活动构成了“需要的体系”,在其中“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16]231。如此,市民社会无非就是一个通过彼此的劳动而相互依赖、相互满足的社会。就劳动的中介性来说,黑格尔只不过是将早年的零星思想放到了逻辑体系中重新加以考察而已。劳动的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在劳动与需要的相互依赖性关系中,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种辩证运动的积极成果就是每个人在为自己的享受而进行生产-劳动的同时,也在为所有人的享受而生产-劳动,这种全面交织的劳动-需要体系带来的就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财富。
《法哲学》更加深刻地批判了这种以“特殊利益”为起点和终点的劳动分工体系导致只会是“需要的无限性”,“每一次舒适又重新表明它的不舒适,然而这些发现是没有穷尽的”[16]235。黑格尔的确看到了这种需要体系的虚假本质,并指出需要的无限性并非来自我们自身,而是由追求利润的商人创造出来的。因此,黑格尔这里的劳动是带有原罪性质的,它是个人与他人需要的中介,是市民社会的必然环节,是必须和必将被扬弃的东西。
第二,包含“解放性”的劳动。黑格尔区分了直接的或自然的需要和观念的精神需要,并且认为社会需要正是这两种需要之间的联系。精神需要是与高于自然的物质需要的文化观念需要,它是作为社会的普遍物而出现的,例如人对普遍物(社会)的观念依赖。黑格尔反对片面贬低自然需要的积极性,他认为正是在这种自然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社会联系之间包含了“解放的环节”。黑格尔批判“这种观念没有考虑到劳动所包含的解放的环节”[16]237,自然需要及其满足在自然中的精神性状态是潜在的,因而是粗野和不自由的,“至于自由则仅存在于精神在自己内部的反思中,存在于精神同自然的差别中,以及存在于精神对自然的反射中”[16]237。
黑格尔的伟大之处是看到了劳动包含的解放意义,但他从劳动作为满足自然需要的中介性质只将这种解放看作形式的。因为从黑格尔的研究方法可知,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劳动尽管是满足一切人需要的劳动,但这种劳动的目的仍然是建立在“特殊性”的基本内容之上。一方面,市民社会的劳动体系所导致的一定是无限的“分工”,黑格尔认为“社会状况趋向于需要、手段和享受的无穷尽的殊多化和细致化。……这就产生了奢侈”[16]237。劳动本身并不能使人从对物的直接依赖中得到真正的解放,这种细致化和精练化的过程所创造的无限的需要反而使人堕入贪婪和奢侈的无限恶之中,这种对劳动体系的依赖性和贫困也无限增长。另一方面,劳动的解放意义在于在劳动的抽象过程中,带来了“技能”和“生产量”的提高。这基本上是重复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
劳动不仅改造世界,而且创造人的世界即人类的历史进程。奴隶的劳动在改造给定的世界时,同样创造了完全不同的条件,因为他的劳动是重复的,并且会在不同的条件中重复他的劳动行为,因此,世界会更进一步得到改善和发展。“哪里有劳动,哪里就必然有变化,有进步,有历史的发展过程”[11]210。因此,劳动同样创造和推动了历史进程的发展。科耶夫明显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将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本性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他始终强调奴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独特贡献,而“人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奴隶劳动者的产物,而不是主人战士的产物。
概言之,劳动在黑格尔哲学中只是包含解放的环节,劳动本身并不能获得解放和自由,这也是与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重大差异之处。黑格尔将形式的解放归之于劳动,而自由的真正实现却只能发生在精神领域。这和阿伦特的意见达到了高度一致,因为他们都认为劳动仍然无法摆脱自然必然性,因而这种自由仍然是形式的而非真正的自由。总而言之,黑格尔只是指认了市民社会中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劳动体系必然导致奢侈和贫困的产生,但却没有深入探讨“无限恶”的根源及其如何产生。因此,他自然也就不相信劳动本身是可以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自由-劳动二者并不存在天然的无法弥合的矛盾。
第三,实质是“抽象性”的劳动。对劳动抽象化的哲学分析是黑格尔的一大贡献,但他一方面批判了抽象劳动导致的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对这种抽象给予了哲学的认同和确证。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敦煌写本百余件,主要为历年征集收购所得,其中包括吴士鉴旧藏,内容多为汉文佛典,间有回鹘文写本。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所获敦煌汉藏文写本700余件,曾保存于旅顺博物馆。1954年,文化部将620件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目前旅顺博物馆仅存9件供陈列展览之用的写经,以及一件再发现的《坛经》。
87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motes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首先,劳动的抽象化内在包含了自由、平等和普遍三个原则。在黑格尔看来,每一个劳动是个别的,也是普遍的,只有是为他人、为社会的并成为增进社会共同利益才具有真理性。这种普遍性使孤立而抽象的需要与劳动都成为具体的和社会的,“我必须配合着别人而行动,普遍性的形式就是由此而来的。我既从别人那里取得满足的手段,……同时我也不得不生产满足别人的手段”[16]235-236。黑格尔承认这种在相互服务中包含的平等人格的存在,即这种为满足需要而产生的劳动体系“直接包含着同别人平等的要求”[16]236。黑格尔的“平等”指的是每一个体作为特殊存在的人格平等,而不是经济上的交换平等,后者是前者的一种衍生。[17]黑格尔是认同这种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的交换原则的。黑格尔相信在这种普遍和平等交换的劳动体系中,并不代表人的个性和特性的消失,反而每一个人的个性和特点要在劳动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之中得到现实的肯定,即“特殊性用某种突出标志肯定自己”[16]236,劳动也由此获得了“自由”的存在方式。
水产养殖是在人工作用下进行水生动植物的培育和繁殖。目前的水产养殖分为粗养、精养和高密度养殖这3种。水产养殖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水环境污染,严重时还会对周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为此,在社会发展中,要加强对水产养殖中水污染的治理工作,在保证水产养殖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黑格尔在认同上述原则基础上再对劳动抽象化给予隔靴搔痒的批判。这里所谓的劳动的抽象化是指“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16]239,这一抽象化所引发的手段与需要的展开和细化也会带来生产的相应展开和细致化,分工也就产生了。这种“生产和劳动的抽象化”所带来的消极意义是使得劳动本身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被积极所排斥和甚至取代。对劳动抽象化的辩证分析在《哲学全书》里尤其明显,“抽象的劳动,一方面由于其单调性而导致劳动变得容易和生产的增加,另一方面导致局限于一种技巧并因而导致对社会联系的无条件的依赖性”[18]。除此之外,黑格尔还批判了市民社会劳动抽象化所导致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化以及抽象对人的规定(统治),即“当需要和手段的性质成为一种抽象时,抽象也就成为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这一点表现出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同样深刻性。
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将现代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而黑格尔则是从“劳动的抽象化程度”将社会进行三等划分,即作为实体性或直接性的农业等级、作为反思的或形式的(回到自身,通过劳动从普遍利益返回特殊利益而未得到扬弃的)产业等级以及代表普遍利益的公职等级。[16]241
农业劳动及其成果仍然受制于土地和自然(如天气),并且是建立在家庭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因此其抽象程度是最低的。不过,黑格尔也指出了“在我们时代,农业劳动也像工厂一样根据反思的方式而经营”[16]243。产业等级更显示出了黑格尔划分等级的“劳动抽象化”依据,手工业等级以具体的方式满足个人需要的劳动,工业等级则是满足属于一种较为普遍需求的个别需要所作出较为抽象而集体的劳动,而商业等级是劳动的最高抽象,他们之间通过“货币”这一抽象劳动的价值实现者进行普遍交换。不过在“普遍等级”即以社会普遍利益为目的而免于参与直接劳动的公职等级划分中再次显示出黑格尔的理论矛盾。一方面,他以劳动的抽象化程度作为划分等级的尺度,另一方面,又是以劳动的普遍意义(实现公共利益)大小将“公职”划分至最高的等级。这仍然体现了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内在矛盾,他始终认为具体的、特殊的个别劳动的真理性存在于抽象的、普遍的社会劳动之中。但他没有将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与实现普遍利益的社会劳动给出原则的区分,因而他也无法透视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注]这种内在矛盾表明了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理论的深刻性,一方面,他的价值立场仍然是社会的普遍利益,反对市民社会劳动带来的异化现象,因此他将公职等级作为最高的普遍等级;另一方面,在寻求实现“普遍利益”之实践路径方面又站到了国民经济学立场之上,也就是市民社会中的特殊劳动与普遍劳动的辩证运动为“普遍利益”的实现开辟了道路,过分肯定了市民社会中劳动辩证法的积极意义。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学习者因素的平均值最高(M=2.34),说明大多数被试都将自身出现负动机现象的原因归结到自身原因方面。二语学习是一个长期持续且记忆任务相当繁重的习得过程,加之习得过程中还会出现程度不同的语言负迁移现象,因此对学习者的毅力、决心和自制力都有较高的标准和要求,而这些品质可能是当前大学生群体中严重欠缺的,极有可能半途而废,甚至还有者在初始阶段就已经放弃;另外,由于学习者之间显著的个体差异性因素的存在,不恰当的习得策略、过去多次的语言学习失败经历,来自于教师、周围同学、家庭及社会的压力,都会对学习者的耐心、毅力和决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其动机强度产生重创。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所指的个人的特殊劳动可理解为“具体劳动”,而社会的普遍劳动就是“抽象劳动”,而《法哲学》的归宿和立场明显受着国民经济学的影响而过于积极地认同了“抽象劳动”的真理性。黑格尔相信,在市民社会中虽然是私人利益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他却坚信这种社会具有“自由平等”的原则,也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也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满足自己,并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得到了普遍的满足。同样从劳动方式来划分阶层或等级的时候,黑格尔的视野里似乎也没有“资本家”即从整个市民社会的劳动体系中分溢出来的“不劳而获”的阶级,这个阶级并不需要通过自身的劳动就能够获得物质的满足。黑格尔在《法哲学》中的劳动辩证法思想看似是《现象学》的一个递进,但是他并未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市民社会仍然是一个“主奴社会”,仍然是一部分人统治、奴役、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的社会。这种社会在劳动上的辩证表现就是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支配和统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一点,在马克思哲学中有着清楚明白的揭示,黑格尔的妥协性、保守性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性质和乐观心态也同样清楚地表现在这种思想差异之中。
在《法哲学》中,黑格尔的着眼点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会中的“劳动”,但马克思从中读出的是“异化劳动”,而黑格尔得出的是为满足个人需要而实现普遍利益的积极劳动。这是黑格尔哲学所必将导出的实践立场,即只是匆匆看了现实中的异化劳动一眼便奔着他的体系建构而去,为的是满足于更高的逻辑追求——国家,即是对市民社会(为满足需要而建立的劳动体系)的扬弃。
四、结语
纵观黑格尔整个哲学思想史,“劳动辩证法”同样是沿着现象(“耶拿时期”)—本质(《现象学》)—现实(《法哲学》)的逻辑而展开的。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尤其观察到了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所导致的“劳动异化”现象,打破了学界的一般结论。黑格尔对劳动辩证法的理解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存在主义或生存论倾向,如劳动作为对外部世界塑形、破坏和肯定的否定性行动,以及货币作为精神劳动的抽象化符号。但在《现象学》和《法哲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自我继承和展开,而是一方面从自我意识哲学出发,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讨论了劳动对人的自我本质的确证、劳动改造和创造了历史以及劳动开辟了人类解放而获得自由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晚年则彻底简化和退守为实现市民社会中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满足的“中介性”劳动。
黑格尔之所以从早年的激进走向晚年的保守,主要源自对“抽象的精神劳动”的信仰,对劳动的内在矛盾和否定的轻视,并坚信从其之中能够获得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统一。这一理论就导向为劳动本身并不能获得解放,劳动只是人获得自由或解放的一个中介和环节。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之所以演变为非批判和非革命的,主要源自自我封闭的哲学体系和保守的国民经济学立场。这一点,且留待另文阐述。
[参 考 文 献]
[1] [德]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 罗森克兰茨.黑格尔传[M]//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58.
[3] [德]黑格尔.伦理体系[M]//拉松本.黑格尔政治和法哲学论文集.莱比锡,1923:420;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8.
[4] 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5] [英]普兰特.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和社会整体性[M]∥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史研究室.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4页。
[6]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 孙乐强.劳动与经济学的双重演绎:黑格尔劳动哲学的逻辑嬗变[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8] 潘斌.“为了承认而承认”:重审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神话[J].社会科学,2017,(11).
[9]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82.
[10]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1] [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2] 高全喜.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3] [法]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4] [美]汤姆·罗克摩尔.马克思:之前和之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8.
[15] [英]斯蒂芬·霍尔盖特盖特.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与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12.
[16]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7] 高兆明.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释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81.
[18] [德]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III:精神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92.
[收稿日期]2019-03-08
[作者简介]何云峰(1962-),男,重庆开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管理及教育心理学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6-0023-17
〔责任编辑:杜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