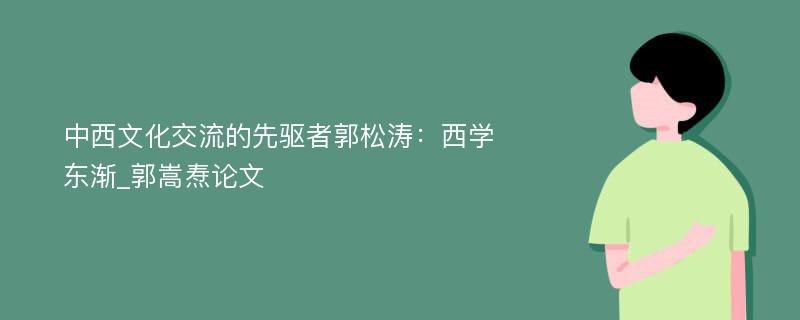
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西学东渐”中的郭嵩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先行者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郭嵩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嵩焘,1818年(嘉庆2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城;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别署玉池山农、玉池老人,又因他的书房标名“养知书屋”,故学者又称他养知先生。
郭嵩焘步入仕途时,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传统观念因此开始动摇,知识群体也开始走向分化。郭嵩焘一生的实践使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特别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一
郭嵩焘,家道殷实,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19世纪初期的洞庭湖区,手工业和商业已经比较发达,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一道在城镇经济中出现。郭家因善于经营逐渐成为湘阴巨富。郭嵩焘在这个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耳濡目染,形成了与传统士大夫不同的性格特点,一是重视工商,主张“商贾与士大夫并重”;二是他偏重词翰而芬芳悱侧,轻略“经济之学”。他的独特性格使他与传统士大夫的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同。
郭嵩焘少年时,曾在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有同窗之谊、换帖之交,后来与左宗棠成为儿女亲家,又结交了李鸿章、江忠源等清末名士。咸丰2年(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自广西逼及湖南,清政府号召各省在籍大臣办理团练镇压太平军。郭嵩焘曾亲到曾国藩家劝说曾国藩起兵,为曾国藩日后成为“中兴名臣”奠定了基础。1859年郭嵩焘又随僧格林沁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与僧格林沁不睦而遭罢免。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以庶吉士累官至翰林院编修、道员、盐运使,1863年—1865年署理广东巡抚,因与总督毛鸿宾不合,遂罢去,以后又署值总理衙门,擢为兵部侍郎。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国订立《烟台条约》,内有‘遣使道歉”一条,郭嵩焘以“道歉”事赴英,即留为驻英公使(后兼驻法公使),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从制度上说中国没有向国外派遣永久性常驻使团的外交传统,而只派遣负有特别使命的使团:即在国势强盛时,奉旨出国,以宣扬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为朝贡国,在国势衰弱时遣使向夷狄求和或结盟。清朝士大夫甚至不承认外交关系,认为“夷务”就是商务,士是耻于言商言利的。从心理上说,大多数清朝官员都自抬身价,回避涉外事务,而把到国外任职视同流放或做人质。因此,朝廷宣布郭嵩焘为赴英使臣以后,很多人纷纷前来规劝他推却此事,以保全声名。而他却欣然受命,声称“数万里路程,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②认为担任外交使臣,任重道远,不是耻辱,而是光荣。这个不同凡响的议论一出,舆论哗然,讥笑、侮骂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慈禧太后也认为郭嵩焘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③可见郭嵩焘是处在一个多么昏庸闭塞的社会环境。
郭嵩焘出使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时,因有当地英国驻官接待,得以参观游览各地名胜、要塞以及学校、官署、监狱等,对各地的政教、军备、民俗等有所了解,他把这些见闻和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下来,写成《使西纪程》一书。书中赞扬了西方文化,指出西方并非蛮夷,其教化“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其城市“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④同时批评中国官僚不明时势,不晓外情,“高谈阔论,而虚骄以自张大。”⑤主张研究、学习西方治国之道。他到达伦敦后,把书稿寄回总理衙门,希望能为开阔国人的眼界起些作用,不料惹来轩然大波。国内封建士大夫万万不能容忍对蛮夷的赞美和对天朝的批评,他们虽然经过几十年欧风美雨的飘打,但千百年来天朝自大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一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哀夷狄应尔。”⑥《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刻印出来,立即遭到围攻,“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⑦“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⑧翰林院编修何金寿甚至“疏劾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⑨讨伐之声遍于朝野。清政府诏命立即销毁《使西纪程》字版,禁止印行。
郭嵩焘到英国后,不仅注意了解欧洲的技术文明,更关心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并且试图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根本原因,研究中国只求“富国”,西方却先要“富民”(资产阶级)的区别。他还十分注意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研究,亲赴下议院旁听会议,直接感受西方民主政治生活,认识到“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教也。”⑩他在英国用大量时间和精力考察西方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参观科学实验,听自然科学讲座,对西方注重实践的精神十分推崇。他对西方文化教育慨叹万端;“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也。”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写道:“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他还对西方的社会文明极为称道,在光绪四年的日记中赞扬了西方公共场合之有序,承认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认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变为先进,这是一种发展的、进化的历史观。
郭嵩焘在英期间的言行为副使刘锡鸿所不容,由于刘锡鸿屡屡作梗,使郭嵩焘心力交瘁,于1879年乞病回归。刘坤一建议委派郭嵩焘到总理衙门任职,但由于有实权的保守派军机大臣李鸿藻和景廉的反对而未果。(11)于是返归故里。在故乡的十余年间,他仍十分注意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常以奏疏和书信方式对外交和时局发表自己的意见。
二
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郭嵩焘与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与封建专制的伦理哲学,与他自己所处的士大夫阶级,逐渐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同时他与热心洋务的朋僚也拉开了认识上的距离,他的中西文化思想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
华夷之辨的争论,是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西学东渐的最大障碍。明华夷之辨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传统士大夫认为,一切华夏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是野蛮民族,即是夷。夷是“教化之外”的动物,其本质是非人。王夫之曾以此观点议论说,汉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换代,而蒙古之灭宋则意味着尧舜禹汤等圣贤教导所体现的文明本身的毁灭。(12)传统观念认为,夷狄是不行仁义,不遵教化之人。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竟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将使中国数千年文明礼仪之邦沦为夷狄之国。(13)就连当时的著名文人王闓运也认为:“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14)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为对西方绝不能再以蛮夷视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15)并举出事实,说明欧洲的文明程度,认为“其风教实远胜中国。”(16)批驳了封建士大夫关于“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化成先进的地区和民族。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18世纪中叶,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开明的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在书写西方国家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而郭嵩焘的文集,包括散文、诗词和奏稿诸卷,却没有把外国人比作禽兽。这反映出他对“严夷夏之大防”的态度。
爱国还是卖国的争论,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十分敏感的问题。封建士大夫认为同西方接触就是辱没祖宗,就是卖国,尤其对郭嵩焘等人反战主和的倡议,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论调。“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17)通常是建立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一般就是国家民族的东西不容侵害。然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在于不断发展,普遍提高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水平。近代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所面对的敌人已不是游牧民族或封建酋长国的进攻,而是资本主义军事、经济的全面进攻,如果仅以“封关禁海”的被动的暂时防御,而不主动了解世界形势,努力赶上世界潮流,纵然自诩爱国,其实只能是误国,一经溃决,就不可收拾。曾国藩认为中外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所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起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18)李鸿章说: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19)郭嵩焘在《使西纪程》和其它书信中批评顽固的士大夫不了解国际形势,对中国军事实力没有正确估计,一味主张蛮干的主战叫嚣,认为他们这种爱国是断送中国。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中国一大变局,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20)主张只有学习外国先进的事物,方能图存图发展,才是真正的爱国。历史告诉我们,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基本要求下,必须有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眼光和意愿,把外国先进的事物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近代中国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爱国与革新相结合,随着时代的推移,革新的口号和程度不一样,性质上有所不同,却都和学习西方有关,它的进程充分地表达了这个历史逻辑。
“体”、“用”的争论,是近代史尤其是中西近代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冲突焦点。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兴起一股思潮,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争后才成为张之洞反对维新思想的口号。正统理学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世界观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无论生物或非生物,一律都是原则和物质的融合。后者从前者那里接受它的本质特征,而前者则以后者为其具体形式。理学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这种本位论的二元论,其中通行的一对概念范畴是“体”与“用”。那么“中体西用”赋予西学的价值只是工具的价值,而传统的儒学被视为高高在上,具有本质的和基本的价值。中学属传统文化,其核心是“伦常名教”。西学的范畴在几十年间是有变化的,初为“格致之学”,七、八十年代延伸为理工医农、声光化电,九十年代以后的西学从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和文化教育、政治体制。1861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诸国富强之术。”(21)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22)郑观应也说:“主以中学,辅以西学”(23),郭嵩焘也主张:“得其道而顺用之”。(24)具有实践意义的是“西学为用”冲破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禁锢,开阔了人们视野,具有引导人们追求新知识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前进,在举办洋务的“用”中,日益碰到有形和无形的“中体”障碍,并发觉西学是“体用兼备”的,“中国求其用而遗其体”,所以成效难期,“西用”日益被“中体”所困扰,答案只好向西方的文化教育和政治体制中去寻找,认识到“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教也。(中国)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25)事实上已经指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和科学,这在当时是十分有远见和胆略的。“中体西用”是在维护“中体”的名义下采纳西学的,这是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唯一能容纳若干资本主义新文化的途径了。如果没有“中体”作前提,“西用”则无所依托,西方思想文化就无法进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所接受。它毕竟使封闭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它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没有丧失其文化特性,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本”、“末”之分的争论焦点是,是否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改变封建专制体制。顽固的封建士大夫认为:“中国自强之道与外洋异。外洋以商务为国本,中国以民生为国本。”(26)“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27)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是立国之本。郭嵩焘站在时代的前沿,勇敢地提出了政治改革问题,主张取法西方政治制度,认为:“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28)并注意到“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29)他经过对西方议会的深入了解,看到“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讳,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西洋一隅为天地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又说:“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30)指出,西方各国的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31)郭嵩焘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上升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军事和工商业上升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要求,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单纯学习西方军事,借以“强兵”还是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是当时朝野关注的分歧点。清政府和封建士大夫官僚们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就能维护其封建统治,就能自强。而郭嵩焘认为,“如是以求自强,适恐足以自敝。”(32)学习西方,不能单学军事,更重要的是教育、冶矿、采煤、铁路、电报等文化科技,“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如果没有诸如采矿、制造、医学、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发展,纵使学得西方兵法,那好比“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33)只有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有用,才能促进中国发展。当时清政府正派30多名青年学生留学欧洲,学习西方海军,而郭嵩焘看到日本来欧洲学习的却以政治、经济、科技等为主,单去英国学习科技和政、经类学问的人就达200多人,甚至原来身为诸侯者,也在那里学习法律,原来做过户部尚书的,也在那里学财经。所以郭嵩焘积极建议中国留学生改学实用的科目,并呼吁各省多派留学生研习实业。这些认识反映了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知程度,体现了他渴望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主张和建议是正确而实际的,顺应了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要求。
三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也是第一位从实践意义上亲到海外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封建士大夫,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爱国者。在清末封闭、麻木的社会环境中,他冒着众人的讥讽嘲笑,前往被封建士大夫们视为“犬羊之地”的西方,身负“放逐”的骂名,身体力行向西方寻求真理,由一名封建士大夫而转变成新时代的探险者,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执著勇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在西学东渐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郭嵩焘对中西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看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保守和落后的一面,主张改革中国政治。他对西方议院制十分推崇,不仅亲临会场,观听辩论,还向别人询问并作详细笔记,将心得写信告诉亲友,上奏朝廷,以期清政府学习西方政治文化,改革中国政治体制。他参观西方监狱等司法机构,对其整洁严明感叹不已。能有此实践精神,实为封建大员中的第一人。
在经济方面,他一方面了解西方的经济学说,探讨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实地考察西方的经济发展。主张中国重在发展实业,采矿、冶炼、电报、铁路是中国富强的基本条件。主张中国的民用工业管理向西方学习,认为西方经营管理方式更科学适用。强调以“利民”政策达到“民富”的目的,实际是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在当时严格的“官本位”社会里,是十分大胆的主张。
在文化上,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世界各民族平等,他的平等主要是指文化发展上的平等,不同的民族、地区的文化或文明水平不是恒久的,是可以变化的。批判了封建士大夫视西方为“夷狄”的错误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政教修明”,文明史也有两千多年,中国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胆略和学识使他在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教育方面,他主张学以致用,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主张多设声光化电等实用之学。迫切要求、呼吁培养涉外人才,加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研究和介绍,使中国人了解世界,跟上世界发展步伐。培养外交人才,让世界了解中国,改变中国愚味落后的形象。总之,使教育文化成为培养中国人文明健康的有效途径。
郭嵩焘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与他本人的特殊条件有关。他出身于书香门第,19岁中举,29岁中进士、点翰林,自幼熟读传统儒家典籍,中学功底深厚,又曾投笔从戎,与太平军对垒,做过封疆大吏,又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所以他的经历、见识就非常人可比,就连被尊为封建士大夫典范的曾国藩也称他“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34)他是二品兵部侍郎,曾做过巡扶,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和郑观应等人是无法同他相比的;虽然林则徐的地位略高于他,但林则徐的思想没有他那么系统,在文化上的建树也不多。由于他完全是按照封建社会入仕的程式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上层的,所以亲朋故旧、学友师长、姻亲乡党遍布统治阶级各个方面,朋僚中有推举他的,也有诋毁他的。在清末半个世纪中的著名人物大多与他相熟,曾国藩、江忠源、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一大批朋僚,也有李鸿藻、刘锡鸿等敌手。他的学识、身份和社交等为他提供了施展文化影响的客观条件。
从主观方面看,郭嵩焘在认定自己的主意后,敢说敢为,不怕人们议论讥讽。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35)他立志学习西方的决心是坚定的,向西方寻求真理,“所以狂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非无端自取其声名而毁灭之以为快也”。(36)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觉得“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声,谁复能举其姓名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37)这正是他敢言敢为的内心思想。
郭嵩焘主张“利民”,要求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革;要求改革旧的文化教育内容,提倡学以致用,为近代教育改革之先声,都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进步呼声,成为从士大夫转变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38)他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人、身体力行的先驱者,梁启超称他与魏源等人是中国“最能了解西学”的人。(39)郭嵩焘作为率先到西方寻求文化良药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西学东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②《玉池老人自述》。
③《曾惠敏公遗集·使西日记》。
④⑤(15)《使西纪程》。
⑥(20)(24)(31)(33)(37)《养知书屋文集》。
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巳集。
⑧⑨(14)王闓运《湘绮楼日记》。
⑩(16)(2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11)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65页。
(12)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5页。
(1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11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08页。
(18)《曾文正公全集》卷29,第48页。
(19)《李文忠公全集》卷11,第7页。
(2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22)《筹洋刍议》第1,卷21页。
(23)《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26)(27)《洋务运动》(六)第212页,(一)第121页。
(28)(29)《郭嵩焘奏稿》第348页,第345页。
(30)《郭嵩焘日记》第3册,第393-394页。
(32)《条议海防事宜》《洋务运动》(一)。
(34)《曾文正公书札》卷18。
(35)(36)《郭筠仙手札》。
(38)见钟叔河《走向世界》第194-205页。
(39)见熊月之《论郭嵩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