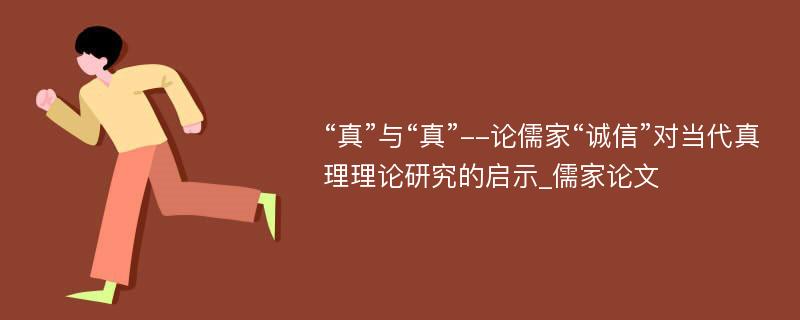
“诚”与“真”——论儒家之“诚”对当代真理论研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哲学设定主客二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相应的便有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的分离,以及真与诚的分离。现代思想家也认为真(true)不同于诚(honest),真被认为是命题或命题体系的属性,只有命题才有真假之分,而诚是人的德性。现代哲学用分析的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也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其中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以及真与诚的分离,便使人们误以为,人类只需在征服自然时遵循自然规律,人类的道德实践与自然规律无关,只要不伤害人,你怎么行动都行,但你若想取得征服自然的成功,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存在什么道德上的“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在现代思想的指引下,人类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终于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各民族国家毫无节制地争强斗富,军备竞赛无法控制,于是人类走不出核战争的阴影。现代哲学是有严重错误的,为克服现代哲学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真与诚的分离,发掘儒家之“诚”的深刻涵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在儒家学说中,“诚”并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诚”也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中庸》有言:“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又言:“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验于外)。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张子云:“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王夫之诠释道:“不妄者,气之清通,天之诚也”[1] (P5)张子又云:“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诚,故信;无私,故威。”王夫之解释道:“气无妄动,理之诚也,无妄,信也”[2] (P51-52)。
据王国维看,古代儒家最初没有什么哲学[3],“孔子教人,言道德,言政治,而无一语及于哲学”。“独《中庸》一书......为诸儒哲学之根柢。”《中庸》为子思所作,孔子不言哲学,子思为什么要谈哲学呢?王国维认为,“《中庸》之作,子思所不得已也。”在子思的时代,除孔子学说之外,谈道德政治的还有老子和墨子的学说。王国维认为,“夫老氏道德政治之原理,可以二语蔽之曰:‘虚’与‘静’是已。今执老子而问以人何以当虚当静,则彼将应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此虚且静者,老子谓之曰‘道’,……由是其道德政治之说,不为无据矣。墨子道德政治上之原理,可以二语蔽之:曰‘爱’也,‘利’也。今试执墨子而问以人何以当爱当利,则彼将应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又曰:‘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则其道德政治之说,不为无据矣。”老子说虚静,诉诸天之本体,墨子说爱利,诉诸天之意志,都是为其道德政治学说寻求哲学依据。孔子的道德政治学说似可简括为仁义。“今试问孔子以人何以当仁当义,孔子固将由人事上解释之。若求其解释于人事之外,岂独由孔子之立脚地所不能哉,抑亦其所不欲也。若子思则生老子、墨子后,比较他家之说,而惧乃祖之教之无根据也,遂进而哲学以固孔子道德政治之说。今使问子思以人何以当诚其身,则彼将应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可见,《中庸》“视诚为宇宙人生之根本”,“周子之言‘太极’,张子之言‘太虚’,程子、朱子之言‘理’,皆视为宇宙人生之根本,与《中庸》之言‘诚’无异”[4] (P124-126)。可见,在中国儒家思想中,“诚”也是个本体论范畴,诚不仅是人之德,也是天地之德。
但中国儒学认为人可以同天,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5],即“与天地并立为三也”[6] (P40)。此一见解与西方基督教思想殊异。基督教认为,人是有限的,甚至是“可怜的罪犯”,因为人生来就是有罪(原罪)的。在基督教的思想框架中,上帝是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人不能仅凭自身而获救,人必须虔诚地信仰上帝,然后才可能获救。上帝是绝对超越于人之上的,是万物的创造者(Creator)。在儒家的思想中,没有终极实在的地位。“道”或“天命”似乎是终极实在,但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 朱熹诠释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8] (P182)。所以,在儒家看来,并没有什么绝对超越于人之上的终极实在。正因为如此,儒家并不特别强调人应该敬畏什么[9],而基督教特别强调人必须敬畏上帝。
儒家并没有在概念上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不重视人的主体性。说“人能弘道”实乃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实际上,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主体性不可同日而语。基督教关于终极实在的思想是值得继承的,只是不必把终极实在理解为人格神。终极实在就是大自然[10]。人能通过倾听自然的言说而得到一点局部真理,但永远不可能把握绝对真理,即大自然的全部奥秘,只有作为绝对主体的大自然才掌握着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是人类的信仰对象,而不是人类的认知对象。儒家无法体认终极实在的存在,这是儒家的弱点。但儒家讲“人能弘道”总是强调道德方面多,强调认知方面少,即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和实际追求中,善始终优先于真,“格物致知”是为了“正心诚意”,为了“修身”,为了“明明德”[11]。现代性则不然,它在宣称“上帝死了”之后,却把人类凸显为上帝,现代人认识自然是为了指挥自然(培根)。现代性的一个愚蠢错误是把自然的全部奥秘当作人类的认知对象,现代人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自然之未知领域会日趋萎缩,从而,人类越来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但实际上自然永远隐匿着无穷奥秘[12]。
二
现代性把知识探究摆在最重要的地位,即真优先于善(以及美),正因为如此,真理论(theory of truth)是现代哲学最重要的部分。语言哲学曾被认为是关于语言意义的哲学,但研究语言的意义离不开真理论。
可把现代真理论分为三种: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
符合论认为,真理就是与独立于观念的实在相符合的观念或观念体系。所以,真(true)是命题或命题集合的属性,而不是实在或实体的属性。符合论源远流长。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代表着真理符合论的最精致的表述,维氏试图通过明确原子命题与原子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去反映事件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后来放弃了符合论立场,这似乎意味着符合论的最终失败(普特南就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符合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类毕竟面对着外部世界,而不能封闭于自己的观念世界,人不能认为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只取决于自己的想法,人的思想对不对确实依赖于它与外部世界中的事物的对应关系。但符合论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思维中产生的观念或符号何以能与非观念的实在相符合?如论者所说,不同的符合论版本都面临着说明符合关系之本质的严重困难,这包括并不存在观念与实在之间的结构相似性[13] (P39)。
融贯论认为真理就是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从而认为真是命题集合的属性。在很强的意义上说一个体系是内在一致的,即指它所包含的命题不但不彼此矛盾,而且能彼此辩护。例如,一个体系包含命题A、B、C、D……Y、Z,由A可推导出B,由B可推导出C,由C可推导出D,……由Y可推导出Z,由Z又可推导出A,则说该体系是融贯的,或内在一致的。歌德尔定理指出,对任何包含自然数系的相容(彼此矛盾的陈述不同时为公设集所包含)形式体系F,都存在F中的不可判定命题,即存在F中的命题S,使得S和非S都不是在F中可证明的。这表明,不可能有以上所说的很强意义上的融贯的理论。但融贯论可退一步:只要求公设集中没有彼此矛盾的命题。根据融贯论,一个信念或命题之真假依赖于它能否与一个信念或命题体系相一致,你无法断定单个信念或命题的真假[14] (P15)。可见,融贯论坚持整体主义,认为真理与意义都只能在一个符号体系(整体)中得以显现,这是融贯论正确的方面。但融贯论若坚决抵制符合论,便解决不了如何走出主观世界的问题。我们可构造许多逻辑体系,其公设集都不包含彼此矛盾的命题,但不意味着它们都是真理。
实用论认为,有用的信念或理论就是真理。说一种信念或理论是有用的,即指,如果我们按照该信念或理论去行动(实践),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原子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重元素发生裂变,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根据这一原理人们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成功地建造了核电站,这便表明这一原理是真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都是这种真理观的鼓吹者。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都持实用论立场。其中罗蒂的实用主义立场最为鲜明。罗蒂曾说:“实用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件事对实践是无意义的,那它对哲学也将是无意义的。”[15] (P243)罗蒂认为,思想观念或理论不过就是我们用语言发展社会合作项目以适应环境的工具。“真的”就相当于“确定的”,这两个语词都可与“在我信念中的”替换着使用[16] (P263)。当代实用主义真理论都与融贯论兼容,都认为“命题态度之间的融贯是对真理的唯一检验”[17] (P265)。但实用论者坚决反对符合论。
其实这三种真理论各有其合理之处,但又各有其弊端。融贯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无法摆脱主观主义,这一点无须多论。符合论认为真理涉及我们的思想观念与外部事物的关系,我们的思想观念是否为真,依赖于它是否与外部事物相吻合。这是很健全的思想。但实用论把这一思想彻底摒弃了。正因为如此,实用论走不出主观主义的泥坑。但符合论若顽固坚持僵硬的主客二分以及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蕴含着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的二分以及真与诚的二分),并认为人类知识总体可日益达到与宇宙一切奥秘的符合,那么它就确实是必须摒弃的立场。
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反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符合论的反驳。普特南的成功之处在于:一、用整体主义语义学论证了事实与价值的相互渗透[18] (P135-136);二、用指称的不确定性论证了人类不可能用一个真理体系去反映宇宙的一切奥秘,即人类不可能拥有“上帝之眼”[19] (P1-74);三、正因为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的,所以,描述与评价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所以,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或主观性)与哲学伦理学的客观性(或主观性)只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即,并非只有物理学一类的科学才提供客观知识,而伦理学只是纯粹主观的表达[20] (P126-149)。在普特南的哲学体系中,或一般地,在当代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价值与事实、价值与真理已能够互相融合。但由于新实用主义在拒斥符合论时过于独断,并一再坚持无论是事实还是价值、无论是描述还是评价,都只是我们观念体系内部的事情,认为,“世界是由什么客体构成的?”这个问题只有在一种理论或描述内部被问及才是有意义的[21] (P49),所以,新实用主义摆脱不了主观主义的束缚。新实用主义者认为,价值和事实都有客观性,但他们所说的客观性,不是独立于人的思维框架的客观性,而只是在特定理论内部的合理性或合理可接受性[22] (P135-139)。然而,普特南等新实用主义者毕竟沟通了事实与价值,从而为沟通真与诚扫除了障碍。如何保留新实用主义者的成果而又走出他们所走不出的主观主义迷宫(新实用主义者也不想走出这个迷宫),是个非常值得尝试的哲学努力方向。
在20世纪的真理论中,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真理论独树一帜。它具有融贯论的倾向,但不同于融贯论;它强烈排斥符合论,但又力图避免主观主义;它与普特南等人的新实用主义有共同立场,但决不接受实用论的表述方式。
海德格尔是一位喜欢做词源学考据的哲学家。据他考据,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儿,aletheia(现译为“真理”)的意思是“非隐藏性”(unhiddenness),这便向我们透露了关于真理本质的某种实质性的东西[23] (P56)。海德格尔不认为“真理”只是个认识论范畴,还认为它是个本体论范畴。在海德格尔看来,本体论的真理(ontological truth)涉及“去蔽”(unveiling)的有效性,去蔽则是先行的本体态度模式。所以,“这种去蔽就是存在的真理(the truth of Being),亦即本体论的真理”[24] (P59)。
海德格尔说,真理的本质是自由。真理表现为一个关系性的过程(relational process)。它涉及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以及基于敏感性和对其他存在者(beings)以及对存在(Being)之不同模式之开放性的有限立场的妥协。自由与在一个开放领域中的开放的东西密切相关,自由就是让存在者是其所是,于是,“自由就把自己展示为让存在者存在(letting beings be)。”不可把自由归结为自我主张的行动和压迫他者的控制[25] (P60)。“考虑到自由是真理的本质,则自由的本质就把自身展现为对存在者之显现(the disclosedness)的展示。”[26] (P62)
海德格尔既不认为真理是观念与自在之物的符合,也不认为真理是主体的创造,而认为真理是一种显现的关系过程(the relational processes of disclosure)。在这种关系过程中,实在的不同方面便持续不断地通过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而得以显现。这便意味着人所经历到的真理永远是未完成的或非封闭的,这也意味着在任何显现中总有“隐而未显的”因素。在任何有限的真理经历中,都据守着非真理(untruth),所以,“此在同时原初地生存于真理和非真理之中。”[27] (P63)
当海德格尔说在任何人类对真理的经历中都存在着非真理的维度时,他表达了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让在(letting-be)让存在者(beings)以特定姿态存在,即与它们发生关联,因而揭示它们,但它也隐藏着作为整体的存在者(beings as a whole)。让在同时内在地是一种隐藏。在此,非真理与据守在任何揭示中的隐藏相连,因为它就是隐藏的部分必然本性(the necessarily partial nature)。海德格尔并不认为,真理只能在“整体”中被发现,他只是强调真理就是不断进行着的过程。我们不能一劳永逸、一览无余地把握事物,因为总存在能唤起进一步揭示的不同视角和解释框架。我们遇见的或和我们相遇的任何存在者都保持着奇妙的对显现的抵制,即总是同时以隐藏的方式坚守自己。真理并不表现为事物立即呈现的确定性,因为这种虚幻的确定性总会固守于理解的一个具体的本体模式(a specific ontic mode)。所以,即使是对一种现象的有效解释也不是最终完成了的,不是绝对确定的。真理只能存在于持续不断的探究之中,真理永远是开放的。
另一层含义是,事物常常“以非其所是的方式呈现自己”。海德格尔把上述第一种意义的非真理称作“尚未显现的”,而把第二种意义的非真理称作虚假的呈现,或“掩饰”(das Verstellen)。对据守着的隐藏的自觉能起到对有限的显现形式保持批判关系的作用,即有此自觉我们就会不断审视已达到的理解,以便促进存在者进一步的显现[28] (P63-64)。
海德格尔用晦涩的语言表达了极为深刻的哲理。可把海德格尔关于真理的思想概括如下:(一)真理就是存在者的显现,“真理”并不只是一个认识论范畴,它也是个本体论范畴,真理是一个关系性的过程,而不是当下的认知确定性;(二)真理的本质是自由,是让存在者存在。这一思想是对现代性的尖锐批判。长期以来,哲学家们认为,真理就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自培根以来,人们认为,人类认识真理是为了控制自然。海德格尔关于真理的本质是自由的思想与这种征服自然的真理观是针锋相对的。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比新实用主义者高明。海德格尔对自由的界定也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自由既不是在个人权利领域的任意行事,也不是自我做主,而是让存在者存在,这与中国哲人(儒家和道家)所追求的境界极为相似,或说,海德格尔的“自由”就是“境界”,相当于王夫之所说的“与时偕行而无所执”[29] (P115)(三)真理与非真理是内在的相连的,人类对任何存在者的认识都达不到一览无余的程度,即人类对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永远是未完成的,事物对人类永远是有所隐匿的。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现代性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未为人知的奥秘日益减少。时下许多人认为,人体基因组的揭秘就标志着人类对上帝创世之最后奥秘的把握,这一信念就典型地反映着现代人觊觎上帝智慧的心态。据海德格尔看来,这是极其疯狂的心态。
三
综合儒家关于“诚”的思想、普特南关于事实与价值的思想和海德格尔关于真理的思想,我们可认真清理现代性关于道德、价值、事实、真理和自然规律的错误。
如果我们认为真理是存在或存在者的本真显现,则真并不仅是命题的属性,也是事物的属性,真理(truth)与真实性(reality)、真(true)与真实(real)密不可分。诚正体现着二者的统一。诚乃天地之德,即自然之德。如王夫之所言:“诚者,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30] (P116)也可以说存在者以是其所是的方式显现自身就是存在者的诚。诚既然是“天理之实然”,也便是道德之本体,即道德规范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在人类所认识和体认到的知识中,道德规范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人才能顺天地之德。现代人将道德与自然知识截然分开,在“真”与“诚”之间划出了一道界线。认为对自然事物,只存在如何认知、如何控制的问题,人是认知者、控制者,而自然事物只是被认知和控制的客体。人类如果发现了关于自然事物的真理,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自然事物。诚只是人在人际交往中需要表现的德性。人对自然事物不再有诚,即现代人不再追求天德。在现代性的框架中,“真”优先于“善”,即知识追求优先于道德追求,而且知识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道德约束,即无论对自然事物怎么运用我们的知识,无论是进行核试验,还是在大江大河上建电站,还是制造转基因食品,都与道德无关。人拥有的“真理”越多,其征服自然物的能力就越强。但正因为真与诚分离了,知识应用失去了道德的约束,所以现代人的征服力越强就越是置自己于险境。现代人用科学所发现的真理去征服自然,非但未创造出人间天堂,反而深陷生态危机,就因为违背了天德。有违天德还自以为拥有真理,是为欺天(欺骗自然)而自欺。
人很难约束自己去做能够做的事情,除非自己坚定地认为那些能够做的事情是坏事情。“能够”表示认知和操作能及的范围,“应该”表示道德要求。人应该做的事必是他能够做的事,但人能够做的事未必都是应该做的。每个人都能够杀人,但每个人都不应该杀人。人若不受“应该”的约束,就会在其“能够”做的范围内无所不为。在中国儒学思想中,自然规律和道德规范是统一的,二者统一于“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31] 于是,道德上的“应该”牢牢地约束着认知和操作的“能够”,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在现代人看来,道德或者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或者是理性人的自我立法,当代最流行的看法则是,道德就是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契约。于是,道德的维系几乎全靠人际监督和制约。在违背道德能获利且能不被发觉的情况下,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违背道德。但中国儒家不认为道德只是人间的契约,而认为道德与天命是一致的,所以,遵守道德规范也就是顺应天命。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32] 朱熹解释道:“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也,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33] (P38)所以,人的道德实践体现为“畏天命”[34],“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倾也。”[35] (P24)
但在现代性的思想框架中,人对自然事物所“能够”做的事已公然脱离了“应该”的束缚,人道与天道已截然分离,现代人已只知科学真理而不知“天命”。于是,现代人在征服自然时毫无忌惮,在人类共同体内部也不再“慎独”。
从现代性的立场看,儒家的这种思想似乎只是缺乏分析的糊涂观念。其实不然。自然规律与道德规范的分离以及真与诚的分离是现代性的许多病症的根源。这些现代性的病症包括人的道德自律水平的降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以及挥之不去的核战争阴影。为医治这些病症,我们需要把道德奠定在真理的基础上,需要把真与诚统一起来。这样的真理须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本体论的真理。
强调本体论的真理的重要性,不意味着必须全然抛弃认识论真理概念。认识和理解毕竟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对于人来说,真诚是发现真理(认识论的)的必要条件。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追求真理的真诚,而一味醉心于金钱、荣誉和地位,他便可能捏造实验数据、夸大自己研究成果的价值、剽窃他人成果。现代哲学解释学也强调真诚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在不可避免地继续游戏传递给我们的东西时更加诚实、更加仔细”[36] (P18)。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也认为真诚是发现真理的必要条件,他说:“有深度的自由思想并不陷于主观主义。”又说:“真诚的意志必然与真理的意志一样坚定。只有具有真诚勇气的时代,才能够掌握作为精神动力在其中起作用的真理。真诚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他在批评现代文明时说:“由于贬低思想,我们这代人已失去对真诚的信念,并由此也失去了对真理的信念。”[37] (P124)这一批评已切中现代性的要害!
本体论的真理是个不断持续的关系过程。海德格尔不愿再使用“主体”、“客体”、“主体性”等概念,所以其表述极其晦涩。如果我们认为主体性和客观性都是可以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且不仅人具有主体性,非人存在者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38],那么,就仍可以沿用“主体”、“客体”、“主体性”等概念。这样,说真理是个关系过程,即指真理就体现为主体间的持续不断的交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主体(存在者)以不同的方式显现自己。每个人在对话交流中的全力倾听和真诚表达都是对局部真理的贡献。谦虚的倾听不仅指倾听他人的表达,还包括叩问自然,即细心的观察,艰苦的思考,小心的验证,这是发现局部真理的条件之一。认识论的真理就是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主体)通过倾听和理解而获得的对其他存在者(主体)的认识,这种认识通过语言而表述为命题,它只是本体论真理的一个维度。人的真诚言说,是人际交流局部真理以达成共识的一个必要条件。自我意识的明晰性和自我的确信只是真理探究的必要条件,不是真理的标准,人际共识只是共识可能为真的条件,而不是确证真理的充分条件。例如,“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是当今人类的共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个真命题,但历史将证明它不是真的[39]。实践的成功只是知识效用的验证,它表明理论可能为真,而不能证明理论就是真理。验证真理须有自然事物的本真显现,需要人在自己的表达与自然物的本真显现(真诚言说)之间进行比较。个人的认识不仅要印证于他人,还要印证于非人主体。一般来讲,要想使人类认识具有真理性,就必须印证于非人主体。真理符合论对于阐明局部真理仍然适用(但没有绝对清楚的符合论)。
对人的真诚的检验需要符合论。一个人可以不断宣称自己是真诚的,可实际上他很虚伪。如何检验呢?我们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只能“听其言,观其行”,即看他的行动与其言论是否一致,即检验他是否总是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便需要符合论。没有符合论,我们便无法判别一个人是否真诚。坚持了局部的符合论,我们才能走出主观主义的陷阱。就此而言,个人的真诚不是获取局部真理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我们对非人存在者的认识是否为真,依赖于我们的认识是否与它们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一个人可能固执地、真诚地认为自己建构的理论体系是绝对真理,今天我们可在现实中发现这种人,如《多四季论》、《统一论》[40] 的作者,他们的理论可能有价值,但得不到多少人的承认,也不可能是绝对真理。
局部真理(认识论的)不能体现为个别语句或命题,须是一个体系,但人类建立不了将所有知识都囊括在内的内在一致的体系,我们只好表达不同的多样的体系[41] (P218-219)。局部真理是处于不断修正过程中的。逻辑融贯是局部真理表达的内在要求,更是人际交流的必要条件。人所能认识的真理是不断生长的,真理的生长既表现为纠正错误,又表现为内容增加。每一个真理求索者都努力扩展自己的视野,扩展自己体认的真理内容,努力理解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整体。真理求索者不能只在某一个方面做越来越细的分析,还必须整合越来越大的体系。例如,我们不能只理解我们在城市的境况,还必须理解我们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境况,在太阳系中的境况,在宇宙中的境况。我们所能拥有的真理体系的扩大,意味着我们视野的扩大。有尽可能宽广的视野,我们才能较为正确地确定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但人类绝不可能把握自然的一切奥秘,因为任何存在者在显现的同时都有所隐藏,更不用说作为“存在之大全”的自然。
每个人都可以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愿望,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发现和体验,真实地描述自己的实际行为。如果人与人之间有真诚,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人的真实愿望、发现和体验。所以,只要有诚,我们就能发现局部真理,就较容易达成共识。若从纯逻辑的角度探究真理,我们就容易陷入极端怀疑主义而否认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就容易否认了解他人之心(other's mind)的可能性。真理论须有个伦理维度才能避免极端怀疑主义。即“真理”不仅是个本体论概念,还应该是个伦理学概念。人对真理的追求,应体现为真与善的统一。现代性的错误之一是认为真(纯认识论的)优先于善。当“真理”不再仅是个认识论范畴时,对真理的追求就内在地包含着对善和美的追求。当纯粹认识论的“真”受“善”和“美”的指引时,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才不会违背天德,从而不会因为追求真理而陷入险境。
标签:儒家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读书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本体论论文; 普特南论文; 中庸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