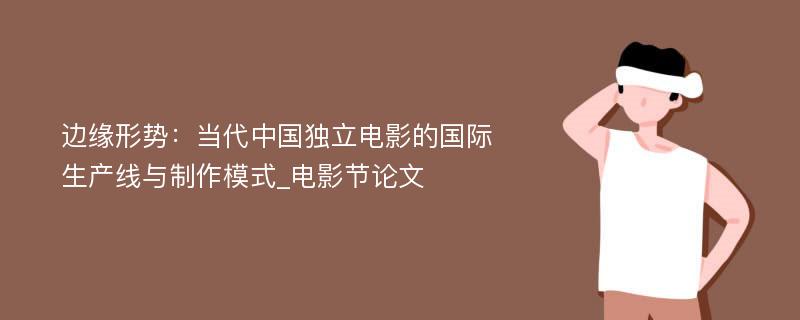
边缘的境遇:当代中国独立电影的国际线路和制作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边缘论文,独立论文,线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11)10-0117-05
美国独立电影专家克里斯汀·瓦其奥认为:独立电影确实具有另类的、原创的想象,但是,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独立电影。[1]16也就是说,不仅是独立电影,即便是“个人电影”,①也总还是有经济问题存在于其中:它们要得到更多的承认,就必须进入市场,而且必须有人想要看到它们。因此,从产业的层面看,中国独立电影,要么以超低成本或几乎“无成本”的制作方式自足地存在,要么以靠近体制并与体制达成协议运作于主流商业电影的边缘;它们通常以16mm胶片或数字视频甚至家用录像机的方式拍摄,影像粗糙;它们的制作团体,或者小至一两个人(比如应亮),或者是一个家庭(比如刘伽茵),或者是一帮朋友(比如早期的贾樟柯),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跨国团体(比如后期的贾樟柯,王超),总而言之,其形态多种多样而且灵活多变。或许,我们应该把独立电影理解为包含了一系列处于主流电影之外的、以小成本为主的、具有自主精神和探索精神的电影模式。中国独立电影虽然已经成为电影人、理论和批评以及传媒关注并标榜的电影事实的一部分,但是,要非常清楚地从经济和制作模式方面得到探讨却非常困难。而且,这些独立电影也总是通过国际电影节的获奖而进入人们视野的。此外,我们还要明确地涉及独立电影与体制的复杂关系。首先,我要试图说明独立电影与国际电影的关系;其次,我需要再一次把独立电影与体制的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并进一步区分出1990年代以来独立电影在经济依存和体制依存关系上的三种可能形态。
当代中国独立电影与国际电影节
毫无疑问,电影节在中国新电影和世界电影版图之间建立了一种必要的联系和一条必要的道路。从第五代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到后来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所谓第六代导演,以及新近的刘伽茵、应亮、彭韬等,这些电影人都通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各种奖项而被识别为艺术电影作者开始引人注目。而且,通过在国际电影节的成功,他们的作品也找到了西方的发行商并进入了西方的某些电影院线。但是,正如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的成功引发了对其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批评,作为后来者的这些导演也因为屡屡在国际电影节亮相却不能于国内现身而受到将贩卖中国的贫穷落后的现实的指责。然而,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
在电影制作者、西方接收者和中国观众之间存在着对“中国”想象的分裂,突出了西方电影节作为一种多层面文化机制,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既对中国电影的美学层面也对商业层面发生作用。
自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早期,伴随着中国政府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的持续性,中国的文化想象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这种复杂的改变也发生在电影产业之中。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以及制片体系的衰退,年轻的电影制作者既面临着体制内的挑战也面临着体制外的挑战。作为电影学院毕业生,很少有人再有机会能进入国有电影制片厂工作。因此,作为独立电影制作者,他们在职业生涯的起点上与西方的独立电影制作人并无多少区别。对他们来说,电影节之旅为他们作品的发行以及他们未来项目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渠道。其次,1990年以来的独立电影人与他们的前驱者完全不同,他们专注于描述城市生活的日常经验、城市生活的流动性以及各式各样的居民群体。这些电影的主题或许是相当富于争议的,但他们的制作模式却是非常明显的,至少在1990年代早期是如此:独立的和“非法的”。这些“地下电影”的发行和流通只能借助于国际电影节,这与他们在国内被禁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确切地说,这体现出早期当代中国独立电影所遭遇的困境。
正如国际电影节循环把第五代电影的某些作品建构为“经典”,同样明显的经典化行为也体现在新一代的独立电影作品上面。来自国际电影节的赞赏使得这些独立电影作品声称要承担的“现实主义精神”被凸现出来。这也使得这些作品逐渐进入理论研究和历史书写的视野,从而再一次得以“经典化”。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白,电影节的选片标准尽管不是固定不变的,但也确实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浸透了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视野的框架。因此,1990年代初期,这些“地下电影”的制作者,很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是反体制的异议分子。但是,更复杂的政治信息应该在电影文本中得到考察,同时也应该从它们的独立/地下的制作实践上得到考察。对于这些独立/地下电影的制作者来说,西方国际电影节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总而言之,独立电影作品在西方电影节上的流行,可以从作品的经典化渠道和商业渠道方面得到更多解释,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电影节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在中国电影的产值和行销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因而,在这里,我们需要对电影节本身的问题稍做探讨。
按照简尼特·哈波德的说法,电影节是一个交叉着商业利益诉求、特定文化信息以及旅游游览线路的混合空间。[2]60同时,电影节对于很多外部人士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当谈到诸如戛纳、柏林、威尼斯以及多伦多电影节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红地毯,大明星,天才的电影人以及独具特色的杰作,而选择过程的潜在机制、一部电影在收获欢呼和奖励之后最终所能到达的目的地,却依然处于迷雾之中。但是,随着电影节数量在各地不断地增长,电影节以及选片程序怎样影响全球电影文化、电影节主办城市的生活以及个别电影和电影人的成功等问题,必须得到严肃地考虑。哈波德认为,在电影节的疆域之内,有四种话语交织在一起。其一,流通于目录、新闻稿件、访谈和其他文本中的独立电影制作者和制片人话语;其二,媒介传送话语,特别是新闻话语,它们对事件、讨论、展出以及“新闻”做出评论;其三,是交易、价格和版权方面的商业话语,它存在于合法交易和合同文本中,存在于口头讨论以及贸易新闻中……第四,是旅游业和服务业、本地新闻、广告和导游手册等等话语,它们把电影话语和本地话语交织起来。[2]60这四种话语有效地构成了电影节的实质,很显然,媒体报道和资本流动促进了这些话语的交织。更重要的是,这个趋势表明,电影仅仅是另一类型的商品而已。电影节,就像电影艺术本身一样,总是体现出相互缠绕的利益冲突——“商业对艺术,价格对魅力”,很显然这复制了存在于经济与文化、日常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一种历史性的分裂。另一方面,哈波德也指出:电影节作为一种特殊的、热闹的、短暂的事件,也通过它的奖励程式,生产出某些期待,创造出一种对于特定知识的管制。[2]69如果一部电影赢得了某种奖励,那么它就可能赢得了某种象征资本,这些象征资本也会通过逐渐累加的方式转变为真正的资本。
很明显,电影节对于民族电影中经典作品序列的形成已经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电影经典序列的建立和某部电影被排斥于经典序列之外,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机制。在《电影经典化的政治》一文中,珍妮特·斯泰格仔细考察并区分了这一过程主要的方面以及它所包含基本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引起批评和电影学术界的注意,被纳入到电影历史书写之中。此外,她还讨论了“选择的政治”如何与价值、艺术以及被认定为既成经典的样本作品等各种各样的话语展开交战。[3]那些话语提醒我们想到电影节的四种话语。因此,理兹·扎克做出了这样的结论:经典化过程的选择结果,有时候强烈地回应着电影节选片程序中暗含的种种评价标准。[4]然而,当涉及某部具体的电影作品时,经典制造者和经典分析者可能持有相互冲突的意见,什么电影应该被纳入或被排斥,凸现出潜在话语的多重性以及选择标准的流变性。实际上,电影节的选择标准也不是持久不变的,年复一年总是要做出某些调整。也就是说,电影经典化的合法性和品味制造者的权威性,不能由于忽略那种固定不变的方面以及这种文化过程的特定历史条件而被随意地破坏。因此,“尽管电影经典化过程与它的排它性政治本质问题多多,但它们仍然是一种评价民族电影的重要工具”。[4]进入电影节,特别是被明确地放入到竞赛单元,也是促进和巩固民族电影文化场域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资本具有多种形式,不仅有作为物质交换的经济资本,还有文化和象征资本。对布尔迪厄来说,文化价值是通过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艺术家活动于其中的那个场域中的代理人而被创造出来的。在一个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化价值是某些社会机构(比如学院,学术出版物,图书馆,博物馆或资料馆等)的产品,这些机构有权力区分好作品和坏作品,并能将它们所认可的好作品编写进教科书或放入历史书写之中。[5]借助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理兹·扎克使用“批评资本”这一术语来指称“一部电影通过电影节传播和流通上的成功所增加的价值”。她写道,“通过作为品味制造者的选片人和批评家的赞颂,一部电影就能得到一种远在于其同时期未能入选的作品之上的声誉”,其结果当然是更容易在作为经典序列部分的民族电影中“找到它在历史中的位置”。此外,批评资本可能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票房和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它依赖于“电影节的地位,在那里,它被放映,被批评家评论,它得到了回应”。[6]而且,正如理兹·扎克所言,一部电影在一个有声望的电影节的目录中的位置,也有助于它的批评资本的增加。王小帅的《青红》被选入第58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而且,最终获得了评委会大奖,这很显然增加了王小帅在民族电影历史中的地位。在2001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之后,王小帅就已经被认为是新一代中国电影人中最具潜力的作者之一。对于戛纳,他并不是陌生人,他的《扁担姑娘》(1998)和《二弟》也曾被选入戛纳的“一种注目”单元。这一次,他的提名不仅显示出他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也有助于增加整个“第六代”的批评资本。基于这些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的成功,批评家和发行商也开始对年轻的导演有了更多的注意力,甚至也对他们之前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就当代中国独立电影中的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曾参加过或大或小的国际电影节这一事实可以看到,国际电影节对于这些电影的重要性绝对不能被低估,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这些电影是用来讨好外国人,是专门拍给外国人看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电影通过国际电影节找到了一定数量的观众并有可能赢得新的投资,而这正是正常电影文化循环的必要条件。
正如张英进在《神话背后:国际电影节和中国电影》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较为深入的分析:“西方国际电影节的影响首先决定了什么样的电影可能在西方的艺术院线发行和放映,因此也决定了西方观众可能接触到的中国电影的形象……国际电影节不仅牵涉到西方的发行和放映与中国的民俗电影生产,还培养了(或至少影响了)西方观众的观赏趣味。据美国学者比尔·尼科尔斯分析,西方电影节的大部分观众是他那样的中产阶级的白人,他们或像民俗学家一样亲临异域文化,或像旅游者探索奇山异水,通过电影想象性地经历了当地人的生活。尼克斯指明了电影节观众所经历的两种主要的‘发现’:一是让某位新导演一举成名的‘成熟的艺术’,二是与好莱坞迥然不同的‘鲜明的民族文化’”。然而,作为批评家,比尔·尼科尔斯注意到这类“发现”的可疑性,“因为西方观众在对异域文化无知的情况下,只能相信当地人主动提供的文化艺术信息的真实性。换言之,‘民族化’的电影愿意提供新异的民俗文化影像,而西方电影节观众又乐于接受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影像神话。对西方观众来说,关注国际电影节不是一种纯娱乐,而是一种人文关怀,一种艺术游览,更是自我优越感的再次确认。”[7]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电影节对当代中国独立电影节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应为过。正如张英进在他的文章最后所分析的,西方电影节对中国电影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某部电影的获奖不一定就意味这部电影代表了某一国家和民族,“民族寓言”只能是一种读解作品的方式,而非该电影全部的含义;其次,某部电影获奖,只代表电影节评审团当年推选的最佳,而并不代表某种一成不变的美学标准,而且,意识形态的因素经常会影响评审结果;再者,国际电影节奖的确也是艺术片在海外商业发行的主要渠道,而这一渠道对流通的商品有相当单一的政治、艺术趣味取向。这意味着艺术与商业在国际电影节里有着不可避免的共谋关系;最后,也是国内批评者最容易忽视的,国际电影节奖仍然是确认导演新人或独特导演风格的最佳途径之一,因此,“为电影节拍片”很难成为指责新导演的理由。[7]
独立意识与制片规模:“体制”内外及其它
与电影节明确的关系相比,中国当代独立电影与体制的关系显得尤为复杂。正如绪论所述,美国独立电影是直接对应于好莱坞主流电影的,一般而言,当我们要说明独立电影究竟是什么情形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说明什么是主流电影。那么,中国当代的主流电影是什么呢?独立电影又是怎样通过与主流电影建立差异而凸显自己的状态和身份的呢?对应于独立电影在时间中的发展变化,主流电影也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风貌和样式。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主流电影划分为三种模式:主旋律电影,商业大片,新主流电影。
主旋律电影与中国的政治风向联系紧密,它不仅仅是一种电影形式,更是中国政治主体借以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一种重要媒介,其目的既非着重于电影形式风格的探索,也不考虑票房效应等商业因素。主旋律电影基本上都是国家投资或政府机关投资,主题集中于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及其丰功伟绩。“主旋律”在中国电影文化构成语境中与本文中所谈到的独立电影尽管在题材倾向上有时候或许会有某种叠合的可能,但是在主旨和情趣追求上却正好构成了相对的两极。当然,这里的相对并不是对立的意思,因为从中国独立电影的产生条件而言,中国独立电影的“独立性”尽管有自外于中国电影生产机制和生产语境的因素存在,但是其主要目的首先是在于实现自己拍摄电影的梦想,并借此进入相对广泛的大众视野,从而在电影生产场域和论说场域中获取一席之地。事实上,主旋律电影并不构成对独立电影任何方面的压力和遮蔽。
1995年之后,引进好莱坞大片成了中国电影文化场域中的一个大事件。在两个“基本”(“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原则的指导下,好莱坞电影再次进入中国,并因此引发了对中国电影产业和商业价值及其走向的再度讨论,也引发了中国电影生产机制中的有生力量投入到商业大片制作中的潮流。从规模上讲,大片之大正好也是中国当代独立电影的对立面。一般而言,主流商业大片通过膨胀成本的方式制造电影的媒介事件效应,以高科技、大明星和国际范围的发行策略作为其风格结构的考量基准。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独立电影无论从投资规模、制作水准、生产条件及其制作目的和市场定位都倾向于小规模、低成本、粗画质的状况。而且,商业大片在商业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双重推力下占据了中国大面积的主流院线,并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尽管,2004年,也曾有两部由独立电影人生产制作的电影《青红》和《世界》进入到中国的院线系统中,其票房收入却不尽如人意,也因此而受到主力电影产业化评论话语的一定程度的否定性批评。然而,我们需要明白一点的是,中国当代独立电影,不管是投资大一点的,还是投资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其主要目标并不在于国内院线的放映。这些电影人也深知他们进入国内院线放映的困难所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瞄准的,都是国际电影节和国外的放映机会。
与独立电影一样,主流电影也是一个模糊和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中国电影层级结构中,除了像“主旋律”影片和商业大片这样一些我们可以直接指认为“主流电影”的电影之外,还存在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这就是所谓的“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制作模式是由上海青年电影人提出来的。马宁在《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一文中对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根据马宁的文章,“新主流电影”的成本范围是150-300万元人民币,立足大城市本土发行,直攻多厅影院,直攻某种层次的观众,“借助于新观众群的求变的各个“新主流电影”的提出,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理想,而是与“纽约人”罗异领导的西安艺玛公司主导制作的电影作品密切相关。郝建将艺玛的产制方式称之为“体制内的独立制片”,他认为:“艺玛的作品特征是在意识形态和审查程序上是标准的体制内影片,而在资金运作上是完全的独立电影”。与此同时,郝建从风格上将这些作品总结为“削去一半的好莱坞”:方面,配合主流电的自我改良,而制造一种顺应新的观众口味的电影”。此外,“新主流电影不鼓吹艺术电影”,它“凭借想象力、新媒介特性和新类型的更加灵活的转换来制造理想的电影。它充分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哲理,把握中国观众特有的俚语状态,用中国文字习惯和现代背景中的兴趣对本国观众作直接传达,以期获得电影自身的优势”。“新主流电影”以小规模制作为“电影提供灵活性”,“关心信息时代的普遍变化”,并“作为一种补充,将在体制内完成电影的模式修建工作”。总而言之,“新主流电影”能为中国电影格局带来新的变化,为观众提供一种“想象力电影”。[8]
罗异的西安艺玛公司的作品以常规化的电影语言,带着冲突引人入胜的戏剧事件、流畅的剪接,亮丽时尚的影像,和讲述机巧、不失花哨的故事传达了比较温柔的现实主义联想。但摒弃了直面现实的思考和理想主义的责任感和理性追求。相比较与美国好莱坞的左翼主流和中国的另一些青年导演以及黄建新等人的影片可以看到他们在创作上以远离现实思考和底层关注而换得的平稳、和政治上保险。[9]
这种所谓“新主流电影”或“体制内的独立制片”,明显不同于我在本文中界定的“独立电影”。在我看来,艺玛公司的这些作品,正如马宁所言,是作为一种补充,以在体制内开拓新的可能的空间为主旨。我以为,它们依然是主流电影的一部分,与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起,与“独立电影”构成了中国电影格局中的四个不同层面。
然而,“体制内独立制片”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却给我们定位“独立电影”提供了新的启示和视点。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独立电影始终与体制有着复杂但是明确的关系,中国独立电影更多不是从资金运作上界定的,而是从与体制的关系加以界定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体制的问题出发,进一步把独立电影分为三类:体制内独立电影,体制外独立电影,“非体制”或与体制无关的独立电影。这样的分类也许有助于我们建立对中国当代独立电影的更为清晰的看法和认识。
体制内(in-system)独立电影:这一分类指的是那些徘徊在体制边缘并与其不断周旋的作品,大致可以包括三种情形在内的影片,第一种是在体制内生产制作,但因为各种原因却被当局施以禁令的电影,比如张艺谋导演的《活着》、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吕乐导演的《赵先生》以及章明的《巫山云雨》、陆学长导演的《长大成人》、管虎导演的《头发乱了》、娄烨的《苏州河》等等,第二种情况是在体制外制作,但力图进入体制内并获得体制认可的电影,比如张元的《妈妈》、贾樟柯的《站台》、《任逍遥》等,以及那些最终获得体制认可的作品,比如王小帅《青红》、贾樟柯的《世界》和《三峡好人》、王超的《江城夏日》等。
所谓“体制内独立电影”,既有体制内的电影人制作的电影,也有体制外电影人制作的体制内电影,我以为,这一分类能够比较准确地说明中国独立电影本身的复杂性和暧昧性。
体制外(out-system)独立电影是更为明确的、具有鲜明“独立意识”的独立电影,从制作一开始,这些电影的制作者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电影不可能与进入体制内得到体制的认可。这一类别中,比如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张元的《北京杂种》、贾樟柯的《小武》、王超的《安阳婴儿》、何建军的《邮差》以及崔子恩的几乎所有电影等等。
无关体制的(non-system)独立电影这一分类,是为了说明在DV技术或其它更为方便的拍摄技术出现之后,那些仅仅出于“想拍一部电影”而动手制作的电影,这些电影既没有打算进入体制,也没有任何违背体制的倾向,这些电影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的电影而存在着,流传着。这样的电影在1997年之后,数量变得多了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宁浩的《香火》、甘小二的《山清水秀》、刘伽茵的《牛皮》、应亮的《背鸭子的男孩》和《另一半》、李红旗的《好多大米》、蒋志的《香平丽》、彭韬的《血蝉》、王晶的《街口》等等以及绝大多数所谓“新纪录电影”和实验短片。
体制内、体制外、非体制的,这三种类别也不仅仅只是说明中国当代独立电影与体制关系的不断变迁,而且说明中国独立电影的“独立意识”在技术与社会环境的双重改变中明显地增强,以至于诸多电影制作者声称应该抛弃“独立电影”这一概念,而愿意接受“业余电影”或“个人电影”这样更加灵活、更加凸现制作者个性和个体影片特征的概念。这一分类也在暗中指涉了独立电影三种主要的投资模式:来自于体制内机构的投资、来自于民间商业团体或者国外赞助机构的投资以及个人自筹资金的投资。因为独立电影的资本规模和投资模式的极大差异,以及它们与“体制”所形成的不同关系,反映在影片风貌上,也更加灵活多变,丰富多彩。一些人强调进入国内院线的重要性,一些人特别强调个人性,还有一些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注释:
①“独立电影”和“个人电影”的定义参见拙作《1990年以来中国独立电影的形成、形式与意义》,北京电影学院硕士论文,2007年;亦请参考拙作《如何电影,怎样独立:问题与方法》,刊于《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