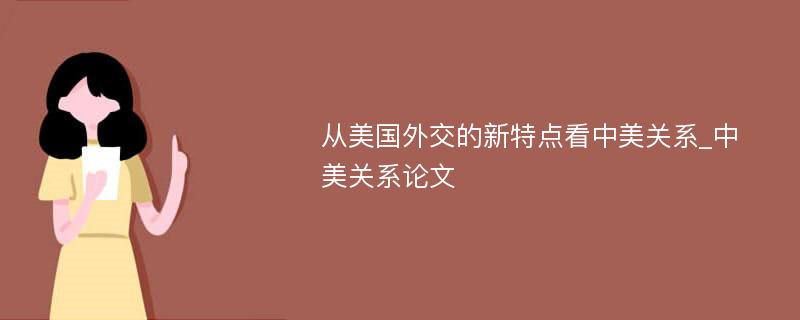
从美国外交新特点看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外交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1997年10月底至11月初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为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江主席访美的重要成果《中美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领导人对未来关系的一种规划。笔者曾就此写过短论,对这一提法的意义加以阐述。[1]其实,中美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本身, 就有利于两国之间逐步消除敌意,避免对抗。通过联合声明,美国政府事实上承诺了不因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寻求同中国的冲突,客观上对美国国内那种“美中冲突即将到来”和“必须遏制中国”的论调是一个打击。中美努力建立高层次、全方位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对国际上某些附和“中国威胁论”、企图借重美国以打击中国的势力,对于挟美自重的“台独”势力,也是一个牵制。从1989年6月中美关系严重恶化, 到克林顿邀请江主席访美,美国用了8年的时间才实现其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其间发生了多次对华政策思想的大辩论。我国国内研究者对此有过不少介绍和评论,这里毋庸赘言。本文强调的是,对华政策辩论的背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逐步定位以及外交思想的逐渐转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外交特点和政策思想变化的分析,展望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外交与内政密不可分
冷战结束近十年来,美国战略家和舆论界一直就全球战略问题争论不休。这场长期辩论的议题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美国在新时期的外交目标有哪些?如何确定其轻重缓急?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存在着经济、安全和人权这三大目标之间的竞争。第二,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世界事务?实行战略收缩是否可取?这是所谓“全球主义”同“新孤立主义”的辩论。第三,为达到美国的战略目标,应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这是所谓“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的问题。当然,这三方面议题是相互交错、难以严格划分的。
从这些年来美国的外交行为和政策思想辩论中,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的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内政和外交越来越密切的互动关系。克林顿在1992年首次竞选总统期间就强调:“在今日世界上,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密不可分。”[2]以后他又不断重复这一观点。 克林顿在为自己的外交行动辩护时说,如果美国不干涉海地局势,就无法遏止海地的难民潮涌入美国海岸;如果不向陷入金融危机的墨西哥提供紧急贷款,美国人就会面临更多的非法移民、失业和毒品走私的威胁。[3]
冷战结束后,加强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 在海外大力开拓商品和资本市场,保护美国商品的国内市场,打击走私贩毒,限制非法移民,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问题,都既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问题,也是其国内政策问题。越来越多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参与到对外事务中去,极力影响外交决策,形成外交决策机制的进一步分散化。与此相适应的是,国会在外交中的发言权增加。近年来中美关系摩擦不断,其中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是重要原因。美国宗教组织在政治上重新活跃起来,有人就攻击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对西藏的政策。美国在国际竞争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产生失业,贫富悬殊加剧,有人就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指责中国向美国倾销产品。1997年美国一些人制造“中国政治献金案”,某些影视公司发行反华影片,也是这方面的例子。从外交角度讲,中国当然有理由、有权利要求美国决策者从大局出发,排除这些干扰;但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外交所受到的国内制约只会越来越大,因此观察中美关系的视角必须放大,更多注意美国国内变化。
外交侧重点的转移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中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趋势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着眼点正在从国别关系和区域政策(如对东亚、拉美、中东等地区的政策)转向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保护能源供应、国际贸易和金融、移民、毒品走私等“功能性问题”(functional issues), 形成所谓“问题政治”(issue politics)。冷战时期美国对其它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以苏划线”,即根据他国在美苏全球争夺中的立场来决定美国对它们的态度。美国外交的主线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转移,提出了经济、安全、人权“三大外交支柱”,在处理地区事务和国别关系中更为注意上述具体功能性问题的解决,推进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在克林顿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宣言里,对功能性问题的论述大大多于对国别关系和地区问题的论述。
从近年来美国就对外关系问题所做的民意调查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外交问题功能化和“零碎化”的趋势。美国政治精英和一般公众都十分重视防止核武器扩散、保障能源供应、制止非法移民、打击贩毒、减少外贸赤字、保护环境和保护国内市场等问题,而把促进其它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援助发展中国家等置于外交目标的末尾。相比而言,政治精英更注重加强国防等所谓“高度政治”问题,而老百姓更为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毒品泛滥、非法移民和环境保护等所谓“低度政治”问题。[4]
美国外交这一新特点也强烈反映在对华政策中。近年来美国方面在军备控制、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贸易不平衡等功能性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有时不惜冒同中国对抗的风险来维护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具体利益。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也经常用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合作所取得的进展,向国会和公众展示同中国保持交往和合作的重要性。据美国官员说,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莱克1996年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两国关系原则很好,但希望增加一句,即“解决问题”。每当中美进行高层对话时,美方总是提出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子,作为改善关系的筹码,要求中方回应。中美官方关系好转,当然有利于减缓两国在功能性问题上的摩擦,至少将防止具体分歧过分政治化。但是,美国不会因两国关系的改善而放弃许多具体利益,而中国也不会为了迁就美国而牺牲长远目标和根本利益。换言之,不能指望官方关系气氛的改善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具体分歧。中美在功能性问题上将有一个长期艰苦的“磨合”过程,在合作面扩大的同时,摩擦面也会扩大,只是摩擦的烈度不至于失控。
抓紧规范制定和制度建设
美国外交的第三个新特点,是更加重视在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各个功能性领域里制定和维护有利于它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这同上述两个特点是相互补充的。所谓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就是企图把美国国内那一套自由经济、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原则扩展到国际事务中去,通过在国际机制中安排议程和确立原则,推广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冷战结束后,美国加紧制定和完善各种国际规范,加大机构建设的力度。核不扩散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信息技术协议、知识产权协定、西方七国(外加俄罗斯)首脑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北约东扩……,美国在这一系列国际条约、协定和组织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制订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egimes)这一中心的。 在亚洲部分地区出现金融动荡后,美国又在酝酿新的国际金融协调机制。用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的话来说,美国冷战后外交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建立一个法治的世界”。[5]从这一层面上看, 美国心目中的“世界新秩序”设想,主要不是在“单极”还是“多极”、“一家说了算”还是“大家商量办”上做文章,而是在尚未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组合能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构成真正的挑战之前,或公开、或潜移默化地企图使它一家的主张在国际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变成似乎是全球应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制度化、规范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短短三千字的《中美联合声明》里,提到的国际宣言、协定和组织有8个, 包括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内的双边协定也有7个, 足见制度建设受到双方重视的程度,同时也说明中国越来越重视以制度安排来制约美国行为,维护中国权益,规范中美未来关系。
政治现实主义的新思考
美国外交思想中的一个传统问题是现实主义同理想主义的争论。无论是强调国家权力最大化和国际权力均衡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注重国际结构的新现实主义,都以追求美国国家权益、维护国际和平和稳定为政策目标。理想主义则将国际斗争视为正义与邪恶之争,以向全球推广美国式的道义原则和价值观为己任。理想主义在冷战时期以反共意识形态为旗帜,在冷战结束后大力鼓吹世界民主化与人权外交。1989年以后美国对华政策思想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脱离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
然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两套政策思路,都随着全球政治形势和美国外交需要而在不断调整,并且相互交叉融合。在现实主义学派里,地缘经济的思想补充了地缘政治的传统观念;相互依存理论试图解释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际机制和规则一直是热门的研究课题;至于美国是否应该追求全球优势地位或曰霸权,也有激烈的学术讨论。但是,对美国全球战略以及同其它大国的关系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仍然是一些相对简单明了的地缘政治思想。现就与中美关系有关的美国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主张,略举一二。
兰德公司发表的《1996年战略评估》报告提出了美国的三种大战略选择。第一种是新孤立主义的选择,不过作者认为它得不偿失,不应成为美国战略。第二种是多极化和国际权力均衡的选择。这种选择要求美国在世界各地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就像19世纪英国在欧洲大陆事务中成为“隔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那样。具体地说, 就是在原苏联版图之内承认俄罗斯的主导作用;在欧洲弱化北约,支持德国取得更大的军事能力,或者让欧盟具有军事功能,防止任何一个大国(包括俄罗斯)在欧洲起支配作用;在亚洲,美国也需要防止任何大国称霸,可以通过在日本和中国两大强国之间转换联盟关系来维护美国利益。该报告称,充当“隔岸平衡者”显然在短期内代价不大,但是从长远看面临其它大国更强有力的竞争,以至侵害到美国切身利益,甚至出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种多极化局面。同时,美国有时不得不为维持大国平衡而支持非民主国家反对民主国家,这将是违反美国政治原则的。
第三种战略选择是美国担当全球领导。为此美国必须巩固和加强北美、欧洲和东亚的发达国家民主同盟,形成民主的“和平区”,并使之逐渐扩大;保持美国军事优势,但在使用武力时要谨慎,防止伸手过长;要发展美国经济实力,保证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报告说,要制止俄罗斯重新帝国化和中国扩张主义,同时与它们两国都发展合作。中国发展速度高于俄罗斯,可能想在亚洲称霸,因此美国应当加强同日本、韩国的同盟,发展同东盟的合作,甚至支持东盟和台湾地区的防务以牵制中国,限制向中国的高技术出口。显然,这份兰德公司报告支持第三种选择。[6]
在美国的战略家里,像基辛格那样提倡多极化的为数不多。他的主张接近于上述第二种选择。基辛格认为日本将企图在亚洲称雄,俄罗斯的传统民族主义还会卷土重来,印度发展速度接近中国,也在崛起,而中国军事力量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美国应借助中国力量维持亚太地区平衡,而不应遏制中国。[7] 亚洲国家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低于每个亚洲国家同美国关系的密切程度,才是一种理想状态。[8] 不过,在欧洲问题上基辛格坚决主张加强北约,以防备俄罗斯“重建帝国”。
另一位美国外交专家、哈佛大学研究员约菲,在研读19世纪欧洲外交史以后得出结论,指出当年大英帝国维护霸权的成功之处,在于选择置身于欧洲大陆逐鹿场之外,必要时在欧洲两大联盟中支持弱者,但这却不是今日美国外交的榜样,因为美国的全球利益已使它无法隔岸观火。美国应当效法1871年德国统一后的俾斯麦外交,来维护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俾斯麦领导的德国同欧洲大小国家分别结成双边或多边同盟关系,这个精心编织的网络成功地阻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今天的美国也应当分别同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泰国、越南,以至台湾发展合作,使美国同这些大小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比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样,它们就缺乏联合反美的动力。约菲说,即便中俄都对美国心怀不满,而且宣布了建立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只要美国同中俄分别加强关系,就不必担心中俄会结成真正的反美联盟。[9] 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大棋局》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地缘战略主张。他说,欧亚大陆是处于世界轴心地位的超级大陆。在欧亚大陆西端,美国的中心目标应是扩大以法国和德国为核心的欧洲民主桥头堡,而英国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他要求美国毫不迟疑地实行北约东扩。布热津斯基认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欧亚中心地带不稳定,将继续是一个政治黑洞。俄罗斯应成为面向欧洲的、优先发展经济的松散联邦,西方不能让它恢复帝国。在东亚,中国是“远东之锚”,很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美中应当建立政治共识,美中关系比美日关系更重要。一个在亚太地区影响增加的“大中华”未必同美国的利益相悖。他建议邀请中国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日本则由于历史原因在亚洲不能发挥重要政治作用,不应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伙伴。布热津斯基设想分三阶段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他提出的短期目标是防止出现一个可能对美国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中期目标是在美国领导下,欧洲各国、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形成一个更具合作性质的跨欧亚安全体系。长期目标是将这一体系转变为共同承担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10]
综合起来看,美国现实主义战略思想家里可能形成的几条主流意见是:(1)极力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加强美欧联盟,扩大北约;(3)支持俄罗斯走上市场经济和政治分权之路, 遏止其民族主义上升;(4)提高中亚和西亚在美国战略棋盘中的地位;(5)同主要国家分别发展合作关系,防止出现反美联合阵线。美国战略家虽然都认为应当更加重视东亚地区,但决策者到底将倾向于兰德公司报告那种联合中国的邻国牵制中国的主张,抑或基辛格式的在中日之间维持均势的思路,还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对华关系高于对日关系的建议,似乎仍未完全明朗。
对美国式理想的反思
美国政府之所以迄今不能按照基辛格或布热津斯基式的地缘政治思想统帅对华政策,其主要思想障碍就是所谓理想主义,也即中国经常批评的“冷战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维用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衡量其它国家,用反共意识形态来看待中国。冷战结束后在美国很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就是理想主义的一个典型。[11]它认为民主国家(指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可以避免战争,而民主国家同专制国家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世界民主化是世界和平和稳定;因此美国推行人权外交既是道义上的需要,也符合美国利益。
冷战刚刚结束时,民主和平论很有市场,因为似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消除了战争威胁。但是,波黑和车臣等地的激烈内战,还有俄罗斯的“日里诺夫斯基现象”,迫使美国战略家重新思考民主同和平的关系,以及民主化同激进民族主义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在集权到民主的转型过程中,竞选者和领导人很容易诉诸于激进好战的民族主义,以增强其政纲的吸引力和社会的凝聚力。因此民主化的过程可能带来内部与外部的冲突甚至战争。[12]
近年来非洲动乱频仍,某些冲突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活,使民主和平论受到更大挑战。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变化,促使一些美国思想家从整体上认真反思美国式理想,考虑西方民主模式是否适合于发展中国家。1997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该刊总编辑扎戈里亚的文章(该文又于1998年初摘要发表于《新闻周刊》),说今日全世界已有半数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但其中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非自由的民主制,其特点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无视宪法对其权力的限制,剥夺本国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在一些伊斯兰国家,民主化导致神权政治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没有宪法保障的自由的民主制度不仅会使民主名声扫地,而且会侵蚀自由,滥用权力,引起种族分裂甚至战争。扎戈里亚认为,虽然中国按照美国的标准不是民主国家,但今天中国公民享受着几代人从未享受过的自主权和经济自由,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他建议,美国的外交目标不应是在世界上扩展民主制度,而应促进宪政和自由。[13]
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学者卡普兰的文章,在对世界民主化提出质疑方面比扎戈里亚走得更远。卡普兰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大公司的巨大权力可能使美国丧失民主,陷入寡头政治。他指出,民主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以为美国式民主会在全世界成功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表现。只有取得社会进步和经济成就的民主才是成功的民主。他举出卢旺达等许多国家近年来的例子,说明多党制和直接选举未必能带来社会公正经济繁荣,反而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动乱。在提到中国时卡普兰说,如果中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导致“民主”,很难想象90年代中国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因为在社会动荡时秩序被摧毁,而腐败可以依然猖獗。[14]
虽然对美国式理想与美国人权外交进行深刻反思的人在美国尚属凤毛麟角,但是这种反思对美国外交实践的影响可能会逐渐显现出来。一贯以倡导人权外交著称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1997年底访问非洲后承认,美国把对非政策重点放在人权上会犯错误。《洛杉矶时报》就此评论道,“这等于是承认,美国的多党民主、结社自由和尊重反对意见的模式也许是不能向第三世界输出的。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进行这种表态还不多见。”[15]可以预料,只要中国继续保持政治稳定,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判断、反共意识形态,以及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终究要发生重大变化。
新全球主义
美国外交思想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各自发展和相互矛盾固然值得注意,但是二者的交汇将具有更大的政策意义。例如,布热津斯基在发展其欧亚地缘战略思想的同时,极力提倡精神信仰,呼吁美国重新确立道德标准的中心地位,认为惟有如此才能维持“世界领导地位”。[16]
上文描述的美国冷战后外交的新需要和新特点,如决策机制进一步分散化,外交问题功能化,国际关系制度化,必然产生一种新的外交思想,姑且称之为“新全球主义”,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结合。这种思想并不简单地排斥前两种思想,而是充分认识到传统的外交思路已经不足以应付世纪之交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要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活动、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和粮食供应短缺、金融危机等诸多功能性问题,必须建立全球稳定前提下的全球合作。
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和克林顿政府的许多官员,还有许多较为年轻的国会议员,都具有这种新全球主义观念。1997年克林顿第二次入主白宫时,主要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49岁。他们形成世界观的年代,不是麦卡锡主义猖獗和尼克松同赫鲁晓夫进行“厨房辩论”的50年代,而是美国黑人觉醒、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造成美国国内政治分裂、种族和文化多元主义开始兴起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因此他们的政治思想带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这一代决策者真正的外交经验,是在冷战接近尾声时才开始积累起来的。就此而言,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在他们脑中的印记应当少于尼克松、里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老一代领导人和外交家。同时,新一代美国领导人又受到近年来国内保守主义回潮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思想务实,重视信息传播,关注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对外交同国内问题的联系更为敏感。他们更重视利用国际规则,通过多边机制、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界的联系来应付国际挑战。
多数新全球主义者意识到中国在美国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中的重要地位,反对遏制和孤立中国,认识到除同中国的接触和合作外,别无他途。他们也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国内稳定是亚太地区稳定和全球稳定的重要保证,一个有权威的中国政府,将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贸易平衡、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更有效地同美国合作。
另一方面,新全球主义也给美国对华政策带来相当多的不稳定因素。首先,崛起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问题,特别是在亚太地缘政治中的定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妨碍了同中国在最敏感、最可能引起冲突的台湾问题上达成某种战略谅解。其次,提高功能性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容易使美国对华政策缺乏中心,缺乏长远设想;参与决策的部门增加,决策机制复杂,易于因国内利益协调方面的考虑而不顾中国的利益和愿望。最后,一味强调民间交往、跨国联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会造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总的来说,美国外交的新特点应有助于美国克服冷战思维。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双边经贸的扩大,是中美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中美联合声明》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两国在相互交往中的各自利益和需要,是走向务实、制度化、正常化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步骤。今后的中美关系应能避免大起大落。同时,利益和价值观的重要差异,特别是美国“领导世界”的要求和中国的多极化主张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
注释:
[1] 王缉思:《〈中美联合声明〉的意义》,载《世界知识》1997年第22期,7—8页。
[2] Bill Clinton:"A Strategy for Foreign Policy:Assistance to Russia" April 1,1992,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LVII,No.14,May 1,1992,p.422.
[3] 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102—103页,海南出版社,1997。
[4] 一项被广泛引用的民意调查是:
John E. Rielly, ed,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Foreign Policy 1995,Chicago: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5,p.15.在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与国内问题相关的外交问题(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扫毒、非法移民等)最受公众重视,其次是核不扩散、国际恐怖活动、环保等全球性问题,再次是军事安全问题,列在最后的是促进民主和人权问题。见美国新闻总署:《美国外交政策议程》,1996年10月,中文版,21页。
[5] Arthur M.Schlesinger,Jr.: "America's Role in thePost - Cold War World"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1994, New York:Pharos Book,1993,p.31.
[ 6]
Zalmay Khalilzad: "U.S. Grand Strategies: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 in ZalmayKhalilzad,ed.,Strategic Appraisal 1996,Santa Monica,Cal.:Rand,1996,pp.11—34.
[7] Henry A. Kissinger: "Outrage Is Not a Policy"Newsweek,November 10,1997,pp.42.
[8]参见刘靖华:《霸权的兴衰》, 148 页,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9] Josef Joffe:"How America Does It" Foreign Affairs,Vol.76,No.5,September/October 1997,pp.13—27.
[10] Zbigniew Brzezinsk: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BasicBooks, 1997, pp.194—215;
Zbigniew Brzezinski: "AGeostrategy for Eurasia" Foreign Affairs,Vol.76, No.
5,September/October 1997,pp.50—64.
[11] 关于“民主和平论”的美国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从1993 年至1997年就出版了至少4部,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刊物上发表的专题论文数量更多得难以统计。有关专题评述,可参见Zeev Maoz: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Democratic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2,No.1,Summer 1997,pp.162—198.
[12] 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and War" Foreign Affairs,Vol.74,No.3,May/June 1995, pp.79—97.
[13] 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Vol.76,No.6,November/December 1997, pp.22—43; " Doubts About Democracy" Newsweek,January 5. 1998,p.26.
[14]Robert D.Kaplan:"Was Democracy Just a Moment? " TheAtlantic Monthly,December 1997,pp.55—80.
[15]《洛杉矶时报》1997年12月17日,新华社联合国12月17日英文电。
[16]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