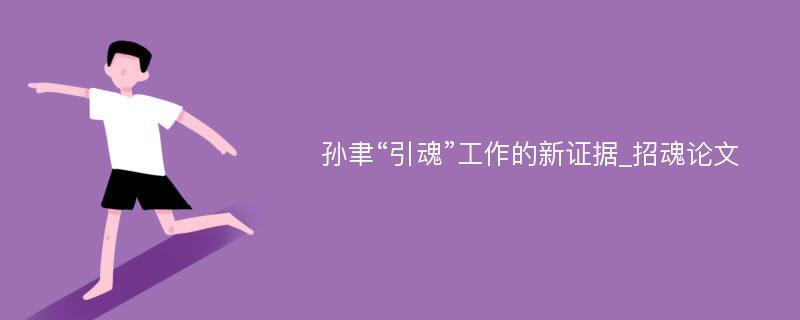
宋玉作《招魂》说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玉论文,说新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自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标识“宋玉之所作也”,迄至宋元,本无争议;直到明清疑古风盛行,才有人提出异议,先是明黄文焕在《楚辞听直》中根据《招魂》的内容与写作时令同屈原之死不符,始疑《招魂》非宋玉所作,其后林云铭于《楚辞灯》中根据司马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的评赞之语,将《招魂》的著作权判给了屈原。于是关于《招魂》作者是屈是宋的学案便引起了大辩论,说者各寻其据,相与驳议,虽屈原说在近代大占上风,但时下宋玉说又回潮重起。尽管前人的大讨论并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但是他们的研究是积极的、有益的,起码在论辩中辨明了考证《招魂》作者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一、《招魂》中所描写的高堂层台、珍怪器物、侍宿美姬、玉食琼浆、歌舞音乐、游戏玩好,按古礼楚制只能是君王才能享有的,因而被招者只能是某一楚王,而不可能是屈原一类的王臣。二、以《招魂》文本和古楚民俗而论,所招者当为人之生魂,而非亡魂。三、《招魂》全文可分为前辞、命辞、招辞、乱辞四部分,前辞是作者代为被招者设词,命辞是记上帝命巫阳招魂之语,招辞是记巫阳招魂时的言词,乱辞是作者“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交待“魂魄离散”的原委,亦即招魂的缘由。四、前辞中作者代为设词的“朕”,实指乱辞中“与王趋梦”的“王”,亦即“君王亲发”的“君王”。而乱辞中的“汩吾南征”的“吾”,则是作者自谓之辞。五、《招魂》中关涉的名物制度、人物事迹、山川地望是考证其作者的关键。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考辨,并以此判定《招魂》的作者。
一、关于招魂的地点问题
招魂的地点问题,是考证《招魂》作者的首要问题,如果明确了招魂的地点,那么就可以参照屈、宋的经历,楚王的事迹来判定《招魂》的真正作者。以《招魂》文本看,有关招魂地点的关键词语是“魂兮归来!入修门些。”“汩吾南征”,“路贯庐江兮,左长薄。”“与王趋梦”等句中的修门、南征、庐江、长薄、梦等词语。下面逐一考辨:
修门:王逸注:“郢城门也。”洪兴祖补注:“伍端休《江陵记》云:南关三门,其一名龙门,一名修门。”研究者以此认为招魂的地点在郢城,即今湖北荆州城北纪南故城。然而,将修门认为是郢城南门却多有疑问。首先,文中描写“故居”的地形地貌是,“层台累榭,临高山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考纪南故城遗址,从宏观上讲“城址位于东南两面的江湖与西北两面的丘陵之间,”[1]古城面积为16平方公里。经考古钻探、发掘,已发现城内有宫城及十字交错的古河道,古建筑台基达84处,城门八座(水门四座),水井、窑址、作坊多处。[2]笔者曾亲临纪南故城考察,曾立于古城墙遗址上举目四望,由于距城址东南的江湖和西北的丘陵太远,极尽目力也望不见江湖及远山。因而觉得说郢城“川谷径复”尚可,说“临高山些”则不合实际。其次,按乱辞中描述的“田猎”路线,是由郢出发南行,前是庐江,左是长薄,抵达“梦”中。若以“梦”指云梦泽,则云梦在郢东南,方位还对,而若以“庐江”为位于襄樊、宜城之间的庐江,则此庐江在郢正北,则是南辕北辙了。有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们以为“田猎”的路线是由陈国旧都(今河南淮阳)出发,经襄樊宜城间的庐江,抵达云梦泽。[3]这样方位是对了,然而楚都由郢迁陈后,楚之邓(今襄樊)、鄢(今宜城)、郢均为秦国所占领,此路不通。况陈国旧都也无“临高山些”的地貌。也有人认为,“路贯庐江”是宋玉由家乡宜城“南征”的路线,然而那里的庐江是在宜城北面,方位也不对。[4]既然如此,那修门究竟是何城之门,又借代楚国的哪一座都城呢?我们认为当指楚国的最后一座都城寿春。《史记·楚世家》:考烈王六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寿春即今安徽省寿县,楚故都寿春城遗址在今寿县县城东南五里柏家台一带。北临八公山和淮水,东有淝水、南为瓦埠湖。笔者考察寿春故城时,曾访问过寿县博物馆原馆长,据老先生介绍,90年代国家文物考古部门曾对古城遗址进行卫星探测和实地局部发掘,据悉,古城面积达26平方公里,城外有护城河,城内为水网式结构,有宫城,城门为一门三道式结构,由于古城尚未全部发掘,所以探测发掘报告还未公开发布。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分析,寿春城和纪南城建制基本相同,如城外都有护城河,城内都为水网式结构,城内都建有宫城,城门都是一门三道的形制,可以推断寿春城是楚人按照纪南城的建制于迁离陈城后始建的。又据史书楚人改寿春而命曰郢的记载,我们有理由推测寿春城的城门名称也是按照郢都故城命名的。因而“修门”当指代寿春古城。寿春古城北临八公山、淮水,内有水网贯通,符合文本描述的“层台累榭,临高山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的地形地貌。由寿春南行,路通安徽南部发源于陵阳的庐江,也符合文本描述的田猎路线。(长薄、梦的问题下文讨论。)
南征:王逸注:“征,行也。”可见“南征”为南行之意。然此语关键不在于字面,而在于表明了《招魂》乱辞中“田猎”路线的方向,故不可忽视。
庐江:有两说。1.《汉书·地理志》说:“庐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为国。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属扬州。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注谓:“汉应劭曰:故庐子国。”[5]考此庐江即今安徽南部的青弋江。古庐子国,春秋时为舒国,汉置舒县,今在庐江县东南。庐江之名春秋前即应有之。2.据谭其骧先生考证:“庐江当指今襄阳宜城界之潼水,水北有汉中庐县故城,中庐即春秋庐戎之国,故此水当有庐江之称。”[6]今人多从谭先生之说,以为襄阳江陵间多沼泽平野之地,与《招魂》中“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的地形描述相吻合,而皖南的庐江多高山,不合于文本的描述。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个误会是没有考虑到田猎的出发地造成的。若从郢都出发,襄阳宜城间的庐江方向在北,无论如何算不得“南征”,尽管地形相符,但方向不对。若从陈国故都出发,襄阳宜城间的庐江在其东南,说“南征”还说得过去,但楚迁都陈前,襄阳、宜城、郢都均为秦攻占,且纳入版图,置为南郡,(《史记·秦本纪》:“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今宜城)、邓(今襄阳),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7])楚王如何能田猎于此!所以田猎的出发地非在寿春不可。或言皖南庐江多山,难以“遥望博”。这个问题出在“路贯庐江”的“贯”字上,王逸注:“贯,出也。”这便让人以为田猎是途经庐江。其实,“贯”亦可训“通”,路贯庐江,可解为路通向庐江,自寿春通向皖南庐江的路上正是江淮平原,何以不能“遥望博”呢?
左长薄:左:五臣注:“在其左。”朱熹注:“左者,行出其右也。”两注均将“左”释为方位词,这并未错,只是解释的未到位,此处的“左”当是方位名词用如动词,意为先走在通向庐江的路上,而后左转抵达长薄。试想,若不是抵达这个“遥望博”的田猎之地,怎能“青骊结驷兮齐千乘。”长薄:王逸注:“长薄,地名也。”又曰:“长薄在江北。”但未具体说明地望。清胡文英注《招魂》曰:“庐江,在今江南,所属巢县,有三闾祠。庐江,战国亦属楚。长,长洲;薄,大薄。皆地名。”又于《思美人》注曰:“大薄,长洲,皆地名,在今江南。”[8]以为“长薄”在皖南庐江附近。虽说明了地望,但言在江南当误。(长薄未必是两个地名的合称。胡注以《思美人》中的“长洲、大薄”释“长薄”有些牵强。)故仍依王逸江北之说。此地当在长江以北,寿春以南。《水经注·淮水》言:“淮水又北经莫邪山西。山南有阴陵县故城。汉高祖五年,项羽自垓下,从数百骑夜驰渡淮,至阴陵迷失道,左陷大泽,汉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及之于斯县者也。”[9]《史记·项羽本纪》记此事说:“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及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阴陵在寿春东,项羽所陷之大泽当在寿春东南,长江以北。我们认为项羽所陷之大泽就是《招魂》中所谓的长薄。此地春秋时是楚之边境,东邻吴,后吴故地亦归楚。此地战国时北至钟离(今蚌埠东),南至橐皋(今巢县),西至寿春(今寿县),东至广陵(今扬州)数百里间无有城邑,以项羽所陷大泽推之,当是人烟稀少的沼泽区。此地汉属九江郡,《后汉书·宋均传》载,“(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井,而犹多伤害。”[10]足见此地为猛兽出没之地,是一个田猎的好场所。
梦:王逸注:“梦,泽中也。楚人名泽中为梦中。……一注云:梦,草中也。”洪兴祖补注:“楚谓草泽曰梦。”以此知“梦”为楚人泛称草泽之名。王逸、洪兴祖又以为“梦”即指云梦泽,虽“梦”引申后亦可以专名出现,但以为是云梦泽,恐未必合于《招魂》本义。我们以为此“梦”当是其本义泛指草泽的引申用法,即指楚中某泽,于文中所指当是上文之“长薄”。《广雅·释草》:“草丛生为薄”。《楚辞·九章·思美人》洪兴祖补注:“薄,丛薄也。”《楚辞·九章·涉江》王逸注:“草木交错曰薄。”看来“长薄”之地的得名实是以其地草木丛生的特点而命之。因此称“长薄”这一草木丛生的大泽为“梦”是合于情理的。
根据上面的考辨,我们有理由认为招魂的地点在楚国的最后一座都城——寿春。30年代,陆侃如先生曾提出过这一观点,[11]我们赞同陆先生的推论。
二、关于招魂对象的考辨
前面我们概括了学者们关于《招魂》问题的一些共识,我们知道招魂的对象是楚国的某一位君王,而且所招的是这位君王的生魂;同时我们还知道《招魂》的作者可能是屈原、也可能是宋玉。这样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屈原、宋玉生活时代的几位楚王,问题就会清楚了。
楚怀王,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公元前299年被秦诱至武关扣留在秦国,公元前297年怀王试图逃归,未果,公元前296年病逝于秦国,秦人送归怀王遗体,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有人认为《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然而招怀王魂之说疑点甚多。一、怀王发病是在秦国,以招生魂而论,是希望其魂归附其体,若于楚郢都招怀王魂,岂不是使其魂远离其体。因而招怀王魂之说不合于习俗。二、《招魂》说:“魂兮归来,入修门些。”怀王时在秦,是在楚郢都之西北,而“修门”是郢都南门(一说东门),怀王魂归理当从郢都西门或北门而入,而不应当让其魂绕一个大圈子从南门或东门回归。因而招怀王魂之说不合于地理方位。
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63年在位。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8年),因秦将白起攻陷郢都,楚迁都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63年襄王病卒于陈城。今淮阳城外有马鞍冢,据考古发掘是楚王之墓,很可能就是襄王的墓葬。有人认为《招魂》是屈原或宋招襄王魂,但此说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症结。一、《招魂》招楚王之魂入修门,而陈城是陈国故都,据考古发掘所知,虽陈城曾被楚人维修加固过,但仍维持陈城旧制,又据文献资料记载,陈城东门名栗门,可证陈城之门自有其名,[12]楚人迁都于此也不当改其城门旧称。因此襄王病于陈城,而招其魂入已沦陷的郢都之门,这是万万说不通的。二、《招魂》乱辞中谈到了“南征”田猎,“路贯庐江”,“与王趋梦”。若以陈城为出发点,前文提到的两处庐江,襄阳宜城间的庐江在其西南,皖南的庐江在其东南,似乎都符合“南征”的方位,但是,楚迁陈后,襄阳宜城均被秦占领,是难以路过那里去田猎的。而皖南的庐江又距陈城近500公里,去那里也不大可能。这就是说,迁都陈城的楚襄王,不可能是那个“君王亲发兮惮青兕”的楚王。
楚考烈王,公元前262年至公元前238年在位。公元前256年,秦攻韩阳城,有直逼楚陈城之势,公元前253年,楚迁都于巨阳(在今安徽太和东),后春申君又听朱英计又于公元前241年迁都于寿春(在今安徽寿县),公元前238年考烈王病卒。
楚幽王,公元前237年至公元前229年在位,都寿春。
楚哀王,公元前228年立,都寿春,在位仅两月。
楚王负刍,公元前227至公元前223年在位,都寿春。王负刍五年秦王翦破楚,负刍被虏。楚亡。
前面我们讨论过招魂地点应该在寿春,那么都于寿春的几位楚王就可能是招魂的对象,而在这几位楚王中考烈王最有可能。这是因为,首先考烈王的事迹基本符合《招魂》“前辞”部分的描写。考烈王为太子时曾入秦为质,有功于楚;即位时楚国益弱,考烈王以春申君为相,历时八年使楚复强,颇有政绩;考烈王二十二年,诸侯合纵,楚为纵长,春申君用事,西向伐秦,然落败而归,楚复衰弱,不得不再次迁都至寿春,考烈王以此怪罪春申君,与之疏远,而春申君又以考烈王无子为由,常求妇人献与考烈王,以求自保,以致楚王嫔妃甚众,甚至将怀了自家孩子的李园女弟也进献给考烈王,没过三年考烈王便病逝于寿春。以考烈王的事迹参看《招魂》的“前辞”:“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春申君进献“妇人宜子者”之事,简直就是“牵于俗而芜秽”的注脚。
所以,我们认为招魂对象应是楚考烈王。
三、关于《招魂》作者的推测
我们已经认定,招魂的地点在寿春,招魂的对象是楚考烈王,这样《招魂》的作者只能是宋玉,而不可能是屈原,因为学者们考证的屈原卒年其年代最迟的是公元前278年,屈原是不会在作品中言及他死后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应当遵从王逸的说法,“《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
关于宋玉作《招魂》,持否定态度的研究者曾提过一些疑问。有人认为宋玉的作品多提楚顷襄王,而无一提及考烈王,于是推断宋玉仅生活于襄王时代,其实,这是一种误识。首先,宋玉的《九辩》、《登徒子好色赋》、《笛赋》等就是襄王后的作品,比如《登徒子好色赋》中的“楚王”就应当指考烈王,因为文中提到了“阳城”和“下蔡”两个地名,阳城在陈城(今河南淮阳)附近,下蔡在寿春(今安徽寿县)附近,而距离郢都很远,这便证明该赋是楚迁离郢都后所作;同时文中又提到“南楚”这一地区称谓,《史记·货殖传》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13]寿春战国和西汉时属九江郡,司马迁在谈南楚时,提及寿春,这说明他确认寿春属于南楚,这又进一步证明该赋是楚迁至寿春时所作。其次,《九辩》中说:“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又说:“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这说明宋玉“失职”之时,已是“老冉冉”之时了。按游国恩先生的推测,宋玉生于楚顷襄王三年(前296)。[14]以此推算,顷襄王卒时,宋玉方三十余岁,算不得“老冉冉”,至考烈王卒时,宋玉已年近花甲,正合于“老冉冉”之说。因而,我们认为宋玉在考烈王之时尚在朝中为官,大概在考烈王卒后才被疏“失职”。这也是宋玉生活在考烈王时代的证明。
也有人说,古代文献中关于宋玉事迹的记载中没有关于宋玉生活在寿春的记载,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是事实。《汉书·地理志》有条记载,值得研究者重视。记载说:“粤(越)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15]这里叙述了寿春、合肥地区的沿革、物产、文化和民俗,在文化介绍中提到了屈原、宋玉、唐勒、枚乘、邹阳、严夫子、严助、朱买臣等一系列著名文士,按照《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凡是在某地区情况中介绍的人物都是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人物。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宋玉的确在寿春生活过,这当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招魂》为宋玉所作,招魂的地点在寿春,招魂的对象为楚考烈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