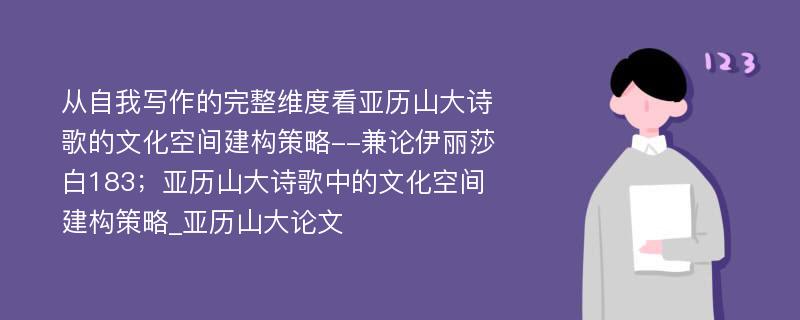
从内部书写自我的完整维度——论伊丽莎白#183;亚历山大诗歌文化空间构建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丽莎白论文,亚历山大论文,维度论文,诗歌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在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仪式上朗诵了诗歌《赞美这一天》(“Praise Song for the Day”)之后,非裔美国女诗人、耶鲁大学教授伊丽莎白·亚历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1962-)似乎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这一现象除了再次证明大众传媒和公共政治的力量之外,也是一个令学术界和诗歌创作界深思的事件。事实上,亚历山大至今已经出版六部诗集和两部论文集,在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两个领域均已颇有建树。①她的诗集《战前梦之书》被美国著名文化刊物《村声》(Village Voice)评为2001年最受欢迎的25部图书之一;评论集《黑人内部》被美国权威艺术杂志《艺术论坛》(Art Forum)评为2004年度最佳图书之一;诗集《美国的崇高》是获得2006年普利策诗歌奖提名的最后三部作品之一。诗人近年来获得了多项诗歌大奖,②并赢得了美国诗歌界的普遍关注,被誉为“当代美国诗歌界的一个种子声音”(转引自罗良功32)。
然而,如果没有这次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上的诗歌朗诵,亚历山大的名字可能只会囿于美国诗歌和评论界,永远也不能进入大众传媒的视野,更不会成为美国民众认知和追捧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亚历山大和以她为代表的在“后灵魂”(post-soul)时期③创作的非裔美国诗人的悲哀。自从非裔女诗人丽塔·达夫1993年成为美国的桂冠诗人之后,非裔美国诗人似乎很难在影响力上有所超越。在20世纪末出版的黑人文学的文集中,非裔美国诗人和诗歌在编者们有意无意的选择中悄然消失。④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当代学者型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首次印刷往往只有区区2500册,⑤他们的诗集也很难有机会再版,其影响力很难超越诗歌界和学术圈,更难以对美国的主流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比声音暗弱更糟糕的是自己的声音被误读和误解。亚历山大就曾经抱怨自己的作品被狭隘的白人评论家过度赞扬,却被目光短浅的黑人前辈诗人批评;她的作品从她认为应该被收录的文集中漏掉,却被收录进她感觉自己并不属于的文集中。可见,对于亚历山大的诗歌作品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误解。当亚历山大从象牙塔最终走进大众媒体之际,可能却是更大的误解产生之时。因此,对亚历山大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进行一个全面的定位、梳理和解读也将成为诗歌研究领域的一项使命。然而,遗憾的是,与热闹的大众传媒对亚历山大的热情关注不同,美国诗歌研究界似乎对这位学者诗人保持着审慎的热度。从学术角度对她的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的研究屈指可数。至于我国国内的文学评论界,目前对亚历山大的研究还基本处于译介阶段。⑥
作为一位学者型诗人,亚历山大的诗歌创作和她对非裔美国诗人和诗歌的研究是相生相伴的,换言之,她的诗歌创作过程往往是其诗学理论构建的实践过程,是一种有意识的诗学策略的选择和应用的过程。因此,对亚历山大诗歌解读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将其置于诗人本人的诗学理论的框架之中,并在两者的交互参照中相互投射、相互诠释。亚历山大诗学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当推2004年出版的文论《黑人内部》,该书集中阐释了她的核心诗学观——“黑人内部”(Black Interior);2007年的文集《权力与可能性》又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了这一诗学观。顾名思义,“黑人内部”是一个空间感鲜明的观念,是女诗人诗歌创作原则和理念的形象化的喻指。这一具有“空间的诗学”⑦特征的“诗学的空间”是一个当代黑人情感的收纳器,也是一个当代非裔诗人创作灵感的发源地。亚历山大的这一空间诗学建构策略在非裔女诗人中是颇有代表性的。正如贝克(Houston A.Baker)所指出的,从空间类比和喻指入手是非裔美国女性诗人偏爱的文学实践(22—35),因为身处边缘的她们心中的梦想和困惑是“我们会把宇宙的/空间溶解到我们的味道之中吗?”(Dove 28)。可以说,亚历山大的“黑人内部”诗学观既是对非裔美国作家以空间意象作为诗学建构策略之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当代族裔研究领域“去族裔”、“去性别”倾向的挑战和颠覆。⑧
那么,这样一个极具空间感的概念到底容纳了怎样的黑人女性的智慧、黑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以及黑人诗人的诗学理念,而亚历山大的诗歌又是在怎样的写作策略中实现了与这一空间诗学理念的对接,并最终完成了在“后黑人艺术运动”时期和“后灵魂”时代创作的非裔女性诗人的主体建构的呢?作为一个具有负载量的文化空间,“黑人内部”最鲜明的指向性是“族裔”和“性别”的文化内涵,(Alexander,Black Interior 5;Power and Possibility 159)而在亚历山大的诗歌书写中,此双重内涵又分别被抽象和具象成为两个带有内趋性的空间,即灵魂深处的心理空间和生活之核心的家宅空间,从而从广义和狭义、心理和物质、比喻和真实的多重维度诠释了“黑人内部”的深刻含义。本文对亚历山大诗歌的解读将从她本人的诗学阐释出发,在探究“黑人内部”的文化内涵的同时,考察女诗人如何在诗歌中拼贴出一个“族裔化”和“性别化”的文化空间,并因此建构起一个颇具后现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并最终实现了她从内部书写“自我的完整维度”的理想。(Alexander,Black Interior 5)
一、亚历山大的“族裔化”心理空间
对于主流媒体和大众传媒的关注,亚历山大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她在对非裔女诗人格温朵琳·布鲁克斯的研究中,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更广大的公众对黑人诗人的期望是一回事。本民族的人民的要求——不管围绕着这一民众划定的范围可能有多么使人烦恼——一直是另一回事”。(Alexander,Black Interior 56)可见,亚历山大是一位种族意识十分强烈的诗人,而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她的诗学构建和诗歌创作之中。正如亚历山大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的那样,“黑人内部”首先是一个“族裔化”的心理空间,是从内心空间的维度构建黑人性的诗学观念和写作路径。如果把“黑人内部”看作一个整体的话,“族裔化”的心理空间应该是处于其内核部分,是亚历山大诗学观的核心。建立在这一意义上的空间观念是极为广阔的,正如里尔克所言,“内心空间在世界中展开”(转引自巴什拉220)。与丽塔·达夫等走向“世界主义”,⑨并更多地以“普适性”的价值审视种族问题的前辈诗人相比,亚历山大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种族性”的适度回归,是从“种类”向“种族”的复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族裔化”的心理空间不是种族对立的二元性空间,而是把黑人族群作为完整的种族群体,在摈弃了刻板化的黑人形象之后,对黑人从人性最本质、最复杂的层面探究人性的弱点、人性的枷锁,考察的是黑人作为人的喜怒哀乐。换言之,亚历山大试图探究的是刻板化的黑人形象背后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从而最终完成重塑黑人主体,回归自我的历史使命。泰瑞·弗兰西斯(Terri Francis)认为,“正是通过把黑人意识归因于内在领域或者梦幻空间,人性的心理层面,亚历山大使我们想象社会力量如何作用于主体性,作用于一个人、一个社群,以及它们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塑形所有这一切”。可见,这个“族裔化”的“黑人内部”心理空间堪称一个抵抗刻板化的黑人形象的内在的动力之源。
亚历山大对于刻板化的黑人形象及其文化生产机制有着深刻的认识,在《黑人内部》和《权力与可能性》的多个章节都有详尽的论述。例如,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刻板化的黑人身体形象的本质:“在美国文化中黑人的身体形象一直要么被超性欲化要么被去性欲化,以服务于美国白人的想象和目的。”(Alexander,Power and Possibility 99)然而,尽管亚历山大对刻板化的黑人形象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却谈不上新鲜。类似的认识和表述在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和安德洛·罗德那里似乎得到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阐释。⑩亚历山大的高明之处在于她解构刻板化的黑人形象的策略。与罗德走向女同性恋的极端的行为主义方式的解构策略和“爱欲书写”策略不同,(11)亚历山大走入了黑人的内心世界,并建构起一个“族裔化”的心理空间。
亚历山大的“黑人内部”挑战刻板化的黑人形象的生产是通过揭示黑人“他者性”的不确定性和荒谬性来实现的。亚历山大的大量诗歌都或多或少地触及到这一话题。在《早场电影》(“Early Cinema”)中,两个黑人小女孩认为这场黑与白的游戏该结束了,因为她们早已“厌倦了有色的正与误”;(Alexander,Antebellum Dream Book 11)在《保罗说》(“Paul Says”)中,保罗的父亲告诉他如果别的黑人孩子说他像白人男孩一样说话,那么他就回击说,“是啊,你说话也像白人男孩。/唯一的不同是,你像一个无知的,/没受过教育的白人男孩”。(Alexander,Antebellum Dream Book 13)可见,对于“他性”与“刻板形象”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的认识颇得霍米·巴巴的精髓。巴巴认为,“殖民话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在‘他性’的意识形态构建上对‘固化’概念的依赖性”,因此揭示出“固化”概念的荒谬将直接导致“他性”生产从根基上的轰然倒塌。(219)与巴巴一样,亚历山大也敏感地意识到,挑战刻板化形象的切入点不应该着眼于对形象的认同是否正确,而应该明白刻板形象话语造成了主体化的过程,并给人以貌似有理的假象。刻板化的黑人形象就是西方殖民话语不断进行生产的结果,是殖民幻想的武断的结论。针对这一现象,亚历山大独辟蹊径,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黑人是西方人头脑中的潜意识,那么什么是‘黑人潜意识’的个人和集体的表达呢?”(Alexander,Black Interior 4)显然,亚历山大试图探究的不是白人如何形塑了刻板化的黑人形象,而是黑人的自我界定、自我认识的过程和结果。正如她本人所言,她感兴趣的是“超越了社会自我表面的”、“复杂的”、“通常不可探知的内在”(unexplored interiority),(Alexander,Black Interior 4—5)是打破主流话语建构对黑人的意识形态上的羁绊之后,黑人的自我认知。她想要探知的是,如果在主流想象中刻板化的黑人形象被认为是真实的存在的话,那么在一个“超现实”的梦幻空间中,黑人又有可能呈现出何种形象和特质。
亚历山大在《种族》(“Race”)一诗中呈现的就是这种“黑人潜意识”的个人和集体的表达,这一表达戏仿了殖民话语的生产过程,却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黑人主体活动的空间,从而从根本上瓦解了黑人的“他性”的生产根基。黑人主体性的不稳定性在“种族”一诗中得到了全面的阐释。这首诗歌在一个亚历山大偏爱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空间中发生,采用的也是亚历山大惯用的自传性的叙事方式。一个黑人女孩在讲述着她的叔祖父保罗和他的家族的传奇经历:
有时候我想到离开阿拉巴马塔斯基吉的叔祖父保罗,
在俄勒冈成为一名森林人而那样做
使他的余生基本成为白人,除了
当他不带着他的白人妻子旅行却拜访他的兄弟姐妹——
现在在纽约,现在在哈莱姆,美国——一样的浅色皮肤,
一样的直发,一样的蓝眼睛,和保罗一样,也是黑人。保罗从未告诉任何人
他是白人,他只不过没有说过他是黑人,谁又能够想象,
1930年的俄勒冈森林人不是白人呢?
在哈莱姆的兄弟姐妹每天早晨都确信
没有人误把他们看作黑人以外的任何别的什么。
他们是黑人!棕色皮肤的配偶们减少了混淆。
许多其他人已经讲了,或者没讲,这个传说。
当保罗从东方肚子而来时,他和他们一样,他们的兄弟。(Alexander,Antebellum Dream Book 22—23)
这个黑人“他性”的解构和建构空间就是一个典型的亚历山大的“梦幻空间”,这一空间使得她的诗歌具有一种魅力独特的“预言的”(phophetic)和“幻想的”(visionary)抒情性。(Alexander,Power and Possibility 139)在一个“创造英勇的时刻”,女诗人讲述了一个“关于种族的故事”:叔祖父保罗与他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妻子之间传奇而复杂的关系。保罗因为成为一名俄勒冈的森林人而成为“白人”,因为大家认为“1930年的俄勒冈森林人”都应该是白人。可见,白人与黑人的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生理的、天生的,不如说是后天的、建构的。保罗和他的兄弟们因为有着浅色的皮肤和蓝色的眼睛,在外表上与白人无异,这种外表上的隐藏性使得他们的身份建构具有了富有戏剧性的过程和结果:保罗因为有一位白人妻子,而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白人;而他的兄弟们因为有黑人妻子,而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黑人。亚历山大对种族身份这一戏剧化的呈现仿佛是对法农的“那么黑人是什么?/是否属于这肤色的人?”的回答(法农32)。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通过对一名黑人女子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的梦境的分析而接触到她的无意识,而这一接触使法农有了惊人的发现:她非但绝对不暴露自己是黑人,反而要改变这个事实。她得知自己外祖母是白人,并对此感到自豪。她也因此感到自己的混血儿母亲“更加漂亮,更优雅和更出众了”。(法农32)而她最重要的心理改变是,她决定爱一个白人,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把亚历山大在诗歌中构建的梦境空间中的保罗和其兄弟们的种族身份建构的悖论放在法农对梦境的心理解析的背景之下,亚历山大的梦境空间因此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心理意义。而诗歌的结尾呈现了一个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结局:
许多其他人已经讲了,或者没讲,这个传说。
这次叔祖父保罗带着他的妻子去纽约
他让他的兄弟姐妹不要带他们的配偶,
那是这个故事结束的地方:不带着他们的讲故事的配偶,
象牙白的兄弟姐妹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兄弟。
“种族”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家庭,也是陌生人。
这里的一首诗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种族的故事。(Alexander,Antebellum Dream Book 24)
当保罗想要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兄弟姐妹见面,却要求他们不要带自己的黑人配偶的时候,“象牙白的兄弟姐妹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兄弟”。这个结局意味深长。保罗的心理在黑人中是颇有代表性的。“保罗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是白人,他只不过没有说过他是黑人”,这种对种族身份的模糊性定位是很多黑人,尤其是混血黑人的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暗示,是被殖民者的“从属情结”。而亚历山大对保罗的这种心理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她让他的兄弟姐妹拒绝再看到他和他的白人妻子。保罗和他的兄弟姐妹显然代表着黑人个人和黑人族群的关系。哈罗德·伊罗生认为,“相对于身体的原初性,构成族群认同的其它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74)然而,亚历山大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身体也是有欺骗性的,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身体也可以成为黑人自我否定和自欺欺人的帮凶。
在这个“族裔化”的心理空间中,“黑人性”得到了更为深刻而复杂的表达。在《今日新闻》(“Today’s News”)一诗中,亚历山大表达了自己对黑人性独特的理解:
我不想写一首讲述“黑人性
是什么”的诗歌,因为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们不是一个也不是十个甚至不是上万个东西
没有一首诗歌我们可以永远指望
也从来在数字上达不成一致。(Alexander,The Venus Hottentot 54)
显然,对于亚历山大来说,黑人性是多元的、开放的,以至于没有一首诗能够道出万一。同时黑人性也是动态的,在共时和历时的坐标之中不断调整和变化。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身份本身只有在一个动态的文化关系领域的语境里,被建构、被瓦解而重新流通。”(巴特勒166)看来,亚历山大想要探究的就是这个经过瓦解和重构,又重新流通的黑人身份的复杂性。
二、亚历山大的“性别化”物质空间
尽管“黑人内部”的空间意象性似乎更多的是在喻指层面上与亚历山大的诗学观发生着联系,但是细读她的诗歌和文论,我们不难发现亚历山大对物质空间意象近乎痴迷的偏爱。在《黑人内部》的开篇《趋向黑人内部》中,亚历山大援引了非裔美国女作家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黑人表达的特点》中关于“房间”的意象,并引领读者进入了一连串的空间意象之中。核心空间意象当属母亲的“起居室”。这个空间述说着母亲朴素的“美学”,同时也成为“她向我们揭示我们是谁”的温馨之地。可见,这个由母性的光辉充溢的空间是一个“性别化”的物质空间,而且在“家宅”的意象中这个性别化空间被演绎到了极致。在她的诗歌中,“家宅”的意象比比皆是:“祖母的公寓靠近/联合国”;“美国黑人公主”“住在纽黑文市一间没有老鼠的公寓里”等。
亚历山大的诗歌表现出了对不论是真实意义上,还是心理层面的黑人之“家”的执着的信念,而对于习惯于在“中间地带”游荡,对“无家”的流散状态习以为常的后现代作家、评论家和读者来说,亚历山大对“家”的这份执着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因此招来不少诟病。评论家吉尔洛伊(Paul Gilroy)就对亚历山大把家园理念融入政治幻想的做法不屑一顾,并不客气地指出亚历山大陷入了危险的“存在主义的泥潭”(255)。然而,如果深入到亚历山大的“黑人内部”的动态模式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吉尔洛伊等人的批判有失公允,也似乎操之过急了。这个看似琐碎的家园空间所具有的情感承载量和含义的丰富性非同一般。
亚历山大协商自我与群体的策略的出发点就是在物质和喻指双重意义上的“家宅”:一个黑人的女儿国。事实上,此种书写策略并不是亚历山大的首创。“家宅”的意象是法国当代评论家和哲学家加斯东·巴拉什著名的“空间的诗学”(12)建构的基础和中心意象,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诗意地安居”哲学观的落脚点,更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言的“文化空间”(13)的最终归宿。然而,对于认为“对空间的占有和运用是政治行为”的非裔美国女作家而言,“家宅”的含义恐怕要复杂而丰富得多。(Parmar 101)事实上,亚历山大的“家”的意象的内部操作和理念与贝尔·胡克斯等人的“家已经成为反抗之所”的观念不谋而合。(47)胡克斯曾经指出:“纵观我们的历史,非裔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家园所具有的颠覆性价值,我们由此进入一个无须直接遭遇到白人种族主义者侵犯的私人空间。”(Hooks 47)在《黑色美学:陌生与对抗》一文中,胡克斯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在讲述她在其中成长的屋子的故事:
这是一个屋子的故事。许多人在这个屋子里住过。我的祖母巴巴以此作为她生活的空间,她认定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由各种实物以及我们看待、摆布这些实物的方式所决定的,她确定地说我们是空间的产物。(103)
也许同为非裔女性的缘故,亚历山大的“家宅”意象中填充的也是由祖母、祖父等带有原型特征的人物和他们的琐碎却温馨的家庭生活:“一位带我出去用餐的教父”;“带我去喝茶的曾姑母”;“带我去博物馆的曾叔父”等都在强化着日常的家庭生活。甚至亚历山大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上朗诵的诗歌《赞美这一天》,也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有人缝拢褶边,缝补制服上的一个洞,补一只轮胎,缝补需要缝补的东西。/有人在一些地方,用在油桶上敲打的一对木勺、大提琴、扩音器、口琴、歌喉试图演奏和演唱。母子在等公交车……”(亚历山大166)事实上,“日常生活的政治学”是几乎所有非裔美国女作家的共同选择。(Rose 138)日常生活不但成为她们“历史书写的策略”(罗良功33),也成为她们空间建构的法宝。艾丽斯·沃克、托妮·莫里森等非裔女作家的小说几乎都是由非裔女性在“家”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的琐碎生活连缀而成,就像她们擅长缝制的被子。胡克斯对祖母巴巴生活的描写是颇具代表性的:
她擅长缝被子,她教我如何欣赏色彩。在她的房间里我学习观察实物,学习如何在空间中悠闲自在。在挤满各种家什杂物的房间里,我学习认识自我。她给我一面镜子,教我仔细端详。她为我调制五颜六色的酒,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美。(103)
祖母们在“家”这个看似狭小的空间中创造着生活、繁衍并哺育着后代,因为她们相信“空间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Hooks 103)。亚历山大的很多诗歌呈现的就是这个掌握着黑人女性命运的“家宅”空间和在这个空间中的非裔女性的典型生活。在《知识》(“Knowledge”)一诗中,一个非裔女孩讲述了自己一天的家庭生活细节:“并不是我们以前一无所知。/毕竟,有色女孩一定要知道许多事情/为了生存下来。我不仅/能缝扣子和褶边,我还能/从头开始做衣服和裤子。/我能挤牛奶,打奶油,喂/鸡仔儿,/清理他们的鸡笼,拧他们的脖子,拔鸡毛/烹饪他们。/我砍柴,生活,烧水/洗衣洗被褥,拧干/它们。/我能读《圣经》。晚上/在火炉前,无休止的工作和新英格兰的严寒/让我的家人疲惫了,/他们闭上了眼睛。我喜爱的是/歌声之歌。/当我开始读,‘一开始’/他们大都很喜欢。”(Alexander,Miss Crandall’s School for Young Ladies & Little Misses of Color 2)干净的白描勾画的是一个黑人女性生活中最私密的空间,简单、琐碎却温暖、亲切。这个空间画面显然带有女诗人鲜明的自传性因素,是一种典型的亚历山大式的“个人模式”(Alexander,Power and Possibility 139),也带有一种族裔女性的普遍性,是一种“我+我”而成的“第一人称集体声音”。(Francis)亚历山大在对黑人女诗人安娜·库柏(Anna Julia Cooper)的研究中发现了库柏的这种独特的诗学策略,并指出,这种第一人称的集体声音开辟了一条审视和记录不可调和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最有效途径,而库柏不但在书写中创造了自我,而且为非裔美国女性知识分子构建了一个共同空间。库柏的策略和壮举也成为亚历山大的目标和自我赋予的使命。正如她在《诗艺第100首:我相信》(“Ars Poetica#100:I believe”)一诗中所写的那样:“……/诗歌是你在/角落的尘埃中找到的,/在公共汽车上听到的,是/细节里面的神,/是唯一那条/从此处通向彼处的路径。/……/诗歌(现在我听到我的声音最响亮)/是人类的声音,/难道我们彼此没有一点兴趣?”(Alexander,American Sublime 56)对于亚历山大而言,诗歌是容纳一个非裔美国女性生活细节和生命精华的唯一的空间,也是一条把自我和集体联系起来的唯一路径,同时也是一种把非裔美国女性带向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可见,亚历山大的“黑人内部”所承载的是非裔美国女性共同的生活空间和共同的生命体验。
然而,以上的解读还只是从表层考察了亚历山大“黑人内部”的“性别化”特点。与她那极富包容性和承载量的“族裔化”空间一样,这也是一个承认“他者”之间差异的空间,换言之,这个“性别化”的空间不是男/女二元对立的,也不是排他的。与贝尔·胡克斯、安德洛·罗德等黑人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把性别和女性身体本身作为政治和解放的力量的操演不同,亚历山大诗歌中的女性性别的定位不是以牺牲黑人男性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亚历山大与艾丽斯·沃克、托妮·莫里森等前辈均有很多不同。亚历山大的理想是做一位“美国黑人公主”,如格林童话中的潘索拉公主一样,等待着“被男人解救”,然后为自己的丈夫烹饪美食佳肴:
一位美国黑人公主,
嫁给了一位非洲王子,
住在纽黑文市一间没有老鼠的公寓里,
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屋檐下。(Alexander,Antebellum Dream Book 62)
“一个屋檐下”为亚历山大的性别空间做了最好的诠释。首先,这个空间是一个与外在的世界相互参照的黑人女性的共同的家园;其次,这个空间并不排斥男性的参与。正如普拉提哈·帕莫(Pratibha Parmar)所指出的,黑人妇女的身份创造不是在“关系”、“反对”或“纠正”中完成的,“而是内在、自为的”。(转引自索亚123)黑人女性身份的完整建构更多地取决于女性自我认知的完整性和对两性关系和谐的追求,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黑人女性的独立和自信的基础之上的。
三、结语
亚历山大所建构的“黑人内部”诗学空间继承并发展了非裔美国诗人的诗学建构策略和诗学理想,同时也赋予了这一诗学理念以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富有承载量的文化空间在抽象为“族裔化”心理空间和具象化为“性别化”物质空间之后,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而亚历山大的诗歌也因此实现了与非裔种族和女性群体的身份建构的对接。这样的诗学空间所建构的是一个多维而动态的黑人文化身份,从而实现了亚历山大不同寻常的诗歌理想,使得她的诗歌成为了“有生命的东西”,并具有了能够抵抗暴力的力量。(14)
亚历山大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建构在当代非裔美国诗人中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首先,作为学院派诗人,亚历山大的诗歌作品延续了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从而使得黑人文学的知识传承和书写传统逐渐受到了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说,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当代非裔美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创作扭转了非裔诗歌研究中“口头标题,方言标题,说唱、音乐的标题”一直居于评论的主导地位的现状。(Alexander,Power and Possibility 159)其次,在“后灵魂”时代的文化领域,音乐和娱乐文化似乎控制着主流的话语权,并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成为广大听众和观众接受、消费和娱乐的对象。纵然是诗歌创作,似乎表演诗歌也比印在纸张上的诗歌文本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然而,在这场喧闹的视听盛宴之外,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诗人以他们的深邃、冷静和知性的表达为文化的含义开启了另一个空间,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所倡导的价值是“知识的”、“文化的”和“美学的”。(Pereira,“The Poet in the World,the World in the Poet” 722)他们的知性创作使得充满商业气息的“后灵魂”时代的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坛增加了一丝厚重感和知性美,从而为全面定义这一时期和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注释:
①亚历山大主要诗歌作品包括《霍屯督的维纳斯》(The Venus Hottentot,1990)、《生命之躯》(Body of Life,1996)、《战前梦之书》(Antebellum Dream Book,2001)、《美国的崇高》(American Sublime,2005)、《年轻女士和有色女孩的克润代尔小姐学校》(Miss Crandall's School for Young Ladies & Little Misses of Color(与Marilyn Nelson合著,2007)、《赞美这一天》(Praise Song for the Day:A Poem for Barack Obama's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by Elizabeth Alexander,2009);论文集包括《黑人内部》(Black Interior,2004)、《权力与可能性》(Power and Possibility,2007)等。
②亚历山大获得的诗歌奖项包括杰克逊诗歌奖、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奖、诗歌手推车奖、古根海姆奖、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诗歌奖等。
③Post-Soul最早由Nelson George提出,泛指利用黑人演员拍摄电影时代(Blaxploitation Era)之后的黑人流行文化。这一说法被Mark Anthony Neal借用并拓展,用以描述黑人权力运动之后的非裔美国社群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经历。在《灵魂的孩子:黑人流行文化和后灵魂美学》一书中,他又提出了“后灵魂美学”观,用以特指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黑人流行文化的独特表达和审美。参见Mark Anthony Neal,Soul Babies:Black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ost-Soul Aesthetic(New York:Routledge,2002)1—22。
④例如,在Nelson George的Buppies,B-Boys,Baps,and Bohos:Notes on Post-Soul Black Culture(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2)中,Ishmael Reed,Bell Hooks,Toni Morrison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关注,而诗歌和诗人却缺席了这场非洲美国文化的盛典;在Mark Anthony Neal的Soul Babies:Black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ost-Soul Aesthetic中,也没有对20世纪末的非洲裔美国诗歌给予足够的关注。
⑤该数据参见Nelson George的Buppies,B-Boys,Baps,and Bohos:Notes on Post-Soul Black Culture(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2)10。
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亚历山大的诗歌创作。张子清教授翻译了亚历山大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上朗诵的诗歌《赞美这一天》,见《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第166—67页;范晨、吕洪灵对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和她的《赞美这一天》进行了介绍,见《译林》2009年第3期,第171—73页;罗良功教授则以《赞美这一天》为例,对亚历山大诗歌的历史书写进行了探究。详见《济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31—35页。以上三篇文章均聚焦于诗歌《赞美这一天》,对亚历山大诗学和诗歌的全面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⑦“空间的诗学”是法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科学哲学家巴拉什从现象学和象征意义的角度,对空间的全新解读。他提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他的这一空间观不但对建筑,也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拉什于73岁高龄时创作的《空间的诗学》一书成为他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文借用了巴拉什的“空间的诗学”理念考察亚历山大的“黑人内部”所具有的文化和诗学容纳性和包容性,颇有收获。
⑧在《黑人内部》中,亚历山大对当代学术界的“去族裔”、“去性别”的趋势提出了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界滋生了一种诡辩的趋势:理论化、建构并解构身份‘种类’以至于有些人往往忘却了女性和有色人种本身,身体,他们写作那些我们急于需要读的东西,他们总的来说在学者中没有得到充分呈现,那些女人和有色人种的声音和行为在历史、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常常被边缘化、琐碎化,被忘记或者抹去。……极端的程度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女性的性别研究;没有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研究;就好像这些使得这些课程、书籍、节目和科系存在的人们的政治抗争毫不相关了,好像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平坦的运动场上。”详见Elizabeth Alexander的The Black Interior,第201—202页。
⑨关于达夫的“世界主义”文化身份的内涵参见Malin Pereira,Rita Dove's Cosmopolitanism(Urbana and Chicago,IL:U of Illinois P,2003);拙文《阅读·误读·伦理阅读“俄狄浦斯情结”——解读达夫诗剧〈农庄苍茫夜〉》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论述,详见《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73—85页。
⑩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刻板形象的经典论述见贝尔·胡克斯:《“大众热屄”:文化市场对黑人女性性欲的再现》,引自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5—85页;以及Audre Lorde,ed.,Sister Outsider:Essays and Speeches(Freedom,CA:The Crossing Press,1984)2—10。
(11)罗德的爱欲书写策略参见拙文《爱欲的神话》,载《济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36—43页。
(12)“家宅”意象的建构参见巴拉什:《空间的诗学》第一章“家宅”,第二章“家宅和宇宙”。
(13)弗洛伊德曾经说,“文化空间很有可能是唯一配得上家这个奇妙的名字的空间,在那里艺术家和读者们作为创造和再创造的主体,相安无事地保持着‘他们各自的家的主人’的[身份]。”引自Therese Steffen,Transcultural Space and Place in Rita Dove Poetry,Fiction,and Drama(Oxford:Oxford UP,2001)23.
(14)在《诗艺1002号:重整旗鼓》(“Ars Poetica#1,002:Rally”)中,亚历山大表达了她对诗歌的看法:“诗歌/通过它所说的/或者它如何说的/什么也改变不了,改变不了/但是诗歌是有生命的东西/由鲜活的生命创造/(一个小盒子中的现场的声音)/像生活一样/它是能抵抗/暴力的一切)”。参见Elizabeth Alexander,American Sublime,p.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