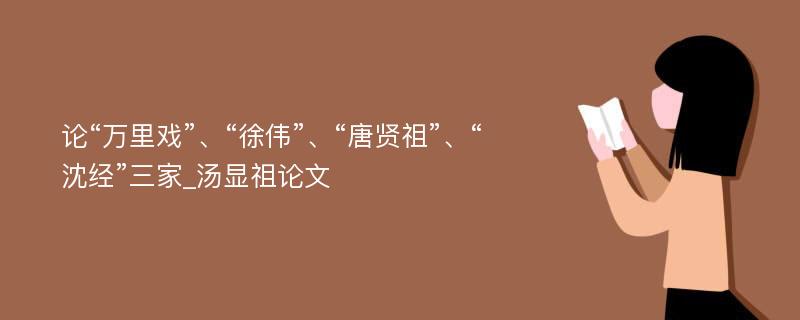
万历剧坛三家论——徐渭、汤显祖、沈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坛论文,万历论文,三家论文,汤显祖论文,沈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6世纪中叶,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涌起,它要求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呼唤新的精神价值和社会性格的诞生。这种叛离传统轨迹的观念逆动,在一代剧作家的思维模式、人格模式、生活模式中得到多角度的折射,于是,有率先疾呼者,有深沉鼓荡者,也有拼力抵拒者。投影在万历剧坛上,就出现了三位代表人物,他们的人格、文学观念、社会观念各不相同,生活和创作道路也不同,但他们各自取得了自己的辉煌。他们无疑可以作为这一时代的象征而存在。他们就是:徐渭、汤显祖和沈璟。
徐渭出现在万历文坛的时候,思想界还被压挤在王阳明理学的躯壳中呻吟,诗界则弥漫着后七子的堆垛陈风——这位先行者开始了他孤独的长啸。
在色彩斑澜的明代文化史上,徐渭无疑是一位奇才。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曾这样评价徐渭:“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余渭文长无之而不寄者也。”(《徐文长传》)确如所言,徐渭的一生,在在皆“奇”。他的经历奇:九赴科举,连战皆北,三次从军,二度出塞,击杀继妻,坐监六年,声名噪起,终老布衣。他的个性奇:豪放无羁,狂荡疏纵,傲诧权贵,时而宣愤。他的病奇:忽忽发狂,引锥自锥其耳,以槌捶碎阴囊,数度自杀未遂。他的艺术成就奇:诗、文、书、画、戏曲、文论,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凡所涉猎,无不惊世诧俗,各种艺术样式到了他手里,无不成了抒写个人情性、宣泄胸中磊落不平之气的凭藉。
徐渭奇特的生命形式归源于他所具有的“异端”思想。他从幼时就不为儒检,杂涉老庄仙释,“独喜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及古书法”(《萧女臣墓志铭》)。先是“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学。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自为墓志铭》)。究徐渭之思想基础,可以归结于一句:法乎自然。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而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读龙惕书》)他把顺应人的血肉之躯而全其自然天性视为人生的基本要义,这就是“中”,所谓“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论中》)。徐渭推崇人的自然天性的认识和当时另一位思想家李贽反对禁锢“人欲”的哲理达到了殊途同归。
徐渭曾师事过一位王学左派的得道弟子王龙溪,王龙溪的一种理论就是徐渭一生行为的写照:“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脱洒,本无挂碍系缚。“尧、舜、文、武之兢兢业业,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体不失此活泼脱洒之机,非有加也。”(《明儒学案》)徐渭终身追求适心任性,放情恣怀,不为心违,不为性拘,恰恰是为了维护自己活泼脱洒的天性。更重要的,徐渭生活的时代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晚明个性解放的大潮已经开始了它初期的波涌。作为一代思想先驱,徐渭已经敏感地觉到了时代的胎动。这才是他不安于正统儒教理学而旁求它索的根本动因。
徐渭这种不受理性约束的意志与正统儒家思想的要求有着很大的距离,因而他在俗世里被碰得头破血流,终生坎坷,穷困潦倒,甚至不得不屡屡入人幕府而求温饱。徐渭的悲剧在于:现实的改变比理想的升起缓慢得多。历史的反差是那样巨大,它所引起的不能不是渗透骨髓的痛楚,难言的失望,以及置身于荒野之中的寂寞。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苦闷和困扰,充溢于徐渭内心世界的,正是这种苦闷。作为新旧思潮交汇中的先觉者,徐渭经历了由传统命运向人的解放艰难蜕变过程中的全部痛苦和别人无法代为受过的精神折磨。
然而徐渭的价值却显示为:尽管面对如磐的压力,他绝不退缩。他奋争了,他呼喊了,因而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道鲜亮的痕迹。徐渭生命的特殊魅力,在于他对自己人格理想孜孜以求的贯彻。长期以来,坟墓一样的精神困禁使人们习惯了坟墓一样的生活,在理念对自我的持续抑制和压迫下,欲望消失了,情感枯竭人,个性泯灭了,“无怨”、“无己”成为人们世世代代所遵循的人格模式。而徐渭竟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其疏狂纵横的独立特行,以其敢歌敢哭敢笑敢骂的自由旷达,向死寂般沉静的旷野投出扎枪!在人们的冷眼和侧目之下,徐渭独自坚持着他顺应天性的做人原则。如果说,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统治所培育的传统性格是以“无个性”为其基本特征的话,徐渭的怪异行为恰恰显示了一种强烈的个体意识。
徐渭的剧作精神,足可以被视为明清文人杂剧抒怀写愤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意蕴已经与前代根本不同。首先,他对于封建主义本身有着更深刻的否定。元代剧作家虽然也嫉恶如仇,但他们更多在政治上还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在严厉批判社会的同时,总是设法为人们指出一条光明的出路,在揭露丑恶灵魂的同时又着迷于一些天使般至善至美的形象。他们普遍努力向社会推荐善战胜恶、美战胜丑的济世药方,以光明的尾巴表现正义和公理的最后胜利。而徐渭,则已经放弃了对理想主义的肤浅崇拜,开始真正直面混乱、荒谬的人生。其否定的锋芒,不仅指向了自己存身的现实社会,而且指向了传统的精神世界,这样,他就揭穿了封建社会所有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其次,正因为徐渭的否定是全面的,所以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把对于具体社会问题的批判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以整体象征的方法,向我们展示一种荒谬的人生状态,一个污秽不堪的世界。这与元杂剧作家总是把批判矛头对准社会的某一局部问题有着明显区别。再次,徐渭不象元杂剧作家那样,把目光始终放在本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上,而注目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人的自然属性,他所实现的,很大程度上是对人自身的审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们是一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相对恒定的东西。正是在这些临界点上,徐渭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完成了中国戏剧文学由元代的政治、社会层面进入到明代人生意识觉醒层面的超越。
在那晦雨如磐、孽风横肆的世界里,徐渭恰似一道划过长空的迅疾闪电,那样地勇猛,那样地神奇。他以自主自立、我行我素、充满浪漫色彩的精神和个性特征,在晚明的天空上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他那以个人情性为最高存在的执着追求,他那孜孜不倦、至死不悔的人生实践,他那卓然不群、敢笑敢骂的个体形象,显示了一股强大的闪耀着时代亮色的个性力量。这种力量在那个时代,无疑具有历史的超前性和进步性。
当徐渭独自在文坛上奋争的时候,他是孤独的。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了自己的同道和同盟军,那就是后来的剧坛大纛汤显祖。
汤显祖与徐渭在哲学思想、文艺观以及人格理想方面都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两人都得力于明心见性的左派王学,也都受到佛、道的不同影响,崇尚性灵。两人都提倡以真情作文作剧,徐渭所渭“人生坠地,便为情使”,“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选古今南北剧序》);汤显祖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牡丹亭记·题词》),“不真不足行”(《答张梦泽》)。出于共同的文艺观念,两人在反对当时垄断文坛的复古主义文风时起到互相支持的作用。为人行世,两人也都孤高狷傲,只不过徐渭近狂,汤显祖趋清,这与二人不同生活道路和社会地位的影响有关。
当时和以后的人也都以徐渭和汤显祖相提并论,虞淳熙《徐文长集·序》说,王世祯、李攀龙虽横扫文坛,“所不能包者两人,颀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钱谦益说法略同:“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岿然有异。”(《列朝诗集》丁集袁宏道小传)袁宏道《喜逢梅季豹》诗曰:“徐渭饶枭才,身卑道不遇。近来汤显祖,凌厉有佳句。”王骥德《曲律·杂论下》:“于南词得二人:曰吾师山阴徐天池先生,瑰玮浓郁,超迈绝尘……曰临川汤若士,婉丽妖冶,语动刺骨”。
汤显祖是一位在晚明的思想异动中有着多方建树的人物,正不只是一位剧作家而已。在人生理想上,他有自己的超常抱负,并终身为之奋斗。在政治领域里,他有自己的卓绝见解,并付诸尝试。在思想领域里,他有自己的独特观念,并以之作为自己生命的最终目标而终生追求。在当时诗坛上,他也有着自己独辟蹊径的闪光。因而,汤显祖的生命,显现了另一条独异的人生道路。
汤显祖一生清傲,磊落好侠,常有出世之想。然而为实践政治思想,他强迫自己在科举仕途的道路上勉为经营,但清傲仙侠之气不泯,终不能为时所用。发为歌吟,则时而仙佛,时而侠情,总是封建礼教缚不住者。当时人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享叙》中所说的“《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可谓概括出了汤显祖思想驳杂不一而色彩斑澜的特点。
汤显祖生命中的第一件独异之事是永远不依附于人,这在其他封建官场中人是绝难做到的,也是他不同于徐渭的地方。尽管这使他一生倍受坎坷,但也成就了他极其高洁的人格。汤显祖名高心杂,致使他场屋困顿,长期郁郁,入仕后又久滞下僚。但他决不因此而放弃原则,依人而贵。他一生中屡有被贵宦引重的机会,但却屡次拒绝,即使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也决不后悔。这给他换来了清名,从而赢得了包括正统官修《明史》在内的各种传记里面异口同声的赞誉。汤显祖之所以有这些举动,当然是由其追求个体独立的精神所决定,所谓“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他的个性孤傲,从不肯屈就于人,为官“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查继佐《汤显祖传》),这也是他终身仕途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汤显祖生平所透示出的这种豪迈俊达的意气,恰恰体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倾向,那种突破传统束缚而追求个性自由的人生气概。
汤显祖生命中的这种慷慨气势,促成了他建立自己的政治抱负,并终生为之奋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象徐渭那样终身潦倒,营营苟苟,而是以俯拾功名的气概,取道仕道,希望一展政治思想,实现自己个体生命的辉煌。他自认为有治理天下之术,他三十七岁在南京时曾充满豪气地作诗自赞曰:“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也曾对辅臣余有丁说过:“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恨不见吾师言,言之又似迂者然,今之世卒卒不可行。”他一生与人书信谈论,所言也多为天下事,沈际飞为作《王茗堂选集·尺牍题词》说:“于国家利病处纚纚详言,使人读未卒篇,辄憬然于忠孝廉节。”
正因为汤显祖生命中充满了蓬勃真气,当他发为歌吟,就凝聚为一点之情,在晚明思想界的躁动中,汤显祖拔地而起,高擎着“为情作使”的旗帜,呐喊鼓荡了一生,掀起阵阵波涌,影响了几代精神。
当汤显祖写出《牡丹亭》的时候,他已经在人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而变得坚强老辣,有了为追求理想而百折不挠的体验和经历。他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认识已经走向成熟,而在哲学思想上也找到了情理冲突的突破口,即发明了“情至”的理论。汤显祖认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记题词》)他说,对于常人,世上的许多事情往往不容易理解,这是由于他们只会用常理来衡量,他们怎么能理解“情”超出“理”的那部分呢?这是汤显祖对于人性正当欲望的肯定,对于人生追求精神的赞扬,对于腐朽理学意识的抨击。有感于封建社会对于人们的精神统治,有感于礼教文化对人类本性的残害和压抑,汤显祖艺术地将人的天性还原、放大,赋予其合理的存在和实现的权力。因而,企盼人的自然天性的复归,是他在《牡丹亭》中所要揭示的人生真谛,也是他创作这部剧作的真正契机。
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把人的解放狭隘地理解为实现某一政治制度或某一经济模式的话,那么,它还应当是一种更自由、更深入的人的生命本质的全面实现。汤显祖的伟大,正在于他第一次把淹没在神圣庄严的封建礼教模式中的个人的人性欲望作为一种合理的存在,提升到可以令人正视、令人崇尚、令人反省的高度;正在于他将人的生命的实现作为一种理想和憧憬,艺术地准确地展示出来;正在于他写出了觉醒的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正在于他推出了一个值得几代人去为之奋斗的人生主题。就《牡丹亭》来说,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在作品所提供的文学世界的表层徜徉,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决不是用“语言”、“人物”、“情节”等尺度所能衡量的。如同孕育了它的众多文学外的原因一样,它的意义也超越了这一界域。
简而言之,在价值观上,它公开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对当时控制了社会各个角落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和否定。无论谁都不会以为汤显祖只是在没完没了地跟人闲扯一个女人爱美、伤春、动情之类小到不能再小的生活琐事。正由于作者的笔触深入到了人的本质方面,才使杜丽娘这个普通贵族小姐的个人命运和整个社会的进程连结起来。其次,它摆平了从来就不平等的男女之间的位置,使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站在了和男性比肩的同一地平线上。杜丽娘那丰富、热烈的情感世界,她那郁勃、蒸腾着的青春生命冲动,令多少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为之瞠目结舌,也引起多少妇女发自心灵深处的强烈共鸣。人不能总迷失在外部世界里,让自己的精神王国无所依托。当众多呻吟辗转于礼教文化罗网里的女性,觉察并感知了自己强大而热烈的生命冲动之后,必然会对陈腐扭曲的观念世界表示不满,她们要挣脱传统的桎梏,寻找重新衡量自己生命行为的合理尺度。在这种文化背景与社会心态中,汤显祖的出现,无异于给人们提供了一座庇护心灵的屋宇,收容下众多的田野上流浪无依的魂灵。因此,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盛开了戏剧领域里的一条奇葩,更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使人们在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发现了生命本身的光彩和生气。
如果说,徐渭的价值在于他以怪异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震落了万历剧坛初期弥漫的浓雾晨星的话,那么,汤显祖则以其日月经天、气贯长虹的魄力宣告了中国戏剧一个崭新局面的到来。
徐渭年长汤显祖二十九岁,也就是说,当徐渭开始他文坛的苦苦探索时,实际上是在长期孤军奋战。当他被强大的社会力量碰得头破血流、气衰力竭时,终于偶然发现了自己的同道汤显祖,他是何等的高兴!那是在徐渭于万历八年到十年间(1580-1582)客居北京的时候,他偶然读到了汤显祖的诗集《问棘堂集》。他称颂不已,誉汤为“真奇才,生平不多见”,并作诗一首:《读问棘堂集……拟寄汤海若》。当时徐渭尚不认识汤显祖,这不知道这首诗能否寄到汤的手中,所以说“拟寄”。徐渭诗中说“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对汤显祖不随波逐流,独奏均天之响的诗作作了高度的评价,并说自己是“执鞭今始慰平生”,终于找到了同好。徐渭对汤显祖的推崇从他摹仿汤诗的形式也可以看出,这就是采用汤氏七言古诗《芳树》复沓回环的手法写作《渔乐图》。以徐渭一文坛前辈而摹仿后生创体,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况且徐渭平生自负极高,极难对人表示佩服,足见他在文坛挣扎一生终于找到知音时的兴奋程度。徐渭尽管一直没有见到汤显祖,但他对汤的情谊已经非常浓厚,当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被贬徐闻后,徐渭托人给他带去自己刻印的自选诗集和些许礼物,并索要汤的其它诗作(见《与汤义仍》)。沈德符对此评价说:“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崇甚至。”(《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
二人对于对方的戏剧作品也都极其称赞。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太觉頫心。而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
不过,汤显祖对徐渭的态度似乎并没有那么热情,他在读到徐渭的诗和信之后,回了一首诗,只是淡淡地写道:“将公无死或能来。”(《秣陵寄徐天池渭》)希望能够与徐渭结识。他对徐渭作品的评价也没有那么高。沈德符说:“余后遇汤,问文长评价何似,汤亦称赞,而口多微词。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沈德符把汤显祖对徐渭的态度解释为高傲,不一定准确,但汤显祖大概会对徐渭的过于狂放有看法,因为他本人并不采取这种生活态度。当然,汤显祖对徐渭还是很关心的,这从徐渭死后汤给自己的朋友山阴知县徐瑶圃写信要他照看徐渭的后人(《寄余瑶圃》)可以看出来。
与徐渭和汤显祖相反,沈璟却是一位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人物。在他的时代。因了一些思想先驱的奋力鼓荡,以及众多平庸士大夫文人的推波逐浪,士风已经变得颓靡。而身处周围放浪狂荡的文人群里,他能独自傲岸挺立,不为流俗所动,谨言慎行,斤斤于礼法,其行为举止受到当时诸多谦谦君子的推崇顶礼,成为一代中流砥柱。然而,尽管沈璟作为曲学家取得了崇高的荣誉,也留下了丰厚的戏剧作品(共有传奇十七种),但他一生所执着遵循的人格模式,却限制了其戏剧作品的成就。
沈璟的一生,是以道统为己任的一生。他的文化性格和人格模式自始至终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规定和制约。在政治领域,道统是他恃以批评朝政、抗礼王侯的精神凭借;在艺术领域,道统是他据以安排戏剧情节、塑造典型人物的心理依据。
沈璟的性格,耿直而又谦恭,属于典型的正统士大夫人格。无论是在仕途沧海中跋涉,还是在乡间社里中居处,都鲜明体现出来。他的崇拜者、曲论家吕天成说他:“束发入朝而忠鲠,壮年解组而孤高。”(《曲品》)也说出了一部分实情。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万历十四年(1586)上疏请立君储而忤旨、被连降三级之事,这是沈璟生命历史中的一段重要插曲。他的抗言极谏,完全是出于“公”心,他所挂怀的,只是要“定大本”、“详大典”、“固国脉”,亦即要遵循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道”,和体现上下尊卑长幼关系的“礼”。在他的头脑中,这些天地间至上至尊的法则,是包括皇帝在内任何人都不可逾越的,他有责任来监督实现它,哪怕个人因此而受到打击也在所不辞。
但是,沈璟上疏的着眼点却与五年后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有着差别。汤显祖攻击的是当朝执政的施政弊端,矛锋直刺神宗,着眼于改变现实政治。沈璟抨击的是皇上不按祖宗常规行事的举止,着眼于守护传统礼法。汤显祖唯其对于现实政治不满,故而一直与执政保持清晰距离。沈璟因为只注目于国本法典,对当时的党争派斗倒没有什么嗅觉。这种差别是由二人不同的思想观念造成的。
沈璟以道统自任的精神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剧作家都选择了耽情耽性的道路,有些甚至走上个性解放之途,而他却丝毫没有感受到时代气息,虽然一边以词曲自娱,一边却仍然以卫道为己任呢?这不能不归因于他“金张世裔,王谢家风”(吕天成《曲品》)的出身环境和师受于唐枢、陆稳理学大儒的经历。家庭环境、慈父严师所代表的正统文化规范对沈璟的塑造是多方面的。它们不仅使之成为博文通书、娴熟礼乐的专家,而且造就了他内在的心理性格和价值观念。它们以其超然于个体存在之上的历史文化的意志,强有力地影响了沈璟的自我选择。沈璟命中注定地要接受这种文化规范对他的教化和制约。出身这种既定的文化环境,沈璟过早地积累了对于“道”的理想和信念。以这样的心理和精神基础去感知与体验世界,沈璟很难对外部世界采取一种自由、开放的顺应态度。他只能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精神领域的狭小范围内,和他的家庭、和他的师长、和他所接受的既定文化,一起失落于时代。
孔子曰: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沈璟在政治生活中求道碰壁、失意而归后,就自隐于词曲创作,所谓“袖手风云,蒙头日月,一片闲心休再熟。鹍鹏学鸠各有志,山村钟鼎从来别。”(《红蕖记》首出【千秋岁引】)“词隐生”的自号就是他心境的剖白。一个正统封建士大夫,怎么肯于拉下脸面,以被道学先生视为末流旁枝的戏曲创作为精神依归呢?这一方面要归结于当时的社会风气,沈璟的生活环境和他的个人兴趣使然,一方面也可看出沈璟对政治失望的程度。而且,沈璟在最初开始戏曲创作时,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畏畏缩缩的。我们看他的处女作《红蕖记》,署的是假名“施如宋”,只在结尾处曲文里暗寓作者真实姓名籍里,就能够明白他的这种犹豫。不过,以后也就一发而不可收了。然而,即使是在放情驰意的“征歌度曲”生涯中,沈璟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道统理想。甚至可以说,沈璟在戏曲创作中又找到了体现自己理想的另一途径。由政坛而剧坛,这其间几多曲折,几多辛酸,但,沈璟依然是沈璟。
打开沈璟的“属玉堂传奇十七种”,你看到的,不是孝子贤妻、忠臣义仆,就是奸夫淫妇、强徒暴吏,随处可以嗅到一种浓郁的道学气味。沈璟将宏道的热情,物化为实在的艺术创作,使他在政治生活里没有得到的“道”,在他自己的传奇作品里复活了,复活在精心安排的人格形象中,复活在因果报应的情节模式里,沈璟的作品,大多隐寓着他讽喻、劝世和教化的目的。《埋剑记》首出“提纲”开场副末所说的“作劝人群”的主张,就是他的创作宣言。吕天成在《义侠记·序》里所说的“先生诸传奇,命意皆主风世”,就是他的意向追求。
传奇作品在明代中叶已经形成生旦离合的套子,沈璟自然也不能不借用。然而他自己就说他不长于此,所谓“先生自逊谓不能作情语”(《曲品》)。试读他的此类作品,确实令人感到情短而“道”长。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书后,世人皆为其生死之情所动。沈璟希图与汤显祖一较雌雄,起而仿之,创作了《坠钗记》(又名《一种情》),即如王骥德所说:“词隐《坠钗记》,盖因《牡丹亭记》而兴起者。”(《曲律》卷四)从存本《一钟情》看,沈璟创作《坠钗记》确实在构思上极力模仿《牡丹亭》。然而,就象沈璟改编《牡丹亭》是佛头着粪一样,他模仿《牡丹亭》也是东施效频、画虎不成反类犬。吴兴良感念崔兴哥而身亡,遂借妹妹庆娘的体骸还魂会崔,一年后离去,遗言父母将妹妹嫁崔。这本来已经是无稽的附会,根本没有了《牡丹亭》讴歌青春生命和人间至情的内蕴,加之兴娘会崔生是因为二人有一载夫妇之份,而原为双方父母约为婚姻也不算私奔……就这样,沈璟将一个神驰色动的情恋故事又归到了天赋姻缘和符礼合德的夫妇之伦上。
沈璟情短而道长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他以道学自任的必然结果。他缺少的是晚明思潮中那种肯定情欲的理性自觉,反而有着反情窒欲的自觉,因而他在处理少男少女春情萌动的情节时,只好归之于姻缘前定的宿命,这是他失败的根本所在。在沈璟的十七部传奇中,王骥德仅仅肯定了他的处女作《红蕖记》,而说他“其余诸作,出之颇易,未免庸率”(《曲律》卷四)。也从一个方面接触到沈璟创作的弊端,即为了自己的讽世需要而写作,艺术上则粗制滥造。
和他的传奇作品一样,沈璟一生曲律著作也非常丰富,这些著述集中阐述了词曲的格律和语言问题。正如许多学者一致指出的那样,沈璟的格律理论是中国戏曲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推究沈一生孜孜致力于曲学的深层动机,仍然和他以道统自任的思维方式相连。王骥德说:“词隐生平,为挽回曲调计,可谓苦心。”(《曲律》卷四)说出了沈璟希望在曲界力挽狂澜的使命感。沈璟戏曲理论的中心意旨是强调创作要遵循形式框范,他给自己定的任务就是制定创作守则,《曲品》所谓“差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辟路”。守则的基本原则是“法古”,正如王骥德在《曲律》里一再指出的那样:“词隐于板眼,一以返古为事”,“斤斤返古,力障狂澜”,“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沈璟为此用尽心力,鞠躬尽瘁。
于是,一场貌似围绕着形式格律实际却是基于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论争——“汤沈之争”,就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沈璟和汤显祖两人可能曾经谋面,万历八年(1580年)汤显祖赴会试,沈璟为授卷官。但二人一生没有任何交往,甚至连争论都是通过曲折的方式由中介人吕天成等转达信息而进行的,尽管沈璟对于汤显祖的作品极其熟悉甚至佩服,汤显祖对于沈璟的活动也颇为留意和重视。
沈璟对于汤显祖的要求:“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沈璟【二郎神】套曲)似乎只是从形式方面提出了问题。但汤显祖却看出了其中的内涵,一针见血地反驳:“彼恶知曲意哉?”(吕天成《曲品》)汤显祖平素在文艺观念上有着“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汤显祖《答吕姜山》)的主张,这和他张扬独立的个体意志,以及和晚明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都是相通的,岂能为了区区格律就被束缚了个性!追究沈璟的深层心理契机,不正是要把鲜活的有机生命体强捺入某个坚冷的行为框范吗?
可以看出,沈璟在这里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执着追求道统的理念有着明显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然,沈璟在曲律上面成功了,他的成就使他有了一大批追随者,使他成为曲中之“圣”,吕天成说他是:“顾盼而烟云满座,咳唾而珠玉在豪。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游刃余地,词坛之庖丁。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为北面。”(《曲品》)然而,他的创作实践却使他永远无法进入天才剧作家的行列。
其时,人文思潮已经开始裹挟大地,道统已经不再是每一个文人的必然选择,处身于同一块文化土壤,徐渭选择了新的人文理想作为自己生活信念的参照系。他追求独立和自由意志,蔑视环境、拒斥法度、任性而为,在乖戾任纵的行为方式里传达一种严肃的人生观念,在放荡无羁的人生形式中呈现一颗先觉而痛苦的心灵。他将自己奇特的个性和生命,化为一束璀璨而耀眼的强光,照亮了当时的文坛。汤显祖生活信念的参照系是现实的血肉人生。在宋明理学业以规范化、制度化了的精神桎梏中,他訾议社会为人们所设计的人生道路和人格形式,热情发掘生命自身原色的美丽,为那些在茫茫暗夜里彷徨无着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目标,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唯有沈璟,把自己的个体生命紧紧绑在道统的腐朽车轮上,因而只能成为一具封建正统文人的干枯标本而为后人所见。
与徐渭、汤显祖相比,沈璟的剧作缺乏个体意志、情感和价值的显示。他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更象是根据既定的人格模式、根据一定的脸谱、类型设计出来的。他从不在群体环境中张扬个性,他从不会与现存的总体秩序有半步的差池。即使是一生以道自任,他也从不敢把它归之于对特殊自我价值的追寻与实现。也许在内心的体验沉思中,他也默默地咀嚼着个人命运沉浮的悲哀,但出之于口的却都是为“道”、为天下、为君国、为世道的高尚目的。他把自己的意志完全消融在这些抽象的内容之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支点。
沈璟的选择尽管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和些许学究气味,但也不乏崇高。它根基于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深深忧患。面对晚明世道人心的历史颓势,沈璟本可以有其它选择。例如象许多无行文人那样在官场中随波逐流,以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为依旧;或者象更多的清人高士那样蔑视理法,以放纵自己的情性为日课。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这两种选择都不难实现,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沈璟必须放弃他的人生信念,对他来说却是最难。以“道”自任的理性意志,已经成为沈璟的血液和灵魂,凝聚着他全部愿望和痛苦,集结着他全部情感和理智,他无法在新的选择中来否定它,他只能固执而坚毅地走向自己既定的归宿。沈璟这种以过去为本位的社会人生模式,赋予了他迂腐、僵化、刻板、保守的精神胎记,注定使他不能创作出对世人震聋发聩的作品。
然而,沈璟也有他幸运的地方。在科举的路途上,徐渭二十岁才得中生员,然后三年一赴试,接连七次失败,到老也只是布衣一个。汤显祖十四岁进学,二十一岁中举,三十四岁中进士。沈璟则在二十一岁时即考中进士。到万历八年(1580)大他三岁的汤显祖赴北京春试时,他已经是授卷官了。这是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对于沈璟坚持道统观念的报答。当徐渭作为时代狂士被社会砸得浑身血污的时候,当汤显祖因为盅惑人心被道学先生罚入阿鼻地狱受苦的时候,沈璟却保持着绅士的风度,心安理得地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并接受着后人的钦敬和仿效。
从以上对徐渭、汤显祖和沈璟三人的比照中,透示出万历剧坛的整体面貌。一个时代前进了,必然推出它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意志创造出来的作品都深深烙印着时代的印痕,无论他们对于潮流顺应与否。然而,其感应时代的能力却极大支配了其成就,决定了其艺术生命或辉煌或惨淡的前景。当我们对于万历剧坛作出如上审视时,能不得出这样一种启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