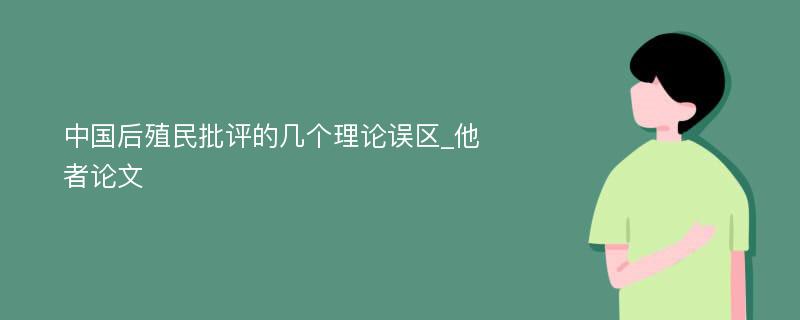
我国后殖民批评中的几个理论迷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初开始传入我国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曾经在我国文化理论界激起过极大反响,它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猛烈批判引起一些年轻学人的深刻共鸣。受这种理论的启发,一些学者改变以往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迷误,凭藉这种新的理论支点,重新审视我国种种文化现象,并对它进行阐释,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
然而,视阈的拓展,并不意味着盲点的消失。相反,在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范围内,我国后殖民批评中存在的理论的迷误也是不可忽视和回避的。
拆解与建构:“东方”可是东方?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谱系可谓源远流长。最直接的理论根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的历史学知识与现代法国社会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转化理论。其理论家有很多,但从理论的完整性及系统性而言,当以赛伊德最为典型。赛伊德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引进到对殖民主义文化的讨论中来,他认为西方(尤指欧美)的自我中心意识通过知识的生产被殖民者构造成他者,以作自我肯定;这种表现又因为西方的文化霸权而不断被重构,从而使他者终于湮没在西方的话语中,并被西方的话语所取代。
很显然,后殖民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以解构中心和本质主义权威为核心的新的理论形态。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后殖民批评对于本质认同与族性倾诉等等都持有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姿态,它所致力于解构的是诸如普遍主体、西方中心和文化同质等等本质主义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后殖民主义话语本身所反抗的本质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诸如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之类的东西,而且还包括诸如民族主义等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立场。
但是,因为后殖民批评的理论外衣裹挟着一种惑人的色彩,人们容易将其等同于民族主义的东西,把一种西方学者自觉地对自身文化恣意歪曲和贬低其他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看作是西方人为东方主义的一种张目。所以,后殖民批评在传入我国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有意甚至刻意的误读,人们大多把它看作是一种冲破西方中心罗网的理论盾牌,这从接受后殖民理论的时间背景上可以找到证明。后殖民理论传入我国,正是在我国理论界开始严肃地反思自身的学术立场的时候,这种反思本身就带有一种失却话语权的愤懑,这种情绪使得我们具有一种强烈的族性诉求需要,而表面看来明显带有东方民族情绪的后殖民理论的出现,似乎满足了这种诉求的渴望,所以,它被很快接受并被广泛传播开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在这么一种接受情境下,误读甚或有意误读也就往往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事情。
这样,就像有的论者已经注意到的一样,中国的后殖民批评,自一开始就进入一种文化本真性的幻觉和迷误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其中“我”所需要的“东方主义”的东西,而较多地忽视了它的解构主义理论背景。就像后殖民理论家赛伊德所说过的,原本是解构理论的一种批评实验,却被人当作是又一种本质主义的圣经。所以,我们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又悖论式地将“东方身份”和“本土经验”绝对化本质化,试图寻回一种本真的、绝对的“东方话语”和“中华族性”,以与“西方话语”和“西方中心”对举,构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从解构西方中心合乎“逻辑”地走入“中华性”。而新的二元对立的形成,实质上是在解构一种中心时,又建构一种新的中心论。对民族主义公开或潜在的倚重,实质上是把自我放到了二元对立的其中一端,而从内部来改变这两者的等级关系就成了我们的“后殖民批评”的出发点。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论悖误就无以挽回地形成了:用以解构“元话语”(西方中心主义)的“边缘话语”(后殖民理论),在我们所操持的一些批评中却走到了它的反面,直接表现为一种族性诉求的本质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是哪一种“东方”?
意识形态化:陷阱还是天堂?
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根基是解构主义。正如赛伊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的思想,其他的后殖民理论家则更多地从解构主义中受到启发,如斯皮瓦克对德里达(Derrida )理论的运用是人所共知的。福柯认为:任何一种知识和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以某种方式与权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即任何一种知识都是某种权力的表征,因此,他对赛伊德的启示在于强调了对诸如普遍意义或绝对真理的大胆怀疑。而解构理论则通过强调边缘话语的作用以达到颠覆“元话语”或“权力中心”的目的,通过对差异的强调来形成一种无强力中心的多元对话格局。这一点恰恰成为后殖民批评理论话语的基本思路。因此,颠覆中心、瓦解“元话语”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典型特征其实也是后殖民主义的内在形态之一。
由于后殖民理论批评得更多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权力话语,因此,我们在运用它来进行文化批评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其意识形态化了,或者如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后殖民问题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说, 我们的后殖民批评常常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挪用”。
这种挪用的结果是:作为一种解构的力量,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威力一方面被消解,另一方面却被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神奇化了、无限夸大化了。其直接的表现是:在我们的大多数的后殖民批评中,都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反西方中心重新确立东方文化神圣地位的理论,所以,根本无需考虑具体的时间空间环境,只要能为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压抑下的东方文化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华夏文化张目,就可大大地运用它来扬眉吐气一番。殊不知,这样一种实证主义的假设与后殖民主义本身的解构策略恰恰是矛盾的,因为后者的立足点根本不在于此。
后殖民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就了新的文化守成主义。一谈到西方文化,要不认为它一无是处,要不就认为到处充满殖民野心。本来在西方比较激进的后殖民理论,到了我们的手里就变了形,它由一种消解权威话语的批判性力量而变成了一种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化焦虑,使得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也被看成是大可值得怀疑的东西。这种片面性直接地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形成阻碍,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影响文化批评,从而对自身文化形成扭曲性摧残。
比如说,我们运用后殖民理论对中国的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批评时,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把批评的靶标指向在西方获得较高评价的一些文艺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是在某种彻底出卖的程度上把中国艺术的民族性贬损地贩给了西方人,以满足西方人对东方落后文化具有猎奇性的后殖民心理。”而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张艺谋电影更是成了众矢之的,因为这种批评模式用在张艺谋电影上再合适不过了。如有人对张艺谋电影本文重新进行解读,认为张艺谋屡屡从西方讨来“说法”的神话,正是由后殖民语境这个“隐身的导演”一手炮制的。张艺谋影片靠的正是寓言化的中国形象、空间化、符码化、脱离中国历史连续体、异国情调等等,投合了西方中心权威话语,“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东方神秘和蒙昧国度的好奇心”而受到首肯和青睐的。
这种批评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其失当之处正在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焦虑和紧张,影响了我们对文化产品的正确判断。正如赛伊德所说过的,文化首先“意味着那些所有的惯例,诸如艺术的描写、传达和再现等,它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常常存在于审美形式之中。”作为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文化,虽然也会影响到经济、政治等意识形态并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决不是线性决定论的关系,它还具有着一些超意识形态的特质,而其中“一个原则性目标是追求快乐”。这种简单的批评作法,正是忽视了文化这个原则性目标。因此,这种批评表面上使用的是新理论新方法,实际上沿袭的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我们认为,上述作品的成功之处正在于用一种边缘化的言说方式,消解了中心话语,解构了中心权力话语;而它们得到世界的基本认同,正说明西方中心被逐渐打破、被逐渐拆解,从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了对边缘化叙事的体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成就正在于成功地运用一种解构策略,完成了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实现。应该说这正符合后殖民批评的基本思路,可为什么到了我们的批评视野中却成了向西方中心权力屈服的象征呢?
我们认为,要消除这种因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变形,就必须“把后殖民从与当代权力形式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共谋的关系中解救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如德里克所说的将后殖民历史化,以避免人们将后殖民理论作断章取义式的滥用。因为“这种知识形式很容易被人们挪用到当代权力机构中”,作出一些与后殖民理论本身背道而驰的判断。
话语操练:盾牌还是投枪?
后殖民理论被我们接受了过来,这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所操持的后殖民批评,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我们手中,它究竟是应该用作盾牌呢,还是用作投枪?
这里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我国接受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过程。我们接受这一理论的时间大约是九十年代初,那时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调整时期,在经过前一阶段西方理论的狂轰乱炸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从“本土”这个身份中感觉到一种责任。在力图依靠“本土”从边缘返回中心的时候,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一个“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当然不可能是国内的官方话语,也不可能是其他的与中国有别的“本土”,而只可能是“西方”。而恰在这一时刻,后殖民理论开始传播,这种理论似乎与我们的某些需要暗合,所以,我们就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欣喜不已——从这个方面看来,我们对后殖民话语的选择也许有一种出于“一己私利”的嫌疑。而在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敏感的理论悖谬,即:接受这个理论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过程,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的理论,而是一个“他者”的理论。这样一来,问题就凸现出来了:后殖民话语,是我们用来找回自我的武器,还是防范他者的庇护伞?
另外,我们说过,表面看来,后殖民主义理论是西方学者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或者第三者的位置上对自己所属文化及其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所作的深刻反思,但是事实上这种理论本身并没有为我们解开东西方文化之间纠缠不休的各种矛盾。相反,却使我们更加感到西方权力话语的无所不在,甚而至于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理论本身,是不是后殖民理论家们带着一种优雅的贵族姿态、以同情的口吻唱出的几句高调,以表现一种同情心、怜悯感呢?换句话说就是:后殖民批评家们力图解构西方中心话语的同时,是不是自己却无意中掉进了西方中心话语的泥淖?比如说,“殖民”“自我”等等语词就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然而,无论谁来讨论它们,都不得不套用西方中心话语早已先入为主地确定好含义的概念,就连进入我们视野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本身也十分值得怀疑。这样,又一深刻的悖论就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在企图突破、拆解一种中心权力话语的时候,却不得不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在这种情况下,后殖民批评理论,我们是用作长矛还是用作盾牌?
标签:他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