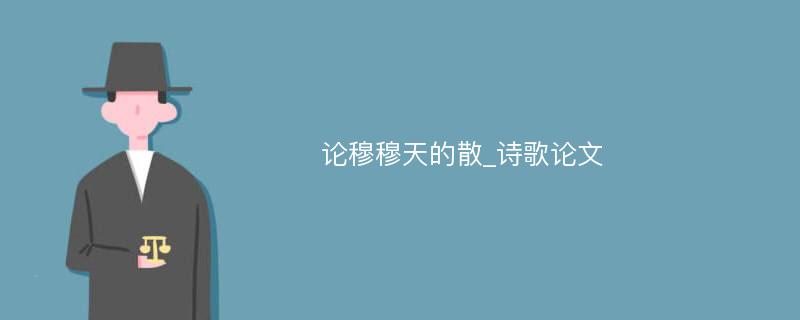
穆木天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木天散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207.25
20世纪的文学已成过去。在历史的天幕上,星汉灿烂,名家辈出。穆木天是曾经闪现过光点的诗人、翻译家、学者。问题是:他将以什么留在历史上?
穆木天是按部就班,读完大学,拿到学位的人。他是在日本读的大学,而所学专业又是法国文学。从他的翻译看,除了法国文学作品而外,还有不少苏俄作家作品。可见他懂多种外语;不消说,他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也是厚实的,从他的《我的文艺生活》和《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等文章中还透露出,他在法国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文学海洋中游泳过,在那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百花园中饱餐秀色,采千种花蕊,酿自己有限的蜜。这是“五四”一代人的共同特征,他们博览群书,中外文学功底深厚。他们厚积薄发,人言人殊,每个人都在创造。他们否定一个旧的文学历史时代,自创一个新的天地,开辟一片崭新的文场。
一
穆木天翻译出版书籍,有名有姓的即达二、三十种之多,还有大量的篇什未集结出版。这是一笔可贵的遗产。若能加以搜集,集中,整理,对照原文,分析他的取舍标准,审视他的译笔,统观他在所译的序跋中又对此说了些什么,必然会从中发现一些先前未能引起注意的话题。鄙人缺乏这样的学识和天赋,唯望有识之士不妨一试。媒体似曾披露,现在的翻译界,有人中文无根底,外文缺常识,竟然也敢在这块神圣的园地里来践踏。结果不免粗制滥造,良莠莫辨,污辱精华,抬高赝品,贻害嗷嗷待哺的善类。对此,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所遵从的原则,所积累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择善借鉴的。
穆木天出版的第一本翻译作品是《王尔德童话集》。当时译者年仅23岁。此书笔者经多方努力搜寻,亦未能见到。但从“五四”时期张闻天为自己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所写的长篇序言中,见到过一段穆译引文。那一段引文行文流畅,朴实之中含着秀逸。关键还在于,穆木天为什么一开始就译唯美主义大家王尔德。这和他后来提倡纯诗,一再以肯定的口吻提到唯美主义,似不无关系,也不难验证他所受到的影响。
二
当然,归根到底,穆木天留在历史上的,恐怕主要还是他的诗歌创作和那为数不多的理论批评。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中外文学的碰撞中诞生和发展的。中国的文学家们勇于进取,敢于拿来,精于挑选,善于吸收。凡人类创造的文明,他们都引进,都由模仿而独创,终成自己的佳酿。西方文学思潮流派中,对中国影响最大者,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而外,应数象征主义。中国文坛介绍和论述象征主义的文章,不管是从情感体验上,还是从理性分析上,真正能传达出象征主义的底蕴的,我以为数量实在不多,其中仅有穆木天的《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什么是象征主义》、《王独清及其诗歌》和田汉的《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王独清的《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梁宗岱的《象征主义》、张若名的《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蓝苞》等文。
《谭诗》是作为诗人的穆木天对象征主义内涵的感情描述,《什么是象征主义》则是作为左翼作家的理性说明,评王独清更是诗人兼学者的剖析,是过来人的理解和对价值的评判。三文相得益彰,互为参照,从情感倾泄,到理性诠释,再依例解剖,层层递进,分明昭示出一个发展过程。
《谭诗》将穆木天的唯美主义艺术观和盘托出。第一,做诗重视印象和感觉。他的那一段关于写月光曲的心音:“我忽的想作一个月光曲,用一种印象的写法,表明月光的运动和心的交响乐。我想表现漫漫射在空间的月光波的振动,与草原林木水沟农田房屋的浮动的称和,及水声风声的响动的振漾和在轻轻的纱云中的月的运动的律的幻影。”哪怕诗还没有写出,读者却已被他迷住了。这是一种天人感应,是天籁人籁的协和。第二,主张诗的统一性和持续性。就是说,一首诗只表现一个思想,不要庞杂和枝蔓。一首有统一性的诗,是一个统一性的心情的反映,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凡好诗都是一种生命的韵律的流,诗就怕断弦。“我要求立体的,运动的,有空间的音乐的曲线。我们要表现我们心的反映的月光的针波的流动,水面上的烟网的浮飘,万有的声,万有的动!一切动的持续的交响乐。”诗是一个有统一性和持续性的时空间的律动。第三,诗的内容和形式要统一。诗的律动的变化要与思想内容的变化相一致。诗的形式力求复杂,形式越多越好。第四,追求纯粹的诗。要求“纯粹的诗歌”,要求“诗的世界”。他说,他喜欢细腻。“我喜欢用烟丝,用铜丝织的诗。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的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我要深汲到最纤纤的潜在意识,听最深邃的最远的不死的而永远死的音乐。诗的内生命的反射,一般人找不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深的大的最高生命。我们要求的是纯粹诗歌(the pure poetry), 我们要住的是诗的世界,我们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我们要求纯粹的诗的感兴(Inspiration)。”因此,诗要暗示,最忌说明, 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然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奥秘。诗最忌说明,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诗越不明白越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诗是最忌概念的。诗得有一种魔力。由此,穆木天认为中国的新诗运动,胡适是“最大的罪人”(注: 以上引文均见穆木天《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3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因为胡适主张作诗须得如作文。根据穆的这种价值观,就诗的世界说,维尼超过雨果,李白比杜甫伟大。最后,穆还说,一个诗人,从观察生活、构思开始,就必须是诗的,就得进入诗的世界。不能先用散文去思想,然后才将这种思想译成有韵律的诗。诗要有诗的思维方法,诗的逻辑术。诗有诗的文法,不能用散文的法则去拘泥它。
总之,穆木天追求纯诗。要捕捉诗的感觉,记录诗的印象。运用诗的思维和逻辑,进入有韵律的世界。取暗示,忌说明。诗只描绘世界,并不解释世界。这篇论文是用通信的形式写出来的,才情毕露,直抒心臆,既是论理,又是心音。它从情感的要素出发,抓住了象征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又纤毫毕露地传达出诗人自己的纯诗的要求,即他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带着他自己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书海中浸泡过的特殊印记。
象征主义重暗示和朦胧、混沌,重声、光、色、味的感觉及其交错与契合,本来不容易以清晰的语言把它条分缕析,说得明明白白。说得太直白,过于理性,就失去象征的味道了。穆木天的《什么是象征主义》,是以刚刚习得的唯物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来浅释难以明晰的象征主义的。他试图从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精神、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嬗变入手,揭示象征主义出现的社会和阶级原因。他说,所有的象征主义诗人都是对于丑恶的现实社会生活感到憎恶,感到一切是幻灭的绝望,而成为颓废和发狂的。因此,“象征主义,同时是恶魔主义,是颓废主义,是唯美主义,是对于一种美丽的安那其境地的病的印象主义。这种回避现实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到处找不着安慰的绝望的状态,自然要使那零畸落侣的人们到咖啡店酒场中去求生活,到神秘渺茫的世界中去求归宿了。”(注:穆木天:《什么是象征主义》,见《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7月出版。)从这种背景出发, 穆木天认为,零畸落侣的象征主义诗人们,就要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神秘的境界,一个生命的彼岸,以便到那里去求灵魂的安息。为此,他们便努力创造神秘的世界,制造宗教的气氛。那些象征主义者的作品的基本特征,可以说,就是对于神秘的非现实的东西的信仰,即宗教的神秘的见解和气氛了。
穆木天又以个人的特别修养,将象征主义诗派的美学(诗学)特征归纳为两点:第一,“交响”的追求。交响,即波特莱尔在《感应》(Correspondances)诗中所说的世界是一座“象征的森林”, 各种芳香、色彩、音响全在互相呼应,目可听五音杂陈,耳可看七彩缤纷,触觉可与味觉相通,味觉可感知冷热、软硬。一切皆浑然,世界是一个整体。它们和人的心灵状态之间也存在着极微妙的相类的关系。第二,轻蔑律动,追求旋律。即轻视古典诗歌的格律,而以朦胧的音乐性去暗示诗人心中万有的交响。由于追求朦胧的音乐性,因而就产生了散文诗和自由律。
这种对象征主义的理性分析,差不多可以说代表了左翼作家对象征主义的总体的基本的看法,然而又明显地表露了穆木天个人的理解和感受,个人的好恶和取舍。
三
李金发第一个将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引进中国文坛,但他的诗晦涩难懂。30年代的人们责怪他败坏了象征主义的声名,破坏了象征主义的美学原则,授他以“诗怪”之称。穆木天的《旅心》(注: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4月出版。)则是一本“好懂”的象征主义诗歌集。
《旅心》充满了一个飘泊异国的青年凄苦的心情和感伤忧郁的情调。一方面,他抒写人生飘泊的苦闷与内心朦胧的寂寞,他喊道:“我不知/哪里是家/哪里是国/哪里是爱人/应向哪里归/啊 残灯 败颓”,也不知道哪里是明哪里是暗,哪里是朦胧,眼前所见的只有败颓和残灯。(《鸡鸣声》)一方面,不少诗作又充满了对祖国故乡风物的清新细腻的描写,洋溢着一个爱国青年深切动人的情思。《北山坡上》怀着深情描绘了登上吉林市北山的见闻和心境,“心欲的家乡”始终是诗人歌颂的对象。他怀念薄暮乡村渺渺的冥濛,他掇拾山村的闲情野趣。《心想》所唱感情尤为真挚,游子的拳拳之心、抱国之情浸透纸背。他身在异邦,心怀故国,渴望“能看见九曲黄河/盘旋天际”,亟盼滚入母亲的怀中,“含住你的乳房”,希望看见祖国“流露春光”,“杂花怒放”。此诗情真意切,诗意葱茏。《薄光》、《烟雨中》、《雨丝》、《苍白的钟声》、《朝之埠头》、《腥红的灰暗里》、《鸡鸣声》、《弦上》、《沉默》等首可视为穆木天象征派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它们借助具体的意象来表现诗人的心态和对外物的感受。景即情,情亦景,和谐、浑一。如《雨丝》:“一缕一缕的心思/织进了纤纤的条条的雨丝/织进了淅淅的朦胧/织进了微动微动微动线线的烟丝”。心思、雨丝、烟丝、混混沌沌,朦朦胧胧,不知哪是景哪是人,哪是雨丝烟丝,哪是心丝。以清晰写朦胧,以有限寓无限。
穆木天爱用暗淡的灰色,使诗篇低沉、凝重、晦暗、感伤。“白色的幽梦”,“苍白的钟声”,“腥红的灰暗”,尤渗透出悲凉。《烟雨中》和《朝之埠头》中的“油烟”、“醉乳”、“油灰”、“浓烟”,不但是逼真的具象,油画效果强烈,而且表明诗人心境之压抑。灰濛、油腻、污浊、沉闷、烦嚣,由心境化为物景,由物景而挤压心境,从真实出发,登上象征的堂奥。《苍白的钟声》将象征的意蕴推向极致。千年古钟发出的“苍白的钟声”,飘散“在水波之皎皎”,“在风声之萧萧”,“在白云之飘飘”。“皎皎”是色,“萧萧”是音,“飘飘”是形。钟声化为色,化为味(后有“一缕一缕的腥香”),化为形,它或飘散,或栖息,或衰腐,或荒凉,或沉睡,或清醒,都是诗人心境和情绪所生。钟声织入远远的云山,穿过茫茫的四海,沉蛰在瞑瞑的先年,但终究又无可奈何地落在苍茫的家乡,埋入灰黄的深谷中,深植进诗人的心田里。魂兮归来,诗人还是东北大地的儿子。“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的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这才是典型的“诗的世界”。
诗人在这些诗中,不是着力要具象什么、表现什么,他主要是在写出自己的感受。如《雨丝》就是突出一个“织”的印象,所以全诗用十七个“织进了”。下雨了,诗人捕捉到“织进了”这个具象特征,并由此展开想象。可以是“织进了”具体的林梢与河湾,也可以是“织进了”冥冥之中的“无限的呆梦水里的空想”,还可以“织进”“渺渺的音乐”和“永远的虚线”。《朝之埠头》由“朝”这特定的时限和“埠头”这特定的空间出发,诗人逮住“薄冥”和“油灰”这两个特征,写他五官的感受。《苍白的钟声》的构思和《雨丝》相似,他在钟声中凝神寂想,声音的“飘散”的感受振动了他的情弦,他就在“飘散”上做文章。思随钟声“飘”,魂追钟声“散”(和“荡”),跋山涉水,穿云破雾,上天入地,凿古扬新,无心界,也无形界。丝丝入扣,字字入情。这些诗,当然也记录心迹,也表现情绪,但这不是创作的目的;象征诗人所欲写的,其实仅仅是他对声音、对香味、对形象的某种深刻的印象、感觉和感受,是主体与外物的某种契合。可以说,这就是象征派诗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区别之所在。
穆木天对声音特别敏感,想象也丰富。《雨后》写六个“要听”。其中,水珠的低语,微风的足迹,水沟的歌曲,远寺的钟声,是实在的声音,而薄薄的云纱和袅袅的炊烟也能“听”,就是通感的运用了。诗人对钟声的感受尤其敏感。《苍白的钟声》已如前述;在《不忍池上》中,他将感情织入声音,使声音也有了呼吸和感触,能聚能散,可疾可徐,或微或重,不但有频率、振幅的变化,甚至有颜色的显示,有香味的裸呈。大自然的声音一概都是诗人的心音,是这心音的扩散和寄托。于是,不但无声似有声,声音还可以转换,因暗示的需要,化为一切。这样,诗就丰富了,韵味就浓了。
在20年AI写作象征派诗歌的诗人中,穆木天的诗既有浓郁的象征派气味,又算是最好懂的。当然,“能懂”、“好懂”都不能作为评价诗歌的标准;懂与不懂,是相对的,有作品本身明晰与否的问题,也有读者学识水平和欣赏趣味的问题。但过分朦胧,甚至晦涩,让人完全不知所云,也不见得就是象征派诗的正宗。像穆木天这样,他能让读者进入他的诗的世界,去感受游子孤寂的情怀,去体验远行人思乡爱国的心迹,去辨析风声、雨声和心音的混杂、交响与契合。不乏暗示与浑漠。声音的低回婉转,情绪的升腾震颤,节奏的抑扬顿挫,音调的铿锵悦耳,可读可诵。即或它们不是波特莱尔的嫡传,那也可说是中国式的象征派诗歌。就中国读者而言,恐怕还是喜欢像穆木天的这种象征派诗作。至少他是中国象征派诗歌流派中的一支。学习欧美象征派诗歌的主要表现方法,融进中国诗歌传统,结合现实和个人的特性,各人创造各人的样式,样式越多越好,路要越走越宽。在这丰富之中,再行选择和扬弃,必然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象征派诗歌创作的路来。可惜,我们的历史不是这样写的。这不是哪一个的责任。
四
穆木天是中国诗歌会主要成员。诗歌会关于诗歌大众化民族化的理论: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诗集《流亡者之歌》是实践大众化民族化的代表作。
中国诗歌会走的是与象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都迥然不同的路。形式上,它要通俗到用歌谣俚语;内容上强调反映现实,写重大题材;表达方式上,要一泻无余,一览无遗,连必要的含蓄、象征、隐喻等手法都少用,极而言之,要以大众能听懂为原则。用穆木天的话说是:“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注:《新诗歌·发刊词》, 穆木天执笔,1833年2月11日《新诗歌》创刊号。),“要紧的是要使人听得懂”(注:穆木天:《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新诗歌》创刊号。)。穆木天原说胡适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大的罪人”,因为胡适说白话新诗要做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此时,穆木天也说,“有什么就写什么,要怎么写就怎么写”(注:穆木天:《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新诗歌》创刊号。)。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以穆木天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成员,关注大众的命运,反映大众的情绪,充当大众的代言人,是他们在创作时的自觉意识。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而且到了急功近利的程度。
《流亡者之歌》(注: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7年7月1日出版。)首首都是亡国的痛苦呻吟,都是抗日的高亢呼喊。诗篇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滔天罪行。诗人饱含热情,直逼现实,掷出憎的匕首,射出恨的子弹,倾泻着爱,诗人的镜头对准祖国的安危,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苦乐,时代的波澜,生活的旋律。诗人轮番运用广角镜、变焦镜、滤色镜,远的把它拉近,小的把它放大,突出反映本质的颜色,使其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
应当说,同样是通俗化、大众化,穆木天的《流亡者之歌》和中国诗歌会其他成员,如蒲风、杨骚、任钧、王亚平、温流等人的作品也还不太一样。即穆木天的诗比较阔大、浑厚、沉郁,浓缩着时代的呼唤。内涵丰富,视野开阔。他的那些叙事诗,如《守堤者》、《在哈拉巴岭上》、《江村之夜》等,被茅盾视为“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注:茅盾:《叙事诗的前途》,1937年2月1日《文学》第8卷第2号。)。
还可与他自己的《旅心》比较。《旅心》既有新鲜意象,也有真实的抒情。人生如旅,心儿没有栖息的地方。苦闷,寂寞,感伤,朦胧。时而是轻轻的叹息,时而是淡淡的雨烟。远山,云雾,人影,钟声。这就是《旅心》的内容和诗行的色调。但到《流亡者之歌》就一切都变了。《又到了这灰白的黎明》、《在哈拉巴岭上》等诗,同样是有声音有色彩,同样是有景有情,但这里再也不朦胧,一切都是那么明白好懂,不用任何解释,诗人写什么表现什么,全都显现于笔端,直露出来了。对于一个有修养的作者来说,通俗化,不等于随便写,他们还是讲究谋篇布局的;只不过这种讲究,首先得让位于政治上的宣讲,得让位于浅近和明确。就说上举的两首诗,也还是有环境气氛的烘托;哪怕是细小的地方,也都考究。如后一首在“围着孔明灯”之后,再递进一句“团团地围住”,这就在平面的叙述中,有了动感,出了形象,是诗的写法,而不是散文的写法。
如果穆木天等中国诗歌会成员不把通俗化大众化推向极端,而能从原先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中吸取较多的写诗必备的要素,两者加以有机地融化,不忘“诗是诗”(《现代》杂志编者施蛰存的话),可以想见那将是另外一种景象。
收稿日期:1998-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