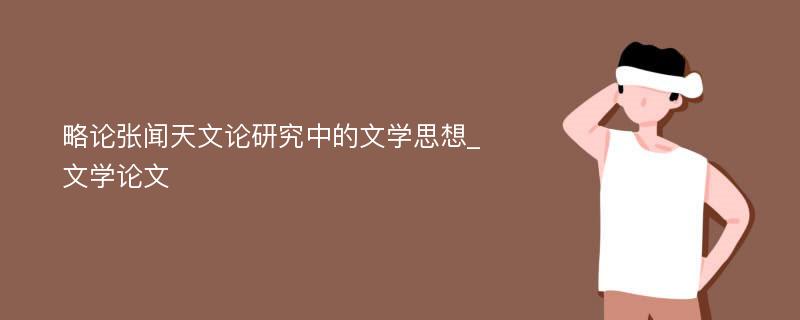
文艺理论研究 张闻天文学思想浅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说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文艺论文,思想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从张闻天对文学真实性的看法入手,探讨张闻天对文学真实性之美的审美基本属性以及与倾向性、典型性相互之间关系的见解。
关键词 真实性 倾向性 典型性
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人们比较熟知的,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东北从事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工作。解放后,在较长时间内从事外交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人们也许不大熟知,他还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热情战士。早年,他从事新文学创作(这包括新诗、戏剧、小说、散文),翻译和介绍外国作家作品,并撰写倡导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的理论文章。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在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常委负责文化艺术工作中,发表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里有许多关于美学方面的真知灼见。这包括有:共产主义理想之美、共产党人崇高人格之美和文学真实性之美。本文仅就文学真实性、文学真实性与文学倾向性、文学真实性与典型性三个问题,阐述张闻天的一些看法。
一
文学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也是文学的审美基本属性。
张闻天在考察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时候,始终是把文学真实性放在首位。他认为,文学只有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和规律,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伟大的作家创作出来的这种具有真实性的“文艺作品,只要它充满着生命,不论它描写的是‘恶之华’或‘善之华’,都是要得的”。
在他看来,凡是具有这种独特审美基本属性的文学作品,决不是作家纯主观精神活动产物的结果,更不是作家“立在人生的旁边叹息痛恨于人生无意义”。那种“立在人生的外面,决不会知道人生,立在人生的外面说人生是无意义,等于看着一碟菜而说他不好吃的一样”。而他们总是“投到人生的急流中去奋斗”,他们“要大着胆挺起胸,有时竟至硬着心肠奋斗过去”,在生命的急流中间,“在奋斗中间,在与最大的障碍物战争的中间,在为了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幻想贡献一切的中间,生命才达到最高潮,人生才有意义”。如果一些作家们做到了这一点,不仅执着人生发展人生而且创造了人生。作家运用艺术的手段真实地把这种对人生的审美感受、体验和认识形象化再现与表现出来,这样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耐人寻味经久不衰的。因此,他说:“一切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人生的战场中奋斗过来的。他们经过了种种的苦难与欢乐才得到了一种信仰,他们都信仰未来的光明,信仰真善美,信仰精神的存在与伟大,虽然他们中也有诅咒或是厌恶社会与人生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总是在于他们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信仰,我们遍读世界文学家的传记与作品,觉得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的。”这种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决不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人生刻板机械的摹仿或复制,它既是被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所制约、支配,又要超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反制约、反支配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因而,这种文学作品内容就“要不为现社会上无病呻吟与苟且偷安的恶习所支配,要超出时代要直透进人生的里面,找出一点永久的东西来。”这“如像荷马的史诗,它的的价值是在描写恋爱、嫉妒与勇武等这些人间的永久性,不是在它所提供的史料,其他如乔叟如莎士比亚如歌德等伟大的作品的价值也都在此。”
新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呢?张闻天认为,只有用革命的方式去破坏旧世界,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才会为创造出内容丰富、情真意实的富有生命力的健全的优秀作品,提供肥沃而丰腴的历史土壤,作家的精神境界也将随之而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
文学真实性与文学倾向性,二者是统一的。
张闻天认为,凡是在文学发展历史上,真实地反映了一定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真相与真谛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总是和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对于一定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真相与真谛的表现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社会政治倾向性相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角度,要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人生问题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制约与被制约、支配与超出的关系;从微观角度,揭示出社会现实生活中人生的种种特定的或真或假、或善或恶、或美或丑的真相与真谛同时,要具体回答诸多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缘由,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评说社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指出前进道路的坎坷与曲折,展示出社会发展的美好未来前景,他称赞说“《红楼梦》的作者他是人生的罪状宣布者而同时又带有指导意义在内。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他对于人生的经验,对于人生的观察和他所体味到人生的意义的记述和描写。”
他极大的重视新文学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特殊审美教育作用,1932年11月18日他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1941年6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深刻地阐述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其中值得提出的是他特别注意纠正左翼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不重视文学的特殊审美教育作用的偏向和在组织上关门主义倾向以及实践上“左”倾空谈的毛病。1932年11月3日在他写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他就左翼文艺运动中关于文艺性质与大众化讨论中,反映出来的关于革命文学的功利性种种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批评,并主张在实践上加以纠正。
表现之一,是对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存在观点的批判。左翼文艺运动中某些理论家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他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是忍耐的解释,是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表现之二,是对“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留声机’”观点的批判。照这种理论观点看,“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大大地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大大地缩小了革命文学的范围,实践上不利于团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中间,有不少的文学家固然不愿意做无产阶级的‘煽动工具’或‘政治留声机’,但是他们同时也不愿意做资产阶级的‘煽动工具’或‘政治留声机’,他们愿意‘真实的’‘自由的’创造一些‘艺术的作品’。这样的文学家我们也是需要的”。现在“我们的任务不简单在指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文化政策之下,不能有文艺的创造的自由,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没有超阶级的自由,而且还要去领导这些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了解我们所指示的道路的正确,而走到我们的道路上来。”张闻天主张,对于反映复杂而又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批评,决不可以采取形而上学简单化的方法,那样的话必然会产生一种误解,误解为“煽动”的东西都可以列入文学创作之中。其实,并不是一切“煽动”的东西都是文学创作,一切文学创作也不都是可以用来作“煽动”的。当然,“在‘煽动的工具’‘政治留声机’中固然有文艺的作品,然而决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作品”,“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甚至许多文艺作品有价值,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某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作品,而只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
表现之三是对于无产阶级大众化片面狭隘教条主义的理解的批评。张闻天认为,左翼“文艺应该大众化”“应该采取各种通俗的大众文艺的形式,通俗的白话文,写出能为大家所了解的文艺作品,这完全是正确的”,这是“利用一切通俗的文艺形式号召工农阶级起来斗争宣传鼓动的需要。如果有谁认为只有这种宣传鼓动的通俗作品,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且事实上这种作品的大多数却并不是文艺作品,这当然并不是左翼作家的耻辱”。他说:“我认为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应该利用这种新的形式”。可能有人会“说这种形式,工人看不懂,就是‘有头有脑’的《红楼梦》与《水浒传》等,工人何尝看得懂。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抛弃现代艺术的形式与技巧,而是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使工人们懂得这些艺术品”。这一切,不能不顾及工农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状况,其中先进分子正在进行争解放求自由的伟大斗争,提高工人的鉴赏水平,必须在完成伟大斗争任务过程中,遵循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进行普及的原则去进行。
三
文学真实性与文学典型性,二者是统一的。
张闻天指出,文学发展历史证明:伟大的作家创造出来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叙事性或戏剧性作品),如果是真实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及其规律,伟大的作家必然在其优秀的作品中创造出典型性很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其性格特征必定会是突出鲜明的,丰富复杂,栩栩如生,跃然纸上。1921年7月12日他发表的《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一文中,写道:“诸君请特别注意我的‘人的中心’四个字,这‘人的中心’就是我的真生命,就是我的标准,也就是我的宗教,我的爱!”他在论述这一文学理论问题,虽然更多的地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去揭示文学创作中的这些审美特征,即使是这样,他的这些观点却是同新文学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发展总趋势是合拍的。他热情积极的向中国广大读者推荐和介绍中外一些伟大作家的优秀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身上的“二重人格”审美特征,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作家塑造病态的、性格分裂的畸形人物性格,他也不是要读者去欣赏模仿那些畸形人物性格特征,而是让读者认识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人生是丰富复杂的,决非是刻板单调划一的,这是合乎生活的辩证法和艺术创作的辩证法的。对于作家能够创作出有血有肉性格特征突出鲜明丰富的或复杂的人物艺术形象,无疑是有着借鉴作用的。1920年2月13日他在《致张东荪的信》中,就曾指出人的性格中有善和恶二种对立因素。1923年初,他又在《〈狗的跳舞〉译者序言》中指出:“任何人大都有二重人格,这是近代心理学已经给了我们以证明的。”并且进一步的阐述说这种“二重人格”一是社会的,一是非社会的。社会的人格是虚伪的,快乐的,保守秩序的,普通一律的,机械的;非社会的人格是反抗的,突进的,凶暴的,悲哀的,各人不一的(用法国柏格森的话)”“现在的社会,处处鼓励社会的人格,而压制着非社会的人格,结果将要使人类完全机械化,变成蜜蜂与蚂蚁一样”。在现代的社会里对“这种趋势在少数感觉锐敏的人是不能忍耐的,于是他们起而反抗,反抗不遂,加之诅咒与讽刺”。“一切伟大的艺术家都有敏锐的感觉和洞察的直觉,他们把他们所观察到的,所感觉到,经过了他们的个性的溶化,更受了他们内部的迫切的表现的冲动,用了某种方法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伟大的艺术品,所以任何艺术家的作品中间都是以时代为背景而以作者的个性为中心”的。作家创作出来的具有“二重人格”的人物艺术形象,其实是双重的“二重人格”。一方面,是被作家再现与表现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审美客体的人“二重人格”;另一方面,又是有些作家在再现与表现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审美客体的人的“二重人格”同时,不可能不把自己的“二重人格”溶合进去合而为一了。在他所撰写的外国作家作品“译者序言”和对作家作品评介文字中,用浓重的笔墨充分肯定这些作家在创作方面取得的艺术成就和这些艺术成就所提供给人们可以借鉴的创作经验。特别是他在《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1921年7月)《王尔德介绍——为介绍〈狱中记〉而作》(1922年4月)《〈浮土德监狱〉译者序言》(1922年8、9)《培那文德戏曲译者序言》(1923年7月)和《〈狗的跳舞〉译者序言》(1923年12月),在这五篇文章里,他通过对曹雪芹、王尔德、歌德、培那文德和安特列夫的作品中典型人物形象“二重人格”的审美特征的分析和评论,科学的揭示了产生这种典型人物艺术形象“二重人格”一定社会时代的现实生活内部深层底蕴中存在着的深刻的激励的矛盾和人的(包括作家)精神世界灵魂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内部自我矛盾冲突奥秘的缘由,进而使读者(或观众)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生诸多问题获得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当《红楼梦》研究还在“索隐”“考证”的岐路上徘徊的时候,张闻天却用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二重人格”观点,揭示了《红楼梦》中两个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与美学价值,提出了对《红楼梦》的研究不应离开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他认为《红楼梦》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作者成功地塑造黛玉与宝玉这两个人物的性格。成功之处在于运用“二重人格”相反相成的艺术辩证法,在人物的性格内部矛盾冲突与外在对立不和谐中刻画人物。他在《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受》一文里写道:“林黛玉之天真和薛宝钗之虚伪”构成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的基调,他赞赏作者抓住了他们的性格审美特征。又说:“黛玉不自意的装出常人之所谓小狡猾,而因此愈足以见其天真”,“反之,宝钗常常故意装出宽大和善的样子,而因此愈足以看出伊的虚伪和恶毒。”他还对比了两个人物对宝玉的爱,说林黛玉的“恋爱是以伊的心坎中流露出来的,伊拿出全人格交给伊所恋爱的人而同时接受伊所恋爱的全人格”;而薛宝钗呢,“伊所要得到的人(不能称为恋爱的人)是由伊的虚荣心、名利心所虚构成的。并且就是伊自己的真心也被这一层帐帷深深地遮蔽住了。伊接受了伊的假自我的支配,失了伊的真情,失了人性。就是偶然有些流露,伊就拚命地压制下去,伊终究变了机械人了。”在这种自我矛盾和相互对比中,产生了一种对照互补的艺术效果。他在《〈浮土德监狱〉译者序言》一文中,不仅就所处的时代特征、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形成以及歌德作为伟大作家所承受时代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都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而且着重对浮土德这个典型人物艺术形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二重人格”审美特征做了论述。他指出:《浮土德》是歌德的代表作品,是“歌德一生的经验的反映和思想的结晶!”这种思想在歌德的《浮土德》中有所体现。浮土德这个典型人物艺术形象性格身上,体现着歌德的对于人生的欲望与满足“二重人格”的互相交替与交织。人生的欲望与满足是永无止境的,可是在浮土德这个典型人物艺术形象性格反映出来的,不是贪欲无止境,更不是挥霍无度,而“浮土德自从对于智慧的生活厌倦之后,就投身到生命海中,去体尝人生的真味,他始终执着人生”。浮土德“自从经过了种种试验之后,因为能替别人谋幸福,替别人争自由,所以他快乐了,他满足了,但这不过是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的一段,如其能迟十年而死,也许他对于这种行为不能满足吧!也许有新的欲望产生出来吧!”“就是活到百岁(浮土德死时差不多在一百岁左右),还是对于人生不能满足,他将要死的时候,还想再干完他的工作,他觉得生是好的。”浮土德性格中这种欲望与满足二种因素,不是相背相反的矛盾冲突,而是在对立中求得与达到了圆满的和谐统一。这就是从产生欲望到经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被救”,进而由向上努力又产生了满足,必然演变成的圆满结局,不是由邪恶压倒善良,而是由善的欲念变成善的圆满结果。所以浮土德的欲望审美性格特征和浮土德满足审美性格特征,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张闻天虽然并不是专门从事美学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然而他早年在文学创作、翻译、文学评论、理论研究以及后来他在党内外所起草的报告、决议、发表的演讲中所反映出来的美学观点,在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是占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1925年期间,他由激进的资产阶级倡导文学要真实地反映富有意义的社会人生,鼓励作家到富有意义的人生战场中去,用犀利战斗的笔,再现与表现积极进取人们为争取自由民主、追求个性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过程中,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两个方面,他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创作的《旅途》长篇小说,被称为“实践早期革命文学主张而首先开放的花朵”。这一时期,他的美学思想虽然并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范畴,但有些观点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他的许多美学观点,同“五四”以来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瞿秋白等人,对于文学和现实审美关系的把握论述有近似与相通之处。1925年以后,他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急骤变化,他是“放下笔拿起枪”的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行列中之一员,他由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和批评活动进而转向从事职业革命工作或革命领导工作,特别是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在他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以后负责中央文化艺术工作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一直和党的文化艺术工作、理论研究工作、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保持密切的联系。建国后,自身在处于顺境或逆境时,他结合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从党的文化艺术、理论教育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方针和路线角度,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特点、任务、作用以及活动方式、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重要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独到见解的看法。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在反对“左”倾空谈、“左”倾理论观点、“左”倾政策和“左”倾路线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纯洁性,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美学思想起到了许多人根本不可能起到的作用,他在理论战线上已是属于不可多得的理论家。在这一时期内,他所形成的美学观点已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大厦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当然,在他的美学思想中,对于许多美学中重要理论问题还没有涉足,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苛求于他的。
标签:文学论文; 张闻天论文; 文艺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红楼梦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二重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