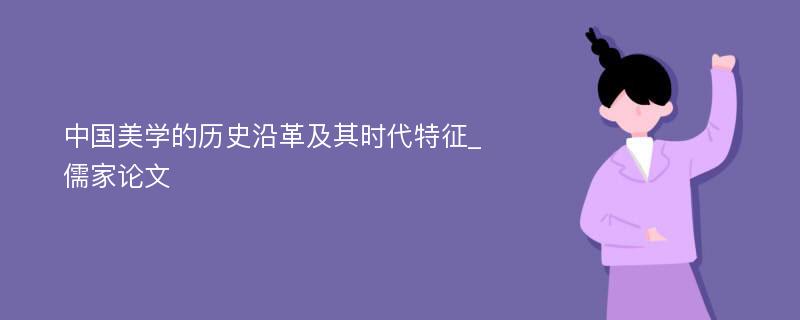
中国美学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时代特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1-0172-11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业已出版的各种中国美学史,就会发现对中国美学史的时代分期是人言言殊、歧义百出的。这当中存在一个主要问题,是对中国美学史运行的轴心——中国美学精神缺少一个明晰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因而对中国美学史的时代分期缺少一以贯之的有说服力的依据。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美学精神主要是一个由以“味”为美、以“心”为美、以“道”为美、以“文”为美构成的复合互补系统①,以此去考量中国美学史的历时演变和时代特征,就会得出全然不同的认识和判断。
一、先秦两汉:中国美学的奠基期
一般的中国美学史都把先秦、两汉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来看。笔者主张则将先秦两汉合起来视为中国美学的奠基时期。这是基于如下考虑:中国古代美学精神,特别是以“味”为美、以“心”为美、以“道”为美、以“文”为美的美论不只在先秦,而且直至两汉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各家美学(如儒、道、佛)的初步建构也直至两汉才大功告成。比如先秦人以“味”为“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才明确“美”、“味”互训;先秦人说“物一无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则明确界定“错画”为“文”。先秦儒家强调心灵的道德表现美,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说苑》、许慎的《说文解字》发展为自然物“比德”为美。先秦《尚书》提出“诗言志”说,汉代《毛诗序》加以继承,扬雄《法言》发展为“心声”、“心画”说。先秦儒家有《乐记》、《乐论》,汉代司马迁《史记》中有《乐书》。先秦道家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味无味”、“至乐无乐”,汉代的《淮南子》则阐释为“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形而有形生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无味而五味形焉”、“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如此等等。可见,在美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及其神理上,先秦两汉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与后来六朝美学相比,其整体特征非常明显。这种特色是:一、美学思想集中在现实美领域里展开,文艺美学尚未取得强大的独立形态。二、儒家美学阵容强大,紧密呼应,在肯定情感欢乐的美满足的权利的同时,主张用道德理性加以节制。道家美学以“无情无欲”为自然人性,主张“自然适性”的结果是去除情欲的欢乐之美,是否定肉体感性生命的存在。于是,节欲的美成为这个时期的整体追求,从而区别于后来六朝情欲释放的美学追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孔孟的人道精神和老庄的天道精神,经过这个时期的夯实,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精神的两元,开创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两大传统,共同支撑起中国美学思想库的大厦。
1、儒家美学
强调道德美,是儒家美学的首要之义。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指出道德“充实之谓美”,“仁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奠定了儒家以“道”为美的道德美学传统。荀子继之,重申道德之“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指出“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使儒家的这一道德美学观得到夯实。先秦另外一些儒家著作亦然。如《尚书》告诫人们“玩物丧志”,“志以道宁”,“作德,心逸日休”。快乐的根本在道德心灵,而不是感官形式。《礼记》主张以“人道之正”要求“礼乐”之美,揭示“德音之谓乐”、“温柔敦厚《诗》教也”。《易传》要求君子“反身修德”,强调君子“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以此为“美之至”①。审美中会情不自禁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打上道德烙印。《左传》强调“乐以安德”、《国语》强调政“和”为美,“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屈原赞美香草等自然物,因为它们是美好道德的象征。汉代从秦朝任用暴政迅速灭亡的惨痛中吸取教训,高扬儒家道德仁政之美。《诗大序》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肯定“声音之道与政通”。董仲舒揭示自然山水比德为美。司马迁重申“礼”者“洋洋美德乎”,“乐音者,君子之所以养义也”。刘向重申自然比德为美、“乐者德之风”的道德美学观,要求人们“修文”与“反质”。扬雄高扬“足言足容,德之藻矣”,鄙薄“雕虫篆刻”的文辞形式之美。班固重申诗乐的道德审美功能。王逸在评价屈原辞赋时称赞其“玉质”。许慎释“玉”时揭示“石之美,有五德”。郑玄解释“赋比兴”时强调道德美。王充肯定“善”具有“可甘”之美。如此等等,都表现了对先秦儒家所奠定的道德美学传统的重视。
综观先秦两汉儒家美学,发现呈现出如下整体特色:
首先,儒家认为美感是一种快乐的情感(“乐感”);追求快乐的美感,是人的天性,不应简单、粗暴地加以扼杀;人的感官天生地喜欢令人愉快的色、声、嗅、味、佚,人的心灵天生地喜欢仁义道德;感官的愉悦与心灵的愉悦、各种不同感官的愉悦之间同为快乐的情感,没有本质的不同,这样,快感与美感的界限也就随之消失。不过,儒家又认为,过分沉迷于感官愉快及其对象形式会使人“玩物丧志”,乐不知返,因而对此必须加以一定的节制。而对心灵愉悦、道德快感的追求则没有这个限制。恰恰相反,由于“心好仁义”常常受到“心好利”的欲望的干扰,使其丧失对“仁义”的喜好,因而尤须加强道德美感的培养。
其次,从承认人的感官愉快的基本权利出发,儒家肯定人的感官愉快所由产生、对应的对象形式——美色、美声、美味、美嗅等纯形式美的存在权利,指出这种美是不依赖道德善而存在的“纯美”,儒家有时又称之为“文”;同时,从节制人的感官愉快的思想出发,儒家又不赞成人们一味追求纯形式美,强调人们应在此之外有更高的美学追求。
再次,从对人的心灵愉悦的充分肯定出发,儒家反复强调心灵愉悦所由产生、对应的仁义道德美。人格美以道德充实为转移,艺术美以象德载道为标准,自然美亦以“比德”为依据。儒家的道德究其实是心灵理念。于是,美是道德的象征,又呈现为美是心灵意蕴的表现。
复次,对审美主客观属性辩证关系的认识。尽管由于主体心灵意蕴的投射,审美中会发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③ 的情况,但这并不能抹杀“口之同嗜”、“目之同美”、“耳之同听”、“心之同然”的美,这种美是经过大众审美经验普遍检验过的客观存在的共同美。
2、道家美学
道家的美学,过去由于其反世俗美的表象,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未被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道家虽然否定世俗的美感和美,并不否定本质的美感和美——“至乐”、“至味”。它之所以否定世俗的美感和美,是因为这种美感不是“至乐”,这种美不是“至味”。那么,什么是“至味”呢?就是“无味”之“味”——超越一切色声嗅味的“道”。什么是“至乐”呢?就是体味“道”时不可感受的“无乐”之“乐”。由此出发,道家建构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系统。它站在儒家美学的对立面,丰富了中国美学对美和美感的认识,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的另一极。
与儒家美学一样,道家美学亦以“道”为美。如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庄子指出:主体游心于原初的道,即可获得“至美至乐”。不过,道家的“道”与儒家之道内涵截然有别。在老子,“道”指派生天地万物而又寓存于天地万物中的虚无本体。在形式美上,认为“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至味“无味”、至言“无言”,以此反对世俗的感官愉快及其对应的形式美;在内涵美上,认为“上德不德”、至仁“去仁”、至为“去为”,以此反对世俗的仁义功利道德美。这种道德称为“玄德”,落实在做人上就是守柔、谦下、愚拙。庄子继承老子的道德美学,将“道”改造为“自然”的“性命之情(实)”,提出“彼至正者,不失性命之情”,这“正”即完美的意思。天下万物各有其自然的“性命之情”,所以对不同的生命体而言,至正至美就是“自适其适”,而“适性”的形态也就“不主故常”,呈现出多样性,对于此物是美的对于他物也许是丑,不同的生命体就有不同的审美尺度。这种随顺生命自然本性的得道之美的美感反应是“无乐”,但却是“至乐”。而世俗人热衷追求的“声色嗅味”、“富贵寿善”虽然快乐,却不是真乐。《吕氏春秋》继承庄子“安其性命之情”的美学主张,建构起“贵生”的美学系统,探讨“性命之情”、“养生之道”,反对违反人的天性“逆生”或“迫生”,既承认人有情有欲的实际,又力戒过度的奢侈享受伤性害生,从而深入到人类审美的主客体结构阈值的对应问题。《淮南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以“无”为美的思想,对这个美学命题的奥义作了丰富而明确的发挥。“无形”、“无色”、“无声”、“无味”为什么是最美的“形”、“色”、“声”、“味”呢?因为“无形而有形生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所以说:“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在美感论上,继承庄子的“至乐无乐”说,重点阐释了“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的玄机。
二、魏晋南北朝:中国美学的突破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原先的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这时汇合为儒道合一的玄学美学;另一方面,诗文美学伴随着诗文书画的繁荣摆脱了先前的依附状态而走向独立,呈现出一片辉煌。
先秦两汉创立发展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在魏晋时期被融合儒道的玄学所取代。玄学继承了道家“适性”“逍遥”的美学主张,后来又改造了道家“无情无欲”的“人性”观,给“人性”注入了有情有欲的现实内容,于是“适性”一变而为“人性以从欲为欢”,变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于是,“情”从心灵的理性约束中挣脱出来,形式从道德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以“情”为美的情感美学和以“文”为美的形式美学潮流一下子突涌出来,覆盖了人格美和艺术美,一直延展到南朝。在人格美方面,形成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④、放浪形骸、不拘形迹的“魏晋风度”;在艺术美方面,诞生了“缘情”而“绮靡”的山水诗、宫体诗、格律诗及其相应的理论形态。在情感美学和形式美学取得巨大突破的同时,中国美学在诗文美学领域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论文。他以一代开国君主之尊肯定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彻底摆脱了孔门儒家道本艺末、文章为雕虫小技的传统价值成见,大大提高了文章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文本同而末异”的体裁和“文以气为主”的风格,批评了“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文学批评态度,竭力倡导一种客观公允的审美态度。其“诗赋欲丽”是对诗赋体裁形式美特征的最早揭示。晋代陆机《文赋》是分析中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过程及其审美特点的最早专文。文学创作的发生、构思、灵感、创作方法、文体特征等等,较之曹丕,《文赋》都有更为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他论述文学创作过程紧扣情感与物象,触及艺术思维的两大特征。他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奠定了诗歌作为美文学的形式美和内容美特点。挚虞肯定诗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批评“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揭示了中国美文学的心灵表现特色。南齐沈约明确以“情”为文之“质”,要求“以情纬文”,在文学形式方面,发明“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的声律美规律。刘勰在南齐末完成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分文之枢纽、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全面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作家论方面论及“德”、“气”、“才”、“学”,发生论方面论及客观生活的触发和具有丰富感受的主体,艺术构思论紧扣“象”与“情”的互动,创作方法论方面深入剖析了“比兴”、“用事”、“夸饰”、“声律”等,文体论方面本着解释概念、说明要理、列举作品、历史观照的方法花二十一篇分别论述了三十多类文体,风格论方面“数穷八体”,通变论方面兼顾“通则不乏,变则其久”,批评论方面建构了完整的“知音”说,并用“原始表末”的历史主义方法品评历代文体作品。通观全书,贯穿着“以雕缛成体”的形式美和“辩丽本于情性”的情感美观念。梁代钟嵘的《诗品》结合当时诗歌创作现实亦破亦立,重申“吟咏情性”的诗学纲领,建立了“滋味”说为核心的诗学系统。萧绎、萧统、萧纲兄弟以皇帝、王子之尊,编选历代美文,创作宫体诗,倡导“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具有文采美与情感美的美文。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美文自觉的时代,尤其是诗文的辞采声律美与情感风流美澎湃勃发的时代。
三、隋唐宋金元:中国美学的发展期
从隋唐至宋金元,中国美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与魏晋南北朝美学不同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六朝时期,儒家思想失去了一统天下的统治地位,在玄学逍遥适性思想的推动下,美学日益往自律方面发展,以“文”为美的形式美学、以“情”为美的情感美学取得重大突破。这种美学思想具有人性解放的启蒙价值,但发展到极端,完全抛弃儒家理性规范,又未免落入一偏。它给隋唐宋元统治者和思想家重铸儒家道德理性规范提供了现实依据。
杨坚统一南北朝、建立隋朝后,便着手整顿世风。在朝的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李谔连续三次上书隋文帝,要求革除浮靡文风,整顿轻薄的社会风气。在野的儒家学者王通仿《论语》作《中说》,以远绍周、孔自命,批评南朝以“文”灭“道”的诗人,广带弟子,传播儒道。朝上朝下遥相呼应,标志着社会价值取向的根本扭转。隋炀帝中断儒道,骄奢淫逸,结果隋朝毁于一旦。这告诉唐初政治家:统治者的欲望不可放纵,儒家克制欲望的理性和为民着想的仁政不可废。在恢复儒道统治地位方面,唐太宗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命孔颖达负责收集以往的五经权威解释,重新加以统一的注疏;二是命魏征为监修,新编、重编南北朝史,总结政治兴亡得失,证明儒家以民为本的仁政是长治久安之道。唐太宗确立了儒家道德学说在唐朝思想界的主宰地位。整个唐朝思想界,诗人如唐初四杰、陈子昂、杜甫、白居易、元稹、张籍等,文人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吕温、韩愈、柳宗元、李翱等,无不以儒家之道为第一位要求做人与作文。他们不仅是文章家,而且是道德君子。
唐、宋之间,经历了一个几十年的藩镇割据的五代十国阶段。这是一个道德失范、天下大乱的时代。宋太祖统一天下后,吸取唐代藩镇兵权过大的教训,建立了皇权更加集中的独裁专制。与此相应,在思想领域进一步确立了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儒家的温馨之“道”一变而为沉重的冷冰冰的“理”。周敦颐、二程、邵雍、朱熹、陆九渊是著名的理学家。而柳开、王禹偁、石介、孙复、欧阳修、真德秀等人虽以古文家著称,同时也是一再要求“文以载道”的道学家。
元代思想界的情况,诚如《元史·列传·儒学》所云:“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⑤ 元朝统治者袭用宋代理学之旧为其大一统的政治服务,虽无所发明,却在推广理学方面颇有劳绩。
从隋唐道学到宋元理学,尽管儒家之道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在恢复、高扬儒家道德理性方面是一致的,与六朝任情纵欲的时代风尚形成鲜明对比,也与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反叛理学的启蒙思潮有着鲜明不同。这是我们把隋唐宋元视为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想依据。这一时期,儒家重新在中国思想界获得统治地位,儒家道德美学再次成为这个时期美学界的主流。其历史发展的座标是隋代的王通、唐代的古文家和新乐府诗派、宋代的理学家(或称道学家)和古文家。儒家道德美学高举以“道”为美的大旗,对魏晋南北朝的情感美学和形式美学大张挞伐,奠定了这个时期美学的时代特色。然而,形式美学与情感美学并不愿意束手待毙,魏晋南北朝异军突起的这两大美学狂飚在隋唐以其巨大惯性朝前奔突,在唐宋以其自身魅力朝前推进,二者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携手,与道德美学作抗争,在个人的天地中、在词曲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在文艺美学园地中,这个时期形式美学的代表是初唐和晚唐的诗律派、宋代的西崑诗派和江西诗派、宋元词曲领域的格律派;这个时期情感美学的代表是唐宋金元时期一些重个性化的“意”、“气”和艺术创作审美特点(如“境”、“意境”、“兴象”、“境外之境”)探讨的文学家。因此,这个时期中国美学界的状况就不仅仅是对先秦两汉时期儒家道德美学的复古,而且有着自身的新的发展和贡献。
四、明清:中国美学的综合期
将清代作为中国学术乃至美学集大成的综合时期,这几乎是共识,在学界没有疑义。把明代也划进来,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综合期,则是笔者的一家之言。明代美学的综合特征虽然不如清代美学那么明显,但在中国古典美学的起、承、转、合中,它明显地带有转合特征。所谓“转”,即向“合”的过渡和转化。像明代的小说美学、戏曲美学,与清代的小说美学、戏曲美学水乳交融,难解难分,融为一体,是对此前中国小说美学、戏曲美学的总结发展。所谓“合”,即综合、总结。这样的著作不只清代有,明代已开始出现,如诗学方面谢榛的《四溟诗话》,曲学方面王骥德的《曲律》等。
在明清时期,不仅涌现了许多集大成的美学家和带总结性的美学论著,而且以滋味为美,以道德为美,以心性为美,以文饰为美的中国古代美学精神进一步得到过滤和积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隋唐宋金元时期文艺美学中呈现的儒家道德美学主潮显然不同,明清时期即便是道统观念很深的美学家(如清初三大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也没有以理斥情,而是在情理合一中表现出对情感和个性的崇尚,使情感美这一思想内核放射出炫目的光辉。
明清美学学派林立,思想多元,端绪纷繁,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过,在众声喧哗之中,总是回荡着以“道”为美的道德美学、以“心”为美的表现美学和以“文”为美的形式美学的三个主旋律。
1、诗文美学
这个时期诗文领域的开场人物要数宋濂。宋濂曾官江南儒学提举,是明初文坛的一代宗师。他论文求美,反对唯形式追求,认为美丽的文采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我们的道德修养实践中。文章应当成为“道之所寓”,而“道”又“存诸心”。只要善于培养道德之“气”,然后“随物赋形”,自然为文,就能成就一代美文。宋濂的诗文美学主张是对唐宋古文家和道学家道德美、心性美思想的一次综合。明代中叶的王守仁不赞成仅在“文词技能”上用工,主张“志于道”而“游于艺”,并把“艺”重新解释为“义”和“理之所宜者”,认为“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而“理”就在“心”中,“心外无理”。这与宋濂的诗文美学主张相呼应,可视为古代儒家道德美学尤其是宋代理学家美学主张的一种回响。
明代文坛出现了要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这虽然有拟古之嫌,但同时我们注意到,这实际上包含着对秦汉散文、盛唐诗歌美学法则的清理和盘点。这种美学法则既有属于形式美学范畴的,如李梦阳总结的“法式”、“规矩”,王世贞总结的“格调法度”,何景明、王廷相的“意象”论,也有属于情感美学范畴的,如徐祯卿的“因情立格”说、谢榛的“情景”说。它们深入揭示了秦汉文、盛唐诗的美学本质和特征。尤其是谢榛的《四溟诗话》,详细剖析了诗歌寓情于景、即景传情的特点和一系列形式法则,堪称古代诗歌美学的系统建构。
在前后七子之间,有一个散文流派不同意七子的“文必秦汉”主张,认为唐宋散文创作也很有成就,进而要求取法唐宋散文。这就是“唐宋派”。如果说前后七子主要的建树在诗歌美学方面,唐宋派则把着力点放在了唐宋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散文创作美学法则的总结上。唐宋派并不否认秦汉散文的成就,但认为秦汉散文“法寓于无法之中”,无法可依,而唐宋散文则有法可循,易于学习。学者可以先由唐宋文入手,最后进入秦汉文境界。唐宋派所标举的唐宋散文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其实是很重视文章的载道之美的。然而唐宋派则没有重复他们的道德美学主旨,而是将文章所表现的“道”改造为自家的“真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之见”⑥,在创作方法上强调“神明变化”之法。这是在明代中后期崇尚个性的时代风潮影响下对苏轼为代表的唐宋散文美学神韵的总结和发现。
中明以后,王阳明心学走到了它的反面,反抗理学道德磐石的沉重压抑,要求解放自然人欲人情的启蒙思潮奔突弥漫于整个社会,流泽所被,延及清代。于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真心”、“真情”、“个性”、“见识”为美的美学新潮。而这一美学新潮,未尝不可视为是对六朝美学否定之否定的继承和扬弃。六朝人崇尚自然情欲之美,但末流所及,荡而忘返。明清人崇尚“一人之性情”,又兼顾“天下之性情”;既肯定“情”的可贵,又认识到“情极”则“俚”。当然,这是就整体倾向而言。具体说来,又异彩纷呈。李贽拈出“童心”与传统道德相对抗,高标自家“胆识”和不羁之“才”,公开宣称“以自然之为美”,一时影响甚大。徐渭、焦竑、屠隆、公安派、竟陵派、袁枚、龚自珍等等,都主张以自家“性灵”、“情性”为主,不受陈规旧律的限制,也不为道德理性所拘。如焦竑主张“脱弃陈骸,自标灵采”;屠隆主张“文章止要有妙趣”,“性灵不可灭”;袁宏道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认为“情至之语,自能感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竟陵派尊性灵,尚人情;袁枚指出诗以“性灵”传世;龚自珍明确提出“宥情”、“尊情”,主张以人性之“完”的状态为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虽以大儒名世,却没有汉儒和宋儒的迂腐,而是将诗文之美与自然之“情”紧密联系起来。如黄宗羲指出:“情之至真,斯论美也。”“情至”之文才是“至文”。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和《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中分析了“情”在诗中的各种表现形态,成为谢榛之后中国诗学的又一座高峰。章学诚尽管史学观念很重,但仍然肯定“情”在文章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气畅而情挚,天下之至文”。如此等等,标志着情感美学在明清启蒙思潮中所达到的辉煌。
2、小说美学
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小说创作经历了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宋代话本小说诸阶段。与后世相比,小说创作的规模、手法、成就均不可同日而语,加之由于鄙薄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此前的小说评点美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明初诞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长篇小说,加之明中叶思想界相对比较活跃和解放,于是围绕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评点,在嘉靖、万历时期出现了小说美学的繁荣局面。明代中期《西游记》、《金瓶梅》两部划时代长篇小说的问世,又引发了晚明小说评点的兴盛。在明代后期,《三言》、《二拍》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而编者冯梦龙亲自操刀对《三言》等小说集的批评,也反映了晚明小说美学的最高水准。明末清初,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觉得明人的评论意犹未尽,于是分别评点《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从而将小说美学的成就推向最高峰。清代中叶伴随着《红楼梦》的诞生出现的脂评,可以说曲终奏雅,成为清代小说评点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由此可见,如果说小说代表了明清文学的最高成就,那么明清小说美学则是对这种艺术成就的理论总结。
明清小说评点美学是从蒋大器、张尚德的《三国演义》评论开始的。二位的观点基本一致,一方面肯定《三国演义》有裨“风教”的道德美,另一方面又肯定《三国演义》可以通俗的文辞“羽翼信史”,成为传播正史的有效辅助手段。这些评点尚未触及历史小说的深层审美规律。稍后继出的李贽和托名李贽的叶昼的《水浒传》评点则深入到小说在奇幻的虚构中“像情像事”、“逼真传神”的审美特点。于是,小说真幻相即的艺术真实问题饶有兴味地提出来,成为明代小说评点的中心话题。谢肇淛指出《西游记》“虽极幻妄无当,有至理存焉”,袁于令评论《西游记》“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李日华评论《广谐史》时说它“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冯梦龙评论话本小说《三言》时说它“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凌濛初评论《二拍》时说它“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标志着艺术真实问题已成为明代小说美学的共识。清人接过明人小说评点的接力棒奋力冲刺,创造了最终的辉煌。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不仅达到了这四大奇书评点的最高峰,而且深入分析了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完成了对中国小说美学的系统建构。如关于创作发生,金圣叹提出“怨毒著书”说,张竹坡提出“泄愤”“寓意”说,脂砚斋提出动“情”说。如关于艺术真实,金圣叹说小说是“因文生事”,“凭空造谎”,然而“任凭提起一个,都是旧时熟识”;毛宗岗说小说文字“有虚实相生之法”,要“出人意外”,又“在人意中”;脂砚斋强调“事之所无,理之必有”。关于人物塑造,金圣叹提出“格物”“动心”,过剧中人生活的思想;张竹坡要求作家“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脂砚斋反对“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简单化,强调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关于人物个性的重要性,金圣叹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写个性的方法主要有“背面敷粉”、“同中见异”;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最大的成功是塑造了一系列“奇人”“奇才”;张竹坡揭示《金瓶梅》之妙在“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能为众角色摹神”;脂砚斋认为《红楼梦》“写一人,一种人活像”,“移之第二人万不可”。关于古代小说的情节处理,则要求敢于设计相同相近的情节(犯),并在同中显异(避)。金圣叹谓之“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毛宗岗将犯而能避叫做“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并分析其缘由:“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张竹坡概括为“特特犯乎,绝不相同”。关于古代小说以情节取胜的美感特征,金圣叹称之为“险绝妙绝”、“险极快极”;毛宗岗认为“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⑦。
3、词论美学
关于明清词的发展状况,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概括说:“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王煜《清十一家词抄自序》云:“词自两宋而后,衰于元,敝于明,至清而复振。”词的创作自宋代出现婉约派、豪放派、骚雅派争奇斗艳的辉煌后,元明间则跌入低谷,清代则迎来了词的中兴。清代词人、词作之多,大大超过宋代。在词人辈出,词作众多的同时,清代词坛出现了云间派、西泠派、广陵派、浙西派、阳羡派、常州派等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与此相应,清代词学理论也迎来了宋代之后的又一高峰,呈现出与宋代词论乃至此前词论不同的“尊体”取向。
所谓“尊体”,即推尊词体的价值、地位。清代词论的“尊体”取向,是相对于五代两宋以来的词论多视词为“诗余”、“小道”的观念而言的。而这个时期的词之所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诗余”,是因为它大多以娱宾遣兴、表达与道德寄托无关的艳情或羁旅之情为主,这恰恰是诗不屑表现的。方智范先生在分析以宋代词论和清代词论为代表的中国词学批评两个高峰阶段的不同特点时指出:“前一个阶段自唐代至明末,以欧阳炯《花间集序》的‘侧艳论’发端,到北宋末年李清照《词论》提出‘别是一家’说,标志着以婉约为宗的传统词学观的正式确立……”词学批评的后一个阶段,是由清初至民国初年,随着词的创作的再度繁盛,理论批评也进入一个更为辉煌的时期:“纵览清代各家词论,几乎都贯穿着尊体观念,只是或显或隐而已。”⑧
明代词作,不出花前樽下的小词范围,词论则以词为“小道”、“小乘”。清代词风为之一变,所作词以道德为承当,以沉雄阔大为气象,各家各派均笼罩在“尊体”的词学观念中。云间派词人陈子龙认为词“小道可观”,沈亿年说“词虽小道”,但可“羽翼大雅”,报道了清代变“小道”为“大雅”词学观转变的最早信息。西泠派词人丁澎以“德业之余”重新界定“诗余”涵义,广陵派代表王士祯盛赞东坡稼轩词为“天地间至文”。阳羡派继续为素、辛变体张目,陈维崧认为“诗词经史,语无异辙”,任绳隗指出“不得谓词劣于诗”,史惟园要求词“入微出厚”,有风骚之“志意”。常州派论词主“风雅寄托”,张惠言主张“以内言外”,周济要求“意能尊体”,刘熙载强调“词莫要于有关系”,谭献甚至认为词之“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陈廷焯高标“沉郁”,大力推举辛弃疾,况周颐以“重、拙、大”为“词心”。这些都是从儒家道德意蕴方面给词注入厚重内涵。与此同一路径,查礼、郭麐、王昶、吴锡麒等人既否定“小道”观,也排斥学苏辛而流于“粗豪”的偏向。而浙西派论词“以雅为尚”,推尊姜夔张炎,如厉鹗声称词“必企夫雅”,朱彝尊主张以“雅”制“秽”,汪森进而认为“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侧重从超俗的道家道德方面使词从艳科之中摆脱出来,从而达到与诗平起平坐的地位。经过清人的努力,词成为与诗并列的一种诗体而为人们广泛接受。
4、戏曲美学
在经历了元代戏曲——杂剧的辉煌之后,明清戏曲迎来了传奇的繁荣,同时,杂剧在明清也间有创作。明代戏曲创作的兴盛对戏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内在要求,推动着明代曲论的发展。明代戏曲批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诞生了王骥德《曲律》这样的持论公允、剖析系统的曲论巨著,体现了戏曲美学的综合趋向。清代曲论在局部上继续有所深化,并出现了李渔的《闲情偶记》这样集大成的戏曲论著。而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则把中国戏曲美学推向了高峰。明清曲论不仅分析了中国古代戏曲的两种最主要的形态,即北曲杂剧和南曲传奇的不同特点,而且抓住戏曲创作的一般规律,诸如曲词特点、协律入乐、情节结构这三大要素展开探讨,并就戏曲“能感人”、寓教于乐的审美功能以及演员表演等问题提出要求,从而显示出戏曲美学的特殊个性。
明代中叶以后至明末,戏曲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论争。论争中出现了三大派。一派是本色派,主张戏曲创作符合戏曲本来的审美规律,曲词要入乐协律,明白易晓。如沈璟提出“宁协律而词不工”,冯梦龙要求“以调协韵严为主”,李开先主张“明白而不难知”,何良俊声明“填词须用本色语”,徐渭呼吁“贱相色,贵本色”,徐复祚崇尚“本色当行”,贬低“藻丽堆垛”,凌濛初也主张“贵当行不贵藻丽”都可归入这一派。另一派与此针锋相对,可以叫情趣派。不仅唯情,而且重趣。从“情趣”出发,汤显祖“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曲词“为情作使”,趣味所至突破音律制约,然而宁可“拗折天下人嗓子”。汤显祖的《牡丹亭》问世后,因为情节虚幻、文词典雅、音律未谐,遭到吴江派的批评,有人讥之为“案头之书”,非“场中之剧”。茅元仪、茅暎则竭力维护汤显祖,“事不奇幻不传,辞不奇艳不传”。王思任则不从“音律”,而是从“文义”方面赞赏《牡丹亭》。而张琦作为明末唯情论的代表,其《衡曲塵谭》则把情感至上的观点从戏曲扩展到散曲。在这两派的激烈论争中,也有一些人兼取两派的合理意见加以折中,可称之为折中派。他们主张,戏曲既“可演之台上,亦可置之案头”。王世贞主张戏曲既要“近雅”又应能“动人”,屠隆主张“雅俗并陈,意调双美”,臧懋循主张“雅俗兼收,串合无痕”,吕天成肯定“即不当行,其华可撷;即不本色,其质可风”,孟称舜认为“达情为最,协律次之”,祁彪佳“赏音律而兼收词华”,都体现了这种倾向。在折中派中,王骥德从“大雅与当行参间”出发,提出“以调合情”的主张,指出“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雕镂”这两种值得防止的偏向,在吸收以往各派各家成果的基础上,分四十章,就戏曲的源流、南北曲特点,音律、文辞、宾白、结构、创作方法等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清初李渔在此基础上著《闲情偶寄》“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首重“结构”,次论“词采”和“音律”,兼论宾白、科诨、格局和导演、表演,其中特别触及戏曲的人物塑造和审美接受特点,成为古代曲学的集大成者。金圣叹将前人的戏曲美学思想运用于《西厢记》评点并有自己的独特发挥。他从儿女“至情”的表现方面肯定《西厢》是“妙文”,驳斥“淫书”的诬蔑;围绕《西厢》之人物塑造、个性特征、情节结构、创作方法作出极为深入细腻的分析;并揭示了“借古之人之事以自传道”的创作发生奥秘和今日之读《西厢》不同于前日所读之《西厢》、“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⑨ 的审美创造特点。其深度和广度真可谓是登上了中国古代戏曲批评的最高峰。
五、近代:中国诗文美学的借鉴期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日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史称“近代”。这个时期,西方的各种人文思想蜂拥而至,冲击着传统的学术理念和思维方式,并与之发生化合、转换,促进了现代学术范式的诞生。美学学科也是如此。人们引入西方“美学”的学科概念,借鉴西方美学思想,同时继承中国几千年形成的美学观念,对艺术和现实中的美学现象加以讨论,“美学”走出原来散存于文艺理论和宗教哲学理论的依附形态,走向了独立的学术行程。
康有为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其美学思想大体由现实人生美学与诗歌书法美学两部分组成。在现实人生美学方面,他揭示了现实人生的一般痛苦本质和在当时君主专制下现实人生更为痛苦丑陋的本质,指出人类活动的历史就是“去苦求乐”、实即求美去丑的历史,人类社会的最终理想是“人人极乐,愿求皆获”,从而为用“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改良现实的“君主专制”社会,最终进入“民主共和”的“大同”社会、“太平之世”的政治主张服务。与他的人生美学理想和现实批判精神一脉相承,他于诗歌崇尚自然人情之美以及雄劲风格之美,于书法崇尚“点画峻厚”、“骨法洞达”、“魄力雄强”、“精神飞动”的北碑。梁启超继承康有为的快乐至上美学,肯定“爱美是人的天性”,明确提出审美至上、“趣味”至上:“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他借鉴西方学理界说“美”和“美术”(即艺术)的内涵:“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美术是情感的产物。”“美术的任务,自然是在表情。”“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由于“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握了”,他细致入微地分析了诗歌、书法、绘画、音乐之美的不同风格与种类以及书法“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表现个性的美”、小说“熏”、“浸”、“刺”、“提”的美,并以新的文艺美学观掀起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其变法实践张目。王国维的政治主张虽然与康、梁不同,但在借鉴西方美学、打造现代美学基础方面却异曲同工。他引用西方的超功利观点界定“美”的属性和价值:“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⑩ 美之价值,正在“无用”而“独立”。人间无用的“嗜好”,即是常见的美的表现形态。由此出发,他别出心裁地创造性地研究分析了现实中的各种“嗜好”形态,诸如“烟酒”、“博弈”、“宫室车马衣服”、“驰骋田猎跳舞”、“书画古物”、“戏剧”及“文学美术”,特别肯定“文学美术”是“最高尚之嗜好”。“文学”区别于“科学”、“史学”的审美特征是具有“玩物适情”功能,能够用“情感”和“想象”去表现科学的“知识”和史学的“道理”。“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他借鉴叔本华的“悲剧”观分析小说《红楼梦》,认为《红楼梦》的最高美学价值是作为“悲剧中之悲剧”,塑造了个性鲜明而又具有共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描写了“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从而使读者可以“得暂时之平和”。与此同时,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汹涌而至的小说创作热潮,人们借鉴西方美学思想分析小说的美学特征,如夏曾佑指出“小说之所乐,与饮食、男女鼎足而三”,黄人指出小说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徐念慈首倡“感情美学”、“理想美学”、“形象美学”概念,狄葆贤因而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章炳麟通过对西方“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文学特征论的反思,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都为蔡元培宣告“美学”学科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丰富的思想基础。
六、现当代:中国诗文美学的转型期
以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为起点,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
蔡元培早年留学现代“美学”的故乡德国,倾心“美学”研究。1915年访学法国期间,他编著《哲学大纲》一书,其中《价值论》一编中的第四节便是《美学观念》,该书191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他在湖南连续作了七次讲演,其中,《美学的进化》完整介绍了西方美学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历程。同年,他着手编著《美学道论》,写出《美学的倾向》、《美学的对象》两章。在北京大学主持工作期间,他首次将“美学”课程引进教学,并亲开“美学”课程。在《美学的进化》中,他揭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德国美学家鲍姆嘉敦创立:“……美学的进化……直到十八世纪,始成立科学。”揭示“美”的特质是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标志着现代科学美学与中国古代以“味”为美美学观念的根本分野,并于民国元年从德国单词译出“美育”范畴,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力倡导“美育”,后来一以贯之。蔡元培译介的“美学”和“美育”,标志着一门独立的“美学”学科的诞生。
与此同时,鲁迅在“五四”前后写下了有关美学的系列论文,强调愉快无用的“美术本质”,概括“悲剧”、“喜剧”的美学特质,留美的胡适和留日的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发起的从形式到内容的文学改良与革命,彻底奠定了不同于古代的美文学观念,从不同角度呼应着蔡元培,为现代科学美学的诞生推波助澜、铺平道路,也为文学由传统的杂文学向美文学的转型扫除了最后的障碍。1923年,吕澂的《美学浅说》、《美学概论》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陈望道的《美学概论》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蔡元培因为社会事务缠身没有完成的现代科学美学系统建构在他们手中完成。此后直到当代,可视为中国美学向现代科学美学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美学状况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里不再赘言。
收稿日期:2011-08-30
注释:
① 祁志祥:《中国古代美学系统整体观》,《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② 《易·坤·文言》,《周易正义》卷一,载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③ 《荀子·正名》,载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31页。
④ 《世说新语·伤逝》王戎语,载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⑥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载《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⑦ 毛宗岗批点:《第一才子书》第四十二回回评,邹梧岗参订本。
⑧ 方智范:《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前言》,载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⑨ 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载《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清顺治十三年本。
⑩ 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载《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标签:儒家论文; 美学论文; 国学论文; 形式美法则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水浒传论文; 读书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金瓶梅论文; 说文解字论文; 三言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