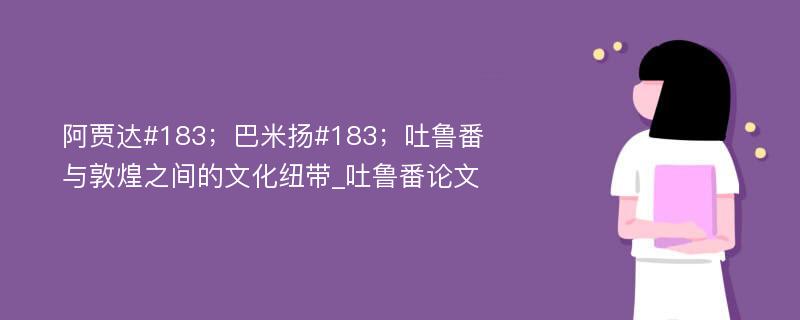
阿旃陀#183;巴米扬#183;吐鲁番与敦煌间的文化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敦煌论文,文化论文,阿旃陀论文,巴米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这一课题所含内容众多,本文仅就几个方面作一论述。历史告诉我们,阿旃陀(Ajanta)、巴米扬(Bamiyan)、吐鲁番和敦煌尽管相距遥远,但在文化上却不无联系。
首先,应该声明,这些古址的每一处都是文化发展中的里程碑。
阿旃陀位于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邦的奥兰伽巴德(Aurangabad)县,以其岩刻支提堂(Chaityagriha)和毗诃罗(Vihara)窟而闻名于世。石窟中现存壁画堪称世界艺术之瑰宝。阿旃陀艺术与建筑的影响远播巴米扬、中亚与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犍陀罗(Gandhara)、伊朗艺术传统亦为其翻版。
巴米扬,位处阿富汗中部峡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亦为繁荣的佛教艺术中心。
石窟开凿于兴都库什山区海拔8200英尺的山谷南面断崖上,在古代,有两条道路在此交汇:其一由中国出发,经葱岭和兴都库什山而至伊朗,另一条则经印度河而至缚喝(Balkh)。古典作品称巴米扬为“中亚语言、文明和宗教的前哨与十字路口。”来自印度的这条道路被称为“大王道(the Great Royal Way)”。①
这些商道也经历了不少战火的洗礼。居鲁士(Cyrus)、亚历山大(Alexander)、塞琉西斯王(Seleucids)、汉人、哈里发(the Caliphs)、成吉思汗、帖木儿(Timur)、巴布尔(Babur)等人及其军队就是循此二道而远征的。
作为不同部族、不同文化所交之一都会,巴米扬融汇了各种不同的艺术传统,如伊朗、犍陀罗、印度(包括笈多王朝和阿旃陀)之风格。阿旃陀的岩刻建筑直接刺激了巴米扬石窟寺的形成。
如所周知,巴米扬也是外来思想意识进入印度或印度思想意识传入西、北方诸国的门径。敦煌在中国文化西传及西方艺术与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起着类似的作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窟艺术也相当辉煌,除克孜尔之外,其余石窟寺都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的吐鲁番绿洲。
吐鲁番素有艺术与宗教“溶炉”之誉。在古代,世界四大宗教:佛教、摩尼教、教和景教都在这里并行不悖。吐鲁番的艺术亦以这些宗教的口味和需要而异彩纷呈。
吐鲁番绿洲为一低于海平面300余英尺的盆地,处于天山博格达峰与库鲁塔格山之间,气候非常干燥,然而,丰富的高山冰雪溶水却为其五谷、水果和棉花的生长提供了固定的水源。但这并非吐鲁番繁荣的主因。它之所以繁荣,是因为自然条件为它提供了与天山北部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契机。
中国西陲的敦煌,如同巴米扬一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受着中原、中亚和印度的影响。丝路古道横贯敦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它也是中原王朝统治塔里木盆地城邦诸国的军事前哨。
佛教在敦煌的繁荣相当早,3世纪的竺法护即为其最著名的高僧之一。②他精通汉语、梵语等多种语言。据载,他先后译有《正法华经》、《普曜经》等多种经典。他的活动促进了4世纪时佛教在中国北部的传播。此外,4世纪时还有不少佛僧为避战乱而流入敦煌,使之进一步发展为当时的佛教中心。
在敦煌东南约10哩处就是著名的千佛洞。敦煌之盛名主要就仰仗于历时千年之久的石窟壁画和其它艺术珍品。该石窟群为一大乘经典及以这些经典(如《大阿弥陀经》、《法华经》、圣猛(Aryasura)的《本生(Jatakamala)》和《维摩诘经》等)为依据所绘壁画的巨大宝库。
本文所述的这四处遗址都因佛教而盛,也都由著名的丝路古道维系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及思想在这里进行交流。
前所提及的商道,是后来才以丝绸之路而闻名于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西方诸国(远及罗马世界)的丝绸贸易是通过这条道路来实现的。但若抠字眼,“丝绸之路”这一术语并不准确,因为除了丝绸之外,其它商品也是通过此路来贸易的。它之所以能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人喜欢丝绸,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些奢侈品对罗马人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若说中国是通过丝绸而发现欧洲的,一点也不为过。
丝绸之路始于长安,经由河西走廊而至敦煌。离敦煌经由著名的玉门关而分为南、北二道。北道穿沙漠而至哈密,然后沿天山南麓而达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图木舒克和喀什。南道则经米兰、于阗和莎车等绿洲小城,由莎车北行可与北道交于喀什。从喀什沿丝绸之路继续西行,横穿葱岭而抵浩罕(Khokand)、撒马儿罕(Samarkand)和布哈拉(Bokhara),继续西行即至谋夫(Merv),再穿过波斯、伊拉克而达地中海岸,最后舶至罗马和亚历山大城。③
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佛教与佛教艺术也广播阿富汗、伊朗、粟特、新疆、敦煌及中原等广大地区,它象一条共同的纽带,把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联系了起来。以其慈悲之怀,佛教受到广大信徒的崇拜。除了给中亚人民输入一种宗教外,佛教的文化,尤其是艺术也在这里生根发芽。中国虽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和诸如儒教、道教一类的宗教体系,但佛教的确渗透了进来,并战胜对手,顶住压力而得以存活。在中国,佛教已发展成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佛教最后发展为有着折衷主义外观的综合性文化。无论走到哪里,它传播的并非全是法音(无疑这是其主要目的),也有印度文化的其它成分,如医学、音乐和天文学,更无庸说丰富的艺术、建筑、文学、宗教仪礼了。值得一提的是,大乘佛教在中亚和敦煌找到了合适的场所,使其文学和建筑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据称,2世纪的支娄迦初开入华传播大乘佛教之风,他的活动为以后(3世纪晚期和4世纪)大乘教深入士大夫的生活与思想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空门”思想在士大夫中很流行。发韧于安世高的禅法在早期中国佛教史上一直相沿不绝,尽管其影响范围主要局限于僧伽。④
阿旃陀
有了上面的背景,我们可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阿旃陀的岩刻洞窟及其壁画。就石刻建筑的起源与功用而论,广言之,山崖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与信仰中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山是苍天与大地、伟大与渺小、人间与天界间的连媒。以佛教宇宙观来看,“妙高山(Meru)就是宇宙的中心”。
在印度的岩刻石窟中,阿旃陀最负盛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连结达克辛那巴他(Dakshinapatha)和乌他拉帕特(Uttarapatha)的商道由此而过;其中不少石窟有着独特的建筑学特征,更重要的是窟内辉煌壮丽的壁画。
山上神之庄严总是诱惑着人们,并引导着信徒的宗教活动。山不在高,有仙则鸣。正是这些神祗激发人们尽自己的能力与幻想去修饰那些岩刻窟龛与庙堂。
此外,很多的宗教团体,不管是佛教的,还是耆那教的,甚或其它宗教的,都把出家视作精进和获救的最佳途径。如此,那此游僧自然就需要找到挡风遮雨的地方。山洞遂成了理想的场所。久而久之,洞窟艺术兴盛起来了,岩刻建筑亦随之蓬勃发展。伽耶(Gaya)附近的巴巴尔(Barbar)诸石窟群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这些窟群中最重要者有洛玛什·日希(Lomash Rishi)石窟群和苏达玛(Sudama)石窟群。其中后者是阿育王为正命论(ajivika)苦行者开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印度成了这类建筑活动的中心。自公元前2世纪始,大约一千年间,这里相继开凿了一千余处石窟,它们大多都是佛教徒祈愿的产物。这些石窟中,以阿旃陀石窟最为著名。遗址主要分佛殿、僧房两大类。现共编号大小30座。就时代而言,这些石窟可分为两大独立阶段。较早者包括9、10、8、12、13和15A,属于纪元前的遗物。⑤其中以10号窟最古,凿于公元前2世纪。其余均为5~6世纪所开(与前者间隔4个世纪),主要是在瓦卡塔卡(Vakataka)王朝(在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官员与封建主的资助下建成的,该王朝与北印度的笈多(Gupta)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阿旃陀石窟的一些建筑颇有特色,造型艺术也独具匠心,但其芳名之远播却主要凭借于它的壁画。在印度,壁画一般都为雕塑与装饰性雕刻的附属品。但在阿旃陀,壁画却使该石窟的其它特征都相形见绌。
第10号窟为我们提供了阿旃陀壁画的最早例证。因为当时佛像还未产生,窟中的壁画(公元前2世纪),如同巴尔胡特(Bharhut)塔和桑志(Sanchi)大塔中的纪元前栏一样,表现的为传统的小乘教主题,如本生故事、堵波、菩提树崇拜,且与旧的以平行栏来表现情节的叙事风格相一致。⑥
随着时代的变幻,印度艺术日臻精美。公元5~6世纪的瓦卡塔卡石窟壁画不仅题材扩大,而且在技法与风格上都较早期更为完善。阿旃陀的瓦卡塔卡艺术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全景,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人间的还是天堂的;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尽管佛与菩萨、本生故事与譬喻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艺术家的想象力,但世俗生活的诸方面却并未因此而被忽略。宫殿中的王子,闺房中的小姐,以及信使、苦行者、乞丐、农民和兽类等都表现得维妙维肖。变化多端是阿旃陀壁画的灵魂。肇源于阿玛拉瓦提(Amaravati)或安德拉(Andhra)艺术的优美线条及韵律变化之妙用,使阿旃陀壁画更加熠熠生辉。然而,阿旃陀雕塑艺术却为当地传统与鹿野苑(Sarnath)以佛像与菩萨像为特征的笈多艺术风格相结合的产儿。
阿旃陀壁画自成体系。没有哪个印度画派可与之匹敌,不管在永久性上,还是在深度和数量上都是如此。阿旃陀风格的影响在9~10世纪东印度的贝叶细密画中可清楚地看得出来。
阿旃陀壁画中的人种多样性体现了阿旃陀作为宗教中心,同时又为印度文化与邻国相联系的枢纽的重要意义。阿旃陀之名也引起了中国西行僧玄奘的注意,并书之于他的《大唐西域记》一书。阿旃陀艺术闻名遐迩,成为邻国艺术家争相学习的楷模。
巴米扬
谈起印度文化向西亚、中亚及中国之输入,巴米扬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它是犍陀罗僧侣、商人循丝绸之路通往中亚和中国的始发站,也是中亚、中国人进入印巴次大陆的最后一站。巴米扬的另一重要性在于其地理位置。这里地近兴都库什山,越过此山,可达喀喇昆仑山系。贵霜(Kushana)时代,阿富汗中部在文化上已相当印度化了,尽管那里仍受着希腊与伊朗的影响。贵霜帝国幅员广大,统治着从中亚直到恒河谷地的广大地区。迦毕试(Kapisa),今贝格兰(Begram)为迦腻色迦王(Kanishka)的夏都,秣菟罗(Mathura)则为其冬都。
贵霜王朝政策宽容,鼓励境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思想文化的交流。国家确保商道的安全,并充当着当时两大超级大国——罗马帝国与汉朝间发展商业活动的中介。
在迦腻色迦王的支持下,犍陀罗艺术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有贵霜一代,佛教在犍陀罗(Gandhara)和邻近地区独领风骚,这里的佛教雕塑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希腊诸神。⑦巴米扬也受到了这一潮流的冲击。
巴米扬峡谷二侧均为砾岩峭壁,上有很多石刻圣址和巨佛竖龛构成的窟室。⑧峡谷东端的佛像约有120英尺高,呈犍陀罗风,约建于公元2世纪,而邻近的几座饰有壁画的石窟则应迟至公元5~6世纪,受到了当时声被中亚乃至中国的萨珊(Sassanian)风格的影响。特别应该注意到巴米扬某些石窟的窟顶饰有模仿萨珊织物圆形图案而绘制的壁画。⑨新德里国立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New Delhi)所藏由奥利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取自吐鲁番绿洲阿斯塔那古墓的猪头萨珊织物残片也值得联系起来考虑。
巴米扬峡谷的西端为另一巨佛,高175英尺,身处一三叶形龛内,其饰有“线状脊背”的帐帘昭示着它与笈多风格之秣菟罗佛、菩萨像间的姻亲关系。
笈多艺术形式在巴米扬峡谷的广泛流行也可从距巴米扬二、三哩处卡克热克(Kakrak)的有着“卵形脸”、大头和“莲花(Loti)形眼睛”的佛像中得到佐证。我们在巴米扬石窟中见到的萨珊艺术的种类属于东伊朗艺术型,其影响广播远方,一方面传入阿姆河北岸的瓦拉卡沙(Varakasha)、片治肯特(Pyandjikent)和巴拉里克达坂(Balalik Tepe),另一方面又传入多克塔里—纳西万(Dokhtari-Nasirwa)和巴米扬。10
有证据可以表明,巴米扬的繁荣一直持续到7~8世纪,玄奘于632年游历至此,并对这里的人民与习俗及其佛教情况作过详尽的记述。该国的国王自称为迦毗罗卫国释迦族的后裔,盛情款待了玄奘。玄奘参观了巴米扬的大佛和弥勒像。至于这里的佛教寺宇,他记述道:
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有伽蓝
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11)
该说出世部(Lokottaravadin)即为大众部(Mahasanghika)的一个支派。该派认为:“世间法但有假名,都无实体。”唯有“出世之法”才是真实的。
巴米扬艺术家颇受说出世部的影响,他们制作巨形佛像以产生佛的面貌难为一般人理解的效果,这就适应了该派所认为的“世界之法,为自颠倒惑业而生之果,悉是假名”的思想。
尽管玄奘已记载巴米扬为小乘佛教,尤其是说出世部的一个中心,实际上它同时也是大乘信仰的一个据点,现存的艺术品即可证实这一点。学界已注意到,卡克热克的石窟有一些很有趣的壁画(现已移入喀布尔博物馆),其中之一为曼陀罗(Mandala),中心有毗卢遮那(Vairocana)佛,四周为小佛。曼陀罗在卡克热克壁画中的出现似乎支持了爱德华·昆泽(Edward Conze)所谓金刚乘(Vajrayana)佛教源自犍陀罗地区的观点。(12)卡克热克所见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曼陀罗范例。
这里,须顺便提一下巴米扬西120公里、喀布尔北117公里处的冯度斯坦(Fonduskistan)大佛寺(7世纪)。
冯度斯坦的壁画,如同巴米扬的一样,既受印度、又受伊朗艺术表现方法的影响。(13)喀布尔博物馆藏品中的冯度斯坦观音菩萨(或为弥勒菩萨)之线条可与阿旃陀石窟1号洞的莲手菩萨(Bodhisattva Padmapani)相媲美。该塑像的上身,亦即胸部有着犍陀罗传统的男性特征。冯度斯坦作与愿印(Varada mudra)的菩萨纯粹就是犍陀罗式造型与笈多式高雅的结合。
巴米扬艺术风格与题材传到了中亚与中国。云冈石窟的巨形佛像似乎即受到了巴米扬艺术与建筑风格的启发。(14)很可能,如同巴米扬一样,云冈也是说出世部的一个据点。巴米扬、中亚和敦煌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是这些地区太阳崇拜的流行。
“巴米扬120英尺大佛龛的下部为一乘四轮轻便马车的太阳神巨型壁画。”(15)这里似应注意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太阳神与月亮神,还有冯度斯坦佛寺中所见的太阳与月亮。太阳形象亦可见于塔克拉玛干北缘丝路北道库木图喇附近的明屋(Ming-oi)。(16)敦煌石窟288窟(17)绘有太阳与月亮的四轮马车。从这些例子可清楚地看出中亚人民中广泛流传的对日神、月神的崇拜。(18)
巴米扬日神像为圆面,衣着方式与秣菟罗所出迦腻色迦像近似,这种类似性引导一些学者将日象与王室联系了起来。(19)佛有时也被称作“Arkabandhu”,以表明他属于太阳(即the Suryavamsa)之后代——甘庶王家族(Ikshvaku family)之一支——刹帝利皇室这一事实。
克林凯特(Klimkeit)教授持巴米扬有一圣地与王室有交这一观点,理由是有一铺壁画上国王与王后戴着上有日天、月天象征的王冠。
吐鲁番
如前所述,吐鲁番是丝路北道上的一处交通咽喉,地处塔克拉玛干西北缘。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丝路北道变得生机勃勃,所以吐鲁番地区的安全也就深为中原王朝所关心,以免遭到游牧民的袭击。公元前73~49年间,中原王朝首次征服了吐鲁番,继之,包括莎车在内的其它地区也并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保证了商业交流的顺利进行。
在吐蕃所占领的那一短暂时期之后,约在8、9世纪间,吐鲁番受到了回鹘政治势力的统治。回鹘对吐鲁番的统治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3世纪沦陷于蒙古。“宋朝使臣王延德于982年访问了回鹘王国,对吐鲁番的兴盛、佛教的发达、波斯摩尼教师的存在及回鹘文化都做了有趣的记载。”(20)大规模的艺术活动在9~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相当兴盛。
吐鲁番地区的考古发现含有各种遗物,诸如壁画残片、纸画、绢画、佛教陶塑、刺绣及回鹘文、吐蕃文、汉文和摩尼教徒所用的变体叙利亚文写本残片。
如上所述,各种宗教,诸如除佛教之外的摩尼教、景教、教都在吐鲁番找到了合适的土壤。(21)尽管回鹘王室崇信摩尼教,但对其它宗教也持宽容态度,佛教在吐鲁番的地位并未因其它宗教的存在而有所动摇。
在早期的吐鲁番壁画中,最显著的因素有两个,一者伊朗,一者中国,当然印度因素并非全然无存。伊朗因素在摩尼教壁画和德国学者于高昌发现的细密画中占有优势地位。还有一些壁画残片是属于景教团体的,这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叙利亚和西方艺术因素。(22)至于中原对吐鲁番壁画的影响,那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柏孜柯里克的壁画。
德国对吐鲁番的考察以其发现摩尼教壁画及典籍而特别令人难忘。(23)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约于公元215或216年出生于波斯所辖巴比伦省的塞斯风(Ctesiphon)附近。受其父思想的感染,摩尼开始了其宗教生活。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富有感召力的教师,因为他有着纯粹的波斯血统,所以他所传播的宗教也自然有着波斯的传统,亦即光明与黑暗互相斗争的二元论思想。(24)
摩尼教是一种严格的禁欲主义宗教,禁止所有的性行为,禁食酒肉,禁止享有任何财富和贵重物品。为了传播他的宗教,摩尼踏遍了有可能包括印度和中亚在内的一个又一个地方。据信,他与佛教徒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解释了摩尼教与佛教间的在多种因素上的契合。除了他做为摩尼师的神秘特点外,摩尼也颇具审美意识,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和音乐家。传说与文献资料都称摩尼在壁画和细密画上都很有造诣。哈拉和卓附近的高昌故城所出的摩尼教的写本在其它地方都未曾发现。这些写本书以优美的书法,饰有鲜花和绿叶。(25)也有一些摩尼教写本是用叙利亚文和粟特文字母写成的。
柏林所藏哈拉和卓摩尼教写本尚待甄别,笔者已识别出一份摩尼教细密画残片,(26)其画中人物为印度教诸神,如梵天(Brabma)、毗湿纽(Vishnu)、湿婆(Siva)及讹尼沙(Ganesa)。尽管这些画像的真实内容尚不敢确定,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摩尼教已经吸收了包括印度教在内的各种因素。如所周知,摩尼到过印度,他的教会组织也是以佛教为模型的。很有可能,他熟悉印度教思想,所以在摩尼教寺庙中也可以看到印度教神祗。勒柯克(A.von Le Coq)在高昌故城发现了一个绘有摩尼及其信徒的壁画残片。(27)
德国探险队在哈拉和卓附近的高昌故城中发现有非常有趣的景教壁画,与吐鲁番或中亚所出其它类型的壁画迥然不同。聂斯托利(Nestorian)否认基督同时可以是神也可以是人的说法,为此,他被送上了以弗所(Ephesus)宗教法庭。他的很多信徒逃往萨珊(即今伊朗),又从那里流亡中亚和中国。公元638年于长安建立了第一座景教寺院。大量的景教写本和遗物出土于塔里木盆地的不少地方和敦煌的藏经洞中。(28)
在高昌出土的景教壁画残片中,有一幅描述的是宗枝节(Paem Sunday),(29)已由勒柯克鉴定出来。关于景教绘画,可以观察到的是它们表现出一种空间感,不象大多摩尼教壁画那样表现得拥挤不堪。在像与像之间留有空间,以显示每个人的个体。在壁画左端的牧师是叙利亚人或拜占庭人(Byzantanian),而朝拜者们却似乎为蒙古利亚人(Mongoloids)。
在德国的收集品中,有相当多的纸和其它材料的绘画,表现出各种风格都在吐鲁番绿洲时髦过,我们可以参考的例子也仅有这些。例证之一亦即高昌故城所出的一幅壁画,绘有三个女摩尼教徒,她们的黑发垂落到背部和肩膀,卷发垂于耳鬓。(30)这种发型与丹丹乌里克所出还愿木板上的“丝绸公主”相仿佛。耳鬓的垂发尤同于米兰所出的一些人像。在塔里木盆地,最早的壁画发现于米兰。米兰的造像艺术对中亚乃至敦煌的艺术有着既深且巨的影响。相似的例子也可见于敦煌的一个散花飞天。(31)吐鲁番与敦煌间艺术风格的相似性毋需惊奇,因为这两个地方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中原的统治和文化影响之下。
吐峪沟
在开始描述柏孜柯里克石窟这一吐鲁番地区最大的石窟寺之前,我们尚需对吐峪沟的文物作一简述。这里有许多岩刻石窟,在历史上曾有佛僧定居过。该遗址已由勒柯克、斯坦因作过调查,他们都在这里收集到过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可见,地处哈拉和卓东南的吐峪沟在8、9世纪间一度是繁荣的佛教艺术中心。
至于德国所藏勒柯克于吐峪沟所获的收集品,可举之例不多,其中包括一只彩绘木匣和一件绢画。该绢画中绘有护法神(Lokapala)头像、观音菩萨头像,这些内容可与属于公元706~711年间的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中的壁画以及那两个造型优美的女供养人相互比较。这些例证再现了中原对塔克拉玛干,尤其是吐鲁番绿洲的深刻影响。在斯坦因于吐峪沟发现的绘画残片中,我这里只举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它出自吐峪沟一佛龛的圆顶,其上有大量附有婆罗谜(Brahmi)铭文的人物形像。笔者已认出了其中一些印度星座(Nakshatras)的名号,有张(Purvaphalguni)、翼(UttaraPhalguni)、房(Anuradha)、氐(Visakha)、星(Magha)、虚(Dhanistha)、觜(Mrgasiras)、亢(Svati)、胃(Bharani)、角(Citra)、毕(Rohini)。(32)这意谓着这种印度的星座形式在中亚流行过。印度的星座体系在新疆的流传也可由鲁道夫·赫恩雷(A.F.Rudolf Hoernle)所研究识别的韦伯写本(Weber Manuscripts)的某些内容来证明。
我们知道,学者们于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遗址中发现的印度医学、天文学、音乐和其它科学技术都是由佛僧带入中亚的。
柏孜柯里克
柏孜柯里克位于哈拉和卓的西北,是吐鲁番地区最大的石窟寺群,计有100多号洞窟,所有这些石窟原来都有壁画装饰,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其中许多已损毁了。柏孜柯里克石窟群已由德国、俄国的学者和斯坦因爵士作过考察。壁画被剥走,现分别保存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the Indische Kunst,Berlin)、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the Hermitage,Petersburgh)和新德里国立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New Delhi)。柏孜柯里克壁画绝大多数属佛教内容,其风格当属9~10世纪,系高昌回鹘王国的遗产。尽管回鹘王室崇信摩尼教,但他们也奖掖佛教和其它宗教,这可以从柏孜柯里克的壁画中出现有回鹘王子和公主这一事实得到证明,他们是柏孜柯里克佛教石窟寺的功德主。柏孜柯里克产生有规模巨大的佛僧绘画,既有印度人,也有东亚人,从他们的体态即可分辨出来。不同类型的佛像或坐或站。佛本生的不同场面也都活灵活现,有的表现他乘船旅行(或许是去吠舍离城),也有表现其弟子们的悲伤场面,还有誓愿场面等等。除了其它所谓的荼家女(Dakini)像外,还有印度传说中的题材,如天神、女神、伎乐天、龙王和魔鬼。
这些壁画表现的人种也是五花八门的,既有印度人、波斯人,也有回鹘人、阿拉伯人和汉人。柏孜柯里克壁画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所有的造像表现的都是侧面。佛像有胡子,这或许是受犍陀罗影响的结果。所有的佛像都饰有精美的头光和宝石璎珞,都脚着凉鞋。汉风在柏孜柯里克壁画中占统治地位,正如安德鲁斯(Andrews)所指出的那样:“其衣着特征暗示着其原始底样有些是由汉人画家绘制的,在某些情况下,纯粹就是中原画家画的,绘画的处理方法也是中原式的。”
吐鲁番画家艺术之精巧在塔克拉玛干的其它地方很难见到。有一些绘于丝绸或墙壁上的回鹘人像表现的纯粹就是肖像画。吐鲁番壁画中的山水画也值得重视,仿佛它们力图再现现实世界。吐鲁番和敦煌间的共同因素是很多的,因为比起塔克拉玛干的其它绿洲城邦而言,它们与中原文化联系更多。
敦煌
我想以对敦煌的介绍作为本文的终结。
敦煌石窟均被刻于比较疏松的砂砾岩中,上下分为几层。“凿为灵龛,上下云矗,构以飞阁,南北霞连。”
据敦煌的一通碑刻记载,莫高窟的兴建始于366年,当时乐和尚看到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于是便怀着崇敬之心,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以后越开越多。敦煌堪称中国宗教绘画之大全。敦煌石窟先后历魏、隋、唐,直至宋初,它本身就是一部从4世纪到10世纪的中国美术通史。
敦煌的佛教造像领域宽广,既有佛、菩萨像,也有本生故事、兜率天宫,还有维摩诘故事、千佛、护法神、摩醯首罗(Mahesvara)、讹尼沙、日月神的四轮马车、山水画、韦提希夫人(Vadehi)故事、天宫伎乐、过去七佛、伎乐天、玄奘取经图、于阗王、罗汉与供养人、飞天与天人。
佛教传至敦煌,经过了丝路南北二道,所以敦煌艺术受到的影响也是迥然不同的。北边的受克孜尔和吐鲁番影响,南边受和田和米兰的影响。
至于印度方面,对敦煌影响较大的是迦湿弥罗(Kashmir)。敦煌和迦湿弥罗的一些佛像和背光几无二致。很多迦湿弥罗的和尚东至敦煌和中原,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功勋卓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求那跋摩(Gunavarman)和昙摩蜜多(Dharmamitra)。求那跋摩尽管出生于迦湿弥罗王室,但他屏弃了其优裕的生活,而开始了化缘生涯。424年,他受宋文帝使者的邀请,乘印度商船游至广州。据说,在邻近的一处庙宇中,求那跋摩亲手绘制了罗罗(释迦牟尼之子)像,同时描绘了在犍陀罗地区很流行的燃灯佛本生。(33)
另一位迦湿弥罗和尚昙摩蜜多是由陆路经龟兹、敦煌而入中原的。在敦煌,他“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离开敦煌后,他来到凉州,又于424年抵达四川。继之顺江而下,至于南京。据称,其“道声素著,化洽连邦,至京甫尔,倾都礼讯。”但他却宁愿居于县之山,建塔立寺。又于435年,“斩石刊木,营建上寺。士庶钦风,献奉稠叠,禅房殿宇,郁尔层构。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讽诵肃邕,望风成化。”(34)
从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些佛僧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多才多艺,懂得绘画与建筑。
山水画不管在阿旃陀还是在敦煌,都起过重要的作用。阿旃陀的山水画是一种自然的装饰,附属于建筑的需要。而在中国艺术中,山水画的创造倾向于妙手信笔,不受约束,所以象岩石、水、树、草、云、雾等自然因素都担当着重要角色。
敦煌的重要意义并不局限于其壁画。尽人皆知,斯坦因和伯希和在中亚探险时,于莫高窟藏经洞中收集有以不同语言文字书写的大量写本,还有许多丝幡和各种风格的绘画。
斯坦因收集的各种幢幡已由瓦累(Arthur Walay)爵士作了透彻研究。以他之见,这些敦煌幢幡的主要风格可分为三组:印度佛画、中国佛画和中国世俗画。还可以说有另外的两小类,那就是吐蕃画和泥婆罗(Nepal)画。
恰如瓦累所分析,印度佛画风格是“半裸和卧姿”(头在一侧,身体在臀部弯曲,一腿上提,等等),且脸型为印度式的。中国式佛画一般姿势匀称,汉人脸型,至少不是印度脸型。幢幡的二侧为施主,著典型的汉族服饰,标示着中国世俗化的影响。偶而也可在这些画中看到几乎已中国化了的印度人。在敦煌幢幡中的一些吐蕃、泥婆罗影响可以吐蕃曾于670年占领塔里木盆地,继又占领敦煌,并在这里统治了相当长时间这一因素来解释。
有幸的是,部分敦煌的作品署有明确的日期,这便为那些没有署明日期的作品从施主的服饰上提供了断代的线索。另外一条断代的依据是壁画所使用的颜料。
至于绢画的质量和技巧,可以参考伦敦大英博物院(the British Museum,London)和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的藏品。瓦累观察到,“这些绘画的实际创作水平并不在手艺人之上,其大部都可能临自7世纪的原件。当然,即使在最粗劣的复制品中,也要赋予这些佛画以深刻含义的主旨还是存在的。这种特性的秘密在于其原则——现实的图案(描黑、高光、轮廓线等等)转化为无意义的图解形式。这个过程首先适用于雕塑。人们在犍陀罗艺术中看到的帐帘密褶在敦煌已由聚会场面所取代,意在表示除了纯粹的泥制品外,一切都是空的。敦煌壁画中给平面标界的曲线足以清晰地表明,它们是从雕塑艺术中借用过来的。”(35)
注释:
① Earnst Diez《亚洲古代世界(The Ancient World of Asia)》(W.C.Darwell英译本),伦敦1961年,第138页以下。
② Kenneth K.S.Chen《中国佛教史(Buddhism in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1972年,第60、89、365、367页。
③ Peter Hopkirk《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Foreign Devils on theSilk Road)》,伦敦1980年,第16-31页;Tamara Talbot Rice《中亚古代艺术(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纽约 1965年,第176页以下。
④ E.Zurcher《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莱登1959年,第35页以下。
⑤ Debala Mitra《阿旃陀(Ajanta)》,新德里:印度考古局1983年,第5页以下。
⑥ Debala Mitra《阿旃陀》,第43页。
⑦ 同第70页注②,Tamara Talbot Rice《中亚古代艺术》,第162页。
⑧ Benjamin Rowland《阿富汗的古代艺术(Ancient Art from Afghanisthan)》,亚洲学会,1966年,第162页。
⑨ Benjamin Rowland《阿富汗的古代艺术(Ancient Art from Afghanisthan)》,亚洲学会,1966年,第95页。
⑩ 同第70页注②,Tamara Talbot Rice,《中亚古代艺术》,第104~110页。
(11) E.W.Rhys Davids和S.W.Bushel编《托马斯·瓦特斯论玄奘的印度之行(Thomas Watters on Xunzengs Travels in India)》,印度 1973年,第116页。译按:语见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页。
(12) 同第73页注②,Benjamin Rowland《阿富汗的古代艺术》,第98页。
(13) 同第73页注②,Benjamin Rowland《阿富汗的古代艺术》,第116~118页。
(14) 同第73页注②,Benjamin Rowland《阿富汗的古代艺术》,第95页。
(15) Hans-J.Klimkeit“中亚之被视作神灵的太阳与月亮(The Sun andMoon as Gods in Central Asia)”,载SARAS,第11~12页。
(16) Basil Gray《敦煌佛窟壁画(Buddhist Cave Paintings at Dunhuang)》,伦敦1959年,第44页,图22A、B。
(17) 当为285窟。——译者
(18) 同上,Hans-J.Klimkeit“中亚之被视作神灵的太阳与月亮”,第18页。
(19) 上注,第18页。
(20) 勒柯克《新疆之文化宝库(Buried Treasure of Chinese Turkestan)》,伦敦,1928年,第57页以下。
(21) M.Bussagli《中亚绘画(Central Asian Painting)》,日内瓦,1963年,第110~114页。
(22) 同上,勒柯克《新疆之文化宝库》,第55~63页。
(23) 同上,第22、32、35、45页。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其实,这一内容早已由德国学者克林凯特(Hans-J.Klimkeit)识别出来,并有详尽论述。见其所著“摩尼教艺术中的印度教神祗(Hindu Deities in Manichaean Art)”,载《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第14卷2号,1980年,第179~199页。——译者。
(27) 同第70页注②,Peter Hopkirk《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33、158、165、173~176、182~189、205、207、217、226、235~240页。
(28) 同第75页注②,M.Bussagli《中亚绘画》,第110~114页。
(29) 同上书,第56页及附图
(30)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编《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西柏林国家博物馆藏中亚艺术品(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纽约1982年,图124。
(31) P.贝纳尔吉(Bannerjee)“吐峪沟石窟天井所见星座(Nakshatras in the Ceiling of a Buddhist shrine in Toyuk)”,《菩提之挽缰》(Bodhi-Rastni)》,新德里1984年,第146~49页。
(32) 同第76页注⑦,P.贝纳尔吉“吐峪沟石窟天井所见星座”。
(33) Alexender Goburn Soper《文献所载中国早期佛教艺术(Literary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瑞士:亚洲艺术出版社,第43页。
(34) 上引Soper书,第43~44页。
译按:语出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 1992年,第121~122页。
(35) 瓦累《斯坦因爵士所获敦煌画品目录(A Catalogue of PaintingsRecovered from D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伦敦,1931年,第X~XI页。
标签:吐鲁番论文; 佛教论文; 壁画论文; 明教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艺术论文; 中原论文; 敦煌博物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