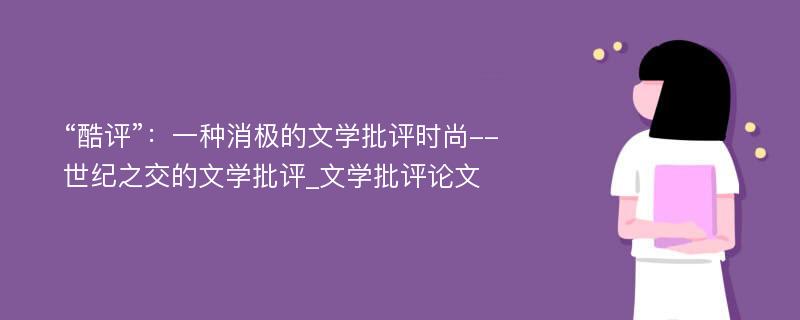
酷评:一类反调的文学批评时尚——世纪之交文学批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世纪之交论文,酷评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多潮的纷繁状态。“酷评”,一类专以唱反调的否定名作家作品为主,追寻时尚,制造商业化效应的文学批评,也惊世登场。
“酷评”,和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种在青少年中引为时尚的“酷”文化相联系,却又不尽相同,它是以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潮做基础,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展示批评者面貌的,以专门批判名人名作的否定性结论作为特殊标志,并带有相应商业化(广告化包装化)手段的一类文学批评。可以说,它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风景,一类值得评价的文学批评现象。
一、“酷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种被称为“骂派”批评的现象,在中国文坛浮现。应当指出,这种“骂”,在社会中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解。一类是指与完全赞美(其中有的同样也包含商业化目的)的作家作品评价不同,有不同意见的批评文章。一类则是并非一般的不同意见,而是以否定作家作品的全部(或基本方面)文化意义,甚至用语失去文雅节制,带有血色与喊腔的激愤之评。“骂派”批评的叫法并没有多久,它们作为潮流也并非抢眼。以后,这种骂派批评中的后者,与现代文学史研究乃至社会文化中,对基本的人文精神,对鲁迅、老舍、茅盾等经典作家的否定性倾向的思想文化潮流相混合,又与社会时尚中的“酷”文化相结缘,而被称为“酷评”。应当说,“酷评”现象极为有趣的一点是,目前没有一个批评家公开自称为“酷评家”(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酷评”一词多出现于对这类文学批评不满与否定的意见之中。而出版界则兴趣盎然。有些出版者一则以发表(甚至策划)这类文章而惊人,一则干脆将这类批评公开宣称为“酷评文丛”。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列入该丛书的一位作者却公开声称,自己“这样的文章不算酷评”。
“酷评”这一词,并没有得到特别认真的专门梳理。有的指时尚批评(新潮前卫),有的指骂派批评(广义的否定性结论),有的指不讲学理的批评(残酷无理)。
本文则试图通过分析,给出一个我所理解的严酷评”定义。
二、“酷评”样本
我所理解的“酷评”,是一种对具有文学意义的命题,带有文学批评的言语方式,以激烈的方式否定批评对象的文学意义而带有整体否定的文学批评。简言之,是文学的,却非学理的;是激情的,却非理性的。
由此,我将两类批评划出“酷评”之外。一类是学者的学理批评,如王彬彬的《文坛三户》,虽然也激烈地批评了余秋雨,却是“从学术和学理的层面做个案研究”,是其“最具学术和学理功力的一部专著”。(注:丁帆《“与人驳难”的批评姿态》,《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虽有否定性意见,却是学术姿态的学术观点。一类是文化批评,如王朔的《我看鲁迅》,(注:《收获》2000年第3期。)它在精神上与世纪之交的“酷评”是同一潮流(且是这一文化潮流中的高音),但却是非文学问题的文化思想批评。它违背了一般的文学常识。
“酷评”最有代表性的文本,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书是《十作家批判书》,(注: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文章是葛红兵先生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写一份悼词》。(注: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坛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之所以选这两个文本做代表,一是出于我对酷评的理解,它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二是从社会的、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它们也较广泛地引起了注意和批评。
三、酷评家
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批评家自诩为“酷评家”,这大约说明了“酷评”尽管很“酷”,却并非有好的名声,对酷评的批评也限于具体的“酷评”文章,或笼统的“酷评”现象。这当然显示了批评的成熟,是为了讨论问题,而非讨论作者的名义。同时,也显现了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宽厚与宽容(一度在政治批判运动中的粗暴指名不在其中)——与“酷评”立场正好相反。
对“酷评家”,曾有一种误解。将严厉的批评家称为理想的“酷评家”,如“别林斯基就曾是俄罗斯文坛的一个‘酷评家’”。汤奇云先生称其是一种“心目中的酷评家”,还把中国的鲁迅,还有茅盾这样的批评家,也列于其中。这位作者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认为“话语尖刻,立场偏激,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酷评家。这种人与愚昧而缺乏修养的骂街的泼妇没有两样”。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是用褒义的内涵使用的。(注:汤奇云《“酷评家”:批评界的谬种》,《文论报》2001年2月15日。)我对这样为“酷评”之名翻案的意见深不以为然。“酷评家”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酷评”现象,已使真正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文学批评蒙羞获耻。在一些“酷评”中,鲁迅已被彻底否定了。把“酷评”当成了褒语,将“酷评家”作为心目中伟大、杰出的标准,不但不能划清严肃批评和“酷评”的界限,反而有损于伟大、杰出批评家的声望。不但没有积极意义,相反,还有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具体说到中国“酷评家”时,有这样几个例子。代迅先生提到,余杰强迫余秋雨忏悔是一例,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坛写“悼词”又是一例。(注:代迅《关于“酷评”:以余秋雨现象为例》,《文艺评论》2001年第2期。)客木先生在《“骂派”批评家档案》中提到了八位,既有大陆的,又有台湾的,既有文学批评的,也有文化批评的。(注:客木《“骂派”批评家档案》,《作品与争鸣》2001第3期。)李运抟先生在《关于“骂派批评”的新思考》中,则提到王朔讨伐金庸,朱大可等人的《十作家批判书》,还有韩石山,余杰、王彬彬等。(注:李运抟《关于“骂派批评”的新思考》,《芳草》2000年第10期。)显然,“骂派”批评在使用上,是被有些论者看作与“酷评”同一语义的。
我以为“骂派”与“酷评”还是有区别的。至少,我认为应当加以区别。正如李运抟所论:“对于‘骂派批评’决不能一概排斥和贬低”,而应看作“是一种非常复杂和含义丰富的批评现象”,“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李运抟《关于“骂派批评”的新思考》,《芳草》2000年第10期。)我本人是不认同将对作家作品的否定性意见,概括地称为“骂派批评”的。因为它掩盖了同是否定性批评的许多文章的本质差异。同是否定性批评,有的是对局部的否定,有的是对整体的否定;有的是学术性的,有的是商业性的;有的是理性的,有的是谩骂的。决不应该一概而论。有一种意见,将“酷评”扩大为或者还原为否定性批评,将一切具有否定性意见的批评,称为“酷评”。这不利于否定性批评——文学批评中必要的调节——的存在。我们应当容许否定性批评,前提它应当是学术的说理的,而不是漫画的、非理的。所以,我们应该态度鲜明地反对“酷评”,而容许学术上的否定意见。这样,我们也许可以达到具体分析和判断的目的,而不是简单化地对待一切具有否定性意见的观点。
四、酷评的特征
《十作家批判书》批评了十位作家,这里以最具有代表性的第二篇文章为例子,加以分析。朱大可先生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注: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第27-2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是特别具有漫画化的“酷评”代表作之一,将余秋雨的散文视为“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他解释了其作品的流行,在于其市场化和大众化的口味,这种流行的唯一(也不容其他读者作其他想法)原因是“媚俗”,而“媚俗”则必然是放弃乃至放逐“精英”的思考,被大众所支配。余秋雨的“渗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的‘爱国主义’(在朱文章中看作是‘民族主义’),是“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而余文的某些在朱大可看来的“失当”,乃至过失,严重问题,用朱大可的“全球化”的“世界主义”的标准(在读该文后,我感到朱先生所使用的是另外一种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对应的而未明言的标准)加以对照,便大错特错了。此外,余秋雨散文中有“嫣然一笑”,也被认为是问题,经过提炼——未经过学理分析的提炼,形成了如下方式:笑——煽情——软体哲学,从而使余作品的错误铸成。显然,朱大可先生既使用了漫画和丑化,还另外确立了自己的标准,在得出结论时,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过程,没有遵守普遍适用的逻辑规则。
葛红兵的《悼词》,在全面否定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时候,采用的是先对作家进行人格贬低,从而否定作品的姿态和方法。他不是根据确凿的事实直接分析,而是以不确定的材料(许多事实不存在,参见秦弓先生文(注:秦弓《学术批评要有历史主义态度》,《人民政协报》2000年1月4日。)),对作家人格进行轻蔑的贴标签。谈到作品,同样脱离历史,以个人的偏嗜的狭隘趣味和抽象理念做标准,不合自己趣味者,便贴上涩、枯、嫩、粗、俗、直的标签。
对葛红兵的《悼词》,秦弓、陈漱渝等评论家先后柞了深入分析,以事实、义理作了有力的回应和驳斥。(注:陈漱渝《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对朱大可等的《十作家批判书》,许多作家、评论家也纷纷回应,指斥其商业化、非学术化等倾向。
总结《悼词》和《十作家批判书》,它具有“酷评”的几个极为突出的特征:
一、绝对否定的单一判定。酷评者自认为真理在握,便可以高于其他作家、评论家,不顾具体事实和逻辑,随意地批评与贬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彻底否定,就反映了这种绝对思维中的极端心理。这种思维方式,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采用了非历史化的主观臆测,把复杂、严肃的学术活动,简化为标签式的随意粘贴,是对作家的不尊重,也是对学术的不尊重,极大地破坏了学术的规则,败坏了学术的声誉。
二、谩骂式的丑化论敌。“酷评”采取了谩骂式、漫画式的夸张方式丑化论敌,借以达,到“骂”声夺人的非常气势,这也是被有些人称为“泼妇骂街”的根本原因。(注:汤奇云《“酷评家”:批评界的谬种》,《文论报》2001年2月15日。)谩骂不是学术论战。不可能解决学术问题。学术论战不是古战场上的肉搏,只有你死我活。学术应当是文明、文化的积累,不同观点的同存,丰富了人们的认识角度,也是发展学术的正常之路。即使是可能错误的观点,也是骂不倒的。况且,对一种学术观点,文艺现象的判定,从来不可能由哪一个人(或集团)专门说了算。历史已经证明,即便是通过政治的、法律的、甚至暴力的方式,也无法对一种学术观点做出最后判决。历史是无情的。
三、追求时尚的商业动机。“酷评”的时尚化、商业化,在于其炫耀化、包装化以及通过尖厉的声音,吸引读者,以用较短的时间获得更多的注意力,这是不讲学术道德的。不考虑是否对学术发展有利,对贬低的对象是否尊重,只考虑“酷评”者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
四、偏离学术的非理倾向。学术是理论建设,需要以理服人,以实在的材料作证明,以合乎逻辑的推理达到比较坚实的结论。情绪化、随感化,情绪过度扩张,失去冷静理性,偏激的结论,没有稳定的事实做依据,没有合于学术的规则做推导,这只能是一顶不合适的帽子,是一幅变形扭曲的失真的画像。私下里做个游戏节目自娱,倒没有社会公害(也不值得提倡),作为学术成果,就立不住脚了。甚至会违背自己善良的学术愿望,达不到学术建设的目的,淹没那些可能包含正确意义的命题。
我们把具有这些基本特征的文学批评称为“酷评”。这里的几个要素是:一、是学术问题。尽管采用了非学术的做法,讨论的却是学术问题,使用的是学术语言。而背离了常识,便已不是学术问题。二、绝对化的思维,背离学术方法的彻底否定批评对象,不讲学理的彻底否定。学术讨论并非不可以得出否定性的意见,同样对于余秋雨,我认为有些否定性的批评意见(尽管我并不是无保留的接受),是学术性的,便不是酷评。但非学术性的不讲逻辑,不讲学理的否定,则是酷评。三、是在否定批评时为商业效果而丑化对象,作为时尚化,以偏执的结论或惊世的题目而引人注意,以求一鸣惊人,成为追求时尚的学术商人(获取的不是有价值的成果,而是泡沫式的学术名声)。
五、酷评与时尚
“酷评”的“酷”,与社会时尚之“酷”,是有着同为文化现象的联系,又有着文学批评之“酷”与社会时尚之“酷”的区别。
按包铭新《时髦辞典》中对“酷”的定义,它是英文单词(cool)的汉语音译,是在1997、1998年以后中国都市人(特别是白领阶层)时髦的一种时尚,指衣着、举止、形象、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前卫意味的时髦。(注:包铭新《时髦辞典》第4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青春男女之“酷”,还带有反抗压抑的青春文化,试图摆脱社会秩序的羁绊时的一种激荡,以所谓的格格不入和特立独行来凸显自我价值,显示出年轻人渴望挣脱成人的文化脚镣的心理,还可以将它理解成是一种文化的作秀乃至于文化的造作,还有一点商业集团的小小把戏。(注:王唯名《游戏的城市》第109~11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社会时尚的特点,具有商业化、反抗化、炫耀化的特征。在这些方面,也都为文学的“酷评”所收纳。所不同的是:其一,社会时尚之“酷”已不再与残酷、严酷、酷爱联系在一起,虽然它们之间仍残留着一些若有若无的残余,而文学批评之“酷”,则给人以棍棒,横扫、打倒在地的冷面;其二,时尚之“酷”,突出的在于,时尚者个人的推销与展示,通常则不需要以毁损他人来显示自己的特异与突出,而批评之“酷”则紧紧地与批评的对象(乃至形成大批判的声势)联系在一起,不显示批评对象之狰狞、卑劣,则无法显示自己论点的峥嵘、高明。
“酷评”之“酷”既有其时尚性的一面,即力求通过商业化的造声势,显示作者的存在,引起大众的主意。也有其非时尚性,真正带有严酷、冷酷乃至残酷的一面,这正是使“酷评”在文坛上的称谓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酷评”即是冷酷之评、严酷之评。这也可以推断为无一个评论家自称酷评家的原因。“酷评家”是一种给正常的正当的研究对象——作家作品蒙上耻辱而使自己获耻的一个称号。它并不是一个好名声。酷评者虽然可以在很短时间便让人们记住了他的面貌,却也污染了空气,破坏了规则,也败坏了自己的形象。以一时之“勇”,赢一时之名,得一世之误,换来的将是历史之失、长久之痛,总的说,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酷评”的批评,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帮助“酷评”者,也是告诫未来的批评家,以免再误入“酷评”歧途。
六、“酷评”的双面刃
“酷评”确实给文坛带来了一定的轰动,商业化效果不能说不显著。
“酷评”出现后所形成的结果是:一、“酷评”现象为人们所注意,所换来的是大多数公开的否定的指责,批评其主要的毛病在于违背文学批评作为学术活动的严肃性、科学性,没有求实精神与良好学风,得出的尖刻结论更是难以服人。二、对“酷评”的批评,作家、评论家则显示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对其给以充分的宽容,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其明显的偏颇和极端。(注:参见白烨等《〈十作家批判书〉的是耶?非耶?》,《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24日;王安忆等:《批评,有话好好说》,《文汇报》1999年12月11日。)这种矛盾心态影响了对“酷评”现象的深入剖析与严肃地批评。作家、评论家们的矛盾心态,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其一,长久以来,批评中的吹捧强风扶摇直上,吹得作者、读者晕晕乎乎的,使得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大为降低。人们希望有一定震动力的尖锐的批评,改变文坛的沉闷之气。其二,对批评者批评权利的尊重,珍惜来之不易的较为自由的批评环境。在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奉行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尊重你表达意见的权力。其三,在对商业化炒作表示反感的同时,却承认批评商业化的成功所带来的轰动效果。以商业成功当作批评成果传播的有效手段。其四,透过“酷评”中非学术化倾向与非科学性的论证与结论,看到有的“酷评”文章中有时包含某些局部的、合理性的内容。其五,低估了“酷评”败坏文学批评风气的破坏性影响,也同时丧失了通过对“酷评”的讨论,建立文学批评科学性原则的有利时机,“酷评”文本,是不良学风的典型标本,深入地剖析和评判,有利于真正的良好文学批评的大好局面的建设。
实际上,有些界线是明确的。其一,无理性的“尖刻”并非是尖锐。用“骂”之恶,并无法从根本上驱赶“捧”之恶。况且,从思维方式上,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是同出一辙的。其二,尊重批评者的权力,并非意味着不尊重被批评者。“酷评”者在骨子里,缺乏对文学和作家以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批评家的尊重。其三,商业成功,不是批评成果评价的尺度。其四,合理的内容、命题,用非学术化的方式表达,不仅无法产生以理服人的自然、正常效果,反而在丑化他人时,败坏了自身的声誉,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水平。其五,“酷评”的破坏性,难以改变文学批评的不良环境,反而使批评环境、学术环境更加恶化,从而消解了整个学术的健康风气。
世纪之交的“酷评”现象已成为历史。但是如果不正视这一段历史、不总结这一段历史,分析“酷评”的失当,“酷评”——许多严肃学者所不齿的“酷评”,还可能重新出现。
“酷评”的双刃,一面对着批评对象,另一面对着批评规范。“酷评”的失当,使人们明确,正确的命题、观点,如果不能用严肃的学术理性来分析、表述,偏狭的夸张,失度的结论,不仅无法解决学术问题,还败坏了学术空气、学风。
七、“酷评”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酷评”出现于90年代中后期的世纪之交,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酷评”现象便形成了。
在20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的思想文化潮流中,现代迷信已被视为一种消极的历史惯性,社会民主法制的进程,使思想者、文化人既获得了批评的权利,也具有了批评的勇气。鲁迅和所有的名人都是可以批评的。(但是反对神化并非意味着可以任意丑化,不讲事实的哗众取宠)在消解神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丑化的倾向。
“文革”结束以后,人民从林彪、江青这些政治家、阴谋家的谎言中感受到了理想被愚弄的痛楚,同时,有些在总结十年浩劫形成的原因时,把责任也算在笼统的历史传统上,产生了不分清红皂白,全部否定文化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潮流。与此同时,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接纳吸收了西方文化。在有些人那里变成了以西方文化的某一种尺度(实质上,西方文化也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具有多种内涵的)为标准的盲目接受,从而否定一切中国文化。
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改变着许多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界、学术界也出现了追求商品化,放弃学术化的不良风气。学术粗鄙化,学术成果泡沫化,和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融为一个潮流,便出现了学术成果商品化的“酷评”现象。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酷评”是自然的。能否深刻地认识它,评价它,也成为文学批评总结自身的一个重要问题。
激进主义的思想文化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形成了一股激进主义的潮流,它以全盘反传统为根本特征,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具有极端主义的态度与立场,有人甚至将其上溯到近代、现代,乃至“文革”期间,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中出现并一直延伸到当代的,一个十分触目的现象。(注:参见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第五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还有学者林毓生、余英时、俞吾金的相关论述。)这种激进思想文化,对文学界有若干影响。“酷评”持有的许多观念,与其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学术制度中的若干弊端。在80、90年代的学术制度中,过多地倚重“权威”——成名专家意见,而在很大程度上,轻视年轻学者的情况,应当说并不鲜见。如何评价学术成果,人们有时会依靠专门的研究者,这是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在学术发展中分工越来越细,又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的状况下,有时专家也未必一定会得出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专业以外或相关专业较远的专家来做出评价,而又缺少学术上的完善制度相制约时,专家的道德水平、个人偏好、思维习惯、视野范围、科学观念等,都将可能否定年轻的非知名学者的新鲜意见。而采用激烈的情绪化态度,以偏颇的结论显示自己的声音,也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富有反叛精神、而又不甘寂寞的年轻学者的便捷方法。
学术研究的不规范。学术规范至少包括科学精神、求实态度、严谨论证、情绪节制等方面。而不能将未经深入思考、严密论证的随意性感受,夸大其辞地加以表达。学术评价中过分要求学术成果的表达以数量(或篇数或字数)为单位,必然促使学术成果的泡沫化,助长浮躁、轻率的学风,改变学术论文踏实、严肃的方向。耐不住寂寞,急于表达,不讲规范,缺少制约,还缺少对违背学术道德现象的批评。不良的学术生产环境,会酿出非学术的恶果,而恶果又会进一步恶化学术环境。
八、“酷评”的启示
我对“酷评”的看法,是基本否定。我否定、批评的是“酷评”的态度、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在批评中得出否定性的结论。这个前提,便是依照学术规范,进行理性的,而不是随感的,严肃的而不是浮躁的,是学术文明语言,而不是冷嘲热讽、夸大其辞,是尊重文化,而不是毁灭文化。
“酷评”的作者大多是青年(以我的揣测,还有一些也许是青年的延伸——年轻)。我对“酷评”的做法感到不满,但对酷评者的失足而痛心、惋惜。
“酷评”现象的出现,启示批评界、学术界,应迫切改进几个方面,建立科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创新不能背离科学精神和严肃态度。学术规范,即便是令人枯燥的,也应是严格把握的,应该纳入学校的教育内容。
在学术研究中,完善的学术制度,对中青年作者的成长、创新,予以一定的优惠条件,使他们不必通过非常的手段,便可以脱颖而出。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不因商业化冲击而动摇,不以成果的反响作为评价标准。而以学术成果在学术进展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为主要标准。
采取严谨的学术态度。学术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学者的精神状态。有理也要讲理,争论不是争吵。更不应该骂人、丑化人。不能尊重论敌,也不可能获得学术界的尊重、弘扬严肃的学术精神。学术活动不是以捷径捞取声名的职业。文风可以活泼,却不应该是做戏、作秀。既要在事实方面讲究客观性,也要在材料和结论之间讲究逻辑性。一个严谨的结论未必就是肯定性的结论。不论肯定还是否定,都应讲究学术规范以理服人,平等讨论。
“酷评”已败坏了文学批评的学术声誉,具有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如果放任其存在,不指出其危害性,不仅难以建立严肃、科学的学术规范,而且会使后来的年轻学者继续将其作为成名的捷径。我认为,应该把“酷评”(而不是酷评者)钉在耻辱柱上。“酷评”对于生产者来说,是一种方法的失当,理性的失落,情绪的失控,结论的失真。“酷评”在短期内获取了超常的声名,却也同时赢得了失足的恶名;是永远无法洗刷得了无痕迹的。这对于后来的年轻学人的得与失,是应当三思的。
标签:文学批评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朱大可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