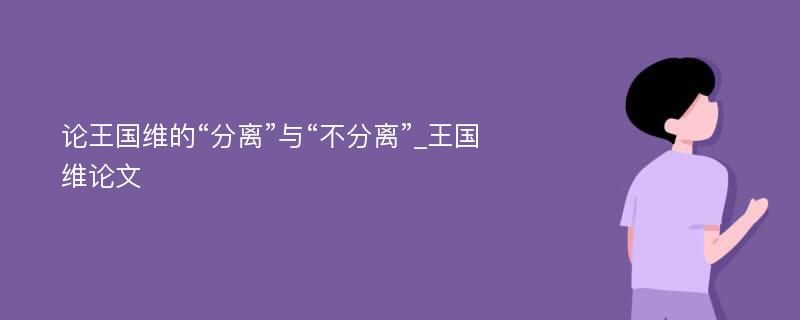
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之前,虽然在文学批评中可以见到“隔”字,但还不是文学批评的术语,如《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1](P494)之“隔”是一般意义上的“隔”,《二十四诗品》的“晴雪满汀,隔溪渔舟”[2](P7286)反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种诗境。袁宗道在《论文》中所讲的“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辗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3](P4)这里的“隔”亦未可看作理论术语,但它把从孔子到东坡的“辞达”说联系起来,已有王国维所论之意。
“隔”在佛经中较常见,如“情生智隔”,(注:可参看(唐)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文见台湾版《大正藏》第三十五册。)佛学追求“智”,故不使“情生”才可使“智”“不隔”。追求“不隔”的诗境是中国文论传统,虽然很少有具体的“隔”与“不隔”之概念上的使用,但诗论中不乏如王国维描述“不隔”的理想,如梅尧臣云:“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4](P10391),近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诸法俱备,无妙不臻,写景则如在目前,叙事则节次分明。”[5](P256)都可以说是王国维“不隔”论的先声。王夫之的“现量”说实际上便是追求的“不隔”之境界,“现量”亦本于佛语,王夫之《相宗络索》“三量”条:“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6](P238)王国维之“隔”与“不隔”虽然可以说本于中国诗学传统,但作为文学理论术语,则是他“新创”之“学语”。
一、审美直觉
不论是要求文学有“境界”,还是要求诗人怀有“赤子之心”,有一个问题渐渐表明了,那就是贯穿《人间词话》的一条主线实质上是直觉论。
直觉是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一种方式,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以及以后的黑格尔、谢林、斯宾诺莎等,尽管突出强调理性关于获得知识的作用,但并不否认人可以通过直觉获得知识,而柏拉图、康德、克罗齐等在审美领域的直觉论者,当然也承认理性分析是获得知识的手段。直觉论者和直觉主义者是不同的,博格森是直觉主义者,他认为直觉可以深入到事物内部,而分析只限于表面现象,因而见不到事物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在于“绵延”,只有通过直觉才可以把握,而分析则从时空入手,隔绝了“绵延”,所以只能停留在表面上,现象主义把直觉当作检验知识的最后标准。这些都把直觉推向了极端。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在西方这条线继承的是柏拉图、康德和叔本华的直觉理论,在艺术问题上,他主张直觉的体验。
由于王国维使用的概念有观、直观、直觉等,并且现代文艺学领域也常常把这些概念相混淆,我认为有必要梳理一番。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对直觉的语源进行了分析,他说:
夫intuition者,谓吾心直觉五官之感觉,故听、嗅、尝、触,苟于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皆谓之intuition,不独目之所观而已。……则但谓之观,亦有未妥。然在原语,亦有此病,不独译语而。intuition之语源出于拉丁之in及tuitus二语。tuitus者,观之意味也。盖观之作用,于五宫中为最要,故悉取由他官之知觉,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7](P532)
在当时,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大批涌入汉语,出现不贴切的翻译是难免的,王国维所使用的直观和直觉都是指intuition而言的。直觉在西语中指两个方面,一是动词intuit,它指动态的,是直觉过程;另一是名词intuition,它又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动词的名词化,即抽象化的直觉过程,另一方面又可以指通过直觉在人脑海里形成的直觉物,直观则是指知觉和直觉的结合,在英语中用perceptual intuition表示,而康德和叔本华却使用了德语中所特有的一个概念Anschauung,现在通译作“直观”,这个德语词的动词词形为Anschauen,它是可分动词,an是介词(相当英语中的at),schauen是“看”(与英语的show同根),因此动词anschauen译成英语应是look at,名词Anschauung在英语中没有由构词而形成的单词可与之对应,只有用intuition来表示,在这里,直觉和直观是交替出现的。Anschauung在康德、叔本华以后由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继承,形成以直觉(intuition)理论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体系,因此,可以把康德和叔本华的Anschauung论看作直觉论。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使用频率较高的另一单词是Kontemplation,这个词含有思考的意思,王国维译作静观,现通译作“观审”。似于“凝神观照”,所以,宗白华先生把《判断力批判》中的这个词就译作“观照”,[8](P40)。我认为“观审”是指主体的态度,而直觉是物我关系的中介,只有在观审的条件下,直觉才可能发生。
东方民族比之西方更侧重于直觉知识,传统中国美学把见到美、和宇宙统一视为人生最高境界。宇宙之本质就是老子所讲的道,道是浑然之物,不可名之,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和直觉主义者博格森的“绵延”说很相近,那么如何才能认识道,老子认为只有通过“观”。这“观”便是直觉的认识。观道须涤除玄鉴,即排除一切杂念,“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9](P65)庄子将此发挥为“吾游心于物之初”。[10](P712)因为人和万物在“初”时,与道是浑然一体的,所以,人生中的事物在“游”时必须全部忘却,他又说:“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10](P119)神遇就是直觉活动。至佛教传入中国,“悟”用来补充了“观”的结果。南宗顿悟说在现象上看有点像所谓“灵感”的产生,但从本质上看,它是直觉的结果。王国维在讲文学与哲学的不同时指出:“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7](P649)王国维把直观和顿悟统一起来作为文学与哲学的区分便说明了这一点。
王国维在其历史学、考古学上重视理性分析,在艺术上则强调体验,重视直觉,提倡顿悟,并且从直觉上升到了境界说,这一点和克罗齐是不同的。
康德的直觉论在西方由克罗齐所继承,在东方的继承人是王国维,尽管王国维的活动时期比克罗齐早,但是其美学思想却比克罗齐更为深刻。克罗齐从直觉出发,到直觉而止,虽然他创立了“表现”(Express)之“新学语”,而实际上,他的“表现”还是他的直觉。而王国维从直觉出发,上升到了境界,上升到了艺术美,这与中国重视直觉而不以直觉为目的的传统哲学相关,所以,王国维达到了克罗齐以及近代西方美学家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由于“直觉”认识是一种普遍的认识方式,因此,我们把人在审美活动中的直觉活动称之为审美直觉。审美直觉是审美感受的条件,并贯穿美感始终。其特点表现为:第一,审美直觉是纯粹的,不借任何概念的,没有任何标准,任何联系,在这过程中,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第二,审美直觉的目的不是直觉物,而是美本身。第三,审美直觉过程必须伴有快感,否则就不是审美直觉,王国维指出:“独类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于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11](P251)
王国维把直觉认识和借助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对立,并且认为直觉感受高于概念分析,他说:“故直观可名为第一观念,而概念可名为第二观念,而书籍之为物,但供给第二种之观念,苟不直观一物,而但知其概念,不过得大概之知识;若欲深知一物及其关系,必直观之后可,决非言语之所能为力也。”[7](P407)所以直觉之知识高于概念知识,那么在审美领域之内,审美直觉也自然高于审美判断,如果人从艺术中得到了“美”而不是直觉到的,那么这“美”一定是人的概念判断的产物。进一步说,这并不是美,而只是第二形式之美,即“古雅”,它由概念而得到,它比通过审美直觉所达到的美低一层。
审美直觉的对象不仅仅限于艺术,对自然的观照更多的是审美直觉,自然美便是通过审美直觉而达到的。因为王国维以直觉论来研究美,那么美的对立面就不再是“丑”了,美是通过审美直觉在瞬时占据并充满了人的意识的审美形式,其结果是使人摆脱了意志,达到物我的和谐统一。就“美”作为一种存在而言,美是有对立面的,如淫诗、鄙词,“玉体横陈”的美女图等,但是这些并不是丑,叔本华称之为“媚美”(Reizende),王国维译之为“眩惑”。而“丑”属于概念范畴,应和“古雅”相对而言。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建立在直觉论上的,在《人间词话》中,他更进一步地把直觉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提出了“隔”与“不隔”的批评标准。
二、隔与不隔
“隔”与“不隔”的提出,是王国维直觉论在文论实践中产生的结果,这对概念是其文论体系的重要范畴。
当代学术界在王国维文论思想的研究方面也有许多文章论述到这一对范畴,然而看法却很不一致,褒贬不一。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对“不隔”持肯定态度,对王国维的“隔”论(并不是“隔”本身)持否定态度,甚至主张对“隔”都须具体分析。朱光潜从诗的“隐与显”的相对性出发,批判了王国维对“隔”的贬斥态度。”[12](P56-61),这一点叶嘉莹先生已对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用“隐”与“显”来套“隔”与“不隔”是不妥当的。[13](P248-261)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支持“隔”与“不隔”的分界和批评标准,认为“不隔”是“有形象、生活的真实才能以即目可见具体可感的形态直接展示在人们前面,使‘语语都在目前’。”[14](P162)就研究者对“隔”与“不隔”的理解来看,有人则将之局限在语言表达上来研究,如叶朗先生说:“从王国维自己的话来看,‘隔’与‘不隔’的区别,并不是从‘意象’(朱先生说的‘意象’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表象——原注)与情趣的关系上见出,而是从语言与意象的关系上见出。”[15](P619)这是有道理的,但又是不全面的。因为“词以境界为最上”,诗词的创作实际上就是美的创造,对于自然美,人必须通过直觉才可以把握,对于艺术美也同样如此。我在讨论王国维的“写境”与“造境”时已指出,诗人的创作首先是诗人的感受在促使人去创作,这感受就是对“美”的感受,那么把引起诗人审美感受的美“镌之于不朽之文字”便是诗歌艺术的创作目的”[16](P14-16)。诗歌创作也就是对美的摹写,如果诗人在创作前没有与自然通过审美直觉而和谐地统一起来,那么,他的作品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受,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就不存在境界。另外一种情况,即诗人对自然之美已深切地感受到了,然而他在创作时却“文不逮意”,用词不当,因而其作品到读者那里,读者不能直觉其境界,这两种情况在以直觉论为前提理论系统中都被称作“隔”。
什么是“不隔”呢?王国维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17](P68)只有“语语都在目前”,人才可以通过直觉来把握它,如果不在“目前”,就得用“目”去搜索,经过“目”的搜索,这语语才进入了人的意识,这是一个渐近过程,在人的意识中“语语”不是“瞬时”占据人的意识的,因此,不是“须臾之物”,也就与“境界”无缘了,也就“隔”了,“语语都在目前”的意义在于,通过语言所组成画面不需要更多理性分析,这“语语”形成的画面是人的直觉对象,从语言到意象到美的过程是瞬时的,只有如此,诗才在“不隔”。
诗的创作,首先关系到诗人的感悟能力,诗人须得有一颗无尘垢的赤子之心,这样,通过直觉他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本质,王国维评美成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云:“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17](P22)评稼轩词:“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说:“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事,与科学上密合,可谓神悟。”[17](P55)即使是“造境”,诗人对自己脑海里的意象也必须通过直觉来把握,如此,其所造之境与所写之境在读者那里是分辨不出的。如果诗人对眼前的景象不是通过纯粹的审美直觉来把握的话,那么,他的写境实际上等同于造境。所以“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17](P28)
其次,诗的创作还关系到诗人的表达能力,也就是他能否使文辞达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提出要少用替代字,如桃用红雨、刘郎,柳用章台、灞岸所替代,“宜其为《提要》所讥也”。[17](P11)这原因是:“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17](P10)这说明诗人直觉感受能力是一个方面,表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代字能够影响读者的直觉感受,代字代的是什么,这就使直觉渗入杂念,因此,诗也就“隔”了。
欲达不隔,在写情方面,必须写出真情实感,甚至于像“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样的诗,因为其真,虽淫也能使“读之者但觉其沈挚动人。”[17](P102)
在写景方面,要自然,王国维说:“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7](P537)这话说得似乎有点太过分了,不过王国维确实崇尚自然美,而对自然美的描绘就必须“自然地”去描绘,他之所以推崇纳兰性德是因其“以自然之眼观物”。因此,其写景必自然,甚至写情也要“以自然之舌言情”。
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41则中说: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17](P72)
当然,情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就表现的境界来看,不论描写什么都须真、须自然。
王国维反对使用代字,但不反对用典和拟人,如他称“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17](P68)这里明显是大量用典。这说明借古人之境界只要借得恰到好处,也可以不隔的,这和皎然“用事”论相似,但那些为用典而用典、以用典来显示学问的当然要反对了。王国维把姜白石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17](P67)有人据此认为王国维反对拟人,其实不然,如王国维所赞赏并用来说明境界的两句诗“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闹”字和“弄”字的使用都可以说是一种拟人手法,他之所以认为白石上面几句“隔”是因为这几句诗给人一种景象模糊,不得要领的感觉,也许是因为诗人没有通过审美直觉与黄昏雨中的山峰、西风中的寒蝉达成统一。
“隔”与“不隔”虽然涉及到读者,但这依然是美的创造问题,而不是接受美学所面对的文本问题,因为王国维并没有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A是隔的作品会不会对B来说不隔呢?或者今天读者感到隔而明天读就会不隔了呢?所以“隔”与“不隔”的研究仍然是关系到诗人的修养的。除了诗人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来体验宇宙人生、以自然之舌来言之外,还要求诗人尽可能运用简洁的语言来描绘自然美。王国维强调太白以气象胜时的“寥寥八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另外在第34则说:“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东坡所讥的是“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王国维要求“不用装饰之字”。[17](P40)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隔”与“不隔”不一定对诗词作总体评价,可以以一句为单位,上句“不隔”则可能下句就“隔”了,如第40则他说:
……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17](P68)
所以,姜白石也是有的诗“隔”,有的诗“不隔”。“隔”与“不隔”也不是截然两分的,有“隔”和“不隔”,还有“稍隔”,同时“不隔”处还有“深浅厚薄之别”。[17](P68)
一般说来,人能够通过审美直觉感受到美,便是“不隔”,否则就“隔”。“稍隔”如何存在呢?这一点我认为是限于艺术作品而言的。诗人的创作过程是否有理性在起作用,王国维没回答,我认为是有的,诗人感受到自然美是直觉的,“不涉理路”的,读者欣赏作品也是直觉的,但是,读者的直觉对象和诗人的直觉对象是不同的,诗人的直觉对象是自然美,所以不借助概念,而读者直觉到的境界并不像自然物一样,直接呈现给读者的直觉认识,而是隐含在作品中,从表面上看,这作品只是文字符号,文字符号转化为境界需要一个过程,即:由文字符号转化为概念,由概念在人意识中组合成“意象”,这意象还只是审美形式,只有当它和人的心理结构相吻合时,渎者才达到境界。诗人在感受到美以后,必须借助概念才能把诗人所直觉到的美转化为作品,而这概念在读者接受时,又必须融消在意象中,正所谓“得象而忘言”,如果诗人在把自然美转化为作品时,其所用以表达美的语言文字影响到了读者的直觉感受,这影响的程度就会显出差别,因而才有“隔”、“稍隔”和“不隔”之别。
总之,“隔”与“不隔”的概念是针对人的审美直觉的程度而设立的,在美的艺术中起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