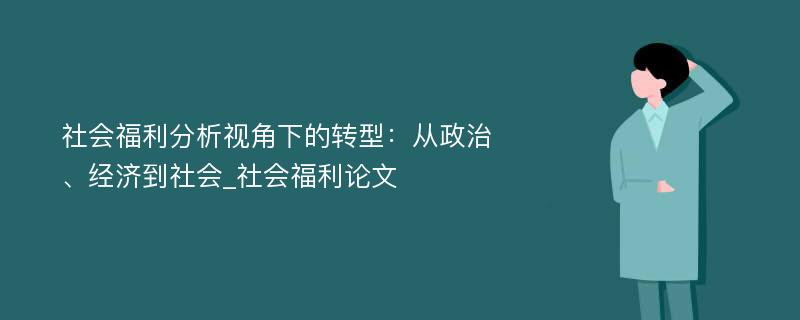
社会福利分析视角的转型:——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视角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为消除社会贫困,保障公民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增强个人幸福感与满意度,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了社会福利政策,二战以后,社会福利制度逐渐成为这些国家一种独特的政治纲领、经济政策与社会设置,并成为社会学家们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1958年,美国学者Wilensky和Lebeaux提出了“补缺型福利”(the residualwel fare)以及“制度型福利”(the institutional welfare)两种模式,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得家庭和市场无法为个人提供满足其自身需要的福利,需要国家的社会福利机构提供制度化的补充,这是公民自我权益的体现,也是工业社会使然。1974年,英国学者蒂特姆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工业成就型福利”(the industrial achievement-performance),认为社会福利的供给不仅要考虑到公民权利,同时也要兼顾“生产力情况”以及“个人的工作表现”,从而使得福利供给增添了效益因素。1985年,英国学者George Victor和Paul Wilding指出,社会福利的供求受到了“集体主义、反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1990年丹麦学者埃斯平2安德森以福利提供“去商品化程度”为视角把当代主要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类型(埃斯平·安德森,2004:32-45),实质上就是从经济(商品化、工作义务)与政治(公民福利权利)视角去总结社会福利类型的。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我国从单位制福利向社会制福利转变,不少学者从经济视角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后来则有学者综合了政治、经济分析视角,如王延中、郑秉文等提出“全面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命题,认为社会福利应以政府为主导,贯彻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福利的供给要能够促进就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9:26)。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福利与社会的关系。周沛等人试图从社会体系角度分析社会福利,认为它包括“政策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网络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以及“公共福利”等方面(周沛,2007)。还有一些学者从“需要”出发去理解社会福利,把社会福利当成“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的所有面向全体公民整合社会资源的制度、规章或服务”,强调福利不仅涉及行动者、市场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涉及与社会的关系(马广海,2008)。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仅仅零星地触及社会福利的社会分析视角。为此景天魁提出,社会福利与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社会运动、社区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关系十分密切,必须深化这个视角,否则必将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福利(景天魁,2009:21)。本文则在总结社会福利的政治、经济分析视角之后重点阐述社会福利的社会分析视角,以期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建设。
一、社会福利分析的政治视角
作为制度的社会福利与政治统治、民众权益密切相关,因此从政治视角出发探讨社会福利建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正义论等社会福利理论派别。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既是工人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资本家用来迷惑工人的一种工具,社会福利的提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所需要的经费直接来源于工人的剩余价值,是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必要扣除,它们不会白白地施舍。20世纪70年代以后,马尔库塞、奥菲等人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社会福利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而不是其“固有属性”,它是“资产阶级控制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以便把整个民众变成缺乏革命性与斗争性的“单向度的人”,资产阶级不可能制定出满足工人阶级需要的社会福利制度,因为这与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理念、经济结构背道而驰,所以资产阶级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避免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功利主义将福利当成一种社会伦理,强调社会福利就是要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人们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边沁认为,人总是按照“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任何行动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我们称之为它的功利”(杰里米·边沁,2000:58-115)。穆勒认为,要想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应当提倡每个人为增加他人幸福、增加社会总体幸福而工作;为此,政府就要进行有限的干预,如开展“救济穷人、初等教育、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等(约翰·穆勒,1991:558),以实现个人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之间的公平发展。功利主义认为,社会福利不仅包含《济贫法》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救济”原则,包含着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消除“贫困、疾病、愚昧、肮脏与懒惰”等五大目标,而且包含着阿玛蒂亚·森所说的一种基本的物质生活、医疗保障等“生存状态”,因为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重要的不是“个人的责任”而是“个人的无力”。所以,社会福利应该成为政府与社会的责任,保证民众“幸福”与“满足”(诺曼·巴里,2005:17)以及对这种幸福和满足的理解、体验与认同,进而对民族国家产生认同。
与功利主义相对应的则是社会福利正义论。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卢梭强调财产权利的获得与保护则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与体现,社会福利的供给不能损害个人财产所有权,它们之间应当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微妙的平衡。康德认为公平正义是道德和法律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是社会福利分配的基本原则,它来源于人的理性自由、行动自由以及政治参与自由;为此就要“按照你认为同时也能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康德,1982:72)。罗尔斯则强调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罗尔斯,1982:66)。在罗尔斯看来,一个残疾人与一个正常人的福利需求应当有所差异,社会就应当针对每个人提供不同的福利。但是诺齐克却认为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是社会而不应该是国家,它是社会为其成员提供合理程度的安排,使他们免受匮乏和暴力,促进公正和基于个人价值的评价系统。费尔莱认为,社会福利主要包括“社会工作、公共福利以及其它相关的行动或计划”(Farley,2000:3),它们强调人们在身体、教育、精神、情感、心理以及经济等诸方面的良好状态。
总之,从意识形态、国家权力、国家责任等角度探讨社会福利构成了社会福利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由此形成了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国家福利模式,强调政府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有限责任,认为国家只能进行有限的社会保护以避免出现社会负效应;也形成了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合作主义等福利模式,认为国家就是要维护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强调个人福利的获得取决于“自身的工作与参保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水平”;同时还形成了以英国、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坚持社会福利的普惠性,认为社会福利主要取决于“公民资格或长期居住资格”,而几乎与个人需求程度或工作表现无关(艾斯平2安德森,2003)。
二、社会福利分析的经济视角
作为一项制度设置的社会福利总是需要特定的公共财政支出,社会福利供求必然要受制于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情况。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福利活动尽管早已有之,但是它更多地表现为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救助对象仅限于鳏、寡、孤、独、废、疾者,救助内容只是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最迫切的疾病医治,而且救助层次较低,有的国家社会福利主要由宗教慈善机构提供,政府在其中的责任极其有限,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公共财政非常匮乏,统治者无法提供那种体现“美好幸福生活”的社会福利。所以,人类早期的社会福利大都坚持私人善行原则,表现为慈善行为。
近代以来,欧美国家日益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匮乏型经济走向丰裕型经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财政的增加使得政府有能力将一部分公共财政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当中,建立健全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切实改善民众生活。同时,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日益面临着自身无法控制的风险因素,产生了贫富分化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制定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健全相关福利设施,对困难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为此,很多国家将社会福利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强调社会福利就是政府对全体民众在收入、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等方面提供的制度性安排,减少民众的不幸福感和不满足感。这样,社会福利就从选择性拓展为普惠性,从剩余性转变为全面性,针对全体国民的各种社会福利设施、社会福利项目以及社会工作服务日益完善,社会福利支出逐渐上涨,有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到整个公共财政支出的2/3以上。当然,也有些国家并没有实行全面、普惠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仅限于对年老、疾病、因生理或心理缺陷而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教育、住房、医疗、司法等方面的救助与服务,进而提高和改善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
从历史上看,福利经济学主要从最大化角度探讨了社会福利供求问题。在旧福利经济学时期,庇古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福利供给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福利所体现出来的幸福满足感就愈高。因此,要增加社会福利就必须设法增大国民收入总量,消除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新福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伯格森以及阿罗等人认为,个人效用水平的高低无法用基数而只能用序数表示。帕累托认为,社会福利总目标应该是个人福利的增加并没有使他人的福利减少。在伯格森看来,这种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要想达到最优状态还必须保证福利在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地配置。20世纪50年代之后,阿罗提出,社会福利函数只有在已知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偏好次序情况下把它们归纳成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确定出最优社会秩序。阿玛蒂亚·森、弗里德曼、奥肯等人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框架,西方国家形成了剩余型、制度型以及工业成就型等社会福利模式,以及福利国家主义、合作主义、社团主义等社会福利模式,强调社会福利可以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会化的福利设施和有关福利津贴,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服务需要并促使其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的一种社会政策”(郑功成,2000:20),也可以指“帮助特殊的社会群体,疗救社会病态而提供的社会服务”(尚晓援,2001)。
三、社会福利分析的社会视角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社会福利的分析视角不同,人们对于社会福利项目与内容的理解存在着诸多差异,并由此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安排与实施。这些分析视角的差异还表明仅仅从经济或政治的视角去研究社会福利还远远不够,因为经济或政治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离开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本身并不存在。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设置与安排应该考虑到这个国家的社会因素。也就是说,必须要拓展社会福利分析视角范围,不能仅仅从“权力结构”、“商品化”等角度去认识社会福利,而要更多地从“分层化”、“去商品化”角度把握处于特定社会之中的福利(艾斯平·安德森,2003),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社会的视角来理解福利就是要把福利当成整个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福利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一方面,福利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内在地包含着“福利”要素,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解决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促进社会结构的和谐。另一方面,社会福利总是针对处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个体或群体而设置的,他们的福利需求种类、层次以及方式也要受到特定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社会福利体现着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心理倾向和政治态度,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运动。它实质上就是政府或社会为满足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而调配经济社会资源、增强社会成员生存能力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设置。这样看来,各种类型与模式的社会福利之所以存在就在于特定的社会福利项目、内容以及实施等都要依据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以及作为一种场域的社会文化。总之,社会是福利赖以生长的土壤,福利的安排与实施必然要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制约。
第二,从社会的视角分析福利就是要探讨与特定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福利项目和内容,分析社会福利制度的安排对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阶层的影响,思考社会福利项目的实施对于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功效,提出经济增长、福利供给以及社会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历史上看,社会福利最初就是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减少社会动荡的面孔出现的。因此,社会福利项目一旦实施势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形式。比如一些不发达国家,很多人往往把生儿育女作为提高自身福利水平、改善自身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多子(女)多福思想根深蒂固。然而如果政府提供良好的社会福利设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强了人们抗击生存风险的能力,那么将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少生优生,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家庭结构由原来的大家庭、联合家庭逐渐向核心家庭转变。这种家庭结构反过来又要求各种社会福利项目责任化、系统化、全面化乃至强制化,否则就会对整个社会结构造成危害。
第三,社会福利塑造着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自己的价值理想。人们制定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实施福利项目主要是解决社会成员的生存能力不足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着原有的社会阶层、社会关系,产生出新的社会力量,使得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福利越来越成为社会成员提高生活水平、提升政治地位、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手段。于是,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社会福利的最高目标,社会福利越来越成为实现人的价值的手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使得整个社会日益形成尊重人权、凸显人的存在价值这个发展目标。
当然,我们坚持社会福利分析的社会视角,不是排斥或否定经济、政治视角,而是要完善分析视角,强调社会视角是政治、经济视角的基础与前提,前者要依赖于后者;我们也不是否定社会福利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可以完全抛弃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基础,而是指出社会福利供求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所以,从社会的视角分析社会福利能够准确地把握福利与社会的逻辑关系,能够很好地解释中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差异,从而为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实践提供指导。由此,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福利体现出以下三点特性:
首先,满足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供给与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从救济型福利逐步走向普惠型福利,从来也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超越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福利政策。当然,中国长期处于经济匮乏型、家庭伦理型、政治权威型的社会之中,它需要我们把社会福利优先确定为民生建设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如“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生活需求、解决看病难以及公共卫生服务的基本健康需求、解决基础教育问题的基本发展需求”等(景天魁,2009)。
其次,体现着文化特性的社会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良好的经济基础、自由的政治意识以及百年来的福利运作实践,社会福利已经日益内化为公民的一种自觉行动以及权利意识,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福利权利,社会福利越来越成为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可是,中国人通常不是从个人权利、意识形态而更多地是从社会文化尤其是家庭伦理角度去理解福利,把社会福利当成是家庭福利无法满足之外的补充,进而把它当成促进社会和谐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要侧重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福利文化去理解和建构社会福利。
再次,个人满足与社会认同相统一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也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范畴。为此,西方国家往往强调福利的“自我幸福感”以及个人的“生活满足感”,而处于中国社会之中的民众还要强调福利供求的“社会认同感”,努力实现“自我幸福感”、“生活满足感”与“社会认同感”的有机统一,实现个体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可能的有机统一。这样,根植于中国社会之中的社会福利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将能够形成自己的运作逻辑,解决自己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