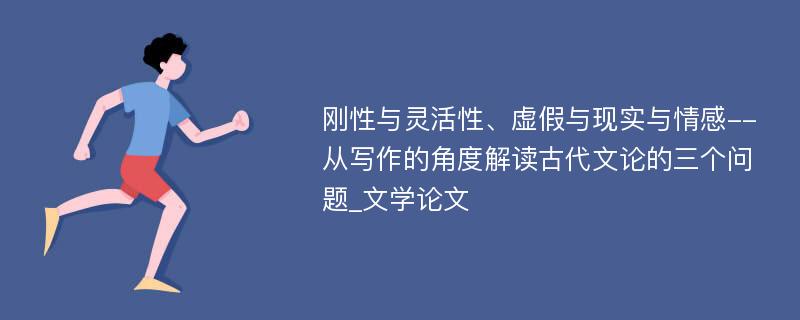
刚柔、虚实和合乎情性——从写作角度理解古代文论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虚实论文,刚柔论文,角度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古代文章学是现AI写作作学的胚胎,而古代文论则是古代文章学的核心内容。从写作风格、表现手法和写作动力等角度对古文论中的基本概念“刚柔”、“虚实”和“情性”进行剖析,以揭示其中包含的写作原理,论述传统文章观的现代意义。
一、刚柔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
——姚鼐:《复鲁絜非书》
据俞文豹《吹剑录》载,苏东坡幕僚对柳永和苏东坡两人的词评价为:“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比喻虽俗,却道出了苏词和柳词一刚一柔的不同风格。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阴阳刚柔的交替是宇宙运行的根本规律,《老子》有“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说法,《易传》则进一步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历代文学理论家认为“民禀天地之灵”,〔1〕“才有庸俊,气有刚柔”,〔2〕人秉承了自然界阴阳交合的元气,所以写出了刚柔相济的文学作品。及至姚鼐的《复鲁絜非书》较详细地阐释了由于刚柔此消彼长、隐显起伏的变化而形成风情万种的文学风格,“刚柔”才作为一个文学风格的概念而定型下来。“阳刚之气”以遒劲、雄浑、豪迈、壮烈、宏毅为主体;“阴柔之美”以温润、清丽、幽雅、寂寥、惋抑为特色。
姚鼐以动态的审美眼光来总观文学风格现象的形成过程,既将自然气象和作者气质、作品风格联系起来研究,又用辩证的观点切入文学风格内部多样化的景观,正确梳理了“刚柔”之间互动互济和各有侧重的关系。他认为即使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也不是阴阳各半,刚柔等分的不偏不倚的作品,而正因为“刚柔”的有所倾斜,文学风格才由固态转变为流动状态,才形成“阳刚”、“阴柔”的不同主流。“阳刚”和“阴柔”是两种最基本的文学风格类型,阳刚之美如雷霆、纯金,如君王、将帅;阴柔之美如晨曦、涧泉,如忧思、轻叹。这两种基本风格的交织变化,组合出“品次亿万”,各禀异彩的文学风貌来。但从“相济”的原则上来说,“刚柔”又不是可以割裂的,至刚至柔或无刚无柔这种孤立的“纯阳”“纯阴”,是阴阳失调刚柔失真的外显,非但不能带来风格的丰富性,反而会造成文坛的单调索漠。姚鼐自己就说过:“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文者矣。”〔3〕
阳气是向上、开放的,阴气是下降、内守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就说过“阳化气,阴成形”。以阳刚为主体的文章可以在从属的“阴柔”掺合下将表面化的激情净滤为内蕴和含蓄,高亢转为沉酣,浓烈转为壮越;以阴柔为主流的文章可以通过潜在的“阳刚”的调和作用,化恬淡沉郁为清朗幽逸,哀惋转为低昂,柔弱转为纤巧。“刚柔”互为节制使文章不至流于“亢阳”与“阴沉”的病态。在刚柔互补中显出主色,使文章风格生动鲜明,加上文章意蕴气势与语言形式的侧阴侧阳、递变交织,又形成或外柔内刚、或辣语柔肠等文学风貌。据此我们认为:(一)刚与柔不是互相对立的状态,纯刚绝柔是对文学风格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会导致风格的单一、文气的衰竭。因为缺乏互动互补,只有恒式没有变式,只能趋向静止和寂灭。(二)刚与柔又不是等分的绝对均衡关系。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它们的相互渗透在具体表现形态中有主次之分,有显隐之别。这种益损、消长的比值不同,产生了文学流派之间的迥异和作家作品之间的微殊,文学风格才得以不断地融化和分解,激活了文学创造的生命力。(三)刚与柔既互补又互律,以防止极端化或互相湮没、阴阳等消、个性的自我失落,所以《易卦·既济》说:“刚柔正而位当”,“济”是刚柔结合的极致。(四)刚柔的变化指向风格的变化,而风格的变化又源自人的个性特征。这就需要从文学本体出发,消解权力话语的干预,用个人话语来建构文学风格理论,对“刚柔”重新命名和定位。“刚”不是政治抒情,而是人性的意气风发;“柔”也不是本我的潜意识扩张,而是自我在现实层面上的解放。对“刚柔”等一系列文学概念和范畴的重新确认,显示出文学主体的精神可以超越世俗的框范而生存,预示着人们心底的人文精神可以在物化的时空中有自己独立的一方净土。正如唐宋时期的文学大师们所倡导的中国“文艺复兴”(古文运动)那样,对人的永恒价值的追求昭然成为文学前行的大旗,故而有“边塞诗”以雄风遗世,“花间词”以温雅流芳,“豪放派”以洒脱呈阳刚,“婉约派”以缠绵显阴柔,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千年”。
杜甫的诗是诗坛上刚柔相济的典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萧瑟与豪迈并存,柔中透刚,以刚健的“峻骨”为主。欧阳修的散文也够得上刚柔结合的代表之作。《秋声赋》肃杀与朗畅齐发。《五代史伶官传序》在委婉简约的叙事中更透出严正清健的说理、见微知著的推论、宏阔锋利的思辩,确是“阳化气,阴成形”的杰作,具有外柔内刚的“绵里针”特色。我们不妨对它作一简略的分析:文章从国家盛衰源于天命还是人事这一矛盾切入,运用沉痛婉折的笔调叙述后唐三代君王的演变,点染得人物言语情状都历历在目,接着引出创业、鼎盛、衰亡的线索,然后突入质问:“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再由质问过渡到精辟的立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欧阳修以不容置辩、刚劲无俦的论说力量对兴亡的规律作出了合乎历史与现实的明确判定。但这种哲理性的判定又不是凭激情的喷射,而是穿插经典论述和前朝史实,做到有理有据,语气上又象《醉翁亭记》多用助词“也”来舒延音调,使行文雄健而不浮躁,徐缓而有力度,可谓刚柔互补的妙用。
“刚柔”作为文学风格的基本理论,启示我们以社会的文化背景、前人的经典文本、个性化的才情气禀来合成文学风格生长的沃土。在强调“刚柔”有主,风格有异彩有棱角的同时,要求“刚柔”互济,写出风格纯和、圆熟的文章。
二、虚实
张青述鲁达被毒,下忽然又撰出一个头陀来,此文章家虚实相间之法也。然却不可便谓鲁达一段是实,头陀一段是虚。何则?盖为鲁达虽实有其人,然传中却不见其事;头陀虽实无其人,然戒刀又实有此物也。须知文到入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联绾激射,正复不定,断非一语所得尽赞耳。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总批
作为一种表现手法,“虚实相生”是文艺创造中另辟一重境界的重要途径。“实”是正面、直接地表现写作对象实际面貌的写法,具有明确、具体、真切的特点;“虚”是回避正面直接表现写作对象,借他人物他事来烘托、衬垫,为表现对象渲染气氛、营造气势,从侧面间接地丰富或强化写作对象,达到避实取虚、以虚指实的艺术效果。“虚写”是“实写”另一角度的生发与点染,具有隐蓄、空灵、活泼的特征。“虚”与“实”的关系是曲指与直指、暗示与敞亮的关系。“实”未必纯是客观的实象,自有它的形神兼备处,只不过它侧重呈示,诉诸直观,用语凝炼显白;“虚”未必都是闲笔,也自含有“真象”的一鳞半爪,只不过它侧重暗寓,借助想象,用语蕴藉。虚实相映,可以带动文章写作手法的灵活变化,意旨容量的丰富广阔,结构线索的跌宕腾挪,因而“虚实”又何止是一种表现技巧,而是深刻关联着作者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造诣。
虚实相生,用之绘画,如笪重光在《画筌》中说的“无画处皆成妙境”;用之作文,则如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的“非实不足以阐发义理,非虚不足以摇曳精神”。《水浒传》二十六回张青述鲁达被毒得救后又撰说头陀一节,可以说是“虚实相间”艺术手法的充分表现。鲁达是小说中多次正面出现的人物,而“被毒”一节却从来没有得到直接描写,只在十六回中被鲁达自己叙述过;头陀也从来没有在书中露面,但戒刀是实实在在的遗物,“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里啸响”。鲁达写实中有一段虚笔,头陀虚写中含几件实物,虚实互相绞结,文章就曲折多变,形神毕备。鲁达绝处逢生的可喜映衬出头陀误食屈死的可悲、张青爱才来迟的可惜;头陀被毒又映示了鲁达粗莽、武松精细,英雄遭际各有不同;“数珠”、“戒刀”是杀人的见证,又是奇人奇物、身具异禀的寄寓。头陀这无名无由之人,却连挽鲁达、扬志,武松、张青四人,萦系景慕与缅怀、豪迈与痛惜等复杂的情思,隐藏着不尽的意蕴,诱发着读者的创造性阅读。这就是哈斯宝所谓的“牵线影动”,脂砚斋称之为“一击两鸣”。
我们可以认为:(一)“实”是通过直接描写,使写作对象具体化定型化,它追求的是作用于“目视”的直觉形象,在艺术创造中着重表现“实象”,使写作的主旨含在“形象之中”;“虚”是通过侧面的点染,使写作对象获得实象之外的另一重含义,使写作对象走向象征化和多义性,它追求的是作用于“神遇”的艺术联想和想象,着重表现“虚境”,使写作主旨藏在“形象之外”。这是虚实的各自差异。(二)“虚”与“实”在曲折性和直接性各有所指的同时,又互相包容、渗透与转化,形成复合的“互指”关系。而这种“互指”的结果,使虚写和实写综合起来的意蕴处于不确定和确定之间,比“虚”或“实”的单纯含义要丰厚得多,从而形成“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意象群。(三)“虚实相生”又成为“意境”的重要构成因素。蒲震元在《中国艺术意境论》中认为完整意境的产生经历了“原象——原象的综合或分解——触发丰富的象外之象等自发或自觉的表象运动过程,亦即从实境到浅层虚境到深层虚境的运动过程”。实质上,意境的产生过程不仅是一个由“实象”逐步虚化的过程,而同样应该是“虚”“实”从表层共存到内层交流再到深层融化,直至消失两者边界的一个不断加强表现力感染力的过程。它一方面与传统文艺批评的“有虚有实”、“尽其灵而足其神”〔4〕相接轨,另一方面又紧紧依附于老子“有无互立”、“大音希声”和王夫之“虚必成实”、“实中有虚”等哲学思想背景。(四)从写作功能看,“虚实相生”在营造意境上固然要求由“有我之境“向”无我之境”〔5〕转化,即从主观之境向客观之境转化。作者的主观情感、 意旨只能通过旁人旁物得到折射,而不能直接出场中断艺术作品自身的发展,这样更具有“艺术真实”的强烈效果;而且在结构上往往明线和暗线交织,使艺术表现不只停留在外部的现实生活空间,而可以激发想象,进入内部的心理空间,从而加强了艺术对心灵表现的力度;在语言上,使语词的多元含义和特定的语境意义相互交叉,拓展了汉族语言的寄寓性和移动性,丰富了汉族母语的表现力。(五)“虚实”这对艺术矛盾的统一,证明了艺术创造中既有象“映衬”这样相辅相成的成功途径,也有象“虚实”这样相反相成的艺术经验。
金圣叹在《水浒传》十二回总批说:“画咸阳宫殿易,画楚人一炬难;画舳舻千里易,画八月潮势难。”认为虚写难于实写。《水浒传》十二回借梁中书及军士呆看、喝彩来侧写杨志与索超比武,五十二回中以罗真人法术高深来暗示公孙胜的本领玄奥,都极尽以虚写实的能事,但这总不及虚实相间那样天衣无缝,所谓“文到妙处,纯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水浒传》二十六回张青述说头陀一节达到了这样的艺术高度,《三国演义》三十八回写刘备三顾茅庐可以与之匹对。毛宗岗在总评中说:“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这一回里孔明不在,但他的茅居、书童、友人、胞弟、岳丈都是真实的“在场”,他们无一不是孔明高标逸韵、雅洁拔俗的气质的“分形”。虽不见孔明,但孔明那遗世独立、志存高远、罗藏万机、胸怀天下的人杰形象已在读者心中成形,运筹帷幄、从容自若、计智百出、豪气纵横的飞扬神采也已在字里行间激荡。虚化的卧龙灵气被实事真人所赋形,而实在的境、物、歌、诗,又在艺术的氛围中提升为孔明的精神。
“虚实相生”是古代文学家留给我们的一条宝贵艺术经验。艺术辩证法继续引领我们探索和总结矛盾中所孕育的艺术规律,不断地发现或创造新型的艺术表现形式。
三、发乎情性
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李贽:《杂述·读律肤说》
许慎《说文》对“情”解作“人之阴气有欲者”,对“性”解作“人之阳气。性,善者也”。《孝经》引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都指出了人具有欲望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李贽提出的“发于情性”即主张文学写作应该从人的本性真情出发,而剔除外加理念和功利的困扰,回归人性的“自然”形态。“发乎情性”的文学观与李贽提倡至纯至真的“童心说”,在理论内核上是一致的。他在《童心说》中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却真人。”可见保持童心,就是文学家始终袒露一颗不被世务沾染的水晶心,也是保持文学是人的感情学,是人的真情学的本真面貌。
在这里,李贽发挥了《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经典意义,构成了“礼义”(精神准则)、“情性”(人的感情、本性)、“自然”(表述形式)三位一体的文学审美观,而“情性”是主轴:(一)以“发乎情性”构成文学本质观。认为情性之外无“礼义”,礼义这一理性规范只有合乎情性的人性要求,从人性出发,才能被人性接纳,情性之外,不能有其他侵害人性的理念干预;情性之外无“自然”,所谓文章的自然,就是人性的本真流露,任何对真情的改变和扭曲,都会丧失文学作品的自然本色,情性之外不能有其他的语言粉饰。情性是“礼义”和“自然”的发源地。(二)以合乎“情性”构成文学形式观。肤浅单薄的文思没有深度,空洞显露的言辞也不会有内涵,这样的作品无情味可言,文学的情味来自厚积薄发的人情人性的自然流露。自然流露就是有真意,去粉饰。过分雕琢或故作高深、拘泥格式,放弃表现真情或张扬虚情而篡改破坏声律,都会导致文学的卑琐低俗与装腔作势,沦为“诗奴”或“诗魔”。自然流露还指不着斧痕,形式如童心一般纯粹、透明,这种透明不是低浅,而恰恰是一种情感体验的深湛,是“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是“文”与“情性”的和谐一致,文如其人的融合统一,所以“旷达者自然浩荡”,“沉郁者自然悲酸”。作者个性、心情的差异带来文学表述方式的变化,从而构成了“文”与“人”之间的“自然”传达关系。(三)以抒写“情性”构成文学价值观。文学价值正负量的交锋是“情性”真假两种力量的对比,崇尚童心、崇尚情性是与反对虚情矫饰对情性的遮蔽相互并进的,而且发现情性受遮蔽的原因是发挥情性的前提。强加理念的干预是文学写作的障碍,也是童心丧失、真情受阻的根源;恣意仿古是文学写作的桎梏,也是文字守旧、新情受戕的文坛通病的母体;刻意经营、虚饰情性是文学写作的误区,也是假情假文繁衍蔓延的腹地。驱逐这些对写作不应有的束缚,文学才能自由地吐露真言、抒写真情,才能发展与繁荣。
堪以传世的文学作品都是自觉地“发乎情性”的产物,从风骚到诸子到韩柳三苏,从传奇到话本到《西厢》、《红楼》,无不是率性而发,为情铸文。对人间离合悲欢“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的曹雪芹,以“泪”与“痴”来凝结文学巨著《红楼梦》。这部文学精品屋中的珍品,将爱情从物欲权势的浊境中疏离出来,投放到超越生命与功利、生理与心理的审美制高点上进行观照,让情种的痴情至纯至美,具有“字字看来皆是血”的艺术震撼力。三十二回写黛玉听了宝玉的肺腑之言“你放心”后,情肠百结的心态、形态,完完全全是真情性的自然呈现:
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只管怔怔的瞅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词,不知一时从哪一句说起,却也怔怔的瞅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黛玉只嗐了一声,眼中泪直流下来,回身便走。宝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都知道了。”口里说道,却头也不回,竟去了。因为是肺腑中掏出来的话,就揭去了现实原则下的“自我”人性面具,裸示出两人真实的情感世界,使两个原本在性格、气质、心理等方面产生无数次错位的“小儿女”,有了这瞬时的情感“通电”。两个“怔”,是两情激荡的无声地带,空间似乎凝固,作者无需言传,让真情自呈。“泪直流”是感情长期压抑而获得释放的表现,林黛玉外表的佯痴佯怒与内心的患得患失互相映衬,体现了在感情终于找到依托这一突然的转折中这位孤傲女子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心态经过了从压抑到释放再进入更深层的压抑的心灵历程,是自尊和自卑的双重人格在她心中的绞结和冲突,这是性格内倾的林黛玉最逼真的性情写照。
从真情出发,对文学写作来说,就是要求以追求人性本真作为审美的标准和尺度,以实现对人性的终级关怀作为任重道远的使命,使文学作品成为真正抒写情性的载体。
注释:
〔1〕《宋书·谢灵运传论》。
〔2〕《文心雕龙·体性》。
〔3〕《海愚诗钞序》。
〔4〕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
〔5〕王国维:《人间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