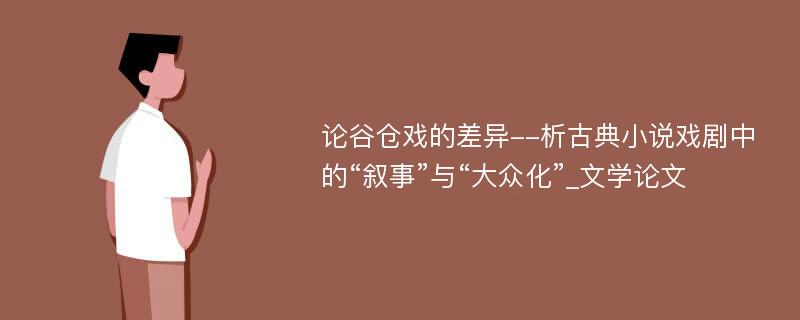
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异论文,通俗性论文,古典小说论文,戏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20世纪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就研究观念及其方法角度言之,古典小说戏曲研究成果的丰厚除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视小说戏曲为“小道”的观念之外,实得力于两大研究观念的确立:一是“叙事文学”观念,二是“通俗文学”观念,这两大观念在小说戏曲研究领域的确立大大开拓了小说戏曲的研究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中一大批重要学说和成果的产生大都缘于这两大研究观念的倡导和张扬。“叙事文学”观念的确立促成了小说戏曲研究中对故事本体和行为主体的重视,尤其是戏曲文学的研究大大突破了传统曲学的藩篱,而小说研究也打破了以往零散琐碎、点滴赏评的格局。小说和戏曲这两种文体被同置于叙事文学这一大的文类概念之中,使得对“叙事性”的重视成了20世纪小说戏曲研究的共同格局和特征,对小说戏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通俗文学”角度看待小说戏曲尤其是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和杂剧南戏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贯的传统,并非自20世纪开始,但20世纪小说戏曲研究中“通俗文学”观念的确立却有一个与传统观念大异其趣的重要前提:它是建立在充分认可乃至有意拔高“通俗文学”地位和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以“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观念来研究古典小说戏曲是合理的,从性质而言,小说和戏曲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性是这两大文学门类的重要属性,亦是它们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标志。从艺术风格和表现形态而言,小说和戏曲在整体上属于通俗文学范畴,而不是根本意义上的文人自咏自叹之作,它们均以读者本位作为其基本的生存状态。同时,小说与戏曲在中国古代还有着相近的遭遇,其地位、状态也大致相同。据此,古往今来视小说戏曲为相近之文学品类者代不乏人,李渔称小说为“无声戏”,也即无声之戏曲,蒋瑞藻在《小说考证》中谓小说与戏曲“异流同源,殊途同归者也”②。黄人(摩西)更直称“小说为工细白描之院本(即戏曲——引者),院本为设色押均(韵)之小说”③。然而,任何文学样式都有其特殊性,以“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观念对小说戏曲作一体化看待有其合理性,但仅抓住了小说戏曲的某些共性,而漠视了小说戏曲在“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这一大的前提之下的独特个性。故当我们对20世纪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作出深入回顾和反思时,我们也发现,“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观念的确立对于古典小说戏曲研究而言,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确实抓住了古典小说戏曲的基本特性,促成了小说戏曲研究中全新格局的形成;然而它同样也是以部分舍去小说戏曲各自的“个性”为代价的,故20世纪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以“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观念为指导思想所带来的弊端已日益明显。本文提出“稗戏相异论”这一论题,正是试图在承认“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这一研究观念具有重要价值的前提下,揭示小说戏曲在“叙事性”和“通俗性”上各自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小说戏曲的研究格局提出新的设想。
二 “诗心”与“史性”:戏曲小说的本质差异
我们先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看小说戏曲的差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叙事文学”的两大主干,小说戏曲其实在精神实质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简言之可以这样表述:戏曲的主体精神实质是“诗”的,小说的主体精神实质是“史”的。戏曲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上包含了强烈的“诗心”,小说则体现了强烈的“史性”。
怎样理解这一差异,我们不妨作进一步的推论:
我们认定戏曲的主体精神实质是“诗”的,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上包含了强烈的“诗心”,基于两方面的理由。第一,戏曲的外在形态乃是“以曲为本位”,而所谓“以曲为本位”一方面表现为“曲”是戏曲艺术诸要素中的核心成分,它是戏曲艺术用于表现故事、抒情言志的主要艺术手段,脱离了“曲”的本位性,古典戏曲也便失去了它的自身特性,而“曲”在本质上是诗性的。同时,古典戏曲艺术的结构形式是一种情节结构和音乐结构的组合体,而这种组合体的基本要素便是“曲”,“曲”既要体现戏曲情节的内在发展,又要表现音乐的自身构成,还要使情节结构与音乐结构有机地统一起来。正因为古典戏曲“以曲为本位”,故“曲”在剧本创作中居主导和正宗地位。剧作家通过“曲”驰骋才情、抒写情感和推演情节,而“填词”也几乎成了戏曲文学创作的代名词。第二,戏曲在表现形式中体现出了浓烈的诗歌韵味,极为强调抒情艺术中的主体性这一本属于诗歌艺术的创作原则,而作为叙事文学最基本的要求——故事情节的客体性制约——在戏曲创作中倒被相对淡化。一个极为显明的事实是:古典戏曲的故事本体在创作手法上所接续的是传统“寓言”的创作原则,“这戏文一似庄子寓言”④、“要之传奇皆是寓言”⑤、“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等表述在古代戏曲史上不绝如缕。将戏曲故事称之为“寓言”、将戏曲与寓言相比照,实际所要强化的正是戏曲创作中的主体表现性。何以言之?我们且看“寓言”的精神实质,从形式表象而言,“寓言”是一种观念与叙事的组合体,这种观念就创作者来说是一种先于故事与形象的纯乎理性的概念,而就欣赏者而言,这种观念又是一种超越故事与形象之外的、需凭借联想与想象而获致的“言外之意”。故“寓言”中的故事和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仅是一种借以表现某种观念的“喻体”,它不必完满地追求自身的客观性与内在逻辑性。同时,正因为“寓言”有其明确的寄寓性和观念指向性,其艺术形象便常常是某种观念的浓缩赋形,是象征性的和类型化的。古典戏曲接续寓言的艺术精神,故同样是“叙事文学”,戏曲在故事本体上表现出了独特的品貌。而古人将戏曲称之为“曲”、将戏曲的故事本体称之为“寓言”,两者其实是二而为一的,它所要强化的正是戏曲艺术的“诗化”特征。诚然,“寓言”是一种叙事艺术,但在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中,“寓言”是一种最富于写意性、象征性的艺术样式,“寓言”的精神实质乃是最大限度地摒弃叙事艺术所固有的客体性制约,而将叙事结构落实到创作指归上,从而完成寓言艺术的象征性和寓意性。而这正是古典戏曲的故事本体所刻意追求的。王国维评元杂剧云:“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⑥ 可谓深中肯綮之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明清时期的传奇创作。
我们评价小说的主体精神实质是“史”的,小说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上体现了强烈的“史性”则缘于三方面的因素。首先,从小说的外部形态而言,古代小说是“以故事为本位”的,而所谓“以故事为本位”是指小说以“故事”为其本质属性,抽去了“故事”这一内涵,小说也便丧失了它的本体特性。同时,小说之表现内容无论是得自传闻,还是据正史演绎,其结构亦无论以哪种方式叙述,都是围绕“故事”加以展开的。相对来说,诗词在古代小说中虽然也占有一定比重,但毕竟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是一种继承“说话”艺术传统、出自于小说“形制”需要的“附加物”,而并未真正渗透到小说的内在精神中去,不会影响小说的本质属性⑦。中国古代小说“以故事为本位”,而“故事”又带有强烈的历史内涵,故真正影响小说创作的是“史”。如同戏曲中的“曲”是“诗性”的那样,小说中的“故事”是“史性”的。其次,中国古代小说有浓烈的“史性”特征,故在小说创作中追求故事情节本身的客体性,而不以作家的主观情感抒发为目的。所谓“客体性”原则是指在小说创作中应尊重小说故事本体自身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一“史性”原则最为明显地体现于历史小说创作中,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所谓“客体性”即指历史真实性,故小说与史实之关系的所谓“虚实”问题始终是小说家们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所谓“虚实”问题的探讨是由《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的创作所引发的,自《三国演义》问世之后,以正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颇为兴盛,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上均受到《三国演义》的深深影响。庸愚子作于弘治七年(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首先以“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来评判《三国演义》的特色,与该序同时刊行的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亦以“羽翼信史而不违”来确立作品与所谓“信史”的内在关系。历史小说创作是否一定要“事纪其实”,在人们的观念中也不尽一致,如熊大木:“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⑧ 认为小说固然应以正史为标尺,但亦不必拘泥于史实,小说与史书是两种不同的文本形态,应区别对待。但也有人认为小说创作应恪守“信史”的实录原则,如余邵鱼创作的《列国志传》,自谓其作《列国传》“起自武王伐纣,迄于秦并六国,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并宣称“其视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⑨。陈继儒《叙列国传》也为其申说:“《列传》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核而详,语俚而显,诸如朝会盟誓之期,征讨战攻之数,山川道里之险夷,人物名号之真诞,灿若胪列。即野修无系朝常,巷议难参国是,而循名稽实,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譬诸有家者按其成簿,则先世之产业厘然,是《列传》亦世宙间之大账簿也。如是,虽与经史并传可也。”在对小说与史实之关系的认识上,可观道人评冯梦龙《新列国志》的一段话最为通达,其云:“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⑩ 由此可见,在小说与史实的关系上,无论是哪一种意见,强化小说与“史性”原则的关系是小说创作中一贯的传统。第三,在一些非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也大都习惯于将小说与历史相比较。如金圣叹评《水浒传》:“某常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11) 就是《金瓶梅》、《红楼梦》等世情小说,人们亦自然地与史书相对比,张竹坡评《金瓶梅》即以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来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12) 二知道人也认为《红楼梦》与《史记》相比有其独到的价值:“太史公记三十世家,曹雪芹只记一世家。太史公之文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曹雪芹记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虽稗官家流,宁无裨于名教乎?”(13) 至晚清,小说家们更在与史书的比照中来确认小说创作的特性与地位:“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且认为“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14)。而就描写之特性言之,则小说胜于史书:“小说者,以详尽之笔写已知之理也……故最逸;史者,以简略之笔写已知之理,故次之。”(15) 以上言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脉相承,不绝如缕,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在创作观念和创作特性上充满了“史性”的特征。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形成的上述差异使得同样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戏曲体现了相异的艺术特性。这种差异性的根源来自于两者艺术渊源与文学渊源的不同。古代戏曲是在说唱艺术、滑稽戏和歌舞戏等基础上完成自身艺术形态的,在这多种艺术要素中,又以说唱艺术表现故事的叙事体诗为其主干,而说唱艺术的叙事体诗又直接承继了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因此诗、词、曲相沿相续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几为不易之论,而古代戏曲家的创作正是秉持这一观念的。小说的艺术渊源则不然,古代小说最为重要的艺术渊源是神话传说与史书,但神话传说一则在古代并不发达,同时在其自身的演化中又常常作了“史”或倾向于“史”的更易。相反,史书在古代中国极为成熟和发达,故史书对小说的影响更为重要。中国古代史书对小说的影响表现在题材、体裁和表现形式等多方面,而正是这多重影响确立了古代小说“史性”的品格。
三 “词余”与“史余”:戏曲小说本体观念之对举
古代小说戏曲在其精神实质上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各自的创作中,同时在本体观念上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词余”和“史余”是古代戏曲小说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典型的本体观念,两者之对举在观念形态上凸显了古代戏曲小说及其研究格局的内在差异。
所谓“词余”观念是以“诗歌一体化”观念为背景的,“词”者,“诗之余”也,“曲”者,“词之余”也。故所谓“词余”的观念也就是“曲”的观念,戏曲是“曲”,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进程中一种特殊的“诗体”。这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本体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发展,也深深制约了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史的进程。当然,中国古代戏曲本体观念是复杂的,绝非“词余”或“曲”的观念所能涵盖,但“词余”或“曲”的观念确乎是古代戏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本体观念。为了确认这一本体观念在古代戏曲观念中的主导地位,我们不妨先简要缕述一下古代戏曲观念的演进历史。
古代戏曲的本体观念从剧本文学成熟的宋元开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相对独立的戏曲本体观念,即“曲”的观念、“文”的观念和“剧”的观念(16)。从宋元到明代中叶,在戏曲论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曲”的观念,人们将戏曲艺术视作是诗歌的一种,或者说戏曲就是“诗歌”。此一时期,剧作家们将戏曲创作主要看成是“曲”的创作,而戏曲研究论著所注目的中心也是戏曲艺术中“曲”的部分,包括“曲”的作法和唱法。一个比较显明的事实是:人们在研究对象上往往是戏曲与散曲不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夏庭芝的《青楼集》、钟嗣成的《录鬼簿》,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徐渭的《南词叙录》乃至王骥德的《曲律》,其研究对象均是散曲和戏曲的合成体——“曲”,“曲”是诗歌,是文辞与音乐的统一,是一定格式的诗歌与某种音乐的统一。而此时当人们追溯戏曲的源流时,亦往往视戏曲与诗歌同宗,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词曲》谓:“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歌曲,则歌曲乃诗之流别。”王骥德《曲律》在其论著的开首也标有“论曲源”一款,从音乐文学的角度把戏曲的源流一直追溯到上古,形成了“诗、词、曲”相沿相续的“诗歌一体化”的倾向。明中叶以后,一方面是传统的“曲”的观念在进一步固定和强化,同时,随着戏曲评点的出现,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戏曲艺术的叙事性,“文”的观念即叙事文学的观念逐步出现,尤其在明末清初,当金圣叹、毛声山父子对《西厢记》、《琵琶记》的叙事艺术作出深入赏评时,戏曲艺术的叙事性才得以深入地探讨。一直到清初,“剧”的观念即综合艺术的观念在李渔的《闲情偶寄》中得以确立,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所论述的已不再是传统的“曲”,“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款所讨论的是整个的戏曲文学。而《闲情偶寄》的“演习部”和“声容部”更将戏曲研究伸向了舞台表演,戏曲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得到了系统的研究,故在李渔的观念中,所谓戏曲是一种故事与曲文的统一并诉诸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至此,中国古代戏曲的本体观念得以向多元方向延伸。然而,戏曲史上“文”的观念和“剧”的观念的出现其实并未真正撼动“曲”的观念的主导地位。在明中后期,当“文”的观念开始出现时,吕天成在《曲品》中仍然按照“音律”与“词华”的标准给戏曲作品评等第张曲榜,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叙》所体现的评判标准更说明问题:“韵失矣,进而求其调;调讹矣,进而求其词;词陋矣,又进而求其事。”音韵词华是主要的,叙事性只居第三位。一直到晚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仍然秉持着“曲”的观念。
“词余”观念或曰“曲”的观念深深制约了中国古代对于戏曲艺术的研究格局。中国古代戏曲本体观念以“词余”观念或曰“曲”的观念为中心,而“曲学”——对于“曲”的创作法则和演唱法则的探究也便成了古代戏曲研究的中心内涵。吴梅曰:“声歌之道,律学、音学、辞章三者而已。”(17)“律学”当指“曲谱”,“音学”主要指“曲韵”,“辞章”则指对文辞及文辞与音律关系的探讨,再加上“唱法”一端,构成了古代戏曲研究的中心。这一研究格局自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发端,经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等曲学著作的深化,至明中后期形成热潮,沈璟的戏曲格律研究、王骥德的《曲律》对曲学研究的系统化、戏曲史上著名的“沈汤之争”等均主要围绕曲学展开,李渔《闲情偶寄》亦以“词采”、“音律”两章详细讨论曲学问题。一直到近代,吴梅的戏曲研究仍以曲学为主体,其《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可谓是对传统曲学的总结之作。相对而言,戏曲史上对于戏曲“叙事性”的探讨比较薄弱,金圣叹等戏曲评点家对于戏曲文本的赏读虽颇多注目戏曲的故事本体,但这种文本赏读对戏曲史发展的实际影响甚为微小。李渔《闲情偶寄》提出“结构第一”,并对戏曲的情节结构作出了细致阐发,但《闲情偶寄》的这一理论追求在中国戏曲史上诚为空谷足音,是“特例”而非“常规”,“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18),从李渔的语气中正可看出这其实是一种对曲学研究的反拨或补足,在戏曲研究中是非主流的。
与戏曲史上的“词余”观念相对举,在中国小说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本体观念是“史余”观念。所谓“史余”观念是从小说“补史”功能的角度看待小说的,即小说在表现范围和价值功能上可补“史”之不足。这一观念并不从通俗小说开始,在中国小说史上可谓延续久远,但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的“史余”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史余”观念在桓谭、班固有关小说概念和小说功能的阐释中已露端倪,其中已蕴含了小说可补经史之阙的认识。至汉末魏晋时期,随着文人杂史、杂传和杂记创作的风行,小说“补史”意识更为昭晰,葛洪《西京杂记序》谓:《西京杂记》乃“裨《汉书》之阙”。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亦谓《洞冥记》是“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裨《汉书》之阙”、“籍旧史之所不载者”均已明确说明小说的补史意义。王嘉评张华《博物志》乃“捃采天下遗逸”,而自署其书为《拾遗记》,亦已阐明小说的拾遗补阙功能。至唐代,刘知几《史通》在理论上作出了更细致的阐释,其拈出“偏记小说”一辞与“正史”相对举,且认为其“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而唐宋小说家更进一步张扬了这一功能,李肇《唐国史补自序》谓其撰《国史补》乃“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宋郑文宝撰《南唐近事》乃虑“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共四十年……君臣用舍,朝庭典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故将“耳目所及,志于缣缃,聊资抵掌之谈,敢望获麟之誉?”明确其撰述的“补史”目的(19)。由此可见,将小说视为对“史”拾遗补阙的观念乃源远流长,汉末以还杂史笔记小说的创作风行正缘此而来。
通俗小说的“史余”观念即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其理论指向有显明的不同。如果说,文言小说的“史余”观念着重于小说乃是对“史”的拾遗补阙,是对“史”不屑著录的内容的叙述。那么,通俗小说的“史余”观直接针对的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讲史演义,评论对象的变更自然引出了不同的理论趋向,“正史之补”也好,“羽翼信史”也罢,通俗小说的“史余”观均以“通俗”为其理论归结,将“史”通俗化,以完成“史”所难以承担的对民众的历史普及和思想教化,是通俗小说“史余”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林瀚在万历己未(四十七)刻本《批点隋唐两朝志传序》中提出小说“正史之补”的说法(20),在他看来,小说之所以可为“正史之补”,关键亦在于“两朝事实使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的通俗性。明人由《三国演义》及讲史演义的风行而接续了传统的“史余”观念,又因讲史演义特殊的文体特性将“补史”之功能定位在“通俗性”上,而不再以“拾遗补阙”作为小说基本的“补史”功能。这一内涵的转化使“通俗”这一范畴在明清小说学中越来越受到小说家的重视,并深深影响了小说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小说本体观念,“史余”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古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我们甚至可以说,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围绕着“史余”观念而展开的。我们姑举古代小说理论批评范畴为例对此作一说明:相对于诗学、词学乃至曲学而言,小说理论批评范畴比较贫乏,往往是对传统文学理论范畴的“移植”,如“教化”、“幻奇”等,而小说评点家使用的范畴术语又有较大的随意性,缺少相对意义上的理论延续。但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那些最贴近小说文体特性的有限的理论范畴却大多以“史余”观念为中心,如“演义”、“虚实”、“补史”、“通俗”,可以说,这四大理论范畴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体系的四个“链结”,“演义”为文体概念(21),“虚实”指创作特性,“补史”为价值功能,“通俗”指表现形式,而这四大理论范畴无一不从“史余”观念延伸或演化而来,实际上是从不同侧面支撑着“史余”这一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中居主导地位的小说本体观念,故这四大范畴均是与“史余”观念相表里的,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发展进程影响深远。
四 雅俗之间:戏曲小说的文人化进程
从“通俗文学”角度看待小说戏曲,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这里我们可以采用一种视角——“小说戏曲的文人化进程”来梳理小说戏曲的内在差异。所谓“文人化”,本文拟作这样的界定:“文人化”原则并不仅仅指小说戏曲文辞的典雅,它的第一要义是小说戏曲创作中文人主体性的张扬,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明确的文人本位性,突出其通过小说戏曲之创作来实现作为文人所固有的价值,具体而言,是指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作者对现实、历史、人生的思考,表现他们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文人化”的第二要义是在艺术形式上追求一种相对完美、稳定的艺术格局和在语言风格上实现一种与文人自身身份相合的雅化原则。以此来衡定小说戏曲的文人化进程,其中之差异显而易见。
宋元以来,中国古代之雅俗文学明显趋于分流,从逻辑上讲,所谓雅俗文学之分流是指通俗文学逐渐脱离正统士大夫文人之视野而向着民间性演进。宋元时期,这种演进轨迹是清晰可见的,话本讲史、杂剧南戏、诸宫调等,其民间色彩都十分浓烈。因而从分流的态势来看待通俗文学的这一段历史及其所获得的杰出成就,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中国通俗文学的成就是文学走向民间性和通俗化的结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民间性和通俗化诚然是通俗文学在宋元以来获得其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雅俗文学之分流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通俗文学逐渐失却正统士大夫文人的精心培育,而这无疑也是通俗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缺失。因此,如何在保持民间性和通俗化的前提下求得其思想价值和审美品位的提升,是通俗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宋元以后,通俗文学在整体上便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尤其是作为通俗文学主干的戏曲和小说,但两者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和平衡。
戏曲的文人化进程非常明显。中国古代戏曲就其发展脉络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时代:杂剧时代、传奇时代和地方戏时代。从元代到明初,杂剧艺术占据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中心位置,而早于杂剧产生的南戏此时期却在南方民间默默地滋长着。至元末明初,随着杂剧艺术的日益衰微,“荆、刘、拜、杀”和《琵琶记》跃起于剧坛,于是,戏曲艺术的中心位置逐步由杂剧艺术转向了由南戏演化而来的传奇艺术,传奇艺术在明清两代延续久远。一直到清中叶以后,传奇艺术随着昆腔的衰落和传奇文学创作的荒芜,其艺术生命力慢慢地趋于消歇。而活跃于民间的地方戏因其丰富性和民间性而赢得了观众的青睐,它不断地从成熟的戏曲艺术中吸取养料来壮大自己,从而逐渐地主宰了戏曲舞台。从杂剧到传奇再到地方戏,中国戏曲艺术有其艺术传承的整体性,同时也体现了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就剧本文学而言,所谓戏曲的文人化进程主要涉及杂剧和传奇两个时代。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戏曲自元代杂剧以后并未完全循着民间性和通俗化一路发展,而是比较明显地显示了一条逐渐朝着文人化发展的创作轨迹。这种进程就其源头而言发端于元代,这便是马致远剧作对于现实人生的忧患意识和高明剧作中重视伦常、维持风化的教化意识,这两种创作意识开启了明代戏曲文人化的发展进程。丘浚的《五伦全备记》、邵灿的《香囊记》等理学名儒的戏曲创作,将高明《琵琶记》中的风化主题引向极端;而李开先、梁辰鱼等的剧作则对马致远作品中的现实忧患意识作了进一步深化。如李开先《宝剑记》,如果将元代的水浒戏与《宝剑记》作一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元代水浒戏所表现的是大众化的除暴安良,而《宝剑记》则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有浓烈的文人个体意识渗溶其间,一般认为这是明传奇走向高潮的前奏,此后的戏曲创作在表现风格、艺术内涵等方面基本上都沿此而发展。至万历年间,戏曲的文人化成为一时之风尚,大批文人剧作家投身于戏曲创作,使戏曲文学的文人化倾向更为浓郁,汤显祖“临川四梦”正是其中之代表。万历以后,戏曲史上曾有一股回归大众化的趋向,如吴炳、阮大铖、李渔的创作,他们都强调戏曲的故事性、可读性与可看性,然而文人化的进程犹未中止,在清初“南洪北孔”的笔下,这一文人化的进程终于被推向了高潮。诚然,明清传奇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但以上简约的描述却是传奇文学发展中一条颇为明晰的主线,这条主线构成了中国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一代之文学——文人传奇时代。
与戏曲相比较,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进程要比戏曲来得缓慢,通俗小说创作并没有形成像文人传奇那样一个独立的创作时代。综观通俗小说的发展历史,其文人化进程是有迹可寻的,尤其是它的两端: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清乾隆时期的《红楼梦》、《儒林外史》,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可说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完满的收束,但在这两端之间,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却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缓慢的进程。明代嘉靖以后,随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刊行,通俗小说的创作在明中后期形成了一股热潮,然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引发的这一股创作热潮并未完全循着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文人化”的创作路向发展,相反地,倒是激起了一股“通俗”的小说创作思潮,无论是历史演义还是英雄传奇,也无论是神魔小说还是初起的言情小说,世俗性、民间性都是其共同的追求。如果说,戏曲文人化在明中后期已成风尚,那此时期的通俗小说仍然弥漫着浓烈的民间性与通俗性,就是明代“四大奇书”和“三言二拍”都未能在整体上真正消融小说的“通俗”特性。小说戏曲在文人化进程中的这一“时间差”是中国小说戏曲在自身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明事实,对各自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故通俗小说真正的“文人化”进程是从晚明开始的,且不直接来自创作者,而更主要的缘于文人批评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影响通俗小说发展进程的除了小说家自身外,文人批评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与小说作家一起共同完成了通俗小说艺术审美特性的转型。在文人批评家的参与下,通俗小说通过批评家的改编和批评,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此,自李卓吾以还的文人小说评点家如金圣叹、毛氏父子等对小说的评改提高了通俗小说的历史地位,也使通俗小说提升了文人化的程度。明代“四大奇书”即最后定于文人评点家之手,而成了古代小说的范本,对小说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得长期缺乏高品位文人参与的古代通俗小说终于在清代中叶迎来文人化的高潮,这就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出现,至此,小说的文人化才最终成型。然而,这一文人化进程所达到的效果还是有限的,一方面,文人评点家对通俗小说的关注有他自身的选择,小说史上真正可以让他们倾情投入评改的作品毕竟有限,故文人评点家对通俗小说的评改主要在“四大奇书”,而“四大奇书”的标举还不足以真正改变通俗小说的整体面貌。同时,通俗小说史上很少如明清曲坛那样有大量的文人投身于创作,曹雪芹、吴敬梓等在小说史上的出现诚为难得一遇。故由这种状况所引起的通俗小说“文人化”程度的淡薄乃是不足为奇的。
小说戏曲在文人化进程和文人化程度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学渊源的差异,通俗小说源于民间说话,而作为明清通俗小说直接源头的宋元话本讲史,其本身就没有如元杂剧那样,在民间性和通俗化之中包涵有文人化的素质,基本上是一种出自民间并在民间流传的通俗艺术,通俗小说的胚胎中相对缺乏文人化的内涵,故而缘此而来的明清通俗小说就带有其先天的特性。二是“文本”创作所依托的对象不同,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剧本文学的创作必定要受到特定的声腔剧种的制约,明代以来,戏曲的文人化进程发展迅速,而这恰与南曲的勃兴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明中叶以后昆腔的兴盛更是戏曲文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昆腔柔美、婉丽,以文人性见长,透现出浓郁的书卷气,它在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深深制约了剧本文学的创作,剧本文学的文人化正是与昆曲的这一特色相一致的。当然,文人化确实是促成了戏曲审美品味的提升和思想价值的提高,但文人化发展到极致也使戏曲艺术逐步偏离了戏曲艺术的本质属性——民间性,故清中叶以后昆曲与传奇创作的同时衰落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通俗小说所依托的对象则不然,通俗小说自明中叶以来一直依托于以“书坊”为中心的商业性传播,书坊以赢利为目的,以传播的大众化、民间性为依归,故在商业传播的制约下,通俗小说与戏曲文学相比较,其文学商品化的特性更为强烈,这种特性也妨碍了通俗小说向文人化方向发展。三是创作队伍的差异,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主宰着中国戏曲艺术发展进程的是文人剧作家,在元代,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元代剧作家以其有用之才而寓于“声歌之末”,剧作家在思想品格和艺术品味上均居于时代之前列,故元杂剧虽在总体上是大众化的艺术样式,但剧本文学还是充盈着文人的色彩和情调。明代以后,创作者的文人化更趋浓烈,朱权、朱有燉等皇室成员,丘浚、邵灿等理学名儒都投身于戏曲创作,至明万历年间,大批文人对戏曲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戏曲创作的文人化可谓达到了高峰,这一境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地方戏的兴起,中国古代戏曲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由以剧作家(剧本文学)为中心转向了以演员(舞台表演)为中心,戏曲由此向民间性方向发展,文人化趋于消歇。相对于戏曲文学的创作队伍,小说的创作者则以下层文人为主,当明代万历年间的文人士大夫紧紧把握着戏曲发展之脉搏的时候,小说创作的主体则是书坊主及其周围的下层文人,这一境况可以说一直延续在小说史上,故下层文人始终是小说创作的主流队伍,至近代,这一格局才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把上述分析作一收拢,那我们可以对小说戏曲在文人化进程和文人化程度上的差异作这样的归纳:从杂剧到传奇,戏曲文学发展的主流趋向是文人化,其中民间性、通俗性的重视常常是以“反拨”的面目出现的,体现为在文人化的前提下有意向“下”拉的倾向。而从宋元话本到明清章回,小说的主流倾向则是通俗性,文人化的重视恰恰表现为在通俗性的前提下有意向“上”提的趋向。如同戏曲史上以“民间性”、“通俗性”反拨戏曲文学的文人化是局部的一样,小说史上以“文人化”提升通俗小说的艺术品位其实也是局部的、非主流的。
五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大主干,小说戏曲在“叙事性”和“通俗性”两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古代戏曲小说的本体观念中也得到了明确的反映,“词余”观念与“史余”观念的对举正清晰地说明了这一问题。那戏曲小说的这种差异性对戏曲小说研究是否应有所制约呢?20世纪的小说戏曲研究以“叙事文学”观念和“通俗文学”观念对这两种文体作一体化对待是否与这种差异性相矛盾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站在新世纪初来回顾20世纪的小说戏曲研究,我们不难看到,“叙事文学”观念与“通俗文学”观念的确立为小说戏曲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格局,对小说戏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这种研究观念所引起的弊端也已日益明显,综合起来,这种弊端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20世纪的中国小说戏曲研究常常忽略小说戏曲在“叙事性”上的本质差异。“思想、形象、结构、语言”的四分法是20世纪研究小说戏曲“叙事性”的共同格局,“思想”的深刻性、“形象”的典型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的性格化是小说戏曲研究中几乎相同的标尺,这一格局和标尺就小说而言有一定道理,然亦难尽如人意,但与戏曲文学的本体特性之间有着明显的距离,实际上难以真正揭示作为叙事文学的戏曲所具有的本质属性,而仅仅是以小说的研究格局来套用戏曲。如以“形象”的典型性来分析戏曲就与戏曲的“寓言”特性难相吻合,至于“语言”的性格化则更非“以曲为本位”的戏曲文学的普遍追求。其次,20世纪的小说戏曲研究常常模糊小说戏曲在“通俗性”这一点上的非对等关系。同时,“通俗文学”观念的确立仅表现在观念形态上,而缺乏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其表现为:它在观念形态上拔高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然其研究方法仍然采取的是“雅文学”的研究路数,包括价值评判与形态分析。
由此,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欲求得深入和发展,对于20世纪小说戏曲研究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研究思路确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对此,我们拟提出这样几个设想与学界共同探讨:首先,从“通俗文学”的角度研究小说戏曲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与“通俗文学”相适应的研究模式,在思想方法上为“通俗文学”研究设定相关的研究视角、评判标准和价值体系。其次,从“通俗文学”角度研究小说戏曲要打破小说戏曲各自的文体限制。“通俗文学”其实不是一个文体概念,而是一个“文类”概念,它涉及小说戏曲等多种文体但又不能以文体来界定,实际上是指一种在“价值功能”、“表现内容”、“审美趣味”和“传播接受”等方面基本趋于一致的文学类型或文学现象。故在小说戏曲研究中,那些充分“雅化”的作品如《牡丹亭》、《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应逐步淡化,不再以这些作品作为“通俗文学”研究的中心,从而梳理出符合通俗文学自身特性的发展线索和揭示通俗文学的自身“经典”,如李渔的小说戏曲、《三侠五义》等。以《牡丹亭》、《红楼梦》等作为“通俗文学”的“经典”实际上是掩埋了“通俗文学”的自身“经典”和模糊了通俗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往往使通俗文学的研究脉络不清且“经典”不明。第三,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戏曲研究要努力寻求和确立一种符合小说戏曲自身民族特性的“叙事文学”理论及其研究框架。20世纪对小说戏曲“叙事性”的研究在思想方法上所接受的主要是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但小说戏曲有着浓重的本民族的特色,与西方的文学观念及其理论方法其实并不完全适应。对于中国“叙事学”的研究近年来已受到了相当的关注,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欲求得深入,还有两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一是要密切关注小说戏曲各自的文体特性,对小说戏曲不能加以一体化对待。如以“诗性”原则探讨戏曲作为叙事文学的本质特性,梳理曲体与戏曲叙事性的关系;而以“史性”原则探讨小说“叙事性”的内涵,并由此确认小说戏曲在“叙事性”上的独特品格。二是文体研究的“细化”。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体都是复杂丰富的,就小说而言,其文体有“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等的区别,戏曲也起码有“杂剧体”和“传奇体”的不同,这些在小说戏曲大的“文体”概念下的局部“文体”均有自身的文体渊源和形态特色,故局部的“文体形态”研究要加强,并在相互的比较中梳理小说戏曲文体形态的发展史。只有这样,所谓中国“叙事学”的建立才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和充分的依据。总之,我们期待着新的研究格局和思路的不断出现,也期待着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
注释:
①本文所谓“小说”主要是指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即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而不多涉及文言小说。
②蒋瑞藻《小说考证·附录·戏剧考证序》,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黄人《中国文学史》第一编《略论·文学华丽期》,东吴大学堂讲义,国学扶轮社(上海)1906年版。
④丘浚《五伦全备记》。
⑤徐复祚《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
⑦《红楼梦》中的诗词突破了这一格局,较多以诗词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但这种突破在小说史上非常少见。
⑧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嘉靖三十一年刊本。
⑨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列国志传》明万历三十四年三台馆刊本。
⑩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清初覆明金阊叶敬池刊本。
(11)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12)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13)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14)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15)别士《小说原理》,《绣像小说》第三期(1903年)。
(16)详见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吴梅《中乐寻源·叙》,见《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18)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
(19)郑文宝《南唐近事自序》,四库全书本。
(20)林瀚《批点隋唐两朝志传序》末署“赐进士第资政大夫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致仕前支部尚书国子祭酒春坊谕德兼经筵讲官同修国史三山林瀚撰”。林瀚(1434—1519)为明弘治、正德年间之显宦,此序是否真出自其手笔,尚多疑问。此序真伪之考订详见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1)一般认为“演义”为小说类型概念,指称“历史演义”这一小说类型,但其实古人是将“演义”视作小说文体概念的,“演义”即指通俗小说这一文体。详见拙作《“演义”考》,《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标签: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古典小说论文; 古代文人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史记论文; 金瓶梅论文; 文化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闲情偶寄论文; 读书论文; 寓言论文; 琵琶记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