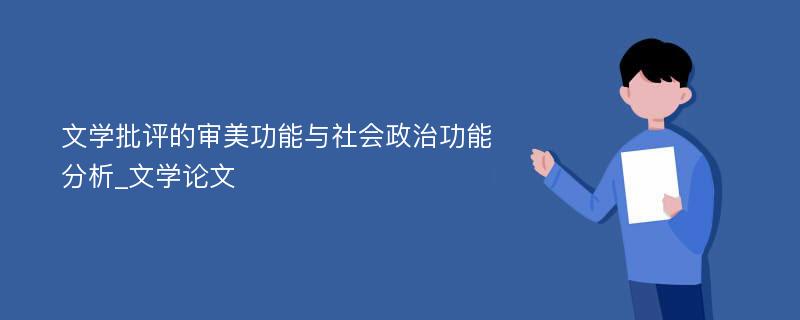
文学批评的审美功能和社会政治功能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批评的审美功能
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它的性质和功能不能不首先受到文学特征的制约。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作品的美具有飘忽、朦胧的特点,它决定了批评审美体验和意义阐释的不确定性。批评家只有用直觉领悟和心理体验的艺术思维方式才能进入艺术,也只有用空灵蕴藉的语言才能传达作品的审美蕴涵。批评家美感领悟和美感传递的方式决定了批评写作的艺术化特点,文学批评因此被人们称作艺术王国的第十位“缪斯”。文学批评的文学性特点,必然吸引着读者的审美关注,并由此产生激发读者美感的功能。
文学批评以艺术作品为工作对象,它首先必须以艺术的方式才能进入艺术。这就决定了文学批评不是纯粹客观、抽象的科学活动,它同时还是一种富有艺术情趣的审美活动。批评家通过直觉领会作品的艺术神韵,用形象比喻来传达批评家的美感印象,是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流传久远的传统。中国古代批评家常用形象比喻和意境描绘的方法,将作品的审美意蕴和批评者的美感领悟化为可触摸的形象画面。以形象喻义的美感传递方式最早见于魏晋的作家品评,《南史·颜延之传》记载,颜延之曾问鲍照,自己和谢灵运的创作谁优谁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初发芙蓉”和“铺锦列绣”,分别传达了品评者对两种不同风格诗歌的感受印象。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中大量采用取譬引喻、立象尽意的方法比较不同的诗风,唐代杜甫《戏为六绝句》开创的以绝句体组合论诗方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把形象的感受描述和理性的思考点拨结合起来,通过自然境界的描绘将读者引向审美的境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形象喻诗的方式。中国古代批评追求批评的趣味和文采的诗化倾向,避免了纯客观理性的逻辑分析带来的凝固和僵化,在对作品的浑融解读和整体把握中透露出灵活、机智与才情。现代的文学批评家也常常凭借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领略作品的艺术美,用富于弹性的诗意语言向读者具体地传达阅读中所体验到的审美感受。鲁迅曾经这样描述柔石《二月》中肖涧秋的性格特征:“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个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个,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注:《柔石作〈二月〉小引》, 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批评家艺术灵性中产生的新鲜贴切的比喻,缩小了批评分析中的抽象推理给读者带来的距离感,增加了文学批评的审美吸引力;批评心得的诗意传达,在激发读者美感同时,又能够引导读者玩味、领会批评家深沉的人生体验和独到的审美发现。对此,德国批评家弗·施莱格尔说:“对艺术的一项判断如果本身不是一项艺术作品,内容上若是没有显现作品本来的必要印象,或是没有美的形式和体现古罗马讽诗精神的开通笔调,那么它在艺术王国就无公民权。”(注:转引自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2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文学批评的职能,是引导读者去发现艺术的美,“评论的作用是什么呢?评论应该成为美的解释者,同时教给读者更好的区别美和更好地热爱美”(注:罗杰·法约尔:《法国文学评论史》,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由于文学作品的艺术美“不能用纯粹客观的词语来描述”(注: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1页。),批评家就往往通过模糊的具有诗意的弹性语言进行富于情趣的美感描述,激起读者自己去欣赏玩味的兴趣。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只是艺术王国的一个“导游”,文学的美景主要靠读者自己去领略。批评家采用形象比喻和意境描述的方法,就能够有效地传达批评家意识和作家意识相遇、相认、相融合时的初始经验,同时也容易诱发读者的想象,对作品的审美韵味产生创造性的理解。我国现代文学批评长期受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影响,自身不能走进艺术,也无法引导读者领略艺术之美,批评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近年来,我国文学批评界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呼吁文学批评的文体解放,意在用批评的美文改变几十年庸俗社会学批评干瘪、枯燥的教条面孔,呼唤批评表达的激情和文采,恢复批评对读者的审美吸引力和美感激发力。
批评文本自身的美感吸引力,仅仅是批评审美功能的一个方面。文学批评更为重要的职能,是通过它的思想和艺术分析,深化读者的审美体验,增加读者的审美愉悦。文学作品具有的审美愉悦作用,源于文学的生产者,完成于文学的接受者。对于读者接受来说,作家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和深刻体验,文学作品新颖独特的艺术内容,无不是对接受主体审美经验和审美能力的一种挑战。“夫作者皆禀灵含异,各充其极,缛旨绮文,情变气殊,故以浅涉者不能深,以泛猎者不能得,以己见者不能该,以辞类者不能达意”(注:安磐:《颐山诗话原序》,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文学创作不断融入作家新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趣味,不断以艺术创新冲破成规定律,越是人生体验深刻、形式新颖独特的作品,读者接受起来难度越大,这时就需要批评家的提示和帮助。批评家的分析把读者引向作品的精微之处,体验蕴含在艺术中的人生真谛,从而获得强烈深邃的审美享受。中国传统小说中较少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作家只是用行动、对话来暗示人物心理。领会这种暗示,需要感知的敏锐和细心的揣摩,一般的读者因此容易轻轻放过。《水浒传》第36回“船火儿夜闹浔阳江”中,有一处对宋江的心理描写,它的精彩全靠着金圣叹的评点才得到众多读者的赏识。宋江在张横船上受了大惊,忽听有人救他,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星光明亮”,金圣叹评论说,“此十一字妙不可说。非云星光明亮照见来船那汉,乃是极写宋江半日心惊胆碎,不复知天地何色,直至此,忽然得救,夫而后依然又见星光也。”(注: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5页。)创作上高手的含蓄写法, 得到批评家的分析,才能使读者领会作品艺术技巧的优越和生活内涵的丰富,产生审美的愉悦。有些作品创作出来后,由于它们的创新和传统之间的距离很大,常常会成为一时的焦点,并引起人们的争论,这时,一般读者就特别想听到批评家的意见。80年代末王朔的小说在中国文坛曾经引起轰动效应。令人费解的是,王朔小说的格调不高,但它为什么会拥有那样多的读者?批评家指出,这与小说独特的话语方式密切相关。例如,王朔的小说《顽主》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要过早上床熬得不顶了再去睡内裤要宽松买俩铁球一手攥一个黎明即起跑上十公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意念刚开始飘忽就去想河马想刘英俊实在不由自主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
这段话使用了“黎明即起”和“刘英俊”两个语言材料,而指称却是“顽主”向客户兜售性心理健康的办法。这种话语方式是王朔特有的,它典型地代表了王朔作品特有的那种把从传统教育、特别是为宣传传统而编造的文学作品中学来的话语模式,运用于实际生活中所产生的反讽意义。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作者是如何使它的作品达到反讽效果的呢?批评家分析说:
中国字每一个都有特定的含义,当它被组合到文学作品的句子中去时,它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句子的特定语境,它自身的含义仍然会勾起人们习惯上的联想;同样,每一个句子被用到文学作品里,不仅承受着作品总体构思所形成的特定语境的压力,它自身依靠字面组合而产生的相对稳定的意义也将起作用。王朔正是利用了这两者间的距离,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注:陈思和:《黑色的颓废》,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批评家进一步指出,历史的反讽是王朔小说的基本特征,作为一种语言特征,反讽在作家那儿不具备纯粹的技巧意义,倒是在修辞效果上暗示了平民心理。王朔成功地选择北京市民作为他的主要读者,相当敏锐地捕捉到市民阶层中年轻人的心理情绪,以及表现这种情绪的特殊话语方式。批评家的分析没有对“王朔现象”作简单的价值判断,他通过对当时“王朔热”的冷静反思,提高了读者接受王朔小说的欣赏水平。波兰现象学批评家罗曼·英伽登指出,“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的构成”,而一般的文学消费者“是把文学作品仅仅作为通向自己的幻想的跳板或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注:罗曼·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页。),因此, 由作品暗示但却要读者具体化的诸多层次并不能在阅读中全部实现。批评家对作品形式意味的领会描述,对隐含意义的探究分析,把读者引向一个观照文学作品的新窗口,激发起艺术接受者“重读”的欲望,在仔细品味、反复探求中纠正自己对作品肤浅、含糊和不充分的理解,从而获得更为深刻的艺术享受。
二、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功能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它的社会性无法割裂,因此,文学批评在分析文学的艺术性时,必然要涉及文学作品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并对它们作出衡量和评价。例如,指出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貌,分析作家通过艺术形象流露出来的对生活的理解和评价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在这中间,批评家必然也会表示出他自己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解,表示出他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和观点。和文学创作相比,批评家的分析和评价是一种理论形态,因此,它所表示的这种思想倾向就比文学创作更为明晰、更为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可以说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评论,依照作品内容的不同和批评角度的不同,分别带有政治批评、道德批评的性质。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变化时期,在社会斗争激化的情况下,文学批评的这些性质会更显突出。它会使批评家站在一定立场上,自觉投身意识形态斗争,把文学批评当作提出或维护某种政治思想主张的途径和手段。当社会处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时期,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功能则主要表现为通过道德教化,推进社会发展所必须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学批评的社会批评性质,不仅使批评在透视作品的社会性时发现其独特价值和局限,而且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评价,使文学批评超越审美和艺术的层面,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也获得自身发展的契机。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优秀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决不只限于审美和艺术,它们包含着对人性人心的深入体验,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批评家对作品艺术内容的领会和阐释因此不可能停留在审美的层面,它必然会从审美的分析引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的分析,注意考察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哲理价值、教育价值以及对现实生活可能产生的一切影响。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像孔子和别林斯基这样的批评家,常常会从精彩的艺术分析入手,深入挖掘文学作品的道德价值、政治价值。这种批评,也有可能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佳作,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处于激烈动荡,或者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等政治生活内容往往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关注的热点,成为制约社会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导因素。当社会成员的“政治情结”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时,批评家“仅仅从美的方面来理解艺术恐怕就不可能了。并且,如果那样做,就不会成为对现实的把握”(注:桑原武夫:《文学序说》,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34页。)。这时, 批评家就应该着重分析文学作品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分析作品中的政治因素、道德因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9世纪中叶俄国第一次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夜评论屠格涅夫的小说《阿霞》时说,小说中的男主角在革命需要他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犹豫不决,甚至临阵脱逃,这种自由主义的性格特征,在他那个时代“比公开的坏蛋还坏”。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对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分析,隐含了他对在俄国革命走向成熟的历史关头彷徨不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批判。自由派批评家把“多余的人”说成是社会的优秀人物,说成是俄罗斯人的“道德典范”,却把从平民知识分子中出现的革命者攻击为“虚无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革命高潮尚未形成的三四十年代,说“多余的人”是优秀人物尚无不可,但到了革命迫在眉睫的五六十年代他们还在“扮演着高尚人物”,作家仍旧用这种形象充当青年的楷模,就只能视为一种文学欺骗。车尔尼雪夫斯基预告:“我们蒙受这种梦想的影响已经不会太长久了,还有比他更好的人,也就是受他所侮辱的人。”(注:《在幽会中的俄罗斯人》,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第2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别林斯基分析果戈理早期作品《小品集》时,从作品具有引人发笑的艺术效果入手,指出这种喜剧性中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的卑污一面的反映,隐含着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罪恶的深刻意义。这种批评,把读者的接受心理从审美的境界引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思考,进而把握作品所具有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变化时期,在社会斗争激化的情况下,文学批评“总是充满着政论的性质,有一部分简直就成为政论”(注:普列汉诺夫:《俄国批评的命运》,载《世界文学》1961年第11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极力倡导现实主义文学,他们的艺术理想和变革农奴制的社会理想密切相关,他们不仅把俄国文学推向现实主义的高峰,而且这种鲜明的政论性也使他们的批评达到社会历史批评史上的最高水平。后来,这种政论性很强的批评文章,在社会状况极为相似的中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艺术家,投身于文艺事业都是为了改造社会,改善人生,象牙之塔的艺术,在中国没有市场。此外,批评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专制政体的高压统治下,正常的社会批评和舆论监督无法进行,这也会“驱使文学书籍的评论,变成了掩饰的政治、社会与道德的批评”(注: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1页。)。 创作和接受的时代特点,决定了批评的社会性、战斗性。20年代末至30年代成为主流的左翼文艺批评,选择具有明显社会批判意义和政治倾向性的作品,关注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生活,注重分析文学中的革命者形象,对那些表现劳苦大众反抗斗争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现代中国进步的文学批评不是学者书斋中的学问,它自觉把艺术的批评和社会的批评结合起来。尽管这种结合并不完美,面对动荡的、紧张的政治斗争,革命文学家在强调文学作品社会政治功能的同时,往往多少忽略了艺术中的审美因素;在追求文学作品战斗性的同时,往往多少放松了对作品艺术性的严格要求,但它的战斗性由于和时代的要求合拍,仍然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
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功能,不仅表现为影响特殊年代政治斗争的战斗性,它还表现在批评家通过对作品中蕴含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倾向的挖掘,提高读者理解现实生活、辨别美丑善恶的能力。尽管批评的第一要务是对作品美学优点和艺术品格的评价,但是批评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艺术评价或者技巧解释,它应该使读者看到作品中丰富多采的人生,进行和作品内容相适应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分析。“每一部艺术作品一定要在对时代、对历史的现代性的关系中,在艺术家对社会的关系中,得到考察”(注:《关于批评的讲话》,见《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5页。)。批评家把对作品的艺术性分析和社会性分析结合起来时,也就必然会表示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评价。在分析当代小说《人到中年》时,批评家指出,中年人问题,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问题,把它放在刚刚结束的十年文化专制主义的背景中考察,是一个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小说家对中年知识分子陆文婷在家庭和医院、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疲于奔命的描写,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批评家把作品置于时代、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在分析中年科技人才具有承上启下的骨干作用的同时,呼吁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解决他们的困难(注:《留给读者的思考——读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见《朱寨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02页。)。批评家的分析评价对纠正长期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偏见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文学批评活动既是对美和艺术的领悟感受,又是一种社会的精神文化现象、一种舆论工具。当社会生活处于各种矛盾比较尖锐的转型时期,文学批评的舆论导向功能主要表现在为社会变革的政治斗争服务,为维护或推翻某种社会制度大喊大叫;当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文学批评的舆论导向功能则主要表现在推动社会的文明化程度,为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等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总趋势时,文学批评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更偏向于后者。伴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休闲娱乐产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文化市场兴起,商业竞争激烈,文学创作逐步渗透市场运作机制。文学作品的策划、创作、包装、营销等一系列环节在市场需要的拉动、刺激下,其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必然出现不同于政治斗争激烈年代的新特点。从文学的生产者来说,作家的社会良心和市场需求经常发生冲突,一旦作家把握不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引导社会大众之间的“度”,就有可能生产出庸俗、落后的作品。对文化产品的接受者来说,现代社会发达的传播媒体可以很快将信息传递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禁止受众不接触某种文学已不可能;而要求社会大众有能力辨别作品趣味、意义的精华或糟粕,也不现实。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批评家对素质良莠不齐的大众文学产品及其接受活动的分析指导就显得特别重要。借用鲁迅的话:“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注:鲁迅:《关于翻译〈上〉》,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297 页。)介入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批评家,针对文学作品中落后、反动、黄色的描写,针对读者已经有或者可能有的病态欣赏趣味和错误理解,用犀利的一针见血的分析,揭示作品掩盖着的实质,指出它们错谬之处以及为什么如此错谬,限制其负面影响,引导读者在批判性的阅读中扩展自己的思想视野,提高自己的艺术趣味。
恩格斯曾说过,文学艺术是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部门,和经济、政治、法律相比,文学艺术和老百姓的关系显得更为松散。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功能,使文学批评超越审美和艺术的层面,拉近了文学和受众的距离,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也获得自身发展的契机。文学批评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它在文学结构中的表现,它还与批评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由此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有关。尤其是在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受众往往不满足于批评的纯艺术化分析,他们更看重批评介入社会生活的力度和水平。如果批评家以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当代精神,满足了这种社会需要,它同时也就获得了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源泉。思想史表明,文学批评最活跃、文学思想最丰富的时期,常常是时代最需要批评智慧关注的变革时期。批评家感应时代精神,通过对文学的政治、道德评价,表达他对敏感的社会问题的态度,参与政治思想的论争,这样,文学批评在关注社会的同时也被社会所关注。这种充满鲜明政论精神的批评,尽管常犯忽视文学特殊规律的简单化毛病,但它却容易产生出某种深刻的启蒙思想和哲学、文学观念,使批评超越具体的文学现象,获得传世的价值。我国的先秦、魏晋六朝和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西方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俄国19世纪中叶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无不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充分发挥批评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完成思想启蒙的同时把文学批评推向一个个历史的高峰。
收稿日期:1999—01—12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王朔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