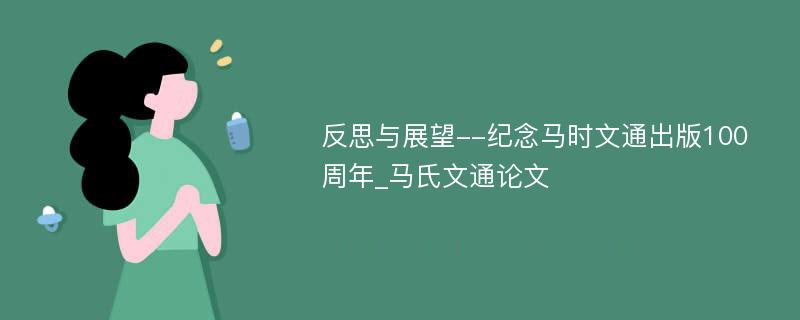
反思与前瞻——纪念《马氏文通》发表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一论文,周年论文,马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H14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722X(1999)02-0001-05
马建忠在清末所著《文通》一书,至今已一百年。在此期间,逢五逢十,人们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规模纪念《文通》的出版,追思《文通》的作者。
有关纪念《文通》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格调:有褒有贬,有表扬有批评,有肯定有否定。差别只是天平向哪一端倾斜——是三七开?是四六开?还是对半开?对《文通》和作者的赞誉之处有:它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法书;它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我国语言,特别是古汉语的特点;收集较多古汉语语料,举例达七八千;介绍新的研究方法,如对比和规律;语法描写与修辞功能相结合;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后继者提出了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者具有科教兴国的爱国情怀,等等。评价最高的称它为“一部开创性的不朽之作”。(张清常,见王海,1991:1)对《文通》和作者垢病之处有:《文通》削足适履,模仿照搬西洋语法;忽视汉语语法的特殊性;厚古薄今,只引用韩愈以前的语料;引书粗疏,有多处引证错误;缺乏历史知识,追求恒古不变的语言规律;从意义(概念)出发研究语法;个别偏激文章,还给作者带上“封建文人”、“反对改革”的帽子。
1983年,《文通》作为《汉语语法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曾为该书和丛书分别作序。吕叔湘先生特别提到他不是把《文通》“当作考古学标本向读者推荐的”,而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今天,当我们集会纪念《文通》发表一百周年之际,吕叔湘先生的这番话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即我们今天还可以从《文通》学到些东西。本文的用意便是如何加深我们对《文通》的认识和消化,包括与前人意见相左者。
1.引进与模仿不是缺点
如上所述,《文通》的一大缺点是不顾中国国情,引进了西洋语法。其理由是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因而汉语的传统是训诂学,于是也没有发展语法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次,汉语对于语法学的讨论早于《文通》。
我认为,引进本身不是一个缺点。这是中国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不论是20世纪末的今天,还是19世纪末马建忠所处的时代,奉行闭关自守,以天朝为中心,或以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之灯塔,都不利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现代化。语言学科也不例外。一个民族,除了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之外,总是需要了解、引进和学习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此基础上,加以消化和融合,使本民族的文化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若干年的结果。在这个发展的连续体中,先走的人多搞一些引进,后跟的人加以改良和创新,科学的高峰就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之上攀登的。因此,我同意季羡林先生对现代语言学三个时期的划分,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末为套用期,以马建忠和黎锦熙为代表;3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引发期,以王力、吕叔湘、丁声树、张志公等为代表;70年代末至现在为探求期,以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胡裕树、张斌等为代表。没有套用期,何来引发期?没有引发期,何来探求期?如果我们采用历史发展的观点,便会认识到《文通》起到了应起的作用,而不会苛求于它。
至于在《文通》之前,中国是否已有了自己的语法学,一些学者所做的考证告诉我们,周代的《史籀篇》、秦代的《仓颉篇》、汉代的《急求篇》等都是传授文字之作。清代刘淇的《助字辩略》和稍后的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主要就作为语法成分的虚词作了较多研究,还不能称为语法之作。(朱林清,1991:4)反之,肯定马氏这一开创之功的大有人在。如“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梁启超,引自张万起,1987,下同)“中国向天文法之学……自《马氏文通》出后,乃始知有是学。”(孙中山)“中国人说了几百万年的话,并且作了几千年的文,可是一竟并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文法。直到1898年,马建忠先生底《马氏文通》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古话文的文法书。”(刘大白);“中国的系统的语法,从《马氏文通》创始。这部书无疑是划时期的著作。”(朱自清)(以上转引自张万起,1987)
2.是单纯仿效,还是有所创造?
对《文通》诟病最甚之处,是认为它照搬仿效拉丁语法,缺乏新意,这样的批评在今天看来不够公平,有些过头。我同意王力先生的意见:“马氏以后,有许多人都批评它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转引自张万起,1987:413)
首先,照般不是马建忠的真实思想。马氏谈到对编写《文通》的指导思想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后序)这里,马建忠并无“华文=西文”的想法,也无西文的语法学可完全套用于华文的语法学的想法。
正因为马氏坚持了“求所同所不同”这个基本出发点,他提出了西文所没有的“助字”这个词类。“凡虚字用以结煞字于句读者,曰助字。”(526页)对其功能的描写为,“所谓助字者,盖以助实字以达字句内应有之神情也。”他特别说明这是汉语所独有的,“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536页)我们知道,拉丁语法没有助字这一词类,只是在动词类下有一个助动词小类,可见马氏并没有盲目照搬拉丁语法。
马氏结合汉语特点所提出的九个字类,即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介词、连字和叹字,对分析汉语是基本适用的。正如吕叔湘和王海所评价的那样,“这九类字的划分大体上是合理的,发展到现在,除把‘字’改为‘词’,也还没有什么大变化。拿现在通行的分类来比较,只是把数字从形容词(静字)中分出来,单独成为一类;增加了一类量词。”
3.语法术语和元语言
马氏把汉语分析成九个字类,在认识上突破了故人的实字和虚字之分,是一个大进步。这反映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法的诞生。这不仅仅是多几个语法术语少几个语法术语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解剖。虽然马建忠不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对语法术语已能从元语言的高度加以认识。元语言(metalanguage)“指的是用较高层次的一种语言描写研究的对象”,(Crystal,1980)这就是说,元语言是用来描写讨论语言的语言。没有元语言,就谈不上现代语法学。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要讨论汉语语法,便首先要有一套讨论汉语语法的元语言。正如马氏在《文通》里开宗明义地指出的那样,“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名义之所在者,曰界说。”正因为马氏采用了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相当于今天的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讨论传统的实词,采用了介字、连字、助字、叹字(相当于介词、连词、助词、惊叹词)谈论传统的虚词,我们对汉语词类的认识终于突破了实词和虚词的局限,这不能说不是汉语语法学的一大进步。
有人认为,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我们的祖先没有词类的概念,一样说话,一样写文章,因而不需要区别词类。如果按这个意见行事,那么我们对汉语的认识只能是仍停留在“古经藉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文通:例言》)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马氏使用的元语言借鉴于拉丁语法,不合汉语传统。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没有说明,传统的语言经籍中在句法学方面,除了实字和虚字外,还有哪些传统?也没有说明我们在即将告别的20世纪开创了哪些完全摆脱拉丁语法的新的传统?这些传统,是否足以担当起对汉语的描写和解释?这里,又涉及到学术研究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我们知道,英语语法也是仿效拉丁语法建立起来的,虽然拉丁语法的某些元语言及相应的规则不完全适用于英语语法,英语语法在整体上还是得益于拉丁语法的。我还认为,当某些标准或元语言在国际上被接受,有共同认识,并在实践中基本上行之有效后,再去讨论要不要用国产的传统的标准(具体说,实字和虚字)去替代这些国际上公用的标准或元语言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国际上公认的公历是以未经考证核实的基督教的耶稣诞生年份计算的,尽管有不合理、不科学之处,但假如我们不顾这在国际上已经公认的纪年方法,硬要恢复“光绪××年”或“民国××年”的历史传统或民族传统,只能增添交际中的麻烦。或者,让我们国家领导人个个脱掉西服,穿起长袍马褂出现在国际场合,总有与时代格格不入之感。如果我们大兴高俅和皇上玩过的中式足球、废贝利和马拉多纳头项脚踢的现代足球,该多么大煞风景!由此可见,马氏对元语言的讨论为我国20世纪的汉语语法(对马氏来说,是古汉语语法)的讨论奠定了基础,意义重大。尽管马氏对某些汉语词语的归类有不当之处,或者所介绍的“次”类用处不大,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研究讨论中逐步澄清。但没有语法术语或元语言意识,人们根本不具备对语言进行抽象思维和概括的有效工具,那我们对汉语的认识只能停留在“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的模糊阶段。
4.对汉语研究分类方法的认识
季羡林先生和邢福义先生把《文通》之后一百年对当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分成三个时期,即套用期、引发期和探求期。这是大致的粗线条的分期。某一学者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上有时会突出套用,有时会突出引发;有的在套用过程中志在探求,有的在探求过程中也会仰仗套用,这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王力和吕叔湘在后两个时期中都是代表人物。以马氏为例,在进行拉丁语法和汉语语法对比时,在模仿拉丁语法建立汉语语法时,也会迸发出探求的激情。
拉丁语法是按词语的形态变化来确定词类的,如名词有性、数、格的词尾变化,动词有人称、数、时态的词尾变化,等等。《文通》作者认识到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因此另辟蹊径,着眼于按成分排列规则来区分词类。我们可从《文通》找到不少如下绝妙的描写:
——“余”字用于主次与动字后宾次者居多,若偏次,有间以“之”字者,而介字后宾次则罕见。(44页)
——询问代字凡在宾次,必先其所宾,其不先者仅矣。此不易之例也。(71页)
——凡状者,必先其所状,常例也。(227页)
——凡字之有数义者,未能构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矣。(23页)
——“所”字常位领读,或隶外动,或隶介词,而必先矣。读有起词者,“所”字后之。(60页)
我们知道,对词类的划分标准,除了拉丁语法所开创的按词语形态变化作界说外,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是结构主义倡导的排列(arrangement)与分布(distribution)法。就句法分析而言,分布分析要标出较大的语言单位里较小的语言单位出现的位置,如一个句子中词的分布。(Crys-tal,1980)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到,马氏的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萌发出分布分析法的幼芽。当然,马氏的方法是草创的、不系统的,但他这一思想火花的出现终究比美国描写主义的分布学说早了30多年。
同样,马氏既然着眼于参考词语分布作词类的界说,必然要考虑到词语的结构关系。马氏说:“文中遇有数名连用而意有偏正者,则先偏于正。”(27页)这里所说的也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偏正结构。又如,马氏谈到“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反以言起词所有之动静者,曰语词。”(24页)从他所举实例看,在“孔子行”句子中,“孔子”为起词,“行”为语词,这非常接近于今天的主谓结构,至少说明了语言中不同成分存在组合关系。
通过一定的结构关系,又可以考察词类的异同,如他引《韩贾谊传》中的一段文字:“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吾危,故吾得与之皆安。”(46页)马氏指出,“彼”两句两用,但第三句易“彼”为“夫”,这可作为“彼”与“夫”同义的明证。马氏在这里虽然采用了传统训诂学的互文见义、对文互举的论证方法,多少接近了现代的结构分析法,其中既包括组合或结构的概念,也包括聚合或选择的概念。马氏的专著发表于1898年,而索绪尔的组合与联想关系是在1916年才正式发表。马氏的论点虽然没有索绪尔那么明确和系统,但19世纪末在认识上能达到如此高度,殊为不易。
马氏对词类的认识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如上所述,拉丁语法是从词的形态变化来区分词类的,马氏一反旧制,大胆提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名,当知其上下文义何如耳。”(24页)这里,马氏首先表达了内容决定形式,语义先于词类的功能主义观点。其次,一个词可以表达多种语义,因而可以属于多种词类。再次,由于语义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步扩展的,一个词最早的词类形式可认为是基本词类。在《文通》中,马氏采取“假借”的提法来解释词类转化的现明,如他举《汉张敞传》一例,“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书不能文也。”(34页)句中的“精微”和“微眇”原为“静字”(形容词),今假借为“通名”(普通名词)。又如,《史冯道传》有“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同上)一句话,其中的“饭”字可作动词。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文通》中俯拾皆是。有人说,马氏的“词无定类说”和“词类假借说”,是矛盾的,我认为并不如此,两者是互为补充的。“词类假借说”主要阐明一个词类在一定条件下可假借为另一词类,而“词无定类说”则旨在说明,某个词语并非永远属于某个词类,一成不变。把马氏的“词无定类说”理解为词语不分词类,我认为是曲解了马氏的本意。再者,如果马氏真的认为词语是不分词类的,那他就没有必要把汉语词语分为九类,也没有必要写《文通》一书了。
这一现象在国外也不时发生。1959年版的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中的regardless of 被看作是副词,在1989年版的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中已接受为介词,如He continued speaking,regardless of my feelings on the matter。1959年版词典对Must is for kings,And low obedience for low underlings—例中的must是这么解释的:“动词Must作名词用”,这与马氏的假借说是一致的。在1989年版词典中已界说must在非正式用法中为名词,如His new novel is a must for all lovers of crime f-iction。由此不难看出,马氏早在1898年就观察到了词类转换现象,并提出了对词语重新定义分类的看法。从国内看,我国语言学著作中或坚持词语只能属于一个词类,不提假借和一词多类;或者走另一个极端,避而不提词类,以语感代替科学分类,这对科学研究和语言教学毕竟是不方便的。
5.在语言学领域中的超前意识
《文通》是在19世纪末写成的。作者在建立汉语语法学时所持观点,反映了他对20世纪语言学研究方面的高瞻远瞩,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从事语言学研究工作的宝贵启示,可以说具有超前意识。
马氏正确地揭露了一项事实,在语言教学中有些老师对自己所传授的内容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他说:“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且同一字也,有弁于句首者,有殿于句尾者,以及句读先后参差之所以然,塾师固昧然也。”因此他反对在语言教学中“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10页)在最后一节,马氏看到搞学问既有“可授受者规矩方圆”一面,也有“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一面,这就是说,他既肯定了文学创作中属于个人思想奔放的文气或文心,也肯定了讲究规律性的语法。掌握了语法,有助于了解文学创作。不能认为文学创作的某些方面难以用语法解释,把原来存在的语法也束之高阁。这个具有论述语言系统与言语关系的观点是可取的。
马氏在总结语言规律时是实事求是的。他不是单纯追求规律的百分之百的精确性,而是采用了概率法,说话留有余地。我们从《文通》中可找到不少这样的表述,如:
——“之”字单用,宾次者其常。(47页)
——“之”字有为主次者,经籍中仅一二见。(47页)
——“何”字单用与宾次者,为止词则先於动字,为司词则先於介字,不先者鲜矣。(76页)
——经生家误以“夫”字为提倡之连字,盖未知夫“夫”字之位,在句首者其常,而在句中者也数见也。(80页)
——表词后乎起词者,常也;先之者,惟永叹之句为然。(129页)
马氏在立论中采用概率法,在国内外都是领先的。在西方对语言进行概率的描写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被较多学者接受,特别是功能主义语言学派,如系统功能主义学派的韩礼德和美国功能主义的吉汶(Givon)。马氏采用上述描写方法比这些学者早了五六十年。马氏采用概率法进行语言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它符合语言“约定俗成”的固有特性。用马氏自己的话说,“至同一字而或为名字,或为别类之辽,惟以四声为区别者,皆后人强为之耳。”(35页)“后人强为之耳”意味着语言规则不是先天的,是后人约定的。二是正如马氏自己所说的,“则以字形字声,阅世而不能不变,今欲於屡变之后以返求夫未变之先,难矣。”(9页)这是因语言的历时的不断变化,日久沉淀所致的困难。如果再考虑到语言在某些地区和时间发生变化,在某些地区和时间不发生变化或发生另一方向的变化,则更难做到“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这一要求。
这里,我顺便回答对马氏的一个批评,即说他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把语法规则看作“历千古”而一成不变。其实,马氏最本质的思想是强调研究规律,不论是语言,还是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一切现象,都要研究其规律,知其所以然,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错的。其次,如果把“或少变”三字仔细品味,加上前引“则以字形字声,阅世而不能不变”等观点,那么马氏是接受语法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变化的观点的。考虑到当代乔姆斯基等对普遍语法的研究,马氏的说法不算过分。
《文通》的主旨是科学地解释分析古汉语语法,属句法学,但马氏的视线有时超越了句法学,注意到句法学和音系学的联系,注意到语言的多层次和互相关联现象。虽然在古籍中,“字同义异者,音不异也”。马氏注意到,后人为了便于交际,以四声之别来解决字同义异的问题,如“王”字作名词,读平声,但在“王此大邦”中作动词,则读去声。(35页)又如,“中”作形容词时为平读,但在“百发百中”一语中为动词,读去声。(196页)马氏研究的这一内容基本上属于西方的形态音位学(morphophonemics)或形态音系学(morphophonology)的研究范畴。马氏的观察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
一些专家提到马氏对汉语语法的讨论,时与修辞相结合。我认为,尽管马氏在《文通》中强调专论句读,以及句读与字的关系,他已具有一定的语篇意识。同样是引用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般人只引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一句话为止,马氏则不吝笔墨,继续引用了“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10页)其用心是要我们既了解字句是篇章的基础,也了解篇章决定语言使用者对字句的安排和选择。这表明马氏在研究句子语法的同时,内心中已有语篇语法的轮廓。在《文通》中也有不少实例可证,如他以《史滑稽列传》中的“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之礼葬之。”为例,说明“所”字和“葬”字后的两个“之”字都是代词,(41页)其先行词要在第一句话中查找。这一分析明显地跨越了句子语法。马氏在73页还列举了不少“是”的用法,如《孟梁上》中的“是乃仁术也。”一句中,“是”指前文提到的以羊换牛之事;《滕上》中的“是率天下而路也”一句中,“是”指前文中的“徐行之道”;《左哀二十五》中的“是食言多也”一句中,“是”指前文中的“郭重”这个人物。至于马氏常在各卷之后,以整个语篇作为语料进行分析,指导读者如何操作,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如果我们考虑到当代语言学中语篇分析还是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马氏的远见卓识更令人钦佩不已。
6.《文通》能否一通到底
上面讨论的概率法也引发我们讨论对《文通》的一条意见,即《文通》里有一些例句,“作者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吕叔湘,1980)吕叔湘先生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文通》的,他说:“《马氏文通》之可贵,就在于它充分提供矛盾,我们现在谈《文通》主要也是为了揭示矛盾。通过这一揭露,更深入地探索这些矛盾的根源,了解问题的实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研讨。这样就有可能把我们引导到解决汉语语法体系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去。《马氏文通》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许是马氏始料所不及的吧。”(孙玄常,1984)
所谓研讨,实际上是通过《马氏文通》所揭示的问题来回答,今后汉语语法的研究将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问题。意见有多种多样,有的认为跟着《马氏文通》走一百年,此路不通;有的认为回到一百年前的时代,不合逻辑;也有的倡导积极探求新的理论和方法。
我认为,要使汉语语法有新的突破,“闭关自守”不可取,应使民族传统和国外先进理论相结合。与其一技独秀,不如百家争鸣。那么,马氏的一派之言,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认为,在方法论上,综合与分析,演绎与归纳,应取得辩证的统一。马氏引入分析的方法没有错,引入比较的方法也没有错。现代语法学,如果不用现代的方法,只能回到训诂学的老路上去。
我认为,不论采用哪一种研究方法,对自己的目标都要有一个现实的估计,那就是充分认识到“通”与“不通”是相对的。对语言学和语法学来说,很难说存在一个十全十美的语言学或语法学理论。不论是历史上的拉丁语法、思辨语法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或是当代的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或是国内正在探求的各种模式的现代汉语语法,都存在“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就是现在也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分析”之弊病。(吕叔湘)例如,《文通》问世后,除按照《文通》格局研究的修正派外,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便有力图推翻《文通》格局的以刘复和金兆梓为代表的革新派,至今也有80年了。他们并没有比《文通》取得更大成就。道理很简单,在交际中产生的自然语言既有合乎逻辑的一面,也有如上所说的“约定俗成”的一面,因此,要探求—“通”到底的规则确是很困难的。为此,对一个语言学理论或语法理论的评估,主要应看它能说明或解决多少语言现象,看它大面上的问题能解决多少,以及哪一种方法解决的问题多、遗留的问题少。
总结以上的讨论我想说明,马氏及其《文通》是时代的产物。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列强蚕食、政治腐败的非常不利的形势下,我国的精英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掀起全方位的改革浪潮。有的革命,有的改良,其共同点是都意识到了维持现状是没有出路的。就语法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过程而言,也不例外。这一历史事实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马建忠是时代的代表,在他身后有早期的陈承泽、金兆梓、黎锦熙、杨树达等,也有后来的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驱。我们纪念马氏和《文通》,实际上也是回顾总结这代人的业绩。其次,研究汉语语法要考虑汉语的特点是应该的,但完全脱离或否定国际上语言学理论的进展和科学方法的观点则是狭隘的。成功者往往能妥善地摆好两者的关系。马建忠如此,赵元任、罗常培、高名凯、王力、朱德熙、吕叔湘也如此。所有这些先生,似乎对西洋语法了解颇深。
标签:马氏文通论文; 吕叔湘论文; 文通论文; 语法分析论文; 中国语言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汉语语法论文; 读书论文; 马建忠论文; 语言学论文; 语法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