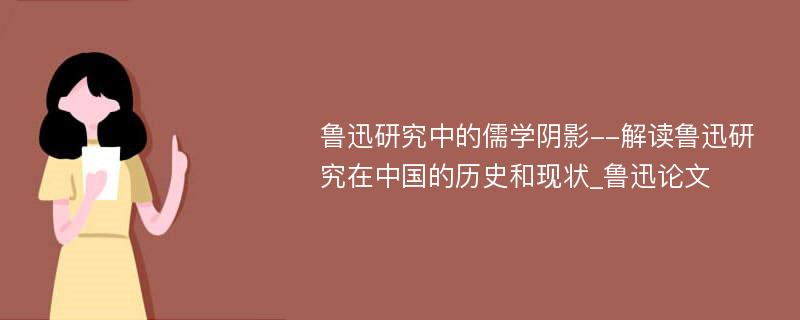
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对于《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儒学论文,中国论文,阴影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中国的鲁迅研究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一研究领域始终充满着各种思想观点的矛盾乃至斗争,从来都没有平静过。如何总结长期以来鲁迅研究的历史,开辟鲁迅研究的新前景,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研究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王富仁先生在1994年《鲁迅研究月刊》上连续发表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计十一篇)从新的时代高度和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全面、深入地梳理并剖析了鲁迅研究的历史,并对今后的鲁迅研究作了预测。这是鲁迅研究的再研究课题中取得的突出成果。
王富仁把迄今为止的鲁迅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从开始到1927年为第一个时期;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为第三个时期;从“文革”结束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有各自的成就和突破、失误和局限,王富仁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对这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他对这四个时期鲁迅研究的系统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每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有一些派别明显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儒学的影响贯穿了整个鲁迅研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是王富仁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他的重点分析所在。本文只是试图对王富仁的系列论文作这样一种解读,并按照他的分期顺序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无疑是最占有支配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在二千多年来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控制、主宰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和命运,儒学文化因子已经深深地铸入国民的深层心理结构,成为支配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潜在意识契机。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革新,但是,思想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整个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儒家文化因子的隐性传承也无法从根本上割断。它依旧支配着20世纪人们的心理和灵魂。这其中当然包括相当的一部分鲁迅研究者,他们在研究这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正统儒学的思想家时,自身却往往陷入儒学的阴影之中,虽然不少研究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有的研究者甚至还高举着反传统、批孔子的旗号、贴着新思想的标签,骨子里却是认真地贯彻了正统儒学的宗旨。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学的阴影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地给各阶段的鲁迅研究带来了思维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迷误。
(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使鲁迅研究无法上升到研究的高度。
“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是对文学作品或某种思想学说的内涵与外延的阐发,因而传统的个人道德的赞扬和否定都不可能上升到研究的高度”〔1〕。 而鲁迅研究中第一个时期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对立派和第二个时期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在进行鲁迅研究时都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中,对鲁迅及其杂文作出了歪曲的评价,进而走向了对鲁迅及其杂文的根本否定。
以正统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伦理与政治相结合,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它把调整封建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作为衡量人的唯一的、最高的和固定不变的价值标准,人的善恶美丑完全是以其行为是否符合这种规范为主要尺度的”〔2〕。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伦理道德的统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封建王朝可以更迭,而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伦理体系却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而封建伦理道德的总基础和总纽带是等级观念,它是以承认社会人的不平等权利为前提的。鲁迅引证《左传》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排列,认为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上由至高无上的皇帝一统天下,形成一个宝塔形的巨大网络,“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3〕。 他激愤地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弟, 还是依赖祖宗”〔4〕,“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厉害”〔5〕。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观念, 鲁迅是向来痛恨并给予无情批判的。因此,要求实现社会平等,一直是鲁迅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陈西滢和梁实秋等人却与鲁迅持着相反的态度。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北京学生始终未曾超越民主体制下法律的许可而表达自己的社会要求和意志,相反倒是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北洋军阀政府超越了法律许可的范围,用暴力镇压了和平请愿的学生”〔6〕。而陈西滢却沿袭了传统儒家的态度, 认为学生无权反抗学校和国家,而学校和国家则理应约束学生。按他的思维方式,胜利属于有权有势者,支持无权无势的学生争取自由的鲁迅自然也要在道德上受到否定。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是直接学习西方新思想文化学说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世界新文化学说是最有发言权的。然而,当他们带着新思想文化学说回到自己的国土时,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中的旧思想、旧意识又像幽灵一般缠绕着他们。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核心是文化精英意识,认为整个社会就是由他们这些少数的聪明而又有文化教养的人和广大的愚笨而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组成的,梁实秋就侈谈“聪明绝顶的人”和“蠢笨如牛的人”,反对“男女平等”、赞同“贤妻良母”式的教育,这显然贴紧了儒家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他们的社会理想是求安定、讲秩序,反对广大群众由于经济政治压迫而进行的反抗斗争,这显然又暗合了传统封建专制主义“不撄”的理想。这样,“他们接受的新文化反而带上了严重的旧文化性质,他们在西方接受的文化教养反而有了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最新的反而成了最旧的,最先进的反而成了最保守的”〔7〕。 难怪鲁迅要感叹:“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8〕。在这种情况下, 具有保守主义本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对要求实现社会平等和建立现代社会观念的鲁迅的态度自然是否定无疑的。
无法摆脱传统儒家思想束缚的陈西滢、梁实秋等人与鲁迅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而在传统等级观念和封建礼教的制约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心灵和情感是难以进行交流的,正如鲁迅所说的“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以相印”〔9 〕,“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10〕。承袭传统儒家伦理观念的陈西滢、梁实秋等人站在“高墙”的另一侧,当然无法理解被压迫者、无权势者的痛苦,也无法理解鲁迅的痛苦,更无法进入鲁迅的作品和精神世界,体验鲁迅的人生感受。根本价值观念不同,又不在理解的基础上思考研究客体,使得他们离开了从社会人生的整体意义感受鲁迅作品的有效角度,而仅仅停留在个人道德的评判上,当然难以做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文学或思想的新发现,也难以对鲁迅作品的潜在意义做出独立阐释,更难以上升到一个研究的高度。他们是以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阻死了自己的研究之路。
(二)独立性与主动性的丧失阻碍了鲁迅研究取得探索性的突破。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一阶段的国内鲁迅研究是在一种文化整合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标志着中国马列主义文化思想的胜利,各派鲁迅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被整合起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一切言论的最高指导方针,鲁迅的思想及创作的历史价值只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体系中分析和评判。这样,在权威理论话语的支配和压力下,研究主体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无法在鲁迅研究中取得探索性的突破。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以正统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束缚和钳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被迫沉溺在封闭和禁锢的精神牢笼中,完全丧失了自由思想与活动的权利。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个体的分量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反映到社会政治伦理中,又表现为社会对个人、个性的无情打击和扼杀,个人只不过是实现政治、伦理价值的一种手段。“五四”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其主要标志就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的确认。“五四”文化先驱们极力张扬个性、鼓吹个体,希望广大民众从专制主义的精神牢笼中解放出来,确定自己作为“人”的独立价值和自主意识的存在。鲁迅鲜明地指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1〕,把人作为高度自觉的主体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要求“人各有己”、“朕归于我”〔12〕;认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3〕,鲁迅把“人国”理想的希望寄托在“自觉至,个性张”的基础上,这与以人为中心的新文化观念的意识形态是相一致的。鲁迅所追求的思想启蒙,正是在中华民族进入现代社会后如何摆脱中国固有文化的束缚,重新意识自我和人生的问题,是一个警醒人们如何进行自我的人生选择和文化归位的问题。他急切地渴望和热烈地呼吁出现“真的人”〔14〕,“完全的人”〔15〕和“觉醒的人”〔16〕,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对人们精神的钳制和摧残。
然而,鲁迅关于确立“人”的自觉意识和独立价值的呼声尚未得到实现就又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和禁锢,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之后,并在“文革”达到了极致。“文革”的指挥者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高呼着“批孔子”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削弱。相反,他们是利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推行政治家个人的权威,在新的形式下培育了国民的奴性性格。这无疑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接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的主旨,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一种涂上了洋化色彩的翻版。在文化整合运动中推行的一元化政治思想形成了低沉的文化天空,而在低空中从事鲁迅研究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精神、意志都受到了严重的扼杀与钳制,在研究活动中丧失了研究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又一次陷入了儒学的阴影。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评价先于感受。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对作品有所感受,有所理解,然后才能进入研究和评论的阶段。文学批评是观念的表达,但却不能从观念出发。然而,这个时期却有相当的一部分鲁迅研究者违背了这种文学研究的客观规律,他们不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把对鲁迅作品的独立感受与理解作为研究的基础,而是让一种非自我的观念先入为主,以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作为立论和评价的根据,以下级服从上级的姿态研究鲁迅。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鲁迅的评价越来越高,赞美之词越来越多,研究活动走向了非自我化。第二,理论代替思考。任何一种理论、思想学说都是人们认识和探索世界的工具,一种思想不论多么伟大,都不能代替个人的独立思考。但是在领导意志和服从意识的支配下,这个时期的不少鲁迅研究者却放弃了理论运用的主动性,使个人的情感和思考都隐在了权威理论的背后,他们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考察作家的创作活动,而是把它当成了诠释各种现实政策要求的理论依据,用毛泽东文艺思想代替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机械转述者和宣传者。第三,总结代替探索。由于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维和理论运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鲁迅研究者只是以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高体现的毛泽东思想衡量鲁迅思想及创作的价值,一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有价值的,而不符合的就是没有价值的。这样,他们的鲁迅研究也就成了总结性的、同一式的,而不是探索性的、开拓式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往往评价多于分析、赞颂多于论述,缺乏理论上的开拓。鲁迅研究被引向了对权威理论支配下的流行价值观念的简单诠释,丧失了对现实文化的批判性考察。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任何研究活动,其目的都在增益人们的认识。但如前所述,由于研究主体独立性与主动性的丧失,这个时期鲁迅研究的认识职能消失了。研究者在对权威思想理论和革命政治领导的绝对服从中失落了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责任,他们对内看不到一个真实的自我,对外看不到一个真实的鲁迅,“所有的研究活动似乎都是为了证明一个与自我的实际人生追求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是非,而这种历史的是非却与他们实际人生经验中建立起来的是非观念毫无关系甚至取着对立的形势”〔17〕。这种研究活动强化了政治性而消解了学术性,把研究领域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是他们的思想形式束缚了自己的探索之途,使鲁迅研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三)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影响。
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是在中国大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潮流中重新起步的。灾难性的“文革”的结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返回自我”的历史条件。鲁迅研究者们开始努力跨越凌驾于自我以及凌驾于鲁迅之上的权威话语的栅栏,摆脱政治对学术的束缚和干扰,力图站在自己的思想立场上,对鲁迅的思想及其作品作出独立的阐释。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引进了西方大量的新思想、新方法,打破了鲁迅研究的封闭局面,开拓了鲁迅研究者的视野。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中,鲁迅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但是,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并没有从此散去。在思想解放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的促成,中国固有的各种传统思想文化又在社会上活跃起来,掀起了“国学热”、“新儒学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无疑要对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产生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文化还原过程中,不少鲁迅研究者又跌入传统文化的旧圈子,再次给鲁迅研究带来局限。王富仁把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史称为文化整合期,把从“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化史称为文化还原期。在新时期的文化还原过程中,一些二、三十年代鲁迅研究派别的观点复活了,而鲁迅研究活动也随之再次受到了传统儒学的羁绊,其突出表现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和青年浪漫派的文化思想的复活。如前所述,三十年代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在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学说后,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又重新返回到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之中。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在新时期复活后,这种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出现了。新时期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传承者虽然走出了权威理论和流行话语的框范,在对鲁迅作品的艺术分析和鲁迅前期思想的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再次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他们的研究文章往往表现出肯定鲁迅的前期,否定鲁迅的后期;肯定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否定鲁迅的杂文;肯定鲁迅的才能,否定鲁迅的道德。这些都没有走出其前辈的局限。主要由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青年浪漫派在二十年代就热衷于追逐最先进的思想目标,但是没有独立的文化空间,无法确定自己的文化原则,往往依附于别人的价值标准。这就决定了他们只有通过两种方式意识自我价值,“一、把自我的价值寄托在一个公认的最伟大的人物身上;二、用社会公认的标准否定掉所有的权威,把自己提高到所有以往权威之上”〔18〕。二十年代,他们以鲁迅祭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战旗;在“文革”期间,他们又把毛泽东、鲁迅当作圣人、完人供奉。在“文革”的绝对化的个人权威告终后,各种不同的鲁迅观点浮出水面,青年浪漫派的文化思想也实现了还原。新时期的青年浪漫派在社会上公开表现出了一些对鲁迅的冷嘲式的否定,这种否定在表面上虽然与“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不同,但深层实质却是一样的,“个人崇拜与否定一切权威实际上是出于同一种文化心理”〔19〕。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新时期对鲁迅的否定与在“文革”期间对鲁迅的崇拜一样,都有传统儒学的根源。新时期进行鲁迅研究的知识分子本想通过文化还原“重新返回自我”,寻找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契合关系,但是,上述两方面已表明,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文化还原中摆脱了“文革”中一元化政治思想统治的枷锁,却再次跌入了传统文化的旧圈子,他们在自救的同时也走向了自缚,历史让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连环套式的悲剧。
第二,“新儒家”的复兴带来了对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使鲁迅研究再次面临历史的考验。现代新儒家,是指“五四”以来形成的“以接续孔孟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为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融合西方哲学,谋求中国社会和哲学现代化的思想派别”〔20〕。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他们的思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旨向,认为唯有孔子的人生态度才足以解决中国人的人生问题,唯有以“孔子的人生”为基础,新文化才能有一个新的结果。新儒家学派一开始就抨击“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反对把封建传统道德规范说成“吃人礼教”。五十年代的新儒家学者徐复观认为“五四”思想启蒙的发动者们大都“浅薄无根无实”并“数典诬祖”,还认为鲁迅是个读书不多,成就甚微的“三流作家”〔21〕。八十年代中期,“新儒家”在大陆再次兴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获得了复兴。新儒家直接论及鲁迅的文字不多,但今天的鲁迅研究不能不注意“新儒学”。新时期以来,新儒家学者们继续批评以至否定“五四”激进的反封建道统和学统的文化革命精神,认为“五四反传统延宕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22〕,造成了文化虚无主义,并把现代社会的道德滑坡归因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五四”新文化是儒教的对立物,而鲁迅又终其一生在做着儒学的批判和清理工作,因此在“新儒学热”中,作为“五四”经典的鲁迅思想及其著作难免要受到非难。新儒家学者余英时就指责鲁迅悲观、世故、复杂、刻薄,是“高度非理性”的人物,并攻击鲁迅作品“在文体风格上表现出一种流氓文风”〔23〕。这些歪曲、丑化鲁迅的观点已经引起了鲁迅研究界的注意,1995年5月以来, 《鲁迅研究月刊》开辟了“五四精神与中国文化”的专栏,研究儒学的历史作用,“新儒学”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由鲁迅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来讨论“新儒学”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参加讨论的多数学者都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儒学的历史作用,批驳了某些新儒家学者对鲁迅的歪曲、丑化和诋毁。这些都表明“新儒学热”的冲击无法动摇鲁迅和“五四”新文化的历史地位,鲁迅研究又一次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3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一直呈现着复杂的格局,反传统与复古主义交织在一起,如藤缠树般难解难分;新思想与旧观念错杂在一处,也如明山暗水般难以分辨。在这样一种文化格局中,正统儒学文化因子的隐性传承一直无法割舍。鲁迅在探讨“中国进化的情形”时认为“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24〕。用这种分析来说明中国的文化现象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旧文化,但同时各种盲目称颂儒学(包括各种新儒学)的思潮也不断出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已牢固地根植于人们的精神中,“并不废去”,且时时“反复”。陈旧的精神与传统的思想成了束缚新时代的幽灵,鲁迅研究也因此一次又一次也笼罩在儒学的阴影之下。
鲁迅作为中国伟大转折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宝库。而我们研究鲁迅的目的是吸收鲁迅的思想成就,并超越鲁迅,但走过了八十多年风风雨雨的鲁迅研究并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在“五四”启蒙运动中鲁迅始终以人的精神解放作为出发点来考虑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对造成“畸形国民性”的封建主义旧思想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他批判的矛头又致命地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核心——儒家文化。他把以正统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对广大人民的野蛮和残暴的蹂躏概括为“吃人”的势态,激愤地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并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25〕,认为不扫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根子,“国民性”的改造无法实现、新的现代化观念也无法树立。“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26〕。在中国思想史上批判儒家正统文化的任何一个思想家,都远没有鲁迅这样的认识深度。然而,鲁迅一直是个孤独的“呐喊者”,他早年就体会到了“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27〕的痛苦。他不被同世人所理解,也难于被后世人所理解,鲁迅所批判的文化现象几乎都在他后世的社会舞台上重新上演,而他所批判的传统儒学的痼疾又时时缠绕在他的研究者身上,干扰甚至破坏了鲁迅研究的进程。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鲁迅的孤独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化的孤独,鲁迅的痛苦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化的痛苦。对于“五四”来说,思想启蒙仅仅是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整个民族改造“国民性”和走向现代观念的思想革命还有一条漫长的文化苦旅。正统儒家学说中适应和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整个思想体系摧残了国民的精神、造成了畸形的“国民性”,无疑是应该彻底否定、批判的,遗憾的是直到当前,学术界和文学界仍有不少人在提倡新儒学。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儒家学说中也有一些积极的东西,而且鲁迅对民族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概否定的,他曾明确提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传承,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28〕,鲁迅本人也继承了孔子身上的一些优秀品格。但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继续完成“五四”思想启蒙的使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有形和无形的统治,而不是复兴儒学,寻找“国粹”。在当前以任何新形式去提倡和复兴儒家学说都是与时代潮流相逆的,封建主义的根子牢牢地扎在人们的头脑中,正统儒学文化的因子深铸于国民的深层心理结构,这是阻碍我们整个民族前进的历史惰性力。长期以来,这种因袭的惰性力已经把我们的民族拖得太苦太累。今天,对于以传统儒学为核心的束缚国民精神的传统文化,对于死而不僵的封建主义,我们是唯恐弃之而不及,何需费力去恢复、去复兴、去寻根呢?而对于这些情况,鲁迅早有预见并深入进行解剖、反复阐述清楚了。如果我们的鲁迅研究者能领会鲁迅的精神,理解鲁迅的“呐喊”之声,吸取他总结的这些结论,尽快摆脱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阴影,进入同鲁迅一样的思想追求过程,我们的鲁迅研究才能少走弯路,整个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才能尽快走上健康之途。
注释:
〔1〕〔6〕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一),《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一期。
〔2〕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第31页。
〔3〕〔25〕《坟·灯下漫笔》。
〔4〕《坟·论“他妈的!”》。
〔5〕《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7〕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三), 《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三期。
〔8〕《花边文学·偶感》。
〔9〕〔10〕《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11〕〔13〕《坟·文化偏至论》。
〔12〕《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14〕《狂人日记》。
〔15〕《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16〕《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7〕〔18〕〔19〕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一),《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十二期。
〔20〕韩强《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评述》(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1页。
〔21〕转引自袁良骏《“五四”·新儒学·道德重建》,《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六期。原载《中国思想论集》及《续编》,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初版。
〔22〕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初版。
〔23〕参阅袁良骏《为鲁迅一辩——与余英时商榷》,《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九期。
〔24〕《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
〔26〕《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27〕《呐喊·自序》。
〔28〕《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标签:鲁迅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论文; 鲁迅研究月刊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梁实秋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