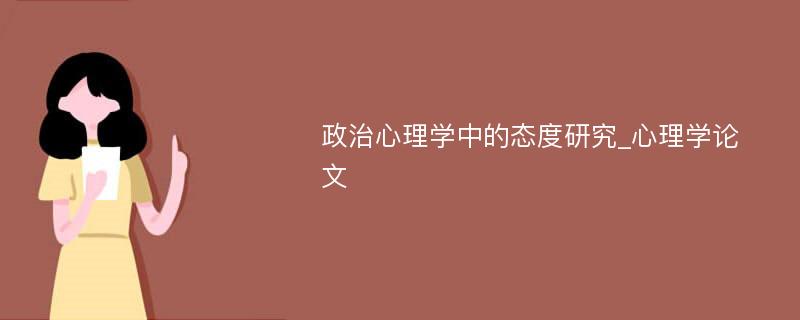
政治心理学中的态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中论文,态度论文,政治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1—0132—10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20世纪30年代晚期民意调查的出现使态度研究由社会心理学领域扩展到了政治心理学领域,也使态度研究真正从校园进入了现实政治生活。譬如对总统竞选中投票行为的决定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对人的因素的分析,如居住于农村还是城市、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宗教信仰等)。当心理学家将其注意力转向投票研究时,他们仍将研究重心放在态度方面,包括对候选人的态度、对政党的态度以及对竞选问题的态度,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蕴藏在这些态度中的信仰。不管是受惠于心理学还是社会学,调查研究为心理学中的政治态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描述性实质内容,从而在其研究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由于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有关态度研究的这一历史与学术渊源,深受社会心理学影响的政治心理学对态度的界定往往借用社会心理学中对态度的界定。一些政治心理学家在探讨“态度”的界定问题时明确指出,由于政治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性,其注意力将集中于对态度本质及其过程的探讨,而不会着力于政治态度的政治性的一面。① 因此,从态度、社会态度到政治态度, 其概念内涵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在使用时所侧重的内容和方面有所不同。从政治心理学领域“态度”概念的引入来看,应该说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态度研究扩展的结果,而政治心理学领域中对“态度”的研究反过来又深化了社会心理学领域对“态度”的认识。
态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活动,是一个主观概念。对“态度”概念的界定,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领域中“态度”概念的界定,不仅包括对“什么是态度”的认识,还包括对“态度怎么样”作具体的分析。因此,对政治态度的研究不仅要在态度的结构和基础、态度的改变、态度的结果这三个领域展开,还应把态度的测量作为态度界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分析,以使对“态度”概念的界定更为精确。
一、态度的结构和基础
一般而言,态度的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态度的结构和功能基础,一是作为态度基础的个体差异。态度的结构和功能基础主要涉及态度的一些内在特征和重要影响因素,作为态度基础的个体差异则与作为态度这一精神活动和现象的主体的人有关。
态度的结构和基础作为态度研究的一个传统主题,与之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有关其内在特征和重要影响因素的研究,往往是在态度强度(attitude strength )的标签下进行的。② 态度结构具有一些重要的特征,如态度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态度的矛盾性(ambivalence)、态度的情感/认知基础(affective/cognitive bases)以及作为态度基础的价值与态度功能(values and attitude functions)。但是,对这些特征的认识则存在分歧。
关于态度的可及性,一些研究者认为,客体和评价间联系的强度对于理解态度的功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这一认识却受到了来自近期研究的挑战。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态度有时仅仅因为遇到态度客体而被自动激活(automatic activation),并且这一效应的强度随人们对客体态度的强度的增强而增强。这种看法同样也受到了诘难。因此,学者们寄希望于未来研究“澄清能够控制可及性在什么时候能或不能调整态度的自动激活的心理机制”[1]。在这方面, 将重复的态度表达用以控制客体与评价间联系的强度,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一个人表达其态度的频率影响着其态度的可及性,但却不会改变态度的其他特征。这一命题虽然得到了较大的认同,但潜在于这种影响的确切的机制及其普遍性还需要认真思考。与此相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分析了重复的态度表达导致可及性的条件。尽管态度问题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被感知的自我相关性(self-relevance)决定的,但有学者的相关研究却表明态度重要性随态度表达次数的增加而增强。
矛盾性(ambivalence)态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矛盾的, 是态度研究领域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些学者假设积极的评价和消极的评价往往是此消彼长的,但大量的研究文献却无法支持这一假设。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普遍存在的积极的评价反应和消极的评价反应之间的负相关的错误解释。对态度矛盾性的这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对态度进行计量时存在的一些缺陷联系在一起的。譬如,态度量表存在的有关指标设计的问题,无法使人们在有意义的维度上对态度进行细致的分析,无法获知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的不同态度的细微差异,从而使得对态度的认识产生重要的偏差。也就是说,态度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积极和消极之间发生变化是普遍的现象,如果称之为态度的矛盾就过于简单和不准确了。
态度的情感/认知基础(affective/cognitive bases)把态度概念化为具有情感/认知基础(affective/cognitive bases )是一种最流行的对态度据以确立的多种信息所进行的分类[1]。态度的形成虽然是态度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观评价,但这种评价的形成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态度主体的情感与认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情感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有时并不能被正经历某种情感状态的人所认识。
简单地说,情感(affect)是人们体验到的一种愉快或不愉快的心理状态。在态度的形成过程中,情感可能具有的决定作用经常被人们忽略,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的情感反应虽然为许多公开的判断和行为决定提供了基础,但却往往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情感与态度或判断之间建立了确定的联系,在有些情况下却没有。在政治心理学中,一般通过四个概念来考察情感对态度形成的影响:(1)对客体或客体的某一具体特征的评价; (2)对一个客体的情绪反应(emotional reaction);(3)心境(mood);(4)情感唤起(affective arousal)[2]。相对于情感基础,态度的认知基础比较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由于情感与认知经常联系在一起,使得对认知作用的考察也变得复杂起来。
在对态度基础的情感/认知分类之下,对与态度相关的情感和认知的恰当的度量在近十多年来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切。同时,在不同的领域中,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情感与认知的影响,也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问题。譬如,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高权威人格者主要受到符号信仰和既往经历的驱使,而低权威人格者的态度则主要是由传统的信仰和情感所决定的。[1] 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已经涉及影响态度的个体差异的问题。
态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活动,基本上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因此,它还被认为具有一些基因基础(genetic basis),即强调个体差异。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 随着可归因于基因要素的态度变化的增加,存在于记忆中的态度的可及性、态度对于一致性压力的抵制以及态度对人际吸引的影响也会增强。对态度的基因基础的研究是对传统态度理论的挑战,而后者强调的是作为态度基础的经历的作用(role of experience)。将基因因素作为态度的重要基础,解释了处于相同环境和背景(经历)条件下的不同个人之所以会有不同态度的原因,它注重的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但是,这一研究也存在重大的缺陷。首先,方法上的问题使得对态度的基因基础的精确估计与对环境基础的精确估计相互冲突;其次,缺乏被清楚地表述或由经验证实的中介过程。[1]
对态度的结构的研究已经构成了态度研究领域不可缺少和充满活力的一部分,也明确指出对态度的总体概括评价之外的其他特征如可及性、情感/认知一致性、矛盾性等方面所作的分析有利于增进人们有关态度的知识。
二、态度的改变
在态度研究领域,对态度改变的研究一直是研究者的兴趣所在。态度的改变与说服有着重要的关联,也与学习、认知过程、人格、态度本身的特点有重要的关系。其中,对说服沟通的研究构成了态度改变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政治心理学的态度研究领域, 实验态度研究(experimental attitude research)是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在这一思路下,研究者在经验概括(empirical generalization)和理论的相关性方面(relevance of theory )展开其研究。在经验一般化研究中,说服沟通(persuasive communication)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一沟通过程所传达的实际上是可能导致态度改变的影响因素,并在整体上呈现出影响态度改变的一个可能的过程。在这一研究中,说服者(The Persuader)、表达问题的方式(How to Present the Issue)、作为个体的听众(The Audience as Individuals)以及群体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Groups)都是态度改变的可能的影响因素。首先,在说服者方面,说服者是不是专家,其可信度如何,对说服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说服者所期望的态度改变幅度的大小,也对说服的效果具有影响;其次,在问题的表述方面,如果听者比较友好或只期望即时的即便是暂时的意见转变,那么你只需陈述问题所引发的争论的一个方面即可。如果听者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么你就要把争论的两个方面都提出来。如果将相互对立的不同观点次第提出,那么最后提出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等等。这些实际上涉及的是说服的技巧;第三,在作为个体的听者方面,说服者最想说服的人最有可能不在听者中间。同时,听者的知识水平决定着说服的有效性。要进行有效的说服还必须依据态度改变的情况而调整说服技巧,等等;最后是群体的影响。在这方面,个人的意见和态度的变化受到了他所从属或希望从属的群体的影响,个人会因符合群体的标准而受到奖赏或因背离群体的标准而受到惩罚,被他人知晓的意见比不被人知晓的意见更难以改变,等等。[3]
实验态度研究中对理论相关性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与态度的形成和变化相关的理论的研究。由于态度首先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态度的改变也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因而学习理论(theories of learning)就成为使态度改变概念化的一个主要途径。态度因而可以被看作体现了信息处理的结果,并影响个体对其周围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认知过程理论(theories of cognitive processes)是有关态度改变的假设的第二个来源。态度作为对心理客体的有组织的倾向,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态度变化的第三种理论取向的根源是人格理论(personality theory)。这些不同的理论取向涉及有关态度改变的不同变量,因而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4]
即使是在态度改变的研究领域,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也在发生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者关注的是对说服的有利因素或不利因素的分析;其后,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些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基本过程,其着眼点在于态度变化的变量是在发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作用,以及变量使信息处理具有倾向性的方式。
有关说服沟通的研究是对态度改变的心理学所做的大量实验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尽管还存在诸如没有对抵制变化的心理惯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及研究者没有对理性争论的内在特征进行实验性审视等缺陷,但此类研究对政治心理学的贡献却是不容忽视和否定的。对态度改变的相关理论的研究,虽然在理论解释能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却与说服沟通研究一起构成了态度研究三大传统研究领域中态度改变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对政治心理学而言,重要的是,它为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说服和被说服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和准备。
说服充斥着政治生活,是政治的核心。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家说服选民支持一项政策选择,利益集团为其目标和计划说服大众和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大众中的一些成员为使其他成员在请愿书上签名而进行说服,等等。在政治生活中,说服和被说服是非常自然的事。
政治说服是民意(public opinion)的一个重要动力。在信息社会中,民意和公众的态度无可逃避地受到了无孔不入的电子传媒的影响,而其中政治精英对公众的政治态度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政治精英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意见是否一致对公众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精英们发出的是一个单一的、一致的信息,那么公众就会绝对地与这一信息保持一致;如果精英们意见分歧并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公众意见的一致性也会降低。民意的构成与结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持不同意见的精英们所发出的信息的互动状况以及普通公众对这些信息的不同解读。
在政治说服过程中,政治精英们往往采取政治辩论(political arguments )的形式传达其态度信息。产生于政治竞争的政治辩论体现了政治说服的艺术。由于政治涉及的都是稀缺资源,因而是高度冲突性的。与此相关,政治辩论中的赞成-反对(pro-con)模式仍是重要的和普遍的说服形式。 尽管赞成与反对两种不同意见信息的分野会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政治辩论中对政策动议持反对意见的一派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民意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一般而言,趋利避害是理性的人的本能。但是,当对可预期的“利”没有十足的把握时,人们宁可选择放弃可能的“利”而规避因“利”而会产生的风险(“害”)。在人们的个人生活中,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政治生活中,这种现象的效应充分体现于反对的意见比赞成的意见更有说服力的事实:面对一项新的政策提案,人们对潜在获益的重视远远不及对避免潜在损失的重视。③
政治辩论中持反对意见的一派对公众态度的影响更大。这一命题对代议制民主的运作具有深刻的启示。公众在面对不确定时自然会选择拒绝变化,因此提出公共政策新方向的人比赞成维持现状的人会遭遇到更多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中“否定的理性”(“rationality of negativity”)。在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眼里,措辞粗糙的攻击性广告最能奏效。[5]
政治辩论的双方谁能胜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辩论中是站在“正方立场”还是“反方立场”,还取决于作为辩论对象的问题。在政治辩论中,作为辩论对象的问题的难与易是影响辩论效果的重要因素。问题的难与易很难界定。一般而言,困难的问题(hard issues )是指涉及技术和手段并且对人们来说比较陌生的问题;容易的问题则是指象征性的(symbolic)、与目的有关并且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不是指现实问题本身的难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辩论双方表述问题的不同方式赋予问题的难易程度。譬如,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有的人将它表述为“如果……,由于存在条件X和Y,Z将会发生”, 有的人将它表述为“如果……,由于存在条件X和Y,Z将会发生,因为……”, 有的人则把同样的问题简单地表述为“如果……,Z将会发生。”前两种表述是对问题的一种复杂的表述, 并且主要关注有关的先例;后一种表述则较为简单。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虽然没有必要低估一般公众的智力水平和理解力,但由于不同问题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不同,一个人肯定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专家,因此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将问题表述出来,才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才能使政治辩论取得理想的结果。④
虽然人们通常被假设是理性的,但人们往往无法关注和理解他们所遭遇的种种刺激,因而感性在其政治判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不能肯定人们通过信息的捷径就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但人们的确是通过直观推断的方法来理解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经济学家安东尼·当斯(Anthony Downs)在四十多年前曾经说过, “理性的公民不应再做其他什么事了”[6]。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凭感觉做就是最大的理性。
假设人们通常凭直观推断来评价政治辩论,但凭借哪种直观推断来作出判断仍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大量的研究认为情绪(emotion)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人们在面对具体的政治问题和事件时,往往会自问自我感觉如何。如果感觉良好,就会对政治问题和事件作出积极的评价和判断。反之亦然。在对所要辩论的问题进行表述时,简单、明了的方式更容易激发人们的积极情绪,因而也更容易说服普通公众。⑤
态度的改变与说服有着重要的关联,但态度本身的特点也决定着态度改变的结果。一般认为,人们的重要态度不易改变。重要的态度往往伴随着大量储存于其记忆中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使人们可以应付对其固有态度发起挑战的信息;而且,人们会在自认为重要的态度方面寄予感情并与其他持有相同态度的人联系起来,因而这些态度还会得到社会支持的加强;人们还会公开地为他们认为重要的态度承担义务,这也增强了他们对变化的抵制能力。⑥
三、态度的结果
态度的结果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对行为的影响,一是对判断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又是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30—40年代态度研究热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心理学家在态度与行为间关系上所持的肯定意见有关。也就是说,在态度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态度与行为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一个人的态度就可以预见其行为。对态度与行为间关系的研究贯穿于态度研究的整个历史。在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中,态度是由刺激(环境、事件或其他“态度对象”)到反应(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中介。态度作为一种中介,既影响行为也受到行为的影响。有关影响态度与行为之间相关性的因素,有的学者提出,当态度变得特别突出时,二者的相关性增大;也有的学者提出,态度的测量越是具体,与行为的关系就会越大。学者费希伯恩(M.Fishbein)和阿泽恩(I.Ajzen)认为,要通过态度来预见行为, 所测量的态度应与所考察的行为相符;一般的态度能够预见一般的行为,却未必能够预见特定的行为。为了对特定的行为作出预测,他们又提出了“行动意图模式”。按照其解释,人的行为都是受意识控制的,意图才是某个特定行为的最直接的决定因素。行为者对该行为的态度和行为者的主观行为规范决定着行为的意图。[7](P246—248) 因此,对一个人的特定行为的预测,必须通过个人对特定行为的态度和规范,而不是个人对一般对象和客体的态度。
在态度与行为的相互关系中,人们一般更注意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并且往往容易将态度与行为一一对应起来;而一度流行的假设也认为,某种态度对应什么样的行为似乎是确定的,只要了解一个人的态度基本上就可以预见他的行为了。但是,相关的经验研究表明,一种态度并不必然导向人们所预期的某种特定行为。在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学者R.T.拉皮尔(R.T.Lapiere)所做的态度与行为一致性的研究。[7](P246) 这项研究使拉皮尔有充分理由得出结论认为,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其后的一些研究也证明和强化了这一观点。
政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之间并没有“态度决定一切”这么简单。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不能简单地以态度推断行为。毕竟政治态度不是解释政治行为的万能工具。政治态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心理现象,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尽管态度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着不一致性,一些学者还是从态度的基础和结构、人格、心理机制等方面对态度与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讨。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态度对行为的作用可以通过选举中选民的情绪对其投票行为的影响体现出来。在选举中,焦虑(anxiety)和热情(enthusiasm)是对选举运动具有影响作用的两个重要的情绪反应。其中,焦虑是对威胁和新奇事物的反应,它能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竞选运动和学习,并使人们减少对与投票有关的习惯性线索的依赖;热情对候选人的偏好有强烈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人们对选举的兴趣和卷入。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可以将情绪用作进行有效的信息处理的工具,从而提高其参与有意义的政治过程的能力。[8]
政策态度是各种政治态度中最容易获得和理解的态度。对态度与政治间关系的研究往往是与竞选联系在一起的。在选举中,态度对政治的影响更明显地表现于公众的政治态度(具体说是政策态度)对其投票行为的影响。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民选出了能贯彻他们所支持的政策的代表。公民选择什么样的候选人做他们的代表,主要取决于公民政策偏好(对政府政策的态度)与候选人政策偏好(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相吻合的程度。因此,对不同候选人的选择可以看作是对不同政策的选择。“政策投票”(policy voting )与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基于态度的相似性之上的相互吸引是一致的。[9] 公民的政策态度以及对候选人政策态度的感知、公民对候选人人格品质以及对在任者表现的评价一起共同影响着公民对候选人的偏好,进而影响着他们在投票中的行为。
由于公民政策偏好与投票行为之间的这种关系,候选人的态度(政策偏好)也间接地影响着选民的投票行为。同时,候选人的态度必须表达出来才能被人们所感知,候选人表达其态度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选民对其态度的感知和评价,而同样的政策偏好如果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选民对它的感知和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对候选人偏好也会产生差异。因此,一些学者有关政治态度与行为间关系的研究还涉及候选人的竞选策略。也就是说,在竞选中,候选人如果用最容易使选民产生好感并接受的方式来传达其态度,使选民趋近和认同其政策偏好,有助于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反过来,如果候选人表达其政策偏好的方式不当,其结果也许是不能准确传达其政策偏好,也许还会使选民对其政策偏好产生恶感,从而不利于在竞选中取胜。
四、政治态度的测量
态度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倾向,虽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研究者可以借助于一些特定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对其进行测量。由于态度测量对于态度研究的重要性,它甚至已经被看作态度概念的一部分。政治态度作为态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测量与态度的测量有许多共同之处,或者说就是态度测量的一部分,虽然在态度的测量中“最多的概念分歧出现在政治态度领域”[10]
在心理学领域和社会心理学领域, 态度的测量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自瑟斯顿1927年在态度测量方面完成其开创性的工作以来,态度领域包括政治态度领域的各种测量表大量出现。瑟斯顿认为,对刺激(态度陈述)的反应可以引出在某些心理维度上的辨别(discriminal)过程。 他对这种辨别过程的本质的假设使他获得了进行比较判断的规则,从而使一系列态度陈述(attitude statement)可以定位于一个单一的维度。这样,瑟斯顿创造了将态度陈述的心理反应(psychological reactions)与对态度问题的回答(responses)联系起来的测量模式。由于确信态度可以被测量,以及调查问卷是可以获得大量受访者的最完美的工具,研究者很快就设计出各种问题用以测量所能想像到的每一个主观领域的任何一个所能想像到的精神存在(mental entity)。[11]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对政治态度的测量涉及与政治态度相关的诸多方面,除了对态度本身的测量外,对与态度相关的倾向和行为也进行了测量。在态度方面,学者们在自由—保守、对政府干预的态度、宽容、种族、政治疏离(alienation)、信任和国际态度(international attitudes)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量化研究工作;在与政治态度密切相关的倾向和行为方面,政治信息(political information)、政治日程(political agendas)、政党认同和政治参与等吸引了最多的关注。为量化研究所做的这种赋予抽象概念以可操作性特征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政治态度的研究,使难以理解和不易趋近的政治态度变得具体和可感知。
譬如,在自由—保守维度上对政治态度所作的分析,是在态度层次上对作为政治学研究中心内容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量表:有的是将自由—保守维度上的不同态度作为一个宽泛的谱系,有的则只是研究处于这一谱系中的某一种意识形态如权威主义,还有的专门分析处在谱系两端的一般被称为左派的激进主义和被称为右派的保守主义。在具体的测量方法上,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进行直接测量(direct measure of liberalism-conservatism)最为人所知的是传统的7点视觉量表(Seven-Point Visual Scale)。这种量表与瑟斯顿提出的测量态度的方法(等距法)相一致,是对不同的态度进行的一种数字等级量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
7点视觉量表
1 234567
极端自 自由的
有些自 温和的
有些保 保守的
极端保
由的
由的
守的
守的
中间的
构建这种数字等级框架的是大量的分支问题(branching question),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派(保守派或温和派)吗?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派(保守派或温和派),你是很强的或温和的自由派(保守派或温和派)吗?如果你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你认为自己是更接近自由派还是更接近保守派?直接的自我标识(direct selflabeling),即向受访者提出大量的只在措辞上有细微差别的问题,让受访者自己为自己的特定态度标识与定位,也是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进行直接测量的一部分。情感温度计(feeling thermometer )是对人们关于政治对象的情感(好恶)的量化分级。具体方法是,用从0到100的分值来计量人们对政治对象的不同评价,50表示一种中立的态度。一些学者对美国全国范围的样本所作的调查表明,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其平均情感分值都在50以上。一些学者在其近期研究中使用了11点(11-point)量表,从而更便于受访者较快地作出回答,尤其是在接受电话访谈时。
除了对政治态度进行直接的测量外,还可以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进行多项目测量(multiitem measures),后者是有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一种间接指标。对政治态度进行的直接测量可以看作是一种单向度的测量,而借助间接指标对政治态度进行的测量则是一种多向度的测量。在具体的操作上,由于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有多方面的界定,其中有的概念和价值对一些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而对其他研究者而言则不重要或不能引发他们的强烈情感。这种不一致还表现在,体现保守主义的价值并非就是与自由主义正相反的价值。因此,研究者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这种测量采取了多种不同的方法。有的研究者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依据不同的指标分别测量,有的研究者则提出一些价值模式(如平等—自由的模式)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进行测量。[12]
与其他一般的态度测量一样,问卷设计的质量对政治态度的测量非常重要。其中,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措辞、回答选项的顺序、等级量表的设计、问题的形式(开放式还是封闭的)等等,都是问卷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进行问卷调查时,调查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方式也影响着结果。
在现在为人们广泛熟知的民意调查出现之前,报纸和杂志使用非正式的民意调查(straw polls), 即从路边的随机采访或从杂志订户中进行邮寄调查来增加有关选举的新闻覆盖面。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民意调查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现的。1935年,爱荷华新闻学教授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纽约创办了美国民意调查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几乎与此同时,珠宝商埃尔默·罗普尔(Elmo Roper)受命于《财富》杂志,负责全国的民意调查,即后来为人们所知的“财富民意调查”(Fortune Poll)。现在的民意调查虽然样本较小,但却是科学抽取的样本,可以被看作对民意的具有科学可靠性的测量。
民意调查所使用的方法与态度、政治态度的测量方法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前者有着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后者的价值则主要体现于学术方面。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更经常地接触到的是民意调查。因此,对于民意调查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也经常引发各种各样的争论。不管民意调查的方法如何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怎样,民意调查事实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及其集团对民意的操纵。因此,民意调查的方法的选择以及对调查结果的分析,都可能被赋予较多的主观色彩,而更难保持中立和客观的学术立场。
五、态度、情绪及其他
在研究态度时,公众情绪(public mood )是被经常与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公众情绪是公民作为一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所经历的一种弥漫的情感状态,它具有明显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13] 尽管私人情绪(private mood)与公众情绪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公众情绪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所经历的私人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的生活态度总是比其他人更快乐,这种差异也会反映到他们不同的公众情绪中。但是,公众情绪不是私人情绪对公共目标的反映,也不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经历的情绪的集合或平均值。公众情绪的概念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个体往往会因其所具有的某个国家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具有不同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类似于他们作为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所体验的情绪反应[13]。
公众情绪既是一个集合概念又是一个个体概念。在作为个人的个体层次上,公众情绪是个人对各种公共对象的一种情感状态,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内心体验,尽管所反映的对象具有公共性;公众情绪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它所反映的是由众多个人的公众情绪所体现的一种趋向,是众多个人的公众情绪在不同环境中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公众情绪虽然基于相同的心理体系(psychological systems),但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简单地说,公众情绪可以看作个人情绪空间中产生于特定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或对特定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的部分。对于作为集合概念的公众情绪而言,某个具体的个人的个体层次上的公众情绪可能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但它与作为集合概念的公众情绪一样是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因此,在这两个不同的层次上都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而研究作为集合概念的公众情绪的意义则主要在于理解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个体。
个人的私人情绪既受所处环境的影响,也是其人格特点的结果。个人的公众情绪无疑也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但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个人公众情绪的起源,有学者依据个体(个人)原因—集体(政治)原因和短期原因—长期原因这两个维度对影响个人公众情绪起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将这种分析称之为公众情绪的“公众情绪病源学”(the etiology of public mood)。
情绪不是态度,但对态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可以看作态度形成前的一种事先表现或态度的一个重要基础。情绪作为态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它往往是通过对判断的影响来实现的。
个体的私人情绪对许多认知与评价过程具有影响。情绪对判断的影响就证明了这一点。一般而言,好的情绪能使人对其周围的世界作出积极的评价,而坏情绪则使人对其周围世界的评价变得消极。个体私人情绪的差异使人们的判断也变得各不相同。因此,社会心理学对情绪为什么、如何和在什么时候影响社会判断进行了理论探讨。尽管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绪与判断间关系的解释模式不同,但在对判断的与情绪相一致的影响(mood-congruency effects on judgments)方面却是相同的。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事物的判断常常会求助于判断捷径,即他们当时所处的情绪状态。
如果人们以其使用私人情绪影响判断的方式来利用公众情绪影响其政治判断,可以预见公众情绪对许多变量都具有影响。个人能力感是影响判断的私人情绪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公众情绪的范畴里,集体能力感(collective efficacy )则是影响公共领域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私人领域中情绪导致判断的关系,可以作为构建公众情绪与判断之间关系的模式。其理论原因在于:其一,社会心理学对控制私人情绪的实验室研究已经明确证实情绪导致与情绪一致的判断(mood causes mood-congruent judgment);其二,政治学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许多民意并不是存在于调查之前的稳定的倾向,而是受访者利用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随便什么信息而创建的“结构”。人们在形成其政治意见时,往往凭借其感觉(feelings);其三,选择将判断作为因变量来加以考察,而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判断受到情绪的影响。[13]
态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赋予态度概念的界定以比较完整和全面的视角,还赋予态度研究以不断深化和扩展的更多机会。态度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界定的,但其核心仍是评价的问题。因此,态度往往被看作对客体在沿从积极到消极的维度上或沿从消极到积极的维度上所作的评价的一个总结。
收稿日期:2005—06—20
注释:
① 参见M.Brewster Smith,“Political Attitudes”,in Jeanne N.Knutson,ed.,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San Francisco,Calif.:Jossey-Bass,Inc.,Publishers,1973,p.59.基于此,社会心理学中对“态度”的界定可以直接用于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周晓虹将社会心理学中对“态度”的界定概括为五类:第一类直接将态度纳入认知体系之中;第二类将态度看作情感的标志;第三类强调从朗格时代起就为人们所重视的行为反应的准备状态;第四类将认知、情感和行为都平行地容纳于态度之中;第五类是指组成群体成员的每一位成员所普遍采取的态度。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1—242页。
② Richard E.Petty,Duane T.Wegener,and Leandre R.Fabrigar,“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i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97,48:609—647.由于潜在于态度结构中的差异会产生态度强度上的差异,因此研究者假定由态度强度就可以推导出有关态度的基础与结构的状况。
③ 即使是在诸如保护环境等已经取得明显共识的领域, 反对的意见也依然占了上风。参见J.J.Skowronski and D.E.Carlston,“Social Judgement and Social Memory:The Role of Cue Diagnosticity in Negativity and Positivity,and Extremity Biases”,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52:689—99.政治辩论中反对意见占上风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历史上曾经有过每一个人都没有从新政策中受益的经历,会使大多数选民对政府失去信任,并对新的政策动议变得非常谨慎。参见Michael D.Cobb and James H.Kuklinski,“Changing Minds:Political Arguments and Political Persuasion”,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Psychology,1997,41:88—121.
④ 如何表述问题其实已经涉及辩论的技巧。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也许可以说服普通的公众,但却未必能说服问题所属的专门领域的专家。这又是政治说服中所要考虑的个人层次上的差异。
⑤ 但是,一些学者对现有研究的回顾却得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1)简单的争论更有说服力;(2)困难的争论更有说服力。虽然学者们对争论的类型已进行了多年分析,但却很少对不同争论结构(argument structures )的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参见Michael D.Cobb and James H.Kuklinski,“Changing Minds:Political Arguments and Political Persuasion”,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Psychology,1997,41:88—121.
⑥ 在早期态度研究中,学者们就依据重要性(importance)、核心地位(centrality)、自我卷入(ego involvement)和突出性(salience )等标准对态度进行区分。事实上,不同的人对态度重要性的界定是不同的,但“似乎最合理的对态度重要性的界定,是将它看作一个人对某一态度倾情关切并亲身投入的程度”,而将态度与价值、需要、目标间的联系看作重要性的一个可能原因似乎也是合理的。Jon A.Krosnick,“Government Policy and Citizen Passion:a Study of Issue Publ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in Political Behavior,1990,Vol.12,No.1:5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