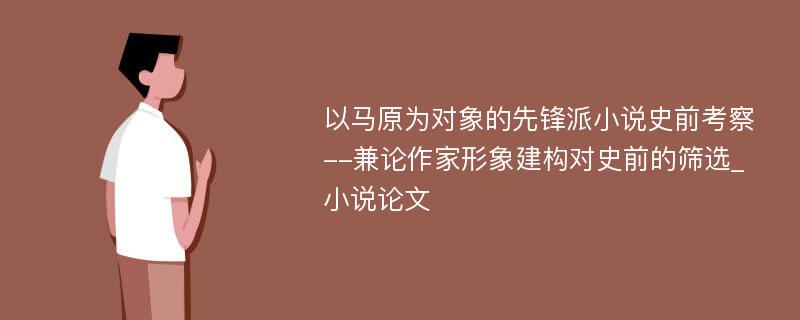
以马原为对象看先锋小说的前史——兼议作家形象建构对前史的筛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原为论文,对象论文,作家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2-0001-10
关于“先锋小说”的提法,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文坛,一直都存有争议。“对这派小说的称呼并不一致,大致有‘新潮小说’、‘实验小说’、‘后寻根小说’、‘探索小说’、‘先锋小说’等多种,但其所指向的作家群是大体一致的,它指向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徐星、刘索拉、残雪、马原、洪峰、格非、余华、孙甘露、叶兆言、苏童等。”[1]而事实上,除了命名无法形成最终的定论以外,关于“先锋小说”所指向的作家范围,也并非没有分歧,比如,将徐星、刘索拉命名为现代派作家而不归入“先锋小说”群体[2]。
但正如程光炜在《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中所说的,文学史研究必须有某种“共识”,否则就无法交流。[3]同样,对“先锋小说”的讨论,首先也要站在某种“共识”之上,然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或者辩护或者商榷。我想,关于“先锋小说”的共识,很大程度上可能要求助于“约定俗成”,也就是我们暂且不去追问它“应该是什么”,而是首先考究我们眼中的它“已经是什么”。那么,“就新时期文学而言,1985年前后兴起的以马原、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作家为代表的小说创作,由于其自觉的创新试验而被评论家普遍指认为先锋小说”,[4]1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审慎而能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的。更明确地说来,“先锋小说”是以其形式上的创新试验而成为某种整体性的文学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原的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在《上海文学》上的发表,成为了80年代的“一个文学事件,以此为先锋小说出现的标志,作家从原来关心写什么到关心怎么写,从先前的文以载道转变为道以载文”。[5]216马原的小说成了“形式试验的范本”[4]85,他也因此“被选定为先锋小说的先锋”[6]165。
然而,这种“共识”很显然也包含着某种危险。提到“先锋小说”,我们通常想到甚至只会想到的就是形式试验、叙述方式的“先锋”。这样很自然地就遮蔽了“先锋小说”在它产生的历史现场所曾经拥有过的其它维度。②同时,由于文学史研究存在的某种“原点”、“标志”情结,我们的文学史视线通常是向后看的,比如从“先锋小说出现的标志”《冈底斯的诱惑》向后看“先锋小说”的发展流变,或者总体性地为这个原点寻找一些背景式的“出生证明”,从而忽略了在这个“历史原点”之前所曾在场的更丰富的信息。
这也是本文尝试考察马原这个“先锋小说”“原点”的“前史”之初衷。
一 马原的西藏梦与西藏题材
1989年初,一位批评家曾这样回顾与描述5年之前的文坛:“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风格瓜分了。贾平凹以他的《商州初录》占据了秦汉文化发祥地的陕西;郑义则以晋地为营盘;乌热尔图固守着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帐篷篝火;张承志游荡在中亚地区冰峰草原之间;李杭育疏导着属于吴越文化的葛川江;张炜、矫健在儒教发祥地的山东半岛上开掘;阿城在云南的山林中逡巡盘桓……”[7]
在这段话里,我们当然能够很容易就发现这张“版图”所缺失的部分:西南角那个在地理上处于边缘的高原省份——西藏——似乎也同时处在文学场的边缘。但如果在1985年再来看这张版图,西藏的位置上,或许已经标上了几个名字:马原,扎西达娃……——1985年2月,《上海文学》发表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1985年6月,《西藏文学》推出“魔幻小说专辑”。西藏的这群作家和他们笔下的这块地方,逐渐被文学视界的目光所认识与关注。
西藏,似乎因马原等人的小说而浮现在文学视界之中。但对于马原来说,他又何尝不是因为西藏而成功地实现了小说试验,从而进入了文学视界的焦点呢?在他离开西藏8年之后,与他重逢拉萨的原《西藏文学》编辑马丽华“记下他的第一句话是:离开西藏就写不出东西了”。[8]117我想,就后来的事实而言,这不算夸张。②
西藏,对马原和他的“先锋小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值得我们首先加以注意的问题。
1982年,马原从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进藏。“进藏”,在当代中国,是一个有着特殊与丰富含义的词汇。政治与人文,责任与理想,民族与国家,在这个词汇背后交织形成了一圈特殊的光晕。关于“进藏”,马原说:“1982年大学毕业,我决定去西藏,中专毕业就想去,但因为西藏没有铁路部门所以没能成行。这次终于如愿。”[5]20至于为什么要去西藏,马原语焉不详。不过马原中专毕业第一次想去西藏是在1976年,我们不妨看看另一个1976年进藏的大学生的回忆:“1976年我大学毕业了,那时毕业分配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学生可是稀罕物,到处都抢着要,在一张学校详细的全国分配名单中,有3个西藏名额。不知道是不是学校担心这3个名额分不出去,还是呼唤大学生激情的需要,反正那次的毕业动员,是前所未有的隆重。一时间,我们那一届498个毕业生中,竟然有492个人报了名,要求到西藏去工作。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到边疆去,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口号真的非常激动人心。”[9]马原的“进藏”是否有被这激动人心的口号鼓动的成分,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不过我想,身处这样的年份中,每一个凡人都不免被社会大潮所挟裹,与大潮做一阵同路人。正如马原在同一篇访谈里提到的“那时候没坐过飞机,听说进藏报到可以坐飞机,以为这一辈子只能坐这一次飞机了,就想借报到坐一回,所以奢侈了一下。报到后急急忙忙拿出飞机票报,生怕报不了,得自己掏钱,起码要两个月的工资”。[10]进藏的大学生马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80年代初那“数以千计”“潮水般涌向西藏”[11]的大学生中的普通一员。③
当然,对于此时已经在辽宁本地小有名气的作家马原而言,进藏,还有一些更为特殊的原因。《收获》的编辑程永新回忆早年在《收获》杂志广西笔会上与马原初识,两人在海南岛“常聊到深夜”,聊到“马原原籍辽宁,为了文学跑西藏去了,他说西藏是个神话世界,可以出大作家”。④从沈阳到西藏,初出茅庐的马原怀揣一个成为“大作家”的梦踏上了那个“神话与现实共存的高原”⑤。这个梦想是否最终达成是后来的事,我们交给历史去评判,这里不加详说。但至少这段旅程却确确实实地反映在了马原的小说里。
马原公开的小说处女作《海边也是一个世界》发表在黑龙江作协主办的《北方文学》1982年第2期上;当年第5期《北方文学》又发表了马原的另一篇小说《他喜欢单纯的颜色》;5个月后,《北方文学》该年第10期又以封面推荐的形式发表了他的《方柱石扇面》。虽然小说名字起得一如马原后来“先锋小说”的风格,但小说的内容却并不“先锋”,三篇小说,都以相对直接的方式作出了对“文革”的暴露与反思,基本可以归入主流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其背景也是相对普泛的。
比如在“姚亮”和“陆高”第一次作为小说人物出现的《海边也是一个世界》里,马原写道:“他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这里。抽工,推荐上学,也许还有别的机会。他知道陆高只能留在这。陆高自己不想走,再说,大小领导没一个得意他的。陆高生性孤僻,他有一个弟弟,但是被他绞杀了。”小说结尾写道:“一本叫《笑面人》的诗篇,在第二十六页上:‘窝莱斯有做美洲土人的野心,既然事实上办不到,他只好一个人单独生活。其实孤独的人就是文明的国家容许的变相野蛮人’。”这篇小说实际上讲述的是“陆高”在知青农场的生活,而姚亮虽然也是知青,在小说中却相对处于次要地位,更多的是作为陆高故事的见证者。陆高就是那个年代里的“变相野蛮人”。而《他喜欢单纯的颜色》则讲述了“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史洪在被污杀人劳改十年后回到家中,并因围绕旧日恋人的种种事件最终回归劳改农场的故事。小说里写道“就是那个‘大革命’开始的年代,他为了真理冲了上去”,“史洪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光明磊落的。可他不希望俞丹看到自己的英雄气派。这个问题他一直弄不明白。十年中,他常常想起这个问题。或许,那时,人类的良知已经在提醒他。”《方柱石扇面》则写了一个即将退休的老革命、新上任的铁路第一职工宿舍主任易莎的故事,小说中写到易莎对铁路列车组的女乘务员们的同情,“这情景,仿佛易莎亲身经历过。她热爱党,她们都热爱党。她们有志气,有热情,她们没有什么过错。有罪的是江青。可是,命令下来了,女乘务员(包括其他繁重工种的女同志)就要淘汰掉。这是关心她们的身体。身体?精神、灵魂是不是也该关心。”如此传统的写法和直白的描述,几乎让今天已经先验地给马原加上了“先锋”标签的我们怀疑,这是不是同一个马原。可以说,这时候的马原还是一个老老实实写人生、反思“文革”伤痕的小说作者,而那个爱好下“叙述圈套”的马原还远未出现。
马原进藏一年多以后,《西藏文学》1984年第5期在“新人新作”栏下发表了署名“孙效唐、姚亮”的小说《中间地带》,我们知道,“姚亮”是马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实际上几乎算是马原的化名,后来这篇小说也确实被收入马原的《西海无帆船》小说集中。所以,《中间地带》可以说是“新人”马原在西藏的第一次公开发声。⑥在这篇小说中,西藏第一次出现在马原笔下,成为故事的背景。无论是小说开篇对萨迦格言“火把虽然下垂,火舌却一直向上燃烧”题记式的引用,还是结尾“第一缕曙光终于照过来。天葬台伸出的巨石上笔直伸起一股蓝烟,曙色使直上天穹的烟缕透明。次巴珠看到,鹰隼从四面八方聚向这透明闪亮的烟柱”,对天葬的描绘,都试图展现出一幅西藏世界的独特背景。
马原也在《海边也是一个世界》里的一个东北汉子所在的知青农场向《中间地带》的“西藏”的位移中,宣告了西藏正式成为他的小说世界的坐标所在。此后,无论是《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还是更后来的《虚构》、《西海无帆船》,马原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无一不是写的西藏世界。事实上,1987年西藏人民出版社曾经为马原出版过一部小说集,名字就叫《西海无帆船——马原西藏小说选》,我们不妨将其中的篇目一一举来:《西海无帆船》、《冈底斯的诱惑》、《虚构》、《风流倜傥——〈拉萨的小男人群像之一〉》、《喜马拉雅古歌》、《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山的印象》、《夜班》、《牧神青罗布》、《拉萨河女神》、《中间地带》、《小扎西和他的一大堆美妙的想法》、《台灯下的灵感》、《叠纸鹞的三种方法》、《游神》。可以说这部“西藏小说选”“几乎包括了”马原“所有西藏题材的小说”。[12]341988年3月16日马原曾写信给程永新,谈到他为做自己的作品选本,“想把已经完成的作品归一下类别”,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已经被国内多种选本选过的西藏部分,以传奇及想象的生活为主”,并说他“选这部分,主要考虑到读者的兴趣,海外华人多为西藏所迷惑,权为满足这种好奇心吧?”[12]38我想,从这私下的信件里,我们能够比较容易把握到马原的心理,他并非如我们后来所评论和他自己所声称的那么不关注故事本身。因为如果马原真的是一个彻底的只在乎怎么讲而不在乎讲什么的小说家,那么,他的小说显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满足读者对西藏好奇心的作品了。而显然,马原对这一点很有信心与相应的预期。
当然,对马原来说,西藏,这个“神话世界”恐怕也不仅仅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场地那么简单。它更牵涉到了马原的小说风格塑造与身份认定。
马原曾多次强调他“到了西藏以后”,“发现自己一直是一个有神论者”。[13]这和西藏本身的人文地理状况当然有直接的关系。比马原早6年进藏的马丽华曾说,“我们是在文革结束的1976年毕业进藏的。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尤不信鬼神。那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派空阔的景象,除了高山大河的自然界岿然不动外,凡传统人为的精神遗迹差不多都被那场运动荡涤一空……80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情形大变。寺院修复,神坛重建,经幡飘飘,桑烟袅袅,六字真言不绝于耳,转经人流漫漫而行……不作政治和观念的评判,就文化意义来讲,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高处,这一派漫浸的古风已足以使人惊奇。即使无神论者如我,也不掩饰自己关注的热情,更何况更具现代意识更年轻于我的这一批外来的学子们。”[8]89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原后来对西藏神秘诱人的念念不忘,显然并不令人意外。所以马原在谈到藏族人的生活时,甚至蕴含了一点艳羡的成分:“他们的生活竟是难以描述地轻松美好。他们耕作放牧时唱歌,休息时喝酒也调情,变卖家产跋涉上千里去拉萨朝佛。这里的生活时时刻刻充满了故事,使人无法辨别是虚的还是实的。事实上,藏族人的生活和神话,藏族人和神是相通的。”[14]因此,才有批评者认为,“正是西藏那种难辨虚实、轻松美好的生活感召了他。在这里,他才发现偶然性不仅是生活的真实,而且是艺术的真谛。我们要记住,正是西藏使马原成为现在的马原。”[15]460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马原的小说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16]464在从《拉萨河女神》开始的一系列小说中,“西藏地区奇诡的自然景观以及与汉族截然不同的藏族的生活形态,还有相当引人入胜、耸人听闻的故事情节,使这些小说充满了神秘诱人的色彩。”[16]464可以说,西藏的“神奇”、“神秘”本身也成了马原小说内里的一部分,与它的形式试验不可分割,一起形成了马原“先锋小说”的风格。
而马原本身也表现出了对于西藏的身份认同。1986年2月,他的小说《牧神青罗布》发表在《西藏文学》藏大学生作品专号上。在此之前,从1985车底开始,一场关于“西藏文学”与“西部文学”的讨论以《西藏文学》为平台逐步展开。《西藏文学》1985年第11期上,李雅平在《西藏:西部文学的圣地》中将西藏视作西部文学的圣地,唐展民的《西部—西部精神—西部文学—西藏文学》则提出,“‘西部文学’作为超区域性的文学思潮方兴未艾,我们可以把西藏文学和西北文学看成一双对等的区域性文学,而在这一对区域性文学中,孕育着一种超区域的文学,这就是中国西部文学。”继而在1986年第2期的《西藏文学》上,海岑又撰文认为,“把西藏包括在西部文学的地理范围内,乃是应有之议、议内之题。”[17]而“就在评论者们忙于证明西藏文学的西部性时,作家们却要追求自己独立的价值”,[15]4341986年4月,马原与色波、扎西达娃、刘伟等人合作《“西部文学”和西藏文学七人谈》,刊登在《西藏文学》该年第4期上,这群西藏的作家纷纷表示了对将西藏文学归入西部文学的异议,扎西达娃“认为西藏文学应该有它自身的价值”,刘伟干脆指出“把西藏文学划归‘西部文学’是不应该的”。马原则一如他曾多次强调的,表示“西藏文化有它强烈的个性……西藏是神话传奇、佛教的世界,这里是全民信教。信仰的是容纳了禅宗、密宗、苯教神秘色彩的西藏化的佛教,也就是喇嘛教了。再加上佛本向善的观念,就形成了西藏独有的文化意识。”谈话中的马原显然和他的作家同伴们一起,已经把自己视作了西藏文学的一分子,在努力挖掘、正视与保持西藏文学的特质与独立性。西藏,对于小说家马原来说,已经是与他的小说作者身份紧紧缠绕不可再分的一个存在。同时,这种认同显然也不仅仅是马原自己的看法。在同一篇谈话中,参与者之一余学光就表示:“一些作者尽管在用不同的手法表达自己的个人感受,写自己认识和理解的西藏,但我从这些小说中品到的味道很相近,有共同的特点,如同身在荒原之中。像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牛皮绳扣上的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还有85年《西藏文学》第6期。”
马原,在这个神秘的高原之上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同伴,他们一起认同西藏,书写西藏,又一同站在西藏作家的立场上,为寻找西藏文学的特质、维护西藏文学的独立价值而纵谈游笔。而这群马原文学上的同伴,显然也是认识他与他的“先锋小说”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小圈子”里的马原
1982年,当马原踏上西藏拉萨的土地的时候,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已经有一群小说作者在默默“耕耘”着。这就是围绕在《西藏文学》周边的扎西达娃、金志国、色波等人。这群作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如扎西达娃,从1979年就开始在《西藏文学》(改版前称《西藏文艺》)上发表作品,陆续发表了《沉默》、《朝佛》、《沉寂的正午》、《江那边》等小说。同一时期,色波、金志国等人也分别陆续发表了《海螺号吹响》、《乌姬勇巴》和《山石》、《帕珠》等小说。今天翻阅这些小说,大部分还明显停留在对“文革”故事的讲述,对“文革”遭遇的控诉与反思,对“文革”后生活的憧憬与图解的层面上,艺术上也相对稚嫩。但是,事情明显也在变化之中,这群身处高原的作者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探索与进步,几乎能一步步看出某种痕迹来。
这种变化首先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西藏文学》1982年第6期刊登的扎西达娃的《白杨林·花环·梦》和金志国的《梦,遗落在草原上》两篇小说中。这两篇小说“苦心构造”了“由形象到理念的象征主义桥梁”[18],“突破了传统题材的范围”,“表现出对形式上创新的强烈愿望”,“标志着当代西藏小说的兴起”。[15]443这期杂志的付印时间在1982年10月10日。我们当然很难判断说,这与在此前后进藏的马原有没有关系,或者说这对马原有没有什么影响。但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马原后来回忆,当时的拉萨只有“一点点大”,“就是一个小镇”,“大概就是十万人”。[10]在这样一个“小镇”中,有着相同背景与爱好的人很容易就能结成相应的“小圈子”。“当年,陆续进藏的大学生,在拉萨营造了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文学艺术娱乐这些很精神的东西是主流,大家能一天一天地谈小说,为海明威的一个小说结尾争得面红耳赤差点打起来,当然他们也能一天一天地打麻将打扑克,但这不妨碍大家交流自己的创作构思,成立诗社。”[12]222-223也就是说进藏大学生与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在这样的“小圈子”中成了彼此认证的标识,也成了他们彼此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契机。
马原的家也在随后成了“西藏文艺界的重要据点和沙龙,文艺界的人经常到他家去‘联欢’,有人开玩笑说他家是西藏自治区‘第二文联’”[19]。马原更坦言“1985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在西藏的确是有个文学小圈子的”[13]。这个圈子“内部人际关系良好,相互提携扶持,作为重精神一族,共同致力于纯文学探讨。在其时国内风起云涌的流派思潮席卷下,却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无论外来的内在的每个人所钟情的一应主义思潮,悉数纳入‘西藏新小说’一派中”。[8]91多年之后,马原如此评价在这个圈子里的生活:“我在藏七年,从29岁到36岁,一生中最好的时间,经验,精力和健壮的体魄,同时最好的人际关系也在这里。”[8]120
这个身处边疆高原的“小圈子”的存在后来也被圈子外的人所认可,当然,与圈子内的人从私人活动上对“小圈子”的存在进行确证不同,“圈子”外的人只能从他们所发表的作品来确证这种判断。“1985年前后,来自青藏高原的一支生力军异军突起,挟高原之风闯入中国文坛,与内地湍急的文学运程遥相呼应。这批生活在西藏的青年作家集束式捧出的作品,以藏文化为背景,糅合各种现AI写作作手法,将民间传说神话志怪一并吸纳进来,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形成迥异于内地文学的独特风格。这批青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马原和扎西达娃,比较活跃的还有色波、李启达、皮皮、子文等人。”[12]4
这个“小圈子”的小说创作,后来被命名为“西藏新小说”。尽管这一命名“概念模糊”[8]81,但对于一个群体的小说创作而言,它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小说特征上都作了有概括力的归纳。
这种“小圈子”活动的形式首先被马原“如实”记录到了小说中。马原自承“我都写我身边的人和事,要么是我,要么是陆高,要么是姚亮,这都是真真切切的男人在生活,我写的都是我自己的生活,这其中没有特别多的虚构,我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我传奇化了”。[13]这当然可能是作家马原的某种夸张的说法,但当我们看到“成员包括文艺界各方面人士13人。最大年龄40岁左右,最小20稍多。其中一名藏族青年作家,两名女士”的《拉萨河女神》,看到其中按年龄大小排列的“1是剧作家,也是西藏中世纪史学家”,“2是民间文学研究家和作家,是国内有数的西藏民研民俗专家”,“3是个上海学者,主要搞文艺评论工作,他的小说曾引起海内轰动。13个同胞中他学历最高,硕士研究生”,以至13“是藏区最好的作家,又最年轻正在热恋”,最熟悉马原的西藏生活的人甚至可能能一一将他们指认出来,我们就不得不相信,马原确实是在认真地对待“日常生活的传奇化”。对“圈子”活动进行如实记录的《拉萨河女神》,又因为其中间夹杂的“读者应该首先知道几种简单又很要紧的事实”,“我们假设这一天是……”,“这么说下去,读者可以因此推断……”,“还可以进一步假设……”,“为了把故事讲得活脱,我想玩一点儿小花样,不依照时序流水式陈述”等等显示写作者马原不停出来“饶舌”提醒读者的句子,而成了马原被“追认”的第一篇“先锋小说”代表作品。而只比《拉萨河女神》迟一期发表在《西藏文学》1984年第9期上的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则与《拉萨河女神》共同形成了“西藏新小说”创作探索的先声。我们在色波的这篇几乎同时发表的作品上,看到了那些多少有些“马原式”的写法:“如果你有兴趣去打听一下的话,他们便会板着脸给你讲述上面那个古老而又令人乏味的故事”,“但有一点要注意:千万别去问他们悟到了那个梦没有,否则他们会恶狠狠得瞪着你。这是门巴族男人们唯一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
马原与这个“圈子”里其他成员的互动,最早公开出现在《西藏文学》1985年第1期上。
当期发表了扎西达娃的名作《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文后附发了署名“陆高”的评论文章《魔幻的,还是现实的?——读〈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熟悉马原小说的读者后来很容易就能发觉,“陆高”这个经常出现在马原小说里的人物,和“姚亮”一样,其实就是马原的另一个化名。这个“不写魔幻诗的诗人陆高”,就是马原自己。⑦在这篇评论中,马原显得如此了解扎西达娃:“你熟悉扎西达娃的作品,你就会为这篇小说诧异和吸引。你会说他变了,他在走一条全新的路”,“这里充满迷、充满魅惑和生气的人们的生活本身使扎西达娃写出了这个故事,如此而已”,“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哲学家……他只是也只能是一个艺术家”。而在评论的最后,他对读者们说:“你最好想办法到拉萨来……来拉萨找他或找一个叫陆高的不写魔幻作品的诗人。你肯定可以找到他们。”在这里,马原不经意又自然而然地用了“他们”的表述。在同一期《西藏文学》上,还发表了刘伟对《拉萨河女神》的评论《〈拉萨河女神〉别具一格》,刘伟说马原是“带着海的想象和热情,从遥远的东北来到西藏高原,他是拨着文艺女神的竖琴来到拉萨河畔的”,并认为“马原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作家”。马原自己也专门撰写了《我的想法》谈他的《拉萨河女神》。《西藏文学》主编李佳俊也在同期刊发了评论《生活的描写和文学的思考——读〈拉萨河女神〉断想录》。
我们可以注意到,由马原、扎西达娃、金志国、色波、刘伟等人组成的这个“西藏新小说”的“小圈子”,在对西藏人文地理的描述与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只不过相对来说,马原在形式试验上走得更远一些,而扎西达娃则同时致力于对西藏地域文化的发掘。所以,在后来对“西藏新小说”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将两者称为“西藏新小说”的“马原式”和“扎西达娃式”。⑧
1985年2月,马原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冈底斯的诱惑》,将西藏融合在独特的小说形式中推介到文学圈的中心地带,并逐渐引起了一些批评者的注意。⑨4个月之后,《西藏文学》当年第6期就以集束加编后语的形式推出了“魔幻小说特辑”,包括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色波的《幻鸣》、刘伟的《没上油彩的画布》、金志国的《水绿色衣袖》、李启达的《巴戈的传说》等5篇小说。这个特辑的编后语《换个角度看看,换个写法试试》里还表示:“不是故弄玄虚,不是对拉美亦步亦趋。魔幻只是西藏的魔幻。有时代感,更有凝重的永恒感。”如果我们再返身去看5个月前“陆高”在《魔幻的,还是现实的?——读〈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所说的:“你来过这块中国西部的巨大高地,你知道神话、传奇、禅宗、密教在这块高地布下的氛围。你清楚地知道这些,你也因此知道了魔幻意识的祖籍就是西藏。这是至关紧要的,你不能离开这一点去理解这个小说。”我们就会怀疑,这次的编后语是不是“陆高”的另一次发言。
这个西藏小说圈子的探索显然引起了文学中心的注意。扎西达娃1986年8月在给《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信中说,“《西藏文学》6月号能得到贵刊的好评,我感到很高兴。其他作者都收到了你的来信,我们谈了一下,对下一步的创作都有信心。有的正在写,有的也写得差不多了,看情况大概10月份左右差不多都能完成,为《收获》推上一组”。这里,我们大致能看出事情的梗概来:《西藏文学》1985年第6期的“魔幻小说专辑”引起了《收获》杂志编辑的注意,程永新为此特地写信给几位西藏的小说作者,希望能组一期西藏文学的稿。
马原对此的记忆则可以为我们从另一个维度印证此事。马原说在《收获》1987年第5期“实验小说”专稿之前,“《收获》实际上还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举动,但是夭折了。在《收获》整个发展的几十年里,它没以地域为专刊组过稿子,那时《收获》的执行副主编李小林和程永新一起准备出一期西藏专刊。当时我人在西藏,对西藏的事情稍微熟悉一点。我在西藏的那段时间里有一批非常有个人特点的作家,你们现在有的人可能还知道扎西达娃,但另外一些名字你们可能都不太熟了,像色波、金志国、启达。《收获》这本能够影响整个中国文学走向的大刊物,第一次专门以地域、以一个弹丸之地约了一期稿子——西藏别看面积很大,占中国国土的八分之一,但是我在的那些年,整个西藏总共不到两百万人,只有上海的一个区那么大。”关于“夭折”的原因,马原也说得很坦率,“‘二马’当年就把那期西藏专号给毁掉了。因为马建当时写了个小说,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点名批判;加上马原在《作家》杂志发了篇小说,《作家》杂志被停刊整顿。”“二马”小说的“出问题”,就是在民族感情问题上引起了争议,后来西藏自治区党委专门开常委会,“讨论马原有没有伤害藏族人民感情”。[20]也就是在此之后,因为涉及民族感情问题的敏感与不好把握,西藏题材的小说大多被搁置或者放弃。姑且不论这些风波本身昭示了怎样的政治情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马原在这其中,是与西藏,与“西藏新小说”的“小圈子”联结在一起的。而当1985年《收获》编辑程永新在桂林笔会上结识马原时,“他在西藏一批青年作者中间无疑已处于中心位置。”[21]168
当然,身处“西藏新小说”作者这个“小圈子”之中,对马原的“先锋小说”创作究竟有多大程度上的影响,我们很难做出量化的考察,甚至无法从少之又少的关于群体交往的材料中,去梳理出确凿的线索来确证这种影响。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从作品本身来看,如果说从马原在辽宁时所写的《海边也是一个世界》、《他喜欢单纯的颜色》、《方柱石扇面》到在西藏第一篇发表的《中间地带》,还只是一种故事背景的位移的话。⑩那么,1983年马原“从西藏回沈阳,带了4篇小说,包括《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的雏形《西部小曲》、以及《儿子没说什么》”[5]20则标志着马原的“写作发生了大变”(11),从背景的转变进一步深入到了小说形式的全新探索上。而《冈底斯的诱惑》就是在次年,即1984年春节马原“回西藏的时候路过四川灌县”[20]时遇雪而最终写成的。这时候,在东北时老老实实的“姚亮”、“陆高”开始在西藏为一个个读者设下各种“叙述圈套”,让批评者与读者最终坠入其中。(12)
而在与马原的这种深刻转变几乎相同的时段里,色波、扎西达娃等“西藏新小说”的另外几位主将,也集中开始了他们的大步的探索与转变。这种探索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争议。1985年有评论者说“近年来西藏文学屡出奇文,有人叫好,赞为创新,有人摇头,说是看不懂,每每引起一番争论”,比如“82年是‘两个梦’……84年则是《永恒的山》与《阳光下》”,“说来凑巧,这两篇小说的作者刚好就是前述‘两个梦’的作者。时隔两年,他们在象征主义技巧的运用上显然熟练多了”。(13)所以也有人认为,到了1985年,“西藏小说与内地的差距”“迅速缩小了”。“在这一年,扎西达娃、马原、色波等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作品,像《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结》,《西藏,隐秘岁月》,《冈底斯的诱惑》,《幻鸣》,以及在此之前的《拉萨河女神》,《永恒的山》,《竹笛,啜泣和梦》,这些作品,与两三年前同一作家的作品相比,只有‘飞跃’可以形容,在主题开拓的深度和广度,在作品的整体结构,尤其是语言的遣造上,都可以说是相当成熟的”。[15]432
更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是,1984年末到1985年,一场关于“寻根”的文学热潮骤然兴起。从写作的时间上看,马原、扎西达娃等西藏作家的小说与这场“寻根”理论热潮并无直接联系,甚至还要早于这股理论热潮的兴起。但我们也因此不得不更加为这种不谋而合所惊异。在内地的作家们开始各自挖掘地域文化的“根”时,马原和扎西达娃们也在偏远的高原上不遗余力地书写着西藏的神秘魅力。所以,一位批评者在1989年谈到1985年随着“一场文化问题的大论争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创作也在同步发展”时,在列举了“林斤澜的《板凳桥传奇》发表,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问世;张辛欣、桑烨的《北京人》引起广泛的注意;韩少功的《爸爸爸》、《诱惑》等作品带给人的极大的困惶,阵容强大的湘军崛起”之后,将“《西藏文学》于1985年7月,扎西达娃《西藏,隐秘的岁月》为首篇,推出魔幻现实主义专号;《上海文学》发表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也列为了这一潮流的一部分。[7]
而这种叙述如何在之后被“先锋小说”的潮流命名所隐没,是值得我们另外详加考察的问题。
三“文人圈子”的筛选与作家形象的建构
1987年,当“先锋文学”成为批评关注的焦点并逐渐产生统一的命名时(当时所采用的是更为宽泛的“新潮小说”的说法),早在1984年、1985年就“神奇而寂寞地进入文坛”的马原适时地被批评家和后期的“先锋小说”家们“追认”为“先锋小说”的开创者,“当我们称那些先锋小说家为‘马原们’或‘后马原’时,我们似乎把他们当成了马原领进门的弟子。”[6]165但与此同时,相对的,我们又何尝不是用这种一脉相承、弟子相继的“谱系”限制与清理了马原,将他与他的“先锋小说”从西藏和“西藏新小说”的群体中剥离出来,让他光芒耀眼地高悬在“先锋小说”的起点之上。而这种耀眼的光芒无可避免地淹没与遮蔽了他身边的一切,使他成为了一个孤零零的“历史原点”。
显然,在这个原点的前后,在马原的前史与他后来的文学史形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我们今天的意识与叙述里的马原形象,正如我在开头所说的,几乎成了“先锋小说”所代表的形式试验(其实也就是叙述试验)的代名词,似乎更为单纯,更具有“断裂”式的个性。(14)而事实显然比“断裂”式的叙述所呈现的更为复杂。那么,这个近乎“提纯”的筛选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换句话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先锋小说”的命名是如何隐没复杂的前史,将不为这种命名所需要的信息“删节”筛选的过程。
这并不仅仅是关涉马原或者“先锋小说”的问题,事实上,对于文学史的叙述与大众的接受来说,这是一种具有共性特征的问题,许多经典的作家也经历过这种前史的“筛选”与“提纯”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越是经典的作家这种效果可能越发明显。最有代表性的如鲁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研究者们“运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阐释新文学史”,“鲁迅精神”因此“被抽象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鲁迅“变成了一个拿着笔冲锋陷阵的文化战士”。(15)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一维的定位显然值得商榷,但这种将一个作家与某种特定风格或特定形象牢牢联系起来的定位机制又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现实。所以法国文论家朗松在《文学史与社会学》一文中说,“作家并不是通过他这个人而是通过他的书产生影响”,而“书的效用”则“取决于公众”,是公众在阅读中“按自己的形象和为自己的需要而塑造一个笛卡尔和卢梭”(考虑到这位学者是法国人),公众在这过程中“不断修改、重新塑造”作家的作品,“或者使之丰富,或者使之贫乏。作品的真实内容就仅仅是作品意义的一部分,有时甚至完全失去意义”。(16)朗松显然意识到了隐身于历史背后的“公众”对作家形象的强大建构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筛选机制。
但是,朗松并没有对“公众”本身进行进一步的辨析与分层,而且他将批评家排除在了“公众”之外。他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对作家的形象建构而言,批评家也本然地置身在“公众”的群体中,而且在通常的历史环境中,包括批评家在内的“文人圈子”更是对这种建构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期刊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批评家具有极大权威的历史背景下。(17)这个圈子当然不是指如前面所述的“西藏新小说”群体那样的比较单纯的创作圈子,而主要存在于传播过程中。
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为我们进一步定义和区分了“大众的圈子”和“文人的圈子”。他所说的“文人圈子”实际上就是文人群体,“这个文人群体同我们所说的‘文学阶层’相符合,这一阶层中聚集着大多数作家,以及所有同文学事实有关的人,即从作家到大学里的文学史家,从出版商到文学批评家”。这个圈子通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内部的多向交流。与此相对的“大众的圈子”,则虽然“无论是在数量、质量和类型上”,“都具有与文人圈子里的读者相通的文学需要,不过这些需要总是从外部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让负责文学生产的作家或出版商了解自己的反应”。[22]100正因为如此,“大众圈子”通常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上,“大众圈子”中作家形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文人圈子”的引导与制约,(18)尤其是在如“先锋小说”般“因为形式上的极端激进的实验和内容上的晦涩艰深,使广大读者敬而远之”,[23]从而造成“大众圈子”的交流能力与交流欲望严重弱化的状况。
显而易见,在埃斯卡皮所定义的“文人圈子”里,首先形成筛选效果的,当然是他所说的文学生产中除作家之外的另一环、通常也是文学传播过程起点的“出版商”。埃斯卡皮甚至认为,是“出版商的挑选‘创造’了文学”。[22]101而在80年代的中国代行出版商职能的,往往是文学期刊与隐身其后的编辑们。不过,需要更进一步加以辨析的是,筛选效果的形成不仅仅是基于作品的是否发表。在本文讨论的背景中(即如马原那般,许多的作品已经发表的前提下),首先对文本形成筛选效果的,应该是期刊影响力的大小。
1985年,有批评者在研究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的文章开头就说:“西藏的文学创作局于一隅,也许人们不大经意,不过,今年颇有些新信息、新气象自高原东渐。”[24]这里使人们“不大经意”的原因,即所谓的“局于一隅”,显然不是指如马原等西藏作家在生活上偏居西藏、在西藏创作的问题,或者说不是主要针对的这个。最主要的是,马原、扎西达娃等在藏作家的作品大部分发表在偏居一隅的《西藏文学》上。1985年之所以能让人渐渐意识到“自高原东渐”的“新信息、新气象”,最开始的原因可能就来自于马原以西藏为背景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发表在处于文坛中心、广为瞩目的文学期刊《上海文学》上。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十多年之后一部知名的文学史里如下的叙述:“1985年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小说界出现了一批陌生而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名字:莫言、残雪、洪峰、马原、扎西达娃、刘索拉、陈村……伴随他们的名字,一股与寻根小说思潮相互关联而又迥异的崭新而陌生的风气骤然涌入文坛。”[25]姑且不论曾在《北方文学》发表过3篇小说、又于1984年在《西藏文学》上发表了他风格转型最明显的作品的马原,到1985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小说之后才以一个“陌生”的作家身份出现在小说界,确切地说是出现在小说界的关注视野之中。比马原更早发表作品、在《西藏文学》上发表了大量作品的扎西达娃,到1985年之前对文坛的中心来说,也依然是个陌生的名字。这就很明显能够看出期刊影响力的区别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马原带着西藏的背景出现在《上海文学》上,如果不是《西藏文学》以一种集束造势的方式推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这样有争议的专辑,如扎西达娃等作者,被文坛、被大众圈子所了解的时间或许还要往后推迟许久。所以当另一本重要的文学期刊《收获》的编辑程永新读了魔幻现实主义专辑后,分别给他并不认识的小说作者们写了信,西藏的这群作家们才会都“很激动”,因为“没料到专号还会在内地引起反响”。[21]168与《西藏文学》相比,在上海的另一本文学期刊、比《上海文学》更“大牌”的《收获》所能“引起的震动和影响都不可同日而语”,按程永新的说法,“只有《收获》才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和影响力。”[21]168-169
正是在期刊影响力大小不均的前提下,作家的文本实现了在发表基础上的第一轮筛选。发表在影响力大的期刊上的文本有机会进入进一步阐释的空间,而发表在影响力小的期刊上的文本则很可能被忽略,甚至可能被前者所遮蔽,从而使一个又一个“新生”作家以“陌生”的面貌出现在文坛的中心地带。显然,在没有方便的网络数据库可以查询的时代里,期刊的发表方式决定了它只能不断地向后累积新作,而无法去追根溯源重新整理出作家更早的文本。那些文本也因此习惯性地被阐释的视野排除在外,形成了最早的筛选。
而随之形成更深刻筛选的,则是批评家的阐释。简单说来,如果说期刊的筛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哪些文本能够成为建构作家形象的“素材”的话,那么批评家的阐释则决定了主要从何种角度去处理这些“素材”,完成作家形象的建构。这种阐释的过程还往往伴随着作家不会明言的“配合”以及与作家群体性创作倾向的相互“侵染”。(19)
我注意到,尽管马原在1985年就开始引起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比如《上海文学》、《收获》、《人民文学》的注意,(20)但在主流的文学批评杂志上,专门针对或者主要针对马原的小说的评论文章寥寥可数。1985年仅有一篇,即吴方发表在当年《文艺研究》第6期上的《〈冈底斯的诱惑〉与复调世界的展开》。1986年有3篇,即尧正发表在当年《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上的《互渗律:一种新的艺术关系》(部分涉及),张志忠发表在当年《上海文学》第4期上的《一个现代人讲的西藏故事马原小说漫议》以及辛力发表在当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上的《对一个遥远世界的发现——马原西部小说的视角特点》。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尧正的评论将马原的小说与莫言、王安忆的小说联系在一起,提出他们小说创作思维方式上的互渗律说法以外,其他专门的评论文章,主要关注或者切入的点,都在马原小说的西藏背景上。
这种情况在1987年突然转向。1987年,由《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主流批评杂志发表的针对或涉及马原小说的评论文章一下子增加到了十余篇,其中《文学自由谈》与《当代作家评论》最多,分别达到5篇和3篇。而且,这些评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马原小说的叙述方式。其中就有我们后来引为阐释马原的经典评论的,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这篇后出的评论几乎成为了对马原小说的唯一诠释,而早期所见的对于马原小说的西藏故事背景进行评论的角度则最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1986到1987年这个批评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收获》双月刊于1986年第5期开始相对集中地推出“新潮”小说,与马原相伴的苏童、皮皮、孙甘露、洪峰等开始集体出现在文坛的中心地带。(21)其中,以那句几乎成为马原代号、也成为“先锋小说”经典句式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开头的小说《虚构》,就发表在《收获》该年度第5期上。(22)一个更具有独特阐释空间的文本的出现让新进的批评家“终于找到了对手”,批评家也相当诚实地告诉读者,“马原声称他信奉有神论,这当然为我们泄漏了某些机密。不过我这里更感兴趣的是马原喜用的方式,就是说,解释他是以何种方式来接近他那个神的,比考辨这个神究竟是什么更有意思”,并进而表示,“也许,马原的方式就是他心中那个神祇的具体形象”。[26]批评家选择了一个他“更感兴趣”的角度,与之相呼应的,是一大群批评家开始选择从这个角度向马原的文本进发。而同时,以《收获》为中心,一大批适于以这种批评角度进行阐释的作家作品也开始集体登场。在一个如埃斯卡皮所说的存在着多向交流可能的“文学圈子”里,这种筛选也同时伴随着某种群体创作倾向的“侵染”,因为当一整个群体表现出某种共同的倾向时,批评首先会关注到的,往往是共同点。这很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形成对批评家和作家的双重刺激与“鼓励”。
当期刊的筛选与批评的筛选在文学圈子中完成了对作家作品的双重“删节”与“提纯”,进而形成某种舆论进入文学史与大众圈子之后,作家形象的建构也接近于成形,并在随后不断得到强化。而这个强化的过程,正来源于“在本专业中‘流通’的令人‘熟悉’的文学经典及研究方法已经形成一种‘过滤’机制,符合它的‘标准’的都被保留,与之相悖的则被淘汰”,[3]这里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文本,还包括对文本研究的方法与角度问题。而我们同时需要做的,就是对这种筛选与强化的过程本身进行关注与反思。
注释:
①程光炜曾就此指出:“在文学‘进化论’的叙述中,它(指‘先锋文学’——引者注)以‘形式革命’的姿态正式亮相登场,成为文学史读本中的一个公认的‘常识’。但是,潜伏其中的另一个文学‘常识’却始终无人问津:例如,在80年代的文学转型中,它是怎样获得自己的合法性的?”等等。参见《重评“先锋文学”》主持辞,《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
②甚至有批评者认为,西藏成为了马原“作为作家的转折点,或者说一段新的学历,那里的土地、山川、天空、气候,那里热情奔放的人,那里神秘的宗教气氛,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作家,他几乎没有给西藏留下些什么,但西藏却给了他一切”。参见张军:《如魔的世界——论当代西藏小说》,《西藏新小说》,第4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可以对“进藏热”做点补充的是《西藏文学》1985年第8、9期合刊所我徐明旭的评论《评内地小说中的进藏热》,文中说“近年来,内地小说的主人公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进藏热”,在引述了有关的三位作家的代表小说之后说“在三位作家心目中以及三位作家心目中的读者心中,西藏及其邻省藏区乃是一块惩罚之地、避世之地、浪漫之地。每当小说中人陷入绝境、困境、窘境、俗境或者其他什么微妙复杂的处境,需要赎罪、解脱、突变、再生或做出某种惊天动地、耸人听闻的奇事的时候,空气稀薄、日光强烈的世界屋脊就成为最可怕而又最崇高、最悲壮而又最时髦的出路”。并认为这可以代表不少内地作家和读者的心理。
④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第15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另外,1984年进藏的大学生、诗人惟夫把他自己的进藏则说得更明白:“我是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到西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意当老师,其次是想搞文学。我认为,搞艺术中国有两个最好的地方,一是北京,一是西藏。”参见子文(刘伟)编选《聆听西藏——以纪实的方式》。
⑤这是子文(也就是刘伟)2000年出版的一部名为《苍茫西藏》的著作的副题。
⑥网上通见的一篇帖子《西藏问题之我见十三——马原》中提及《中间地带》“这是一篇故事改写,他(指马原)的一个朋友讲故事,他来写,发表的时候朋友的名字排在前面”,这个朋友即孙效唐(《西藏文学》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7期、1985年第11期曾分别刊发署名孙效唐的《春寒》、《勒依之死》、《明月》等作品)但因为网上这篇帖子未具名,其中有些说法又稍有出入,此说暂存疑。
⑦马丽华在《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中谈到马原“写诗(多以陆高署名)诚恳老实,他把心灵中真诚的一角留给了诗”。《西藏文学》1985年第6期就刊发了陆高的《诗两首》。
⑧杨红:《边缘的吟唱:“西藏文学”之于“寻根文学”》,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⑨1985年马原被邀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文学研讨会。见马原《我与先锋文学——在第二届上海大学文学周的演讲》,《上海文学》2007年第9期。同年获邀参加《收获》组织的桂林笔会,结识《收获》编辑程永新。
⑩1985年,有批评者在评价《中间地带》时认为“自从西藏农村(牧区)也实行责任制后,已经出现了不少描写农村牧民由穷变富的小说。其中自然也不乏佳作,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只写了由穷变富的美好收获……却未涉及由穷变富的劳动过程……现在这一空白终于由孙效唐、姚亮的《中间地带》填补起来了”,小说讲述了“分属于汉、藏、回三个民族的三户农民面对共同的敌人旱灾”,一开始各自自救没有效果,甚至造成重重误会,后来结成互助组,合力战胜旱灾的故事,“作者显然想说明某种道理,这意图自然是好的,但是过于急切,效果反而不佳……多少给人以图解之感”。(参见徐明旭:《发现、发展、危机——〈西藏文学〉1984年小说漫评》,《西藏文学》1985年第6期。)这说明小说就题材和总体写法上来说,其实和马原最早的凡篇小说还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11)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第46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当然我们可以额外加以注意的是马原在之前的小说中就显示了某种探索的意图。比如《方柱石扇面》的结尾方式是“故事的结尾是几句对话”并以剧本对话的形式记录老耿与易莎的对话。而《中间地带》在结构上采用了“前面六节写抗旱过程,用顺叙,后面三节写明久之死,用倒叙。倒叙中又有顺叙,这样就制造了三重悬念”,语言方面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极端冷静的、新闻报道式的”,“冷静得近乎冷漠,平实得近乎干巴,但仔细品味,却能感到深蕴的热情与生活的表现力”。(参见徐明旭:《发现、发展、危机——〈西藏文学〉1984年小说漫评》,《西藏文学》1985年第6期)但与后来的变化相比,这显然还算不上“大变”。
(12)“姚亮”、“陆高”最初出现在马原在《北方文学》发表的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里,在这篇小说里,马原还没有在小说中自承虚构。
(13)徐明旭:《发现、发展、危机——〈西藏文学〉1984年小说漫评》,《西藏文学》1985年第6期。“两个梦”即扎西达娃的《白杨林花环·梦》和金志国的《梦,遗落在草原上》。
(14)比如刘志荣在《百年文学十二谈》中谈到王小波时曾拿马原来作对比,说“王小波其实是一个很先锋的作家,但这种先锋和以前的马原等人单纯在技术层面上的先锋不一样,是‘综合的先锋’”。(参见《百年文学十二谈》,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种对马原的看法虽然并非十分严谨的学术表述,却也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一般看法。
(15)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第26、118、3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程光炜在该书中以“鲁郭茅巴老曹”等文学大师为对象,对其作家文化形象在1949-1976年间的建构做了细致而系统的梳理,形成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16)参见[美]昂利·拜尔编,徐继曾译:《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第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7)李陀就在回忆中说:“1980年代的批评也是有权威性的。即使是在官方政策制约下的批评家(以下简称为“官方批评家”),也是有权威性的。”“1985年以后形成的新批评家群体,他们的权威性来自文学发展的创新诉求。”参见李陀:《批评是批评出来的》,《南方周末》2006年11月30日第D28版。
(18)当然,在交流更为便捷多样、信息交互能力增强的网络时代,这种效果显然有减弱的迹象,不过本文主要还是基于80年代的社会文化与技术背景之上,因此这种减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19)李陀在《批评是批评出来的》里提及了作家对于批评家的“态度”:“全世界都一样,作家一般都假装不在乎批评。1980年代,有作家甚至说,文学批评只不过是长在文学这棵树上的蘑菇。但作家都偷偷看批评;不但看,批评还能对他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0)这牵涉到80年代特殊的编辑氛围,即“1980年代,各个编辑部还都把‘为他人做嫁衣裳’当作编辑的天职”,“当时编辑一旦发现好作品,就会把作者请来,住下改稿,成熟了就发表。发表后还会请作者来开会。其他刊物的编辑看到新作者的出现,也都会马上约稿。”参见李陀的《批评是批评出来的》。
(21)据程永新的回忆,他在《西藏文学》的魔幻小说专辑以及与马原在桂林笔会上长谈的启发下,萌生想法,于1986、1987、1988连续3年在《收获》每年的5期、6期上比较集中地组织编发一批包含着新的创作倾向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尽管出于客观情况的考虑,《收获》“已足够谨慎。不树旗帜,不叫专号,不发评论注解性的文字”,但“事后据说作协有关领导颇有微词,说是把多数人看不懂的先锋小说集中起来隆重推出不知有何企图”。参见程永新:《八三年出发》,第1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22)有关这一时期“新潮”小说的发表状况,有黄发有的《先锋文学与期刊分化》一文中对《收获》所发小说的简单统计可供参考,参见黄发有:《媒体制造》,第22-2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