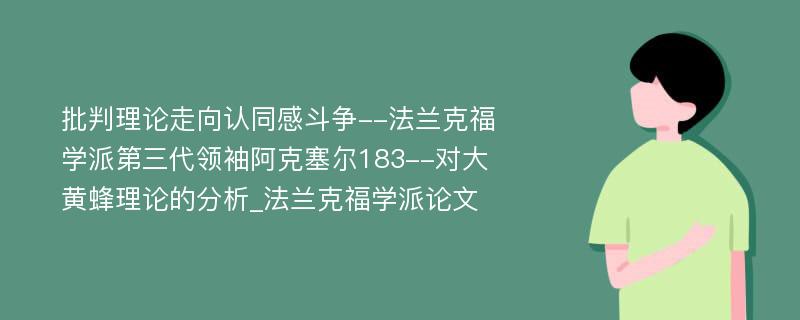
走向承认斗争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导人阿克塞尔#183;霍内特理论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理论论文,学派论文,领导人论文,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3年2月3日,经德国教育部批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虽然该所第一任所长是卡尔·格林伯格(Carl Grünberg),但由于在他领导下的法兰克福学派相对地默默无闻,所以人们普遍将更加有影响力、也取得了更加瞩目成就的霍克海默(M.Horkheimer)和阿多诺(T.Adorno)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领导人。第一代理论家时代的终结是在1970年前后,代表性事件主要包括:1969年阿多诺去世,1970年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去世,1970年弗里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出任黑森州教育总长,霍克海默退休,哈贝马斯于1971年前往斯坦堡大学任教等等。此后,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形成。就理论发展而言,这一代大约形成于1971—1981年间,在此期间,哈贝马斯带领一批研究人员将批判社会理论导向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就是哈贝马斯于1981年出版的巨著《交往行动理论》。可以说,该书基本上确立了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倾向与立场。除哈贝马斯外,第二代理论家还包括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布兰特(Gerhard Brandt)、弗里德堡、内格特(Oskar Negt)和施密特(Alfred Schmidt)。然而无论是成就还是影响,他们都无法与哈贝马斯比肩。
如今,虽然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还很活跃,然而1994年哈贝马斯的退休标志着批判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崛起。如果说这一代人中有谁接近于以哈贝马斯的规模来维系批判社会理论事业的话,那就是阿克塞尔·霍内特(Axel Honneth,1949— )。霍内特于1969年开始在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当时他深受阿多诺的影响,在政治上并不很活跃。1971年他转学进入波鸿大学,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在那里,霍内特开始研读哈贝马斯的著作,并在其硕士论文中论述后者的精神分析阐释学。之后他进入柏林自由大学攻读社会学。1984年他为哈贝马斯所聘用,成为他的助手,为期六年。在此期间,他们亲密合作,经常一起主持讨论会。聘用期满后,他先后任教于伯林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康斯坦茨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并于1996年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接过了哈贝马斯的社会哲学教席。(注:Axel Honneth,“Critical Theory in Germany Today:An Interview with Axel Honneth”,interviewed by Peter Osborne and Stale Finke,Radical Philosophy,65(Autumn 1993),pp.33—41;reprinted in A Critical Sense:Interviews with Intellectuals,ed.Peter Osborn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p.89—106.)2001年5月,霍内特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职务,终于有机会将一群研究者揽聚于自己的麾下,以复兴批判社会理论。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理论家,霍内特生活在前两代批判理论家、尤其是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巨大阴影下。然而,霍内特并未就此止步不前,他通过批判地反思前人的理论,树立起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中的一些薄弱之处,也为批判理论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霍内特的理论代表着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新趋势,值得我们重视。本文拟通过对他的主要论著《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中的诸反思阶段》(注:Honneth,A Critique of Power:Reflective Stages in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trans.Kenneth Baynes(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85).)、《支离破碎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论文集》(注: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Ess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ed.Charles W.Wright(Albany:SUNY Press,1995).)、《争取承认的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注:Honneth,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trans.Joel Anders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等的解读,简要介绍他对批判理论的反思及其理论创新。
一、反思批判理论,强调社会性在批判理论中的基础地位
霍内特对批判理论的反思有其独特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批判理论必须立足于人类的经验利益或道德体验。只有这样,它才不是无根之木。他将这一观点追溯到从马克思到卢卡奇的批判理论,指出这一传统始终坚持任何批判都必须“能够在社会现实中重新发现自身所具有的因素”(注:Honneth,“The Social Dynamics of Disrespect:On the Location of Critical Theory Today”,in Habermas:A Critical Reader,ed.Peter Dews(Malden,Mas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9),p.322.)。霍内特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回到社会层面的研究上去,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权力的批判》中,霍内特指出,批判理论的发展中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那就是对社会层面的研究不断被边缘化。他认为批判理论真正应该做的是对“社会性”进行描述,以强调社会是通过现实中的社会群体之间常常是互动的冲突而实现再生产的,这些群体本身是参与者不断进行阐释和斗争的结果。在《争取承认的斗争》一书中,他提出,社会群体既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也代表了人类全面发展的资源。
霍内特以上述理论作为出发点,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权力的批判》中,霍内特高度评价哈贝马斯和福柯“对社会性的重新发现”,认为这克服了从霍克海默到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在社会分析方面的缺陷:“阿多诺必定不能完成分析社会的任务,因为他毕生受困于一种总体化的大自然统治模式,因此无法理解社会的‘社会性’领域。”(注:Honneth,“Author's Preface”,The Critique of Power,p.xii.)按照霍内特的理解,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过分关注工具理性对大自然的宰制,从而忽视了社会群体的兴起与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影响与作用:霍克海默的历史哲学主要关注社会劳动维度,因而无法从概念上对日常文化生活和社会冲突展开有效的分析;而在阿多诺那里,对社会劳动维度所作的概念重估却产生了一种否定的历史哲学,其中,批判理论实践自身所基于的那个领域已经无法辨认出来了,因为所有的社会行动都被看作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统治的一种延伸。(注:Honneth,“Afterward to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The Critique of Power,p.xvi.)
然而,在福柯和哈贝马斯那里,理论的研究对象终于回到社会行动层面,因而社会性这一领域得到了更好的处理。霍内特认为,福柯将社会统治的根源追溯到主体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之中,从而卓有成效地揭示了被阿多诺系统地误解了的社会互动与冲突。不幸的是,福柯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分析在阐释更为复杂的社会统治结构的形成与维系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它的构想偏离了规范性共识(normative agreements)和道德动机(moral incentive)。霍内特认为,相比之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要优于福柯的系统理论的解决方案,因为它认识到共识(consensus agreements)以及策略性冲突在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权力形式中所起的作用。
尽管如此,霍内特还是认为,哈贝马斯没有给社会存在领域以应有的关注。早在《工作与工具性行动:论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一文中,霍内特就指出,哈贝马斯从主体间理解的方向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发展,导致了“在社会劳动中依然可寻的冲突潜能在行动理论中的消失”。换句话说,通过将劳动简约为人性(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纯粹技术性的关系,哈贝马斯“消解了马克思力图在社会劳动与社会解放之间建立起来的直接联系”。(注:Axel 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pp.40—48.)在霍内特看来,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世界模式:
不仅放弃了对经济生产和政治管理之具体组织形式的合理批判的可能。更关键的是,哈贝马斯还丢弃了他最初开拓的交往理论路径(这再次使他成为我们在此考察的批判社会理论传统的继承人):即将社会秩序理解为由文化整合在一起的群体之间经由制度中介有可能产生的交往关系。就权力的不均衡分配而言,这种关系通过社会斗争而产生。(注:Honneth,A Critique of Power,p.303.)
霍内特认为,“有希望成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的惟一路径不是在合理化的逻辑的参照下解释社会发展,而应该是在一种社会斗争动力学的参照下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动力学在结构上身处于互动的道德空间之中”(注:Honneth,“Afterward to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The Critique of Power,p.xvii.)。在霍内特的模式中,社会整合过程被看作是社会行为者之间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在此,可以看出霍内特开始着手建构他自己基于承认斗争理论的交往范式了。
二、建构新的批判理论:承认理论
霍内特的模式调和了哈贝马斯的道德洞见与马克思的物质兴趣,从根源于“物质财产分配不公”的描述,转向了“文化与心理的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公”。霍内特认为构成工
人斗争基础的不是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公,而是“文化教育、社会荣誉和工作机会等的分
配不公”。霍内特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是“社会尊严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隐蔽的
伤害”。他们缺乏政治上认可的一贯的语言来表达他们所受的伤害,然而他们随时都有
可能采取社会抗议和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寻求自己意志的表达。(注:Axel 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pp.217—219.)因此,霍内特不是将批判理论建立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之上,而是将抵抗的根源建立在“处于得到认可的规范性冲突的阈限之下”的行为者身上。霍内特并非要描述工人们为取得更大的自主权而进行的斗争,而是致力于发现他们的自立自主所依赖的“道德语法”。这是霍内特与传统阶级斗争理论最大的不同,也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在他那里留下的深刻印记。不过,霍内特的交往范式与哈贝马斯的范式不同在于,它主要不是按语言理论来构想的,而是从有关承认关系及其所受到的侵犯的理论来设想的。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被锁定在对这类侵犯的典型反应即羞辱、生气和义愤的体验以及蕴涵在这些体验之中的对社会正义的渴望之上。这就是霍内特提出的承认理论的交往范式,它构成了霍内特对哈贝马斯的批评的核心。这也是霍内特对批判理论所作的独特贡献。
霍内特的承认理论直接借鉴黑格尔早年在耶拿时期所阐发的承认斗争理论。为了超越黑格尔的思辨和形而上学特性,霍内特诉诸米德(G.H.Mead)的自然主义实用主义,诉诸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科的经验研究,以明确个体的自我实现所需要的主体间条件。在阐释这些条件的过程中,霍内特形成了他有关“伦理生活形式”的概念,即一种批判性的规范标准。
霍内特的承认理论以人的认同形成(identity-formation)为开端。他将人的认同形成描述为一个为了在互动中获得同伴的承认而进行的主体间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自信、自尊和自重的发展。霍内特认为这三种关系是个人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这种关联涉及一种主体间过程,就是说,个人对自我的态度形成于个人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关系中,即争取某个你所承认的人对你的承认。因此,自我实现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建立起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这些关系不是脱离历史被给定的,而是通过社会斗争才得以确立并展开的。在《争取承认的斗争》一书中,霍内特总结出三种形式的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应自信、自尊和自重这三种个人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
第一种形式的承认是“爱”。(注:Honneth,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pp.95—107;pp.132—133.)“爱”先于其他承认形式,霍内特因此将它宽泛地界定为原生关系。(注:Ibid.,p.95.)他认为,个体只能在得到无条件的爱和情感所支撑的与原始他者的相互承认关系中获得健康的自信。如果孩童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顺利的话,那么它就逐渐能够产生一种对环境的根本信任,同时也能够发展对自己身体作为自身需求的信号的可靠来源的信任感。没有这一点,他们就无法信任自身以及周遭世界的基本稳定性。霍内特坚持认为,爱与自信乃是任何人类社会中自我实现的前提。这是自信与后面两种承认模式的区别。
第二种形式的承认是“权利”。(注:Ibid.,pp.107—121;pp.133—134.)这种承认乃是对人类主体的普遍特征的承认。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承认而获得自尊。自尊是在对人的自主道德行动的相互认可中获得的。因此,要拥有自尊,就是要感觉自己是一个道德上负责的行为者,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有能力参与哈贝马斯所说的“话语的意志形成”这种社会决策活动的人。个体能够通过法律体系赋予社会所有成员的普遍权利,将自己理解为与其他成员平等的人,每个人都必须在对等的相互关系中对待他人,他们也有权就如何构想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作出自己的决定。权利之所以对自尊很重要,是因为权利保证人们有真正的机会来发挥普遍能力。这并不是说一个没有权利的人就没有自尊,而是说一个自尊的、自主的行为者,只有在被认为拥有“法定”的能力、被承认道德上能够负责时,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第三种承认指的是与“社会尊严”相关的“团结”。(注:Ibid.,pp.121—130;p.134.)与权利的法律承认不同,社会尊严乃是对人“具体特性与能力”的承认,它预设了“价值共同体”的存在。在这个共同体中,人如果作为一个独特的、有着特性和能力、能够为该共同体的共同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个体而得到承认,他就能获得自重。因此,如果说自尊是认为自己与他人拥有同样的地位和待遇,那么自重更强调的是自己独特、个别的性质。不过,这种视自己为一个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个体的感觉并非只是建基于一些琐碎的或消极的性格特征之上。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是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个性与自重是相互关联的。霍内特用“团结”这一术语来界定一个能够广泛地获得自重的文化氛围。虽然“与他人团结”有时候等于同情,但霍内特认为,只有当共同的关怀、利益或价值存在时,人们才能恰当地言及“团结”。霍内特宣称,在一个好的社会中,个体能够真正拥有充分实现自我的机会,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能够兼容个体关心的问题,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给共同利益作出贡献,从而赢得尊崇。然而,与权利领域不同,团结缺乏法律关系所特有的普遍性:一个社会支持何种特殊价值具有偶然性,它是社会文化斗争的结果。
霍内特指出,以上三种承认形式是现代社会自律自主的个体认同形成的条件,对这三种承认的形式的否定——霍内特将这种否定称为“不敬”——将造成“负面情感反应”,而这构成了“争取承认的斗争”的“动机基础”。(注:Ibid.,Chap.8.)因此,社会斗争不能仅理解为利益冲突。他认为,由争取承认的要求被拒绝而产生的侮辱和愤慨暗含着对各种社会安排的规范性判断,因此,这类斗争的“语法”成了道德性的东西。这样,一个公正的社会的规范性理想就经由历史上的争取承认的斗争而得到了确证。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霍内特对哈贝马斯的继承与批判。霍内特师从哈贝马斯,以一种理想的未受损的主体间关系作为批判理论的规范性根基,然而与哈贝马斯将这一理想基于未被扭曲的语言交往情境之上不同,霍内特将它锁定在未被扭曲的社会承认之上,以社会成员健康的、未被扭曲的自我实现作为美好社会的前提。这种理想为解释社会变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基础,也为个体和群体获得承认的斗争提出了规范性要求。遭遇不敬是一种普遍的个人经验,当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获得完全的自我实现所需要的承认遭到了系统的否定时,集体的政治抵抗就有了潜在的动机。
1994年在题为《不敬的社会动力学》的演说中,霍内特以承认理论为基础,对哈贝马斯基于语言理论的交往范式进行了批判,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理论。(注:Honneth,“The Social Dynamics of Disrespect:On the Location of Critical Theory Today”,in Habermas:A Critical Reader,ed.Peter Dews(Malden,Mas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9),pp.320—337.)霍内特认为,主体所体验到的道德期待(moral expectations)受挫的感觉“不是因语言规则受限制而引起的,而是因获得的认同要求被侵犯而造成的”。(注:Ibid.,p.328.)因此,必须将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更普遍地落实到个体对“道德期待”被侵犯的消极体验之中。霍内特指出,这并不是一件可以从外部推演出来的事情。相反,被冤的感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道德要求,源自于受害者的主观体验,并且在某些文化条件下表现到社会斗争中。他认为,虽然某些社会斗争的确是由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然而一旦瓦解了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斗争也表达了人们的道德要求,而这些要求可以充当规范性标准。
三、承认理论的缺陷
霍内特的承认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将批判斗争的根基重新落实到了社会层面,将目光重新投向社会各群体的日常生活和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上的群众斗争的关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彻底解决了批判理论的困境。实际上,霍内特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批判理论传统中固有的一些问题。
首先,虽然霍内特的承认理论代表着社会批评理论的一种转向,即从只关注物质剥削与统治、财产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身体伤害转向对人的荣誉感、自尊心和尊严的伤害。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主张“道德性”与“物质性”的分离。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文化根源的关注,霍内特使这两者之间的分裂永恒化了。如果说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过多地关注社会体系对个体的异化统治,那么霍内特的问题就在于他过低估计了社会体系“损害”主体间性的能力。他并未将批判理论建立在个体克服社会系统的他律性的斗争之上。物质性与道德性之间的分离加深了这一问题。(注:Bob Cannon,Rethinking the Normative Content of Critical Theory:Marx,Habermas and Beyond(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2001),p.147.)
其次,《争取承认的斗争》一书的副标题是《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所谓语法,显然是从具体社会冲突中抽绎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阿多诺早就指出,抽象的语法和概念必然扼杀具体语言和事物的丰富的特殊性。霍内特对所谓“语法”的关注,导致社会成员决定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能力被忽视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关怀和价值被取消了,剩下的只有抽象的语法。因此,霍内特所构想的只是一种专家文化,其中完善的社会制度从外部被强加给社会各成员。
霍内特批判理论的最大困难在于,“承认斗争”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正如霍内特本人所承认的,承认的获得不仅可以在民主群体中、也可以在新纳粹组织中寻得。霍内特不得不承认,遭到轻视的感觉实际上缺乏“规范性方向”。
总而言之,霍内特理论中最深刻的矛盾,其实就在于对具体的社会存在领域的关注与对普遍的规范性批判基础之间的对立。这实际上是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挥之不去的理论与实践、规范性与个体关怀之间的矛盾。批判理论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