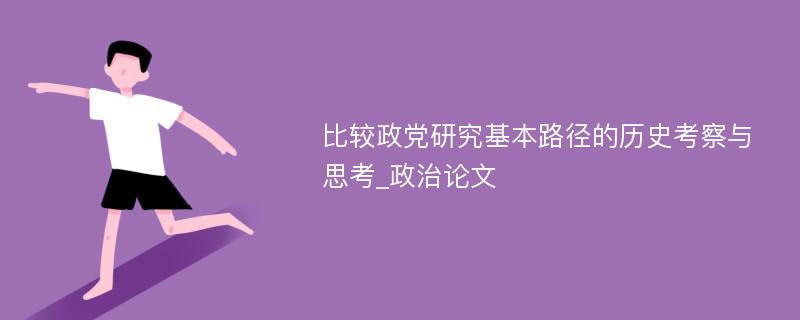
关于比较政党研究基本路径的历史考察及其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路径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西方民主宪政和议会民主的产物,同时也是民主宪政和议会民主的重要标识。易言之,现代政党是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和政治参与的大众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同时,现代政党又是选举权普及和政治参与扩大进程中的主要推动者。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和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政党和政党政治研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题域之一,进而又成为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与此相应的则是各种学术理论和学说、主张层出不穷。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史考察的方式,对有关政党研究的基本路径和相关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描述。
一般公认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雏形源于17世纪70年代的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以及此后的美国联邦党和反联邦党(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随着各国议会斗争的激烈和宪政民主的确立,政党组织开始普遍出现。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批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不仅改变了政党社会属性的质谱系构成和政党竞争的政治格局,而且导致政党的组织样式和活动形式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那种具有明确而具体的政纲、稳固而分化的组织结构、稳定而庞大的党员队伍、统一而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丰富多样的组织活动的政党组织形态,就是经由社会主义政党的启发和刺激,经过传统政党的改造和新兴政党的模仿过程而成为现代政党的普遍形式的。(注:Maurice Duverge,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1964,p.32.)
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与创立社会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写下的诸多著述,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政党的学说理论,不仅成为当时及以后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而且成为政党研究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毛泽东等,都在他们创建和领导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中提出了诸多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学说理论。从比较政党研究的角度论之,这些文献以其对政党纲领和意识形态问题、政党及其阶级基础问题以及纲领指导的行动策略问题的关注和阐发而开出了独特的研究理路。
政党问题进入学者的视野并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则是随着政党组织的普遍发展而发生的。但相对而言,早期的学术作品主要以单一国家的政党为对象,集中于描述某一政党或某几个政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意识形态立场,因而缺乏必要的分析力度和理论建构。例如洛威尔在1896年发表的《大陆欧洲的政府与政党》(注:A.Lawrence Lowell,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1896.)一书,与其说是研究著作,不如说是历史记录更为恰当。其他那些以一国政党为对象的书籍也大体如此。“尽管西方世界几乎所有政党的历史都写成了书籍,但当我们进一步思考政党性质的分析时,却发现这一方面几乎根本就无人涉足。”(注: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2,p.6.)
但这种情形不久就得到了改变。1902年发表了《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注:M.Ostrogosk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ed.& Abridged by S.M.Lipset,Tr.F.Clarke,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4.)一书的奥斯特罗果尔斯基(1854-1919)堪称从事比较政党研究的第一人。他以分别设卷的方式,比较研究了最早出现政党政治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的政党,而且就政党的组织结构及其与民主原则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而1911年出版《政党论:现代民主制寡头趋势的社会学分析》(注: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2.)一书的米歇尔斯(1876-1936),则集中比较了德、法、意三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他对政党组织的内部问题,如领袖、组织专家和官僚与普通党员的关系,领导机关、管理机构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政党的组织动员与政治心理变化等等,表述了相当深刻的看法;对不同的政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党与政府的问题等等,也有极其精彩的见解。《政党论》因而成为比较政党研究的经典著作,而米歇尔斯在书中所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至今仍是政党研究者争论不休的理论命题。上述两部开创了比较政党研究的著作,从方法论上讲,类似于当代比较政治学所指称的“集中比较”,即选择数量有限的个案,确立相对明确的比较框架并选择共同的比较变量,在丰富的个案资料的基础上展开比较精细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讲,上述两部著作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这两部著作对后来者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在其问世后的一个时期内却造成了奇特的空白。也就是说,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间,在比较政党研究方面并没有出现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究其原因,一是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和米歇尔斯确立了一种后人难以逾越的学术标准;二是他们对政党政治和民主发展所持的悲观态度竟在一定程度上为两次大战期间的事态发展所证实。当时代议制政府的各种危机,至少在现象上是与政党竞争所存在的弊病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有关学者的兴趣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二战以民主战胜独裁的结局告终和战后政党政治的急剧发展为改变上述状况创造了基本条件,学者的研究热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因而比较政党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而开风气之先者首推法国学者迪维尔热。在那本被誉为比较政党研究“里程碑”之作的《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注:Maurice Duverge: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1964.)一书中,他继承了米歇尔斯所开创的传统并加以光大,以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政党制度作为中心,全面论述了政党的历史来源、组织结构、党员与领袖等主题,深入讨论了政党制度的分类、政党竞争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党制度与一般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他还特别强调,政党是任何现代民主政体所不可缺少的,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运行方式。这本《政党概论》以其论述范围之广泛和分析见解之深刻而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短短几年期间即被译成十几国文字,成为比较政党研究的“百科全书”。
以迪维尔热的《政党概论》为契机,有关比较政党研究的著作大批涌现。在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学关于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模式和大多数理论命题已经基本确立。有关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至今仍是人们在研究政党问题时不断加以引用的。但此后的“行为主义革命”又造成了比较政党研究的特定发展和变迁。概括地说,在研究主题方面,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政党的选举行为、选民的政党选择和政党内部的组织行为等方面的内容;在方法上则大量地使用了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理性分析方法和组织理论以及统计分析等手段,将它们应用于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政党组织及其政治行为(注:参见S.M.Lipset and S.Rokkan(eds),Pary System and Voter Alignments:G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pp.7-8,pp.35-40.)。而同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亦促生了政党和政党制度在研究重点方面的扩展,主要涉及第三世界大批新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政党研究、政党政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等等(注:Joseph LaPalobara and Myron Wein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
在有关比较政党研究的专题性成果大大丰富的基础上,综合性的研究著作应运而生。萨托里1976年发表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第1卷(注:Giavani 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A Framework for Analysis.Vol.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安杰洛·帕诺比昂科1982年出版的《政党概论:组织与权力》(注:Angelo Panc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published in 1982;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98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以及同一年由列昂·爱泼斯坦推出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注:Leon D.Epstein,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都是在宏观理论和基本观点方面均有所创新的学术著作。尽管各有偏重,但这三部著作在政党组织与政党制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更加深刻地开拓了自迪维尔热以来所开始的比较政党研究。
此后也有类似的综合性著作问世,例如阿兰·威尔的《政党与政党制度》(注:Alan Warem,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Oxfro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再如彼得·梅尔的《政党制度的变迁:研究途径与阐释理解》(注:Peter Mir,Party System Change: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不乏原创性的意见,但较之于前述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更像是比较政党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因而不可能具有前述各书所造成的轰动性和启迪性效果。
在比较政党研究领域,除了上面提到的综合性著作以外,还有不胜枚举的专题研究著作和文集。但综合起来考察,这些林林总总、数量繁多的政党和政党政治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按照研究所涉及的具体领域的对象性差别而首先区分为政党组织研究和政党政治研究两大部分。而确切地说,这种区分所体现的是不同的学术理路。这就是所谓政党研究的功能路径和结构路径的区别。(注:参见William R.Schonfeld,Political Parties:The Functional Approach and the Structural Alternative,i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16(July),1983,pp.477-499.)
所谓功能研究路径,是指侧重研究政党在政治体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功能作用问题的学术努力。在这一方向上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往往强调政党居于政府与选民之间的中介地位,发挥着特定的中介功能,因而主张研究政党在政治体系内的影响力,注重政治环境与政党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按照政治学功能主义学者阿尔蒙德的理论框架,政党在政治体制内的功能大体包括目标制定、利益聚集和利益表达、社会化与政治动员、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推选。(注:参见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其中,目标制定是指政党作为特定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和承载者,往往会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提出有关社会发展总方向或基本的政策主张,并以此教化、感召和激励党员和大众遵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向着特定的方向共同努力以改造社会或改变公共政策。为此,相关的政党研究须考察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一立场与基本政策主张之间的关联及其体现——政党纲领、政党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最高宗旨和最低宗旨等等。利益聚集和利益表达是指政党为争取选民的支持或服从党内政治压力的要求而将选民和党员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和政策主张,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渠道,收集起来并条分缕析、综合概括,再以系统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以此向政府施加有组织的压力,争取有利于自己所主张的政策变化或人事调整。为此,相关的研究集中于政党的政策声明、对于特定的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表态。社会化与政治动员则是指政党作为特定人群的集合体,往往会利用组织教育、培训和宣传手段,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党员和大众,以期将这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内化为党员和大众的个人性选择,同时,动员党员和大众参与特定的政治活动和募捐与捐献、竞选、股票、集会、游说、游行和签字、写信等等,以有组织的方式宣示和传播某种政治要求和政治意愿。为此,相关的研究关注于政党实行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机制、途径和效果以及社会化的受众或对象等等。政治精英的形成和推选是指政党往往会在其内部培养精英人物或将社会优秀分子纳入党内,最终将这些信奉本党意识形态、忠实于本党组织和执行本党政策的政治人物推举到政府职位或公共权力职位上去。为此,相关研究侧重于政党精英人物的产生过程和推选机制、精英人物的特殊才干和背景、政党制约这些精英人物的机制和纪律及其效果等等。
由此可见,所谓政党的功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于政党与政治机构的关系,关注于政党作为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承担的独特功能。而这在理论上也就预设了政党是为政治体系维持自身所不可缺少的功能性部件。进一步讲,这也预设了政党是一个独立实在、内部均质的行为主体,且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与政治机构发生关系。就此而论,这种政党的功能研究路径实际上受到了政治学当中功能主义理论的明显影响。
但恰好是针对政党的功能研究路径中的理论预设和理论资源,不少学者又以社会冲突理论作为替代性的理论依据而展开关于政党问题的研究。但相对而言,这种研究主要还是体现在政党研究的结构路径中。这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党的组织结构研究,二是政党与政治结构研究。
所谓政党的组织结构研究是指侧重于研究政党本身的组织形态、活动样式和内部结构关系的学术努力。主张这一路径的学者往往强调政党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团组织之一,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为政治体系实现了何种功能,而在于政党是追求共同目标的人们的集合体,其内部结构关系对其活动和行为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而他们特别注重对政党内部活动或权力角逐的研究。但应当指出,几乎所有政党政治的研究者都十分强调对于政党组织结构的分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使用不同路径的学者中都预设了政党组织结构对于政党的重要性,也都从这一点出发研究政党的功能或其内部活动。总之,政党的研究者都认为,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不仅影响着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而且决定着政党成员之间的活动领域与权力互动关系,甚至关联着政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
首先在这一方向上努力的学者关注的是政党具体的组织结构样式对于政党的影响。例如迪维尔热认为,政党的组织结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特定的组织结构往往设定了党员活动的总体环境,建构了党组织内部团结的基本形式,决定着政党领袖的选择机制及其领袖间的权力运作,因而会直接影响政党的政治竞争能力,进而塑造不同政党间的地位关系。为此,他分类研究了政党组织内部党员与党组织的直接结构与间接结构问题,即个人入党和集体入党所造成的结构差异,政党内部基层组织的结构和基层组织与中央组织之间的结构关系,并且评价了不同结构所造成的政党组织力量和活动能力上的区别(注:参见Maurice Duverge,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1964,Chp.1.)。再如潘尼比安科对反对党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组织结构对于反对党而言更为重要,因为反对党无法像执政党那样依靠官僚体系的支持,也无法利用国家及其所属机构,无法得到其他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援,因而只能凭借组织结构的优势来有效和持久地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与执政党进行长期的政治竞争。(注:Angelo Panc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published in 1982;translate into English in 198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其次,组织结构路径的主张者所关注的是影响政党组织结构的历史因素。在他们看来,当下的组织结构是由历史因袭而来的。例如潘尼比安科认为,对于政党组织结构的研究,应当首先集中于研究影响政党组织结构演变的各种因素。而从组织理论的角度而论,探讨政党组织结构的现状与未来走向,必须回溯政党的形成及早期发展阶段。具体而言,必探讨政党形成的历史渊源、其制度化方式与程度、外界环境特征三大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影响与作用。(注:Angelo Panc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published in 1982;translate into English in 198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所谓政党组织结构的历史渊源,主要是指在政党创生时或创生之初对政党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来源”问题。这主要有三类:其一是政党组织结构创生和发展的方式、方法、出发点或起点的问题。迪维尔热认为,现代政党无非是从议会内的组织演化而来或从议会以外的团体扩充而来,二者必居其一。因此,现代政党可分为内生(源)政党与外生(源)政党两类。由于历史起源的不同,两类政党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不同的组织结构。前者往往体现为议会党团高于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且有很大的权力和自主性,而后者则有强大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议会党团不得不更多地服从于党的领导而不能自由行事。而爱泼斯坦则提出新的区分标准和评价准则。在他看来,政党组织由上向下的渗透式建立与组织由下向上的扩散式建立有所不同。组织由上向下的渗透或深入,是指首先建立中央层级的组织机构,然后再有控制或有主导地建立和发展地方或中间层级的组织;组织由下向上的扩散,是指首先由地方精英建立地区性的组织,然后再逐渐扩大并在全国范围内整合为政党组织。前者意味着中央机构相对于地方基层组织有较高的权威和领导效力,而后者则相反。(注:Alan Warem,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不同的发展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组织结构特点。而从欧洲历史发展来看,尽管大多数保守党和自由主义政党都是属于内生(源)性的政党,但从具体发展过程来看,保守主义政党大多是组织的深入或渗透类型,而自由主义政党大多是扩散而来的。相对而言,社会党和共产党大都属于外生(源)政党,且具有组织深入或渗透式的建立过程。
其二是政党是否有外在支持力量。在潘尼比安科看来,政党的外在支持力量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国内的有组织力量,如工会组织或其他社会团体;二是国外或国际性的有组织力量,如共产国际等。一般说来,政党在有外在支持力量的支持下建立,无论其是来自国际还是国内,都会使政党成为外在力量的政治工具,进而影响政党领导阶层合法性的来源。因为在有外在力量支持的情况下,政党成员的主要效忠对象是外在的支持力量,而政党内部的组织效忠则成为间接的、次要的。由此,外在支持力量不仅成为领导阶层合法性的根源,甚至还左右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成为影响政党组织结构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在另一方面,外在力量的支持容易使党扩大影响,迅速取得成功。
其三是克里斯玛(个人魅力)型的领袖存在与否。按照潘尼比安科的说法,一方面,任何政党的草创时期,在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中,或多或少地都有克里斯玛的存在,这甚至成为领导者合法权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一些特殊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无此则无新生政党的生存;但另一方面,政党如果完全依赖克里斯玛型的领袖而生存,则当个别领袖人物凋零之后,政党的发展也将停滞,甚至陷于解体。因此,政党在发展中能否将其创建者个人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成功地转化为政党自身的组织权威,显然成为政党组织结构发展的关键课题。(注:参见Anglo Panebianco,Political Party: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52-53.)
政党组织结构路径的主张者所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所谓政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问题。因为所有的历史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政党组织状况的影响,而测度组织状况历史发展的有效指标就是制度化程度。就此而论,一般的规则是,如果政党的创建与随后的发展表现为由中央深入地方的样式,并且不依赖外在制度的支持,克里斯玛型个人领袖的权威较早地转化为政党的组织权威,则政党就能够发展相对健全完善的组织结构,其政治竞争力也会逐步加强;反之,则政党组织结构的制度化进程将严重受阻,组织自身经常面临重大的内外挑战,最终会弱化政党的相对竞争地位与政治竞争能力。
当然,有关政党组织结构的制度化与制度化程度是政党研究中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问题。亨廷顿在1965年发表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并用作测度政党组织强弱与否的关键性指标。尔后便引起了诸多学者参与讨论,因而对这一概念也提出了不同见解。例如威尔夫林将政党的制度化程度界定为制度“具体化”的不同环节,包括制度设定、创造、发展与维持的过程以及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所具有的特征问题。(注:Mary,B Welfing,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frican Party System,Beverly Hills,CA:Sage,1973,p.11.)而潘尼比安科则认为,政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在个人层面与组织利益的维护和组织效忠的扩散有关,而在组织整体的层面则与自主性和系统性有关。自主性是指政党与其外在环境的关系,系统性是指政党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就自主性而言,任何组织与其外在环境间必然存在着交换关系,也就是说,任何政党组织都必须提供其自身所具有的内部资源或独占资源,用以与外部交换对自身运作不可缺少但自身又无法提供的人力与物质资源;同时,一个政党所提供的不同类型的刺激不仅应当针对其内部所属成员的需要,也须考虑组织以外的支持者的需要。因此,当一个政党组织能够直接控制其与外在环境的交换过程时,它就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而当一个政党组织所需要的部分或全部必要资源掌握在其他组织手中时,则其自主性就较为脆弱。就系统性而言,任何组织内部的不同部门或部分之间均会发生互动关系。一般而论,当一个政党组织允许其内部的次级部门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时,即意味着这一次级部门可以独立于中央组织之外,掌握自身运作所必须的资源或单独与外部环境交换以取得自己之所需,因此这一政党组织的系统性程度就较低;相反,系统性程度较高的组织则意味着组织内部次级部门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与维持,是建立在组织资源与交换过程均由中央集权式控制的基础上的。由此,一个政党组织的系统性越高,则其对外部环境关系的控制程度也就越集中;反之,如果次级部门能够独立地由外部获取资源,则显示其政党组织的系统性较低。必须注意的还有,上述自主性与系统性是密切相关的。政党组织较高程度的系统性,通常也就意味着其对于外部环境的高度自主性,反之亦然。(注:参见Anglo Panebianco,Political Party: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54-57.)
但相对而言,仍是亨廷顿的定义较为周详。在他看来,“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注: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一定义显然是兼顾了结构面与行为面,因而为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按照他的论说,制度化程度的测度指标有四个,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结性。其中,适应性是指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函数,遇到的环境挑战越多,经历的时间考验越久,则组织的适应性就越强。在现实生活中,组织的适应性可以由组织存在的时间长久与否加以判定。其判定方式有三:年度的、代际的和功能的。复杂性是指组织的次级单位在层级与功能上的繁化与分化。其规则在于:一是次级单位的数量与种类越多,政党组织获取和维持个人成员效忠的能力就越强;二是组织的目标具有多元性,则政党自我调整适应的能力就越强。自主性是指政治组织及其程序安排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或行为方式以外的程度。一般来说,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参与政治生活的新兴团体,它们既不认同于既有政治组织,又不听命于既有的政治程序安排,最终将摧毁原有的组织与程序安排。相反,在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体系或组织内,其自主性为各种机制所保护和维系着,限制了新兴团体对于既有体系的冲击,因而保障了体系本身的正常运作。凝结性是指在组织内部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这是组织制度化的关键条件。一个有效运作的组织,其内部对于在组织的功能边界内解决争端的各种适用程序必须具有某种实质上的共识;这种共识还必须扩散到所有的组织成员。应当说,亨廷顿的见解对于理解和研究政党组织的制度化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政党组织的研究者还关注着影响政党组织结构制度化的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政党组织的中央官僚组织体系的完善程度,所谓组织结构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必然也是官僚化与中央集权化程度较高者;如政党内部同一层级间组织结构的同质程度,因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其散布各地的地方或次级组织结构、建构原则与方式应当趋于一致;如政党财政来源的多元与稳定的问题,因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通常有多元与稳定的财务来源,以确保其财务的充足与独立,避免为外在团体所控制,以达到自主性;如政党与外在支持团体的互动关系类型,因为任何政党皆需依赖外在团体的支持。但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必然是能够充分主宰而不受支配于外在团体的;如政党内部程序运作与实际权力的结合程序,因为尽管政党内部的权力运作未必尽如其明文规定之法规与程序,但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其外部支持团体和力量不易干涉和左右政党内部的决策与权力运作。最后则涉及政党组织成员与选民队伍的数量关系及其稳定程度,因为相对于选举实力而言,如果政党党员的数量太少,或是无法随着选举实力的发展而增加,则政党本身必然不易走向制度化;另一方面,一个政党如果无法获得固定选民的支持,甚至无法充分掌握支持选民的来源与特质,必将难以发展其组织,其制度化程度也就相当低了。当然,政党在代议机构中的力量及其稳定程度也会影响其制度化,因为政党在代议机制中的席位多寡是其实力和政治竞争力的最佳体现。一个政党,特别是反对党,倘无法在代议机构中占有相当数量的席位,则其影响力微不足道,进而影响其吸纳资源与支持的能力,生存既已堪忧,何论发展制度化。
相对而言,所谓政党与政治结构研究,是指那些关注于政党组织与其所在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关系的学术研究。
在这一方向上努力的学者,自然承认政党组织的重要性,但又强调其并非能够独立存在和发展,政党组织实际上是外在政治结构的因变量。易言之,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党组织结构,同时也就规定了政党在政治结构中的角色作用。
在这方面,李普塞特和罗坎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政党选择冻结”。在他们看来,当选民在大选投票之际,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择一而行的,但实际上在其个人的投票决定之前,其决定即已历史地、逻辑地存在了。而这种个人选择的“冻结”又是“政党结构滞后”的体现。他们认为,现代政党和政党体制实际上主要是几个世纪以前即工业化初期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冲突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的各国政党制度,除极少数但却不无意义的例外,均反映了20年代的社会分裂结构。”按照他们的区分,这类分裂线包括“中心—边缘”、“国家—教会”、“土地—工业”和“业主—工人”。当然,这类分裂线对于政党组成和政党结构而言往往是交叉作用的。而在这样的分裂基础上所组成的政党又通过其意识形态宣传和外围组织所展示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功能,通过由家庭代际传递的政党忠诚而实现的社会化功能,而在若干年里不断强化着特定的政党认同。而其后果就是,旧的政党组织能够超越政体变迁的影响而生存下来;新的政党组织出现和崛起的机会相当弱小,且很难得到相当数量选民的永久支持;既有政党之间出现竞争垄断局面。(注:参见S.M.Lipset and S.Rokkan(eds),Pary System and Voter Alignments:G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pp.35-40.)
但沙特施奈德却认为,政党组织未必总是被动地取决于各种社会分裂和社会冲突的现实,相反,政党往往会主动地在社会分裂与社会冲突中进行选择,以谋取党派的最大利益。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分裂,其中一些对于政治竞争并不具有意义,而另一些则有可能成为政党间分裂的关键。在这种情形下,政党领导人会尽可能地利用这些能够为他们带来掌握政权机会的分裂和冲突,并将这种分裂和冲突加以意识形态化和合法化。也就是说,政党并不产生社会冲突,也不是简单地取决于社会冲突,但“为理解政党冲突的特点,必须考虑政党在争夺最高权力时所利用的分裂之功能”(注:E.E.Schattschneider,The Semi-Sovereign People,Hinsdale:Dryden Press,1955,p.73.)。
综上所述,有关比较政党研究的研究成果由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早期,到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的现在,经历了由小到大、由不成熟到相对成熟的发展历程。这一发展向我们揭示的就是:随着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演变,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每一代学人都能够且应当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