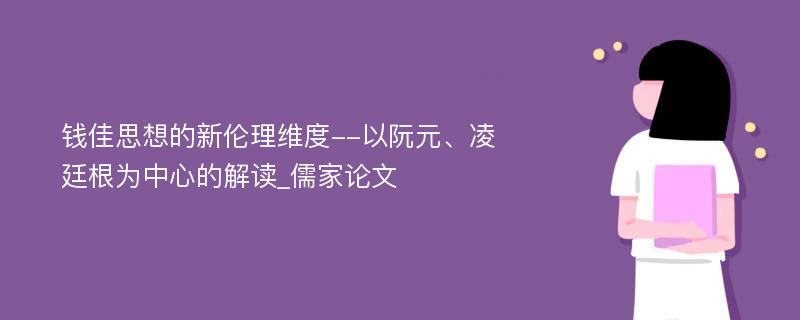
乾嘉思想的伦理新向度——以阮元、凌廷堪为中心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思想论文,中心论文,凌廷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在道德观点上乾嘉学者并没有跃出传统儒学特别是先秦儒学之范囿,与道学并无不同。“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中国传统伦理的观点是传统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凝结,在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是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的。但是对于传统伦理观点的论证却不必统一标准。乾嘉学者的道德论证与道学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迥异于道学的道德形而上学方式来为儒家伦理辩护。道学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前提为清初学者的内部批判所纠正,而乾嘉学者更是从外部根本否定其合理性。乾嘉学者反对道学的体用思维模式,认为其乃来自佛学,非孔孟真传,反对道德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反对受到佛教佛性论影响的人性论,对于性理之说深致不满,认为不足以成为道德基石;对道学的“心体”之说以及由其所导致的知行脱节问题大加批判,对诚、仁、慎独等道学关键概念加以新说。对伦理学而言,这是不同于宋明道学的道德形而上学的路向。在理论上认真地对待这些变化,是需要去除那些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的。
一 “理出于礼”
宋明理学在道德哲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以天理为道德根源,以性善论的形式论证修养功夫之可能与必要以及其成圣的目标。理学话语的出现极为曲折,性与天道本非儒家之长,它汲取了佛老的思维方式,创造出了以“理”为中心概念的哲学体系。就伦理学而言,在家族相似的意义上,宋明理学的道德哲学是一种本体论(ontological)的美德伦理。①在本体论的美德伦理看来,自然便是一个充满着道德意义的价值世界,“是”(实然)与“应当”(当然)并无阻隔。理学家的基本世界图景的标准表达便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过二气五行阴阳太极的天道运行来确定人伦五性。在这里,天道与人道打成一片。用先秦哲学话语来说,便是要承认“天命之谓性”,人需“各正性命”,这整个世界方是道德的,人之所是可自然得出人之所应当。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我们很自然地得出心即理、性即理、天即理的结论,从而为传统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伦常奠定了本体论基础。
清代以来,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有三条进路:一是以字源考索的形式进行的批判,这种考证浮面看来极似语文学(philology)工作,但是其中蕴含着语言哲学的洞见;二是历史主义的进路,通过考索本体论进入中国思维的历史考察,批判“理事对举、体用并提”的本体论思维方式何以不能够与中国人的生活样态相合适;三是在理论内部通过对“心灵主义”(“内圣”在哲学意义上的表现)的批判,从而推动理论的实践转向。乾嘉以降,除了戴震仍然用理学话语思考问题之外,其余大多不取这种路径。凌廷堪就说:“吾郡戴氏著书专斥洛闽,而开卷仍先辨理字,又借体用二字论小学。犹若明若昧,陷于阱擭而不能出也。”②其余诸儒大多通过对佛老的批评或间接或直接地批评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群体,他们主张不能将道德根源放置在“天理”或“即理”之“心”上。
他们不是以天理作为道德的根源,也即否认将应然之理作为道德或者善的根源,而是将道德根源放置在据实然之人性所制的“礼”上。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关于《论语》中“礼后”的讨论中。宋儒重理,将礼视为末,特别发展到王学以后,极端者甚至将礼视为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乾嘉诸儒重礼,从对儒家元典的解读中,考究理与礼的先后本末问题。理学家谈性与天道,拈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为其渊薮;而清儒却将“学”“庸”重新纳入《礼记》系统,认之为讲礼之书。“《大学》虽不言礼,而与《中庸》皆为释礼之书也明矣。”③《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以及“林放问礼之本”等多处论礼,理学家固执于体用思维,强要将体用并提思维嵌入礼论④,总体意见是“礼后于理”或“礼出于理”。
子夏与夫子关于“礼”的对话,理解的关键在于对“绘事后素”的理解。“绘事后素”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郑玄的解读,二是朱子《集注》的解读。郑玄解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朱子注不取郑玄的解释,而是“以后素为后于素”。这个解释并不是细节性的,其所带来的重大后果在于对“礼”的认识。据朱熹,众色在后,拟况礼为末,其存在必须以“理”为前提,而在郑玄,则众色在前,正如礼为本,后来的各种发展都是以“礼”为基础的。凌廷堪说:“朱子论语集注解释‘绘事后素’,将后解释为后于素,遂以礼为末。仁义礼智信五者皆为人之性,‘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然则五性必待礼而后有节,犹之五色必待素而后成文,故曰:礼后乎。”⑤乾嘉思想的后学黄式三《论语后案》亦同此意见。黄氏认为以礼为末的观点是受到道家之学的暗示,非圣人本意。老氏轻视礼,说“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而《礼器》篇则主张礼中自有忠信,无忠信礼亦不虚道。儒家重言礼,“八佾篇详言礼,此言礼为后,犹言礼之不可以已也。礼兼忠信节文而言,倩盼美貌当有礼以成之,亦重礼也。后,犹终也,成也。近解专以仪文为礼,遂滋本末轻重之说。申其说者,遂云未有礼先有理也。信如是,则忠信,理也,本也。礼,文也,末也。与礼器之言不大相背谬乎?”⑥阮元则从朱子中晚年讲学之不同,得出朱子思想由理转向礼的结论。他说:“朱子中年讲理,固以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故宜忠宜孝即理也。然三代文质损益甚多,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⑦
“礼后”的争辩得出了乾嘉学者“理出于礼”的结论,对比于理学本体论思维中所言的理在先天,无疑有一大转圜。乾嘉学者大多否定有一个超验的先天之理实存,同时否认师心自用、独坐默然即可复性。“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⑧理出于礼,礼先理后。这意味着乾嘉儒者否定超验本体作为其道德根源,而把道德根源放诸于作为生活形式之浓缩的“礼”中。礼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总结,其根源于日用常行,一旦凝结为制度形式,本身就带有约束和规范能力,在古代中国,甚至还带有法律效力。道德起源不是来自于不依赖于经验的本体,而是来自于经验生活的总结。乾嘉学者致力于礼学,把行为的合理性和道德性揆诸礼的历史性考察,将历史性的礼视为道德根源。这当然是对宋儒注重心性而不注重仪礼的一种纠正。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一点转变对于伦理学的重要作用,它不再取一种美德伦理学,而是取一种“礼法型的伦理”概念。⑨因为礼为规则,对人的行为有直接的范导作用,守礼即合乎道德。道德如果根源于超验之本体——天理,那么意味着道德的永恒性;而道德如果来源于一个社群或者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则意味着道德的历史性。清儒对礼的考索一方面有着回归原始儒学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又谨记“礼者,时为大”之遗训。凌廷堪特别引用《礼运篇》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⑩这就为他们随着时间变化和生活形式的变迁而改变其道德标准提供了合理依据。这种思想,在其后学那里得到发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改革(或革命)的合法性根据之一(11)。
清儒为传统道德伦常的辩护不再采用一种先天的方式,而是直接承认伦常的合理性。他们将已然之“礼”视为道德之当然,认为伦常的合法性乃是源自于先民生活形式之凝结,并不需要另取一个超越的天理为其道德根源。这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理论进路,不同于以超验本体为基础的美德伦理学。
二 节性
由于天理的本体论保证,天命之性乃性德,性之德醇乎善矣。宋儒立论,多从应然之性出发。理学本体论的批判相应地带来了关于人性论学说的改革。乾嘉诸儒否定性理之说,故而其论人性亦不从性之应该出发,不取宋儒的义理之性的说法,而直接诉诸于血气心知之性。乾嘉学者大多接受戴东原的人性说。“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本,故曰成之者性也。”(12)既然血气心知为性,先王制礼作乐的根据不在于超验的义理之性,而在于“气质中之性”。乾嘉学者借助于先秦典籍,助攻戴氏。钱大昕、阮元、凌廷堪、孙星衍等皆以血气心知为性。
在以血气心知为性的前提下,乾嘉学者首先肯定了声、色、味等感官欲望的合理性,反对理学家的存理灭欲,从根本上肯定了欲望不可磨灭。这是承接晚明以降对“无欲”思想的批判之风,正面肯定了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在乾嘉学者看来,理学家主张静坐修身,通过欲望的祛除求得与天理的拢合,类似于佛老二氏的无欲之论,与先秦儒家的说法不符合。理学家未免将人看做纯粹的理性存在,忽视了对其他方面的关注。第二,承认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并不一定导致一种享乐主义的结论,因为乾嘉学者比理学家更为重视外在的“礼”的制约。既然血气心知为性,那么血气心知往往会有偏颇,必须要有正确的引导和规范,需要作节制,使之合理地外化,得到满足同时避免过犹不及的差错。清儒不以复性之说为然,大多主张“节性”说以代替“复性”说。
阮元遍举《书》、《诗》、《春秋》等,尤其是孔孟之前的典籍,拈出古人只有节性之说,而无复性之说。阮元作《性命古训》说:“性命之训,起于后世者,且勿论说,先说其古者。古性命之训虽多,而大指相同,试先举尚书召命、孟子尽心二说以建首,可以明其余矣。”《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阮元加案语曰:“召诰所谓命,即天命也。若子初生,即禄命福极也。哲与愚,吉与凶,历年长短,皆命也。哲愚授予天为命,授予人为性,君子祈命而节性,尽性而知命。故孟子尽心亦谓口目耳鼻四肢为性也。性中有味色声臭安佚之欲,是以必当节之。古人但言节性,不言复性也。”(13)《尚书》有“虞性”“节性”、毛《诗》有“弥性”的说法,阮元认为这些当是“言性者所当首举而尊式之,盖最古之训也”,而理学家远涉二氏,则近忘圣经。凌廷堪更有“复礼说”以代替“复性说”,直接判定“圣人之道,一礼而已”。他说:“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非礼以节之,则过者或溢于情,而不及者则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中节者,非自能中节也,必有礼以节之。故曰‘非礼何以复其性焉。’”(14)人皆有好恶偏向,并非纯然理性的存在,如果顺其自性,走向的就是过或不及,不能达到中和。因此,达到中和不是行为者所能独自完成的,还须要有外在的礼来“节之”。他们的一般结论就是用凝结着社会合理性和可行性的礼来正确地范导民性,使之合乎伦理规范。
乾嘉诸儒借助孟子“性善论”的权威,将孟子所批判的告子“生之谓性”(作用即性)的观点纳入到其人性说中;承认“生之谓性”之性为善,实际上类似于承认性无善无恶之论。如果转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在否认天命之性,且接受气一元论的背景下,乾嘉诸儒有理由相信性是无关道德的(amoral)(15)。这也就意味着道德的判别标准放在外在的行为规范上,道德与否在于行为是否符合礼刑等人类生活形式的规则,而不在于能否去心中之私。假如人性本私,由于人性不能改变,故而不应该再追求对于人心的纯净,而应当制定外在的礼和刑来防范由于人性之不善带来的后果。在这里实则体现了思考视角的转化,也体现了道德评价标准的转变,道德与否不再是从人的内在品质,而是从外在的行为后果去评价,即,如果独立于一个行为旨在产生的后果或结果,行为就无所谓善恶。
三 为仁
乾嘉学者对理学的空疏学风多有排斥,对心学的逾越礼教行为更加厌恶。他们较为重视从外在的礼的规范、礼的践履来理解道德,而不是从心性层面来解释道德。这种新的解释意味着,对于道德事实的评价不再是只注重于“心”,而在于“事”(行为的后果和成效)。阮元借古喻今,他说:“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实,而易于率循。晋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虚,而易于附会。”(16)理学家皆以为能够以修身直接推展之于“齐”、“治”、“平”,将克己之己理解为私欲,认为只要克去私欲,自然能够复礼。但在乾嘉学者看来,从修身工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其作用而言并不能够一贯而下。“谓自治敬则治人必简,亦躐等在,须到‘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时,方得贯串。”(17)判断行为的道德与否不仅要从本体上区别,而且要从行为的后果来区别,亦即不能仅从行为者的内在动机而论,还必须关注其行为的效果。
乾嘉诸儒特别重视行为的“合礼性”,特别重视道德行为的后果,他们对理学家所惯用的伦理词做了新的解读,认为没有诉诸行事而只是在内心修为,并不能得儒家之道。一个道德行为必须是合乎礼制的,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乾嘉诸儒将理学家美德理论所具有的道德心理学给予了一种新的解释。原本具有内在性或心理主义的理学关键词都得到了一种外在主义的处理。在理学家看来,人们通过内心的“敬”、“慎独”和对流行不已的“仁”的觉解(18),通过修身自省自然便能提升德行,通过内在修为自然便能够从容中礼,而无需外在的规定约束。乾嘉诸儒首先反对将儒家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仁”理解为一种心理状态或一种神秘的本体,也不认为这种仁德通过端坐静观或者直觉顿悟所得。如果说理学家重在对仁的本体的考究,乾嘉学者则重在从仁的发用来强调。
对于“仁”,阮元的解释是:“所谓仁者,己之身欲立则亦立人,己之身欲达则亦达人。所以必两人相人偶而仁始见也。”(19)其重视的是对仁之“为”。“其曰为仁,可见仁必须为,非端坐静观即可曰仁也。”(20)“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盖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与人相偶仁乃见也。”(21)“仁”必须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对社会的承认,故而不可能对其采取一种内在主义的态度,而必须“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那种认为只要能够克尽自己私欲,就能够成仁成圣的说法,无疑与二氏一般。因为从内里克去私欲、修养身心的角度而言,或如戴震所说的,仅仅就对心理修养的躬行践履而言,释老与儒家并无不同。那么如何区分儒家与二氏呢?当然只能就其动作的后果即“仁”之发用而言。但这并不表示乾嘉学者不重视自身的德性培养,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要纠正那种不外推的“仁”。“仁虽由人而成,其实当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即不仁矣。”(22)
综上可知,阮元说“仁”,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仁并非一种心理状态,或者道德心理,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事实状态。第二,仁必须“为”,也就是要以行动的后果或者效用而论,阮元不否定“为仁由己”,但更注重仁的扩充、兼济。这些思想在当时的考据学家中已是共识。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朱熹注曰:“扩,推广之意。充、满也。四端在我,随处发见,知皆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已者矣。”而焦里堂则以为扩者彍也:“彍而充之,即引而大之。”论语有“颜子之三月不违仁”之说,程子注曰:“不违仁,只是无纤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刘宝楠《论语正义》则云:“颜子体仁,未得位行道,其仁无所施于人,然其心则能不违,故夫子许之。日月至者,谓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皆至仁,非谓日一至也。积日成月,故曰日月至。”乾嘉学者的新解颇受置疑。关于前者,陆宝千认为“云‘推广’,则己为主动;曰‘引’,则有被动意。凡工夫皆发之于己,不能由他力所引出。故理堂之说,显不如晦庵之得孟子本意。以理堂本人未尝做此功夫,徒事文字考据,故有此隔阂也。”关于后者,陆氏认为乾嘉学者不通之极,极为鄙夷地说“对于何谓不违仁不著一字,则此义固非饾饤之士所知也。”(23)陆氏深执于理学家说,对乾嘉学者的思想并没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其实,乾嘉学者所解释的仁,当如刘师培所言,“仁当指作用而言,非仅指忍心而言也。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二。郑氏礼记注云:仁读如相人偶之人(谓以人道待人能相耦也。阮元云人耦者,尔我亲爱之词)。盖人必合两人而后见人与人接,仁道乃生。”(24)“足证仁道之大必以施之人民为凭”,而非只是自我的德性修正。如果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解释,那么乾嘉学者对孔孟之解释就水到渠成,情有可原,理由所据。
可见,清儒以外在之“礼”代内在之“理”,作为判断人的行为道德标准,把对于善恶的评价放在外在的行为是否合乎礼(规范)上,而不在是否成圣上。他们注重人的合理欲望的实现、反对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把道德评判标准放在行为是否合乎规则上,又表现出了某种规范伦理的倾向,相对于传统的道义论,表现出后果论的色彩。
四 理想人格
先秦儒家孔子未尝轻易许人以仁,更未许人以圣,其理想人格类型大概只能是“君子”。在早期社会,“圣人”是有特殊含义的,他必须兼具德和位,显然不能随意予人。圣人人格作为理想人格,只有在佛教“成佛”理论传入之后才得到广泛认可。成圣是宋明理学的第一要着,它的实现需要通过内外兼修、慎思明辨等功夫。宋儒的人格理想,对人之道德要求极高,他们眼中的圣人是无私无欲的。这种理想人格乃是以性善论为其基石的。随着清儒对人性论的革命性看法的形成,其理想人格亦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这与其道德评价标准也是一致的。前文说道,在家族相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宋明理学的伦理学为一种美德理论。美德理论传统往往以理想人格、道德楷模等为道德修养之完成目标。理想人格之变化,亦可以看出对于道德评价之标准的变化。
在北宋,胡瑗教训学生,问孔颜所乐何学。程子作《颜子所乐何学论》,(25)希圣希贤之心跃然纸上。“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细究其文,伊川的观点有二。第一,圣人可学而至。途径是“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第二,成圣之道不在于“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究其实,程子似乎把道德的醇善作为圣人的定义标准。朱子深知成圣问题对解决儒家的终极关怀(即修养的终极目标,亦如宗教中的彼岸一样)的重要性,他虽然知道先秦典籍中“圣人”的内涵,也知道程子此处说法太过于重德性而忽略“圣”的其他方面,但他在《集注》中还是肯定程子的说法。王船山赞同朱子的做法。他说:“朱子《语类》以有位言圣,却于《集注》不用。缘说有位为圣,是求巴鼻语,移近教庸俗易知,而圣人语意既不然,于理亦碍,故割爱删之。宁使学者急不得其端,而不忍微言之绝也。”(26)船山为朱子辩护说:“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曰‘圣则吾不能’,岂以位言乎?下言尧舜,自是有位之圣。然夫子意中似不以圣许舜汤夷尹以下,则亦历选古今,得此二圣,而偶其位之为天子耳。程子言圣仁合一处,自是广大精微之论,看到天德普遍周流处,圣之所不尽者,仁亦无所不至。”(27)
“位”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地位,而且是一种与之相匹配的能力的体现。“位”必须要有功绩来佐助。对“位”的重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能力外化之事功的重视。理学家认为圣人主要是以“德”而言,可知道德的醇善为圣人的标准之最核心部分。到王学横流之时,圣人满街走,阳明以致良知教导世人,愚夫愚妇皆与圣人同,将儒家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圣人理想推向极致。
随着清初对王学的反动和对理学的反思,乾嘉学者在道德理想人格类型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最为典型实例是阮元在创立学海堂书院的来年(1825年),便首先以“学者愿著何书”问堂中学生。对比一下胡瑗对程颢的提问,可见时代风气之变化。在乾嘉时代,成圣已成奢望,即便是孔子的圣人形象亦有所争议,这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一大争点之一,同时也涉及到乾嘉伦理学中的理想人格问题。
与一般情况相似,乾嘉学者往往通过重新解读经典来诠释,其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孔子尚且不能为“圣人”,更何况其余。鲁国时人之论已皆以圣仁尊孔子,而孔子曰“则吾岂敢”。与“成圣”理想不同的是,乾嘉学者首先在理论上斩断了“成圣”的可能性,宣告“六亿神州皆尧舜”的不可能性,恢复了先秦儒家的人格差序:“以圣为第一,仁即次之,智又次之”(28)。如果说,儒家在宋明是以成圣为第一目的,那么乾嘉时期甚至整个清代都无此宏愿。按照余英时的说法,儒家思想在清代存在着“知识主义”的转向,他们在对儒家德性体系的排序上是有变化的:道问学在价值上优先于尊德性。(29)
其次,乾嘉学者反对仅仅以“人品”论理想人格。《论语》中论人,可以从德性角度解读,亦可从“位”的角度解读。如前所说,理学家往往从“德”的角度解释,而清儒则一反前说,主张古书都以“位”言:“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上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白虎通号篇曰:君之与臣,无适无莫,义之与比。是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非古义矣。”(30)如果仅仅将“位”理解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如果不理解“位”与“政”的相关性,就很难理解清儒背后的意思。“位”必须以功绩、“政”来佐证,以行动的后果来判断,这是与乾嘉诸儒对行为价值的评判标准相一致的。
第三,理想人格必须有为,本身具有的德性必须要外化为德行。有为就是要有所作为,人本身具有某些能够推行扩展的能力,因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必须将自己的意志推展外化。判断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不仅要看行为者内心的动机,更重要的是看它的后果以及它能否给其他人带来某些福利。“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能知,亦能行,人们需要将这种知识转化为行动,同时又能遵守社会规则(礼),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成员。这种人格其实就很接近现代社会的人格,这也是清儒对宋明思想的一种扩展。贺麟所展望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即认为“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31)可以算是乾嘉诸儒伦理思想的合理结论。
五 伦理反思中的乾嘉思想
宋明理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重新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在价值上肯定了儒学对佛老的优先性,从而使得儒家伦理纲常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正是由于理学几百年的流传才使得儒家伦理成为天经地义。理学家往往借助于本体论思维为其道德哲学伦理思想辩护: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二气、万物解释宇宙化生过程,并由此阐发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虽然理学内部存在着气、理、心之分,但又有其共同之处。.
在乾嘉学者身上,这种思维方式很是少见。原因之一在于清初关于太极图的辩论已经使得“先天之学”遭遇理论难关,使得坚持儒家正统的思想家不得不与之划清关系。第二个原因在于这种理论方式的封闭性,这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伦理学本身所带来的弊端。普特南曾谈到以本体论(ontology)为基础的伦理学的封闭性:即价值的单一性,他认为,不应当将伦理学视为一个道德原则(a system of principles)的系统,而是一个“相关的各种关注(concerns)”的系统,这些关注既互相支持存在紧张。(32)著有《伦理教科书》的刘师培就曾痛陈理学思维所带来的伦理学上的弊端有三:“一曰阻学术之进步。……名为守道,适则自小其道业。”“二曰启社会之纷争。……主一之人,凡仁之学行与己不合者皆加以摈斥,入主出奴,无容人之量,善不与人同,志不与人通,彼此相持而竞争。”“三曰贻国家之实祸天下,惟主一无适之人于先入之言.,奉为终身之典则而不敢稍迁。”(33)其中,第三个原因尤其不能忽视,它涉及到理学所面临的现实背景。理学为儒家生活方式的辩护中发展出来的天理世界观是以佛老为其对手的,而佛老在明清之后理论无甚发展,也就是说儒家的生活方式、制度威仪之类的现实维度均无对手,故而在某种程度上,儒家伦常已经由“应当”上升为“是”,这一点在历史上也屡有佐证。如洛克在讨论社会契约论的时候还要借助于上帝的权威,而几十年之后的卢梭则直接判定人生而平等是自然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清儒不需要天理世界观为其理论根据,与卢梭不需要上帝的保证是一致的。清儒的理论对手已经不是佛老。他们的规整对象是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某种程度的“礼崩乐坏”现象:即伦理规则失范问题(34)。程朱理学是庙堂之上的官学,由于其本身的理论缺陷,而无法对社会变迁所导致的世俗化和风俗的败坏发挥切实的作用,尚不如阳明心学的趋向底层路线。理学本身注重心性,如何从心性规整人的行为准则,本身带有理论上的困难,朱子晚年已有警觉,准备以礼(制度)的建设弥缝内外之别。心学走化民成俗的路线,但仅限于乡社民约,不能推广到一般的社会层面,加之重己身而忽略制度建设以及实际行迹,已产生诸多流弊。乾嘉学者大多主张“礼学”,这不仅仅是考古的需要,还有整饬民风以及制度建设之意,其用意无疑在于将儒家伦常落到实处,而非仅仅限于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清儒之学乃是对宋以来的经世学说的推进(35)。
乾嘉学者治学,如龚自珍为王引之所作墓志铭所云:“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赵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36)“舌人”者,翻译者也,也是再创造者。其志虽不在“大道”,其实与大道不远矣。如果要理解近代思想,特别是伦理思想的变迁,乾嘉学者在伦理学方面的洞见尤其不可放过。它不仅仅在理论上对理学有批评,在实际上也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清代思想的走向。乾嘉学者尝试建立一种没有本体论支撑的伦理学(ethics without ontology):立足于人的真实存在的伦理学。这种哲学不需要超验的天理为基础,不需要心体或者性体作为其道德基石,而是从实然之人性出发;注重道德行为的实践后果,注重德性与幸福、理和欲的平衡。这些洞见,在晚清思想中得到了回应,是中国思想走进现代的重要资源,是吸收西学的接榫点(37)。
注释:
①参见黄勇:《理学的本体论美德伦理学:二程的德性合一论》,载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与文化研究所编:《思想与文化》第4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又可参见其《二程兄弟的本体论神学》一文,载《哲学门》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2页。
③⑤⑧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第142、146—147、32页。
④俞樾:《群经平议》,《续修四库》卷一七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8页。
⑥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0页。
⑦阮元:《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62页。
⑨礼法型的伦理学(law conception of ethics)与亚氏美德伦理(Aristotelian conception of ethics)的区别,参见G.E.M.Anscombe,"Modern Moral Philosophy",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Vol.XXXIII,No.124(1958)。
⑩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第29页。
(11)清末民初鼓吹革命或者改革的刘师培和章太炎,在某种程度上,梁启超也受到乾嘉学者的思想影响。这个问题系本论题的应有之义,限于篇幅,俟之另文。
(12)戴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1页。
(13)阮元:《研经室集》,第211页。
(14)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第27页。
(15)乾嘉学者的后学,尤其是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形成具有革命性影响的人物如龚自珍、刘师培等都接受了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说,章太炎亦然,章氏主张性无自性,亦可纳入无善无恶之论中。
(16)(19)(20)(21)阮元:《研经室集》,第1059、178、180、176页。
(17)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4页。
(18)对“敬”的解释,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44-45页;阮元:《研经室集》,第1016页;对慎独的解释,参见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第144—145页。
(22)阮元:《研经室集》,第181页。
(23)陆宝千:《清代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6-188页。
(24)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60页。
(25)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7-578页。
(26)(27)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第300、302页。
(28)阮元:《研经室集》,第179页。
(29)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30)俞樾:《群经平议》,第491页。
(31)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32)H.Putnam,Ethics without Ont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2-28.
(33)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2041页。
(34)这里可以提出两个佐证:一是《儒林外史》中徽州府的秀才王玉辉一生宏愿是做三件事,写三本书“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其中两个都与社会制度建设有关。二是钱大昕所写的《正俗》一文:“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小说的兴起与现代性的兴起关系极大,这里面特别涉及到理欲之辨的问题。对自然欲望的规整是清代儒学调整的重要动机之一。
(35)参见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潮试释》一文,载《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3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7—148页。
(37)关于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关联,过去的研究一般注意到理学或者心学,却忽视了与时间序列上最先的乾嘉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晚清的一大批思想家都具有乾嘉思想的背景,他们比理学家群体更为积极来学习、接受或比附西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