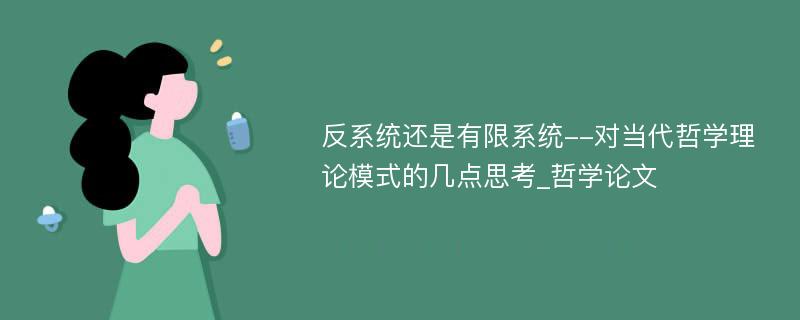
反体系还是有限体系性——关于当代哲学理论方式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的体系性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讨论中无疑已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在黑格尔 之后,“哲学必须是一种建立体系的活动”的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怀疑,并出现了 从叔本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的反体系运动;另一方面,持现代主义立场的哲学家虽然 也拒斥近代哲学的绝对理论体系,但在捍卫理性、主体性的同时,必定主张某种形式的 体系性。可以说,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理论体系性,还是彻底清除任何形式的体系,是现 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争的一个重要侧面。无疑,这一争论涉及未来哲学的理论方式问 题,其重要意义已不言自明。近年来,虽然国内也出现了关于哲学体系问题的探讨,但 对于此问题及其背景并没有一个充分的自觉,只是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 定和特质”的问题(注:参见孙伯鍨、张一兵、仰海峰《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 法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针对的也只是斯大林的哲学教科书体系。 因此,可以说目前国内的探讨并没有真正进入体系问题的问题域。笔者以为,要真正进 入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场域,就有必要在马克思现代实践哲学的视野下重新理解体系 性问题(注:关于现代实践哲学的概念,参见王南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发展理路之检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这显然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范围,对整个当代哲学同样有效。
一、什么是体系的本质
如上所述,虽然体系往往并不被视作一个严格的哲学概念,但体系问题的确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把体系仅仅当作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因为其成为一个问题本身已表明了这样的共识,即体系必与某种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关联。这样,我们首先必须做的便是对体系的本质的考察。
首先应该明确,这里讨论的体系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而不是对某些哲学家思想的外在描述。文德尔班将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描述为古希腊哲学的“体系”时代,因为他们三人的创作具有体系性,这种体系性在于他们的“问题的全面性”和“处理这些问题的统一自觉性”(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7~138页。)。文德尔班的描述无疑道出了一种思想体系的总体性特征和内在一致性特征,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对体系深层本质的理解。因为它仅仅 意味着体系哲学家具有广阔的理论视野,并能面对杂多的问题,按一定标准将其分门别 类。如果以此作为体系的本质内涵,那么,现代哲学的反体系就显得荒谬,因为这势必 导致反对现代知识的学科划分。
因此,这里讨论的体系只能是作为哲学思维内核的范畴体系或逻辑体系。要了解体系的本质,就必须对历史上各类逻辑体系进行分析。按现代实践哲学的观点,历史上已存 在着两类理论哲学的范畴体系: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体论范畴体系和以康德为代表 的主体论范畴体系。这是以提出体系的原则为划分标准的。实体论的范畴体系暗含着这 样的假设,即范畴或概念是对象的内在划分。从而,建立体系实质上就是“发现”对象 的某些内在结构,并把这些结构列举出来。第一个试图建立这种体系的是亚里士多德。 亚氏的范畴又称“云谓关系”或谓词,这些谓词“从本质上谓述了所称呼的东西,也就 是说它们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归根到底是什么”(注:罗斯:《亚里士多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因此可以说,范畴就是存在的分类。亚氏似乎不需要给出这一范畴体系的理由,因为实体的客观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实体论体系的随意性和不完整性。事实上,亚氏的范畴体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目,难怪康德说它只是经验性的列举和“毫无原则的拼凑”。亚氏范畴体系的缺陷实质上代表了实体论体系的缺陷,但这种理论方式却“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
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默认实体性为其原则,但在康德看来,这无异于“无原则”,因而要克服这个体系就必须自觉地提供一个可靠的原则,以使其中的范畴得到准确的规定。由于知性的作用在于判断,所以康德便依据判断的类型的形式制定出一个“范畴表”,并断定这些范畴的数目不多不少,“足够纯粹理智构成我们对物的全部知识”(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9页。)。可见康德的体系是一个知性范畴体系。黑格尔虽然同意康德所倡导的主体性原则,但却认为体系的最高原则不是知性而是理性;并且,康德的体系之外仍存在着一个物自身,因此,这个体系是不完备的。所以,黑格尔对康德体系的改造和发展就是通过历史的原则将主体性绝对化,确立理性作为体系的最高原则的地位。
关于什么是体系的本质的问题,以上两类不同的体系本身便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答案:或者认为范畴体系是对象所固有的结构,或者认为是主体先天的形式甚至就是主体本身。这实质上是将提出体系的原则作为体系的本质。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理论哲学,将体系归结为某一绝对的原则是必然的,因为理论哲学必须有一个抽象的阿基米德式支点。然而在现代实践哲学看来,无论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的原则都不能完全克服对方,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选择什么作为范畴体系的原则,而在于理论哲学必须拥有一个范畴 体系。因此,我们虽然不能断定体系应该归结为主体还是客体,但其与主客对立结构的 本质关联却不容怀疑。对于实体论者而言,如果不预设对象有一个体系,即是没有分类 的基础,那么,对象便是不可认识的;而对于主体论者而言,如果主体不具有一套先天 的形式,那么也不能构成关于对象的知识。但正是这两种立场的可选择性表明范畴体系 的本质并不源于二元结构中的某一方,恰恰源于主客对待的结构本身。
主客对待实质上是一种“理论的”结构,或者说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看”或者“透视”的关系。如哈贝马斯所说,“用哲学的语言讲,理论就是对宇宙的观察”(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由于这一观察,观者与被观者的设定成为必要,这也就是主客体关系的原型。就古代的实体哲学而言,观者是不自觉或隐而不显的;而在主体哲学中,观者却占据主导地位,被观者只能依其获得意义。无论如何,观者总是需要一个视角,这一视角也就是理论的原则,而由某一视角构成的理论必然是有体系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体系便不能成为理论。如果黑格尔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体系这一概念的,那么,他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哲学终究也是一种理论活动。所以,我们可以将体系的本质归结为一种理论的态度。
然而,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理论哲学,主客体的对立都被视为终极结构,从而,基于这一结构之上的体系也就获得了某种终极价值。以往我们很少能触及理论结构本身 的本质,从而也就很少触及体系的一般本质。事实上,通常讨论中的体系往往只是指它 的典型形式——近代主体性体系。以主体性为主导的二元对立是近代理论哲学的终极结 构,因此,体系也必须获得相应的绝对地位。事实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 的发展就是一个走向绝对体系的过程。胡塞尔哲学的初衷虽然是“反体系”的,但由于 其理论哲学的态度,最终也不得不建构一个形式体系(当然,与黑格尔一样,我们不可 否认胡塞尔的理论已包含了打破这一形式体系的因素)。另外,近代哲学的体系性是与 其主体性相匹配的:主体性作为体系的绝对真理,而体系则作为主体强制性和总体性的 实现。这便是目前备受批评的体系,所谓的“体系哲学”也应该特指近代理论哲学范式 下的绝对体系。笔者以为,区分出体系的一般本质与其在近代哲学范式下的特殊状态, 是讨论体系性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很多争论便源于这两层含义的混淆。虽然已有论者用 “哲学体系”与“体系哲学”表示了这一区分,但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性时, 往往又将其解释为一种理论哲学(注:参见陆剑杰《体系哲学·哲学体系·方法论问题 辨析》,《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二、“反体系”的意义和问题
明确了体系的本质及其与近代主体性体系的区分,我们便不难理解“反体系”运动的意义。就近代哲学而言,反体系意味着对其强制性形式结构的谴责和反抗;就作为理论的必要形式而言,反体系则意味着对理论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超越。但由于对体系的一般本质及其与近代体系的区分没有充分自觉,以往的反体系哲学家往往从反对近代哲学体系走向对任何体系的反对。
事实上,反体系的因素早已存在于理论哲学的体系之中。任何理论体系无疑都需要关于其自身合理性的说明,在理论哲学范式下,这种合理性的提供只能是在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中作选择。近代哲学选择的是主体。虽然主体相对于古代哲学的实体而言有自身的优越性,但选择主体作为克服主客分裂的方式必然要涉及主体活动的过程性和历史性。事实上,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都自觉地采取历史主义的方式作为综合客体的媒介。然而历史原则的引入却带来了如下问题:历史性暗示了理论哲学的二元结构之外的领域;主体的历史性势必导致对其绝对性的否定,而历史的无限性也势必导致对体系的总体性和封闭性的否定。哈贝马斯认为,这些因素“激发了后形而上学思想”(注: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这些“革命”的因素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恩格斯认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的体系,但这一体系与他的辩证方法相矛盾,因此,黑格尔哲学 是一个革命的方法与保守的体系的结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2 19页。)。无疑,恩格斯已洞察了黑格尔体系的本质。但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来 强调却容易使人将体系与方法两者对立起来,以至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现代 哲学都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体系。这里暂且不论一种方法是否可以脱离体系而独 立存在的问题,但将辩证法仅仅作为一种方法,无疑会妨碍我们对其所属的思维范式的 理解。笔者以为,恩格斯这里欲表达的乃是黑格尔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超出理论哲学体系 的原则——历史性原则。这就表明了理论哲学体系的悖论:为了实现“终极论证”,必 须引入体系之外的某些因素,然而这一引入本身又对理论体系构成挑战。
后来的反体系哲学家大都以这一悖论作为理论切入点。最先向近代哲学强制性体系宣战的是唯意志论。唯意志论的理论逻辑乃是企图在传统的理论体系之外寻找第一性的东西,以作为对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和终极性的否定。叔本华宣布世界只“作为意志和表象”,而理论认识不仅以意志为基础,也必须为意志活动服务。尼采运用谱系学的方法揭示了知识、道德内部的权力机制,从而认为理论逻辑是“偶然的”、“不合理的”,建构完整的体系实质上正是其某种不完备性和理论家缺乏自信的表现。唯意志论似乎是极端反体系的,甚至也反映在其写作方式上,但这种反体系却只是主体哲学立场的简单反转。为了反对理论哲学体系的强大主体,唯意志论又不得不塑造一个同样强大的意志主体作为其理论支撑,因此可以说,它终究没有超越理论哲学的视野。
然而,唯意志论开创了一条彻底地否定理论体系的思路。这一思路热衷于立足理论体系之外的某一点,揭露理论体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二元结构的悖论性和虚假性,从而主张完全将其抛弃。其中最典型的有阿多尔诺和罗蒂等。阿多尔诺认为,理论的概念物必须以非概念物——精神经验为“奠基”,而精神经验作为物化体制的“逆概念”,其本质在于否定性和差异性,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反对体系的批判要求有处在体系之外的东西,而使认识中的辩证运动获得解放的力量,同时也是反抗体系的力量”(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因此,阿多尔诺断定真正的哲学是“反体系”的。罗蒂通过对笛卡尔以降的哲学史的回顾,发现了理论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心物二元的“镜式”哲学。当他解构掉这种“镜式”结构之后,自然地提出一种“无镜”哲学,即教化哲学。这种哲学不是提出一种理论,而是对诸多理论体系的治疗(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笔者以为,这一思路的成就主要是“袒露”了理论哲学体系的悖论, 其功能主要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最终必定要由对近代哲学体系的否定走向对任何体 系的否定。
与以上纯粹否定性的思路不同的,自然是试图超越理论哲学思维范式的思路。这一思 路并不热衷于宣布二元结构及其理论体系的非法性,更多的工作在于揭示其本质和真理 。这里我们主要涉及的是海德格尔,特别是后期海德格尔。前已提及,德国古典哲学曾 引入了历史性原则,虽然说黑格尔的理论哲学体系内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历史性和时间性 ,但其“竟可能一试从形式辩证法上建树精神与时间的联系,这就已经公开出了二者的 一种源始的亲缘关系”(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91页 。)。历史性和时间性实质上已暗示了超出二元框架的更为本真的领域,海德格尔正是 以此作为切入点打破理论哲学体系并实现存在论的具体性的。海德格尔认为,具体的人 首先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中的,这是人与世界的一种非对象状态,惟有世界的某 一部分成为问题并凸显于人的眼前时,才构成主体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理论正是源于 这种对象性关系。应该说这样的存在论视野已经构成了超越近代理论哲学体系的“平台 ”,然而海德格尔却倾向于强调主客对象性关系的非本真性,即理论活动的非本真性, 以至于将真正的“哲学”与理论对立起来。因此,后期海德格尔主张以“思想”取代哲 学,“思想”的标志性特征就是非对象性和非体系性。这样海德格尔的思想便与阿多尔 诺、罗蒂等人呈现出某种相似性,无怪乎有人认为他是后现代思想的开启者。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反体系”的困难:彻底的反体系不仅置人的对象性存在状态于不顾,而且意味着走向一种“非理论”的哲学。事实上,这些反体系哲学家 都在进行哲学的“非理论”实验,但必定以哲学的自我否定告终。阿多尔诺宣称哲学应 该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异质经验”,却不能成功地向我们表明这种“异质经验”;后期 海德格尔所倡导的“思想”似乎也只能以文学或艺术的方式才能暗示出来;罗蒂的“教 化哲学”最终必定导致一种无休止的“批评”。可见,彻底反体系的初衷是消除近代哲 学的体系,但当其指涉自身时,却导致了“完全自我放弃”。无疑,这就是“反体系” 的悖论。
三、现代实践哲学的有限体系性
事实上,前面的分析已暗示出摆脱这一悖论的可能方式:在超越理论哲学思维范式的基础上,保持某种理论的体系性。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论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典范,因为这种特殊的体系性实质上代表了现代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我们知道,实践哲学并无超出生活实践的理论,所以,理解这种特殊的体系性就必须从实践概念的含义或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开始。
笔者以为,这里有必要区分出实践概念的两层含义,即对象性层面和非对象性层面。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里的实践就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它既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又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因此是非对象性的,并标志着人与周围环境的原初关联。人的理论视角不可能超脱于这样的生活实践的背景,因此这绝不是理论的领域。意识到实践的非对象性层面的含义是实践哲学打破理论哲学二元对立的终极结构的标志,也是其思维范式转换的关键性一步。20世纪一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正是因为立足于这样的存在论视野,我们才说他们与马克思同属于一个时代。最近有论者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应是前概念、前逻辑和前反思的(注:吴晓明:《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见地。
然而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才能理解这个非对象性的存在论基础,这就不得不涉及实践的第二层含义。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从不讳言人及人的对象性活动,相反,他始终坚持承认这种活动具有重要地位。其实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野也是通过对具体的人的活动的分析达到的,只是后来惟恐与近代哲学划不清界线才避开“人类”活动。而马克思一生的理论都是基于人的对象性活动这一领域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说,应该把事物、现实和感性等概念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16页。)。对人的感性活动的强调就是对具体主体性或主客体关系的强调。这 里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是以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为背景的,因此与理论哲学范式下的主 客二元有着本质的区别。
无疑,实践的对象性层面就是理论的领域,而非对象性层面在理论的范围之外。但我们考察实践哲学的理论却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因为前者是理论的本质,而后者则作为 理论的真理。以往我们并未发现对象性活动的非对象性背景,往往只强调人的能动性活 动,从而给这种活动以终极性地位,其结果势必就是建立以“实践”为绝对真理的理论 哲学体系;当我们开始发现实践的深层含义时,却又容易忘却人与外物的对象性关系或 将其斥之为不真实的东西,从而认为马克思哲学应该是彻底“反体系”的。但两者事实 上并不冲突,而且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超越近代 体系哲学的意义:一方面,它立足于前理论、前反思的存在论视野,从而表明理论哲学 将二元对立作为终极结构的荒谬,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反体系的,这种反体系 意味着反对理论体系在近代哲学中的绝对地位;另一方面,主体性及主客体关系在实践 论中又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这便表明理论及其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必要性。换 言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作为理论也是一种“观”和“透视”,然而这里的“观者”却 严格区别于近代哲学的绝对主体性,而是一种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有限主体性。为区别于 理论哲学的无限体系性起见,我们暂且称之为有限体系性。
实践哲学体系的有限性首先是其理论范围的有限性和真理性的有限性。理论哲学的观者是超脱于世界之外并永远在场的主体性,因此必然要以这个世界(存在者的总体)作为其对象,必然要发展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然而这又必然陷入所谓的“大全悖论”之中。实践哲学的“观者”是历史过程中具体的主体,“被观者”则是在实践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因此就不存在“大全悖论”的问题。其次,实践哲学的有限体系性意味着一种面向实践的开放性。实践哲学在承认了理论范围的有限性之后,便没有必要采取某种强制性的形式结构作为吸收客体的手段。这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实践,其目的不是达到一种绝对的、客观的真理,而是现实问题的解决。
实践哲学的有限体系性还意味着一种自我超越的机制。既然理论的问题在于现实的“问题”的解决,那么,它最终必然是对主客体对立的有限结构的超越。当然,这里并不是强调主客关系及理论的非本真性并否认其存在的价值,而是表明理论是走向实践的通道。
标签:哲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