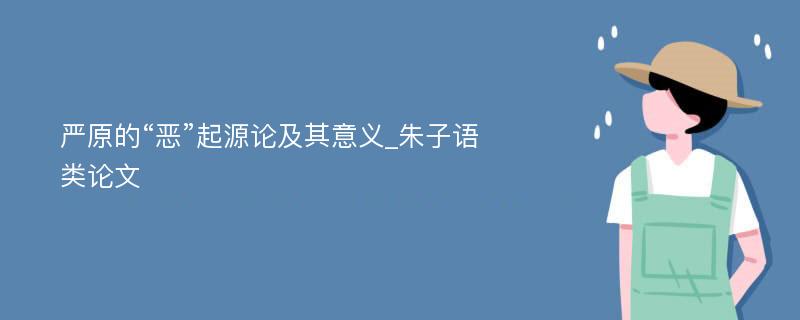
颜元论“恶”的来源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来源论文,颜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颜元(1635-1704年)以尚习行、重功利、反对静坐空谈等名于世,梁启超叫他“实用主义”①,刘师培谓其“近于墨家”②。如果细绎其著,不难发现,颜元尚行、重利的理论根据乃是“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的理(性)气关系,其最终目的是“作圣”,而不是“利”。为了阐发即事明理、由行见道的原儒精神,他力追三代,反古开新,以“驳气质性恶”为切入点,为谋食、谋利正名。鉴于目前学界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尚待深化,第一,“驳气质性恶”乃“四存编”之首论,此论与其重事功、反光景有何关联?第二,在颜元对“恶”源的追问中,其中蕴含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意识尚须进一步发掘。 一、“谓性无恶,气质偏有恶乎”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二分,始于张载,后经伊川发扬,至朱熹而盛。《朱子语类》载:“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③朱子以“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赞誉张程的“气质之性”之说,其原因就在于此说解决了性善论体系中有关“恶”源的棘手问题。所以,他深叹“圣贤说得‘恶’字煞迟”④。于是,有关道德实践诸问题如理欲之辨、善恶之异,甚至人物之别等,皆诉诸理与气之关系来解决⑤,如朱子曰:“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朱子语类》卷四,第65页)又曰:“才说人欲,便是气也。”(《朱子语类》卷四,第68页)“人物性本同,只是气禀异。”(《朱子语类》卷四,第58页)从宇宙论的角度来看,尽管朱子认为理气之间相互依存,但在道德实践领域,“气”则往往成为阻碍“理”之实现的消极存在,这正是颜元极力批驳之处。 首先,颜元从程朱思想体系内部入手,通过分析其中道器、理气关系之自相矛盾、各相牴牾之处,来阐明“认气为恶”的荒谬性。《存性编》以及《存学编》之“性理评”章皆以此立论,如“四存编”之首编《存性编》曰: 程子云:“论性论气,二之则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朱子曰:“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恶?所谓恶者,气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隐为佛氏六贼之说浸乱,一口两舌而不自觉!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⑥ 在此处,颜元分别称引程朱具有代表性而又相互矛盾的二句话,揭示二人“一口两舌”的龃龉体系。“二之则不是”一语载于《河南程氏遗书》卷六⑦,后被朱子举为明道语来说明性气不离不杂之关系(《朱子语类》卷四,第70页)。按照“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的理气关系,“生生之理”(或“天道”)体现于气之流行与万物繁茂,舍此则无所谓道,亦无所谓理。世界万物千差万别、气之清明昏浊,皆为“道”或“理”之作用与显示,为何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颜元的质疑,不但合乎伦理常识,而且有先秦儒家道器关系为义理根据。不足之处,颜元并未指明“程子”谓谁,“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一语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并未标注谁语。《宋元学案》纳为程明道“语录”,牟宗三亦认为是程明道语。一般而言,程明道喜作“道亦器,器亦道”之体用圆融的表述,程伊川则善分解地思考理气等关系,但都主张道器不离。如果“程朱”并举,则“程”应以程伊川为主,而不是程明道,毕竟朱子与伊川更接近。不过,颜元确实抓住了他们共有的理论缺陷,即“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 其次,颜元常以归谬的说理方式,来论证气质有恶的荒谬性,如他说:“是以偏为恶矣。则伯夷之偏清,柳下惠之偏和,亦谓之恶乎?”(《颜元集》,第11页)在先秦儒家经籍中,伯夷与柳下惠是为圣的标准,孟子甚至称之为“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然二者气质或偏清或偏和,如果以为气偏为恶,则会推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另外,设将道德实践上的“恶”归咎于实然之气质,必然陷入宿命论的困境,颜元说: 程、张于众论无统之时,独出“气质之性”一论,使荀、扬以来诸家所言皆有所依归,而世人无穷之恶皆有所归咎,是以其徒如空谷闻音,欣然著论垂世。而天下之为善者愈阻,曰:“我非无志也,但气质原不如圣贤耳。”天下之为恶者愈不惩,曰:“我非乐为恶也,但气质无如何耳。”(《颜元集》,第12页) “气”是一种既定的实然,而非应然,其清与浊、正与偏不是行为主体自己造成的,如果将“世人无穷之恶”归咎于“气质”,则天下为恶者皆以“我非乐为恶也,但气质无如何耳”为借口,推塞恶责。同样,无志于圣贤者亦可以“我非无志也,但气质不如圣贤耳”为由,拒绝善事。这种“问罪于兵而责染于丝”(《颜元集》,第2页)的做法,既不能惩恶,亦不能扬善,还会导致“天下之为恶者愈不惩”与“天下之为善者愈阻”的尴尬境地。 朱子确有“生下来便恶底”的宿命论倾向,如他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朱子语类》卷四,第69页)这种“生下来便恶底”是禀气以后才出现的,它虽然不违背性善论,但是,如何解释天有“生生之德”,却出现“生下来便恶底”人呢?人们又如何通过道德修养的努力,来解除气对理的限制呢?于此,朱子并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虽赞张载“气质之性”之说,但对“变化气质”并不乐观,如他说:“人之为学,却是变化气禀,然极难变化。”(《朱子语类》卷四,第69页)这种“极难变化”的现实,似乎堵塞了学以成圣的门径。至于门人问:“尧舜之气常清明冲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朱子却“答之不详”(《朱子语类》卷四,第59-60页)。可见,朱子亦为此困惑。 最后,颜元并没有满足于论证气质无恶而已,他以孟子的“践形”说为依据,突显气质的“作圣”之用。因为人的躯体亦属于“气质”,所以他指责说:“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俱秀且备者,人之质也。”(《颜元集》,第15页)血肉之躯乃气所凝成,岂可曰尧舜皆为圣人,然其血肉之躯却为恶乎?以此,他通过诠释孟子的“践形”之说,历史地追索原儒道气并重的实学精神。他说: 孟子一生苦心,见人即将言性善,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明乎人不能作圣,皆负此形也,人至圣人乃充满此形也;此形非他,气质之谓也。以作圣之具而谓其有恶,人必将贱恶吾气质,程、朱敬身之训,又谁肯信而行之乎?(《颜元集》,第3页) 上文“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的“指示”不是仅仅指“迹”给人看,而是由“迹”见“性善”。“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则是由“践形”以见“圣人”。“性善”为道,“才情故迹”为形气,道不离气,成圣不离形气事功。若未成圣,不单是无事功,而且“负此形也”(枉费了一身形气)。朱子的“敬身”之“敬”,不是敬物性之身,而是敬“德润身”之身,而“德润身”正好说明德与身、理与欲、义与利的关联性。既然如此,就不能一方面有“敬身之训”之说,另一方面却认气质为恶,如此两难,则“谁肯信而行之乎”。 孟子论“性善”与“践形”,不仅没有上精下粗、道善气恶之意,而且舍形无以见道,颜元说:“熟阅《孟子》而尽其意,细观赤子而得其情,则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则吾所谓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学是也。”(《颜元集》,第32页)此处“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亦即程伊川“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义,惜宋儒所言“用”多限于伦理而未及利民实学。颜元谓尧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行、六艺即是“气质”,显然是为谋利谋功立基,又有借圣驳朱之意。其中“三事、六府”等泛指一切躬行利民之事,否则,颜元为何曰:“莫谓日月、星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人伦、世故举为道外,并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视为累碍赘余矣,哀哉!”(《颜元集》,第48页)此语是说“日月、星晨、山川、草木、鸟兽”等虽为气质,却是先圣关注的对象,缷罪于气,势必视之为“累碍赘余”。颜元将“气”还原为具体的事功与万象,不再限于伦理之一域,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根据“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也”(《颜元集》,第15页)之原理,济民厚生之实事实功就成了求道的必要条件,如他说:“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试观虞廷五臣,只各专一事终身不改,便是圣;孔门诸贤,各专一事,不必多长,便是贤;汉室三杰,各专一事,未尝兼摄,亦便是豪杰。”(《颜元集》,第667页)相反,如果“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颜元集》,第78页)。这就是颜元倡导躬行与反对“主静求道”,却从“驳气质性恶”入手的根本原因。前此亦有反气质有恶者,如罗汝芳曰:“然则相远,原起于习,习则原出于人。今却以不善委为气质之性,则不善之过,天当任之矣,岂非古今一大冤枉也哉!”⑧此为近溪回答学生疑问之偶言,且没有如颜元将气视为“作圣之具”而指向事功与躬行。 一般情况下,颜著中的“性”既是孟子的“四端之心”,亦是《易》之乾道,如他说:“人者,已凝结之二气四德也。存之为仁、义、礼、智,谓之性者,以在内之元、亨、利、贞名之也。……人之性,即天之道也。以性为有恶,则必以天道为有恶矣。”(《颜元集》,第21-22页)此处,“性”达天道,其中既涵“仁义礼智”,亦摄“元亨利贞”,它是道德创造之源、立身之本。可见,颜元虽重形下之气,却未因此忽视人的真性命,正如钱穆先生说:“据余所见,习斋种种持论,更似颇有近阳明者。”⑨钱先生认为颜习斋持论近阳明,以其能够承接孟子而肯定人的内在道德生命。当然,颜元所论与阳明学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单就论善恶与主张躬行而言,王阳明是在良知至善的前提下,以“正念头”保证实践上的善,以“知行合一”来联结良知与躬行。再者,阳明对前贤得失之评量显得更加宽容与平和,如其曰:“仆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岂欲操戈而入室者?”⑩相较而言,颜元措辞更加激励,猛药方能医顽疾,其历史地位不可掩也。 二、“恶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气质” 那么,谁该对“恶”负责呢?颜元说:“然则恶何以生也?则如衣之著尘触污,人见其失本色而厌观也,命之曰污衣,其实乃外染所成。”(《颜元集》,第3页)又曰:“知浊者为土所染,非水之气质,则知恶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气质矣。”(《颜元集》,第8页)实际上,“污衣”与“浊水”皆不能谓之恶,这只是一种比喻,用以说明实践生活中的恶乃成于外染,而非本来之气质。更具体地说,染于性的“外物”就是“习”或“引蔽习染”,如他说:“恶乃成于习耳。”(《颜元集》,第10页)又曰:“其恶者,引蔽习染也。”(《颜元集》,第2页)这种严格区分“习染”与本来之“气质”的做法,是颜元论恶的显著特色。 颜元仍以先儒为标准来区分“习”与“气质”,如其曰: 大约孔、孟而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之谚矣,其误世岂浅哉!(《颜元集》,第7页) 此处“习”是指遮蔽至善本体(性)的私欲习气,它成于后天之私意,故曰“本无”。“气”则不同,它是人物必不可少的构成质料,故曰“本有”。“气”虽为形而下者,但在原始儒家的生命体验中,它往往获得了与主体道德生命相统一的连续性,如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充塞宇宙的大生命,并非无义理定向的情感冲动,它以道义为根。反观习气则不然,习气是因物欲而起的私念,它不仅是偶然的,而且带有逆理和遮蔽本性的特性,故持心性一体的性善论者皆有复性、去蔽、立志、正心的修养工夫。颜元以为朱子“憎其所本有”是一种“山河易改,本性难移”的命定论,不过,朱子用了一些难以捉摸的模糊语言来避免这种幼稚的结论,如他说:“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滚来滚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朱子语类》卷四,第68页)“才说着气,便自有寒有热,有香有臭。”(《朱子语类》卷四,第68页)此处“滚来滚去”只是一种想像似的语言,寒热香臭属于感官知觉中气质特性,以此解释善与恶,显得十分荒唐。正如陈来先生所说:“实际上张载提出气质时本是用来说明禀性的刚柔迟缓。程朱学说进一步发展到用以说明善恶本质所由生,这就不可能对人的道德本质的形成作出有价值的解说,而且这种学说越细致也就越荒唐。”(11) 既然“习染”非人性固有的偶然之物,自然可以清除掉,而“气质”则不然,如同可去衣之污,却不能除衣之质料(丝或棉)。颜元通过重释朱子的“纸罩灯火”与“京人洗水”之喻,生动地阐明了“气质”不可去的道理。他在《存性编·理性评》中引用朱子“纸罩灯火”喻气质遮性一段话后,评曰: 此纸原是罩灯火者,欲灯火明必拆去纸。气质则不然。气质拘此性,即从此气质明此性,还用此气质发用此性。何为拆去?且何以拆去?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谓戕贼人矣!(《颜元集》,第12页) 朱子的原话是:“且如此灯,乃本性也,未有不光明者。气质不同,便如灯笼用厚纸糊,灯便不甚明;用薄纸糊,灯便明似纸厚者;用纱糊,其灯又明矣。撤去笼,则灯之全体著见,其理正如此也。”(《朱子语类》卷六十四,第1572页)朱子以“笼纸”喻气质、“灯”喻性,“撤去笼”以见“灯之全体”,此喻是值得商榷的。“灯笼”之所以如此称谓,以其有糊纸也。拆去糊纸,就不能再谓之“灯笼”。“气质”之于人性亦是同样的道理,能谓“除去人之气质,则人性之全体著见”否?朱子之所以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导源于此。尽管朱子并没有否定合理的人欲,但却没有相关的理论支撑,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颜元根据“即从此气质明此性,还用此气质发用此性”的原理,责问朱子“何以拆去”,是合乎逻辑的。在另一处,颜元又纠正了朱子的“京人洗水”之喻,他说:“此正洗水之习染,非洗水之气质也。”(《颜元集》,第11页)如杂于水的细菌或尘土等,皆为可以清除的水之外染,而水本身就由气所成,岂能除去水之气质? 颜元将恶归于“外物染乎性”的说法,远可溯至《孟子》“牛山之木”一章,近可见于陆九渊的“蔽心”说和王阳明的“客气”说。在看待恶的问题上,自陆王依《孟子》建立道德本心,始出现与程朱不同的微妙变化,如陆九渊曰:“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12)此处所言“物欲”与“意见”是由行为主体的私欲所引起,它使道体本心受到了蒙蔽。于此,王阳明论述得更加详细,他说:“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29页)“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29页)无善无恶是良知,循良知而动就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主体一旦自愿放弃了良知,选择驰求于外,便是“动于气”,便是道德自主的恶。此“气”显然不是从万物构成处立言,而是指“作好作恶”的私心欲念。王阳明称这种私欲为“习气”,如他说:“夫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家书墨迹四首·与克彰太叔》,《王阳明全集》,第983页)因为障蔽本性的“习气”非人之本有,故又名为“客气”,王阳明曰:“私欲客气,性之蔽也。”(《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68页)“大抵吾党既知学问头脑,已不虑无下手处,只恐客气为患,不肯实致其良知耳。”(《与杨仕鸣》,《王阳明全集》,第186页)显然,此“客气”并不是“本有之气质”。既如此,张载“变化气质”的修养工夫,在陆九渊就成了“剥落物欲”和“立乎其大者”;在王阳明就成了“致良知”、“正念头”、除“客气”。王阳明在激励后生从师问学时说:“夫君子之学,求以变化其气质焉尔。气质之难变者,以客气之为患,而不能以屈下于人,遂至自是自欺,饰非长敖,卒归于凶顽鄙倍。故凡世之为子而不能孝,为弟而不能敬,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于不能屈下,而客气之为患耳。敬惟理是从,而不难于屈下,则客气消而天理行。”(《从吾道人记》,《王阳明全集》,第249页)此处,王阳明教人并不以“变化其气质”为然,惟在循天理、消客气;其中“气质之难变者,以客气之为患”一语,还涉及本有之“气质”与“客气”的区别。不过,王阳明很少有意识地作这种区分。 颜著中的“习染”是作为名词被使用的,它不是服从因果律的时空存在物,而是由主体自由控制的私欲,诸如“堂有父母而怀甘旨入私室”(《颜元集》,第31页)之恶行即是“习染”所致。我们不要混同下面两种用法:第一,以“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及“习与性成”(《尚书》)中的动词“习”来阐释人性之成。朱子谓“性相近,习相远”是说气质之性(13),而非性本身;王夫之以为孔子是说“后天之性”(14),亦非性本身。持性善论者,一般不从后天的训习来说人性之善。只有持“善恶无准”者,才将善恶归于后天渐习,如王廷相曰:“是故敦于教者,人之善者也;戾于教者,人之恶者也。……故无生则性不见,无名教则善恶无准。”(15)王廷相的善恶观遭到刘宗周的强烈反讥,他在《习说》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浑然至善者也。感于物而动,乃迁于习焉。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斯日远于性矣。无论习于恶者非性,即习于善者,亦岂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习相远’。”(16)刘宗周认为无论是“习于恶者”还是“习于善者”,不仅不是说善性本身,而且“日远于性”。尽管朱子、王船山、刘宗周对“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皆以为此语并非说“性善之善”(性本身)。颜元以“天之道”言性善,显然不是由后天所习成,其言“习”只是“外染”。第二,以气性为前提,尽管“习气”作名词用,仍然与颜元所论不同。如陈确说:“虽张子谓‘学先变化气质’,亦不是。但可曰‘变化习气’,不可曰‘变化气质’。变化气质是变化吾性也,是杞柳之说也。”(17)此处,陈确虽然区分了“习气”与“气质”,却直视“气质”为“吾性”。由于缺少“义理之性”,所以就无从言对内在本体的遮蔽,因而这种“习气”也不能视为颜著中的“习染”。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见颜元有关“恶者是外物染乎性”的说法,主要继承了陆王的道德本心与“良知”说,同时也吸纳了张朱等“气质之性”的某些内容。由于“外染”是可以清除的,相对朱子而言,颜元给予人性更为乐观的积极态度。另外,由于“习气”与本来之“气质”的严格区分,有关人的自由意志的主题必然会凸显出来。当然,王阳明针对“恶念”的“正念头”已经充分地预设了人的选择与自由,只不过它没有颜元所言“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更加明确与条理一贯。 三、“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 恶源被颜元追问至“外染”,此是消极地从本源受到遮蔽的角度进行阐释的;积极地说,恶的真正发动处却是行为主体自己,即“人可自力也”。颜元以“墙卑易招盗”为例,非常形象地追溯“恶”的最终发源地,他说: 人之自幼而恶,是本身气质偏驳,易于引蔽习染,人与有责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伦!人家墙卑,易于招盗,墙诚有咎也,但责墙曰“汝即盗也”,受乎哉?(《颜元集》,第11页) “自幼而恶”是一种经验的溯源法,在性善论体系中,此论很容易将恶归咎于“本身气质”,如上文提及程颢所言“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即是。颜元认为,即便是“自幼而恶”者,亦是“人与有责也”,其原因就在于“人可自力”。此与“墙卑易招盗”而不能“责墙”,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天生的恶棍,可以将各种恶行粉饰为由于“气质偏驳”所酿成,但只要他意识到促使行为的“自力”因素,仍然免不了自责。一个自幼就显出恶性的人,可以将种种恶行归于他的自然气质,但却仍然要像气质清明者一样承担责任。陈确亦反对程朱“卸罪气质”,使“气质蒙恶声”(《陈确集》,第452-453页),却未充分地认识到“人可自力”的根本原因。 毋宁说,“自幼而恶”者是他自愿接受了顽固不化的后果,以自然性状为托词,只会暴露出更加卑鄙的“恶念”。属于自然现象的气质,根本不可能建立任何道德责任,而人的意志以人性(至善)为准则,它不属于现象之列,因而,“人可自力”所包涵的道德主体的自由意志与“本身气质”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康德把主观意志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立性”称为“自由”(18),颜元则称之为“自力”,他们阐释了一种相同的自由原则。 如果说“人可自力”尚止于道德实践层面的话,那么,“自玷其光莹之本体”完全是从哲学本体层面追问恶源,颜元说: 其所谓恶者,乃由“引、蔽、习、染”四字为之祟也。期使人知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颜元集》,第49页) “极神圣之善”是谓天德至善,亦谓人性之善,此须关联“人之性,即天之道也”来理解。《周易·系辞上》曰:“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易道生生不息,无所不存,在人则谓之性,若谓之善,则是“无条件的定然的善,是‘体善’,并非‘事’善”(19)。这种“体善”颜元称之为“光莹之本体”,它是自做主宰的自律根据。道德修养就是要自觉地将这个“人皆有之”的“本体”充显出来,使之润泽、充满“固有之形骸”。《孟子·尽心上》曰:“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所言“睟然见于面”等即是颜元所谓“充其固有之形骸”之义。颜著《存性篇·明明德》引用孟子此语,说明颜元于此深有体悟。当行为动机摆脱了纯粹“形骸”的束缚,将“本体”做为唯一的根据时,主体便从这种优越于“形骸”的“极神圣之善”中获得人性的尊严。相反,如果只是为了感性的动机(物欲),自主地放弃这个最高准则,就是舍心逐物、躯壳起念,这就是道德上咎由自取的恶。这种由于主体自主造成的“本体”受私欲蒙蔽的状态,颜元称之为“自玷其光莹之本体”。所谓“自玷”,意即恶行是由主体为了私欲而自由、自主地发动的,它明确地预设了人的自由本质。 因为气质直接关联着“利”与“作圣”,所以,如果以“气质偏驳”为借口,推诿恶责,必然是“纵贼杀良”,颜元说:“恶既从气禀来,则指渔色者气禀之性也,黩货者气禀之性也,弑父弑君者气禀之性也,将所谓引蔽、习染,反置之不问。是不但纵贼杀良,几于释盗寇而囚吾兄弟子侄矣,异哉!”(《颜元集》,第13页)自主选择为恶的“渔色者”、“黩货者”、“弑父弑君者”,没有担当应有的道德责任,却责其“气禀之性”,这就等同于“释盗寇而囚吾兄弟子侄”。以此为原则,不仅无法通达“人可自力”的自由本质,而且还会导致人们对正义事业的拒绝,以及对“天道”不公的抱怨,岂不哀哉! 四、“驳气质性恶”的意义及颜学缺憾 颜元“驳气质性恶”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二点: (一)以尧舜至孔孟为鹄的,以“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为理论基础,还原“经济生民,无所不为”的原儒精神,并提出“身心道艺,一滚加功”的修养工夫以及“义中之利,君子所贵”的新义利观。 颜元所言“气质”可分为二类:一是尧舜三事、周孔六艺等利民厚生的实学技艺。熊十力先生说:“古言艺者,其旨甚宽泛,盖含有知能或技术等义。六经亦名六艺,取知能义也。”(20)颜元倡躬行实用之学,必资乎古代圣王六艺等学,即是取其“多能鄙事”、“经济生民”、“多材多艺”、“造就人材”之知能或技术义,如他驳朱子称“李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时说:“只‘不作费力事’五字,不惟赞延平,将有宋一代大儒皆状出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试观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自儿童嬉戏时即习俎豆、升降,稍长即多能鄙事,既成师望,与诸弟子揖让进退,鼓瑟,习歌,羽籥、干戚、弓矢、会计,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盖无所不为也。及其周游列国,席不暇燰而辄迁,其作费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艺,吐餔握发以接士,制礼作乐以教民,其一生作费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气’,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辅世泽民,参赞化育故也。若夫讲读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养性,不肯作一费力事,虽曰口谈仁义,称述孔、孟,其与释、老之相去也者几何!”(《颜元集》,第68-69页)可见,颜元称古以其利民而遂其生,因天地之化而开物成务。颜元所言另一类气质就是上文提及的“耳目、口鼻、手足”等“人之质”。因为“气质”包涵了“艺”与“身”,所以,在颜著中,传统的理气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表述为身心、道艺的关系。如此一来,根据“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的道理,实学技艺就合理地成为道德修养的“下手功夫处”。 钱穆先生机敏地觉察到了颜元思想中的道艺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修养功夫的特别之处,他说:“若谓本心之天理,与事物功利交济互成,实属一体,则下手功夫,将自事物功利以认识本心之天理乎?将自本心天理以完成其事物功利乎?”(21)诚如钱先生所问,颜元提出“身心道艺,一滚加功”(《颜元集》,第87页)的修养功夫,一方面,就是要“自事物功利以认识本心之天理”,如他说:“只艺学是实下手功夫处。”(《颜元集》,第192页)又曰:“除了人情物理,更无处下手,更无处见‘万物皆备’之‘仁’。”(《颜元集》,第242页)也就是说,献身于知识、技能的治学精神即是“仁”,离此别无空悬之“仁”。“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矣。”(《颜元集》,王星贤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4页)“艺”成为“德成”的途径,不再仅是谋生的手段,这是对王阳明“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的继承与发展。《易·系辞下》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先圣之学即是于用识体,于博物多能而逢其原。另一方面,颜元虽重事功,但只取事功,却非其本意,如他说:“世间人只为‘温饱’二字,耽搁了多少英雄,埋没了多少人品!夫子就此地扫兴他一场,直令膏粱子弟、肥马轻裘者无立身处,衣敝緼袍不耻,只是‘志’好。”(《颜元集》,第183页)做人先要立志,有了大本,才有“立身处”,否则,英雄主义只是舒发个人的气质生命,膏粱子弟与肥马轻裘者亦只是养个躯体,湮没了所以为人的“光莹之本体”。 如此,义利、身心之表面紧张,实为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利”成了“义中之利”,颜元说:“利者,义之和也。《易》之言‘利’更多。孟子极驳‘利’字,恶夫掊克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颜元集》,第163页)此处,颜元借用《周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与孟子驳“利”之真义,巩固其说。“利”不再是无关道德的个人嗜欲,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其中有“仁”,此与纯粹的功利主义大相异趣。至于颜元将“正其谊,不谋其利”更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颜元集》,第163页),亦不悖“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儒思想。 (二)由于“自玷”、“自主”等观念的引入,丰富与发展了“为仁由己”的儒家伦理。颜元将恶归咎于行为者“自主”的说法,之所以显得格外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澄清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而且如果沿着颜元“自玷”理论向前发展,则与“自主”、“自力”相关的论题,比如自由、责任、独立人格等范畴,都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传统伦理学的论域。人的“自由意志”亦必然得到重视,追求独立人格与社会责任感亦将被驱动起来,正如萨特所说:“就是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22)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儒学自开创初,即建立起道德自觉自发之路径。孟子沿着孔子所开创的生命智慧,建立性本善的内圣之学。人性善并非意味着人之初生即有道德实践意义上的善,而是个人自觉地将这种先天的禀赋(仁义礼智)纳入自己的行动准则之后,他才使自己成为善者。性善规定了成圣的可能性,并激励人们通过道德修养去努力地实现它,而不至于使人们觉得修养功夫是完全无济于事的。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的说法,其中蕴涵着“由自己”创造善或恶的意思。不过,王阳明的“四句教”主要是从境界上立言,因此,后来王龙溪自悟“无意之意则应圆”,不仅未坏师门教法,而且王阳明谓“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或许只有如颜元步步追问恶源,才能使“自由”壁立千仞地站出来。 遗憾的是,颜学发展到李塨,就已到了“恐非绵力所能搘撑”(23)的境况,主要原因如下:第一,颜元虽赞周孔等“多能鄙事”、“多材多艺”,然其论却多拘于“三物”之域,更没有触及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质测”之学。至李塨,他以“礼”统“三物”,以“行礼”为“圣学之方”(《李塨文集》,第770页),致使颜李学术越走越窄。第二,在颜著中,虽不乏精彩言论,但其立体透性之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如其曰:“眶、皰、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颜元集》,第1页)眶皰睛等属于气质,“能见物”则是更下一层的气质之功能。在“棉桃喻性”中,以功能言性尤其突出。功能性如何成为价值之源、“光莹之本体”呢?章太炎以“滞于有形,而概念抽象之用少”(24)评价颜学,并未失公允。后来,李塨本着“目见身试”、“因形以察理”(《李塨文集》,第86页)的学术立场,加深了这种“滞于有形”的经验性质。除上述理论缺憾之外,另有其它因素。首先,颜元深居不出,未能亲播其学,不能大其传。弟子李塨虽广结名流,然二者之学并非完全契合。其次,当时南方学风,或尊程朱,或务考据,皆与颜李之学异趣。此乃时势也,不可尽责于人。 ①梁启超说:“他(颜元)用世之心极热,凡学问都要以有益于人生、可施诸政治为主。所以我又叫他‘实用主义’。”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②刘师培说:“谓颜学近于墨家,要亦近是。”见刘师培:《习斋学案》,载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页。 ④《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第2252页。 ⑤陈来先生认为朱子的“气质”之说主要解决二个问题:“一是说明人的品质何以存在差别,一是着重说明气质的不善是人的恶的品质的根源。”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⑥颜元:《颜元集》,王星贤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⑦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六,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1页。 ⑧见黄宗羲:《参政罗近溪先生汝芳》,《明儒学案》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95页。 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4页。 ⑩《答徐成之》(二),载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09页。 (1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12)陆九渊:《与赵监》,《陆九渊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页。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5-176页。 (1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964页。 (15)王廷相:《王廷相集》,王孝鱼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65页。 (16)刘宗周:《语类十·习说》,载《刘宗周全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1页。 (17)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54页。 (1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载《康德三大批判全集》下,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19)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83页。 (20)熊十力:《原儒》,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2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9页。 (22)[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671页。 (23)李塨:《李塨文集》,邓子平、陈山榜点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9-750页。 (24)章太炎:《颜学》,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