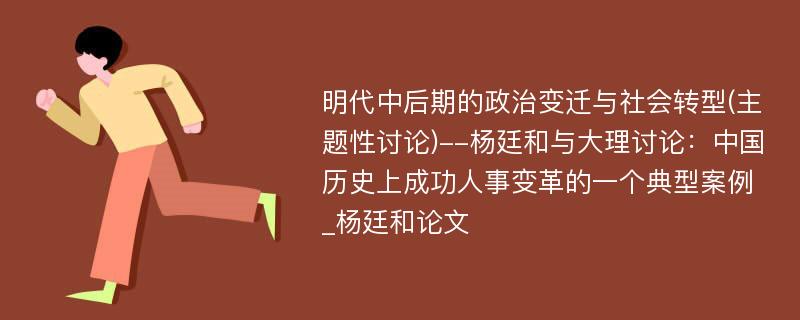
中晚明的政治变动与社会转型(专题讨论)——杨廷和与大礼议——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大礼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变动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明代正常的皇位更迭之际,大多数内阁首辅并无特殊表现,亦很难因此而出名,但杨廷和不同,他因皇位更迭而名噪一时,并为后世学者所关注。因为在他担任首辅时,明朝皇位更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明武宗的绝嗣和皇位一时的空缺将他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于这一特殊时期的杨廷和,学界的评价很不一致,其中大多数沿袭部分明清学者的说法,一味地放大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行为,并刻意为其辩护。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这一时期杨廷和的一味粉饰显然是有问题的,无助于对明代政治特别是嘉靖政治的客观认知。目前对杨廷和总体研究的水平还不高,缺乏有深度、有见地的高质量成果。大礼议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绝非简单的礼仪问题,那种试图以礼仪为视角来解读大礼议是不可能认清这场争论本质的。本文以有明一代的政治演变为视角,就杨廷和与大礼议的相关问题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进一步阐明自己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认识。
一、杨廷和引发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大礼议
研究杨廷和的政治活动,不在于简单罗列一些材料为其树碑立传,而在于选择最佳视角通过其言行来揭示明代政治运行模式的特点和解读明代政治走向的选择,并进一步解释明代为何能够延续276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不间断历史最长的王朝。如果今天仍然停留在580多年前大礼议中的“君子”、“小人”之争的层面上,无视基本事实,沿袭旧说,挺杨贬张,只能说明明史研究的停滞状态。
要客观地认识杨廷和在大礼议中的行为表现,首先要必须明确和承认以下三个基本事实:第一,明世宗朱厚熜的即位完全不同于汉宋旧例,而是一种全新模式;第二,明武宗生前拒绝立嗣,没有亲自选定皇位继承人,临终前也无相关安排[1],死后也无人为其续嗣;第三,由杨廷和等人草拟、武宗之母张太后同意的武宗遗诏没有要求朱厚熜改换父母,而是明确规定他以孝宗之侄、武宗堂弟和兴献王长子的身份继承皇位。也就是说,武宗遗诏的颁布,正式宣告了武宗的彻底绝嗣。这三个基本事实只反映一个问题,即世宗即位模式无前例可寻,自然也就无前例可比。明代历史在武宗死后处于十字路口的抉择之际,而这一时机正是考验杨廷和政治眼光和行政才能的关键时刻。面对陌生的、即将入主北京的藩王朱厚熜,杨廷和如何与其相处,应该是杨廷和面临的最大问题。的确,在这一时刻,杨廷和具有其他皇位更迭之际内阁首辅所不具有的特殊条件,如果他能高瞻远瞩,尊重朱厚熜即位的基本事实,利用“拥立”之功,构建相对融洽的君臣关系,有可能在新朝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避免出现其他时期的首辅在新君即位后不久被抛弃的局面。
然而,杨廷和并未选择这一最佳路线。当世宗命令礼部讨论其父兴献王主祀称号时,杨廷和不容讨论,忘记自己的身份,盛气凌人,以汉定陶王、宋濮王之事向礼部尚书毛澄指示:“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这不是简单的一条指令,而是影响嘉靖政局特别是杨廷和政治命运的一次路线选择,是杨廷和挑起大礼议的标志,也是杨廷和破坏廷议的写照。按照杨廷和的指令,首先反对其大礼观的嘉靖皇帝就是“奸邪”之人,应当斩首!在明代,恐怕再也找不出像杨廷和如此狂妄的阁臣!杨廷和不允许廷议,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他要用“奸邪”来孤立异己者,用杀戮来诛灭反对者,其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令人震惊!对于一个事实清楚的问题,杨廷和不仅自作聪明,指鹿为马,而且还要排斥异己,堵塞言论,拒绝廷议,挥舞“奸邪”的道德大棒和使用暴力恐吓来对付不同的声音[2]。事实上,杨廷和选择了一条与世宗彻底对抗的道路,也就是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和迅速败亡的道路。
作为一名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大礼议中的道路选择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大败笔。在明武宗绝嗣暴卒之后,明代政治客观上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即嘉靖时代。杨廷和能否顺应这一潮流,是评价他、要求他的唯一指标。如果说杨廷和身在其中而浑然不觉的话,那么作为今天的研究者至少要达到这一高度。杨廷和蛮横地干预廷议,引发大礼之争,并试图将一己之意强加于礼部和世宗。在提出汉宋旧例之后,他又找出一些虚无的或不相符的旧例连连向世宗施压,如说:“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未闻追崇其所生父南顿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则圣德无累,圣孝有光矣。”(《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对此不得要领的迂腐之论,世宗不予理睬。杨廷和可以一时阻挠廷议,但他不可能真正阻挠由他引发的大礼之争。礼部组织的廷议被他所阻滞,但更大范围的讨论势不可挡,明代的政治体制不可能使杨廷和一手遮天。杨廷和虽然没有独裁者的权势,却有天大的独裁者的野心,他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3]。
二、杨廷和在大礼议中失败的必然
从杨廷和及其追随者在武宗暴亡后迅速消失的视角来看,大礼议就是杨廷和集团退出嘉靖政坛和败亡的转折点。自杨廷和提出依照汉宋旧例来解决明世宗所面临的新问题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杨廷和及其追随者的政治命运。换言之,杨廷和以议大礼为表现形式而与嘉靖皇帝的对抗,注定了其败灭的必然命运,并由此创造了前朝旧臣退出政坛的新模式。
在每一次皇位更迭之际,前朝旧臣与新君都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大多数表现为皇帝有令不行,或倚信宦官,或怠于朝政,或胡作非为,舆论一般倾向于同情朝臣特别是阁臣。但正、嘉之际可不是这样,大礼议中的主动权并非为杨廷和所拥有。首先,杨廷和的大礼主张是违法之说,他根本无视武宗遗诏的明确规定而试图更换嘉靖皇帝的父母[4]。一些学者顺从杨廷和的思路,也无视世宗合法即位的这一法律文书,引经据典,用超越历史时空的方法为杨廷和的主张一再辩护,并再三嘲弄世宗依据武宗遗诏而维护自己尊严的行为。其次,在一些学者考察杨廷和的大礼观时,根本不考虑明武宗生前拒绝立嗣的行为,也不愿提及杨廷和于武宗生前在选立皇嗣问题上的失职,当然更不愿追究首辅杨廷和的责任。人们故意回避议礼的前提特别是武宗拒绝立嗣的行为以及杨廷和在武宗立嗣问题上的漠然,其目的仍在维护杨廷和的形象。杨廷和在武宗生前没有促成立嗣的实现,那么在武宗死后,他应该想法为其续嗣,但他又未这样做,而是选取武宗堂弟、兴献王的独子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这一选择事实上已正式宣告武宗绝嗣,即杨廷和等人不再关注武宗的继嗣问题,而只注重明朝的继统,即武宗遗诏是朱厚熜继统的宣言书,正式宣告不再为武宗立嗣。不论选择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是否正确,但一经宣告,就变成不可更改的事实。当他事后硬要把继统强迫改成继嗣并迫不及待地宣布异己者为“奸邪”的时候,事实上在反证杨廷和自己的“奸邪”。因为他知道自己强迫世宗改换父母之说是一种违法之邪说。在他主导下,使武宗死后丧失了续嗣的机会。也就是说,武宗生前拒绝立嗣,杨廷和在武宗死后又将武宗绝嗣用武宗遗诏这一合法形式变成了现实,使其永无续嗣的可能性。离开了武宗遗诏而妄谈世宗所面临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而邪与不邪只能以武宗遗诏的相关规定来判定,即违背武宗遗诏者为奸邪,而不是违背杨廷和的主张者为奸邪!在选定皇位继承人时,杨廷和没有考虑为无嗣的武宗续嗣的问题,而在朱厚熜即位后,却要为已死17年之久且有武宗为嗣的孝宗续嗣,其荒诞之举,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了。正如方献夫所言:“臣非敢谓宋人濮王之议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无子,今我孝宗有武宗为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尝育英宗于宫中,立为皇子,今皇上未尝育于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众子,今献皇帝止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此三不同,昭若白黑,乌得牵合而强附哉?”(陈建:《皇明通纪》卷三四)由此可见,是杨廷和等人一手造成了武宗的彻底绝嗣,当世宗即位后,也就根本不存在为武宗续嗣的问题了,当然更谈不上为孝宗续嗣。研究大礼议,必须以此为前提。
政治机遇稍纵即逝。当杨廷和决定要用汉宋旧例来解决嘉靖皇帝的新问题的时候,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明世宗的对立面,成为新朝的阻碍力量,自然也就成为嘉靖皇帝必须清除的对象。从这一角度来看,大礼议事实上就是嘉靖皇帝清除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而组建新的班底的过程。也就是说,清除杨廷和集团就成为嘉靖皇帝即位之后的首要任务。因为嘉靖朝的人事组织只能以世宗为核心来组建,而绝不可能以杨廷和为核心来组建。
迫于杨廷和的淫威,绝大多数朝臣特别是阁部要员和言官不敢站出来向其叫板!相反,他们阿附盲从,寻章摘句,绞尽脑汁,拿旧例向世宗及反对者施压,为杨廷和的大礼观作各种牵强附会的辩护。此时,只有新科进士张璁不怕“奸邪”的污辱和围攻,也不惜丢掉47岁时来之不易的见习官职,不顾个人安危,以武宗遗诏为武器,向杨廷和的大礼观连连发起攻击。张璁的出现,重新开启了被杨廷和所阻止的廷议,这是必需的环节,杨廷和无力干预。而张璁其实是沿着杨廷和草拟武宗遗诏时注重继统的路子来坚定支持世宗的。他认为嘉靖皇帝“为兴献王长子,遵祖训兄终弟及,属于伦序,实为继统,非为继嗣也。”(《张璁集》卷一《大礼或问》)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皇上与为人后者,礼官附和执政之私也……今诸臣任私树党,夺皇上父母而不之顾”(《张璁集》卷一《正典礼四》),并指斥言官“今率甘为权臣鹰犬,甚可耻也。”(《张璁集》卷一《正典礼六》)细读张璁的大礼之论,他都是围绕着武宗遗诏来展开辩论的,并根据事实始终认为世宗与其父的关系不能更改。既然父子关系不能变更,那兴献王自然就得称皇称帝。可以说,是杨廷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议礼的主动权转手给了张璁,张璁高举着杨廷和所绘制的继统大旗,掌握着议礼的主动权,最后获胜没有任何悬念。换言之,是杨廷和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有利地位,助推张璁的迅速崛起。那种张璁“迎合”世宗的说法是一种肤浅的乃至错误的看法[5]。
但是,由于杨廷和人多势众,在其营造的“奸邪”氛围中,张璁的人格被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一再丑化和扭曲,各种污辱之词纷纷落在了张璁头上。可以说,大礼议的过程其实是杨廷和一派强词夺理和污辱张璁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最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一些学者至今沿袭旧说,将杨廷和一派视为正人君子,并将其作为中国士人的传统代表而无限拔高,而把反抗杨廷和淫威的张璁等人看成“小人”。如果他们获得大礼议的胜利,那才是嘉靖政治的一大笑料!
自杨廷和挑起大礼议后,张璁接过杨廷和的继统大旗,沿着武宗遗诏所确定的正确道路前行,并因此走上了创新之路,既赢得了议礼的胜利,又获得了新君的倚信。而杨廷和丢掉继统而高举继嗣大旗走上了歧路,最终一败涂地,连其儿子杨慎的政治命运也一并葬送。杨廷和父子在大礼议中翻船,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左顺门事件是血腥的,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但不能因为血腥反过来证明杨廷和大礼观是正确的,更不能无原则地把一切不满泼向明世宗和张璁。杨廷和集团最终覆灭是不可避免的,左顺门事件是他们执迷不悟和困兽犹斗的必然结局,是他们为杨廷和大礼观甘愿作出的殉葬选择!否则,他们便成为杨廷和所说的“奸邪”之人了。自从他们选择支持杨廷和大礼观之后,也就走向了不归之路。除了碰得头破血流和粉身碎骨,他们再无路可走。他们的政治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而不是在明世宗和张璁等人的手中。父唱子随,当杨廷和大礼观被彻底否定之后,杨慎等人铤而走险,在杨廷和的错误路线上越走越远,他们试图与世宗决斗,这无疑是飞蛾扑火,最终成了杨廷和大礼观完全的牺牲品。鱼死但不可能网破,他们的举动在任何有序的政治秩序中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三、清除杨廷和集团是世宗的首要政治任务
就正、嘉之际而言,杨廷和也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学界对杨廷和的“事功”发掘得很细,有的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急于用“革新”来标榜。事实上,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不可能在职位上只干坏事,不干好事,所以简单地罗列政治人物的所谓“好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大多数情况是时势使然。考察一个政治人物的作为,必须要从时局出发,看他能否把握机遇,顺应历史潮流,化解各种矛盾,聚集各种力量,创造性地作出引领时代发展的决策,并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就杨廷和而言,后世之人在研究他时,首先要回答武宗暴卒后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从事改革的条件具备了没有?因为正、嘉之际与其他时期的皇位更迭完全不同,杨廷和与即将登极的朱厚熜没有交往,不了解他的情况。这种情形就决定了杨廷和不可能像其他时期的内阁首辅那样等新皇帝即位后按照即位诏书来革除一些弊政,而是首先要与嘉靖皇帝建立互信关系,尽量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树敌过多,特别是要避免与皇帝对抗,确保政局的相对和谐与稳定。如果他冷静地分析形势,有效地利用武宗遗诏,创造性地解决世宗所面临的新情况,也许还能在嘉靖朝有所建树。但人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形,他因议礼丢了饭碗,毁了自己的政治命运。于是,有人为杨廷和愤愤不平,把所有的不满洒向嘉靖皇帝,洒向张璁,以谩骂为能事。这在时下的论著中随处可见。这种认知模式急需改变,因为杨廷和无法适应嘉靖政治的新情势,重演着前朝旧臣在新朝被冷漠的情形,所不同的是,这次却因为杨廷和挑起大礼议而被皇帝冷落,君臣关系因杨廷和引发的大礼议而降到冰点,这对阁臣来说是最大的政治灾难。正如李贽所言:杨廷和“虽能委曲于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达礼之主,天资近道而不知学,是最为可惜之人。”(李贽:《续焚书》卷二《史阁叙述》)
正是由于杨廷和对武宗死后的政治形势判断不清,以至于使他在自己挑起的大礼议中迅速败亡。从这一角度来看,大礼议又是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败亡的过程,换言之,就是明世宗彻底清除杨廷和集团的过程。这样一种大换班、大清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典型的案例。这种结果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杨廷和并非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在明代历史巨变之际,他瞬间迷失了方向,缺少把握机遇的能力,由主动迅速变为被动,并很快被淘汰出局。而张璁的崛起,事实上是杨廷和为其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是杨廷和的错误选择造就了张璁。当杨廷和要以牛头不对马嘴的汉宋旧例来解决新问题时,就预示了他已经成为嘉靖政治中的多余之人,即使没有张璁,也会有人挺身而出,向其大礼观发难的。可以这样说,张璁等人在大礼议中不畏打击报复、维护政治秩序和法律尊严的行为是明代士人的真正代表。那种无视杨廷和用“奸邪”的狂妄态度对付反对派,而一味地放大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功,试图为其树碑立传,严重制约着杨廷和及嘉靖政治研究的深化。
当明代历史走过150余年后,积弊甚多,的确需要改革,但能不能改革?改革由谁来领导?改革如何进行?这不是杨廷和说了算的事。如果按照所谓“杨廷和革新”的逻辑来看,那么所有在皇位更迭时的内阁首辅都成了改革家,他们都可以按照新君即位诏书来进行改革了。所以,这样的表述没有任何学术意义。武宗一死,杨廷和就要领导明代的改革,改革能有这样简单和随意吗?相反,在正、嘉之际要真正进行改革,首先就要清除无视法律和破坏明代政治秩序的杨廷和集团,这是杨廷和集团想象不到的。
武宗绝嗣并未预立嗣子,以及选取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这本身是一大变化。事实上,这一变局隐含着变革的机遇,完全不同于父死子继的政治形势,朱厚熜以孝宗之侄、武宗之堂弟、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君临天下,没有回护前朝弊政的心理负担和思想压力,完全有可能对前朝乃至前几朝的弊政进行深刻反思。而他从湖北地方长大,了解政治弊端和社会实情,完全不同于生长于皇宫中的新君,必然会带来新的气象。这些是全新的现象,预示着变革的可能性。而与此同时,杨廷和也必须顺应新君的这一变化,并与其匹配。但杨廷和以不变应万变,当其随意违背武宗遗诏而强令朱厚熜改换父母时,也就表明了他要自行其是,重演历史上专横跋扈的权臣,不把朱厚熜放在眼中。当年仅十四岁的朱厚熜说出“遗诏以吾嗣帝位,非皇子也”(《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时,已让这位小皇帝看清了杨廷和蔑视皇帝、出尔反尔和无视法律的真面目。从大礼议中嘉靖皇帝步步为营并将庞大的杨廷和集团逼上绝路的历程来看,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为蔑视嘉靖皇帝特别是破坏法律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他们的失败不是失败在明世宗的皇权之下,而是输在他们蔑视外来的嘉靖皇帝和他们所选择的错误道路上。在世宗看来,杨廷和挑起的大礼议就是蔑视自己,非要把自己改换成孝宗的儿子才能获得合法地位,但他没有上这一圈套,他明白自己合法即位的条件是堂兄武宗的遗诏,而不是伯父孝宗的光环。他事先没有答应改换父母,登极后更不会改换父母,即使退位也不会改换父母,这是世宗做人做君应有的尊严。世宗对杨廷和大礼观说不,应予充分肯定,而不能无原则地嘲弄世宗。因为换成什么人,都不会因为意外地得到皇位而见利忘义,见利忘孝,随便改换父母。所以,议礼的过程其实就是否定杨廷和大礼观的过程,就是要把问题拉回到武宗遗诏的起点上,尊重基本事实,按照具体问题来确定嘉靖皇帝与其父母的固有关系。只要确保这一关系不被否定,其他对单纯的礼议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论,世宗是能够容忍的。所以,大礼议的核心就是朱厚熜能不能改换父母的问题,而嘉靖皇帝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依据武宗遗诏自己绝不能更换父母。但杨廷和自不量力,非要动员朝臣盲从自己,强迫朱厚熜改换父母,最后全部葬身于自己所导演的大礼议中。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世宗即位后最大、最迫切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杨廷和集团这一政治目标了。世宗事后对杨廷和挑起的大礼议给予严厉的批驳,说:“朕本藩服,以我皇兄武宗毅皇帝青宫未建,上宾之日,遗诏命朕入绍大统,以奉天地宗社之祀,君主臣民。当是时,杨廷和等怀贪天之功,袭用宋濮安懿王之陋事,以朕比拟英宗,毒离父子之亲,败乱天伦之正。朕方在冲年,蒙昧未聪,致彼愈为欺侮。幸赖皇天垂鉴,祖宗默佑,以今辅臣张璁首倡正义,忘身捐命,不下锋镝之间,遂致人伦溃而复叙,父子散而复完。”(《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寅)只有将其全部清除,引用新人,才能组建与新君相匹配的人事关系,才能确保革新的有序进行。
对正、嘉之际杨廷和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而是从明代政治演变的高度对以他为首的旧臣势力在这一时代巨变中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杨廷和的失败和张璁的崛起绝对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进退都有其历史的必然。就明代政治制度的特点而言,杨廷和绝不可能用胁迫他人的做法来达到自己议大礼的目的,他的行政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一些人对杨廷和在正、嘉之际事功的无限放大,其实是在歪曲历史,无助于对杨廷和的理性认识,更无助于对明朝政治的客观认知。杨廷和在大礼议中的失败,再次证明了明代政治体制对权臣防范的有效性,任何人试图要凌驾于明代政治体制之上是不可能的。
杨廷和及其追随者在自我导演的大礼议中彻底失败,明世宗借此成功地清除了因武宗绝嗣而形成的对皇权的危害力量,恢复了皇权,重建了嘉靖政治新秩序,并在这一人事更迭中形成了嘉靖朝的新气象[6],成为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
标签:杨廷和论文; 嘉靖帝论文; 大礼议论文; 明代皇帝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明朝论文; 武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