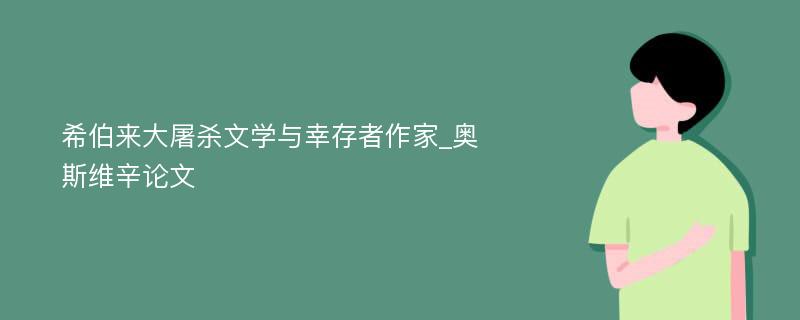
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与幸存者作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伯来论文,幸存者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4-0053-07
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是以色列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反映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与体验,以及战后以色列人在“后大屠杀”时代对历史灾难与民族创伤的面对、认知与反思。大屠杀文学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成为希伯来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数百名作家描写过大屠杀题材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就有300多部,此外还有中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作家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反应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打破沉默的过程。换句话说,在大屠杀历史结束之后,以色列作家在反映与表述历史灾难方面其实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挑战。
一 文学表达的艰难与局限
造成表述灾难历史艰难性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首先是人们对是否有合适的文学样式能够反映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表示怀疑。犹太世界一向推崇美国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里·维塞尔曾经作出的论断:描写奥斯维辛的小说,要么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要么就是它写的不是奥斯维辛[1]。阿尔多诺也有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2]361-373 名言。这种疑虑在犹太世界里带有普遍性,导致作家在试图涉猎大屠杀这段历史时心存余悸。
其次,是如何对大屠杀这段历史进行表述。有的学者曾经提出,这类文学是否只对暴行及其过程本身做忠实的记载?时间是否只限于1933年到1945年之间?对于个人或者群体,对幸存者,幸存者的子女以及我们大家是否有沉重的压力?是讨论某一具体事件,还是人类总的境况?[3]13-32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文学是很难界定的。
再次,是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也对大屠杀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这里先要谈及的是文学类型问题,在大屠杀文学领域,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诗歌以及日记等,文学类型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叙述形式的选择,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模糊性。有的长篇小说看起来像日记与回忆录,有的日记和回忆录又带有相当浓厚的文学色彩。还有,就是文学语言问题。在大屠杀文学研究领域,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表达不可表达之事,描述不可描述之事①。这句话本身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事物本身无法真正言状,那么就不要做任何言状的尝试。换句话说,如果你触及了这个领域,用语言去表述,那么就不是不可言状之物。实际上,这里是指在把握语言上的难度。犹太人,尤其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多无法摆脱对大屠杀历史的记忆。以色列犹太人中有几十万大屠杀幸存者,多数家庭要么有家人、亲友在大屠杀中丧生或在集中营遭受过迫害,要么就是在国家塑造民族历史灾难记忆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大屠杀的深切体验。他们对这场历史事件所做的回顾与反思经历了一场从肉体到心灵的炼狱过程,幸存者本人不愿意去回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痛经历,其子女也本能地不愿意去触摸父辈的伤疤。著名的第二代大屠杀女作家娜娃·塞梅尔曾经说过:“孩子有保护母亲的秘密任务。奥斯维辛是所有恐怖的一个语词密码,是某种东西的开门咒,其背后只是绝对的疯狂。所以不要做这件事,请不要去写。”[4]118 此外,还会有民族的或者是集体的一些禁忌。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成了真正的囚牢。
更重要的,以色列在1948年刚刚宣布建国便遭到周边阿拉伯世界的联合进攻。本-古里安政府在50年代为了国家的生存需要、激励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教育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并倡导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模式塑造新型的以色列人[5]194。注重强调以“华沙起义”、“游击队反抗”为代表的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因而忽略了欧洲犹太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面对强权所遭受的苦难。本土以色列人非但未对大屠杀幸存者的不幸遭际予以足够同情,反而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向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不理解,甚至对幸存者如何活下来的经历表示怀疑。在这种政治话语的影响下,对战争期间像“屠宰羔羊”一样死去的数百万人的纪念也不免会成为新兴国家铸造立国精神时的不利因素。大屠杀幸存者的痛苦即使不会被从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中全部驱走,但也要同主流的政治话语拉开距离,在公共场合没有立足之地。
诚然,以色列建国与大屠杀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但是,幸存者希望在新的土地上获得新生,他们并不为过去的苦难经历感到骄傲,对过去梦魇般的岁月具有本能的心理抗拒。多数幸存者为了新的生存需要,不得不把对梦魇的记忆尘封在心灵的坟墓里。2002年4月,我跟随以色列教育部组织的学生代表团参观奥斯维辛的途中,结识了出生在匈牙利、现住在特拉维夫的大屠杀幸存者爱莉谢娃。她曾见证,在以色列建国之初不可能将自己在集中营的痛苦讲给别人,如果这么做,人家会认为你是疯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如何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如何把历史创伤转换成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政治话语,也成为当时以色列政府颇为重视的一个问题。本-古里安曾有过这样的名言:“灾难就是力量。”[6]xli 意思是要充分将历史上的恐怖灾难转变为激励国民精神的力量,以保证新犹太国家今后能够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围困中取得生存。195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有关法令,要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1959年,又规定将大屠杀纪念日定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历史创伤就这样被铸造成了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神话,以适应新的社会与政治需要。即使有作家勇敢地打破禁区,如大屠杀幸存者卡-蔡特尼克将笔触伸进集中营,但是读者群非常局限[7]157。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后大屠杀时代,希伯来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大屠杀与种族灭绝话题一直讳莫如深。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涉猎大屠杀题材的作家屈指可数。
二 “艾赫曼审判”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对纳粹主要头目之一艾赫曼进行公开审判②,执行了以色列立法机构确立以来的唯一一例死刑。“艾赫曼审判”对以色列人认知犹太民族在二战时期的遭遇、确立民族记忆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犹太人实现了身份转变:从受害者变为审判者来惩罚犯有种族屠杀罪名的前纳粹战犯。尽管审判本身没有“克服在欧洲大屠杀问题上总体上产生的民族困惑感”[8]142,并导致了无休止的争论,但确实改变了以色列人对大屠杀业已成形的集体记忆形式。
就意识形态角度而言,“艾赫曼审判”对本-古里安及其政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本-古里安试图通过这一审判使整个世界感到有责任支持地球上唯一犹太国的建立;另一方面,希望以色列人能够了解大屠杀真相,尤其是要教育年轻一代[9]326。造成本-古里安此动机的部分原因在于,由于以色列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以色列国缺乏统治力和安全性,其未来无法得到保障。尤其是,由于建国之后国家的政治话语总在宣传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年轻人认为犹太人并非是遭屠戮的羔羊,而是像在“独立战争”中一样有能力捍卫自身。然而,在审判中,100多名证人中的大多数并不是隔都战士或游击队员,而仅仅是在日复一日的承受恐惧和屈辱中幸存下来的普通犹太人。作家卡-蔡特尼克身为证人之一,在被问及为何他的书不署真名而用卡-蔡特尼克时,虚弱地昏倒在地。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标志着集体记忆的重新发现。“艾赫曼审判”向以色列人揭示了集体屠杀的全部恐怖。作为其结果,以色列年轻一代意识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并没有像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那样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而是“像送去屠宰的羔羊”那样一步步被送进焚尸炉。
在强调民族统一与自豪感的同时,此次审判还激励幸存者们克服羞耻感,公开自己“在另一个世界”所经历的苦难过去。此次审判标志着50万以色列幸存者融入以色列社会,反映出以色列社会对幸存者们表达“你们的经历是我们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的方式③。描写大屠杀及其后果的叙事文学也表现出这一民族意识形态的转变,对待幸存者和流亡经历的态度亦开始更新。根据希伯来大学谢克德教授的说法,文学社团和个体作家一样被此次审判所吸引,并对种族灭绝的经历反响强烈。主人公不光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模式中反复重现的英勇战士和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受迫害者现在被认为应该给予同战士一样的合法地位和同情[10]88。
三 大屠杀幸存者作家
大屠杀幸存者作家指那些在二战期间遭到纳粹迫害、但是能够得以生还、在战后移居到以色列的作家。这批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有卡-蔡特尼克(Ka- Tzetnik,1917—2001)、阿哈龙·阿佩费尔德(Aharon Appelfeld,1934—)、尤里·奥莱夫(Uri Orlev, 1932—)、约娜特(Alexander Sened,1921—2004)和亚历山大·塞耐德(Yonat,1926—)、娜欧米·弗兰克尔(Naomi Frankel,1920—)、伊塔玛·尧茨-凯斯特(Itamar Yaoz- kest,1934—)等。其中,卡-蔡特尼克和阿佩费尔德从不同角度对犹太人的民族灾难及其余波做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反馈。
1.卡-蔡特尼克135633
卡-蔡特尼克135633原名叶海厄勒·迪努,1917年生于波兰,少年时便开始用意地绪语写诗,德国占领波兰期间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获救,后移居巴勒斯坦。几乎从获得营救后恢复体力的那一刻,他便开始用希伯来语写大屠杀经历。当他让一士兵把第一本书带到巴勒斯坦时,士兵低声说,“你忘记写作者名字了。”他哭了,“作者名?写这本书的是那些进了焚尸炉的人!叫卡-蔡特尼克吧”。卡-蔡特尼克乃德文“集中营”一词的缩写,“1135633”是集中营编号。他以自己家人遭遇为原型创作的“萨拉芒德拉”系列长篇小说,在犹太世界中有“犹太家族编年史”之称。
《木偶屋》[11] 是这个系列小说集的第一部。写女学生丹尼爱拉在战争爆发之际与家人失散,在隔都的劳动营做工,后被纳粹强行送进奥斯维辛的木偶屋。木偶屋是集中营里一个特殊的营房,绝育女子在那里被迫款待从前线归来的德国士兵。木偶屋的犹太女子虽不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作,也不会像集中营中的其他犹太人那样挨饿,但遭受着痛苦的精神折磨。丹尼爱拉试图恪守民族信仰中纯洁正直的美德和道德意识,尽管深知要想满足德国人的欲望,就得吃东西,可她拒绝进食。她凭借对过去美好岁月的追忆,在地狱般的非人境地中存活了一段时间。最后她犹豫着进行反抗,想逃出虎口,却不幸死在了哨兵射出的枪弹下。
系列小说集的第二部《暴行》[12] 的主人公莫尼是个年仅11岁的小男孩。他长着一双酷似母亲那温柔、亮洁的眼睛,并继承了母亲家族所特有的贵族仪表。这使得他成为同性恋者眼里一个非常迷人的童伎,痛苦的生存愿望让莫尼学会了忍受。莫尼的童伎生活与《木偶屋》中丹尼爱拉的一样,代表了卡-蔡特尼克小说中所体现的一种道德控诉。莫尼和丹尼爱拉一样遭受着肉体上的折磨与精神痛苦。在他所生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再也没有人性与尊严可言。但是莫尼自己的心灵深处却依旧保存着他所归属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某种善良的本性。比如莫尼对拉比的忠诚,便表现出他童年时代在家里接受宗教教育时所镌刻在心灵深处的传统价值观念。即使身遭纳粹军官厌倦、被他们称作“老婊子”时,他也在念念不忘孩提时代拥在母亲怀抱中的温暖感觉。拉比怜爱的目光令他想起昔日母亲的温柔呵护。
尽管学会了身为童伎所必须的游戏规则,可在所有的童伎中只有他自己不去伤害别人。纳粹们想要他的身体丰满浑圆起来以引起他们的性欲,可莫尼出于对自身角色的厌恶强迫自己遏制食欲,结果变得瘦骨嶙峋,屡遭遗弃。他想通过死亡来证明所谓生命的价值,因为拉比对他讲过:生命属于上帝,如果我们愿意走进德国人的烈火中——言外之意,顺从了德国人的意志,则成了刽子手的帮凶。
在小说的结尾,莫尼试图逃跑,象征着他为保持人性良善做最后的努力。但饥饿使他筋疲力尽,离开人世,即使纳粹官兵也不免为他力求生存的努力称道。卡-蔡特尼克通过莫尼的遭际生动地再现出集中营内对犹太儿童所做的性剥削,描写出那些束手待毙的人们的苦境,以及那些在集中营里控制着他人生死权力者的腐败与无道。同时,试图解说并维护民族的道德信仰与生存理念。
《冲突》[13] 是卡-蔡特尼克创作的一部意义复杂的长篇小说,它涵盖了《木偶屋》与《莫尼》所展现的主题。主人公是丹尼埃拉和莫尼的哥哥哈利。小说场景在以色列与奥斯维辛之间不断转换。小说开篇,以色列成长起来的女子加利利去看她的心理医生,治疗她因丈夫哈利影响患上的糖尿病。加利利在年轻时代,由于受父亲思想的熏陶,试图寻找一位具备正统派犹太教赎救理想的恋人。偶然之际,读到哈利创作的描述奥斯维辛可怕事件的小说,意识到哈利正是她所要寻找的男人。
哈利如传说里所讲的不死鸟——凤凰,从奥斯维辛死亡营中存活并再生,是三兄妹中的唯一幸存者,但他的意志与精神却遭到了摧毁,缺乏生存的愿望与爱的能力,缺乏弟弟妹妹身上用死亡所保存下来的正义与良善。从奥斯维辛得到解救后,哈利重新发现了在道德与人性方面所承受的压力。通过年轻的以色列妇女加利利,哈利学会了爱和重新进入人类社会的能力,但是当加利利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哈利与其他人在大屠杀经历中所产生的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后,逐渐意识到任何人都无法从奥斯维辛里得到救赎。也就是说,加利利在治疗哈利精神创伤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哈利所带有的仇恨与恐惧。
最后,他们通过爱来相互救治对方的心灵创伤。尽管作家本人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相信通过爱可以实现世界救赎,但他的确相信只有爱能使伴侣之间的道德救赎成为可能。
2.阿哈龙·阿佩费尔德
以色列最著名的大屠杀作家阿哈龙·阿佩费尔德也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与卡-蔡特尼克不同的是,阿佩费尔德一直回避直接描写集中营生活和大屠杀事件本身,而是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将大屠杀体验渗透在带有前大屠杀和后大屠杀背景的文本中,或暗示出欧洲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无处藏身的命运,或表现犹太人在战争结束后在欧洲或以色列寻求生存的历程。在他笔下,大屠杀主题并非体现在故事情节中,而是体现在故事叙述与观察视角中。
阿佩费尔德的童年记忆对小说文学世界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4]4。阿佩费尔德生于罗马尼亚切尔诺维茨一富足的犹太人之家。他也同普通孩子一样,拥有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但8岁那年,母亲被前来进犯的纳粹所杀,他和父亲被分别送进集中营。小阿佩费尔德同妇女孩子关在一起,终日面对着恐惧与死亡。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强烈的求生意识促使他铤而走险,溜出哨卡林立的集中营,爬过带刺铁丝网,在暗夜中徘徊。一个犯罪团伙将他搭救,他便跟随着这群人到处流浪。三年后,阿佩费尔德加入红军,四处辗转,足迹遍及大半个欧洲。14岁那年,阿佩费尔德来到巴勒斯坦。先是到基布兹劳动,学习希伯来语,继之服兵役,进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而后到国外深造,并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创作生涯,迄今已经发表了30余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随笔、文论等,其作品在整个犹太世界反响很大,曾获“以色列国家奖”。自20世纪70年代起,阿佩费尔德便在本-古里安大学任教,并经常到美国讲学。
初到以色列对阿佩费尔德来说极其艰辛。他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没有语言,倘若说世界是他眼中一个难民营的话,那么以色列则像一个位移了的儿童难民营。作为幸存者,他没有同自己多灾多难的同胞同生共死,因而具有一种强烈的负疚感,促使他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去生活。于是他把写作当成一种自我探索,试图在写作中寻找家园和自我:“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冒着酷热在陌生人当中正作些什么。”④ 60年代,阿佩费尔德相继出版了《烟》(1962)、《在富饶的谷地》(1963)、《大地严霜》(1965)等短篇小说集。在这些短篇作品中,他主要写出欧洲难民在战后漂泊不定的生存状态以及到以色列后的痛苦体验。继之又去写父辈,写已经在欧洲被欧洲文明同化了的犹太人,这些人否认自身,憎恨自身,原因在于他们具有犹太人身份,他们体内流着犹太人的血;而后又向纵深发展,写祖母一代人,他们一方面恪守古老的犹太文化传统,同时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接受他者文明的熏陶与同化。文学是深层次了解自身的一种尝试,阿佩费尔德的作品实际上是在不同层面暴露着自己,同时也展示出犹太人的思想感情、犹太精神与犹太特性,以及这种精神与特性在物换星移、岁月荏苒中的变异与发展。
1980年,阿佩费尔德的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长篇小说《灼热之光》[15] 面世,艺术化地再现出自己作为年幼的大屠杀幸存者到以色列后的遭际。小说以第一人称形式,讲述一群失去双亲的少年幸存者到以色列后的故事。小说一开始,写这些少年幸存者从意大利乘船去往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与过去割断联系,走向新生。但是,这些少年由于在战争期间经历了肉体与心灵磨难,丧失了乐观的人生态度与信仰。他们到以色列不是个人选择,而是迫不得已。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相反,少年幸存者没有同以色列土地及那里的百姓融为一体的愿望。他们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对他们来说,在农场劳动这一象征着与土地建立联系的行动本身成了某种负担。巴勒斯坦,这片先驱者们所梦幻的土地,被他们歪曲为“某种集中营”。“想象你是在集中营里……要是你以前在七个集中营里待过,你也能待在第八个。”[15]77 集中营情结成为他们融入以色列社会的障碍。他们酗酒,打架,互相伤害。
与此同时,阿佩费尔德表现出本土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社会对少年幸存者的鄙视、厌恶与排斥。当本土以色列人最初和少年幸存者相遇时,便暴露出二者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我们在这里是劳动者。我们从土地上生产面包。不劳动的人都要被赶走。”[15]96 随着情节的发展,这种冲突进一步激化。
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先驱和政治领袖提倡通过肢体的简单劳作,而不是通过研修祈祷等精神活动与土地建立肌肤相亲的联系。少年幸存者拒绝与土地建立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他们同以色列社会的距离。用幸存者后裔、施瓦茨教授的话说,《灼热之光》是阿佩费尔德唯一提到以色列社会与意识形态背景的小说[14]77,在这种社会与意识形态背景下,大屠杀幸存者的道德水准和社会地位比本土以色列人低劣,被称作“人类尘埃”[16]88。
阿佩费尔德的出生地虽然是罗马尼亚,但母亲讲德语,他的第一母语也是德语,首先接受的是德国文明的熏陶。德国文学,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对阿佩费尔德影响很大。他从50年代便开始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笔下的荒诞世界、卡夫卡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及其优美的希伯来文书法,在阿佩费尔德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阿佩费尔德在同好友、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思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指出,卡夫卡出自一个内在世界,欲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而阿佩费尔德则出自一个现实世界,那就是集中营与森林[17]。但他们同系犹太人,所以卡夫卡的创作让阿佩费尔德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亲近感。
70年代,阿佩费尔德创作了长篇小说《漂泊岁月》,在学术界得到很高的评价。该作描写的是战争前夕一奥地利犹太家庭的故事,叙述人巴鲁诺只有13岁,其父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崇拜卡夫卡,与茨威格过从甚密。但在一片反犹排犹声浪中,他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像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憎恨自己的犹太身份,致使其作品招致骂名。最后,他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朋友,没有尊严,离家出走。30年后,小主人公已经长大成人,从耶路撒冷重返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奥地利,一种无尽的失落感从心中油然而升,为父亲的罪孽乞求救赎。作品中的许多细节与卡夫卡笔下的《审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阿佩费尔德称自己倾注全部心血去了解古老的犹太民族历史和传统。他笃信宗教,守安息日,在逾越节、住棚节、五旬节、赎罪日等传统节日来临之际举行仪式,但不去教堂做礼拜,而是有选择地接受宗教戒律。他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想同上帝说话,同上帝见面,而是想了解上帝,探索上帝之于犹太人的特殊意义。在他看来,任何宗教均以两大情感为基础:首先是人按照上帝的样子创造出来,其次是人终将化作尘土,这两种情感使得每一位犹太人既骄傲又谦卑。在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三部长篇小说《改宗》(1993)、《莱什》(1994)、《直至晨光》(1995)中,表现出明显的要皈依上帝的宗教情绪。在多数情况下,阿佩费尔德所创造的人物对犹太人文主义传统采取呼应态度。同时,背离犹太文化传统的主人公多数会遭到毁灭与失落。然而,那些试图重新寻找犹太文化之根的人们则需解决复杂的身份问题。
《改宗》[18] 叙述的是欧洲犹太人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的故事。作品开篇,教堂里正在为市政府秘书卡尔举行皈依基督教的仪式,前来参加仪式的客人多是他的同窗旧友。其中许多人也在近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们有的征得了父母同意,有的则是出于个人意愿。在他们看来,恪守传统的犹太教意识令人厌倦。他们喜欢美妙的音乐,而拥挤不堪的犹太会堂却总是令人大汗淋漓。卡尔的母亲在病榻上曾鼓励儿子为事业的需要去改宗。卡尔本人幼年上学时期,经常遭受基督教徒孩子们的欺凌。他一方面感到恐惧,另一方面也在试图表现出犹太人不甘忍受、会用拳头回击的一面,但从内心深处则难以想象犹太人是忠于信仰的。他的朋友马丁也非常支持卡尔的选择,认为他做得对,值得庆贺。但他们的共同朋友维多利亚则主张:犹太人应该做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犹太人,他不应该改变;倘若改变,则会非常丑陋,会损害我们大家。
阿佩费尔德通过不同主人公的不同命运着力表现出犹太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也表现出主人公在两种文化间进行抉择的矛盾心理。马丁尽管在形式上接受了基督教神父为他主持的改宗仪式,承认自己是个教徒,但不肯承认自己是异族人(膏伊木),公开表示对“异族人”一词的憎恶。马丁死去后虽然为他举行了基督教的葬礼,但那里没有哭泣。他的朋友卡尔不禁思恋起犹太教葬礼,尽管它匆忙而混乱,但起码是人道的。而卡尔本人,改宗后的最初几个月也感觉非常轻松,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出路,只需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可是后来他才知道倘若不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在教堂里有多么压抑。在母亲的守丧期期间,致哀者似乎有着一个心声:我们是犹太人,没有什么可耻辱的。在守丧期结束前夕,他们甚至哭喊:犹太人活下去。作品最后,卡尔和他自己所爱的女性为逃避各种流言蜚语和伤害到达乡间,他们的住房被当地农民点燃。意味着这对相依为命的伴侣要被活活烧死,借此预示犹太人想通过改变信仰而改善生存境况的努力是徒劳的。故事发生在大屠杀历史事件的前夕,所以主人公的被害便融入了带有象征色彩的、新的历史内涵,同整个犹太民族遭受迫害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直至晨光》[19] 背景置于“一战”前夕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犹太人从身份上虽然属于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阶层,但同时又受这两个阶层的排挤。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姑娘布兰卡出身于已经被同化了的犹太家庭,她爱上一位基督徒,为能够和对方结婚,便皈依了基督教。但后来这位名叫阿道尔弗的基督徒表现出对犹太人,尤其是对自己妻子的无比痛恨。他对布兰卡横加毒打,强迫她抛弃父母,出去工作,挣钱供自己酗酒,对她所生的孩子也漠不关心,并且和乡下女仆私通。布兰卡对丈夫的粗暴与欺凌忍无可忍,用斧子将他劈死后逃走。
与此同时,姑娘心灵深处的传统犹太信仰开始复苏,她放火焚烧了几座基督教堂,到警察局自首,准备接受惩罚。小说中充满了施虐与受虐描写,物理框架模糊,但许多地名和人名均具有象征意蕴。阿道尔弗象征着阿道夫·希特勒,他对妻子的虐待则影射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阿佩费尔德试图证明,人无法摆脱自己的身份。犹太人被异域文明同化,丢失了固有的宗教信仰必然要招致惩罚,但不断加剧的迫害与元休止的暴力定会导致牺牲者皈依上帝。女主人公只有在犹太传统意识萌醒后,才会想证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与生存权利,为生存斗争。也只有在她不再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时,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得到精神上的拯救。
《莱什》[20] 描写的是一群朝觐者到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孤儿寡母。鼓动大家前去圣城耶路撒冷赎救的拉比很快便撒手人寰,朝觐者失去了精神领袖。虔诚的长者仍旧继续祈祷,但商人们则毫不放弃易货赚钱的机会,后来竟然身揣黄金返回。朝觐者中有个15岁的孤儿莱什,他从一位奄奄一息的长老手中接过纪念日志,成为时间、地点与死亡的新记录人。他在学者的指点下,攻读前人圣著,可商人却将他带进妓院,接受另一种人生体验。这些人经历千辛万苦,人数折损近半,终于达到目的地。但耶路撒冷的布道并未给他们留下什么铭心刻骨的印象,由于没钱买返程船票,他们便去偷窃。朝觐者是否真正能够找到赎救的方式?莱什的命运又将如何?此类问题纷纷摆在了读者面前。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阿佩费尔德已经跳出对大屠杀事件本身及个人经历与体验进行纯然叙述的写作模式,正像他自己所说:“我看到过过多的死亡与残酷,促使我去期望。”⑤ 他在作品中,通过象征讽喻等手法,探讨犹太人同上帝的关系,探索犹太人的命运与出路,在整个犹太世界影响深广。
总体上看,卡-蔡特尼克和阿佩费尔德从幸存者的独特视角对民族历史与民族灾难进行回顾与反思,触及犹太人历史、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中某些本质的问题。同时,又将目光移向战后犹太人,尤其是幸存者在以色列的生存与命运,探讨大屠杀幸存者如何负载着沉重的记忆负担、在新环境中寻求生存的途径。这样一来,他们的文学既在解说民族历史,铸造着民族记忆形式,又同现存社会语境与政治话语建构起某种象征性的联系。
收稿日期:2007-02-24
注释:
① 参见Lawrence Langer的有关论述:Admitting the Holocaust:Collected Essay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以及 The Holocaust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② 艾赫曼在二战期间是负责组织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中心人物之一,也是同犹太人领袖有直接联系的最高级别纳粹官员。二战结束时逃到阿根廷,从此更名换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靠做工为生。1960年,以色列特工人员将艾赫曼逮捕并悄悄押解到以色列。1961年2月以色列法院对艾赫曼进行公开审判,同年12月判处艾赫曼死刑,1962年6月1日(一说5月31日)艾赫曼被处以绞刑。
③ 感谢本-古里安大学历史系Hana Yablonka教授在2002年为我们讲授“艾赫曼审判与以色列人记忆”这门课时,将尚未出版的《艾赫曼审判》一书的书稿馈赠与我,此话即引自该书稿。
④⑤ 笔者于1997年8月对阿佩费尔德的访谈。
标签:奥斯维辛论文; 文学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纳粹集中营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以色列人论文; 女集中营论文; 犹太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