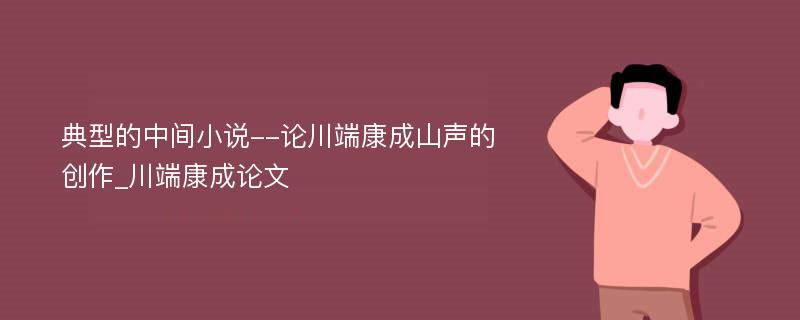
典型的中间小说——论川端康成《山之声》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川端康成论文,山之论文,典型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川端康成的战后代表作、其创作生涯中篇幅最长的小说《山之声》(《山の音》),自1949年9月起开始在《改造文艺》杂志上连载,到1954年4月由筑摩书房出版单行本,前后经历了四年半时间,虽然其间作者同时还在创作如《千羽鹤》之类的其他作品,但是,用较长的时间成熟地、精细地构思一部重要的作品历来是川端文学创作的特点。《山之声》还具有与川端文学其他创作明显不同的特点,可视为经历了战败的川端在战后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独特的变化。本文拟从《山之声》创作中所表现的社会性意义的角度,谈谈对该创作的再认识。
一
与川端的其他创作一样,长篇小说《山之声》的情节也很简单。已过花甲的主人公尾形信吾家住镰仓,与妻子保子、儿子修一、女媳菊子一起生活。常常失眠、健忘、多梦、喃喃自语的信吾已意识到老境的来临。在夏天的一个夜晚,他听到了类似地鸣一般的“山之声”。女儿房子婚后夫妻关系破裂,后带着信吾的两个外孙女返回娘家,参加过二战的修一虽然新婚不久,却以战争寡妇绢子为情妇,经常醺酒夜归,连周日也泡在绢子家。对信吾来说,最大的精神安慰是与儿媳菊子的相处和交流。不久,修一的情妇和妻子几乎同时怀孕,出于人格上的“洁癖”,妻子菊子果断堕胎,而情妇绢子却执意要生下孩子。这时女婿从醺酒到贩毒,最后走上情死的道路。为了菊子家庭的幸福,信吾主动提出分居,但菊子对分居后的修一更为恐惧,愿意和公公在一起并永远照料他的生活。
对于《山之声》,日本文学评论界已作过不少评论,或许因为川端文学属于纯文学的缘故,大多数评论的着眼点都集中在纯文学的角度。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死亡
如同《雪国》、《千羽鹤》等其他代表作一样,《山之声》第一段就写出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其中主要人物、必要的舞台设置和作品的主题俱全。小说是这样描写《山之声》的。住在镰仓的尾形家靠山很近,一个“月夜”,信吾听到了山的声音。当时,知了在不停地叫,被老妻保子的鼾声吵醒的他不相信知了会发出如此可怕的声音,随手把飞到蚊帐上的知了扔了出去,并抓住套窗朝庭院的樱树望去,“有月亮的夜晚令人感到深邃,其深度横向扩展,直至遥远处。”“于是,信吾忽然间听到了山之声。没有风,近乎满月的月亮皎洁明亮,潮湿的夜间空气使树木覆盖的小山轮廓变得模糊,却并未被风撼动。”“在镰仓所谓的低洼地深处,有时夜间可以听到海浪声,因此,信吾怀疑这是海的声音,然而,终究还是山之声。”(笔者为中译本的译者,按原文直译,应为“山之音”。汉语中音量声大于音,显然,准确的译文应为“山之声”。)“像是远处的风声,又可以称为地鸣,深沉有力,这声音似乎传到脑海中,莫不是耳鸣吧,信吾摇了摇头。声音停止了。声音消失后,信吾才感到恐惧,他身子发冷,心想,难道这是在预告自己的死期?”
因此,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这部作品“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步入老年、忘记性很大的62岁的主人公心态不稳的方面。”这种不稳定,就是担心死亡的来临。(见伊藤整:《川端康成(二)》)这一文学主题通过老人的思想活动、同龄老朋友的接二连三的死以及老年人患病做梦的情节来得到充分的表现。长谷川泉说:“死亡也是制造转机的一个方便而重要的方法。《山之声》很巧妙地活用了这一契机。直到《睡美人》结束,死亡被巧妙地应用着。这一手法,与川端文学的开门钥匙《临终的眼》有关。”“《山之声》有作为老人文学受到注目的方面,在老人文学中,是不能抹去涉足死亡的感慨的。”(《“千羽鹤”与“山之声”》)的确,这部作品中有许多与死亡相连的幻影:信吾时时萦绕脑中的、保子去世了的美貌的姐姐,杀死一起情死的年轻女人、自己则生死不明的女婿相原,十年未与信吾见面、受到老婆虐待的老朋友鸟山的死,带着年轻姑娘去温泉旅馆欢乐却猝死的老同学水田,还有战争中发疯的北本的死,日本划艇协会副会长夫妇离家出走的情死,患肝癌的索取氰化钾企图自杀的朋友的死,等等。因此,难怪有评论家要说:“川端的身世使他萌发了一种生即死、死即生般的生死相连的感情,面对‘死者的世界’,不知何时,他产生了‘生的感情’,死中的生,生中的死,总是深深地潜藏在他的作品之中。”(山本健吉:《川端康成》)“对川端来说,从小时候起,死就没跟他分开过。大多数作家把死亡当作故事的终结,而川端却有把死当作起点来写的特色。”(林武志:《川端康成研究》)
(二)关于梦与幻觉
《山之声》中为了说明老人虽然肉体衰老,记忆力减退,但想像力依然丰富的特点,为主人公构思了许多个梦,这些梦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他们分析梦的含意以及梦与梦之间的联系。作品中明确写到的信吾的梦共有9个:(1)与死去的姑娘接触的荒唐的梦。(2)关于日本三景名胜之一松岛的梦,梦中,信吾在松树荫下的绿草地上拥抱女人。(3)保子姐姐叫信吾的梦。(4)有关十四五岁圣洁少女堕胎的梦。(5)有关美国男人胡子的梦。(6)有关在菊子出嫁前与修一有交往的女子的梦。信吾认为,这女子是否就是菊子的化身。(7)年轻的陆军军官刀劈蚊群的梦。(8)蛇蛋与驼鸟蛋的梦。(9)白日梦,梦到以前故乡山上见到的雪崩幻影。这些梦在作品情节的开展、时间推移及主人公心理分析方面,都起着重要而又微妙的作用。“作为梦的分析,它们说明了信吾内心深处的真实。梦将幻想的可能性无限地扩大了,因此,信吾的思绪可以随心所欲地飞翔。”(长谷川泉:《“千羽鹤”与“山之声”》)“他的作品就是真实即假象、假象即真实的世界,就是正常即错乱、错乱即正常的世界,就是梦幻即现实、现实即梦幻的世界。川端所说的‘东方的精神’正是这种意思。”(山本健吉:《川端康成》)
(三)关于色情与不道德
笔者以为,《山之声》对信吾和菊子超越伦理的爱表达得十分委婉、含蓄,并没有什么出格之处,这方面,信吾应该说是冷静和理智的。但一些日本的评论者仍将此作为重要的视点来论述,他们认为,在《山之声》中,信吾的一生,可以说一直在憧憬保子美貌的姐姐,以至于信吾能从菊子的美貌上看出保子姐姐的倩影,这为信吾与菊子的关系作了自然的铺垫。作品中还有信吾在梦中把修一婚前交往的姑娘当作菊子化身的描写,说如能允许信吾随心所欲的话,信吾会爱上与修一结婚之前的菊子。还有人指出通过修一之口对绢子和英子说“菊子还是个孩子”,是修一向其他女性说明妻子的身体状况和对性的反应,并进而说明菊子作为一个女人的性的觉醒是出于修一另有情妇后精神上麻痹和残忍的结果。
关于信吾买“慈童能假面”的情节,也历来被当作表现其精神不道德的一个重要例证。信吾买下能面时觉得很美,差点儿与之接吻,后来,他又让儿媳菊子戴上能面。据此,有人认为这是通过慈童的假面来描写实际上不可能建立的公公与儿媳之间的恋情交流以及妻子等待有情妇的丈夫时的心情。立原正秋认为这是作者通过能面来掩盖信吾和菊子的精神不道德,他说:“读者不能认为这里表现的色情很美便简单地放过,这种场面只有在纤细地描写中把公公和儿媳之‘丑’表达得十分精确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川端文学的色情》)
上述对《山之声》的有代表性的评论观点可以说均基于对作品的分析,反映了日本学者的注意点和文艺观,有助于人们了解日本文坛对战后川端文学创作的看法。同时,似乎也应该看到,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仍是把《山之声》的创作放在对该作家其他所有创作相同的角度——纯文学的角度来审视和评论的。濑沼茂树在《川端康成作品小辞典》一文中的观点代表了川端文学给人的一般印象:“在缺乏社会性这一点上,新感觉派无疑和川端康成气味相投。”“因此,形成近代小说的要素,如对生活的追求、社会制度和习惯的矛盾、思想和性格的搏斗等,在川端的小说中都被抹去,剩下的只是对女性的肉体、自然和旧文化的咏叹。”(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然而,事实上,《山之声》所反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应该说,这部长篇代表作是川端战后创作乃至所有创作中反映问题最多的一部,它既保留了一贯的纯文学创作风格,又力图反映战后许多与社会问题相关的通俗内容,因此对后者进行分析研究和再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二
细读《山之声》便可知道,它不仅仅是表现受到死亡阴影笼罩的老年人的心态、情欲的作品,它所叙述的故事,还充分反映了战后日本近代封建家长制解体之后的家庭面貌以及这一变革给日本人带来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它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私小说创作的写实风格进行虚构创作,作品中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说是川端文学中最积极的一部似也并不为过。
乍看上去,信吾的四人家庭很普通,父子在同一公司工作,有稳定的收入,生活平稳。但作者把这个战后日本社会的普通家庭写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场所。家庭的户主是信吾,他自然成了矛盾的中心,因此,我们不妨通过信吾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来看作者是如何描绘这个战后家庭的。
作为父亲的信吾,有一对儿女,均已成婚。上过战场的儿子修一战败后回来,婚后不久,不仅经常约信吾的女秘书英子陪他跳舞,还马上与情妇绢子发生关系。绢子怀孕后,他又打又踢,逼得绢子说不是他的孩子后才心安理得。对于这样一个堕落的儿子,身为家长的信吾认为他是在“战争中变坏的”。他一再尽父亲的责任,一方面告诫儿子要凭良心对待妻子和私生子问题,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面去与绢子交涉。修一对自己的堕落认为十分正当,大言不惭地说:“我不是那种伤感的命运论者,当敌人的枪弹贴着耳朵尖叫的时候,一颗子弹也没打中我。在中国和南方或许有我的私生子,万一碰到私生子又互不认识地分手,比起耳边呼啸而去的子弹来,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没有生命的危险。”更有甚者,他认为战后日本女人,包括他妻子菊子在内都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含意,修一解释为:不受婚姻约束,男人一叫就来,平时“做出一副高贵的样子,其实没有正经的生活,处于不稳定之中。”而且女人“既不是士兵,又不是囚徒”。修一为自己的堕落寻找的理由从一个侧面代表了战场回归者的思想,应了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所说的:“战争的破坏也使人类本身无所作为,不是因为失败而堕落,而是因为是人所以才堕落。”战后价值观念的剧变和社会的巨变导致了大量的修一产生,对这样的儿子,对儿子这样的宏论,父亲信吾不仅“说不出话来”,而且还“吓得畏缩”。
儿子如此,女儿又怎样呢?在房子小的时候,信吾一直期望她会是像保子姐姐那样的美女,但事与愿违,房子不仅难看,且性格乖僻、脾气大、说话冲、妒忌心和逆反心特强、举止粗俗,还缺少必要的教养。房子嫁给相原后,夫妻俩产生矛盾,最后只身拖着两个女儿、一只包袱返回娘家。女儿的生活是不幸的,她的痛苦,使她发展到歇斯底里的地步。作为父亲的信吾,除了女儿抱怨外孙女没穿过好衣服时,悄悄外出寻觅,为了房子夫妻和睦,平时暗地派公司可靠的人送些钱接济女儿有病的婆婆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他对女儿一直缺少自信,对她的婚姻失败,一筹莫展,只能苦恼地哀叹:“哪儿都不乐观”。
作品中有不少篇幅写了作为公公的信吾与儿媳菊子的关系。菊子知道丈夫在外有情人,她不仅悲哀,而且孤独。房子带两个女儿回娘家住,女用人离家后未请到新的,大部分家务都落在菊子身上。她每天早起做饭,还帮着照看孩子,之所以能忍辱负重地坚持下去,是因为有理解、关怀、爱护她的公公信吾,这种关心和爱护是互相的,最后可以说到了互相依存的地步。对此一清二楚的保子说信吾“只疼修一”,“修一在外另有女人,你什么也不能说,过份照拂菊子……那孩子会觉得对不起爸爸,连忌妒心都不起。”信吾眼里的菊子不仅美丽,而且善良、有教养。大雨天里,当菊子独自边听世界摇篮曲唱片边哼唱时,“信吾的偏爱心就被她唤起”,“对信吾而言,菊子是这沉闷家庭的窗户”,“看到年轻的儿媳他才会松一口气”。平时的闲聊,一起在新宿的散步,使信吾心情舒畅,菊子送的电动剃须刀使他爱不释手,甚至接到菊子的电话会“连眼睑都感到温暖,窗外的东西一下子清晰起来”。每次修一不归时,信吾又感到对不起菊子,“心情阴郁”,“他会避免去观察菊子的表情”。平时很少责备修一的信吾,在菊子人流之后再也压制不了愤怒,痛斥修一“扼杀了她的灵魂”。为了菊子的幸福,当信吾再次提出分居时,“菊子一本正经地说:‘万一分手后,我是否能尽情地照顾爸爸?’‘那是菊子的不幸呀!’‘不,高兴的事情是不可能不幸的。’这好像是菊子第一次表现出的激情,信吾一惊,感到了危险。”可以说,在《山之声》中,最能体现家庭成员间温情的信吾和菊子的关系也是一种危机,菊子的存在,对信吾既是一种安慰,又是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在川端笔下表达得相当委婉,但又确确实实地存在。
作为一家之长的信吾,正如朋友所说,他是“地位安稳,在万人的灾祸之中,过得潇洒”。但表面如此的信吾年过花甲之后也产生了许多苦恼,如:一到“还历年”(指12属相中60岁的那个本命年)就吐血;因为记性不好、多梦和幻觉,极其渴望得到休息,盼望脑袋与身体分离,把不好使的脑袋送进医院去清洗;死去的朋友和邻居时时在召唤他;潜藏心底的对保子姐姐的爱无法泯灭,“回忆像闪电般的光亮出现,亦并非病态”;对于人生伴侣保子,他怀着终生的不满,觉得女儿就像她;最苦恼和遗憾的莫过于儿女的不太平,他无可奈何地期盼有倾诉苦恼的对象,并一再思索:“对于儿女的婚姻生活,父母究竟该负多大的责任。”
笔者认为,川端描绘的这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家庭,其实是较深刻地反映了战后日本家长家族制度彻底解体过程中的家庭面貌。早在明治时代,日本父传子承、家长说了算的家长制度既已受到冲击并开始衰败和崩溃,近代作品如岛崎藤村的《家》等对此都有描述,但这种崩溃和瓦解是需要过程和时间的。二战之后,由家长决定儿女婚姻、长子继承家业和财产、纳妾以及为继承“家”而重视传宗接代的家长制度,可以说已完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而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在民主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规范下家庭成员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得到尊重,生殖行为以夫妇的爱情和信赖为基础,家庭成为孩子社会化的基本场所,兄弟姊妹平等地分配财产的近代家庭。《山之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作品,信吾对修一的放荡、女儿的任性之所以束手无策,其根本原因在于用传统的家长制度的权威和伦理已无法说服处在战后时代的儿女们。我们在信吾身上还能看到家长制的影子。比如他偏爱修一,希望早日得到孙子,对此女儿房子极不买帐,直接说哥哥不像话。当房子婚姻破裂时,竟对着老父质问:“给我这种男人的究竟是谁?”就连信吾疼爱的儿媳菊子,明明知道公婆想孙子,却因为修一在外有情妇,心情不好,也自己作主去打掉了胎儿。这些,是不是能说明战后的青年一代在向传统的家长制度进行最严峻的挑战呢?房子曾抱怨父亲说,外孙女打出世就没穿过和服,只用过尿布,离了婚又要老父亲出资为她开一家化妆品店或文具店。在儿女们的眼中,信吾昔日的家长权威已荡然无存,与战后其他许多日本家庭一样,大概父亲已降格为儿女们的经济援助者了。在《山之声》中,信吾和儿子所有重要的交谈都不在家里,只能在上下班的电车里进行,这一情节也具有相当典型的象征意义,他们已完全不是那种昔日的父子关系,所谈的问题再重要,老子无法一锤定音,只能讨论和协商,允许反驳,相当平等。作者这样安排决非随意,其用意一目了然。
三
川端康成作为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文学“明确地体现了日本美的传统,它代表日本文学走向世界是合适的。有趣的是,川端文学并不代表明治以后日本文学的主流,它的文风、基本点和作者的生活态度都不同于日本近代文学,可以称作是一个异端。”(奥野健男:学研日本文学全集第16卷《评传的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位写微小东西的巨匠”。(三岛由纪夫:《作家论》)他的作品缺乏社会性也是一致公认的。小林秀雄在《川端康成》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如何,我们与社会制度及社会习惯如何发生矛盾又如何屈从,思想和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之间会产生什么烦恼等等,大凡小说家好奇的这类问题,川端都是不关心,其程度只要稍稍仔细地阅读他的作品便可马上明白。”
这些对川端文学的评价是准确的,也是中肯的。但是,《山之声》在这方面是一个例外。作品中对于战后日本的众生相的描写不仅篇幅不少,而且颇有系统。作者从各个方面试图把自己对社会的“日常生活”、“社会习惯矛盾”和风俗、因价值观念变化而产生的烦恼努力表现出来。归纳起来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映战争的损害及阴影
作为二次大战的加害者,日本在给东亚、东南亚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的同时,也给自己的国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山之声》中写道:战后日本年龄较大的人吃尽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失去了儿子和地位,“提起信吾学校的同学,现在都已年愈花甲,从战争中期到战败以后,有不少人尝到了命运的失落,50来岁还在上层的人,一旦跌落就很惨,再不就是一旦跌倒就难以站起。这是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年龄。”信吾的老同学北本在战争中痛失三子,因为公司调整产业,生产面向战争的产品,他就成了无用的技术员,闲在家中,每天对着镜子拔自己的白发,最后全部拔光,被送进精神病院,最终死于空袭最惨烈的时候。这个家庭完全成了战争的牺牲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山之声》是这样描写战争寡妇的生活的。修一的情妇绢子和与其同住的池上都是战争寡妇,绢子没有生育,池上则有孩子。她们的丈夫赴战场后命丧黄泉,年轻守寡,“也是在忍耐”,“战死的人留下许许多多的孩子,一直使母亲们感到痛苦。……男人们早已遗忘的孩子由女人在抚育!”战争使女人们所吃的苦头非同一般,池上说:“无论是否有孩子,要说不幸的话,绢子是不幸的。”绢子出于感情上的饥渴,明明知道做修一情妇是一种堕落,却甘愿受修一的玩弄、欺侮,并把这种时候想象成是在为战地服役的丈夫服务。她在受到指责的时候大声抗争:“要我归还别人的丈夫,就先要归还我的丈夫!”——绢子抬起头,从刚才起她就一直在流泪,现在,新的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潸然而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只停留在写众多战争寡妇这一当时的社会现状的表面,而是把笔触深入到这些妇女的无限痛苦的内心世界中去,是有一定深度的。
战场回归者修一身上也能看到战争的阴影。修一复员后不断地堕落,经常跳舞、醺酒、玩女人,喝醉后逼人唱歌取乐。表面上“修一在恋爱、情欲方面没有苦恼”,但实际上,他不仅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朝鲜战争即将来临的背景下,他说:“今天,也许一场新的战争正向我们逼来,就是这之前与我们有关的那场战争,也像幽灵那样追赶着我们。”修一也有自己的苦恼,因此,他变得自私、残忍、病态。川端笔下的修一的形象也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他从战场上没受任何皮肉伤回归故里,应该说是幸运的,但经历了大战烟焰的修一,恰如池上所说:“修一也是负伤而归的人,他是一个心灵的伤兵。”真可谓一针见血。
(二)反映战后思想观念的改变
关于女性的自立。二战结束后,由于民主主义观念的确立,日本女性有了选举权,从某种角度看,历来从属于男子、家庭的日本女性的真正的自立是从战后开始的。《山之声》中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战争寡妇池上和绢子从丈夫阵亡之后,可以选择留在婆家或择偶,但小说从女性自立的角度反映了她们对今后生活的决心。“我们俩都离开了婆家,也不回娘家,就算是自由之身吧。我们说好要自由地思考,虽然都有丈夫的照片,却把照片放在箱子里。”池上当家庭教师,一人教几个年级;绢子发愤学习时装,自己开店当时装设计制作师,她们都希望有自由地思考和决定今后生活的更多的余地,只要合适,就再婚,却并不首先考虑可依赖的男人。无论是信吾恳求还是修一用暴力逼迫绢子打掉怀孕的孩子,绢子均不妥协,而是设法抗争,表现了战后女性的自主精神。
战后的日本法律把亲子单位改成夫妇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宣告了传统的家长制家庭的彻底崩溃,这一点前文已论及,不再赘述。这一观念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变革是极其深刻的,《山之声》中,信吾在种种矛盾中不止一次地想到要让菊子、房子分居,本身也说明,信吾的家庭正处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对此,我们不能忽视。
此外,作品通过对雨宫家生意失败后卖房、后来发财后盖新房的叙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盛衰荣枯对商人和市民的影响。从信吾的体验来说,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振兴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机会,“商人会卖掉房子重新开始,又迅速地盖起新房,可我们却是十年如一日啊。”这一现象对数千年重复同样的工作而产生厌腻、疲倦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观念上的冲击。
关于性观念的改变。《山之声》借报纸的报道,叙述了初、高中女生大量怀孕和人流的社会问题。在“少女产双胎、青森出怪象”的报道中,说到了除了13到15岁的低龄少女人工流产的现象之外,初、高中学生年龄层中16至18岁人流者仅青森一县就有400名,占了人流的20%。“这报道使信吾受到震撼,所以在睡眠时梦见少女堕胎。”同时,作者在《山之声》中,还借着修一读的书,对战后日本青年的贞操观作了描述。“在这里,贞操观念业已消失,男人无法忍受只爱一位女性的痛苦;女人也无法忍受只爱一位男性的苦恼。双方为了能够快乐地、更长久地爱对方,互相在寻找仲爱者以外的男女,这就是巩固各自中心的办法……”连62岁的信吾居然也觉得,这“既非警句又非僻论,倒像是出色的洞察”。
(三)反映战后混乱的世态
战后的日本从废墟上重建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对于当时的世态,《山之声》中也有不少生动的描述。
娼妓泛滥。作品写道,镰仓这样风景优美的文化人聚集地,“娼妓也多起来了”;在东京新宿的御苑,白人士兵大白天也堂而皇之地调戏娼妓。对于信吾在电车里看到的男娼,作者写道:“青年把外国人放在膝上的手掌向上翻过来,再把自己的手合在上面,柔情地握住,活像一个十分满足的女人。……(外国人)长相可怕,但血色挺好,使那青年人的土色的脸上的疲倦相比之下更加显眼。……那青年身穿暗胭脂色的衬衫,从没扣纽扣的领口望去,可发现他的肋骨。信吾觉得这青年不久就会死去。”
吸毒贩毒。房子的丈夫在作品中没有正面描述,但是,通过房子,读者可以知道相原从喝劣酒开始,接着吸毒,还雇了跑腿的人贩毒,他弃妻女和病母而不顾,最终家中财产包括房子的嫁妆及房屋都属于他人,只约了一个年轻的女招待去情死。作者写道:“没能阻止相原堕落的究竟是房子、信吾呢,还是相原自身?或者谁都不是。信吾把目光投向太阳迟迟不肯落山的庭院。”这原因若谁都不能归咎,那么大概只能归咎于社会吧。
失落的老一代。受病魔折磨的老人想通过自杀来解脱,还有像鸟山那样受更年期老婆的虐待,吃不饱饭,在外消磨时间,要等家人熟睡后才回家,用信吾的话说,这样的情况是“大有人在”。此外,作品中还有菊子的朋友因前途渺茫,堕胎后想自杀的例子。
房子的女儿里子吵着要买衣服,差点儿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的插曲,反映了被丈夫遗弃的妇女生活的窘迫和凄苦。经常的停电,唱片放到一半突然中止;吃一顿饭,蜡烛会熄灭三四次……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面貌。
以上列举的部分内容,使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山之声》所描述的战后日本各种社会问题都是现实的,不可回避的。笔者认为,这至少说明了作者对社会制度、习惯、观念变化而引起的矛盾持关注的态度。
四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觉得似乎可以对《山之声》的创作做这样的再认识。
《山之声》中的确有川端文学中一贯的主题——死亡与梦幻,而且整个作品的16个章节中,随着季节的转换,春夏秋冬,各种自然景观、动植物的描写对烘托主题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其艺术表现手法也与其他创作有一脉相承之处。本文第一段归纳的日本众多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可以认为更多地是从纯文学角度着眼的。我国也有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山之声》及川端战后创作的作品在虚无和颓废的消极方面较战前的创作更加明显。
奥野健男说过,“川端文学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私生活”,“川端没有写自己身边琐事的作品,也几乎没有把自己的恋爱、失恋、愚蠢、挫折、贫穷、疾病、家庭生活及社会、政治行为以直接告白的形式创作的作品。”(学研日本文学全集第16卷《评传的解说》)也就是说,川端是不写私小说一类作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写家庭题材的作品。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山之声》就是一部反映战后初期日本家庭生活的家庭小说。如果说明治时代的家庭小说名作——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反映了封建家庭对女性的伤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家长制意识的社会作用;菊池幽芳的《我之罪》反映了女性的纯真、诚实爱情的胜利,具有提倡一夫一妻的健全的现代家庭道德的社会作用的话,那么,《山之声》则较好地表现了战后日本家长制家庭彻底解体,价值观、民主意识完全改变背景下的家庭矛盾及生活面貌。信吾最后的愿望“经过五万年再被挖掘出来的时候,自己的痛苦、社会的难处就全都解决了,世界也许早已成为乐园”——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所有日本人的一种愿望。从这一点看,笔者认为这部小说很具社会性,可以说它是川端创作中最具社会性的一部。
此外,家庭小说往往以它的现代通俗性为特征,《山之声》所反映的信吾一家的生活及当时社会的众生相明显具有这个特点。如伊藤整在《川端康成(二)》一文中所指出的:《山之声》“更具写生性,而且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形象,用连接的小速写描绘出来。……大概作者想在《山之声》里把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的平时的印象和写生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都正确地表现出来吧。这种态度即所谓面向‘真正的’小说创作的态度。”笔者认为:这“真正的”小说也就是中间小说,而且是典型的中间小说,亦即战后纯文学作家在一定时期内所创作的通俗性文学作品。川端康成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对家庭小说、中间小说的创作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成果,《山之声》应该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