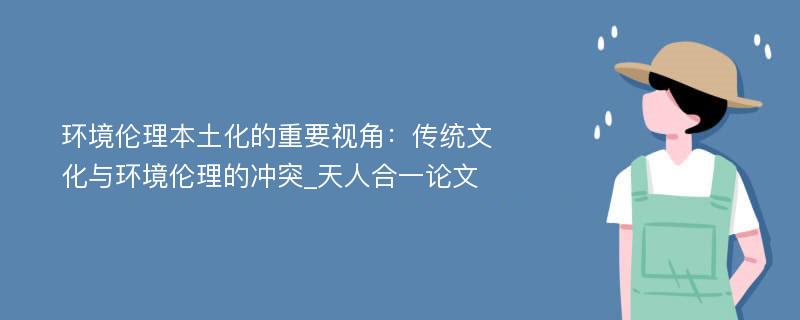
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重要视点:传统文化与环境伦理学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环境论文,本土化论文,视点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5X(2007)02-0024-06
实现环境伦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嫁接,毫无疑问是完成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重要环节。所谓环境伦理的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不能走简单地移植西方理论思潮的道路,而要在理论上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在实践上能够有效地解决和应对环境问题,成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应契合的关系,实质上,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的冲突或矛盾,有待于我们不断地去转化、和解与消融,认真检视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于完成环境伦理的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一、混沌的整体性
环境伦理学主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从现代系统科学的角度加以阐发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原始思维的系统性,因此,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本质上的而不是以时间上的落差为标志的量上的差别。
如果从现代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和谐是保证人类生态系统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反之则必然会导致整个人类生态系统的崩溃、毁灭,所以系统科学倡导人对自然要爱护甚至敬畏,要展开“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但是现代系统科学在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一致的前提下并不否认两者之间的矛盾、差别和对立,因为任何系统的构成要素之间都是以差别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存在理由,也正是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差别,才能在系统整体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相互之间才有了协同弥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强调的是处在差异之中的整体,“没有差异的整体实际上是不存在,事实上没有整体是不存在差异的,系统的整体性正是在系统要素、部分的差异之中以系统整体方式表现出来的系统的一种同一性”[1] 211。因而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实现与发挥是在动态的过程中体现的,是通过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竞争和协同的相互对立、相互转化来促进系统整体的涨落有序,达到系统自身的优化演变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不是通过取消人与自然的差别,使人的自然属性成为其唯一的规定性而实现的。更确切地说,从人类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目的性、稳定性等要求出发来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要使人放弃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回到动物式的生存状态,而是要求人们不要像对待敌人或奴仆一样任意处置自然界,无视其自身的演化规律和内在的规定性。事实上,人类永远都不可能在不触及自然界、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前提下获得生存和延续,因为人的本质是在通过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生成或显现的,这决定了“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亦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所以,只要有人类存在,便有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会必然导向破坏自然这样的唯一的结果上来,而完全可以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介或桥梁。这一方面在于自然界自身具有一定的承载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力,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的实践活动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是不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构成威胁的;另一方面,人类的实践活动从价值或功能上来说既可以按照人的尺度来满足人的需要,同时又可以根据自然的尺度来实现其内在目的,如通过人力的作用来抗御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恢复自然界的正常秩序等等。
由是观之,现代系统科学和环境伦理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并不否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并不要求人们盲目地服从自然力,不去进行改造自然的斗争,恰恰相反,它要求承认人与自然的差别,并且主张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在价值指向上现代的系统科学和环境伦理学并不是以回到原始为价值归宿的,也不是以主张消弭人与自然物的差别为自己的特色,更不是要人们完全放弃追求物质财富,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是在人与自然和谐这一价值导向中包含了对人类追求一种更加健康、文明、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期望,以此来消除由于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所带来的生产异化和生活异化,使人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展现自身价值的空间。而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类完全可以在现实中与自然界形成一种和谐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图景用海德格尔的话来描述就是人类要成为大地的看护者,而自然万物也正是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又获得了它们各自的充分展示,这正是人类与大地关系的诗意所在。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天、地所构成的系统则往往是一个被消解了对立、差别、矛盾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朦胧、混沌而非精确化的,它内含着人对自然的敬畏与依顺。所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论带有非常明显的原始思维的系统性特点。它作为一种传统的整体论,“尽管这种整体思维有其独特的优点,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缺乏分析的缺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的缺陷。缺乏分析的整体,是具有片面性的整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系统的整体”,“这样的整体往往成为一种没有具体内容的整体,从而也就只是没有内容的整体性,或者也可以说是暧昧不清的整体性”[1] 210。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被看成是一种既定的原初秩序,而不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所达到的一种生存境界,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不是通过变革自然的实践,而是依赖于人的“顺天”、“无为”的修为,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观点的强调,是对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关系的体悟”,“有着历史回视性与因袭传统的倾向”[3]。从这一点上讲,传统的“天人合一”学说绝不可能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灵丹妙药,主要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矛盾的现实解决,本身是一个实践性问题,需要在观念转变的前提下诉诸一定的技术手段和实践活动才能得到落实,但是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是一种难以在操作层面上践行的“不结果实的思维的花朵”,是与人的自由自主的对象性活动要求相脱离的思想观念,它并非早熟,而是稚气未脱。因此,不能把它原本照搬在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之中。
二、宗法伦理的阴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虽然包含着与自然相和谐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是命题的主流,实际上这一命题所着力阐发和论证的是封建宗法伦理规范的神圣性、至上性以及人的内在超越性。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把宇宙划分为天、地、人三大要素,但“‘天一地一人’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关系系统”[4]。也就是说,人在宇宙之中是一种有卓越地位的存在物。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上篇》)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董仲舒也认为,人在宇宙中确实有很崇高很重要的地位,“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故其治乱之故,动静顺逆气,乃损益阴阳之化,而摇荡四海之内”(《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宋儒也多认为人是天地之中最卓越的存在,周敦颐认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为物所不能及”(《太极图说》)。朱熹认为,人由于存在伦理上的规定性,故必然超出万物之上:“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也;有生气已绝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故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情,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槁又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答余方叔》)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者之间并非是处于同一层次或序列中的。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探究,但是在天、地、人所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环境伦理学的思想要素,具体表现在:
其一,在天人之间,天道之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规律的探询、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评价的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秩序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于“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的工具或手段。这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定君主的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5] 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形生神知而五行动,五行动而万物出,万物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莫不于五行有见之……故由汉以来,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者之戒深矣。自宋儒《太极图说》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于理而究于诚”(《宋史·五行志》)。但是,借助于自然之序而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理”或“心”,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朱子语类》卷一)“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就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方面;而将道德原则看做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6]
其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
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是“小道”、“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看成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辟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致思理路,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为一种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礼记·王制》中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汉书·艺文志》将方技三十六家(医术、匠艺)列于卷尾;刘歆总天下群籍而奏《七略》,其中“方技”列于七略之末。《新唐书·方技列传》载有:“凡推步(指天文、数学)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这种鄙薄探询自然、工于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这使得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这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与自然的裂缝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思想倾向妨碍了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上升到科学的认知水平。而人与自然的和谐绝不是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压制和忽视所能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值得检视的。
其三,中国是在“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7] 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这就使得宗法血缘关系成为文化演进的重要机制,并且也进一步加剧了“天”、“人”之间的矛盾。
因为在宗法社会中,非常重视家族或宗族的聚合力,也就是说要在人口数量上取得优势,所谓“聚族数百指”。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在宗法伦理观念中,人口的生产是被极力肯定和褒扬的。孔子认为,“孝”是为人之本,而“孝”之本又在于使家族血脉世代相传,以使祖祀不绝,正所谓“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孔子家语·本命解》)。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明确地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命题,强调繁衍子孙的道德意义,认为只要能尽此孝道,在其他方面即便有所违逆,也是可以谅解的,此即所谓“舜之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离娄上》)。对于家族而言,人丁兴旺是至关重要的,而从家国同构的角度看,治理国家也应当以人口繁盛为要旨。对此,孔子指出,“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礼记·大学》),“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亲记下》)。孟子认为统治者要行“仁政”就必须抓住“土地、人民、政事”这“三宝”,要“广大民众”,“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而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历代统治者从“富国强兵”的需要出发,基本上都以鼓励生育、增殖人口为治国之策。中国宗法伦理的这种价值取向确实在客观上制造了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巨大压力,并且为以后人口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激化埋下了伏笔。中国人口在乾嘉之后急剧增长,特别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当时对一切控制人口的下策只能感到厌恶。一个被征服而且贫弱的民族唯一的抵抗方法是指望人口增殖。统治者限制人口增殖的任何努力,一定会激起强硬的、本能的反抗”[8]。
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处于“黄金时期”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基于先秦时期人口状况、生产力水平、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及采取的措施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当时的生态系统基本保持了原始状态”。但此后,自然环境就不断恶化,秦至西汉是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次环境恶化时期;而在唐朝至元朝的700多年时间,又逐渐演化成了自然环境的第二次恶化时期;从明、清直至解放以前是自然环境严重恶化时期。虽然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直接的层面上看,“历史上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时期都是人口较多或增长较快的时期,人口增长通过剧烈的农垦活动而冲击环境。归根结底,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是过多的人口带来的”;“就整体来讲,人们对自然生态规律没有认识,对自然资源只知索取,不知保护,更不知投入,也是生态环境恶化和人口——环境矛盾紧张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9]。
其四,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即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之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一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如从饮食方面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居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也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的相符相合的基点上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更有以奢嗜恶癖为消费时尚。当然饮食奢靡总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追求,史书中此类记载甚多,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竞事奢靡,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看得并不清楚。因为当时麋鹿等野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有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10]。
天地万物对生命的护持不仅在于使生者长寿不夭,而且还要使死者的魂灵不朽,这样天地万物也在丧葬礼俗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表演的道具。古代隆丧厚葬之习俗由来已久,且有不断蔓延之趋势,这与“生死转换”、“生死统一”的观念不无关系。中国古代的隆丧厚葬的风俗是受到宗法伦理观念的支持的,因而形成了一整套的丧葬礼仪规定。正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隆丧厚葬被认为是体现了宗法道德的要求,因而世人广为牵累,“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潜夫论》)隆丧厚葬尽管多是官宦之家之所为,但是它作为一种带有导向性的文化现象迫使许多人追随,以至于贫患之家也不得不竭力而出,这既造成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也对自然环境施加了压力。
三、回归自然的无奈与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不乏对人回归大自然的意境的向往或吟咏,但是这并不总是人在常态心理下所获得的对人生的感悟,而常常表现出的是心理被扭曲后的无奈,因而它与生态伦理学所倡导的生活方式还是存在着距离的。在中国历史上,像老子和庄子都反复申言,人道应该遵从天道,顺应自然,践履无为。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因而“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庄子也反对人为破坏自然,“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宰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只有出于自然之本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此即谓“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养生主》)这是说,生活在草泽中的野鸡,虽然走十步才啄到一口食,走百步方能饮到一口水,但仍然不愿意被养在笼中。因为虽然在笼中可以神态旺盛,却失掉了真正的自由。因而在老庄的思想中,人要真正回归自然来获得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即要逃离社会,背弃纲常礼仪之要求。后世的许多狂放之徒大都免不了经历人世不能,方才以出世的方式来安顿生命的心理痛苦。被称为“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傲然独往,任性不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月忘归”(《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在思想上,阮籍推崇老庄,贬低儒学,认为至德之世当为清静寂寞、是非不分之世,一切都顺乎自然之则,“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大人先生传》)。但是阮籍的这种心态与其生不得志,抱负不能实现,才能得不到展露的人生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他的狂放中时常流露出悲苦与无奈:“谁言万事艰,逍遥可终生。临堂翳华树,悠悠念无形。彷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寄言东飞鸟,可用慰我情。”(《阮籍集·咏怀诗》)而《晋书·阮籍传》中又记载:“(籍)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升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另外,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文人骚客往往表现出了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由于钟情于山水之乐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风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意境,常让人感到人生天地之间的和谐与美,但是在山水意境背后却又常是对生命漂泊无依的感叹,笼罩着对“入世”无门或失意的愁绪,弥散着背离伦理要求才换得的放纵与狂达。总之,在人们回归自然的情绪中常包含着“因为对社会失望后,便以自然为人生幸福的补偿形式了”[11]。所以,它或许并不代表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环境伦理思维的关系,一方面要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了许多能为环境伦理学所接纳、消化的思想养分,这也是实现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重要文化基础,对此决不能完全抹杀,使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有许多缺失之处,还与环境伦理学的价值导向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或冲突,因此理智地反省传统文化,消除由于文化惯性所熔铸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更是环境伦理学在本土化之路上所承担的一项艰巨的理论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