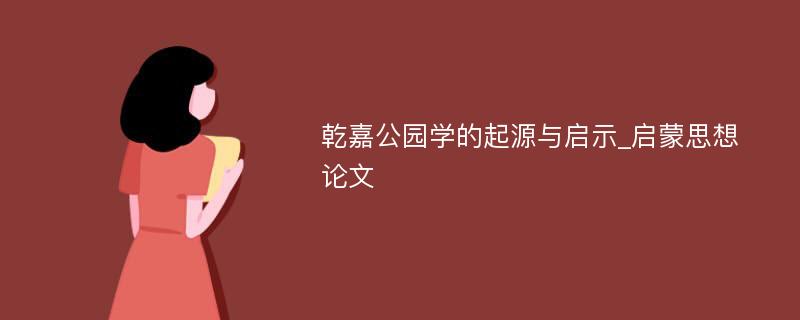
乾嘉朴学的缘起及启蒙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朴学论文,缘起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4-0036-04
明清之际,“经世致用”、“崇尚实用”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主流信仰和理念。围绕着这一信仰和理念,形成了被后世学术界称之为“明清实学”的社会文化思潮。这一社会文化思潮至清代康熙后期即开始变化,至乾隆、嘉庆年间,一种以整理、考订古代典籍为主的考据学,即乾嘉朴学,迅速占领学坛,几乎独占学界势力。明清实学何以转而为乾嘉朴学?如何认识乾嘉朴学的思想启蒙意义?本文试图在这两个问题上提出一些较新的观点,以求正于学术界。
一
乾嘉朴学以“考据”为方法,以儒家经书(兼及史书和诸子)为研究对象,考证字音、字义、名物、制度、版本等等,由此发展出“小学”、金石、辑佚、校勘等辅助学科。朴学全盛时期,考据的对象已从儒家经书扩大到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算法、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但从研究方法上看,仍是以考订、校勘、汇集、整理古籍为主,未脱朴学本色。现代的研究者,从明清实学思潮的角度着眼,一般把朴学称之为“考据实学”[1](P1333),而为了使此种“实学”与以前的“经世致用”之学区分开,又称其为“书本上的实学”。从“经世致用”的明清实学转而为埋头古籍、专重考据的乾嘉朴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学术界已经反复论证过的一个原因,即康熙中期之后,随着清王朝政治上的彻底巩固,对以往尚无暇过多顾及的思想文化领域开始了严密的控制,这对实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其次,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化在古典时代即将全面结束的前夕,必然要对它所留下的恒河沙数般的文化典籍进行全面的整理,这就不允许学者,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学者在更多的领域中进行更多的耕耘。第三,康熙中期以后,汉族知识阶层对清王朝的那种心态上的微妙变化,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原因。自清兵入关,经过几十年的征战,以康熙二十年(1682)“三藩之乱”的平息为标志,清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异己力量已经彻底铲除。“三藩”被平定后,中国出现了持续百年的和平安定局面,满清统治者以塞外少数民族所特有的那种活力,为中原社会注入了少许生机,造就了国力富强、声名远被的“康乾盛世”。如果说,清初的第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主要还是满清入关时的那种血流成河和满目丘墟,因而不能不有一种强烈的反清情绪的话,那么,到了第二代知识分子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康熙四十二年(1702),康熙皇帝西巡陕西,指名召见“关中大儒”李颙。同往常对待类似召见或礼聘一样,李颙仍是以老病缠身为名,拒不出门。但这次,他却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思录》和《二曲集》给康熙。余秋雨先生在论及此事时说:“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2]
此事的确具有象征意义。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序言中就涉及过这一问题:
余治诸家书,犹多余憾。亭林最坚卓,顾其辞荐也,则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为清显宦,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梨州晚节多可讥。晚村独持夷夏之辨不变,然余读其遗训手迹,缕缕数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独曰:“子孙虽显贵,不得于家中演戏”,则无怪后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习斋力倡经世干济,恕谷乃为游幕。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而诸老治学之风乃不得不变……无怪乾嘉学术一趋训古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P2)
可见,从清初第二代知识分子开始,其与清王朝的关系已经由第一代的对峙、抗争变为合作。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高涨,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学术动因,就在于“为未来民族复兴奠定理论基础”[4]。随着这一动因的消失,知识界的文化话语就不能不随之变化,“乾嘉学术一趋训古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也就成为一种正常的文化递转了。
除外在的社会历史动因之外,乾嘉朴学的产生,也与明清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如前所述,现代研究者一般都把乾嘉朴学视为明清实学的低潮,为了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区别开来,而将其称之为“考据实学”或“书本上的实学”。然而这种“书本上的实学”或“考据实学”,又正是从“经世致用的实学”中衍生而出的。
在“经世致用”的明清实学思潮中,热血沸腾的“复社诸子”为了摆脱空虚无用的“时学”(宋明理学),曾提出了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兴复古学,务为实用”。不论他们实际上是否从“古学”中寻找到匡世良方,但知识界对“古学”的热情却从此被调动起来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大师,虽然都是“经世致用”的倡行者,他们的学术研究都含有“为未来民族的复兴奠定理论基础”的实际目标,但是“经世致用”仍须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寻求指导,学术研究更是要以书本的研读为对象。事实上,这也未尝不是一种“书本上的实学”。而且,既然要通过对“古学”的研究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那么对生活在千百年后的学者来说,首先弄懂原始经典的本义,似乎也就成了必不能少的一课。所以,不但是顾炎武提出了“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原则,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等也有同样的主张。以至于后来乾嘉学者在“谁是朴学的开创者”的问题上,或推本顾氏,或推本方氏,或推本黄氏,纷纭其说,莫衷一是。这恰好表明“朴学”的原则是清初诸大师们同倡共行的。这也为我们从“内在理路”上理解明清实学与乾嘉朴学的学术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
二
毋庸讳言,除了少数人如戴震、洪亮吉仍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之外,绝大多数朴学家终其一生,“猥以校订之役,穿插于故纸堆中”[5](卷三《晚步村落》),专注于对典籍文本的训诂考证、辑佚与辨伪,明清之际的那种直面世务关注民生的经世情怀和批判、反思的启蒙精神似乎已经失落。所以,一般在论及乾嘉朴学时,人们更多的是从“学术”、“学问”、“知识”的层面上立论的,对朴学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尤其是其中的“批判”和“启蒙”精神,则缺少系统的论述。
乾嘉朴学的批判和启蒙精神首先表现在以客观、平实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上。在朴学时期,任何儒家经典都只不过是一种可供考订、研究的“学问”和“资料”,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权威。经典不再具有“道统”、“圣言”的意义。著名的“六经皆史”的命题就是在乾嘉朴学时期得到最终的落实(这一命题的提出很早,但未造成广泛影响),并为知识界所广泛认同的。把六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作为“历史资料”看待,“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成为研究之问题矣;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即可成为研究之问题矣”[6](P6)。铅华褪尽,所谓“圣人之言”只不过是上古先民遗留的一堆“史料”而已。这之中所包含的启蒙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后世一般都很推崇“乾嘉朴学”对上古史研究和上古典籍解读的准确性。从“知音、到考文、到穷经,二、三百年来(指清代)人们对上古史资料所能理解的程度,比赫赫有名的东汉诸大儒,不晓得深入了多少倍!从清人解经水平上,回过头来再去看汉、晋经解,有些简直可笑,有些简直在胡乱说话”[7](P74)。这当然不是朴学家有着特别的解经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对“圣人经典”的看法变了,治学取向变了,“圣人经典”在他们眼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圣权威,他们也不想从中发现什么“经世致用”的法宝,而只是把它们作为“历史资料”加以研究和看待。正是脱去了儒经中的那一道道耀眼眩目的光环,朴学解经才有了这种后来居上的辉煌。从这之中,不难看出明清之际的人文启蒙精神是怎样悄细无声地浸润、流转在乾嘉朴学之中的。
乾嘉朴学的批判、启蒙精神更表现在其考订典籍所造成的客观影响上。“朴学”对古代典籍考订的对象首先就是儒家经典。对儒经的考据一是“复原”(又称“复古”),二是“辨伪”。儒经二千年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加以利用的思想武器。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儒经制造出一套套纲常伦理的说教。而朴学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订出儒经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含义,这就抖落了封建政治纲常附加在它身上的种种金粉尘垢,这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冲击和近代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首先抖落的是“宋明理学”这一层金粉尘垢。“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俾陆王不得冒程氏,释氏不得冒孔孟。”[8]就这样,朴学家以他们所标榜的“治经如剥笋”的方法,剥去了程朱陆王强加在“六经孔孟”之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一般说来,朴学大师们很少直接攻击程朱陆王,但程朱陆王的理论权威却不能不在朴学的剥落中发生动摇。
思想的解放,如同江河奔流,后浪前浪,互为推引,相引于无穷。抖落了宋明理学这一层金粉尘垢,唐人附加在儒经中的种种说教,魏晋两汉附加在儒经中的种种说教,直至儒经本身的价值也都不能不受到审视和怀疑。梁启超对此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
综观[清]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
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
放”。第一步,复宋元之古,对于王学而得
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
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
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6](P6)
在“复古”的旗帜下,一层又一层的金粉尘垢被抖落了,儒学经典的原始面目一步步地被恢复了。当所有的神圣光圈都熄灭了的时候,那么“圣人经典”又有什么资格要成为今人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萌芽,多少已经在朴学的“复古”、“复原”中孕育了。
对儒经的“辨伪”则比“复原”更进一步。朴学兴起和盛行的时期,几乎所有儒家经典的真实性都处于被怀疑、被审查中,最终的结果证明,有的儒经部分地属于后人伪造,有的则纯属后人伪造。这对思想文化界的震动又将是何等巨大!关于这一点,还是梁启超论说得透彻:“二千年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不背诵他。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9](P172)
其实,这不仅仅是梁启超的学术见解,更是其斗争经验的体味。因为,近代的康梁变法,正是受朴学的启发而首先在思想界荡起波澜的。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东羊城,督课众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日夜突击,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朴学家的考据手段,推出了洋洋40万字的《新学伪经考》。几年后,另一部“倾动士林”的《孔子改制考》也著成问世。这两部书当然不是标准的朴学考据著作,因为这其中有不少后来梁启超自己也承认的“康梁技巧”——“往往不昔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但其打出的却是一幅虔诚而又正宗的朴学面孔——通过历史考据的方法,断定《周礼》等等皆系刘歆等人伪造。几年以后,康有为正是依靠这“两部大著作”,“取得了维新运动的思想领导地位的”。而这“两部大著作”在维新运动中的真正作用仍然是:
奉行二千余年无一人敢违,无一人敢
疑的神圣不可犯的封建经典,忽然间在康有为手中被彻底宣告为一堆伪造的废纸……它暗中提供人们的不正是:如果这些为统治者奉之为专制制度的理论根据的神圣典籍实际上并不算什么根据,并且还恰恰相反,它们还只不过是某个刁滑的野心家伪造的恶劣赝品;那么,这一专制制度统治本身的存在,不也就完全失去足够的理由和根据了么?[10](P498)
这实在不能不起人联想:百年之前的“乾嘉朴学”和百年之后的“维新变法”,这时代交接点上(古典社会的结束和近代社会的开始)的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股思潮,它们之间流贯着怎样的一条文化血脉呢?
收稿日期:2002-0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