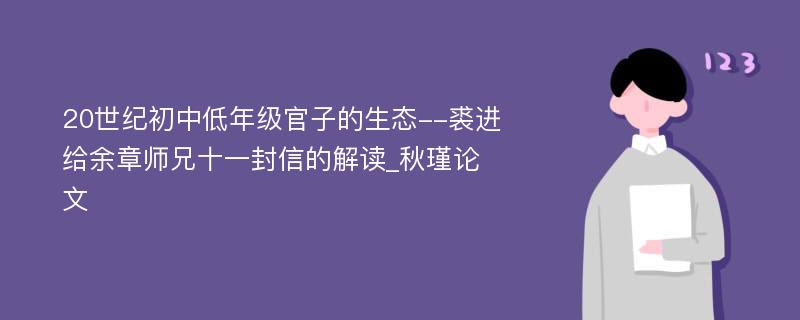
二十世纪初中下层官宦子弟的生态——秋瑾致兄誉章十一函之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宦论文,下层论文,子弟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6—0097—12
20世纪由义和团运动迄辛亥革命的头十来年,是晚清中国社会变化最急剧的时期。这个变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通常由王朝末期各种社会问题累积和激化所引发的传统性变化,二是由西风东渐和中外杂处所引发的比通常王朝末期的社会变化更高层次、更深刻的时代性变化。两方面变化相互掺杂和相互激荡所引发人们的不安和惊恐,及这种不安和惊恐所在社会层面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中国以前任何时代。多年来读晚清史资料,对20世纪头十年中国社会变化两方面内容带给中下层官宦子弟的冲击,以及引发其中多数人对人生前途的不安和惊恐,留下深刻印象。读秋瑾致兄誉章之十一函,再次有深切感受。
秋瑾留存下来的文字中,有致兄秋誉章十一函,写作时间从1905年春其从日本归国,到同年12月末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运动而退学的第二次归国期间。十一函的写作跨度时间为八个多月,全部字数虽仅有6500字左右,但其反映的内容却相当丰富。过去,对秋瑾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的了解,仅止步于其公开的活动,如入读下田歌子为校长的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速成科,加入同盟会为浙江主盟人,因参与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运动而退学归国,等等,研究内容多以革命为主旨。这样的研究中,秋瑾的形象一面倒的开朗、明快和光辉。秋瑾致兄函的内容却告诉我们,在作为女革命家活动的同时,她有许多属于个人的、秋家大家庭的困扰和烦恼,并为之焦虑和痛苦,甚至数度谈及“死”。据秋瑾致兄函内容可知,此间,秋瑾也曾致函在绍兴的母亲、嫂子及在湘潭的妹妹秋珵,并也曾寄丈夫王廷钧一函,但这些函似乎都未保存下来。因此,秋瑾致兄十一函,就成为解读此间其内心世界最有价值之资料。①此项解读,笔者以为将丰富已往已有的秋瑾形象,也将丰富对辛亥革命发生原因之了解。
秋瑾致兄函的主要内容大致有几方面:对誉章之职业和前途的关注;对丈夫和夫家的责骂、不满及对婚姻的痛悔;对绍兴秋家大家庭子侄之前途的担忧和安排,以及关于留学费用的筹措,等等。以下分别对这些内容进行解读。
一 对兄长誉章之职业和前途的关注
秋瑾兄妹有四人,秋誉章(1873—1909年)为秋家长子,秋瑾(1877—1907)为长女,②下有二妹秋珵(1879—1943)和弟弟秋宗章(1896—1955)。宗章为秋瑾兄妹之同父异母弟。誉章虽比秋瑾长四岁,但比秋瑾缺乏主见,秋家大事全由秋瑾做主,且性格亦比秋瑾懦弱。③誉章无科举功名,18岁时娶亲绍兴张氏,④夫妇虽育有二子三女,但未独立门户,其小家庭与母亲及宗章母子同住于祖父嘉禾所置绍兴山阴之“和畅堂”。
1905年春秋瑾归国时,誉章正在北京西城路工局工作,⑤此工作似是二妹秋珵丈夫王守廉(字尧阶)的叔父帮助所谋得。⑥王守廉叔父的情况不详,仅知王守廉是杭州人,其父亲王哲夫为湖南候补知县,并署过湖南安乡县知县。秋珵19岁嫁王守廉,正是王哲夫署安乡县知县之时。⑦
秋瑾为誉章之职业和前途担忧,在得知誉章赴北京谋职后,就向其介绍她原居北京时所熟交的陶大均和江亢虎等人,希望誉章与他们联系,以得到提携和帮助。她致誉章之第一函,即1905年归国后致函称:
陶君杏南只可如此写,吾哥见面时当道及妹在京蒙其夫妇青目,妹常常写信回家说彼夫妇好处及感诚,大约谋一差事,彼总可为力。江亢虎处无非使其指点而已,吹嘘恐不能,但彼能为力之处必尽力,因彼为维新中人,朋友中待人甚好也。⑧
“陶杏南”,名大均(1859—1910),出身绍兴会稽望族,1882年赴东京中国驻日使馆内东文学堂学习,毕业后留任使馆翻译,曾在驻日公使黎庶昌任期内“充任横滨领事馆馆员”。甲午战争发生后归国,“历佐李鸿章办理中日外交事务”。李出任两广总督后,陶被任总理衙门行走。后“以劳绩叙道员,光绪三十年,由道员借补商部会计司郎中,明年授奉天驿巡道”。秋瑾是在与丈夫同赴北京后认识陶大均的,当其与丈夫关系紧张时,陶大均和如夫人陶荻子还参与劝解和协调。⑨江亢虎(1883—1954),名绍铨,江西省弋阳人,仕宦家庭出身,1901年赴日本,归国后被袁世凯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后再去日本留学,1904年因病辍学回国,任职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秋瑾应该是在江1904年归国后与之相识的。由函内容看出,秋瑾在京居住期间,与陶氏夫妇关系良好,在首次赴日前,甚至将贵重首饰和衣服存放于陶家,托陶荻子代售。此事又说明秋瑾留日经费拮据,要由售卖服饰来筹款。
之后数函内,秋瑾都在关注誉章与陶、江之间的关系,及二人是否已向誉章提供帮助。如秋瑾致兄第四函,即同年7月二次东渡后致函谓:“江亢虎如有可为力处,虚与周旋可也;如无可注意者,慢慢与之绝交可也。陶大均允为谋事,近有消息否?”⑩第五函即9月12日函谓:
陶杏南处,妹叠上二函,俱未得复。此我浙人只知有自己,不知有他人,不照顾同乡之通病,即在东留学界亦推吾浙毫无团体爱情,何况富贵中人耶?即兹奉函亦置不答者,如我家稍有势力,彼必趋奉之不暇……故陶处之希望,吾哥可淡置之,另谋设法。
第七函即11月6日函谓:“陶杏南之人毫无学问,新学界中殊不齿其人。江亢虎之人如好,何妨同其为义兄弟,后来亦可互相引进。”(11)当陶大均对帮助誉章谋事之请求未作回应,秋瑾开始贬低此人,可见其对誉章职业前途关注之深、之迫切。
誉章在西城路工局工作的性质和具体职位不知,薪水大约甚少,(12)据秋瑾致兄第二函即5月27日函内容可知,誉章一边在路工局工作,一边用钱谋保取“县丞”,秋瑾提醒说:“恐县丞后在除汰之内,请细细一查为要”。誉章欲谋保取“县丞”之银,来自于母亲的私房钱,因此秋瑾又劝告誉章:“睢日用艰难,母亲年老,能早日出山,以慰母望……未知何日能得保?”(13)当意识到誉章在京另谋他职非易时,秋瑾劝其暂时安心于已有职位。如9月12日函谓:
工局得借一枝,且安之,以养坚忍刻苦之历练。东三省议和本可结局,近因日民愤激俄之不割库页岛事,反对政府风潮甚大,且看平静后如何,再行函告,此时勿冒险前往为要。因时局如兹,难后必无事承平,凡事得安之且无躁。(14)
函内劝告誉章“勿冒险前往”东北谋事,此事的关联大约如后:一、在连致二函向陶大均请托同时,秋瑾也致函时在东北的陶大均本家长辈陶在东。据陶在东忆:“日俄战沈阳,予奉调出关,(秋瑾)由廉、陶转来一函。久之不通音问……且不知何时返至绍兴也。”(15)廉、陶应是指廉泉、陶大均。秋瑾致陶在东函似在1905年初夏归绍兴家中,亦与她致陶大均函同时,推测其举仍在为誉章谋事。(16)二、秋瑾兄妹之堂叔父秋桐豫,即后函所称“十二叔”、“清墅叔”,(17)那时任官黑龙江,誉章可能想去黑龙江投靠此人。
陶在东(1870—?),名镛,陶大均的本族,1895年中举,初为福建督学戴鸿慈幕僚,1904年入商部,1905年入东北总督赵尔巽幕,后署绥中县知县。据其回忆与秋家两代人之关系:
(秋瑾之父)与先君同寅雅故,清光绪初年,同司湘潭榷务,两家眷属,时通往来。女士富天才,自幼即好翰墨,流播人间,一时有女才子之目。……予在童年,粗解文字,有时长辈命同作一题,晤见时谈艺而已,越二十年,当光绪癸卯甲辰间,予调商部,入故都,女士阅邸报来访,见面几不相识……每有撰述,辄倩予视草。(18)
陶在东和陶大均都是绍兴人,尤其陶在东还有两代人之交往,因此秋瑾居住北京后,积极主动地与他们联系。
西城路工局之管理单位北京内城工巡局于该年10月被裁撤,此事大约在此前已有传说,因此9月12日秋瑾函询誉章:
吾哥在路工局,此事何时停止?王尧阶之叔相待情形何如?……吾哥在京曾有朋友否?当择佳士深交之。因我家祖、父、叔俱未有一好友、一世谊者,如我家稍关痛痒毫无一人,故今日无一人照拂我家者。凡一家人之子孙,不能不后日需人照拂者。(19)
秋瑾感慨科举出身且有仕宦经历的祖父、父亲和叔父等人,在官场上均未交有好友,以致秋家子侄在社会上无人提携和帮助。11月6日函内复有第二次感慨,谓:“因秋姓族中如是,十二叔等又如是……祖父以来俱无一好友,以致今日竟无人一援手故人之子者,亦由前辈之无良友也。”(20)
誉章在西城路工局薪水很低,工作又可能不会长久,秋瑾多处利用朋友关系想为誉章谋事不成,加之当1905年7月秋瑾二次东渡,正值大量中国留学生赴日。1904年下半年,清政府制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并于次年举行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参加者14人全部取得进士、举人出身。同年9月,清廷下诏自1906年起所有科举考试一律停止。由此,1905年下半年中国人留日数量大增。(21)应是鉴于以上种种,寄誉章之第六函即10月6日函,开始鼓动其东渡留学。函谓:
吾哥何妨写一函告知清墅叔,能否一年帮四五百金,而吾哥留学日本数年再归,当可扩张势力,不然,恐谋事不易……况吾哥尚在壮年,二则赴日之途非远也。想清墅叔得有子侄出洋,彼亦有名誉也;如不能多帮,则二三百亦可。再托人谋一官费,则尚可兼顾家用;官费不一定须浙中者,各处俱可谋得也。
“清墅叔”,即前述秋瑾堂叔父秋桐豫。秋瑾提议誉章向秋桐豫求告,请其提供留日费用,又提议托人谋取留学官费。致兄第七函,即11月6日函催问:“吾哥留学何如?各处托人运动官费出洋为要。……如今时事,谋事非出洋一回不可也。”半月后,致兄第八函即11月20日函再次催问:“来东之行,必不可稍缓。京中之十余元,实无足恋者。惟经费难筹,妹已向吾嫂言之,商借于张宅千余金,即三年之费,后日归还,亦无不能,想无不允之理。”誉章之妻张氏,娘家似比秋家富有,秋瑾自作主张致函兄嫂,要其向娘家借银一千,作为誉章留日三年之费用。同函内劝告誉章:
吾哥总以今年早来为妙,或明年二月初到日亦可,而此数月可向亢虎处稍学日文则更妙,未知吾哥以为如何?……时事如此,寸阴可惜。
如来,祈早示坐何船及何日动身。到长崎,则寄一邮片。到神户,可坐火车到东,坐火车时,打一电报,以便到车站迎接,或坐船直到横滨,则由神户发一邮片,当到横滨舟中迎接也。(22)
大约誉章无意向妻子娘家借银,仍计划赴东北依靠戚友谋保举,秋瑾在揣度誉章心思后,紧接前函发出第三次劝告,即11月28日致兄第九函谓:
吾哥虽云赴东三省图保举,但今日世界谋事,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年,谋事较易。妹已向嫂氏商量,借张氏千余金为吾哥学费,学成归还云云,且看如何回音,即当告知。如能明年赴东,方不虚掷青年也;不然,北京、东省总觉鸡肋无味也。亢虎近常见面否?
一个月内秋瑾为劝告留学日本事,向誉章连续寄出三函,可见其心情。秋瑾甚至为誉章设计了在日留学的专业,如11月28日函谓:“吾哥能于日语先为练习,他日至东可进蚕业或实业学科,以期实事求是耳。”所谓“亢虎近常见面否”,是因为她在前函内建议誉章为留日准备,而向江亢虎学习日语。
但12月初留学生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运动一发生,秋瑾决定退学归国,她为誉章东渡留学而筹划的一切,顿时化作泡影。12月9日致誉章第十函称:“今留学界因取缔规则,俱发义愤,全体归国;此后请勿来函,大约十二月须归来也。”12月22日致兄第十一函,告知即将归国。函谓:
近日留学界全体同盟停课,力争规则之辱,不取销则归国交涉,因公使不为助力,难答第一之目的,故决议全体归国,故纷纷内渡已及二千余人。妹亦定此月归国,以后再作行止,不能不作后日糊口计也。(23)
12月末,秋瑾离日归国。虽然,誉章东渡留学未成现实,秋瑾希望利用陶大均、陶在东、江亢虎等人为誉章谋职事亦未成功,但通过以上信函内容的解读,秋瑾对兄职业和前途关注之切令人侧目。
二 留学经费匮乏引发的烦恼和焦虑
秋瑾对丈夫和夫家的责骂、不满以及对婚姻的痛悔,事实上是由其不提供留学费用所致。要解读此部分内容,有必要先解读十一函内秋瑾对留学费用匮乏的烦恼、焦虑和所设计的筹款办法。据陶在东忆,1904年秋瑾决定东渡时,“夫家不允供学费,女士愤。斥卖其妆奁,所获有限,吾暂为措数百金”。(24)秋瑾女友吴芝瑛亦忆及秋瑾留学前“脱簪珥为学费”,又称其“脱簪珥谋学费,窘迫万状”。(25)作为世家小姐,又出嫁时父亲尚在湘乡厘金局总办官任上,秋瑾之嫁妆必丰,且夫家亦是湘潭经营典当业的富商之家,无论婚前婚后,秋瑾手中私房钱数目当不小。又,即使夫家不允供学费,私房钱又不足留学费用,其娘家亦可提供帮助。但事实上,无论秋瑾本人还是其娘家,都已不存在提供留学费用之余裕。因为,1901年11月秋瑾父亲寿南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去世,留下妻妾单氏和孙氏、长子誉章夫妇和子女以及孙氏子宗章等约十口人的大家庭。据宗章说,父亲寿南虽“居官以清廉著,鹤俸所积,原非丰裕。脱令子侄力保先畴,兢兢业业,犹可毋虞冻馁”。但仅一年内,寿南所有做官之积蓄化为乌有,秋家生活顿然失去主要来源。原因是誉章在此时作出一个重大举措,即1902年初他未带领家人扶父亲灵榇回乡,而是由父亲原任所桂阳至秋瑾所住湘潭定居。据宗章回忆,是因为秋瑾“孑身远嫔,不欲暌违亲属”,誉章乃“从其志也”。随之,秋瑾“斥私蓄数千金,又商于兄出资如之,合设和济钱肆”于湘潭城内,“逐十一利,以济日用”。此处“私蓄数千金”,乃是让丈夫王廷钧从夫家析分来的资产。(26)次年初,因誉章“书生积习,原未暗阛阓利弊”,秋瑾“又深闺守礼,未便躬亲稽察”,“且待人接物,胸无城府,亦不虞有他”,和济钱肆所托之经理人乃“监守自盗,略无顾忌”,终于导致钱肆倒闭。誉章“为信誉计,悉索敝赋,破产以偿”,秋瑾亦典卖首饰偿债。结果,秋家经济“一败涂地,资产荡然”。誉章最终靠典卖家财,“罗掘所有,得数百金”,才于1903年初夏扶父亲灵榇回绍兴,全家定居于祖父秋嘉禾所置和畅堂,并依靠祖父遗产生活。嘉禾一门子孙未析家产,全部在和畅堂居住,各堂从兄弟、妇孺一门同灶共居,丁口甚众。(27)据秋瑾致兄十一函内容,可以推测和畅堂居住人口在20至30之间。要养活这许多子孙,嘉禾留下的产业应该不薄,即使如此,大家庭过活亦不得富裕。如致兄第五函内谓:“家中尚不致嗷嗷待食,亦无需吾哥焦灼家用。惟能月寄数元,为母亲添补饭菜,则吾哥之孝心可慰。”(28)
秋瑾夫妇从夫家析分来的及父亲留给誉章等家人的资产,全部因秋瑾提议办“和济钱肆”及其倒闭,而丧失殆尽。秋瑾本人及娘家不再可能为其东渡留学提供经费,而此前已将家产析分给秋瑾夫妇的夫家,亦不可能提供费用。(29)因此秋瑾留学的费用,一开始就只能依靠出卖首饰、衣物筹措,或由友人借措。此类资金自然不可能充裕,加之秋瑾的侠气和“挥金如土”的性格,(30)更令其留学费用多次出现危机。1904年6月秋瑾首次赴日前,将由出卖服饰及友人借措所得资金,赠给了被关押在京师监狱中的维新党人王照。陶在东谓当时秋瑾“倾囊中所有赠之,其仗义疏财如此,吾曹再度赆之而后成行”。吴芝瑛亦忆及,当秋瑾得知王照事之后,“乃分其金以应急,展转达狱中,属勿告姓名。……然女士与宁河(王照)初不相识也。”(31)到东京后,秋瑾性格仍然如此。据章士钊回忆,11月下旬,东京留学生发起为万福华在上海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果而入狱案募捐时,“革命阵营中之中外同志,交相震动,尽可能设法善后,秋瑾即为此中捐款出力最显著之一人”。据陈志群称,当时秋瑾“囊中仅四十元耳,竟尽数捐之。”(32)因此,秋瑾手上总是乏钱,从她致兄各函文字中都能感受到经济匮乏及由此引发的烦恼和焦虑。其致兄第一函,就有关于出售服饰筹措留学费用的记载:
妹于陶杏南夫人处……有龙头翠[翡]翠镯一只、珠子及衣服,如彼未售,已嘱交吾哥,玉镯在上海估玉器,已出价二百四十元,大约三四百元。如有售处,祈吾哥随机售出。
11月6日函中问:“衣服、珠子已取回否?二妹处久无书来,不解其故,亦未知存湘之衣饰曾售去否,殊深焦灼也。”11月28日函又告知:“学费虽拮据,近尚可勉强设法,惟镯子卖不出,及二妹处衣服杳无音信,殊令人焦急万分耳。”(33)说明秋瑾东渡前不仅将北京家中的首饰、衣物寄存陶荻子处托其售卖,还将原留在湘潭夫家的首饰、衣物托居住在湘乡的妹妹秋珵出卖。妹妹处没有音信,秋瑾很是焦灼。
大约秋瑾致函秋珵谈及借债筹款的话题,秋珵出策向堂叔父清墅借贷,引发秋瑾不满。11月20日秋瑾致兄函谓:“二妹之函云欲哥向清墅叔商借,为妹学费,不知如何出此无益之策?彼并不知出外人之困难,不直接向王处商借而出此,徒费时日也。”11月28日函又谓:“二妹久无函来,惟于今月方接一函云,已函托吾哥向十二叔处代借款寄妹,并云:若借不到,则向王宅筹寄,不愁不允。不禁又笑又气也。”(34)两函中“王处”、“王宅”,应是指秋瑾湘潭的夫家。
据在东京与秋瑾熟知的光复会人士陶成章说,1905年春秋瑾由日归国的原因是:“本为筹学费计,既抵家,求给于母。母故深爱其女,然家徒拥虚名,实不中资,为勉筹数百金附之。”(35)秋瑾第二次东渡抵东京在7月23日,由于有母亲为其筹措的“数百金”,因此11月下旬她还能说,“学费虽拮据,近尚可勉强设法”。秋瑾在11月6日函中曾告诉誉章:“学费十六元(余俱在外)。须买书参考其价之昂,甚贵。衣服、零用、纸笔等每月须三十元之谱,尚不敢奢侈一点,出门行路,并未坐过人力车也。”(36)每月需要三十元,这是指用于学校和学习的费用。(37)但秋瑾每月费用开销决不只在学校方面,她还有用于参加同盟会、留学生和同乡会活动方面的费用。如华兴会的刘揆一称:同盟会成立后,黄兴“设制造弹药机关于横滨,聘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秋瑾与陈撷芬、林宗素等女留学生“皆加入练习”。又称,当黄兴“创学习炸弹机关于横滨时,其弟道一与秋瑾女士……本有十人团之组织”。(38)王时泽又回忆,秋瑾“常到东京粷町区神乐坂武术会去练习射击技术,又学习过制造炸药。我在横滨李植生处学习制造炸药的笔记,她全部借去抄录了”。(39)
秋瑾9月12日致兄函中曾说,如果夫家并非富有,她可以在外借钱,但是夫家之富名被外界所共知,令她借钱困难。所谓:“因无彼家之富名,妹于筹款之事,尚可藉他人帮助;旁人闻彼富有,反疑妹为装穷,故无一援手者。”(40)夫家既不允提供留学费用,夫家之富名且又造成其在外借贷之困难,因此,秋瑾对丈夫和夫家的怨恨、不满及对婚姻的痛悔,随着留学经费匮乏的加剧而愈来愈深。
三 对丈夫和夫家的责骂、不满及对婚姻的痛悔
秋瑾19岁依父命,嫁湘潭经营典当业的富商之子王廷钧(字子芳),丈夫比秋瑾小两岁。弟弟宗章回忆:姐夫“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秋瑾与之相比“转伉爽若须眉”。京师大学堂教习日本人服部宇之吉之妻服部繁子后来忆廷钧,亦称:“白脸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温顺的青年。”后来秋瑾长子沅德的岳父,即廷钧的湘潭同乡张翎六,亦称其:“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又谓:“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志远大急于仕进,两应童子试,一赴乡闱不与选,遂弃帖括”。(41)
秋瑾父亲寿南虽仅为一中下层官员,但自身及以上三代父祖都是科举正途而仕宦如此人家的小姐嫁给当地富商做少奶奶,决不低身价。秋瑾出嫁次年,就为富商之家生育一儿。她本人又是才女,以诗词著称于湘潭城内,(42)不但与当地名士酬唱题咏,如其诗作《题松鹤图 李翰平[屏]先生王父之小影》,还主动以诗晋谒名流,如其诗《上陈先生梅生索书室联》。李翰屏,名镇藩,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举人(1892),官内阁中书;陈梅生,名嘉言,湖南衡山人,光绪壬午年(1882)湖南乡试解元,十五年(188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历任京畿道、福建漳州知府等官。(43)这些居住湘潭的地方名流,除与父亲寿南的关系外,恐怕更多的是与夫家王氏的关系。如秋瑾对丈夫及湘潭夫家的生活不满,她可能就难以去酬应这些关系。(44)
张翎六说:王廷钧“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以报效秦晋,赈款议叙工部主事”。(45)光绪二十七年即1902年,正是秋瑾让廷钧从夫家析分资产,用之与誉章合开“和济钱肆”之年。王廷钧捐纳得工部主事,捐纳之资自然应出自王家。父亲寿南去世,秋家顿失依靠,秋瑾一面要求丈夫捐纳为官,一面让丈夫从夫家析分资产,用之与兄长合开钱肆,这里已经看到秋瑾欲为秋家开辟出路的规划。1903年6月,当将钱肆倒闭之善后事宜处理完毕,誉章率全家返归绍兴山阴定居后,秋瑾则与已捐纳得官的丈夫同赴北京。
陶在东忆北京时期的秋瑾:“青布之袍,略无脂粉,雇乘街车,跨车辕坐,与车夫并,手一卷书。北方妇人乘车,垂帘深坐,非仆婢,无跨辕者,故市人睹之怪诧,在女士则名士派耳。”服部繁子忆1904年初春第一次见到的秋瑾:
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细手杖,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青年。(46)
秋瑾将自己装扮成男性形象,除去受男女平权的社会因素影响外,大约还有两种思考:一是取代誉章,成为秋家的振兴者,这里可能包含有秋瑾对父亲去世后留誉章及母亲全家定居湘潭,又让誉章拿出父亲遗产合办钱肆,最终将秋家资产全部耗光所产生的内疚。二是对丈夫感到不满,而她本人想要做一个女丈夫。如果秋瑾夫妇未去北京而仍居湘潭,她对丈夫的不满未必不能忍受,但秋瑾随夫居京城后,所交亲友如陶大均、江亢虎均有留日经历,陶在东为举人出身,廉泉、吴芝瑛夫妇则一为举人,一为名嫒,(47)并富诗词之才,在社交界颇有名气。以上诸人完全依靠自身实力谋得官职及社会身份,并非如王廷钧依靠商人家庭出资买官。据陶在东回忆,秋瑾对丈夫最大之不满,在于其非科举出身及依靠小官身份获得生活来源。所谓:
清时京官恃印结费为生,印结者,出仕人分发引见,需同乡京官出具认识并无违碍甘结,而纳费若干,苏浙之外,以湖南收入最多,每员月可分得数十乃至百数十金,一般富家子弟,多捐部曹而坐食此息,子方[芳]当然不能例外,女士意殊不屑,然此类京官如习举业,仍可以附监生资格,赴顺天乡闱,取科第显达。子方[芳]为人美丰仪,翩翩浊世佳公子也,顾幼年失学,前途绝望,此为女士最痛心之事。
秋瑾希望的是一个依靠自身实力养家和取得社会身份的丈夫。陶在东又说,秋瑾因与廉泉、吴芝瑛夫妇关系良好,因此每与言及丈夫之事:
至声泪俱下,多所刺激,伉俪之间,根本参商,益以到京以来,独立门户,家务琐琐,参商尤甚,迹不能掩,于时廉、吴夫妇,吾家陶杏南、姬人倪荻倚(陶获子),及予妻宋湘妩,无数次奔走为调人,卒无效,由是有东渡留学之议。
秋瑾在湘潭夫家居住时是一位少奶奶,写诗作词是生活主要内容,但居京后成为小家庭的女主人,要照顾全家生活,这大约是她不甘心的事情。据服部繁子回忆,1904年初春她访问秋瑾家时见到:“书架上胡乱地放着书籍和衣服。瓜子皮、果皮撒在屋角里发出一股遗臭,并不很清洁。”秋瑾家中雇有女佣,但情况仍然如此,说明秋瑾并非想成为一称职的主妇。服部繁子说,当年6月秋瑾决定要随她归国之机,一同东渡留学,而她表示出犹疑时,王廷钧亲自访问她,请求其带秋瑾去日本。(48)因此,秋瑾东渡留学前,虽与丈夫关系非和谐,但王廷钧似未有大的过错。而秋瑾在致兄函内,却有大量责骂丈夫和夫家及痛悔婚姻的内容。
1905年春秋瑾归国后致兄第二函,即6月19日在绍兴寄函,主要是向誉章数落丈夫之过,函内开始出现痛骂的言辞。所谓:
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为彼篡取……妹此等景况,尚思截取此银及物,是欲绝我命也……嘱二妹讨取此银时,不妨决裂。……妹得有寸进,则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如无寸进,不能自食,则必以一讼取此儿女家财,不成,则死之而已。
痛骂原因似乎是王廷钧未将秋瑾之“珠帽及珠花”及一笔银元交还。从以后秋瑾致兄数函相似内容分析,“珠帽及珠花”似是秋瑾留存在湘潭夫家的陪嫁物;誉章误以为秋瑾返国时将先回湖南,乃将银元一百寄到湘潭王家,当时王廷钧似在湘潭。函内“二妹”指居住在湘乡的妹妹秋珵,秋瑾要秋珵到王廷钧处讨回誉章误寄之一百银元。秋瑾在致兄函内第一次提到要与丈夫离异,所谓“妹得有寸进,则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又第一次在与丈夫关系上提到“死”,即“如无寸进,不能自食,则必以一讼取此儿女家财,不成,则死之而已”。
秋瑾致兄第四函即8月14日函,继续追问二妹秋珵是否已经从王家讨回银元一百,并再度痛骂丈夫,痛悔自己的婚姻。所谓:
二妹常有信来否?讨取百金,不妨决裂,因彼无礼实甚,天良丧尽,其居心直欲置妹于死地也。目我秋家以为无人,妹已衔之刺骨,当以仇敌相见……妹如得佳偶……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今日虽稍负时誉,能不问心自愧耶?……读书之人,虽无十分才干者,当亦无此十分不良也。……抚心自问,妹亦非下愚者,岂甘与世浮沉,碌碌而终者?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他日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无使此无天良之人,再出现于妹之名姓间方快,如后有人问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
函内“今日虽稍负时誉”一语,应是指秋瑾在留日学生界的出名。如上海发行的《女子世界》1905年第3期发表署日本东京调查员“外国特别调查”,其中谓:“据最近调查,中国女子在东京者百人许,而其中最著名者共三十人。就中……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49)在留日学生界内出名令秋瑾对丈夫产生更大的不满,更加痛恨丈夫非读书人出身。她第二次提及与丈夫离异之事,所谓“如后有人问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又第二次在与丈夫关系上,表示已有“死”的觉悟,而说明死的前提条件是青史留名,所谓“他日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
秋瑾致兄第五函即9月12日函,是十一函内最长之一函,谓:
母生我兄妹三人,吾哥孝养得随[遂];二妹虽不能归省,而得常寄银洋、食物,以娱暮景,亦可稍慰;所不孝者,其惟只妹一人耳!不能孝养,反使老母萦心,负罪实深。但此亦婚姻不能自由之遗憾,使得一佳子弟而事,岂随[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
此为秋瑾致兄函内第二次表露对婚姻的痛悔。另外,关于误寄之银元一百之事,继续责骂王廷钧,谓:
况此银在彼已年余,未见一提及,又不寄与妹,此何居心,岂不能明见彼肺肠耶?……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不则宁湮没无闻,断不欲此无信义者有污英雄独立之精神耳。惟钱财一端,妹正困于此,况彼守财奴物,取之无伤于廉。若果能将哲夫太亲家扣留则甚佳,即彼不允,何妨云:“因悯妹经费困难,已借用去矣,出有收字”云云,何如,祈酌行之。近妹曾有一函与子芳,责其百金及珠花、珠帽等事,后云:“经济困难,商借千金”云云,并云:“须还前欠,此后费用,当再设法。”看彼如何作答。如不借及置之不答,则遗书断绝往来,此后王宅不得云有秋氏之女为媳事,吾哥以为何如?(50)
此处表明,为逼迫王家提供留学费用,秋瑾甚至向誉章出策,在北京扣留与湘潭王家关系良好的秋珵丈夫王尧阶的祖父,即所谓“哲夫太亲家”。另外,谈及已致函丈夫,要其借钱“千金”,如丈夫不肯,就与其“断绝往来”。此为秋瑾第三次表示,如果王再不愿提供留学费用,就与其决裂。所谓“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不则宁湮没无闻”,亦是秋瑾第三次在与丈夫关系上表露已有死的觉悟。
秋瑾致兄第六函即10月6日函,再谈及向夫家借钱和与丈夫关系事。所谓:
王二老父子,妹知之熟矣,断不肯汇资与妹者。虽哲老之言,彼允五百元者,因慷他人之慨,一竿允五百,亦无可如何者。机缘不巧,哲老卸事,此仍落空;而妹曾函达索银一竿,至今月余未见回音,其意可知矣。而二妹所言子芳有函达绍者,此乃为彼宅所欺耳,岂有数月而绍中未接其函,此语之假可知也。然此事有所藉口,当与王宅决裂行之。妹一人岂随[遂]不能谋一衣食者乎?(51)
“王二老父子,妹知之熟矣,断不肯汇资与妹者”,似是誉章函告秋瑾,王廷钧父子允诺向秋瑾汇出银元五百,此事由“哲老”即王哲夫转告誉章。另外,秋珵有函给秋瑾,告以王廷钧与绍兴之母亲有函联系,但秋瑾不相信丈夫此举。又,秋瑾第四次表示,欲与丈夫及夫家“决裂”。
以上内容表明,无论秋瑾如何痛责丈夫,数度表示要与其决裂,亦数度表示如果与丈夫关系不能按照自己愿望解决,“则死之而已”,但秋瑾与丈夫关系之症结,仅在所谓“百金及珠花、珠帽等事”,全在于王家未提供留学费用。由可知此东渡留学之事,对其何等重要,秋瑾似视之为改变绍兴秋家大家庭和改变个人命运之举。
11月28日秋瑾致誉章第九函,函内有“索回百金,想二妹自己需用,吾哥去函可勿提及为要”之语,可知誉章误寄王廷钧之银元一百,已由秋珵取回。因此,秋瑾在该函内不再痛责王廷钧和夫家,但她非常心痛地说了一段话:
陶处之衣箱,但差一下人向其东院太太取之可也,不必再向陶老说话也。我兄妹二人毫无戚友勘依傍者,万事非靠自己不行。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告语者,惟妹而居无室家之乐,出无戚友之助,漂泊天涯,他日之结局实不能豫定也。吾哥虽稍胜一筹,而无告语则同,无戚友之助亦同,所幸者,生为男子耳,结局似胜妹十倍也。但妹亦不作杞忧,处今日之世界,国尚如此,况妹乎?惟切齿者,吾之仇,报复无计,实平生隐痛也。惟祈吾哥善筹自立之计。(52)
因陶大均始终未向誉章提供职业上的帮助,秋瑾嘱誉章差人向陶如夫人处取回自己存放的衣箱,不必再与之联系。誉章误寄的银元一百秋珵已经索回,痛骂丈夫的理由不太充分了,但与丈夫及夫家的关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娘家、夫家均无法依靠,秋瑾深感孤立,遂将所有不快发泄于丈夫。“祈吾哥善筹自立之计”,可以理解为1905年11月末秋瑾已准备好给誉章的遗言。
四 对绍兴秋家子侄前途之关注和安排
秋瑾致兄十一函,其中有四函提及绍兴秋家子侄的前途,最后一函即12月22日函,对秋家子弟“俱不足以兴吾门”表示感慨和无奈。此处有必要简单介绍秋家之概况。
定居于绍兴山阴县的秋家,在秋瑾高祖父秋学礼时,开始由务农之家转向科举仕宦之家。如高祖父秋学礼,1789年举人,官秀水县(浙江嘉兴)教谕。曾祖父秋家丞,1813年举人,历任砀山、东台、江宁、上海等地知县。祖父秋嘉禾(1831—1894),1865年举人,历任福建云霄、厦门等地知县、知州,台湾鹿港厅同知等职。嘉禾有兄三人:长兄秋曰觐(?—1862),1851年恩科副贡生,历任台湾噶玛兰厅(台湾宜兰)通判、彰化县知县等职,1861年任淡水同知,1862年死于平叛彰化民变之战,其子孙得授世袭云骑尉之荣;二兄秋宇鸿,曾署金匮、无锡知县;三兄秋鹤皋,运同衔,分发同知。嘉禾还有姐妹八人。父亲秋寿南(1850—1901),1873年举人,历任台湾布政使邵友濂幕之文案、湖南常德湘乡及湘潭厘金局总办、郴州直隶州知州等职。(53)
秋瑾高祖“秋学礼”之名,应出自《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二伯祖“秋曰觐”之名,应出自《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于此颇见诗书传家之风貌。自秋瑾父亲以上四代均为举人出身,多人出任知县、知州、同知等职,属科举时代相当成功的家族案例,在当时社会也是凤毛麟角。可以想见,作为世家小姐的秋瑾将多么重视这种荣耀。
秋瑾父亲寿南一辈,除寿南举人出身外,未见其他人有科举成功的记载。据宗章之回忆,祖父嘉禾一门子孙未析家产,全部在“和畅堂”居住。所谓“嘉禾一门子孙”,自然是指嘉禾三个儿子寿南、福南和庆南的三个家庭,同样要依靠嘉禾之遗产生活,福南、庆南无好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可想而知。秋瑾致兄函多次提及的“清墅”、“十二叔”,及宗章回忆中提及的“青士公”秋桐豫,似亦非科举出身而做官者。父亲寿南早逝后,如长子誉章或长女秋瑾之丈夫能够由科举步入官场,秋家的社会地位尚可维持,嘉禾一门子孙的职业和前途也能够得其照应。可惜誉章和王廷钧的状况都非如此。所以,秋瑾会多次痛悔自己的婚姻,所谓:“妹如得佳偶……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使得一佳子弟而事,岂随[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1904年夏,秋瑾慨然东渡留学,最主要原因似是想由自己来承担振兴秋家之重任。
致兄第六函即10月6日函,除说服誉章向堂叔父清墅借贷留学外,还劝告誉章安排家中少年进新式学堂:“二侄、祥弟明年可进东浦热诚学堂,以造成彼后来自立地步,切不可使其失此读书之年时。官立学堂多腐败,不如私立学堂之佳,况东浦学堂甚办有成效也。”“二侄”指誉章之两个儿子,“祥弟”则指宗章。(54)“东浦热诚学堂”,乃徐锡麟在家乡“与同志数人”集资所办小学堂。因陶成章之函介绍,秋瑾于是年6月在该学堂结识徐锡麟,而徐则介绍秋瑾加入光复会。(55)
致兄第八函即11月20日函,告以为筹措誉章、宗章及绍兴家中子侄东渡留学或进新式学堂的费用,已设计二策:一如前述,已致函兄嫂张氏,请其向娘家商借“千余金”;二是已致函当时似秋家之当家人的“玙弟”,请动用“千余公款”。关于后者,所谓:
家中侄等进学堂亦必需款,玙、珉二弟亦非进学校不可,如许经费,实难筹得。惟有将公款提出,作为诸人学费,不作别用,以期造就人材。因各处卖田求学者甚多,如不自立,坐吃山空,此区区者亦归乌有,不如求学业之为计得。以妹计之,二侄每年须八十元之谱,单膳金,无学费。二弟每年八十元之谱,只膳食。……小姐嫁妆费不如为之求学(入女学堂)。子序亦劝其入学堂。玢妹、己湘二侄女,则或入学堂,或请一先生每天教一二点汉文。不留膳,薪水亦廉。吾哥则拿四百金为一年之学费,后之学费再筹。子序四五十元一年。大约各人一年以三百元即是,家希不学之人,皆有自立之生活,不愁他日不能归此千余公款也。
……公款事,妹已函告玙弟,嘱其向吾哥言之,免吾哥先言也。时事如此,寸阴可惜,祈注意也。
“二侄”仍指誉章二子,“二弟”指宗章,“小姐”、“子序”和“玙、珉二弟”应是秋瑾之堂姊妹、堂兄弟,即父亲寿南之弟福南、庆南之子女。“玢妹、己湘二侄女”则是誉章二女。所谓“将公款提出”、“千余公款”等,似是秋瑾提议从祖父嘉禾遗产中提出原作为秋家一门子孙之生活费的一部分,供嘉禾一门后代的留学和入读学堂之费用。秋瑾除热切希望秋家之人能够跟上时代发展而不落伍,更重要的是她考虑秋家之人今后能否在社会上自立的问题。当听说秋珵之丈夫王尧阶仍在“学幕”时,同一函内愤愤然说:“尧阶乃又学幕,真不知时事者,虚糜光阴,徒求无益之学,为后日计,欲唤奈何也。”
离前函发出仅一周后,即11月28日秋瑾致兄第九函继谓:
二侄进学堂甚善。子序、玙弟如此,俱非久长之计,各宜谋自己生活之后计,因区区之祖产非可久持者,今日不学,后日如何?哥宜函劝子序弟设法进学堂学实业,为自立计,且不可徒荒岁月,销脑力于嬉游中。实业,汉文不佳者,亦佳也。
秋瑾担忧秋家子侄前途,要兄长设法让他们进新学堂,且每位情况都交代到位。当年秋瑾之子沅德8周岁,秋瑾却未有只字关心其入学之事。
秋瑾致兄第十函作于12月9日,即积极投身反对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运动期间,其函非常简短,仅告知:“今留学界因取缔规则,俱发义愤,全体归国;此后请勿来函,大约十二月须归来也。”(56)12月22日致兄第十一函,为留存秋瑾致兄最后一函,函谓:“妹亦定此月归国,以后再作行止,不能不作后日糊口计也。”又忧虑誉章及秋家子侄之前途,谓:
玉如之无知,子序之不学,俱不足以兴吾门,而继之祥弟之顽疲,奈何?而妹生为女子,亦无益于家门,无助于吾哥,不胜自恨,此后糊口四方,尚不知何地驻足也。吾哥如不能东渡,当赴奉天乎?
庚子事变后,清廷实行新政,1905年废除科举制,各类新式学堂应运而起。而秋家子侄几乎都未能像秋瑾那样认识到时代变动,进而调整生存之道。尽管他们仍可以依靠祖产生活,“不致嗷嗷待食”,但祖产终会“坐吃山空,此区区者亦归乌有”。一门子侄前途如何,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能否“皆有自立之生活”,还关系到绍兴秋家之荣光,即如秋瑾1906年致函誉章之子壬林所嘱托的:“若能循良勉学为秋氏争荣光,方不虚生于人世。”(57)
通过对秋瑾致兄十一函的解读,我们了解到秋瑾作为反清女革命家活动的同时,属于她个人内心世界的活动,从中可以探悉她从事革命活动的部分原因。另外,我们也了解到20世纪初的大变动时代中,部分中下层官宦子弟的生态。他们的父辈或已去世,或已退出官场,而自己尚在科举道路上艰难跋涉,无论自身实力还是社会能力,均未作好应对时代和社会急变的准备,因此,当家庭的、家族的,及个人婚姻的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识世变者就会格外焦虑,甚至痛苦。在秋瑾致兄誉章十一函中,字里行间都浸透着秋瑾对兄长、对秋家子侄的职业和前途的担忧和焦虑。秋瑾是诗人,好悲歌,又是一双小儿女之母亲,但是现存她留下的文字中,没有留给儿女的。为什么?因为一双小儿女姓王,而不是姓秋。也许在秋瑾看来,王家是暴发户的商人,他们是无须注重家族声誉和传统的,而秋家是数代读书人,由科举正途而仕宦的,秋家的读书种子和仕宦之途,以及秋家数代的荣光,决不能断于她这一代。
注释:
①十一函之中九函,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秋瑾集》中已经公开,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重印中华书局版的《秋瑾集》时,加入了新搜集的另外两函。
②关于秋瑾出生的年份,笔者参考的资料是秋瑾夫妇之子王沅德的岳父,湘潭人张翎六著《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以及《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的记载。据《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载:十七世裔孙王廷钧“配秋氏,字瑾,寿南公女。……光绪三年丁丑十月十一日卯时生”。转引自赵世荣著《曾国藩的故园》,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42页;罗绍志:《秋瑾生年新考》,湖南省商务厅网站,2010年9月17日。
③此点可由誉章对秋瑾被杀后遗体的处理看出。见秋宗章:《六六私乘》,载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21、128页。
④誉章似曾捐有附生、候选训导身份。参见郭延礼编《秋瑾年谱简编》,载《秋瑾研究资料》,第9页。
⑤秋瑾所有寄兄十一函,收信地址均为“北京宣武门内西四牌楼北帅胡同西路北西城路工局”。见《秋瑾集》第34页注释2。“西城路工局”,与“东城路工局”同属1902年下半年设立的北京内城工巡局。
⑥《秋瑾集》,第39页。
⑦参见陶在东:《秋瑾遗闻》,第110页;《秋瑾年谱简编》,《秋瑾研究资料》,第19页。
⑧《秋瑾集》第33页。此函未署任何时间,但根据函末有“妹即日赴绍,草草解装”之语,可知秋瑾由东京始抵上海;又据宋教仁于3月23日还在东京秋瑾寓所访问,以及周作人4月20日已经在南京见到秋瑾等资料,说明此函作于4月初。见《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周作人文选》,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⑨以上资料参见陶在东:《秋瑾遗闻》;晨朵:《秋瑾与陶荻子》,载《秋瑾研究资料》,第108、109、266、267页。
⑩《秋瑾集》,第36页。此函亦未署时间,但函末述抵达东京的时间为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即公历7月23日。可判断此函作于阴历六月内,即公历7月31日前。
(11)引函内容分别见《秋瑾集》,第37、41页。
(12)秋瑾11月20日致兄函内曾说“京中之十余元,实无足恋者”,乃是“鸡肋无味”。《秋瑾集》第42页。
(13)《秋瑾集》,第34页。
(14)10月6日函亦有同样劝告:“吾哥在京虽乏蔗味,但处今日朝不保暮之势,得安且安之,况今日非略知外交者,恐谋事更难。”《秋瑾集》,第40页。
(15)《秋瑾遗闻》,《秋瑾研究资料》,第109页。
(16)当时秋瑾正在绍兴多方设法谋一官费留学名额,秋瑾分别致函陶大均和陶在东,可能亦有托其为自己谋官费留学名额之计划。
(17)秋清墅,或秋青士,即秋桐豫,字仲谟,秋瑾父亲寿南之堂兄弟。
(18)以上资料见《秋瑾遗闻》,《秋瑾研究资料》,第108、109页。秋瑾父亲秋寿南1895年前后才在湘潭厘金局为总办,因此,陶在东所谓“清光绪初年”,记忆有误。辛亥革命后,陶历任浙江鄞县、定海、杭县知事及浙江省署司法秘书。与郑观应、汪康年、蔡元培、熊希龄等人多有吟咏唱和与交往。
(19)(20)《秋瑾集》,第39页,第41页。
(21)1904年3月,在日本中国留学生仅一千多人,1905年2月达三千人,该年年底数量猛增到“八千或一万名”。参见[日]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4、36页。
(22)以上引言见《秋瑾集》,第41—42、42—43页。
(23)以上引言见《秋瑾集》,第44、45页。
(24)《秋瑾遗闻》,《秋瑾研究资料》,第109页。
(25)吴芝瑛:《秋女士传》,《秋女士遗事》,载《秋瑾研究资料》,第68、71页。
(26)关于“和济钱肆”,秋宗章回忆有两种说法,《关于秋瑾与〈六月霜〉》:“(秋瑾)斥私蓄数千金,又商于兄出资如之,合设和济钱肆”,即秋瑾和誉章兄妹合开钱肆;《六六私乘》:“(誉章)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肆于城内十三总”,即誉章与秋瑾夫妇合开钱肆。另据1905年在东京与秋瑾相识的陶成章称:“(秋瑾)与廷均定约,分家产,瑾得万金,即以之经商,所托非人,尽耗其资。”此处所谓“与廷均定约,分家产”,应指秋瑾让丈夫从夫家析分家产,而王廷钧分得的“万金”家产,被秋瑾用于与兄合开钱肆。秋宗章关于“和济钱肆”的两种回忆之说,是同一意思。以上引言转引自郭长海、李亚彬编著《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4页;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27)均见《六六私乘》,《秋瑾研究资料》,第114、115、157页。
(28)《秋瑾集》,第37页。
(29)有理由相信,王廷钧从王家中分得的资产被秋瑾用于与兄合开钱肆耗尽后,其捐纳北京工部主事之资最终亦来自王家。
(30)徐自华《秋女士历史》述秋瑾的性格:“其生平喜读游侠传,慕朱家郭解者流,任侠好义,挥金如土,广交游,诚女界之豪杰。”载《秋瑾研究资料》,第61—62页。
(31)《秋瑾遗闻》,第109页;《纪秋女士遗事》,《秋瑾研究资料》,第71页。
(32)以上两则资料均转引自《秋瑾事迹研究》第37页。陈志群的说法,应直接听闻于秋瑾。笔者以为,秋瑾于1904年11月从东京实践女学校退学,原因之一就是为万福华出狱案募捐后,其留学费用匮乏。
(33)以上引言见《秋瑾集》,第33、41、43页。
(34)二函均见《秋瑾集》第43页。
(35)《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61页。
(36)(40)《秋瑾集》,第42页,第39页。
(37)王时泽《回忆秋瑾》亦谈到与秋瑾同在实践女学校师范速成科就读的母亲,“每月需三十日元之谱”。《秋瑾研究资料》,第203页。
(38)刘揆一:《黄兴传记》,载《辛亥革命》(四),第282、287页。
(39)《回忆秋瑾》,《秋瑾研究资料》,第202页。
(41)以上资料见《六六私乘》,《秋瑾研究资料》,第114页;《子芳先生夫妇合传》,《曾国藩的故园》,第142页;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秋瑾研究资料》,第175页。
(42)陶在东忆湘潭时期的秋瑾:“自幼即好翰墨,流播人间,一时有女才子之目。”《秋瑾遗闻》,《秋瑾研究资料》,第108页。
(43)参见田翠竹:《秋瑾在湘潭写的诗及佚事》,绍兴秋瑾纪念馆主办《秋瑾研究》第5期,1988年版。秋瑾二诗见《秋瑾集》,第61、62页。
(44)另有资料说明秋瑾与夫家关系良好,据宗章回忆:在秋瑾的首饰中有钏一只,乃是秋瑾“嫁后,王氏所营质肆,受典玉钏,逾期弗赎。姊见而爱之,即属主者留中。钏色青葱,俗称老玉”。《六六私乘》,《秋瑾研究资料》,第147页。
(45)《子芳先生夫妇合传》,《曾国藩的故园》,第142页。王时泽《回忆秋瑾》说:“王廷钧于1902年进京捐官,秋瑾随他同游北京。”宗章《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亦说:秋瑾首次上京,“吾家犹寄寓湘潭”。《秋瑾研究资料》,第199页;《秋瑾事迹研究》,第14页。
(46)以上引言见《秋瑾遗闻》,第109页;《回忆秋瑾女士》,《秋瑾研究资料》,第171页。
(47)廉泉(1868—1931),江苏常州人,1894年举人,时任户部郎中。吴芝瑛(1868—1934),安徽桐城人,善文章、诗词和书法,有当代谢道韫之誉。父吴康之,曾官郓城、信阳知县,伯父吴汝纶,进士,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僚。
(48)以上引言见《秋瑾遗闻》,第109页;《回忆秋瑾》,第175页;《回忆秋瑾女士》,《秋瑾研究资料》,第179—180页。
(49)转引自《秋瑾留日活动纪事五则》,《秋瑾研究资料》,第58页。
(50)以上引言见《秋瑾集》,第38、39页。
(51)(52)《秋瑾集》,第40—41、44页。
(53)关于秋瑾家族情况,参见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83卷“秋寿南”条目,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1页。
(54)誉章长子锡辰生于1892年,宗章生于1896年。参见郭延礼《秋瑾年谱简编》,《秋瑾研究资料》,第15、18页。
(55)参见《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56、61页。
(56)以上引言均见《秋瑾集》,第42、43、44、45页。
(57)《致秋壬林书》,《秋瑾集》,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