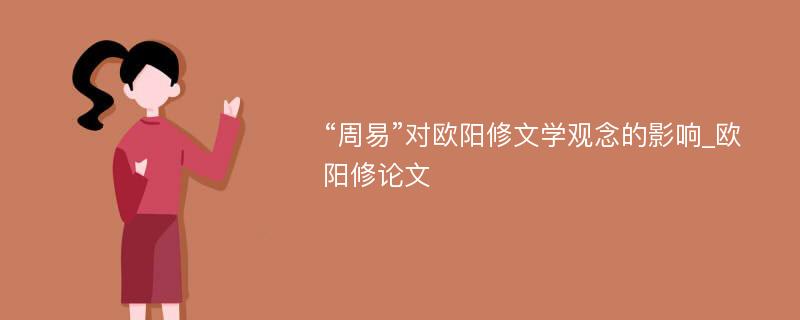
《周易》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欧阳修论文,观念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3882(1999)03—0081—6
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文忠,江西吉水人),以其说理畅达、抒情委婉的散文,清新自然、情意深挚的诗作等创作实绩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作为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他所持、所倡的文学观念,也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远及现、当代。
实际上,欧阳修的文化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以文学成就名世外,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也都有创获。就经学中的一大门类——易学方面而言,从其以《易童子问》为代表、以及散见于赠序、书答、札记、策问中涉及易学的著述文字来看,欧阳修的《易》学修养、造诣相当精深,他对《易》书易理的考辨、持见颇有独到之处。欧阳修的《易》说,有两个方面极具特色,影响深远:其一,是继承了王弼“扫象阐理”的“义理派”传统而有所发展,强调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理性实践精神;其二,是通过列举大量的例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以大胆疑古的精神明确地指出:《易传》中的五种六篇(即《文言》、《系辞》上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非出自一人之手,不可遽定为孔子所作,此说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惊世骇俗。
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形成,其来源与所受的影响固不止一端,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既是文学家又是易学家的欧阳修,其文学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周易》这部“广大悉备”、内蕴丰富的经典的影响。其中,欧阳修所持的“文道关系”论、“简易为文”说及“穷而后工”说,更是受到《周易》的直接、明显的影响。
一
“文”与“道”的关系,历来为古代文论家所注重。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说阐发是不胜枚举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愈,力倡“道统”说,以文道合一、修其辞以明其道作为“古文运动”理论的核心,欧阳修对此加以继承、发展,其辨析与阐说更为细致深入。以下先摘录欧阳修论“文道关系”的部分主要文字,以明其观点:
在《与张秀才第二书》(《居士外集》卷十六)中,欧阳修说: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孙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
在《答吴充秀才书》(《居士集》卷四十七)中,欧阳修说: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者鲜也。
接着,欧阳修以孔子、孟子、荀卿为正面例证,说明“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又以子云(杨雄)、仲淹(王通)为例,称他们是“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而“后之惑者”,更是离“道”学“文”,“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最后,欧阳修总结说:“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在《送徐无党南归序》(《居士集》卷四十三)中,欧阳修把修身、行事、立言三者看作是互相联系的整体,他以圣贤为例说:
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
此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居士外集》卷十七)中,欧阳修说:
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
以上引文,基本上体现了欧阳修论“文道关系”的要点,可归结为:一、扩充了韩愈所倡的“道”的范畴,赋予“道”以崇尚实际、重视实用的新内涵,也就是郭绍虞先生所指出的:“韩愈所言只是空喊口号而已,欧阳修所言就接触到具体问题了。”(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173页。 )二、强调“重道以充文”,把“为道”、“明道”、“履道”作为学者文士必行的修养功夫、实践内容,作为文学写作的素养底蕴。三、即重道又不轻文。圣贤之道,发之以言,载之于经,取信后世,这就体现了文的价值意义。后世文人涨于文辞之工而忽视“道”的作用,欧阳修因此强调“道”,但细察其意旨,却未尝轻文。
欧阳修的“文道关系”论形成,其来源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众多的先秦典籍,宋以前的历代文论,尤其是韩愈等人的相关论说等),当然不仅仅源自《周易》、宗于《周易》,但《周易》于此的影响却也是不可否认、不可低估的。
《周易·乾文言》中曾引孔子的话:“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是对《乾》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阐解。《文言》作为《易传》“十翼”之一,对“君子”“大人”“圣人”道德智慧的修养及其予后人的启示作了纲领性的阐说发挥,而“修辞立其诚”则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注:参看白晓梅《〈易传〉“修辞立其诚”的文学理论意义》,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 )“修辞立其诚”讲到了“诚”与“辞”的关系,强调了处于《乾卦》九三爻位的“君子”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修饰文辞以显发之的重要意义,这里的“诚”,既与“辞”相连并称,实际上就指涉文章的“质”、或文章所体现的“道”,因此,“修辞立其诚”可以视为关于文道关系的最早的、著名的论说之一,它渗透在历代文论家的论著中,成为思想源头,经学依傍。前面所引的欧阳修“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等语,与“修辞立其诚”在义理上确实能通融无碍。另外,《周易·系辞传》中,“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圣人之情见乎辞”、“其旨远,其辞文”诸语,都涉及了“辞”的因素,体现了儒家基本的文学观点,即重视内在之“情”“旨”的决定性的作用,强调“鼓天下之动”之“辞”的现实意义,而在此基础上肯定“辞”的价值。这些观点,对欧阳修也不无影响。
直接而清楚地表现出欧阳修“文道关系”论受《周易》影响的文字,是《与乐秀才第一书》(《居士外集》卷十九)中如下的一段: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
这里,欧阳修分别引用了《周易·大畜卦·彖传》、《大象传》的文辞,来说明学者文士内在道德品质修养之“刚健笃实”对于外在文字辞章表达之“辉光日新”的重要作用,也就是“重道以充文”的易理表达。联系到欧阳修《答祖择之书》(《居士外集》卷十八)中“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以及《章望之字序》(《居士集》卷四十一)中欧阳修称章望之“其洁然修乎其外,而辉然充乎其内,以发乎文辞,则又辨博放肆而无涯”等语,也都可以看出《周易》对欧阳修“文道关系”论的影响,以及他在这方面对《易》理《易》词的发挥、化用。
二
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韩琦在《祭欧阳修文》中称:“公之文章,独步当世。子长退之,伟赡闳肆,旷无拟伦,逮公始然。自唐之衰,文弱无气;降及五代,愈极颓敝;唯公振之,坐还醇粹。”又称欧阳修“事贵穷理,言无饰伪”。这是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学者对他的评价,后世的公论也大致如此。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欧阳修散文创作,扬弃了韩愈文章中过于追求新奇古奥的“险怪”之风格,他从作风平易的韩门弟子李翱入手,而不从作风奇特的皇甫是入手学韩愈(注:本文引欧阳修文,均据〔南宋〕周必大编定《欧阳文忠集》四部丛刊本,第172页。),去韩文“奇奇怪怪”的一面, 代之以既富于变化又平易畅达的形式,故宋以后的散文风气为一变,实自欧阳修始,其影响深及于后世。
与创作实践相呼应,欧阳修提出并宣扬“古文”(散文)创作应该“简而有法”、“易知易明”的主张。他在《论尹师鲁墓志铭》(《居士外集》卷二十三)这篇“创作谈”中,称尹师鲁(洙)作文“简而有法”,而他自己也正持这一主张,“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在《与张秀才第二书》(《居士外集》卷十六)中,他称古之圣贤“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是学者文士所应当效法的榜样,也就是说,今之学者为文,应该追求“易知易明”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欧阳修受《周易》的影响也是可以寻绎、辨察的。
对于垂范后世而为学者文士所效法的“圣人之道”,以及其发于言辞而传世的经书,欧阳修将其特点概括为“圣人之道,直以简,然至其曲而畅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阴阳天地人鬼事物之变化”(《韵总序》,《居士集》卷四十二),这正与他的“简而有法”、“易知易明”创作主张切合。
我们知道,欧阳修在以《易童子问》为代表的《易》学著作中,大胆疑古,指出《系辞传》等五种六篇中,颇有“繁衍丛脞”、“自相乖戾”之处(《易童子问》卷三),多有后儒“措其异说于其间”,是“伪说之乱经”(《廖氏文集序》,《居士集》卷四十三)。不过,欧阳修的疑古辨正,却也确未全然否定孔子作《易传》,即使是最受怀疑的《系辞传》,欧阳修也还承认其中保留的“圣人之言”犹可辨析,辨析以定是非的标准就是“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易童子问》卷三)。欧阳修并未怀疑《彖》、《象》为孔子所作的说法,他在《经旨·易或问》(《居士外集》卷十)中说:
卦《彖》、《象》辞常易而明,爻辞尝怪而隐,是一卦之言而异体也……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
这就肯定了《十翼》中《彖传》《象传》不但在旨意上合于圣人之道,而且文辞也合于圣人之法。这段话还寓含了其文辞“简而有法”、“易知易明”当为学者文士效法的观点。
对于欧阳修所持、所倡的“简而有法”、“易知易明”的创作主张影响最大最深,并为欧阳修凭借为经学依傍的,当属《周易·系辞传》中关于“乾坤易简”的几段文字,《易童子问·卷三》中,欧阳修正是将它们作为正面例证(亦即认为它们属于“圣人之言”)来运用的。如:
《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
其下文,欧阳修又引《系辞传》中“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等句,极为崇尚“乾坤易简”说。
以上引文中,见于《系辞上传》第一章的几句话,其含义为:乾的太初创始纯发于自然,无所艰难;坤的生成万物静承于乾阳,不须繁劳,因此“乾元”以平易为人所知,“坤元”以简约见其功能,此后,层层推阐了乾坤“易简”的道理,最后归于人事,说明人们如果能够效法这“易简”之道,就可以造就“贤人”的德业了(注:参黄寿祺,张善文著《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7~528页。 ),这是《易传》作者(欧阳修认为这几句是孔子所作的“圣人之言”)从宇宙本体、万物生成,以及社会人生等方面的哲学意义上阐说“乾坤易简”之理的,欧阳修对“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的哲理旨趣的认识、推崇,与他所倡导的文章法则之“简而有法”、“易知易明”说有着本质的联系。欧阳修体认的“乾坤易简”的哲理,正是“天下之理”亦即“道”的基本形态,那么,作为认识、反映“道”的手段、工具的文辞,也自然要取一种相应的形式,这就是“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经旨·易或问》,《居士外集·卷十》),“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试笔·六经简要说》)。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将哲学思想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文学原理相结合,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也体现在欧阳修的文学观念中。可以说,“乾坤易简”的《易》论启发、影响了欧阳修的文学观念、创作主张,而“简而有法”、“易知易明”说又在《周易》中找到了重要的经学依傍。
三
最后一部分,将考察、论述“《易》之忧患”与欧阳修所持“穷而后工”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
《周易·系辞下传》第六章中,有“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之语,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释后一句说:“考校《易》辞事类,多有悔之忧虞,故云变乱之世所陈情意也。”《系辞下传》第七章中,又有“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之语,《系辞下传》第十一章,再出现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之语,这是《易传》作者对《周易》成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作《易》者的思想情感状态的推测。因此,“《易》之忧患”、“《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为汉以来的历代《易》学家所共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即以“文王拘而演《周易》”与其它几个先秦时期圣贤发愤著述的事例并列。
前面已论及欧阳修认为《系辞传》非出于孔子一人之手,但其中也保留了“圣人之言”,在《经旨·易或问》(《居士外集》卷十)中,欧阳修明确地指出:
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文王与纣之事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欤?”(按:欧阳修此处引文,与《周易》原文略有字句上差异)若此者,圣人之言也。
肯定这是“圣人之言”,自然也就认同于“《易》为忧患之书”的观点。“《易》之忧患”的认识,对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它对欧阳修文学观念中“穷而后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涉及到对文学创作主体心理状态和情感活动情况的认识,它的确包含着深刻的启示。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教授曾经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痛苦”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特殊作用,他说:“痛苦作为一种最富有活性的内在信息,它最能唤醒或激活情绪记忆和无意识,因为痛苦中枢占优势,摄入的信息量多,经过能量转换的中介作用,再次释放时,比较容易达到激活情绪记忆和无意识的阀限。”所以,它“为作家心理素质的最优化建构准备了有利条件”(注:孙绍振著《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30页。)。当然,生活在距今近一千年前的欧阳修,不可能有如此“现代”的表述,但他对文学创作过程中主体心理、情感的观察、体验、概括而得出的结论,还是相当精当的。在《梅圣俞诗集序》(《居士集》卷四十三)中,欧阳修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所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在《薛简萧公文集序》(《居士集》卷四十四)中,欧阳修说:
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事,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以上两段引文,前者就诗歌创作而言,后者就散文创作而论,都解说了文学创作中“穷而后工”、“穷者易工”的现象。欧阳修的这一观念,从直接的承续关系上看,是受到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中“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悉,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之语,与欧阳修之文加以参照,其间的承续关系是相当明显的。若往前推去,“《易》之忧患”也是影响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源头之一。在《送杨真序》(《居士集》卷四十二)中,欧阳修就提到了“《易》之忧患”:
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心深,而纯古淡激动,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
当然,这段话,欧阳修是从“琴之为技”来谈的,但从其文名中引经典为喻,以及文学与艺术在特性上多相通融的方面上看,这也就是提到“《易》之忧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如果我们再往更广泛的方面联系,那么,欧阳修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提到的读班固《汉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三代秦汉以来著述甚众而传世者少,“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以及欧阳修在其名篇《秋声赋》里所抒发的“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的深沉的人生感慨,故不无忧患之情蕴含其中。的确,忧患之情之思,可能使人颓废、消沉、遁世无为,但也可能使人警醒奋发、努力进取,以深沉博大的关怀,去直面现实的忧患,而争取“不朽而存”的功业——其中,包括了文学创作的“立言”的不朽,这也正是“《易》为忧患之书”说的深刻的启示。从欧阳修的《易》思想中突显的“修吾人事而已”(《经旨·易或问》,《居士外集》卷十)这点上看,“《易》之忧患”给欧阳修的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启示,更多的是积极有益的因素。
可以这么说:“《易》为忧患之书”、“《易》之忧患”之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影响、启示,既有具体表述上的触发,而更多的是形成了一种广大的深沉的思想背景,促其深思警醒。
标签:欧阳修论文; 易经论文; 文化论文; 宋朝论文; 读书论文; 居士集论文; 系辞传论文; 易童子问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