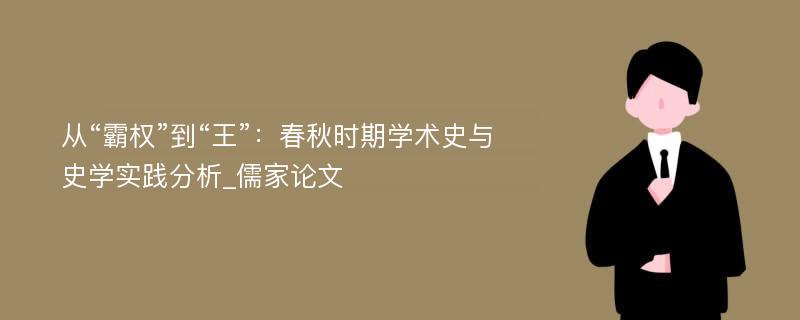
由“霸”而“王”:《呂氏春秋》的學術史分析與歷史實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學術史论文,與歷史實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班固《漢書·藝文志》將《呂氏春秋》作爲雜家的代表作,其特點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即爲了“王治”而博采百家之長而自成體系。当然,諸子大都有自己的“王治”,儒、墨、道、法,陰陽家均然,儒、墨、陰陽家尤其以“王治”之說擅長。但是,它們的“王治”大都存在於過去的理想中而缺少現實性,而《呂氏春秋》的“王治”則面對現實:根據秦國的歷史和現實實踐,論述即將到來的大秦帝國的治國方針和統治藍圖。遺憾的是,呂不韋的這一套理論和嬴政的治國理念不合,隨著嬴政的親政、呂不韋的自殺而束之高閣。這是古今學者的共同看法,確有其歷史基礎和學理支持。①但是,僅此是不够的,因爲人們普遍忽略了《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的學術基礎和對秦朝政治實踐的影響。這不僅關係到對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文化政策及其實踐的認識,也關係到《呂氏春秋》對秦朝政治實踐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分析。
本文所說的學術基礎,包含兩個方面的内容:一是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的政治實踐與諸子之學的關係,二是六國士人對秦態度的轉變問題。之所以討論這兩個問題,是因爲《呂氏春秋》的問世,和呂不韋的學術視野、政治識見、政治地位固然有關,但是,與商鞅變法以來的文化政策、諸子之學與秦國政治實踐、東方士人對秦國認識的轉變以及諸子之學的共同的政治追求,都有著深刻的關係,所有這一切共同構成了《呂氏春秋》的成書基礎。關於諸子之學的政治共性,即實現社會秩序化、天下一統,這是學界共識,不予重複。對於商鞅變法以來的文化政策、諸子之學與秦國的政治實踐、東方士人對秦國認識的轉變,則是有待於深入討論。本文先從這個問題說起。
一
一般認爲,秦爲後進之國,在先秦諸子争鳴過程中是文化沙漠,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②個中原因,就包含了東方各國對秦國文化落後的蔑視。商鞅變法以後,秦一躍而爲七雄之首,雖然兵强馬壯,但在思想上法家獨尊,價值上見利忘義,被六國士人所排斥,在文化上視之爲“夷狄”,在政治上視之爲“虎狼”。這種評價一直延續到漢代,也影響到現代學者對秦文化的認識。所以,本文首先分析對這一歷史現象,然後纔能把握商鞅變法以後秦國的學術走向。
從文化層面以“夷狄”視秦者以《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爲代表。《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敗秦師與殽。”《公羊傅》云:“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③《穀梁傳》云:“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④《春秋》昭公五年記“秦伯卒”。《公羊傳》謂:“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⑤按諸史傳,孔子編《春秋》,謂“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敗秦師與殽”、“秦伯卒”云云,不過寫實而已,不存在公羊氏和穀梁氏所說的“夷秦”或“狄秦”的問題,所謂“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云云,純粹是公羊氏和穀梁氏的附會,這些前賢早已指出,這裏無需多論。⑥但是,這反映了戰國中後期以儒家學派爲代表的東方士人對秦人和秦國在文化上的排斥。儘管這種排斥是以秦國後進爲歷史基礎的,因爲西周時代的秦人被周王室遷之於西北邊陲,以牧馬爲事,其生産和生活帶有一定的戎狄色彩。但是,今天我們不能繼續沿用古人的眼光看待秦雜戎狄之俗的問題。因爲反觀東方各國的歷史,無論是齊國、晋國、燕國,還是吳國、楚國等等,在其建國和發展過程中,無不雜糅了當地原居民的文化,衡以後來的夷夏之防,他們無一不沾染著戎狄或者蠻夷之俗。秦人在商朝的地位本來高於周人,貴爲諸侯,商亡之後纔被貶爲附庸,但在秦人的心目中並未忘記昔日的輝煌而積極東進,大力吸收周人的禮樂文化,春秋時代早已贏得諸侯們的普遍尊敬,特別是在秦穆公的時代,東方各國並不因爲秦穆公稱霸西戎而視秦爲夷狄。其時之秦國和晋、楚、齊等諸侯大國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是相同的,並不存在後來意義上的夷、夏之防。⑦祇是到了戰國時代,東方各國先期完成了社會結構的轉型,而秦還在歷史傳統之中艱難跋涉,國力衰微,纔爲東方各國所輕視,而“夷翟視之”。這兒的“夷翟遇之”並不是因爲此時之秦國保留著多少戎狄文化習俗,而是指失去了春秋時代霸主的輝煌,處於民貧國弱、落後挨打的政治、軍事地位而言。若從習俗上看,一定要把不符合儒家禮樂文明的習俗稱之爲戎狄蠻夷之俗的話,衹要稍稍對《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對先秦風俗文化的叙述略加比較就不難得知:有戎狄之俗者絕非秦地,無論是燕趙大地,還是齊魯之邦,無不如此,更不要說楚國和吳越地區了。⑧所以,公羊氏和穀梁氏用的是戰國時代的思想觀念穿鑿孔子思想,因爲政治上的敵視而在文化上歧視和貶低秦人與秦國。
與公羊、穀梁氏在文化上將秦“夷狄”化同步的,是六國策士出於政治、軍事目的的將秦“虎狼”化。在《戰國策》中有集中的記述。如:
《戰國策·西周策》遊騰謂楚王:“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⑨
《楚策一》蘇秦說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楚威王以蘇秦之語爲然,謂:“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⑩
《魏策一》蘇子說魏王云:“然橫人謀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11)
《魏策三》朱己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12)
《趙策三》虞卿謂趙王:“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益。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13)
按諸史實,春秋時即有以“虎狼”喻國喻人者。如《左轉》文公十三年,士會對秦繆公說:“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14)這兒的“虎狼”是指晋國君臣用心歹毒而不講信義。《左轉》哀公六年載齊國國氏、高氏掌權,陳乞僞事國氏、高氏,對國氏、高氏說:“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15)這兒的“彼,虎狼也”指的是其他幾位不滿國氏、高氏專權的大夫,謂他們心地殘忍,爲了權力,不擇手段。《左傳》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勸齊桓公出兵救邢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16)這兒的“豺狼”是貪得無厭的意思,也是史傳上第一次把貪得無厭和“戎狄”聯繫在一起,意味著貪得無厭是戎狄的自然屬性,帶有一定的部族歧視成分在內。
將策士之詞和《左傳》諸語稍加比較就不難看出,策士們稱秦馬虎狼,包含了兩重意思:一方面謂秦貪得無厭,必欲兼併天下而後快;另一方面說秦的虎狼之心是因爲其文化落後,“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不過,祇要從歷史的角度,將秦國和東方各國稍作比較,我們就不難知道,此時的秦國早已不存在什麽與“戎狄同俗”的問題,就像春秋時代的齊、晋諸國曾經被稱爲“虎狼”一樣,此時的東方各國的政治實踐也不存在什麽“禮義德行”的原則,如果國力强大,一樣地貪得無厭。所謂的“秦與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云云,不過是策士們爲了合縱的主張援引儒家的公羊、穀梁氏之說,將秦國“虎狼化”而已。
儘管公羊氏和穀梁氏之“夷狄視秦”是出於學派的執見,策士將秦“虎狼”化是對秦國兼併戰争的誇張,但是,對社會輿論的影響不容小号码覷,特別是在漢初興起的過秦思潮中,隨著對秦政的批評和儒學影響的擴大,人們不約而同地沿著公羊、穀梁氏和策士們的評價作爲過秦的思想原點並予以泛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莫過於賈誼和司馬遷了。賈誼在《陳政事疏》中云:
商君遺禮儀,棄仁恩,並心於進去,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得色;母取箕掃帚,立而啐語。抱哺其子。與公姘居;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17)
賈誼藉古諷今,所說“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得色;母取箕掃帚,立而啐語。抱哺其子。與公姘居;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云云,決非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的歷史,而是站在儒家禮樂制度立場上,以批評秦政爲名,對戰國至西漢初期而以西漢初期爲主的社會風俗的批評,而歸因於商鞅變法以來的秦制,這不能作爲判定秦國歷史存在的依據。如果說“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即强制分居制度是商鞅推行的話,那麽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得色;母取箕掃帚,立而啐語。抱哺其子。與公姘居;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云云就不是秦國的問題了。這些,祇要看看《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關於各地風俗的叙述就不難明白。因此之故,秦始皇統一之後,鑒於六國風俗不醇,纔大力“匡飭异俗”,表彰節義。(18)
司馬遷是《春秋》公羊學傳人,其價值觀受儒家影響較大,在編纂《史記》過程中難免受到公羊派的影響,對秦人、秦國和秦朝的制度、文化的評價帶有一定的價值傾向性,在《史記·六國年表》序中評論說: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亹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併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19)
司馬遷是站在政治立場上說“秦雜戎翟之俗”的,理由是秦立國伊始就實行祇有周天子纔有資格使用的祭天典禮;謂“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則立足於軍事。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司馬遷的評判顯然是春秋公羊學的延伸,並進一步的歷史化,是對《公羊傳》“夷狄視秦”的歷史論證。這種評判,反映了六國部分士人對秦國文化和政治的排斥,也是我們長期以來分析秦文化特點的歷史依據,現代學者們將重實效、輕言談,重事功作爲秦文化特點並概括爲功利主義價值觀的時候,依然可以看到公羊、穀梁和戰國策士們的對秦人和秦政評判的史影。(20)
二
然而,當我們跳出長期以來形成的思維定勢和固有看法,用歷史的眼光考察秦國文化政策及其實踐的時候,我們又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在東方各國的部分學者和策士們視秦爲夷狄或虎狼的時候,另有部分學者紛紛來到秦國,在秦國把自己的理想變成了現實。商鞅入秦並使法家學說在秦生根開花自不待言,就在商鞅變法以後,入秦的六國士人也不絕如縷。在秦國的政壇上,無論縱橫捭闔的外交家,還是一般的技術官僚,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六國。如人們津津樂道的秦重用客卿就是明證,“客卿”本身就是六國士人的一部分。(21)如果說秦國所用的客卿屬於權謀之士,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士人的話,那麽,諸子傳人在秦國大顯身手更是所在多有。活躍於秦國外交舞臺的就是縱橫家者流,張義是最典型的代表,無需多說。曾經和儒家並列爲顯學的墨家起碼有一部分即“從事”一派在秦惠王時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呂氏春秋》中《去宥》和《去私》所記載的兩個故事都反映了這一事實。《去宥》云: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悅,遂辭而行。(22)
唐姑果害怕謝子取代自己在秦惠王心目中的地位,一方面針對惠王不喜歡“辯士”的特點,謂謝子爲“東方之辯士”(應屬於墨辨一派);另一方面利用惠王和“少主”即太子間的矛盾,使惠王先入爲主,排斥謝子,不去分析謝子所說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謝子主觀上誠心爲秦效力,不料遭受冷遇,祇好辭行。《去私》云:
墨者有钜子腹醇,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醇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死,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醇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23)
依法行事,是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政治的基本原則。腹醇之子殺人,如何量刑,自有法律決定。而惠王竟然改變法律,以腹醇“年長,非有他子”爲由置法律於不顧,而“令吏弗誅”,可見腹醇和惠王關係的不一般。出乎秦惠王意料的是腹醇堅守墨者之法還是將兒子處死了。钜子是墨者集團領袖,腹醇身爲钜子,追隨其左右的不在少數,這些人自然因爲腹醇和惠王關係而發揮著各自的作用,腹醇之堅持用墨者之法處死親生兒子,就是爲了維護墨者之法的嚴肅性。腹醇得到惠王的信任,憑藉的是自己的真才實學和人品。唐姑果是否是钜子,不敢妄斷,但是憑藉其和惠王的關係,決非一介書生可以比擬,亦當有其追隨者。透過這兩個故事,可以反映出墨者集團在秦國政壇上影響力的一斑。
墨家傳人在泰國政壇上的作爲因爲資料缺失難知其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作用不容低估,起碼爲秦國的軍事建設做山了突出貢獻。這不僅體現在具體的軍事技術的應用上,而且體現在理論著述上。蒙文通先生在《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一文中曾將《墨子·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和《商君書·兵守》的內容比較以後指出,《備城門》以下各篇是泰國墨者所作,明確謂韓非所說的“墨離爲三”是指南方之墨、東方之墨和秦之墨。(24)墨者集團除了按照地域分爲這三大集團以外,按其學術特點則可以分爲說書、名辨、事功三大集團,活躍於秦國的墨者屬於事功集團,最擅長的是手工業生産和管理。雲夢秦律的面世,說明蒙說之不誣,比較《備城門》以下各篇,在軍令規定、職官名稱等方面和秦律有著明顯的一致性;在計量制度、語詞行文和秦律也有著明顯的相似性,爲《墨子·備城門》以下各篇爲秦國墨者所作提供了直接的證據。(25)而雲夢秦律中各項生産管理的標準嚴格細密,都是具體的執行標準,秦國墨者很可能參與了這些法律的制定與執行。而上舉腹醇與秦惠王的故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秦律與墨者之法在理路上的一致性。如果說雲夢秦律問世之前,人們對《墨子·備城門》以下各篇是否秦國墨者所作還存有疑問的話,雲夢秦律問世以後,這個疑案可以定讞了。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墨者在秦國的影響,也啓示著人們重新認識商鞅變法之後秦國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生態。
秦國對諸子之學的采擇以及諸子對秦的態度,在荀子對秦國政治的評價中有著直接的體現。秦昭王末年,荀子入秦,經過一番考察之後對秦國地理形勝、政風民情有過精闢的概括。《荀子·强國》篇云:
應侯問孫(荀)卿子曰:“入秦何所見?”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偲(言字旁)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懸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26)
荀子這段話有三方面內容:一是對秦國地理形勢的描述,二是對秦國政風民情的讚賞,三是對秦國政治得失的分析。無論是對自然形勝的描述還是對政風民情的讚賞,都是以考察爲基礎的,在這裏不予多說。我們注意的是荀子分析秦政之後對“王”與“霸”的理論概括,即“粹而王,駁而霸”,意謂秦國雖然取得了霸業,但距離王業還有很大差距,原因就在於“無儒”。如果從形式邏輯的層面分析,在荀子眼中,除了儒學之外,其他學說在秦國都有實踐。楊瓊注“粹而王”謂“全用儒道”,是不符合荀子本意的。“其殆無儒”是缺少儒學,而不是純用儒學。所謂“粹而王”是荀子理想,指能聚集各家精華以治國者才能成就聖王之業,“駁而霸”則是對諸子百家雜而用之,而忽略了所采納的內容是否爲精華、所采納內容內在理路是否一致。秦國屬於後者,是“駁而霸”,缺少儒道而未成王業。不過,要特別指出的是,荀子所說的“儒”自成體系,和孔、孟之儒有著巨大的差异、這除了人性論和孔、孟异趣之外,其歷史觀,哲學觀、政治觀、倫理觀都自成一派,其基本特點是隆禮重法、兼釆各家,立足於現實社會發展、放眼未來,無輪是理想的“粹而王”之“粹”還是現實的“駁而霸”之“駁”,都是兼具各家學說而用之,荀子是爲了王業而兼具各家,秦國是爲了霸業雜而用之。這種雜而用之,是秦國政治現實,也是《呂氏春秋》誕生於秦國的政治基礎。
和荀子對秦政評價相比,荀子入秦這件事情本身更值得我們注意:這標誌著東方士人——特別是儒家傳人起碼是部分儒家傳人改變了對秦人、秦政在文化上的歧視和政治上的敵視態度,表明了上舉春秋公羊學派和穀梁學派以及策士們的宣傳在士人心目中的影響在弱化。
衆所周知,荀子曾三爲稷下學宮祭酒,而稷下學宮是六國士人的聚集地,是戰國後期六國的文化中心,荀子三爲稷下學宮祭酒,起碼是六國士人的學術領袖。那麽,荀子入秦就不能簡單地看做荀子個人遊學的隨機事件這麽簡單了。因爲,自商鞅變法以後,秦排斥言談遊說之士——尤其是儒生,以法治國——無論親疏遠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上兼併戰争的殘酷性,在保持親親尊尊傳統的六國貴族和部分士人的心目中都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對秦的崛起程度不同地持有排斥和敵視態度,上舉視秦爲夷狄或者爲虎狼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這種事實的存在。六國士人遂托古言事、藉理想中的聖王之治諷喻現實之不道,表達自己的訴求,希望君主們能主動師從自己,學習治國之道,不治而議論的稷下學宮因爲齊國文化政策的寬鬆應運而生。荀子身爲祭酒,其言談舉止,自然受到稷下諸公的關注,入秦考察這樣的大事,決非荀子個人的心血來潮,而是六國士人對秦態度轉變的風嚮標:標誌著六國士人起碼是一部分對秦國政治、文化由排斥到認同的轉變,起碼體現了部分六國士人對秦國成功的好奇和認同。荀子對秦國政風民俗的上述評論,儘管和王者之治相去甚遠,但在當時七國中無疑是最優秀的:吏治廉潔、學風醇厚,民生富足而穩定。如果說現實與理想有距離的話,比較之下,秦國的距離最小,六國距離都遠大於秦國,士人的理想起碼部分地在秦國得到了實現。從邏輯上判斷,這怕不是荀子個人認識,而是有著一定的代表性——荀子入秦,尤其是像荀子這樣學術領袖,按照當時學者游學習慣,並非隻身前往,應該有相當數量的弟子或同門同行,荀子對秦政的評價代表了同行者的看法。荀子返回東方以後,自然將所見所聞帶回東方,必將進一步影響東方士人對秦的態度,特別是儒生的態度。儘管荀子學說自成體系,但其政治倫理主張打的仍是儒家旗號,可以說荀子首先是當時儒者群體的領袖,然後纔是東方士人的學術領袖,韓非纔將荀子列爲儒家八派之一,所以,荀子對秦政的評價,代表了部分儒者對秦政的看法。
若從歷史實踐的維度考察戰國後期諸子思想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儘管各家都試圖在政治上程度不同地争取國家權力的支持,把自己的主張變成現實,士人在東方各國都得到相應的尊敬,而以齊國最爲突出。但是,他們的主張並没有因爲自身受到足够的尊敬而變成現實。稷下學宮的設立,學者們享受著列大夫的待遇,可以自由地著書立說,但僅僅是“不治而議論”,其主張並没有變成現實。相反,他們的主張在秦國卻得到了一定的實現。比如,孟子“仁政”的核心內容——治民之産,使民有恒産而後有恒心,也就是保證農民每家每戶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以保證農民養老撫幼的生活需求,這個主張祇有在秦國真正地變成現實。商鞅變法以後實行的國家授田制度儘管在學理上和孟子主張的井田制差异巨大,但是孟子的經濟主張起碼是因爲授田制度的普遍實行部分地實現了。主張授田制度的不僅僅是孟子一派,其他儒家各派以及其他學派也都有類似主張,祇是具體分配方法有別而已。如《周禮·地官·大司徒》、《小司徒》、《遂人》、《考工記》以及銀雀山漢墓竹簡關於土地制度的種種設計,本質上都是授田制度。這些設計並非完成於一人一時或某一個學派,也並非完全是嚮壁之作(27),有一定的歷史和現實基礎,在各國都程度不同地實行過,但是真正地普遍實行並收到良好效果的則是在秦國。(28)也就是說,商鞅變法所推行的授田制度,從內容上來說,並非是法家的創造,而是各家尤其是儒家的共同主張,所不同的是,商鞅用法律手段把些主張變成普遍的現實而已,東方各國雖然也實行過授田制,但遠不如秦國那樣公開、公平和普遍。
土地制度如此,其他內容亦然,就以儒家、墨家的忠、孝等倫理主張來說,同樣是秦國政治生活的內容,所不同的是將其法律化而已。雲夢睡虎地秦律對不孝罪的懲處、《爲吏之道》關於政治道德的規範,所體現的倫理主張,和儒家、墨家等等學派是共同的。本來商鞅就“王道”、“帝道”、“霸道”兼通,秦孝公采納其“霸道”主張以後而以法律手段取信於民、推行新政,其新政內容並非都是學界所理解的法家創造,而是來自於各家各派的設計,比如最受後世思想家所詬病的什伍連坐制度就不是商鞅的發明,《管子》中《立政》、《度地》、《禁藏》各篇以及《褐冠子》、《逸周書》等文獻對什伍制度都有記載,而以《周禮》所述最爲詳細。《周禮·小司徒·族師》規定族師的職責是“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比長的職責是“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袤則相及”。這“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有罪奇袤則相及”就是商鞅變法“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的濫觴,二者起碼有相通之處。司馬遷說商鞅變法“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並未說明什伍連坐制度是商鞅的創造,而是說是商鞅在秦把這套制度嚴格化、法律化而已。(29)
從學派劃分,儒家重禮,法家重法,但是從統治的目的來看,禮與法都是手段,祇要有利於富國强兵、調動農民積極性,手段是可以改變的。《商君書·更法》云“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固;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站在法家立場說的,在儒家看來,禮才是愛民的,這裏不去詳說。現在要說的是,商鞅立法推行新政,在主觀上是以“强國”。“利民”爲目標的,其法律規定的內容,祇要有利於“强國”、“利民”,統統爲我所用,而不局限於哪個學派。東方學者出於學派的隔閡和對於自己理想的堅守,對秦政持懷疑和排斥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們著書立說、課徒講學、相互辯難的目的畢竟是爲了現實政治的建設,當他們走出自己的思想空間,發現秦國的法律制度有許多正是自己所主張的內容以後,他們自然地改變對秦國的態度。荀子之隆禮重法,就是這一趨勢的典型體現。這是荀子入秦的思想基礎,也是《呂氏春秋》編纂的學術基礎。
三
明白了上述諸子與秦國政治的關係之後,我們對呂不韋編纂《呂氏春秋》的學術意義和政治意義也就會有新的認識。
要重新認識呂不韋編纂《呂氏春秋》的學術意義和政治意義,要先從呂不韋養士說起。《史記·呂不韋列傳》云: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遍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而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30)
後世學者大都據此認爲呂不韋養士是效法四公子之舉,編纂《呂氏春秋》是爲了和荀子之徒一争高下,不過是奇計買國、沽名釣譽的組成部分而已。從文本解讀的層面看,這樣理解有其道理,但是,若歷史主義地看問題,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够的。祇要稍加比較,我們就不難明白呂不韋養士的動機和品位與四公子都有著巨大差別。
齊、楚、趟、魏的軍政大權都由宗室控制,如齊國從上到下均爲田氏掌權,楚國則是屈、景、昭、宣諸氏世襲執政,趙國和魏國也是公子公孫操控朝政,宗室之間權力傾軋嚴重,四公子身爲貴族和權臣,是爲了壟斷權力而招來賓客。《史記·春申君列傳》謂春申君養士的背景和原因時說“是時齊有孟嘗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31)這“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八個字道出了孟嘗君、信陵君、春申君的養士動機:對內是爲了鞏固個人權勢,對外是爲了擴大名譽,目的還是爲了鞏固個人權勢。所謂“輔國持權”是指將權力掌握在個人手中,由自己輔佐國家。賓客們是其個人的智囊團,站在個人的立場、出謀劃策,爲鞏固和擴大個人權力服務,而不是站在國家立場,爲了强大國家力量而獻計獻策。唯此之故,這些賓客們除了影響各國的權力格局外,對各國政治並没有什麽改良效應,隨著四公子的逝去,他們也就銷聲匿迹了。呂不韋則是站在國家立場上招來賓客,養士的原因是鑒於四公子名噪一時,感到“以秦之强,羞不如”而“招致士”的,“招致士”的目的是爲秦争光,而不是起碼不完全是爲了擴大個人權力。將《呂氏春秋》懸於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這當然有著自我標榜的成分在內,古往今來的秦國歷代君臣,有誰能夠使天下群賢畢至、編出如此的煌煌巨著?祇有我呂不韋!但是,我們若僅限於此,則大大低估了呂不韋養士和編纂《呂氏春秋》的意義。
因爲呂不韋養士的目的不完全是爲了個人利益,儘管士人們是因爲自己而來,但並不把賓客作爲自己的私産,不以個人利益取捨士人,而是兼收並蓄,量才使用,充分發揮個人才幹。以出仕任官而言,李斯、甘羅等重臣自不待言,普通官僚也不在少數。呂不韋自殺以後,秦王政禁止官員前往吊唁,下詔云:“其舍人臨者(指私自前往吊唁呂不韋的舍人),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毋奪爵。”(32)這起碼間接說明呂不韋舍人出仕秦廷的不在少數,有的做到了六百石以上的高官,有的是五百石以下的普通官吏;既有來自東方的,也有秦國本土人。秦國對官員有著嚴格的考課制度,凡考課不合格或違法官員不僅官員本人到懲處,推薦的人也要負連帶責任,這些出自呂不韋門下的“舍人”没有一定的真才實學是難以出仕的,一定要有相應的能力和才幹。對於那些不能或不願意任官治事而適合或願意坐而論道的人來說,呂不韋則讓他們在議定的主題下著書立說,《呂氏春秋》就是這樣問世的。推薦舍人出仕,是爲秦國官僚隊伍輸入新的血液,而編纂《呂氏春秋》懸於市門之上,則是向天下宣佈,學術中心在秦國,要知道“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請到秦國來,能“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者,唯秦而已!無論是自我標榜,還是宣示天下,客觀上都有利於秦國的進一步發展。
無論是從組織結構還是思想體系來看,《呂氏春秋》都有著完整的思想體系,明確的政治核心。因其綜合諸子,對諸子都有吸收和批判,多少則各有不同,無法歸結於哪一家,故以“雜家”名之,“雜”是因爲兼收並蓄,雜而成“家”則是因爲有完整明晰的思想邏輯體系。關於《呂氏春秋》思想體系的具體內容,本文不予討論,這裏要指出的是《呂氏春秋》自成體系的歷史基礎——由“霸”到“王”的歷史現實及其對諸子理論主張的影響,以便把握其歷史實踐的作用。
衆所周知,自從平王東遷雒邑,各諸侯即展開了規模不等,形式各异的争霸活動,社會結構變遷劇烈,社會制度、思想觀念都發生了天翻地覆式的變化。但是,無論霸業結局如何,社會各階層都飽受戰争之苦,尤其以普通民衆的苦難最爲深重。如何擺脫戰争苦難,使社會和諧有序運行,遂成爲社會各階層共同關心的話題,諸子們就是在這一歷史基礎上提出自己見解的,小國寡民、禮樂秩序、仁政愛民、聖賢治國,等等,都是爲了這一目的。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引《易大傳》說“天下一慮而百始,殊途而同歸”內涵是包括了諸子的這一政治目的在內的。(33)若歷史地看問題,諸子理論無論差异如何,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以西周統一時代作爲考量現時的出發點,或眼睛向後,抨擊春秋以來的“霸者”之政;或眼睛向前,分析“霸者”之政的合理性並爲之作出具體的制度設計,或者兼而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們的共同點,則都希望統一,王權獨尊、上下有序、尊卑有等,僅僅是具體理論和方式不同而已,從孔子的周游列國,老子的冷眼旁觀,墨子的身體力行,到孟子的奔走呼號,再到稷下諸公的坐而論道,以及荀子入秦的現實考察,等等,都是在思考宣傳實現其統一的主張和途徑。呂不韋執掌秦政以後,秦統一天下指日可待,那麽,統一之後的政治模式不僅關乎諸子學說的歷史命運,更關乎著士人的生存,他們不約而同地將統一之後政治思想、統治模式作爲自己思想的原點:一方面承認、驚歎秦自商鞅變法以來所取得的霸業,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思想主張能够在在即將到來的統一帝國中發揮效用,於是不約而同地將統一帝國的政治模式規劃爲“王者之政”,希望帝國統治者真正地聖王合一——霸業轉化王業,霸主轉變爲聖王。那麽,怎樣才是真正的王者?王者如何治理臣民?就是呂不韋編纂《呂氏春秋》要說明的問題。
先秦諸子各有各的“王業”與“王者”,在争鳴過程中,雖然彼此吸納,但依然畛域分明。呂不韋的高明之處就在於高屋建瓴式地把握了各家思想的政治共同點,同時把握了由霸而王的歷史轉折。儘管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呂不韋還不可能具體明確統一天下和治理天下在制度、政策方面的區別,但是在思想上已經意識到了“霸業”與“王業”有別。商鞅變法時就有王道、帝道、霸道的具體內容,秦孝公選擇了“霸道”,秦國完成了霸業,荀子入秦對政治進行了具體的分析,指出秦國雖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懸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認爲秦國的霸業雖然前無古人,但距離王者之功名“倜倜然其不及遠矣”,原因是“無儒”。荀子是站在自身立場作出“無儒”判斷的,用的也是疑問語氣,除了“無儒”之外,秦國要實現王者之業還要有其他思想內容,不同學術背景的人會給出不同回答。對此,呂不韋有著清醒的認識。而荀子入秦這件事告訴呂不韋,六國士人在關注秦國政治走向,在思考未來“王者”的指導思想和運作模式,這就增添了呂不韋養士以效力於秦的信心。關於《呂氏春秋》中“王者之政”和“王者之業”的內容十分豐富,在權力運作上,集中在君道無爲、臣道有爲、尊賢重道、仁政愛民幾個方面,就此而言,各家各派都有其獨到之處,都可以爲我所用。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呂不韋不是思想家,對各家各派學說的闡釋固然不能和諸子相比,但是對諸子學說政治功能的把握,確實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上。
然而,呂不韋清楚地知道,王者自有王者的主張,自己的主張能否變成現實,取決於秦王嬴政也就是後來的秦始皇的認識(嬴政統一六國之後更名始皇,本文按照歷史順序,統一之前稱嬴政,統一之後稱始皇)。呂不韋對此持的是樂觀的態度:憑藉自己的輔佐之功和仲父地位,嬴政是會接受自己思想主張的,所以在《呂氏春秋·序意》中不無自得地藉回答“良人請問十二紀”說:“嘗得學黄帝之所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圓)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34)顯然,呂不韋以黄帝自居,希望嬴政像顓頊師從黄帝那樣接受自己學說。但是,黄帝、顓頊畢竟是存在於傳說中的人物,嬴政則是現實中的君王,現實和理想之間畢竟距離遙遠,嬴政所經歷的宮廷争鬥、所看到的有關人性本質的種種分析,更主要的是專制權力的排他性,都決定了呂不韋的悲劇結局,嬴政不會分權給臣下,而是要集權於一人。所以嬴政親政伊始,就意味著呂不韋政治生命的結束,先是收回呂不韋相權,後將呂不韋貶逐而死。
然而,嬴政和呂不韋之間的矛盾儘管有著指導思想的不同,但更主要的還是現實權力之争,所以,呂不韋死後,嬴政並没有將呂不韋的作爲全盤否定,已入仕的呂不韋舍人祇要没有私自吊唁呂不韋者,繼續留任;六國士人祇要願意即繼續在秦廷效力。對於《呂氏春秋》,嬴政也没有束之高閣,而是有選擇地采納,並以帝王貫穿於秦政之中。
四
秦始皇對《呂氏春秋》的采擇及其對秦朝歷史實踐的影響,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被用作聖化秦始皇、聖化秦政提供政治理論依據,二是爲秦朝統治的正義性提供了神學工具。
自從商鞅變法,秦以“霸道”治國以後,“王道”、“帝道”的理論在秦國朝野即失去市場,以是古非今、道高於勢自居的以儒生爲主體的士人在秦失去了政治空間。這是戰國後期東方士人繼續以夷狄視秦和將秦國虎狼化的深層原因,即使那些對在秦制和秦政没有偏見的思想家,也絕不認爲秦制、秦政與聖王之功有什麽關係。呂不韋開門輯客之後,東方士人才紛紛入秦,獻計獻策,均欲以己所學補救秦政之不足,《呂氏春秋》書中的聖王之道就是各家各派集體智慧的結晶。但是,在秦始皇心目中,秦朝已經實現了空前的大一統,已經前無古人,没有任何一位聖王的功業能與之相比,那麽就不應該削足適履式樣地改變取得這空前偉業的制度、政策去適應那些書生們設計的所謂“聖王之政、聖王之制”,正確的做法應該爲現實功業披上聖王的外衣,說明現實的神聖性。秦始皇在《呂氏春秋》中看到了呂不韋及其士人們對聖王功業的追求和期盼,也看到了秦國歷史實踐與這些聖王功業的距離,遂接過了聖王的名稱,而置換其內容,目的是要使天下人明白,秦朝功業纔是王者之業,秦朝制度纔是王者制度,除此之外,没有什麽王者之業!“皇帝”名號的誕生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
關於皇帝名稱的誕生,爲了說明問題,不得不贅引人所周知的史實。《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詔云:
“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35)
丞相、禦史、廷尉、諸博士都是精通古今的學問大家,他們瞭解主子們反復論說的三皇五帝的道德與事功,他們認爲秦始皇功德超過了五帝,而上名號爲“泰皇”。而秦始皇則認爲自己不僅超過五帝,也超越了三皇,而使用“皇帝”名號。三皇五帝是先秦諸子討論的重要話題,標誌著當時學者對自身歷史反思的自覺和對現實經驗的批判,越是向遠古追溯,越表明對現實經驗的懷疑,把自己的理想寄托於古人。李斯和博士們認爲秦始皇功高五帝、德比三皇,固然有阿諛成分在內,但是若以事功衡量,又有著相應的現實基礎。秦始皇認爲自己功固然高於五帝,德也超越三皇,體現了秦始皇對歷史和現實關係的認識。這些三皇五帝的學說在呂不韋入秦之前在秦國是没有市場的,是呂不韋主政以後纔在秦國流行開來,包含著對秦國“霸道”的批判。李斯和博士們則把秦始皇“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視爲三皇五帝之政,表明了博士們對秦朝功業的認同和對三皇五帝之治的歷史內涵的改變。
正式在這一基礎之上,秦始皇纔不遺餘力地宣傳秦政、秦法、秦政就是聖王之法、聖王之政、聖王之制。這是秦始皇屨屨出巡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刻辭中反復强調的就是這個內容,如:
“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成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
“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
“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强。”
“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
“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36)
這些記載,爲學界所熟知,茲不贅舉。由此可見,在秦始皇心目中,“朕即聖王”,朕所實行的一切法律制度都是聖王之法、聖王之制,任何人祇要俯首帖耳、各司其職、各盡其務就行了。這種聖王理論的內容和呂不韋及其《呂氏春秋》固然大异其趣,但是崇聖、造聖的思潮無疑來自於呂不韋及其《呂氏春秋》。
在各種思想學說中,就對秦朝政治運作的影響而言,應以陰陽五行學派的五德終始說最爲突出:這就是在聖化的基礎上,把秦始皇及其統治制度和方式神聖化,必然化。《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37)
《史記·封禪書》云:
秦始皇既併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黃龍地嬪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38)
這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資料,也是秦法急苛的思想根源。但是人們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秦始皇的“五德終始之傅”與《呂氏春秋》的關係。
衆所周知,五德終始說是鄒衍利用流傳於海岱燕齊地區的陰陽五行學說宣傳其政治主張的産物,其政治內涵是“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39),屬於儒家思孟學派的。這在秦國本來是没有生存空間的,是隨著呂不韋養士傳入秦國的,《呂氏春秋》接受陰陽五行學說,最明顯地體現在十二紀上,同時也接受了五德終始說。《呂氏春秋·應同》篇云: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黄帝之時天先見大演大螻,黄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街丹書集與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倍,將徙於土。(40)
上天預設了水、火、木、金、土五行、五德的內容和運行次序,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這就是“天道”。每一次更替,上天均以祥瑞的方式昭示天下,聖君明王异於常人之處就是體察天道(這就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體道”,君主是“天道”的化身和代表,能“體道”者才是聖主明君),按照天意改弦更張就能成爲一代帝王,也祇有這樣才能成爲一代帝王,黄帝、夏禹、商湯、周文王就是這樣取得成功的。鄒衍所宣傳五德終始說中的“水德”論是要推銷“君臣上下、仁義之施”的政治主張,《呂氏春秋》的“水德”的具體內容是否和鄒衍主張相同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呂不韋希望秦統一以後能以儒家的道德仁義治國,無論呂不韋是真的相信五德終始說,還是把五德終始說作爲推行其政治主張的工具。
歷史常常使人走錯房間,呂不韋始料未及的是,秦始皇及其大臣們没有接受《呂氏春秋》所主張的“水德”的內核,而是接受了五德終始說的外殼,用來解釋秦朝成功的原因。“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在秦始皇看來,秦國的由小變大、由弱變强,統一六國,其制度、思想和鄒衍、《呂氏春秋》所主張的“水德”迥然不同,而所謂的“君臣上下、仁義之施”也從來没有實踐的先例,現在天下已經統一卻要改弦易轍,改變秦國已有的思想方針,顯然是荒誕無稽之談,而“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證明了秦國發展道路的正確性,所以,秦始皇很自然地抽去鄒衍、《呂氏春秋》所主張的“水德”內涵,代之以秦朝已有的歷史經驗,並且以上天的名義昭告天下:秦朝統一是上天安排的,嬴家天下是天命使然,任何不滿、非議都是違背天命的,必然要遭到上天的懲罰。具體到政治運作層面,就是“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以至於“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至此,我們可以明白,秦朝尚法的終極原因原來在這裏!而不能將秦政之失的原因一股腦地歸結於法家學說,僅僅用“暴政”二字判斷秦政是非。
鄒衍五德終始說的問世,本來是批評現實統治、推銷其政治主張、實現政治改良的工具,當其第一次和現實政治權力相結合的時候,卻變成了神化現實權力的工具,並把現實集權政治推向極端,這是鄒衍及其後學以及《呂氏春秋》的編撰者們無法想到的。(41)但是,無論秦始皇“水德”的內涵和呂不韋、《呂氏春秋》的距離有多遠,我們都要看到,是呂不韋編撰《呂氏春秋》把五德終始說系統引入了秦國政壇,深深地影響了秦朝的政治運作。儘管我們完全可以推論,即使没有呂不韋招來士人和編撰《呂氏春秋》,也會有人向秦始皇獻上五德終始說,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忽視呂不韋、《呂氏春秋》在秦政壇上傳播五德終始說的作用及其歷史實踐的影響。祇有這樣,我們纔能歷史地把握思想與政治的關係。
注释:
①現代學者對《呂氏春秋》研究甚多,就筆者所見,代表性的有李峻之:《呂氏春秋中古書軼佚》;劉儒林:《呂氏春秋之分析》,俱見《古史辨》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郭沫若:《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郭沫若全集》歷史编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洪家義:《呂不韋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熊鐵基:《秦漢新道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這些著作對《呂氏春秋》的成書過程、思想内容及其對諸子之學的采擇和改造、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價值,都做出過深入研究,但都没有對《呂氏春秋》在秦國的學術基礎和對秦朝政治實踐的影響做出過系統分析。拙文《呂不韋、〈呂氏春秋〉與秦代政治》(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秦文化論叢》第六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從用人和統治思想兩個方面論述了《呂氏春秋》對秦朝政治的影響,但所論有疏漏,同時没有討論《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的學術基礎問題,故作本文,補充舊作的不足。
②《史記》卷五《秦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下同),第202頁。
③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下同),第2264頁。
④《十三經注疏》,第2403頁。
⑤同上,第2318頁。
⑥參見傅隸樸:《春秋三傅比義》,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上冊第577~578頁;下冊第248~249頁。
⑦關於秦國和東方諸侯國發展道路的异同,參見拙著:《共同的歷史道路,不同的發展進程——秦國社會結構於秦文化散論》,《秦文化論叢》第三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
⑧關於春秋戰國時代各地風俗文化及其走向,以及秦風俗的特點,參閱拙著:《周秦風俗的認同與衝突》、《秦始皇會籍刻石與吳地社會新論》,分別刊《秦文化論叢》第十輯、第十一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2004年;拙著:《周秦漢魏吳地社會發展研究》第二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
⑨《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下同),第50頁。
⑩同上,第503頁。
(11)同上,第787頁。
(12)《戰國策》,第869頁。
(13)同上,第696頁。
(14)《十三經注疏》,第1852頁。
(15)同上,第2161頁。
(16)同上,第1786頁。
(17)《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下同),第2244頁。
(18)參閱拙著:《周秦風俗的認同與衝突》,《秦文化論叢》第十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19)《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序》,第685頁。
(20)最早系統論證這一觀點的是林劍嗚先生,見氏著:《從秦人價值觀看秦文化的特點》,《歷史研究》1987午第3期,目前學界基本上采用這一觀點,或者在林說的基礎上有所發揮。
(21)重用客卿是春秋戰國時代秦國政治特色政治傳統,是學界普遍關注的話題,代表性研究成果見黃留珠:《秦漢仕進制度》,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
(22)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下同),第1013頁。
(23)同上,第55~56頁。
(24)《韓非子·顯學》謂:“白墨子之死也,有相離李氏之墨,有相夫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對“墨離爲三”的理解,學界有分歧,韓非是按照當時各派的領袖人物區分。現代學者根據傳世《墨子》書的內容,從治學特點認爲是談辯派、說書派、事功派三派,或認爲是因爲其活動地域區分不同派別,蒙文通先生根據地域分爲南方之墨、秦之墨、東方之墨。分別見黃建中:《墨子書分經辯論三部考辨》,《古史辨》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禮,1982年影印本,第162~165頁。蒙文通:《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廖平蒙文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583~587頁。
(25)關於《墨子·備城門》以下各篇的作者屬性和成書時代,自清代以來均有争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是墨家傳人根據墨子止楚攻宋之事,采兵家學說附會成文而附之《墨子》。孫詒讓《墨子閒詁》沿四庫提要之說。蘇時學著《墨子刊誤》,認爲是商鞅一派的著作。朱希祖《墨子備城門以下而視頻係漢人僞書說》,認爲是漢人僞作,見《古史辨》第四冊,第261~271頁。蒙文通先生謂爲秦國墨者所作,筆者以爲蒙說是,見上舉《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廖平蒙文通卷》,583~587頁。孫次舟針對朱希祖觀點認爲是戰國學者所作,見氏著:《墨子備城門以下數篇之真僞問題》,刊《古史辨》第六冊,188~189頁。《墨子·備城門》以下各篇與雲夢秦律的比較研究,最早見李學勤:《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收中華書局編輯部:《雲夢秦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24~335頁。
(26)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02-303頁。
(27)《十三經注疏》,第719頁。
(28)關於戰國時代授田制度,參見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會結構研究》第二章第二節,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
(29)關於什伍連坐制度的起源和實行情況,參見拙文:《先秦什伍鄉里制度試探》,《人文雜誌》1994年2期;《周秦社會結構研究》第三章第二節。
(30)《史記》卷八十五《呂不韋列傳》,第2510頁。
(31)同上,卷七十八《春申君列傳》,第2395頁。
(32)《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31頁。
(33)同上,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88頁。
(34)《呂氏春秋校釋》,第648頁。
(35)《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36頁。
(36)同上,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3、249、259頁。
(37)同上,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37頁。
(38)同上,卷二十八《封禪書》,第1366頁。
(39)《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苟卿列傳》,第2344頁。
(40)《呂氏春秋校釋》,第677頁。
(41)關於五德終始說的淵源流變及其與秦漢政治的關係,參閱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四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