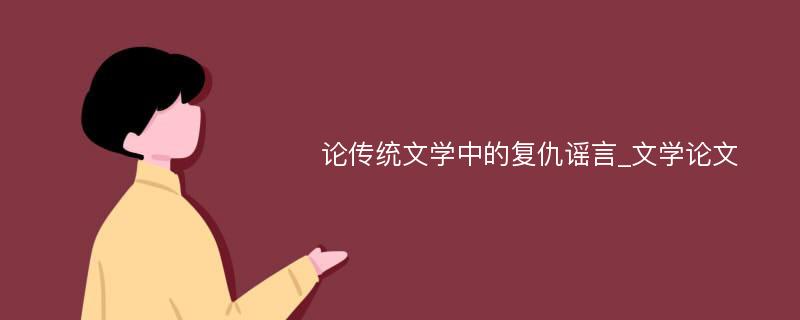
再论传统文学中的鬼灵复仇传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格尔在谈及远古英雄时代艺术美理想时,曾指出这一时代易于有个性的自由表现,一些有着特殊意志、杰出性格及作用的人,“正义的事就最足以见出他们的本性的决定”;也许是由于正义观念同复仇的切近相关,他又接着谈起惩罚与报复(即私自复仇)的区分,前者以普通的标准(法)来执行,而后者——“至于报复,它本身也可以有理由辩护,但是它要根据报复者的主体性,报复者对发生的事件感到切身利害关系,根据他自己在思想感情上所了解的正义,向犯罪者的不义行为进行报复,……”①这段论述对我们的课题颇有借鉴意义。无疑,原始心态持久绵延、血缘伦理浓郁的传统中国,有关魂灵复仇传说中的主体——复仇鬼灵,也是以个体的道德和正义行为,确证了自身的本性与价值,只不过后世类似传闻常常受到宗法制度与礼教的浸染。
复仇的核心组成成份是正义性,正义与公理相联系,这种公理并非“法”,却为人们沿用与认同。主持公理的天神上帝介入人世仇怨,使受害者一方在非现实世界里找到了人世无法伸张的正义,复仇才有基础与前提。广为流传的杜伯冤魂向周宣王复仇,就强调了行为的正义性。宣王妾欲通王臣杜伯,遭拒而诬之。杜伯被害后显形称冤,宣王又杀了帮凶司工锜;显形问罪,宣王又杀了出此计的祝,于是:
后三年,游于囿田,从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司工锜为左,祝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②
所杀非罪的宣王深恐死者索命,一再为自己寻出替身来开脱,但横死者一旦化厉,在正义大旗下彼此间昔日的仇怨就不去计较,而联手对付不义之君。这真可谓孟子说过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③在君主专制未确立,国家施法主义未施行时,这种带有原如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晏子即曾谏齐景公:“今君临民若寇仇,见善若避热,乱政而危贤,必逆于众,而诛虐于下,恐及于身。”④如果君主用行动将自己推到一个非正义的位置上,也会遭到臣民们正义的报复,自食恶果。这种议论若没有六国弑君的大量史实,是不敢对君主当面直言的。
从人类学的角度,拉法格曾指出正义思想的起源是报复的渴望和平等的感情。原始人“规定平分食物和财富的平等的本能创造了同等报复”。⑤这种报复起初是要防止流血复仇的毁灭性后果,后来则表现为“同态复仇”。对此,有名的《汉穆拉比法典》和《摩奴法典》中有较为具体的规定。如古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汉穆拉比法典》第196-197条规定,实行同态复仇法:“如果一个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由于正义、平等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人们逐渐习惯了不是向氏族或全家复仇,而且这复仇限于严格的报复——以打击还打击,以死还死。”⑥从上面所举的杜伯等人的复仇事例看,即带有讲求公正报复的。尤其是杜伯与司工锜,他们被杀死后,都将复仇对象仅限于真正杀人元凶周宣王,而不去计较协从帮凶之罪。《墨子·明鬼下》还记载了燕简王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乘其到祖泽祭祀时,半路上“苛朱杖而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诸侯传而语之曰:‘凡杀不辜,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比憯(惨)速。’……”⑦从这类鬼灵复仇故事所展示的心理内容看,大概罕有比滥诛无辜、枉害人命更能证实某人的非正义了,鬼神诛伐不义,既速且验,给予时人的震撼如此之大,其原形辐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在先秦时代传颂的鬼灵复仇故事中,尚鲜有后世那样复仇扩大化的倾向。那种为泄愤平怨不惜广为株连亲友仆婢的现象是难以见到的。这多半是由于正义思想尚较纯粹,以及避免更大规模血族仇杀的抑制力之超现实折光。就连孟子的感慨,也可以作为当时复仇逻辑中对等性质及正义性的一个佐证: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也,一间耳。⑧
杀害他人所得到的报复居然是这样沉重,其结果就仿佛是在杀自己的父兄。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这里不是说杀人遭报是自己害自己,而是强调亲族所受的连累,从中可见“族”的地位之一斑。在富有理性精神的黑格尔那里,谈及原始人报复,则表述为这复仇是侵犯者自己要求的,即报复者由于实行了报复,便“从为恢复自我而摧毁别人[报复]变成别人的自我摧毁[惩罚]了。”⑨一个是强调亲族受累,一个是申明自讨苦吃,中西方哲人对复仇后果表述上视点差异,也是文化上的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决定的。虽然报复是严格的,却不是毫无节制的滥用。当然,象赵襄子杀了仇人智伯后,“断其头以为觞”,⑩做得的确有些过分,但这除了家族间势力倾轧,亦为报复当年的灌酒之辱,仍可以看出同态复仇、公正报复的用意。
复仇的正义性,积极偿还的对等性质,孳生而又不断延续着复仇的道德伦理倾向及应然性企盼。鬼魂作为较低级的神欲进行复仇,实质上是借用了真正的神——高级的鬼灵那种超现实的能力,由于遭受冤抑不平而横死,鬼魂才具备这种并非所有死者之魂都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派生出许多可以随意增附的神秘力量。因而复仇鬼灵不是个别性的,其作为一个强大的冥世系统的分子,行使复仇使命所动用的是阴诛的系统功能,即使个别的冤厉一时达不到复仇的目的,或求助阳世力量,最终也能靠其正义的动机及系统的整体功能而取胜。
鬼灵复仇的方式,总体上体现了一种超时空的特征,具体可大略分为三种:
一是直接显形索命,如杜伯冤厉射杀宣王,又《述异记》载姚苌杀害苻坚后,“夜梦坚将天帝使者,勒兵驰入苌营,以矛刺苌,正中其阴。苌惊觉,阴肿痛,明日遂死。”《北梦琐言》载杨收被谮害后“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今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仇人),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杨中尉暴得疾死”。(11)这就好比杜伯冤魂复仇的翻版。这类故事渲染鬼灵的威力,也时或刻划其复仇智慧。这里举一则较少为人注意的鬼灵化装复仇的故事:唐华阳李尉因妻貌美被节度使张某借机深文周纳,刑后死于流放途中,霸占其妻后宠爱非常,但李尉妻和张某时常受到鬼灵的骚扰,李妻岁余卒,张在病中见李妻显灵,为报其恩宠,李妻戒告他不要降阶下堂,以免被已诉上帝的李尉魂厉索命,但是“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云:‘此贼若不著红衫子招,肯下阶耶!’乃执之出门去。……”(12)看来复仇厉鬼早已暗中侦测许久,掌握了仇人的心理。复仇鬼灵虽不能冲到设符的阶堂之上,却智赚仇凶。即使不在梦中,冤厉显形一般也多是仇主本人或专门视鬼的人才能看见,颇能反映仇主做了伤天害理事后忧惧复仇的心理。有时连仇主本人也见不到。(13)这样更突出了鬼灵行事的神秘特征。
其二是间接申诉举报,通常表现为托梦或显灵诉冤,而后由他人或官府代为埋怨。《后汉书·王纯传》就曾写女鬼夜中陈冤,诉说亭长害其全家10余口,于是部令王纯代为理冤,收系主犯,“及同谋十余人悉伏辜”。(14)《搜神记》卷16还敷衍了《列异传》等的奇闻,(15)说交州刺史何敞暮宿鹄奔亭,有女鬼名苏娥诉冤,并告之凶犯为亭长龚寿,凶杀过程及尸体埋处也详陈无遗。唐传奇《谢小娥传》写其父夫被杀后,相诸县,而丘池令尹兴将其杀害,投入空井。于是,“曜见梦于光日:‘臣张掖郡小吏,案校诸县,而且池令尹兴赃状狼藉,惧臣言之,杀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报形状如是,’光寤而犹见,久之乃灭。遣使覆之如梦,光怒,杀兴。”被害的官吏冤魂在梦境中倾诉被害缘由还觉得不大放心,竟等到自己的申诉对象醒来后,仍显形不灭,以期加深印象,强调自己被害之冤的真实性。唐前史书与志怪对鬼灵诉冤传闻的关注,无疑为唐传奇及后来的文学作品中鬼灵提供破案线索,求官复仇的母题情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以及在冤厉通过超现实形式复仇雪怨的合理性想象,加进了一些现实生活根据。官员们根据鬼灵在梦中提供的线索破案显得更真切而近乎情理。复仇的曲折与难度增大反显得更真实。
唐传奇《谢小蛾传》写其父被杀后,相继托梦给小蛾,以析字的隐谜暗示仇凶的姓名。(16)由于委婉含蓄地点出仇人,不仅为最终的雪怨提供了方便,且更增添了鬼灵报冤的必然性与神秘性。《禅真逸史》第31回写薛举自称得异梦:“五更之初,梦进一树林,内有一大将,黑脸胡须,魁梧异众,生于两大木之中,双手揲蓍,身下跨着一人,那大将呼我之名,指道:‘此汝父之仇人也,吾儿何不报之?’……”暗示其杀父仇人樊武端。这种好似哈姆雷特复仇的形式,同样显示了“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不同天”,(17)重要的还在于其并不回避、不掩饰冤鬼自身能力的有限,唯以复仇决心和智谋终于赢得了来自阳世亲朋、正义的援助;而这有限之中仍有其超越冥幕、超越时空的能力在。这类故事呈显出被害者本人与正义势力、冥间冤厉与阳世公理交融互补的特色。
其三是冤厉附于仇人身,使之精神惑乱、自寻祸事,最终落得可悲的下场。象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即然。清人写得新害旧的商人胡某,在自己患病时,也以“极凉之剂”服之致命。原来先前为除掉已厌弃的爱妾宝琴,正用此法;而他的新宠爱云,也若有冤厉所凭,“每怔忡忡,时有所见”,昏迷中叹气:“我病何得以寒凉之剂速我生命’”?(18)姜小玉被曾二郎始乱终弃后,父亦病亡,玉仰药卒。于是冤厉辗转来到曾府,附于二郎体上诉冤原委,使之陷入昏病中;又附于其帮凶大郎体上,使之侮辱盲女,做出种种丑行。后来二人虽脱法网,终因此病卒。(19)这类复仇故事更明显地带有果报色彩,且往往在果报过程中较为巧妙地通过恶人之口自诉恶行,颇具劝戒惩恶的意趣。有时这种托体复仇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如《二拍》卷20写巢大郎借姐姐病死串通邻居发难,使姐夫被拘,其妾丁氏自缢,于是其姐姐的魂灵附在巢大郎妻子身上,责其超度,使之日夜不宁;而后于氏冤厉又附上大闹,扰得恶人恹恹得病而死。而《水浒》95回写张顺在水中遭暗算后,其魂竟能附在其兄张横身上,向方腊大太子方天定复仇,杀了方天定后又向宋江诉说原委。《三国演义》第77回写关羽被害后,魂厉借仇人吕蒙躯身出现在吴主孙权的庆功宴上,再显生前的雄风壮慨:
……吕蒙接酒欲饮,忽然掷杯于地,一手揪住孙权,厉声大骂:“碧眼小儿!紫髯鼠辈!还识我否?”众将大惊,急救时,蒙推倒孙权,大步前进,坐于孙权位上两眉倒立,双眼圆睁,大喝曰:“我自破黄巾以来,纵横天下三十余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图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权大惊,慌忙率大小将,皆下拜。只见吕蒙倒于地下,七窍流血而死。众将见之,无不恐惧。……
其实,以上述三种形式为主,其彼此又互相交叉参融,整个鬼灵复仇主题内部又何尝不是复杂多变、光怪陆离。诉诸冥法悄无声息地了结仇人性命的更不在话下。鬼厉既入阴籍,其不公正的横死就需要超现实的复仇来矫枉补偿,不管历时多久,冤魂厉鬼总要乘着某些机缘,用其认为最恰当的方式来向仇主讨还冤债。
复仇鬼灵并不全是所向无阻为所欲为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复仇鬼,尽管能力有限,仍要在有限能力中发挥主动的奋争精神,借助于活人的力量来为自己伸冤。
即便是借活人身躯来返阳诉冤,被托体者也往往能得到鬼灵相应的酬谢。尽管不少相关的传说异文里并没有交待被托体的某妇人得到酬谢,(20)但真正文学化了的作品却忘不了这一重怨的恩主时,展示了某些美好的性情品质。就其求助与酬报方式看,又大体分为两种形式。
其一,鬼灵复仇时求助于人,而后必以适当的方式酬谢。如《幽明录》曾记载,某人被妻子的奸夫杀害,其冤魂欲报仇而力不足,于是恳求李羡家奴协助,获许。“果见人来,鬼便捉头,奴唤‘与手!’即使倒地,半路便死。”尽管这位帮手并没有起什么大的作用,但事成后帮助铲除不平的义士还是得到了千钱、一匹青绞丝袍的馈赠。而细心的鬼灵还考虑到恩公享用这赠物的稳妥性:“属云:此袍是市西门丁与,许君自著,勿卖也。”可谓认真负责到家了。句道兴本《搜神记》载远行经商的侯光被弟弟侯周妒杀后,埋在郭欢地边。善良的郭欢为之安葬并时常祭奠,于是侯光鬼魂表示要报恩的母题。《初刻拍案惊奇》卷14“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写杨化被谋害后,其魂灵附在于得水妻李氏身上,多次诉冤于官。冤情昭雪后,于得水梦见杨化之送一头走失的驴为谢,切不可小觑这一母题的出现,其直接影响作品的主题,使之不是在讲李氏的被托体与还魂的不易,而是冤死者能否伸张正义,为这正义伸张遭受辛苦付出代价的被托体者获得相应的补偿。所生不多所补有限,复仇与恩报同为鬼魂显灵,虽指向各异,但二者所体现的鬼灵神异功能、伦理观念则有类似之点,而故事的警世劝戒作用亦为之明确化了。
其二,受害者的冤魂先施予人以某种恩惠,而后再借助人力雪怨报仇。与前一点不同的是,其不是侧重于鬼灵的重情义不负恩公,而是侧重于鬼灵的豪爽慷慨,为了伸冤雪怨不惜倾其所有,投资给神圣的复仇大业。《夷坚丁志》卷十五写某女鬼先荐寝继赠金,使饱受自己恩惠的张客带着一同归里。原来张客的同乡杨生就是个始乱终弃、导致此女投井而死的负心人。女鬼借助张客找到仇凶后,使其“七窍流血而死”。复仇后冤魂就再也不见踪影了。明末清初小说《醉醒石》第13回中的娼女穆琼琼亦然。她因错认情郎,欲以终身相托,被负心的董文甫骗走积蓄饮恨而死。于是她的冤魂“精灵不昧”,先是假扮主人之妻借种,与客商卜少泉结下恩情,在情义难舍之际,很策略地吐露了被弃后含冤负郁而死的真相并厚赠卜五十两银。她深知即使有一定的恩义缔结,仍不足以托付助己寻仇大事,赠银之举是针对商人爱财特点,投其所好。其实女鬼所要求的,不过是让客商携带自己的灵牌一同还乡而已。以身相许再辅之以金钱,说明为了给成功复仇创造必备的条件,复仇冤魂宁愿用双重的酬报来增加取得最终胜利的把握。这就仿佛是一笔赌注,下这么大一笔赌注的目的无非是要赢个痛快。复仇的意志决心促使主体孤注一掷。又相传康熙时,商邱某富室寡妇被族人谋产陷害,赃官顾某受贿而冤终不白,无奈寡妇于堂上自杀明志以抗议,赃官为此被削职,回苏州老家。于是冤魂相追索命,请求过路商杨某带自己到顾某家,“但于君启行时,呼贤妇一声,及上船、过桥俱低声呼我。至苏日,以伞一柄,我藏于中,到顾某家,一掷其门斯可矣!”这在杨某来说,并非难事,酬答却颇可观,“有金珠一箧,值千金,藏于某处,即以报君也”(21)。于是杨某如约而行,“顾方与客燕饮欢笑,忽见一女鬼,手持匕首,鲜血淋漓于堂下。遂大呼:‘冤家到矣!’众客惊愕,无所见,是夜顾自缢死。”为了达到复仇目的,冤魂们是不惜代价的。但也有鬼魂为求助复仇并未仅靠倾己之蓄酬报,而是辅之以运用某种神异功能。刊行于咸丰七年的《鬼神终须报》第10回写何氏改嫁周六夷后,周骗银遁逃,致使遇人不淑的何氏气绝身亡。于是化厉图报的何氏与赌徒关某相约:鬼助人赌钱,人助鬼报仇,自此,关某每赌必赢,而关也携鬼厉寻访周六夷,终于使这个负心汉横遭索命,随后复仇鬼魂又撮合一女与关某婚配,并赠以生前藏银才算放心离去。
上述两类鬼灵求助活人报怨,求助的人都不是专门理诉平冤的官员,而是并无此专门职责的普通人,所以鬼灵要适当地酬报。这类故事不光突显了鬼灵生前含冤被难的委屈不平,还进一步证实了他(她)们饮恨而死往往正由于其善良率真,其品质人格有着不容忽视的某种连续性。不愿负于有恩者就是这善良品质的直接表现。他们往往是现实生活中平常的弱小者,因而死后复仇的能力也有限,不得不求助近前的人帮忙。从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和文学表现上的内在有机联系:生前是弱者则死后复仇能力有限,因能力有限才求助于活人,又因人相助报了仇而不负恩助尽力酬谢;从而印证并强调了其善良纯朴的品性。这一切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用恩报说明了复仇主体精神世界一系列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其所以要不惜代价决计复仇,以及尽力酬谢恩主的深在动因。
注释:
①《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235-236页。
②《墨子·明鬼》、《史记·周本纪》正义,《国语·周语》韦解等,而以颜之推《还冤记》(《冤魂志》)为最详,这里本此。
③⑧《孟子·离娄下》、《尽心下》
④《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十六》。
⑤⑥《思想起源论》第三章。
⑦李渔叔:《墨子今注今译》。
⑨《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107页。
⑩《吕氏春秋·义赏》。对此《韩非子·难三》、《淮南子·道应训》等记载不一,或“饮器”或“溺器”亦多异辞纷纭,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14,学林出版社1984,789-790页。
(11)此情节为《魏书·羌姚苌传》、《恶书·姚苌载记》、《北史·僭为附庸传》采入,情节稍有变化。
(12)《逸史》,《太平广记》卷122,860-861页。
(13)《隋书·卫昭王爽传》载其重创突厥后,“寝疾,上使巫者薛荣宗视之,云众鬼为厉。爽令左右驱逐之。居数日,有鬼物来去荣宗,荣宗走下如阶而毙。”
(14)又见《华阳国志》卷10中,俱本于陈寿的《益都者早传》。
(15)又见《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注引谢承《后汉书》。
(16)此本《搜神记》卷1“费孝先”,其以“一石谷捣得三斗米”暗示凶手姓名为糠(康)七。
(17)李复言:《续玄怪录·尼妙寂》。
(18)(19)宣鼎:《夜雨秋灯录》3集卷3,续录卷6。
(20)参见谭正璧编:《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53-657页。
(21)钱泳:《履园丛话》卷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