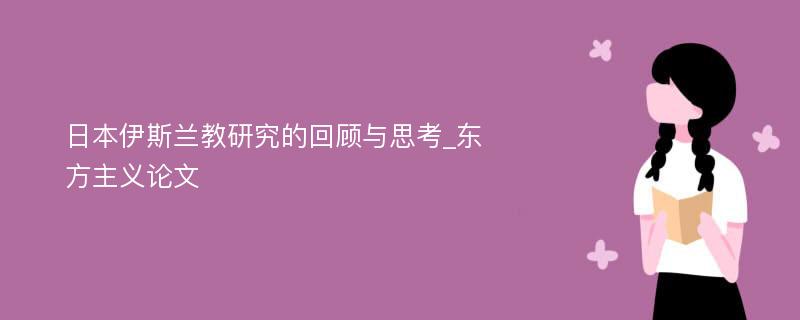
日本伊斯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代日本伊斯兰研究的起点
1.产生于世界多元性认识之上的伊斯兰认识
近代以前的日本并没有和任何伊斯兰国家进行过直接的接触。如下文引用的《日本和回教圈的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就是由著者小林元将其想像力和微乎其微的资料相结合,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探索的日本和伊斯兰的关系。
“明治以前的日本人对回教及回教圈的认识,即使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着,但是从未达到系统化或是细分化的程度。这大概是因为日本人和回教徒相互间的知识交流并不是直接性的而是间接性的缘故吧。也就是说,尽管日本的历史进程和回教圈的历史进程多少应该有过交错,但由于有作为中介的中国史的存在,所以造成了没有直接交流机会的结局。但是日本人和回教徒的通商交流并非不可能。因为日本的海外贸易对象不仅只是中国,通过朝鲜和琉球与回教徒的亚洲贸易发生关系也并非不可能。而且,相当活跃的回教徒的商业活动一定会影响到日本的通商活动。所以,如果详尽地分析日本的海外活动史的话,不会不在其中发现许多回教徒的痕迹的。”(注:小林元:《日本和回教圈的文化交流史——明治以前日本人有关回教徒回教圈的知识》,中东调查会,昭和50年(本书为著者至昭和15年3月末的未完遗稿),第62页。)
即使日本和回教徒过交往,也并不意味着日本进行过系统的伊斯兰研究。近代日本最初对伊斯兰的兴趣产生于对世界多元性思考的基础上。我曾在《对日本人而言伊斯兰是什么》(注:铃木规夫:《对日本人而言伊斯兰是什么》,筑摩书房,1998年,第217页。)之拙著里指出,被迫打开国门的近代日本社会要想被欧美绝对化的世界相对化,就必须要从思想上去合理的解释世界的多元性。而日本对伊斯兰的关心正是以这一契机为出发点的。只有通过与伊斯兰世界接触、进而说明什么是伊斯兰,才能是日本社会真正理解世界多元性唯一的途径。
近代日本政治学家南原繁,在《国家和宗教》之著述中,指出当时出现在日本的基督教现象是“原本是东方的进而成为世界的基督教之东方的还原和其日本化”。南原不仅一语道破了被认为是西欧文明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其实是东方的产物的实质,同时也指出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世界性”是被现实世界的人们所开创的。他的逻辑是,作为犹太教的宗派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形成,进而在希腊文明时代的罗马帝国得以发展壮大并扩张至整个欧洲;又在德意志发生了“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而这一“世界性”正是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
在近代日本对基督教世界性的思考中其实也包括了对同样也把神的惟一性作为其信仰之根本的伊斯兰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思考。对近代日本而言,同样也是东方的进而成为世界的伊斯兰在表示其“世界性”之范围时,也就不存在其范围是否仅局限于东方的问题了。因为伊斯兰的“世界性”与基督教的“世界性”都是在现实世界中被人们开创的。
那么,为什么近代日本对世界多元性之认识划归到基督教范畴,而不是伊斯兰范畴之下呢?我认为这不仅关系到近代日本的伊斯兰认识体系,也牵涉到近代日本社会的政治思想倾向问题。
2.东方主义知识体系的伊斯兰信息
在近代日本,通过欧美文献最初掌握了伊斯兰世界之地理知识并最初明确认识到穆斯林存在的人物是福泽谕吉。可以说,近代日本对伊斯兰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19世纪西欧世界所谓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之思想知识体系(以下统称“东方主义”)即“文明与野蛮”之两分法的认识上的。
东方主义的影响一直蔓延至后来的日本社会。如1970年代在小林的《掌中万国一览》一书中对所谓东方世界的描述,就是“文明与野蛮”两分法的一个代表。
“……野蛮之民不足为取为第二等,居天幕之下,随牛羊而行食肉饮乳;晓耕作之法食物种类之多;并非尚无文字,但书写诵读者甚少。并非无粗质机械,但其制作极为简陋;野蛮之民亦有一群之酋长曰‘希古斯’或‘汗’,其法甚为残酷且无妄;鞑靼、亚刺尼亚及亚非利加北方之土人等即如此;……所谓未开即未被教化所至,风俗未开。其民仅微晓耕作之法但不善;解艺技之道人所用之物颇多;具忌建村落都府、轻辱妇人、欺躏弱小之风。如支那、土耳其、波斯其风为最……”(注:小林元:《日本和回教圈的文化交流史》,第62页。)
在明治初期,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同时又处于西欧列强殖民主义之扩张的国际环境下,因此一方面照原样接受了由东方主义者提供的伊斯兰之信息,使自己相对于伊斯兰世界,另一方面又把已经西化的中东视为反面教师来警戒自身的西化倾向。(注:杉田英明:《日本人的中东发现——逆远近法中的比较文化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第158页。)所以,如同东海散士在其《佳人之奇遇》中记述的那样,在近代日本既发生过和同一时期埃及“阿拉比运动”(注:1181-1182年展开的近代埃及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青年军官艾哈迈德·阿拉比(Ahmad Urabi,1841-1911年)为该运动的领导人,故称为此。该运动在埃及当代政治史中被定为埃及民族运动的起点。)那样对抗西欧霸权的运动。同时,也出现过将英法的中东殖民地统治作为统治台湾和朝鲜的样板的趋势。(注:这一时期是日本加速殖民地统治制度化的形成时期。据新渡户稻造(1862-1833年,近代日本思想家教育家,曾任京都大学教授,国际连盟事务局长等职)指出,为了更好地进行殖民地统治,在帝国大学还特设了有关课程和讲座。)
因此,对日本而言,19世纪以来受到西欧列强直接和间接统治的伊斯兰世界,具有着既有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对象的可能,也具有着成为日本对抗西欧的同盟之可能的两面价值。也就因此,近代日本对伊斯兰的认识是构筑于由东方主义者提供的伊斯兰之知识体系之上的;而在日本的政治体系中则包含了东方主义体系和近代日本的政治倾向这样双重的因素。
二、1920年代至40年代的伊斯兰研究
1.自由主义思潮的伊斯兰研究
从1920年初期到40年代中期是日本伊斯兰研究的上升时期。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伊斯兰研究中,不仅存在着受1920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自由主义学术思潮影响的研究,还出现了大东亚共荣圈之帝国主义思潮及国粹主义思潮的研究,在3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4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直接为战争服务的研究。
在战前,尤其是在1920、3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开始出现了脱东方主义体系的伊斯兰研究。比如为奠定日本伊斯兰研究之基础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川周明在1922年发表的《回教徒的政治的将来》(刊载于《改造》),还有同年被刊载的内藤智秀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大久保幸次的《土耳其的复兴与回回教的复兴》,从题目就可看出这些著述都是脱东方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成果。
比如,似乎是受了近代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在其《亚洲史概说》中提到的“西亚文明东流论”,或是“近世文化东进说”的影响的三木,以生态学的观点描述了伊斯兰文明的扩展形式。
“……首先有一个原初文明,然后在其周边出现了取代它的新文明,新文明中最初没有原初文明的因素,而新文明在吸收了原初文明后才最终实现了其领域的扩大。所谓文明就是以这种同步并行的方式被持续扩展开来的。而被我称为新(西洋)文明的则是以中东为中心,从地理上讲包括西亚、北非、地中海、欧洲的地域;而新文明的核心不言而喻是伊斯兰。文明的同步并行的持续展开是指新文明在不破坏原初文明的基础上与原初文明并行不悖,以此基础上去开拓和激化其领域的扩大化。这样一来在各文明之间反复发生着征服和融合,进而又产生了共同创造言语、宗教等的过程。……例如,作为文明语的阿拉伯语,是使用叙利亚语的叙利亚人,以及在中世纪使用波斯语的伊朗人的知识分子,借助上层人士学习古希腊语之契机而形成的。而波斯语中的抽象语则变成了阿拉伯语。中世纪的拉丁语也是在其上层人士学习阿拉伯语之后而使其文明化的;而拉丁语中俗语部分的法语,则成为17-19世纪的西欧文明语了。所以,所谓人和物以及信息的交流,都是以开放的网络形式同步并行的持续展开的;言语也好,宗教也罢,其时都是在相互借鉴和推敲进而互相融和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伊斯兰恰恰就是这一形成过程的中心,从地理上讲伊斯兰也正好位于正中。”(注:《别册环第4号什么是伊斯兰——以世界史的观点来看》,藤原书店,2002年,第5-6页。)
在40年代,在进行着有着战争背景的中国回族穆斯林研究的同时,还出现了像饭田忠纯、内藤智秀、八木龟太郎、蒲生礼一、前岛信次、松田寿男、小林元、井筒俊严等一批较为年轻的学者那样以自由主义的构思进行的纯学术性的伊斯兰研究,他们的研究为战后的伊斯兰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与帝国扩张主义思潮相关的伊斯兰研究
在诸多的与帝国扩张主义有关的伊斯兰研究中,可举曾去麦加朝拜过的若林半为例。从下文可看出受皇权思想影响的若林对伊斯兰的态度。
“……回教世界以及回教徒蟠居(原文,译者注)国土的兴亡,与亚洲及亚洲人之盛衰有着怎样紧迫而重大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以亚洲盟主自居的日本,作为把确立世界和平作为一大使命的皇国而言,回教政策具有如何的重要性,无须赘言即可明了。那实为天皇之道宣布之基调。”(注: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非卖品,1937年,第89页。)
持有此种言论的当然不会只是若林一人。如同下文著者野原四郎那样,尽管他客观地指出了穆斯林社会的特殊性,但是其文章依然流露着与若林同出一辙的皇权思想。
“……当前我国对回教徒的态度,相信势必将其从国策之中分离出去。回教问题不是脱离其根本原理就能够解决的。但我国过于被这个问题的特殊性所局限,而欠缺从其原理起重新考虑回教问题的鲜明态度。到目前为止的殖民地支配,究极而言是建立在抑制原住民生活向上之基础上的。然而,如果我国采用促进他们生活向上之各有所得的方式的话,那我国的指导地位就能持续地确立和强化。”(注:野原四郎:《关于回教徒问题》,《回教圈》,第7卷第4号,1943年,第2-3页。)
与这样的“指导地位”之言论相呼应,野原又将当时日本的伊斯兰研究状况作了如下的分析。
“籍支那事变为开端的日本之回教研究总算被开始组织化了。而到那时的研究为止,可以说只是少数研究者以各自的兴趣而自行其事的。在日本的东洋学中,像回教研究这样被冷落的现象颇为罕见。除了极少数的先行者,可以极端的说,日本的东洋学是把支那学从世界史及亚洲史之中分离出去;而把被分离出去的那部分称为东洋史……”“……回教研究,如与日本作为大东亚战争之目标而设置的东洋学相呼应,会使其研究得以飞跃发展。如此一来,支那及印度尼西亚就会被(日本)完全理解的。如果再联系到被东洋学所印证的日本人的亚洲观和早晚应该被开通的与西亚的实际性接触,那么,那一定更会是幸事。而以支那事变为契机开始被组织化的回教研究要想在大东亚战争中得以展开,就必须要清除研究松驰的现状,需要更进一步的组织化……”(注:野原四郎:《回教研究之重要》,《回教圈》,第6卷第1号,1942年,第8、13页。)
在这里应该指出,所谓“被完全理解”是野原以东方主义提供的信息为基准的理解,并非是说日本的脱东方主义体系的力量已被组织化了;因为就在野原做出这一断言的半个世纪之后,正像以伊斯兰思想研究而著称的板垣雄三所感叹的那样,到现代为止,日本还没有真正形成所谓有组织的能与东方主义相抗衡的力量。而野原本人早在日本败战后就放弃了伊斯兰研究而转向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去了。
3.战时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调查研究
从规模上来看,战时日本的中国研究,特别是对回族穆斯林社会的研究已呈现出与1960年代越南战争时期美国进行的所谓“地域研究”相似的状态。也就是说,当时军方和政府及民间各部门为了各自的目的,竭尽全力进行了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调查研究。在1930、40年代日本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研究是由众多的组织以各自为政的形式进行的。
据对战时的中国穆斯林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的中生胜美介绍,现在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里还保留有若干涉及到对中国穆斯林政策的资料。根据那些资料的记载,当时,日军试图成立由日军作后盾的“中国回教联合总会”,而以最终建立像“满洲国”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那样的回教徒傀儡政权为目的。(注:在中生的书中还介绍了这个调查团在包头对苏非教派哲合林耶教团进行的采访活动。下文介绍的是哲合林耶教团为应付日方的调查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据张承志说,日军向教团探询对调查的反应后,教团对派谁来应对日本人的调查问题而进行了内部磋商……,最后决定由北京到宁夏学习伊斯兰教的年轻的伊玛目前去包头应对日方的调查,以此对日军适当的放了个烟幕。那时前去进行回答的伊玛目是张承志父亲的朋友,他曾将那时的情况直接向张承志讲述过。哲合林耶教团第八代‘穆热师德-Murshid(教团领袖)’马震武(1962年故)当时蛰居在京。日军特务设想像‘满洲国’的溥仪及‘蒙疆政府’的德穆楚克栋鲁普那样,推出马震武作为第三‘满洲国’的首领……。据说国民党政府对此已有防备,蒋介石令其下属从北京将马震武带到香港,最后在重庆加以监护。岩村忍的调查团去包头调查哲合林耶教派时恰恰就是这个时期,所以绝不能向日本人透露马震武的去向就成为教团最重要的原则。据说教团方面对此调查也感到十分棘手。由北京来的年轻学生回答调查问题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了解到哲合林耶教派内部的真实情况。同时,为使日本人得不到详细的资料,教团方面事先设定好了回答的内容。为此,在战后由佐口透整理的当时的调查资料里并没有什么军方想要得到的特别的内容。”)因军部不了解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情况,便把调查任务委托于民族研究所。1944年夏,民族研究所派出岩村忍、小野忍(注:小野当时供职于上海的满铁调查部,他沿袭满铁的调查方法拟定了细密的调查项目,之后再将那些项目译成汉语并制成小册子,以小册子为中心进行调查采访,最后将其结果整理成卡片保存起来。这一调查工作可以说是制定宣抚回教徒宣抚政策的基础。)、佐口透等人前往张家口,与日本设立在张家口的西北研究所合作,开始了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调查。(注:中生胜美编:《殖民地人类学的展望》,风响社,2000年,第237页。)
在岩村忍著作中提供的当时有关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研究的文献如下。
“……中国的回教徒中特别是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的回教徒是有组织的一种社会集团的情况,浏览下述文献便可明了。(Dabrythierssant,Le Mahometisme en Chine,Paris,1878.2tomes:Emile Rocher,La Province chinose du Yun-nan,Paris,1879-1880.2 tomes:Dollone,etc.,Rech Et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ois,Paris,1911:Marshall Broomhall,Islam in Chaina,London,1910:Martin Hartmann,Zur Geschichte des Tslam in Chaina,Leipzig,1921:Robert Ekvall,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Chicago,1939……)”
岩村忍之著述《对中国本土回教徒的研究调查》就是在战时进行的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从下述引文可看出他对中国伊斯兰社会研究的一些认识。
“……西北、西南诸省的回教徒作为有组织的社会集团而散见于汉人社会之中的现状早已被知晓。但是,在事实上却没有很好地进行过有关中国回教社会的历史以及社会组织的研究。特别是与边境回教徒的调查研究相比,中国本土回教徒的研究调查极其缺乏。更可以认为边境回族与中国本土回族的比较研究完全没有进行也不过分。欧美学者、中国及本国的历史学者之有关中国回教的著述中,尤其是关于中国回教史的研究并不缺乏精髓的研究。但是,中国回教史研究最重大的问题在于,其研究不是被非学问地处理,就是完全不被过问。也就是说,在中国史中散见的各时代——唐、宋、元、明——的回教和现代回教的关系,被各时代的资料片段性的、按年代间隔的原样留下空白,而且仅仅止于年代的罗列。还有,这个问题从来没被作为专题研究来对待过。……根据资料来考察近代回教史的成立是可能的,但对性质各异的现代资料的整理和批判的确不是容易之举。可以认为,对具有异类性质的回教徒社会的有关资料的处理,是需要相当慎重的,仅从很多资料是由非回教徒所整理而成的情况来看也就会清楚的。因此,如果不首先将回教社会的构造弄清晰,那么,对资料的批判及学问的处理也就根本是不可能的。”(注:岩村忍:《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上),日本评论社,1949年,第11、14页。)
前面提到的野原在总括了日本的伊斯兰研究状况之后,也同岩村忍、佐口透一起到中国实地对回族穆斯林社会进行了考察。
这一时期的日本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调查研究与军部有关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战时并没有建立起一体化的伊斯兰研究机构,所以,在战时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也就都被零散搁置了。值得庆幸的是,从已公布于世的与军部有关的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研究中也不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
4.对被中断的伊斯兰研究的反思
在经历了1920年代到40年的伊斯兰研究的上升期后,战后日本的伊斯兰研究却被长期中断。因篇幅所限,在此仅举大川周明为例来说明伊斯兰研究在战后日本被中断的状况。
大川周明最初是德意志哲学研究者,构成他宗教哲学体系的因素中,既有儒家学说及伊斯兰思想等古今东西之宗教思想,又包括与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形成的唯物论思想,甚至还有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大川曾被认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导者;可以说构成他思想体系的因素十分庞大也十分复杂。因此,很难将他的学术贡献和他所进行过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分开去做出合理的评价。(注:除日本的一些评述大川周明的书籍外,在中文著作里,解学诗所著的《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之书中对大川周明在战时的活动及他本人的思想形态有专门的介绍。)
大川在1922年完成了前文提到的《回教徒的政治的将来》后,又于20年后的1942年8月完成了《回教概论》;此著述后来被竹内好(注:1910-1977年,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始人,著名鲁迅研究家。)誉为是战时“最高学术水准的”伊斯兰研究。战时大川供职于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当时在此机构保存的由大川收集的有关伊斯兰研究的文献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数量。大川为1920年代到40年代的日本伊斯兰研究所作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川提供的充实的学术条件的话,在他之后也就不会出现以研究古兰而成为日本伊斯兰研究之权威的井筒俊严。
可是在战后,由大川所收集的东亚经济调查局所藏的资料却全部由美国占领军强行没收。与此同时,从近代以来总是屈从于欧美的日本社会对大川的评价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提及大川的伊斯兰研究则成为学术界的禁忌。而更明显的是,除了前文提到的井筒及前岛等极少数研究者之外,大多数人在战后都放弃了极为敏感的伊斯兰研究,伊斯兰研究也就因此于日本学术界中销声匿迹。因此,在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日本的宗教研究界中,也就没有出现像丸山真男(注:1914-,思想家,东洋政治、历史学者。)那样,作为战前的国学家,却在战后以批判政治学的姿态构建了日本当代政治学基础的现象。
伊斯兰研究被中断也许是因为伊斯兰研究在战时曾有过军部的背景所造成的;驹泽大学就在其大学史的记述中长期避而不谈曾设置过回教圈研究所的有关事实。但事实是,除了部分研究机构之外,日本的伊斯兰研究并不是始于战时,也并不只限于战时;在20年代初期即问世的诸多研究就是证明。大川等人在战时的研究则是其20年代开始的研究的持续。而由他在战时所收集的有关资料是在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即是对日本的研究者进行实证考察有利的时期进行的;就象在同一时期也由满铁调查局进行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那样,如果由他调查的那些资料没有被美军强行没收的话,那么,那些资料会对后来的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界提供极其贵重的参考,进而也许还会进行同中日学者合作进行的象《中国农村惯行再调查》那样意义重大的学术活动的。
无须讳言,战后日本的伊斯兰研究被“中断”的原因其实是与总是追随于霸权主义的日本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关的。比如没有人认为在战时进行过中国穆斯林社会研究的岩村忍在战后转向与美国的东亚战略有关的研究是不正常,同时也没有人对军部有关的研究进行过认真的梳理和批判。
三、伊斯兰研究的再构筑
1.对伊斯兰在世界文明中所处地位的思考
冷战结束后,日本伊斯兰研究又出现了一些与1920、30年代相近的研究动向。比如,前文提到的板垣雄三在其论述中又重新提到了像前文引用过的三木那样的对以伊斯兰为中心的世界文明的思考。
“……一说到伊斯兰,就马上充斥着将其与边境性的攻击相提并论的现象,所以,应该首先要明确的认识到伊斯兰在世界史中所占据的重要性,这是认识伊斯兰的前提。伊斯兰是否在世界史中先天的、命运的承担了作为中心的重任暂且不论,而伊斯兰似乎不存在中心主义的因素才是我试图强调的。因为,伊斯兰的特征恰恰在于其坚持多元性的以及强调事物的差异性和个别性的宇宙观;所以尽管也许伊斯兰先天性的承受着所谓中心的重任,但伊斯兰却具有对中心主义的现象进行不断自我批判和否定的一面。”(注:板垣雄三:《日本的伊斯兰研究和日本与中东的特殊关系》(英文),《日本中东学会年报》17-2,2002年,第11-12页。)
同时,板垣对伊斯兰文明所处的位置和其对世界文明和世界秩序所产生的影响作了重新评价。
“……西欧和日本与伊斯兰的接触方式明显不同。对欧洲来说,所谓伊斯兰世界只是一个地理的连接,而连接点到摩洛族(注:Moro,菲律宾南部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集团的总称,西班牙对伊斯兰教徒的称法。)即为止。与此相反,日本则通过中国、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的某种媒介而感受着其影响。就因为有这些媒介存在,日本才接触到了伊斯兰文明之网络向东方的延伸。日本就是这样和伊斯兰保持着直接和间接的接触。可是,因为西欧和日本刚好对称地处在伊斯兰世界的东西边缘上,因此,日本又轻易地受到了西欧东方主义的影响。……在《世界之中的中东》图中,三个圆交叉在一起的是中东,每两个圆交叉之处则是中东的扩张。而同三个圆形合并成的最中间的三叶草(Clover)形状的地域则相当于伊斯兰世界历史的核心部分。今天的伊斯兰,包括作为其正背面的美洲大陆都在不断发生着由里到外的伊斯兰化,构成全球伊斯兰化,或是伊斯兰全球化的趋势。在历史上三叶草形状确实是世界的核心部分。”(注:板垣雄三:《日本的伊斯兰研究和日本与中东的特殊关系》,第13、23页。)
2.伊斯兰研究的地域化倾向
像上述那样以宏观的视野来解析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也出现了以微观的视野来解析伊斯兰世界的倾向。其代表可举对非洲伊斯兰社会进行实地调查的大冢和夫为例。大冢认为用惟一的绝对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穆斯林社会是不可能的,对此他有如下说明。
“不如就像在眼前(非洲)看到的那样来理解穆斯林的多种思想及行动,之后再将其差异加以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因素去解析(伊斯兰)的方式才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她)们认为,他(她)们原本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她)们就这样行动着;并将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作为是‘伊斯兰式的现象’加以说明。所以,我对伊斯兰的认识也就不是以‘单数的绝对的伊斯兰’为发点,而是围绕着‘复数的相对的伊斯兰’为出发点的。今后也还会这样论证下去的。”(注:大冢和夫:《伊斯兰式的——在世界化时代中》,日本放送学会,2000年,第11页。)
像这样用相对论来脱离神的绝对性和惟一性的来解析伊斯兰世界的倾向,并不只限于大冢。比如,如加藤博在下文阐述的那样,他以近代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准,把“拥有”和“惯习”作为近代法体系而独立于正统的伊斯兰法,并强调了“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法体系”的区别。其文引用稍长了一些,但加藤的立论体现了当代日本伊斯兰研究中出现的地域主义倾向的一个侧面。
“……即使《伊斯兰法(Al-shar iyyah)》确实是伊斯兰教徒生活全体的规范群也好,但却不能不认为,事实上,在近代以来,即使是在前近代,伊斯兰世界的住民、就连那里的多数派的伊斯兰教徒在生活中也并不仅仅是被《伊斯兰法》所制约着的。他们还遵循着《伊斯兰法》之外的法体系。其中之一就是被阿拉伯语称为‘Qanun’而被译为‘行政法’或是‘世俗法’的法体系,那是建立在国家创立者的统治需要之上的。还有一个用阿拉伯语叫做‘ulf’或是‘ada’的不成文法,它是由地域社会的支配者确立的。因其具有时效性和地域性而被译为‘惯行法’或是“惯习法’,因此,具体地来说,所谓伊斯兰法体系是一个以《伊斯兰法》为核心,同时又掺杂着‘行政法’‘世俗法’以及不成文法的‘ulf’的法体系。构成伊斯兰法体系的这三个系统在法学上并不是同一水准。那是因为在伊斯兰世界里法的代表只能是《伊斯兰法》。而‘行政法’‘世俗法’并不是独立于《伊斯兰法》而是作为补助体系被认识着的。另外,‘ulf—不成文法’的其中的一部分要通过《伊斯兰法》的诠释后才能被列入伊斯兰法体系,因而并不是构成《伊斯兰法》来源的一部分……三个法系统因各自产生的背景不同,在运用范畴上都有各自独立的领域和秩序。说起来,作为伊斯兰法体系核心的《伊斯兰法》在现实中并不实用,其形成的过程证明那只是神的启示。此外,其规定到能够在现实中成为实效性法而被适用为至,必须要经过多次的人为的解释的过程……”(注:加藤博:《伊斯兰世界论——作为骗子的神》,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84-88页。)
加藤以其在埃及农村的实地调查为依据叙述了上述的“实感”。虽然他似乎对制定各种法时的知识和权利的问题不太感兴趣,但是,各地的穆斯林社会为了维持各自的地域次序,“其生活并不仅仅是被伊斯兰法所制约的”迹象是可以被理解的。问题是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规范中,其“代表法”《伊斯兰法(Al-shar iyyah)》所规定的规范是其他法不能取代的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存在也许才是解析构成伊斯兰地域社会的关系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像大冢和加藤这样的研究倾向,不仅体现了日本伊斯兰研究的细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伊斯兰研究力量的加强。现在,在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伊斯兰研究力量不断增强,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但这并不等于日本对伊斯兰的认识已达到了宗教学的和哲学水平的层次,也就是说日本的伊斯兰研究还没完全形成清晰的思想和知识体系。
结语
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将近代以来日本的伊斯兰研究进行一概略性的整理。而在不得不结束本文时,最后特别想强调的是下述两点。
其一,日本社会用什么样的信息渠道去获取有关伊斯兰的知识并将如何去建立自己独自的知识思想体系的过程,实际上是日本政治思想走向的一个过程。日本在短时期内也许还会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日本如果要想进一步深化伊斯兰研究,就决不能再盲目附和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东方主义体系,特别是应该对西方世界无视自己的文明是建筑在东方文明之基础上的事实而对同样是东方文明的伊斯兰采取的不公正态度加以思想上的抨击,否则日本的伊斯兰研究将永远陷入一种趋炎附势的泥坑里不能自拔,而且,日本学术界也许会永远处在无法对战时伊斯兰研究进行思想性的梳理和历史性的检证的状态之下。
其二,仅就日本出现的伊斯兰研究的多种倾向而言,我认为具有研究性质的“伊斯兰现象”将会充满全球,而如何将这一趋势整体化则面临着诸多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日本还没有完全形成对伊斯兰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整体思考。这也许不仅是日本而且也许是各国伊斯兰研究者面临的共同课题。
标签:东方主义论文; 大川周明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回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