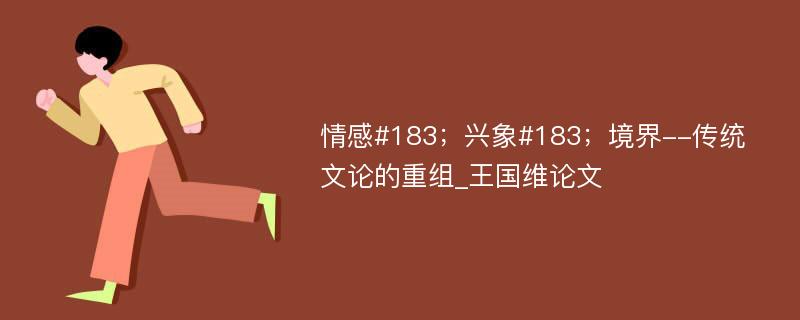
情志#183;兴象#183;境界——传统文论之重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境界论文,传统论文,情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大体上说,西方主流的传统文学观是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之上,故有“镜子”的比喻;而中国传统文学观则建立在感应论的基础上,虽有“镜花水月”之譬,重点却不在“镜”,而在“镜中花”,倒与当代西方符号论者所谓“艺术幻象”相近。明确地将“人心通天”的感应论引入文学观念并进行论说的是刘勰,其《文心雕龙·物色》有云: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随物宛转”是客体对诗人思维的制约,而“与心徘徊”则用心与驭物,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故《物色》篇又云:“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心与物之间是对话的礼尚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诗学追求的将是“思与境偕”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刘氏所论,先后有序。“写气图貌”,即诗人感物而胎孕意象之际,则受制约于物,故曰“随物以宛转”;至“属采附声”,着手创造意象之时,则有所选择、着色加工,故曰“与心而徘徊”。这是一条“流水线”,前后有序而无间。然而此类直观把握的方式缺少“分析——综合”的过程,对心物之间的中介及转换关系语焉不详。我们不妨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为参照,反观这一现象,或可深进一层。
皮亚杰有个著名公式:
S—→(AT)—→R
S是刺激,R是反应。AT是同化刺激S的结构。这就是说, 主体与客体双向建构的途中,有个中介环节——认知结构。客体通过这一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知,而认知结构是通过个体不断学习得来的。客体产生刺激被整合进个体原有的认知结构中,是为“同化”;同时主体调整原结构以适应客体,是为“顺化”。同化与顺化不断双向运动,使主体认知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建构过程既包含主体,又包含客体,即此即彼。“心物交融说”合理之处也正在于意识到心与物双向建构的关系。对于作为中介环节的结构,虽然尚未明确,但已触及,这就是“缘心感物”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感物的中介是“七情”。事实上中国传统文论更多地是强调“情志”。录几则文献材料如下: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虞书·舜典》)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礼记·乐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
先人们认为诗是志的表现,志本于心,情志是一回事。自陆机提出“诗缘情”以来,有些人始注意情志间的异同。如邵雍《伊川击壤集序》称:“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大略言之,志偏重在对社会事件的反应,情则多个人情绪。但无论如何,诗与情志的关系是明确的。问题在于,情志是如何同化外部世界使之进入文学世界?主体情志又是如何顺化、适应外部世界而作自我调整?前贤虽然于此未必有理论上系统的认识,但在其丰富的实践中,已有所体悟。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中国古文论无疑已意识到主客体之间有一个中介环节——作为情感结构核心的“情志”。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意识到文学并不直接表现客观世界本身,而是首先表观主体对客体的经验。这是我们重组古文论的一个基础。
二
外部世界通过情志这一情感结构引起反应,还须用语言表达才能成为文学作品。然而先民对语言的局限性早有觉察,所以另立“象”以“尽意”。故《周易·系辞上》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老子《道德经》亦云:“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以象尽意,事实上就是对意义整体的追求,企图以“象”涵盖在场者与隐蔽者。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言、意、象三者关系明确,象是言与意之间的中介。言是通过“明象”来表意的,让“象”的整体直观性来达到意会的目的。而以象形性为根基的汉字,又促成了这种整体直观的意会思维。有人将汉字比作集成电路,含有最大的信息量,其“孤立语”的一词一义性质可灵活地组合,又强化了汉字的直观形象性,使汉语思维呈现出“卡通”式的图景跳跃,在思维过程中超越了语词。关键在于:王弼所指的“象”,是哲学之象,还不是文学之象。然而“言意之辨”一旦与“文学自觉”相结合,便开始将中国文论推上“情景论”为核心的诗学之路。
起于六朝的文笔之分是文学独立于经史的重要信号。六朝人开始要求文学要有文学独特的语言。萧统《文选序》述其去取标准,将经、子、史排除在外,又云: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对此有二解,或以为“沉思翰藻”应是昭明《文选》之总体标准;或以为“沉思”二句应指史传中的赞论、序述而言。但无论如何,二种说法都认为《文选》去取,颇重语言之文学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对文学语言与象之关系的认识。钟嵘《诗品》则倡“巧构形似之言”。如果与他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主张合看,则所谓的“巧构形似之言”也就是能构建艺术之象的文学语言,不妨称之为“象言”。即以言明象,以象尽意,以艺术之象感发读者整体直观的意会思维,通过在场者(“直寻”出来的“象”)逗出隐蔽者(“意义整体”)。殷璠 “兴象”说,王昌龄“意境”说,司空图“象外之象”说,王夫之“情景”说,无不循此以求。尽管诗论家极力强调言外之味,其实都看重“象言”本身,兴象并举。对此,钱钟书有点睛之笔焉。钱氏强调艺术之象与哲学之象的区别,在《管锥编》中称:“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又云:“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管锥编》第一册)。所以无论诗人将话说得多么绝:“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毕竟不是禅家棒喝,他们还要炼字、炼句,执着于“象言”本身。
“象言”的特点在于往往能将客体与主体的情志紧密结合起来。如杜诗《秋尽》:“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陶潜菊”、“袁绍杯”为何物?它只能是文学语言创构的意象。至如“天畔登楼眼”、“画图省识春风面”,“登楼”与“眼”、“春风”与“面”,已镕铸为诗的“合金”。而“影著啼猿树”、“听猿实下三声泪”、“清江锦石伤心丽”云云,竟是情景的“有机化合物”了。“影著啼猿树”固可释为身羁峡内,每依于峡间之树,而树多著啼猿;但如此分解,“啼猿树”之意味又何在哉!“伤心丽”三字更是混沌不可凿,是“壮丽”、“清丽”、“华丽”……诸多“丽”之外的又一新品种,是诗人独特感受与“清江锦石”化生而成的一个独立的生命。正是唐人对语言极其成功的诗化使用,催生了“兴象”说、“意境”说、“象外之象”说。
三
由哲学之象的暗示性到文学之象的韵味性,这一不断深化的认识、实践过程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诗经》中早就有“兴”的手法。“兴”的产生是中国诗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飞跃,因为“情志”找到了一条物象化的出路。不过汉儒所谓比兴,只取物象与人事相对应的象征意义,至六朝人始取其感应的关系,如上引刘勰所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物象由是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美学意义。在六朝山水诗创作中,山水兴象不只是“引子”或“附着物”,而是“道”的显现:“目击道存”、“以玄对山水”、“山水以形媚道”。玄学孕育了山水,山水摆脱了玄学。至唐人更是隐去象征与理念,让兴象独立自在。如孟浩然《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诗中只孤立出几个画面,但“低”字,“近”字轻轻一点,空间距离因主观而缩小了,人与自然更亲近了,诗人隐逸之情志便在其中。孟诗主体借助感受(“低”、“近”皆主观感受耳,非客观如此)潜入客体之中,即情即景,在唐诗中有典型性与普遍意义,是所谓“情景交融”的境界。殷璠 “兴象说”便是对这一创作实践的总结。殷璠《河岳英灵集》拈出“兴象”二字以评诗,是有见于“象”的自在性。盖兴与象并列,是两端确定,之间关系则不确定,从而留下很大的空间,有很大的容量。与前此的陈子昂“兴寄说”相比,子昂本为倡兴体而斥齐梁之用“比”,但“寄”字倾向太甚,易使人忽略形象独立的重要性,而成为义理之宅,误入“附理”之区。与后来的“神韵说”相比,则不致虚化太甚而魂不守舍。兴象并举,其中包涵着“天人合一”的思想,既不是由人向物的“移情”,也不是物成为人意念化的“象征”,人与物是互相感应的关系,物象具有了多重启发性与象外指向性的品格。这种自足性与指向性的品格在晚唐司空图“三外”说(“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味外之旨”)中获得突破性的超升。“三外”追求的不仅得“尽意莫若象”的信息传递,更是文学所特有的韵味,即情感联想。这一追求与西方符号论有其相通之处。苏珊·朗格在分析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曹》诗时指出:
诗中的每一件事都有双重性格:既是全然可信的虚的事件的一个细节,又是情感方面的一个因素。(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
“象外之象”所表达的也是对诗歌意象双重性格的感悟。然而符号论者更强调的是“一切诗歌皆为虚构事件的创造”,中国古文论却更强调据实构虚、虚实相生的韵味。《二十四诗品》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返虚入浑,积健为雄”,都强调创作时据实构虚而欣赏时则当虚而返诸“实”,虚实是处于不即不离的关系。画论更是言之历历,如方士庶《天慵庵笔记》云:
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见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
“别构”和“灵奇”,是虚境实景相叠,山苍树秀正在笔墨有无间。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三称:“右丞(王维)之妙,在广摄四旁,环中自显。”诗人不说出的地方,正是要读者落入的“圈套”。与朗格“双重性格”的提法相比,中国文论似更重视欣赏者离而复返的参与。“象外之象”,前象是诗人从客观世界“万取一收”而来的意象,后象则是欣赏者在前象启迪下通过情感联想而揉进自家经验与情感的诗人、读者共构之艺术幻象。“象外之象”的追求也是一种符号化的追求,但其表述要比现代符号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更空灵、更圆融。以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为例,她的符号论突出感情因素,却难以覆盖文学艺术的各种功能,如认识功能、教化功能等;而中国古文论总是“情志”并举,“情理”连用,覆盖面要大得多。用古文论的话语评析中国文学史现象,显然要贴近些、亲切些。
四
现在我们可以步入创作的中心环节:作者的构图。按一般规律,作者先要通过其创作准确表现自己的感受,并将此感受形成情感意象,才能唤起读者的情感联想而完成鉴赏过程。关键在“情感意象”之形成。用克莱夫·贝尔的说法,就是:“当一个艺术家的头脑被一个真实的情感意象所占有,又有能力把它保留在那里和把它‘翻译’出来时,他就会创造出一个好的构图。”(克莱夫·贝尔:《艺术》)创作的全过程可用下式示意:
感受—→情感意象—→构图—→审美情感。
由是,日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所引盛唐诗人王昌龄一段话引起我们的关注: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则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
境,是借用佛家语,指心灵空间,境生自心,是外物“内识”的结果。不过王氏沿用了传统的心与物之感应关系,故下文又云:“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综观之,感物与作文之间有个中介:境。这是由心击物所生,是所谓“兴发”,相当于上文所谓“情感意象”。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它表明古文论已深入到创作的核心问题。王昌龄认为,境之生不生关系到诗思之来不来。境生,则创作有了灵魂,当“以境照之”,统摄构图的过程。故上引文“深穿其境”后又紧接着说:
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则用,如无有不似,乃以律调之定,然后书之于纸。
回顾上文我们对情志、兴象的论述,可否对上文作如是观:境是情感结构对外来刺激作出的反应,由此形成选择,即“所见景物与意惬者相兼道”。也就是“思与境偕”之意,是以心境“照”实景的结果。反之,“意”与“景”结合不紧,诗便“无味”。用图式表示,便是:
目击其物—→心境生—→以境照之—→景与意惬。
不难看出此程式与本节开头的程式平行不悖,而更贴近中国抒情诗的创作实际。事实上“境”的提出是“比兴”历史的发展,是前人对诗意的整体性认识的加深。如果说早期“比兴”注重心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那末“境”的提出则标示了人们开始关注心与外部世界的整体性的感应关系。容以律诗为例稍加说明。
“捉对儿”表现事物的“对偶化”,本来就是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诗歌形式中的反映。然而在成熟的唐人律诗中,一联之间的意象不但是对应关系,更是两镜相摄互相映衬的关系。如王维《山居秋暝》名句: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其中景物不是孤立的,而是汇为“一片境”:月、松、泉、石之间形成张力,共构一片澄明的氛围,整个儿蕴含着意味,一联便是一个自足回环的整体。至如杜甫名篇《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迴。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或云,“万里”一联含八、九层意,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况当秋风萧瑟四可悲,登台易生悲愁五可悲,亲朋凋零独去登台六可悲,挟病而登七可悲,此病常来八可悲,人生不过百年却于病愁中过九可悲。这八九层意正是来自万里、悲秋、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诸多意象的交错组合。事实上岂止是此联,全诗中风急、天高、渚清、沙白、猿啸、木落……交织共时,如镜镜相摄的“华严境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味叠出。这种组合的可能性空间正是留给读者情感联想的自由空间,诗中秋景已非夔州实景,而是“离形得似”的艺术幻境,是读者毋需亲临夔州即可感受的一个“秋景”。诗中悲秋的情绪也不仅是杜甫个人的情绪,而是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提取的有普遍性的情感意象。中唐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曾提出“境生于象外”,可谓一语中的,将象与境的关系表述的颇为清楚,惜未及详论。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
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空中之音”云云,显然已不是心与物一一对应的关系,所强调的已经是各种形象的整体融一的感应关系。能将这种关系及作者、读者的双重感应在同一时空中体现出来,则有待今人王国维《人间词话》拈出“境界”二字。
五
《人间词话》有云:
严沧浪《诗话》曰:“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但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滕咸惠校注《人间词话新注》本,下同)
与严羽“兴趣”说、王士禛 “神韵”说相比,“境界”的确更周密,更能提纲挈领地体现文学的特殊性。许多论者指出王国维与叔本华之渊源关系,这固然是事实,但更应看到王氏并不仅仅是撷取西方文论的枝枝节节来阐释中国的文学史现象,更重要的是他从西方学习了先进的方法论,与古文论家相比较,更善归纳,有分析。他不但能明分主体、客体,而且能注重二者之间的联系,追求本质性的东西并加以归纳,这才是王国维得力之处。所以他宣称:“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境界”说的直接来源应是传为王昌龄作的《诗格》及皎然《诗式》。《诗格》有云: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乾隆敦本堂本《诗学指南》卷三)
这里的“境”不但指泉石云峰之类的客观世界,也指情与意,正是《人间词话》所谓:“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只是王昌龄将情、意分说,大略是传统的情志并举意思,而王国维的“情”则统称“感情”而已。皎然《诗式》则曰:
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
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揚上人房论涅槃经义》诗中又云:“诗情缘境发”。所云之“境”,既是外部世界的,又是经过情感反应后的,故曰:“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云云。王国维仍袭其意,曰:“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然而王国维高明之处还在于能以西方的方法论观照“境界说”,意识到境界已非纯客体之反映,而是诗人创构的艺术形象,故又曰:
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唯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文字,使读者自得之。
这里相当精确而明晰地表述了诗人捕捉稍纵即逝的感受并形诸文字的过程,远迈古人。“使读者自得之,又表明王国维对境界之形成必有读者之参与是有所悟的。
境界说的生命力还来自情景说。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宣称:“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事实上境界说的核心还是情景说,但强调的是情与景相乘而不是相加,注重其整体效应。自唐以来,情景关系一直是诗家讨论的热点。特别是清人王夫之,其论情景,可谓全面透彻,已达圆融的境界。王夫之的情景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情意的主导作用;一是强调真景真情;一是“现量”。前二者为学界所熟知,兹条例数则,读者与《人间词话》相参,自能别其源流:
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搏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已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绩中求活计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同上)
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薑斋诗话》)
谢诗有极易入目者……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渺有无之中,得灵蠁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卷五评谢灵运《登上戍石鼓山》)后一节言意象之形成,与上引王国维“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云云相较,尤觉圆机活转,不可替代。现在要说的是“现量”与王国维“不隔”之联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有云:
“僧敲月下门”,祗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现量,除了钟嵘《诗品·总论》所谓“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传统意义外,还借助这一佛家语强调审美心理的直觉性,是王夫之《相宗络索》所云“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这种直截手段来自对真景真情的追求,故其《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又云:
禅家有三量,唯现量发光,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审,便入非量。况直从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无盐之色败露无余,明眼人岂为所欺邪?
可见现量便是真情真景相触而成的艺术境界,正是《人间词话》所云:“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比“直寻”、“现量”更进一步提出“不隔”,要求作者将由真景真情相触而成的境界表达得澄明无碍,使读者易入其境而共创艺术幻境。“不隔”成为《人间词话》品评作品的一条具体标准,与真情、真景合为境界说以衡古今作者: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一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
境界说由是继承了传统的情景论却又更明晰、更具可操作性,弥补其易流于说玄的不足。王国维的努力成功地表明了以现代方法观照古文论,拓宽其内涵,弥补其不足,是一件大有可为的工作。
我们从古文论中选取了情志、兴象、境界这一组范畴进行重组,由此得出如是的程序:
情志—→兴象—→境界
这一程序显示创作的过程,即作者通过情志这一情感结构去感受外部事物,触发为情感意象,并以诗化的语言去创构一种富有启发性的兴象,通过作品中各种因素的整体效应形成氛围感染读者,在读者参与下完成艺术幻象——境界。当然,与极其博大丰富的传统文论相比,这仅仅是造了一块“砖”,远不足构成自成系统的文学批评话语。苟抛此砖可引群玉,则幸何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