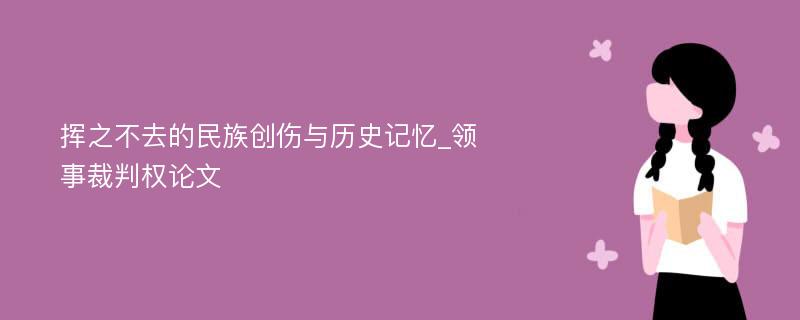
挥之不去的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挥之不去论文,创伤论文,民族论文,记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世纪40年代大清帝国遭遇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强力挑战后,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之一,应该说,租界带给中国人的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远比割地、赔款、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关税不能自主、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开放通商口岸等内容更切实、更持久。因为,与其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平等条约内容相比,租界不但存在于历史记忆中,而且仍鲜活地屹立于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重庆、厦门等大城市的繁华地段,令人挥之不去又思绪万千,甚至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和国民意志的一部分。 说起租界,尽管后世很多中国人都满怀着巨大的情感创伤,但是,真正能将这创伤说清楚的却只有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专业研究者,绝大多数的人都处于不明就里的状态。或者说,中国人的创伤记忆与其说来自历史事实,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文学性、宣传性的各种历史叙事。当然,最能激发国人神经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带有极度民族歧视色彩的宣传文字或影视画面。只要见到这几个字,几代中国人的仇恨瞬间便会凝结在一起,至于其中的学理依据、历史常识,是不会有人在意的。 其实,“租界”原本是个比较中性的词,并不具有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意味。《秘笈录存》中载: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曾在说帖中指出,租界是通商各口“划定专界备外人居住、贸易者”,“租界之地,仍为中国领土。其外人之执有地产者,仍须缴纳地税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无异”,但是治理权“或属于承受该租界之国所派领事馆,或属于纳税外国人民所选举之工部局”。①1925年,法学家周甦生撰文指出:“租界(Settlements or Concessions)不过是在通商口岸内划归外人住居营商之地域;这是出于外人居住生活上之一种便利的办法,而不带着治理权、委托或让渡的性质。所谓租界,正确的说来,只是外人‘居留地’,所以日本人使用‘居留地’之名词,较为明确。”② 即便是1920年代随着苏俄革命的输入,革命党开始用“五阶段论”和“反帝反封建”等阶级话语来阐释中国历史,但这毕竟只是小范围内的一种异域学说,尚未对租界文化产生实质性的颠覆影响。就是到了南京政府时期,“反帝”已作为主旋律被宣传,但是在学界和一般人那里,关于租界的认识依然比较客观。例如,1936年阮笃成在著作中写道:“租界(Concession),中国政府将某处划出之一地段所有土地,全部租与外国政府,再由外国政府分租与该外国侨民,双方租赁关系之当事人,为中国政府及外国政府,故又可称之谓‘国租’。”③民国时期外交学会编撰的《外交大辞典》中这样定义道:“一国在其领土内划定一定地带作为外国人居留贸易者,谓之租界(Concessions or Settlements)。租界之起因,系以两国通商之始,外人以风俗习惯言语宗教之不同,如使中外杂居,诚恐易生纠纷,故为行政管理便利起见,乃指定地点,令其聚居该地。久之遂成今日之所谓租界。”④ 不管在概念的阐释上有着怎样的细微差异,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国人对于租界的认识多半与后来不同,那种创伤情感和耻辱记忆也没有后世深厚浓烈。或者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化寓意的租界,其所承载的中国人的耻辱和仇恨情感,是后来被不断赋予、添加和深化的。 1950年初版、之后不断再版的《新编新知识词典》中这样写道:“租界是外人居留中国享有统治权的特定区域。这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不平等条约之一。普通分为公共租界和专管租界二种;前者是各国人共同居留共同享有立法权(纳税人会议)、司法权(领事裁判权)、行政权(工部局)的地方,后者为一国专享权利之地。中国人民曾为收回租界而不断斗争,至抗战胜利后始在名义上收回了租界,到解放后才真正逐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⑤ 1952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租界的注释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制清政府承认沿江沿海的某些地方为通商口岸后,并在他们所认为合宜的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他们的‘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帝国主义并经过这种‘租界’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⑥ 1961年修订的《辞海》对租界的解释是:“剥削阶级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其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它是剥削阶级国家对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⑦ 历史学家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写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土上,不少城市里有所谓‘租界’,那里的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设立法院、警察、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和税收机关。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武力恫吓,实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象一个毒瘤寄生在人体上那样起着极其凶恶的作用。”⑧ 这些定义和阐释作为现今《辞海》《现代汉语大词典》《新华字典》等权威工具书以及各种教科书、专业史书的蓝本,已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这样极具意识形态化的主流话语下,租界自然难逃各种指责,以至于成为几代中国人统一、固定的民族创伤记忆和全民仇恨的源发地。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掌握了词语(word)、术语(terminology)、词典(lexicon)也就掌握了世界,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 显然,近代中国的租界,是在通商口岸和外国人居留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一般的叙述中,上海道台宫慕久因为1845年与英国签订《上海租地章程》促成第一个“国中之国”的租界诞生而备受诟病,至今仍难摆脱历史的骂名。 其实,翻查历史文献可知,上海道台不过是代人——更是代历史受过。因为,从法理上来说,早在《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中就有条款规约,如第六款中载明:“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准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第七款载明:“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得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赁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⑨ 条约中清晰可见“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等提示性很明显的字句,上海道台在与英国签订《上海租地章程》的告示中,开首便援引了条约内容,然后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区域准予英国商人租住。可见,上海租界的形成并不是上海道台自作主张,不过是遵照条约和奉上谕而具体执行罢了。 而且,如果本着平常心来看,《上海租地章程》的二十三条条款连同1854年签订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十四条条款,签约双方的责任、义务甚至应该享有的权利都很明确和对等,如章程规定了租地每亩年租一千五百文、租户承担租界内修路和挖沟排水等基础建设、华民坟墓不得毁坏、华民定期扫墓、租主逾期不交地租者领事要出面处理等,不但没有新增不平等内容,甚至都谈不上不平等,说成是有偿交换的公平商业行为也未尝不可。如此奉谕行事、遵守契约的上海道台,却在历史上背负了长久的误解和骂名。 鲜为人知的还有,租界不仅算不得耻辱象征,当年还起过另类功效。例如,《广州租界史大事记》中记载:1843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十三行地区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租金是每年6000元洋银。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政府及土地的拥有者中国商人潘绍光都同意出租,但要求必须补偿佃户搬迁的损失二万两。英人想要租界十三行对面的河南田地数十亩,遭当地民众反对后以无果告终。⑩《清季外交史料》载:庚子事变后,当时的闽浙总督许应骙——鲁迅夫人许广平的祖父——在致洋务总局的复电中说:“鼓浪屿或做公地,或做租界,均无不可”。但必须负有“兼护厦门”的职能,“应由中外各国一体保护,以杜东邻(指日本)觊觎”。(11)可见,鼓浪屿租界的设立,是“以夷制夷”的政治智慧和政绩工程的重要体现。雷穆森在《天津租界史》中也提到,英租界原来的那些低洼地区经过填垫后,路灯和下水道设施完备,墙外的推广界地价突飞猛涨,十年前300两一亩的土地,至1920年代已经3000两了,“1922年年底这个地区全部地产的估价总计为1066706两,而房租估价为66151两”,“墙外推广界成为华北最适宜居住的住宅区之一”,“天津已经获得了公众普遍享有健康的令人羡慕的声誉”。(12) 当然,租界备受非议不仅仅是由于划定外国人单独的居住区,还因为管理权限方面的特权,即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而二者与租界一起,构成中国“丧权辱国”和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罪证”之一,也最终成为后世中国人民族耻辱的情感源头和发泄地。不过,激愤之余,还应该有些更理性的思考。 首先,需要考察一下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的历史渊源。尽管近代观念中的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和排他性,与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之间先天存在紧张和不兼容关系,但是在起初阶段它们确实曾经和谐相处过。据刘师舜在《治外法权之兴衰》中考察,1606年的“英法条约”、1696年的“葡西条约”、1701年的“法西条约”、1713年的“英西条约”、1787年的“法俄条约”、1788年的“法美条约”等规定了双向给予治外法权,而这期间的1648年,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签订,独立的民族国家领土完整、国家间互惠性和平等性的国际法则已经初步确立。 后来,随着主权国家观念的逐步深入以及欧美各国不断修正国际关系,治外法权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但是,正如人与人之间因为智力、个人努力程度等因素导致对世界的认知有先有后一样,世界各国的发展也处于这样的一种先进与后进并行的态势中,当有些国家已经在文明大道上疾步时,有些国家却还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或半闭关锁国的阶段,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 因此,相对于近代化程度缓慢、尚未进入国际条约体系内的土耳其、大清国、日本和暹罗等国,被迫适用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一定程度上便是暂时无法分享这一文明成果的体现,但到1899年、1923年,随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断与欧美接轨,土耳其也签署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简称《洛桑条约》),两国分别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而中国迟至1943年才终于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当然,大清帝国当年也并不仅仅是受害国,如1871年9月在与日本平等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第八条中规定:“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第九条规定:“两国指定各口,倘未设理事官,其贸易人民均归地方官约束照料,如犯罪名,准一面查拿,一面将案情知照附近各口理事官,按律科断。”(13)条约内容显示,中日两国当年是互享治外法权的,虽然这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至于大清帝国在朝鲜、越南等藩属国所享有的包含治外法权、租界、驻军等特权,这里权且不作评议。 其次,要知道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适用于大清帝国是国情不同的产物。众所周知,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人身保护律》(1676)、《权利法案》(1689)、《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789)以及民主宪政、法治社会等规则已被欧美文明国家所普遍接受和沿用,并成为其立国法典和行动指针。但是,19世纪中叶的大清帝国,尚不具备主权观念,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从未分立,公民不能“当家做主”,法治无从谈起,司法审判非专业化,自由人权更是天方夜谭。两厢遭遇,必然水火不容、无法调和。 以实例来看,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交涉不畅时便软禁所有外商,其中包括美国、荷兰等守法商人。林则徐以武力围困外国商馆并断绝食品和水一个多月,将英国政府的代表颠地、义律等扣为人质,宣布与英国永久停止通商等,这些举措在大清帝国君臣眼里,是天朝上国的当然权力,是内政;但是在英美商人和政府代表看来,则是违背自由贸易的正当性,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人权,属于野蛮国家的野蛮行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就在1839年4月2日致巴麦尊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们与这个帝国的交往中,它的政府无端地发起侵害英国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冒犯英国政府尊严的行动,这是第一次……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14)在清方这里,对于那些不守法的外商,道光皇帝下旨拟定专条:按开窑口例治罪,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立决”。林则徐奉谕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15)但是这样雷厉风行的条款在执行中就遭遇了挑战,英国商务代表义律等“始肯具结,惟结内但云:‘如有鸦片,将货物尽行缴官。’而于‘人即正法’字样,仍不肯写”(16),因为在他看来不经正当审讯程序即判处人死刑,与英国的法律观念和司法实践相悖。在“林维喜命案”中,林则徐等大清官员认为,杀人偿命,中外所同,英方应交出凶手;义律则根据英国法律拒绝交出凶手,并自行组织23人的陪审团进行审判——结果被英国议会否决,理由是审判资质与权力存在僭越问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鸦片而起的通商战结束中英两国缔结和平条约时就需要进行司法协调和接轨,于是,《江宁条约》签订后,钦差大臣耆英在给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的照会所附清单的十二项交涉内容中,其中第一款提出:英国商人来清国贸易时可居住在通商港口的“会馆”,贸易结束后应“回船回国”;第二条提出:今后如有清国商人拖欠英商款项,“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第八款提出:“英国商民既在各处通商,难保无与内地民人交涉狱讼之事。从前英国货船在粤,每以远人为词,不能照中国律例科断,并闻欲设立审判衙门,如英国之呵压打米挐一样……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为此,璞鼎查在给耆英的复照中提议:“嗣后应如所议。除两国商民相讼小衅,即由地方官与管事官(英国领事)会同查办外,所有犯法讨罪重端者,英人交本国总管审判,华民交内地大官究惩。”(17) 在这种你情我愿中,接下来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第九款规定:“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船、货船避匿者,一经英官查出,即应交与华官按法处治;倘华官或探闻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查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若已经罪人供认,或查有证据知其人实系犯罪匿逃者,英官必即交出,断无异言。其英国水手、兵丁或别项英人,不论本国、属国,黑、白之类,无论何故,倘有逃至中国地方藏匿者,华官亦必严行捉拿监禁,交给近地英官收办,均不可庇护隐匿,有乖和好。”(18)之后是:耆英主动倡议、璞鼎查接受而签订的更为详尽、明晰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其中第十三条款——“英人华民交涉词讼一款”:“凡英商禀告华民者,必先赴管事官处投票,候管事官先行查察谁是谁非,勉力劝息,使不成讼。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者,管事官均应听讼,一例劝息,免致小事酿成大案。……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移请华官公同查明其事,既得实情,即为秉公定断,免滋讼端。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19)这一条款内容本身存在人为地干涉司法的问题,例如“勉力劝息,使不成讼”,司法不在场,结局很可能是公民权益受损而无处申明,尤其是强大的公权力直接侵占和掠夺个人利益时,个人权益是无法维护的。 当然,大清帝国的官吏是不会考虑这一问题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最大可能地减少地方官在中外交涉中的麻烦。或许这样的功利心理与执着追求,也许正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论语·颜渊》中就有自以为伦理道德高尚的国人自豪的古训:“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对于大清帝国君臣主动奉送治外法权一事,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分析道:“耆英和协助他的黄恩彤并不了解这些条款损害国家主权之大,反以为有许多便利。中外人民各按本国法律管理,不失为公道办法,只要英国不庇护汉奸,他们已感到满意。”(20)茅海建也对此评说道:“国家设官治民。既然中国官府无法治理这些英人,把他们交由英国官府来治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21)孟森在《清史讲义》中的评价更值得思考:“此为当时英人所梦想不到,不自意处人法律管辖之下,竟能不受管辖也。是为领事裁判之由来。……英所未请,中国强予之。英人报以甚属妥协四字,不平等之祸,遂延至今而未已。”“若照《白门约》(中英《南京条约》)通商范围与各国订定,原无不平等条约发生。其不平等者,中国君臣强要之,使英人不得不覆,而后节节授以侵占之便利。然其初英人且有不愿承受之端,覆辞责中国官不应退让至此者。”(22)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确,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并非英方强行逼迫,而是大清帝国主动赠予。再后,就是大清帝国与美国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的第二十一条款:“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案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但须两得其平,秉公断结,不得各存偏护,致启争端。”(23) 除了上述法规性的条约约定,还有就是现实问题促成的决定。据《上海租界志》载,1850年代,上海租界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但是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而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成为惯犯。租界工部局和警察局对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这样的结果自然更加促使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推进和固化,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后由民国外交官们在平等协商、文明交涉的基础上于1943年彻底终止。 历史地看,既然中外法律如此天壤之别、南辕北辙,寻求并轨和统一不能办到,二者必选其一,结果自然可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不护短地说:“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24)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是英法美等国屈从或遵照乾隆时期修正的《大清律例》,斩立决、凌迟、满门抄斩等野蛮酷刑以及非法监禁、禁止言论和出版自由等法令被广泛应用,那将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如果进行一下换位思考,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平等,是“丧权辱国”,但对欧美各国来说,却是争取平等和人权的外交胜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前的大清帝国几乎没有给过欧美各国及其民众以平等待遇,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大清帝国19世纪逐渐形成的一套规范和管束外国人的行为准则。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记有这些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条文: 1.外国兵船须停江外,不得进入虎门。 2.妇人不得混入商馆,铳炮枪及其他武器均不得持入。 3.所有航路引水人及买办等,概须我国澳门同知之特许登录;非受买办之直接监视,不许外国船舶与其他商民之交通。 4.各外国商馆不得使用八人以上之华人,并不得雇佣妇仆。 5.外人不得与我国官吏直接交涉,除非经过公行之手续。 6.外人不许泛舟江上,惟每月初八、十八及二十八三日,得游览花地海幢寺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十人。不准赴别处村落墟市游荡。 7.外国人不准用轿,不得用插旗三板船舶,只准用无缝小船。 8.外人买卖,须经公行之手,即居住商馆者,亦不许随意出入,防其与奸商有秘密交易之行为。 9.通商期已过,外人不得在广州居住。即在通商期内,货物购齐,亦须装载而归,否则,可往澳门。 10.外国船舶,得直接航行黄埔,徘徊河外,不得寄泊他所。 11.不准购买中国书籍、学习中国语言文学。 12.公行行商不准有欠外人之债务。(25) 通晓清史的人都知道,此公文集大成于乾隆时期的《防范外夷规条》(又称《防夷五事》)、《防夷四查》,嘉庆时期的《民夷交易章程》《整饬夷商贸易九事》,道光时期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防夷新规八条》,并施行于各国来华的政府特使和商人中,而除第一条外,其余各条无不带有歧视性质,然而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却一直缺少反省。责人容易责己难,虽然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在公平和公正原则下,学者要与普通民众拉开距离,否则便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追求真理无国界等普世文明相背离,其学说本身也就禁不住考验了。 还有一点需要明确,不管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令后世的中国人如何愤恨,但它在当年却并未产生后来被建构起来的那种民族仇恨。孟森在《清史讲义》中就曾指出:“故许英通商,弹劾者纷起;赠人领事裁判权,反历久无抵斥之声也。”(26)蒋廷黻也在《中国近代史》中说:“道光时代的人的看法完全与我们的两样: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因为他们想以夷官按夷法来治夷人是极方便省事的。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想把税则一五一十地订在条约里可以免许多的争执……他们不反对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因为他们想不到有中国人要到外国去,其实当时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27) 毋庸置疑,按照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现代世界的外交惯例,租界以及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内容具备侵犯主权的特征,但是正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适用“不溯既往”而仅限于1980年1月27日生效后一样,解读历史还是应该回到历史现场,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很多历史问题就会陷入自说自话的无谓争论中,所以,看待租界以及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问题,后世人不能凭着激进的民族情绪简单照搬现代文明规则去评头论足、发泄情绪,而是要抱以历史之同情和学术客观的态度。 顺便说,曾经作为主流历史叙事和文学书写的耻辱地——租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变迁后,现今基本都成为城市名片,集商业贸易、城市旅游、休闲娱乐、文化景观于一身,而且愈来愈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这一点,现今的上海、天津、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就是明证。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或者真是与辩证法合辙了。当然,客观世界的变化还在于主观世界的开放和包容,固守狭隘、受害的思想和观念是不利于走向现代文明的。 注释: ①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73~174页。 ②周甦生:《上海租界的性质及组织》,《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七期,1925年6月。 ③阮笃成:《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第2页。 ④外交学会编《外交大辞典》,中华书局,1937,第705页。 ⑤《新编新知识词典》,上海北新书局,1951,第436页。 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第43页。 ⑦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试行本)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61,第22~23页。 ⑧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2,第64~65页。 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5~37页。 ⑩袁东华:《广州租界史大事记》,载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的洋行与租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193~194页。 (11)《“公共租界”鼓浪屿》,载《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鹭江出版社,1990,第16页。 (12)雷穆森:《天津租界史》,许逸凡、赵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第290~291页。 (1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18页。 (1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360页。 (15)《林则徐全集》第5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117页。 (1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一,中华书局,1964,第235页。 (17)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第217~223页。 (18)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6页。 (19)同上书,第42页。 (20)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70页。 (2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97页。 (22)孟森:《清史讲义》,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第520页、515页。 (2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54~55页。 (2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第22页。 (25)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二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第836~837页。 (26)孟森:《清史讲义》,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第520页。 (2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