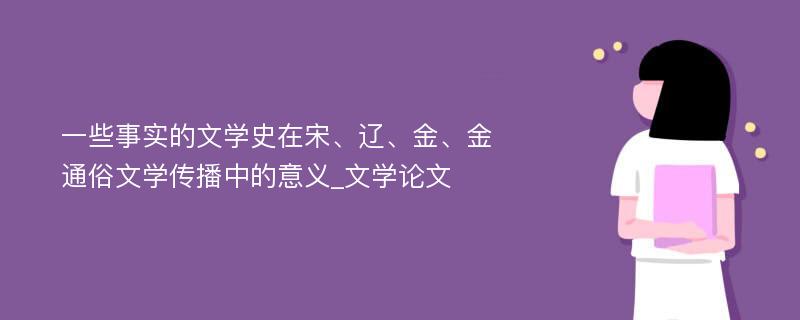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事实论文,意义论文,文学论文,宋辽金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宋辽俗文学的交流
宋辽俗文学交流的事实,因文献有限,可供论述的例子并不很多,但下例却值得文学史研究者们特别关注。
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皆歌之。……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初与女真使命往来所致耳。(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
曾敏行的记载是可信的,刘子翚《屏山集》卷十八《汴京纪事》有诗曰:“仓皇禁陌夜飞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尘埋皓齿,不堪重唱蓬蓬歌。”意思是:金人破汴京后,大批人(皇亲国戚、乐工、手艺人等)被掳到北方,盛行一时的《蓬蓬花》歌曲再也无人唱了。“不堪重唱”还有一重含义是:报应。据江万里《宣政杂录》记载:
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朝辽民来居京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其声而效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公。”本辽谶,故京师不禁。然次年徽宗南幸,次年,二圣北狩。又有伎者,以数丈竹竿系椅于杪,伎者坐椅上,少顷,下投于小棘坑中,无偏颇之失。未投时念诗曰:“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此亦辽谶,然兆祸可怪。(注:据杨复吉《辽史拾遗补》卷三《本纪第三十·天祚皇帝四》引。“辽民”、“辽谶”,现通行的《宣政杂录》版本均作“金民”、“虏谶”、“金谶”或“北谶”,非是。宣和四年九月(公元1122年),辽将郭药师举涿州归附北宋,辽民大量涌入汴京,契丹歌曲由此传入京师。此时的金国立国不过才八年,忙于与辽征战,还没有与宋建立直接文化交流关系(只有外交人员往来),“以归朝金民来居京师”于史实不符,且此时金国尚处于急剧上升时期,何来“金谶”之有?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北宋王朝还在幻想着联金灭辽。再从歌曲本身反映的历史现象来分析,《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之类歌曲,不可能出现于此时的金国,只能出于辽、北宋。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是暂时的,不久便亡国了,此地又被金人夺去,这就是“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的意思。这则材料经常被学人引用,少有辨析者,就笔者有限的见闻,似乎只有李炳海先生《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第195—196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朱瑞熙等人所著《辽宋金西夏社会生活史》(第2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引用作“辽民”,极是。因本则材料涉及的文学史意义重大,故特指出。)
原来此曲流行于汴京,是“上面”有意纵容、幸灾乐祸的结果。时隔三年,北宋继辽之后亡国,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刘子翚此诗可谓是沉痛之至。
这段记载透露出的信息是:(1)宋辽俗文学交流比较活跃;(2)辽代已开北曲先声。
先谈第一点。从曾敏行的记载来看,《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歌曲是从辽输入北宋的。《东京梦华录》卷七对军中蛮牌舞队(百戏之一种)的演出情况有记载:“乐部举动《琴家弄令》,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大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一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东京梦华录》记录的舞队演出情形发生在北宋末,但蛮牌舞队在辽国也上演,它可能存在了很久时间。《三朝北盟会编》“正宣上帙”二十引《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当时(公元1125年)金国新国主招待北宋使者的宴会上,“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砑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簸旗筑毬,角觝、斗鸡、杂剧等,服色鲜明,颇类中朝”。下文(第二节开头)将提到,这个时候的金国刚从辽独立出来不久,基本上还是原始社会形态(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许亢宗到达金国都城附近时,“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而皇城也是“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可见当时金国的社会形态还相当原始。),还远在黑龙江省,与北宋相去甚远,金国此时如有百戏表演,大多也是从辽国掳掠过去的。因此,本处所记载的内容,只能看作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事实。北宋蛮牌舞队所唱曲子是《蛮牌令》,那么,辽代歌曲《蛮牌序》也当是辽国蛮牌舞队所唱的曲子。“令”指一种急拍唱法(注:谢桃坊《〈高丽史·乐志〉所存宋词考辨》,《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此处正适合军队演出的场合),“序”是曲段的称谓,二者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但《蛮牌令》与《蛮牌序》都同指向《蛮牌》曲子是没疑问的。据研究,《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仍保存着《扑蝴蝶》、《大斋郎》、《胡女怨》、《杵歌》、《鲍老儿》、《六国朝》、《蛮牌令》、《乔合笙》、《乔捉蛇》等宋代舞队的曲名。由此可知,《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等辽代歌曲,后来曾进入宋舞队唱曲。如果不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分析,很难理解它们会如此巧合地同时流行于南北两地。换句话说,两国之间俗文学的交流是很频繁的。另一个例子是迓鼓戏。迓(砑)鼓戏是北宋王韶于熙宁五年(1072)平熙州(今甘肃临洮一带)后创制的,数年间流行于世(注: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七。)。《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当时金国也上演此戏,如上所述,这都只能看作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事实。《迓鼓》先从北宋传入辽国,再因战争原因而流入金国,并非宋金之间有直接的文学交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禁番曲毡笠”条记载:“至政和初,有旨立赏钱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着北服之类,并禁止支赏。”这里明确提到“番曲”、“北曲子”,都是指辽代歌曲。辽曲流行北宋,由来已久。
再谈第二点。自明代以来,曲学研究者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曲的起源追溯到辽代,如《盛世新声·引》中提出:“南曲传自汉唐宋,北曲由辽金元。”稍后的刘楫序《词林摘艳》时也说:“至金元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这些论断大多出于直感式的猜测,并没有实证作为基础。将北曲起源时间上溯到辽金,反映出明人已从词、曲音乐的差异性来看待北曲的起源问题,而徐渭在《南词叙录》说得更明白:
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很(狠)戾,武夫马上之歌。北曲岂诚唐宋名家之遗?不过出于边鄙裔夷之伪造耳。
杨栋先生对这种思路颇为赞赏,认为“划清了北曲与唐宋词乐的本质区别,从而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注: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对北曲起源的探讨,有很多说法,徐渭代表了其中的一种。其他重要的还有:源于词说,此说起于元代陶宗仪,明人多附和之,影响最大,复经王国维用统计法推论((《宋元戏曲考》第八《元杂剧之渊源》)),信之者益众;源于《诗经》、汉乐府说,如明沈宠绥《弦索辨讹》、王骥德《曲律》均主其说,宋人论词源时也曾上溯于此,欲尊词体,明人袭宋人故智,不足论;词曲同源异流说,同源即词曲同于唐曲子,后唐曲子经文人之手发展成宋词,而民间唐曲子则为“暗流”,演变成北曲,此说起于任半塘、吕思勉,章荑荪、李昌集畅其说;源于民歌说,此说起于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其时“民间文学源头说”风行一时,郑氏重视俗文学,故有此论;祖其说而进一步深入者,则是北曲源于宋金俗曲说,此说起于王文才《元曲纪事》,而杨栋先生申其论,“我们确定北曲之源为北宋末年流行于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的通俗歌曲”,见杨氏著《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第52页。北曲源于宋金俗曲说代表着目前关于北曲起源的最新成果,本文所论《蓬蓬歌》,亦在杨氏所指“通俗歌曲”内。如果我们确定北曲起源离不开北方音乐,即“蕃曲”,那么,笔者认为,探讨北曲起源,理应对宋辽金俗文学交流的事实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的歌词没有流传下来,但可从仅存的《蓬蓬花》歌词来窥豹之一斑:
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公。
其实,现存的这首歌词是不完整的。《宣政杂录》的记载很清楚地表明,本歌曲还有和声。和声一般在本词末尾,不表实际意义,仅表节奏,故不记录下来。“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如若还原,它或许应该是这样的:
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公。臻蓬蓬。臻蓬蓬。
这种文学样式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萧观音的《回心院》: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
两者相较,句式十分接近,唯前者第二句为七字(“花花”二字明显带有口语痕迹),后者第二句为五字(这种细微差别,正体现了民歌与文人创作的差异);押韵形式相同。进一步看,这种押韵特点与散曲的押韵也是十分相似的。《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蕃曲”不见于词调,而或见于杂剧词和散曲曲调,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蓬蓬花》等歌曲都是一种新兴曲子,即北曲。这说明,在辽代,以《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为代表的“蕃曲”已开北曲先声。过去,对萧观音的《回心院》这种文学体裁,它究竟是诗是词颇有争论,现在是否可以换一个视角,跳出诗词之争的范围,从“北曲发生”这一角度,来重新审视它的文体归宿以及确定它在文学史的意义?据《焚椒录》记载,萧观音写成《回心院》后,曾“被之管弦”,说明它是用来歌唱的,这更加深了我们将它与《蓬蓬歌》进行类比研究的印象。我们对萧观音的创作才能丝毫不怀疑,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相信:与其说《回心院》是萧观音的独创,倒不如说是她借鉴和利用了现有的民间歌谣(如《蓬蓬花》)的形式。《契丹国志》卷七记载辽圣宗耶律隆绪(971—1031)精通音乐,不但能写诗,“又御制曲百余首”,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萧太后的创作决不是横空出世。
辽代文学是否具备“开北曲先声”的可能?从更广阔的辽与中原文化交流史来看,答案是肯定的。辽文化的主体基本上是从五代(中原)文化移植过去的。《辽史》卷五十四载: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遣刘煦以伶官归辽, 带去散乐;会同九年(公元947年),辽太宗出兵汴京,将后晋礼乐器物悉数掠去,这些战利品构成了辽代礼乐文化的基础。辽主与五代的君王们在文化气质上十分接近,后者的文化气质如何?以后唐庄宗李存勖为例:“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箧(古代郎中的医箱),令继笈(庄宗子)相随……后方昼眠,乃造其卧内,自称刘衙推访女。”原来李存勖之妻刘氏出身贫寒,现在做了第一夫人,当她那做江湖郎中的老爸进宫找她时,她拒绝相认,还称来者是田舍翁。李存勖此处扮演实在是调笑妻子。事实上,无论是五代君王还是辽主,抑或是前后蜀主,都有一种亲近戏谑文化的倾向。这种记载到处可见,不烦一一列举。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痛心疾首地对君王偏好俗文化的文化取向提出的尖锐批评了。北宋孔道辅出使契丹时,契丹在招待宴会上进杂剧,以孔夫子为戏,孔道辅愤然离席(《宋史》本传)。契丹人以为孔道辅是孔子后代,戏孔子就是戏孔道辅,戏孔道辅就是戏北宋。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事件。也许,从辽国方面来看,这只不过是一种游戏谐谑罢了,因为这是他们常演的剧目(注:以孔子为戏似乎由来已久。敦煌写卷本3218所载《浣溪沙》词第二首云:“喜睹华筵戏大贤。歌欢共过百千年。长命杯中倾渌醑,满金船。把酒愿同山岳固,昔日彭祖等齐年。深谢慈怜兼奖饰,献羌言。”“华筵戏大贤”大约就是以孔子为戏了。据研究,本词当作于唐大中五年(851)年前后,而本卷的抄写则在后晋开运四年(947)以后(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说明百戏中以孔子为嘲谑对象的表演,自唐末五代辽以来一直流行着。)。这些都是北曲能在辽代产生的极其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词曾流入辽地(《北梦琐言》卷六载,后晋宰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流行于洛阳汴梁等地,辽太宗攻入汴京梁时,称和凝为“曲子相公”,这说明和凝的词已流入了辽国),但辽国文学界似乎并没有受其影响大量转向词的创作,这一点与后来金国的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从现存不多的辽代文学作品来看,辽代作家正在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诗,也不同于词的新兴文学样式。《全辽文》卷十二所收的无名氏《寄夫诗》云:
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题目《寄夫诗》当是后人所起,这四句韵文显然不能当诗歌来看。李炳海先生认为:“其中七字句都加了衬字,从而更接近口语,和后来的小令极其相似。”(注:李炳海《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契丹国志》卷二十五“张舜民使北记”条载:“胡人吹叶成曲,以蕃歌相和,音韵甚和。”金元人称曲子为“叶儿”,盖源于此。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载:辽代大乐的四旦二十八调,“此即今九宫谱之始”。换句话说,辽代的四旦二十八调即北曲宫调之始。这样看来,辽代歌曲开北曲先声更有乐理依据了。
《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歌曲,它们同时流行于南北两地,流行于辽的,开北曲先声;流行于宋的,最后也融入到南曲之中。除前面提到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仍保存着《六国朝》、《蛮牌令》等宋代舞队的曲名外,《风月锦囊》所收《杀狗》戏文中,也有《蛮牌令》曲调。当然,《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虽然开北曲先声,但它们决不是北曲唯一的来源。北曲的形成,还会有其他艺术因子的加入。
二、宋金俗文学的交流
女真族于公元1115年建立大金政权,定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之白城子)。自此至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中都,今北京附近),为金前期,史家称金内地时期;自迁都燕京到金亡,为金后期。女真在辽时尚处在部落联盟制社会阶段(约为原始社会末期),反辽时过渡到军事奴隶制社会阶段,并通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掠夺,在短短几年里,迅速完成了文化上的原始积累,一跃进入部落制封建社会阶段。
金天辅四年(1120)金兵攻陷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族波罗城),辽国的教坊四部乐被金国当作最重要的战利品带回。宣和七年(1125)宋朝使者许亢宗出使金国,金太宗完颜晟设宴招待他,用乐部二百人。这二百人就是金国从辽掠夺去的辽教坊四部乐:“酒三行,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由于刚掠夺过来不久,表演时还要加入女真族的一些巫术因素:“又有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立于百戏后,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如祠庙所画电母。”(《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金灭辽时,辽代的杂剧艺术已有较长的发展史,已经有了成熟的杂剧表演。从河北宣化出土的辽代墓壁画《散乐图》来看,辽代的杂剧表演,演出队伍庞大,分工明确。辽代杂剧是五代时从中原传过去的,《辽史·乐志》“散乐”条记载:“晋天福三年(938)遣刘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散乐”即杂剧。《契丹国志》卷二十五“胡峤陷北记”条记载,胡峤于后晋开运四年(947)被契丹掳去,行至上京,见“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辽代戏曲文学的发展,端赖这些历来源源不绝流入北方的中原文艺工作者。
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史称靖康之变。靖康之变不但是一次政治上的大事件,也是文化史上的大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它客观上为金代俗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灭北宋,艺人之流向大致有二:一是南奔,二是北迁。刘子翚《屏山集》卷十五《靖康改元四十韵》:“肉食开边衅……黔黎惊瓦解,冠盖尽星奔。走辙秦城地,浮舟楚峡村。画堂空锁钥,乐府散婵娟。”《汴堤》:“参差歌吹动离舟,宫女张帆信浪流。转尽隋堤三百曲,夜桥灯火看扬州。”朱敦儒《鹧鸪天》:“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唯有李夫人。自从惊破霓裳后,楚奏吴歌扇里新。秦嶂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停杯泪满巾。”均是歌妓南奔的记录。艺人南奔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只谈谈艺人北迁的一些情况。
《屏山集》卷十八《汴京纪事二十首》有诗云:“仓皇禁陌夜飞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尘埋皓齿,不堪重唱蓬蓬歌。”“南去人稀北去多”,何以见得?《靖康稗史》之二韦承《瓮中人语》载:“靖康二年(1127)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辂冠冕、宫庭仪物及女音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黼、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二十九日,虏索大礼仪仗、大晟乐器等出城。二月初六日,废帝为庶人,令太上、后妃、宫御、诸王王妃、帝姬(共三千余人)出城。十四日,索天官、内侍、僧道、秀才、监吏、裁缝、染木、银铁各工、阴阳技术、影戏、傀儡、小唱诸色人等及家属出城。”《靖康稗史》之六《呻吟语》载:“五月十九日,(分赏)内侍内人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燕人云:‘天会(1123—1138)时,掠夺宋国男女不下二十万人,贵戚子弟天会五年十不存五,妇人十人九娼。’”《三朝北盟会编》第七十七也记载,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人令开封府追寻到杂剧、说话、小说等伎艺人一百五十余家,押送军前。后来还多次索要杂戏、倡优诸色人等不计其数。
南宋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出使金国,经过真定,发现这里还保存着北宋大曲歌舞。他说:“虏乐悉变中华,唯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并有诗纪之:
紫袖当棚雪鬓凋,曾随广乐奏云韶。老来未忍耆婆舞,犹倚黄钟衮六么。(《范石湖诗集·真定舞》)
“棚”指乐棚,即戏台,“雪鬓凋”云云,指原北宋艺人渐渐老去,新一代艺人都是成长于金国。“虏乐悉变中华”,说明此时中原地区流行的音乐主流已是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即北曲音乐。三年后,即乾道九年,韩元吉出使金国,于故都汴京听故国教坊乐,因起黍离之叹:
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
“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韩元吉看到的原北宋教坊乐工也已是渐入老境。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十三记其父使金时,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佐酒侍儿乃宣和殿小宫姬,吴激(米元章婿,宣和四年使金国时被迫留仕)当场赋词云云(此事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徐大焯《烬余录》、元刘祁《归潜志》卷八均有不同版本的记载)。洪皓使金事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与吴激相会的地点是金上京。北宋乐工大部分被金人带回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上京,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这些乐妓们演唱的歌曲,只能是宋词,且据《大金国志·海陵记》记载,金宫廷中演唱的曲子有柳永的《望海潮》等。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甚至夸张地说到,完颜亮听到《望海潮》曲子中称赞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于是下决心要打过长江,占有江南。
北迁艺人带来了金内地时期俗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的繁荣局面。1964年以来,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金都故址白城陆续发掘了数面铜镜,其中的人物故事镜,背面铸有《月夜听筝》、《野猿听经》、《牛郎织女》、《蟠桃会》、《广寒宫》、《柳毅传书》等故事图案(注:本段资料据张福海先生惠赠《黑龙江戏曲史》一书,见该书第63—64页,哈尔滨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故事均见于《院本名目》或《官本杂剧段数》(《野猿听经》除外,但元杂剧有《龙济山野猿听经》)。据张福海先生考证,这些故事来源渠道不外乎两条:一是被掳的北宋艺人所传播,二是来自金院本。但是金院本也是宋金艺术家们一起创造出来的(注:张福海先生认为:“被金人掠到(金)内地的北宋杂剧艺术,经过女真人和汉人的共同努力,酿造出院本的新机制。”见《黑龙江戏曲史》第65页。),因此,这些铜镜故事反映了宋金俗文学交流的一个侧面。
自采石矶战役(1161)以后,宋金两国进入对峙阶段,双方都无法发起针对对方的重大战争,两国因此也都走上了繁荣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稳定的社会秩序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宋金俗文学交流表现在多方面,可供利用的材料也较多,唯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和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为我们研究宋金俗文学交流提供了具体的作品记录,本文试图从二者所透露的某些信息,来探讨宋金俗文学交流的某些情况。
先将《官本杂剧段数》稍作分析。周密《武林旧事》前六卷与后四卷的编纂方式有明显差别,前六卷出于作者精心积累,后四卷系摘抄编辑现存他人相关著述。明白这一点,对理解“官本”二字有一定帮助。请看第九至第十卷目录: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卷十《官本杂剧段数》、《张约斋赏心乐事》(有张镃自序。张镃自号约斋居士)、《约斋桂隐百课》。考虑到周密与张家非同一般的紧密关系,笔者认为《官本杂剧段数》极有可能是出于张家的家族文献,也就是说,《官本杂剧段数》可能是张家历代保存的剧目清单。否则,无法解释这份清单为何偏偏夹在张家文献里来叙述。另外,《官本杂剧段数》后紧接着《张约斋赏心乐事》,张镃自序说:“因排比十有二月燕游次序,名之曰‘四并集’,授小庵主人,以备遗忘。”再联系到《齐东野语》卷二十所载张镃豪奢的生活,笔者推测《官本杂剧段数》就是清河郡王家宴时的演出清单。因此,作为“官本”,它更多地保存了北宋以来的杂剧传统,对南宋兴起的民间伎艺吸收不多。这与《院本名目》大量吸收民间杂戏的艺术成分有明显差异,这种保守性是由于它的“非坊本”特点所决定了的。这是我们在对两份清单进行对比前要注意的。
《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所载基本上是金人院本,这一点,向来没有多大争论。院本共分11类:和曲院本,杂剧名后缀大曲名,如月明法曲等(注:公元1190年,金人王寂出按辽东,于官舍屏风上,见所画大曲故事,如《胡渭州》大曲所演为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新水》大曲所演为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薄媚》大曲所演为郑六遇妖狐的故事,《水调歌头》大曲所演为裴少俊墙头马上的故事。见《辽东行部志》。这四折故事,当为“和曲院本”之类无疑。),上皇院本,上演与宋徽宗相关的杂剧,题材相对集中,并集为一类,当是出于流亡于金的宋艺人所作(“上皇”是宋人对宋徽宗的称呼,金人未必如此称呼宋徽宗;其次,题材如此集中,并在杂剧中占一类,这也许是宋艺人集体反思历史的一种形式),而且它应完成于金内地时期;题目院本,似演与文人有关的杂剧;霸王院本,演与武人有关的杂剧;诸杂大小院本,角色身份不一,但以下层人士居多;院么(自此及以下很难看出分类标准),《中国曲学大辞典》推测它是元杂剧定型早期的一种演剧体制,既不同于院本,也不同于院爨;诸杂院爨,所用曲调有法曲、大曲、词曲,涉及的书籍有《论语》、《孝经》等,其中标明“爨”者有二十一种;冲撞引首,应是院本开演前表演技巧性强而又滑稽的段子;拴搐艳段,拴搐一般都解释为“收束”之意,但《武林旧事》卷一“天基节排当乐次”“再坐第六盏”说:“杂剧:时和以下,做《四诺少年游》。”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有曲唱云:“做院本生点个《水母》砌,拴个《少年游》。”可见“做”与“拴”意思有相通的地方。艳段是杂剧的开始部分,“艳段”又作“焰段”,焰即易明易灭之意,故焰段即极短的小剧;打略拴搐,从剧名来分析,一是组织事物名编成一段唱念词,一是以社会上各色人物作自我嘲弄以取悦观众,据推测,它应是用于院本末尾;诸杂砌,据其名目分析,内容涉及众多历史人物,如梅妃、武则天、黄巢、史弘肇等。
从两份清单所列名目来看,两者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还真不少(注:当然,两份剧目清单也反映出宋杂剧与金院本已有明显的差异。《官本杂剧段数》中,带大曲名的杂剧名目数量上远远多于和曲院本,这说明南宋的杂剧(至少是上层社会流行的杂剧)中,歌舞戏成分还占很大比例,而金院本中,歌舞戏的成分已非常少了。这一方面表明大曲音乐可能不适于北人耳目,如上举范成大出使金国时看到“虏乐”在北方越来越流行,北曲、南曲各自面目渐渐清晰地呈现,另一方面也表明金院本的演出体制已从杂戏中独立出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也许是金人不沿用宋人“杂剧”称谓,将杂剧改称“院本”的原因之一吧。)。《官本杂剧段数》有《王子高六么》,《院本名目》中有《闹芙蓉城》;《官本杂剧段数》有《裴少俊伊州》,《院本名目》有《鸳鸯简》、《墙头马》;《官本杂剧段数》有《风花雪月爨》,《院本名目》有《风花雪月》;《官本杂剧段数》有《病郑逍遥乐》,《院本名目》有《病郑逍遥乐》;《官本杂剧段数》中收诸宫调两种:诸宫调霸王,诸宫调卦册儿,《院本名目》“拴搐艳段”中收“诸宫调”,不言具体内容;《官本杂剧段数》有《迓鼓儿熙州》,《院本名目》中有《迓鼓二郎》、《迓鼓孤》、《河传迓鼓》;《官本杂剧段数》有《黄元儿》,《院本名目》中有《黄丸儿》;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可列出的名单还会增加。如前所述,《官本杂剧段数》是一份相对保守的家族性文献,它的记录范围非常有限。无论此处名单开得多长,都只是宋金俗文学交流的冰山一角。仅仅从名称的相似性或相关联性着手,我们还可在戏文、诸宫调、院本、话本之间找到很多其他事例,这种联系同样具有深刻的文学史意义。
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在当时广泛流传,《官本杂剧段数》中有《王魁三乡题》;《院本名目》中有《蔡伯喈》院本。《西厢记诸宫调》开场曲《柘枝令》唱道:“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一口气说出了金代流行的八种诸宫调剧目。据冯沅君考证,《双渐小卿诸宫调》是南宋初人张五牛创作的(注:冯沅君《古剧说汇·四·说赚词跋》,第161页,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院本名目》中有《调双渐》,说明创作于南宋初的《双渐小卿诸宫调》既传到了北方,也进入了院本。这里提到诸宫调《谒浆崔护》,《官本杂剧段数》有杂剧《崔护六么》;诸宫调《崔韬逢雌虎》故事跟《官本杂剧段数》中的《雌虎》(原小字注:崔智韬)该不会相去太远。《官本杂剧段数》中有《莺莺六么》,金有《西厢记诸宫调》。约作于十二世纪初的《刘知远诸宫调》里也提到“李免负心”(注:冯沅君认为《刘知远诸宫调》约作于十二世纪初,南北宋之交(《古剧说汇》第273页)。谢桃坊先生认为“(《刘知远诸宫调》)肯定是北宋艺人的传统唱本”(《中国市民文学史》第64页)。为何肯定,没有论证。龙建国先生经过详细论证,认为《刘知远诸宫调》就是北宋作品,且其产生年代不应距熙宁时期太远(《诸宫调研究》第29页)。),它与《官本杂剧段数》中的《李勉负心》应是同一故事。前面提到的《武林旧事》卷一“天基节排当乐次”所用《四诺少年游》杂剧,《院本名目》中也有《少年游》。《刘知远诸宫调》所讲唱的故事情节与戏文《刘知远白兔记》基本相合。南戏《王月英月下留鞋》本于《绿窗新话》中的《郭华买脂慕粉郎》及宋话本《粉盒儿》,而《院本名目》亦有《憨郭郎》。宋话本有《太平钱》(见《醉翁谈录》,讲女鬼以绣箧装五百文太平钱与书生朱文故事)与《院本名目》中《绣箧儿》当是同一故事。这些都说明宋金通俗文学创作具有某种程度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表现在:大量题材相同(这一点,也与北宋北方版图及大部分乐人被金国直接“接收”有关),剧目流行时间前后相去不远。相同的题材同时或先后出现在南北两地的通俗文学中,而且进入到不同门类的文艺形式,这都是当时宋金俗文学交流的规模较大、接触频繁的表现。
由于文化强势的原因,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其主体是宋向金输出,但是,随着金国独具特色的俗文学的成熟,金国的俗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南宋的俗文学的发展,至少在南宋俗文学中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我们可就现存的诸宫调和南戏作品,来分析宋金俗文学交流的更为具体一些的情况。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约作于金章宗时,1190—1208)已使用赚曲。赚是自南宋初流行起来的通俗歌曲之一。《都城纪胜》载:“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互迎,且循环间用者为缠达。中兴后,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筛扬处是也),遂撰为赚。”(《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所载大致相同)。诸宫调中所用赚曲当然是从南宋传过去的,但是,据《都城纪胜》载:“凡赚最难,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这里提到的唱赚有时还要综合“番曲”唱腔,此“番曲”是指金国歌曲,北方歌曲流入南方,被吸收进入新兴曲艺赚中,后来赚流入北方诸宫调等通俗文艺中。这也是南北俗文学相互交流和影响的例子之一。
研究宋金俗文学交流,金亡后一段时间理应包括在内,因为金亡后,必有大批艺人流落南方。《南宋群贤小集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卷七严坦叔《观北来娼优》诗:“见说中原极可哀,更无飞鸟下蓬莱。吾侬尚笑娼优拙,欲唤新翻歌舞来。”就是金国艺人流落到南方的纪实文献。南宋后期起,“番腔”、“番曲”频频见于文人记载。刘辰翁《卜算子》(元宵):“十载废元宵,满耳番腔鼓。”《柳梢青》(春感):“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吴文英《玉楼春》词:“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等等。这些南下的金国艺人带来了北方通俗文艺。据钱南扬考证,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作于金亡之后,宋亡之前(1234—1279)这段时间(注: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前言》,第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如果钱南扬的考证不误,那么,《宦门子弟错立身》应该是南宋戏文。该戏文女主角王金榜是东平府人,男主角完颜寿马是西京女真人。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作家总是写他熟悉的生活,如果他没有北方生活经历,是不会写以北方为背景的戏文的。另外,该戏文中唱道:“真字能抄掌记,更压着御京书会。”“御京书会”即“玉京书会”,它是金后期燕京以及后来的元大都的两大书会之一,关汉卿即是玉京书会中的佼佼者。这说明,《宦门子弟错立身》的作者对北方文艺圈比较熟悉。笔者的看法是:这本戏文最初当出于金亡后流浪到南方的金国艺人之手。该戏文第五出《排歌》等四曲共列出戏文31本(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统计是29本(第234页),我以为有31本,尚不包括钱南扬所指出的《鸳鸯会》1本。)。《王魁负心》、《孟姜女》、《鬼做媒》、《卓文君》、《郭华》、《琼莲女》、《临江驿》、《周孛太尉》、《崔护觅水》、《秋胡戏妻》、《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马践杨妃》、《栾城驿》、《西厢记》、《杀狗劝夫》、《京娘四不知》、《张协状元》、《乐昌公主》、《墙头马上》、《锦香亭》、《手帕儿》、《错下书》、《破窑记》、《杨寔》、《赵氏孤儿》、《刘先主跃檀溪》(拟)、《荐福碑》、《丙吉教子立起宣帝》(拟)、《老莱子》、《陈州粜米》、《孟母三移》。第十二出《鬼三台》曲子列出杂剧9种:《紫砂担浮沤记》、《关大王单刀会》、《管宁割席》、《相府院》、《三夺槊》、《陈驴儿风雪包待制》、《柳成错背妻》、《伊尹扶汤》、《螺蛳末泥》,同出《圣乐王》曲子列出院本6种:《四不知》、《双斗医》、《风流浪子两相宜》、《黄鲁直打得底》、《马明王村里会佳期》、《太湖石》。这里提到的几十种剧目,其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值得好好分析。首先,戏文是上演于南方的,剧中主角完颜寿马会唱戏文,会做院本,会演杂剧,这说明,观众对三者的区分是很清楚的,换句话说,金院本已流行到了南方并为观众所熟知;其次,同一题材可同时进入南戏和院本(如南戏《京娘四不知》、院本《四不知》)等,两者自然会形成艺术上的借鉴关系,并促成了南北调合腔的实现(戏文《小孙屠》中有南曲北曲联套)。《录鬼簿》卷下说沈和首创南北调合腔,据推算,正是发生在这一段时期(注:沈和的名字排在《录鬼簿》卷下“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的卷首,而卷首几人都是本书作者钟嗣成的上辈或更长一辈人物。钟嗣成约生活于1279—1360年间,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录鬼簿》提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严格地说,沈和是在此前无数冲州撞府的艺人的艺术实践上总结和提高的。
总的说来,宋杂剧、金院本题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文化的积累角度而言,应该金院本对宋杂剧的继承和借鉴是主流。金院本对宋杂剧有继承(金内地时期),更有发展(金后期),金院本的繁荣为元杂剧的形成作了最好的铺垫;而南宋的杂剧却走向了没落,它的部分艺术因素被南戏所吸收。我们实际上可看出这样两条线索——宋杂剧流入北方,经金国艺术家的发展(特别是吸收了诸宫调的艺术形式),最后造就了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发展的归宿是融入到南戏之中或自然消亡。这就是宋金俗文学交流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分久必合,南宋灭亡后,元杂剧和南戏会面,两者都带着(北)宋杂剧的文化基因,开始了又一轮南北合套的艺术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