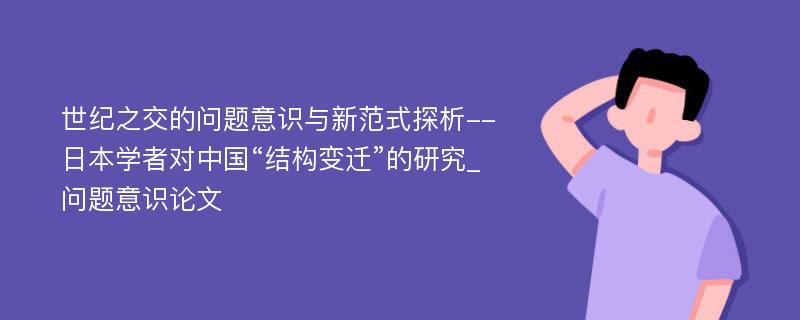
世纪之交的问题意识与新范式探索——日本学者对中国“结构变动”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范式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变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2-0122-06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和当代中国史研究成果被大量地译介到国内,不仅为一般读者提供了有益于我们民族自我认识的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而且在学科建设方面也给中国学者以刺激和借鉴,逐步形成了中外学术对话的互动局面。由于邻近的地缘关系和独特的文化史渊源,日本有着深厚的汉学传统,而其现代中国研究在地区意识和全球化的世界史背景下更是师承兴盛并富创新锐气。从80年代到9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崩溃和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使研究现代中国的日本学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意识,于是他们开始探索新的学术范式(paradigm)以求更加有效地阐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就中国的未来提出了慎重的预测。显然,对于我们身感低水平重复和理论思维迟滞等积弊之困的本土学者来说,了解日本中国研究的重大进展有着毋庸讳言的意义。
一
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基于这种对重大世界史事件的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以及革命论,成为国际汉学界对现代中国历史的主导性阐释模式。相应地,许多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者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思想为中心展开工作,这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研究的思想史范式或革命史范式。然而,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且提出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目标,这给日本的中国研究以极大的冲击。1975年4月,日本著名学者卫藤沈吉作为政府派遣的学术文化使节团的一员,在中国曾当面听到仰慕已久的中国思想家冯友兰作“自我批判”。他极为痛苦地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把这位老先生拖到这种场合?为什么人们竟然对这种政治力量一味地阿谀迎合?他还惊诧地注意到,一切价值判断在“四人帮”倒台后突然被完全翻转过来了;但他怀疑这种改变的可靠性,进而考虑尝试对这种变化作出立于政治狂涛之外的冷静、透彻地分析,并且相信中国政治结构的实态正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而通过政治结构分析则可能掌握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线索。基于这种思想,1979年4月,卫藤沈吉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政府机关的学者组织了研究中国政治结构的课题组,当时的中坚学者毛里和子和新锐学者天儿慧也加入其间。1982年2月,10名学者的论文由卫藤沈吉主编出版题为《现代中国政治的结构》一书,内容是:中国政治的波动节律(卫藤沈吉),现代中国30年的政治过程(中岛岭雄),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冈部达味),“四个现代化”路线的政治构图(德田教之),军队的现代化与军政关系研究序说(安藤正士),中国政治中的干部问题(毛里和子),政治转换时期的大众动向(天儿慧),“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的后退及因果关系(高木诚一郎),中国的台湾问题(中川昌郎),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概观(森山昭郎)。[1]这部论文集可以说是日本研究中国政治结构的开拓性、集大成之作。
如果说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转折刺激了日本学者反思从思想、政策转换层面来阐释中国历史进程的问题意识,进而把研究引向深层次的历史、政治结构领域;[2]那么进入90年代,在充分见证了世界格局变迁和中国的政治波动、经济发展之后,日本学者已经在如何评价中国的20年改革开放以及怎样认识作为大国的中国等新的问题意识的酝酿中,达致了以“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来研究现代中国这种范式转换的自觉。1995年,著名学者石川忠雄在《东亚》杂志9月号上发表题为《如何研究中国》的文章,提出了“中国将来究竟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的问题。1996年,山田辰雄在《东亚》杂志2月号上撰文反思日本学术界90年代初评价和估计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指出:当时发生那种认为中国政权将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或者经济将发生严重倒退的错误看法,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学者中还存在着“单线现代化论”思想,即把冷战后世界的潮流都想定在实现人权、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方向上,而忽视了中国自身内在的历史连续性。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近70名研究中国的学者围绕“中国是否发生以及发生了怎样的结构变动”的主题展开为期3年的共同研究,自2000年初,由毛里和子、天儿慧等7人分别主编、汇集各专业方向研究论文的《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全8卷)丛书逐卷问世。在卷首语中,毛里和子特别强调了对所谓“中国超级大国论”、“中国威胁论”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变动”的视角予以回应的思路。而她主编的第一卷《重估作为大国的中国》由各卷主编的论文组成,可以说是整个丛书的提纲挈领之作。也就是在这一卷中,毛里和子明确提出了以考察“结构变动”来探求中国研究的新范式的学术方向。该卷的构成是:关于中国的结构变动和体制转型(毛里和子),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变迁(天儿慧),国家与社会的“共栖”(菱田雅晴),中国经济——三个转变(中兼和津次),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小岛丽逸),从历史看现代中国的政治空间(西村成雄),东南亚华人世界与中国(田中恭子),中国向何处去——现代化的三个课题(毛里和子)。为了便于把握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本文着重介绍毛里和子、天儿慧与菱田雅晴的研究。
二
在中国研究的“思想史范式”时期,日本学术界有一种从中国现代史向革命史、中共党史以至毛泽东思想史归约的绝对化倾向,而中国内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使这种倾向受到顿挫,那些有着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专业背景的学者便以此为契机,摸索从“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新路径。所以,毛里和子在《重估作为大国的中国》中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改革开放”,而且虽然列举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融入国际社会和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进步等等,但其视点集中在20年间是否发生了“结构变动”的考察上。在她的研究中,“结构变动”被划分为“第一次结构变动”和“第二次结构变动”。第一次结构变动是指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二元结构开始向生成了“中间性状态”的三元结构的过渡,即中央·地方向中央·地方·基层的过渡,国家·社会向国家·半国家/半社会·地区社会的过渡,城市·农村向城市·半城市/半农村·农村的过渡,以及计划·市场向计划·半计划/半市场·市场的过渡。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论,从1994年正式开始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和村民自治使基层社会从中央和省级权力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某种有条件的自主;而在县、乡层次,过去是中央集中型动员体制,现在则出现了分权性质的“压力型体制”;可以说,党政军一体的中央、压力型的中间层和自主化过程中的基层这种“三层化”开始出现了。以城乡关系而论,80年代开始的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民工潮”造成了城乡中间性状态的新空间。第二次结构变动则是包含着与“体制转型”相关契机的变动,具体指:(1)某领域发生的“突破性”变动,如经济领域国营企业的民营化,社会领域中自发性利益集团的出现等;(2)某领域变动的制度化,如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人事权、财政权、资源利用权的法律制度性划定;(3)某领域的变动对其他领域的波及,这可以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多元分化、经济分权对政治的影响、国际性价值与国内人权状况、基层自治对高层次的影响等方面来考察。据毛里和子的分析,中国现在还处于第一次结构变动的过程当中,第二次结构变动的征兆已经可以得到一些观察,总之是一个过渡的时期。而导致向第二次结构变动过渡的契机,是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成长神话”的冲击和一直迂回进行的改革进入核心部分即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失业下岗问题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等。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已经是从经济的20年进入“政治的季节”了。
所谓“体制转型”是毛里和子特别提出与“结构变动”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国家层次的民主化(注:在毛里和子的研究中,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被限定为人们的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及对权力的监督这三个方面的制度化保障。)和经济的市场化。关于体制转型的过程,毛里和子提示了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总结的“体制改革”(transformation)、“体制移转”(transplacement)和“体制置换”(replacement)三种类型;但她强调中国20年改革过程中党政军体制的稳定性,并注意到中国历史传统中固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文化主义的统治原理和人治、德治手段对现体制的补强作用。因此,其结论是中国的第二次结构变动和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尚不明朗,但党的内部也正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促进亦或阻止包括自上而下体制内改革的政治结构变动和体制转型,还有待于进行必要的分析。
总体上看,毛里和子为研究中国的“结构变动”作出了基础性的理论建构,但其中也还存在着问题。菱田雅晴便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毛里和子的“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转变说”提出了学理性批评,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共栖”的形态,是一种过渡性的“准二元”状况。从经典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来看,这一批评是中肯的;而且作为在“结构变动”意义上对中国社会的把握,“共栖”形态或“准二元”状况的表述比较准确。因为中国存在的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计划与市场这些结构形态固然随着“中间性”空间的出现和扩大而形成了三元结构,但就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而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党政体制形态下的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和掌握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征是一体化,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表述本身就缺乏根据。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开始逐渐从国家权力的全能控制中分化出来,但并没有形成作为西欧社会历史那种意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结构,毋宁说是国家与社会界限暧昧、交互渗透的两义性“共栖”关系。总之,据菱田雅晴的研究,欧美学术界的两种命题,即来自前苏联、东欧脱社会主义经验的“后共产主义理论”和来自拉美、东南亚国家脱权威主义经验的“民主化比较政治学”所分别主张的“市民社会再生论”(regeneration of civil society)和“市民社会复兴论”(resurrection),都不适合于中国。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准确地说是从国家对社会的“全面向导”关系向国家与社会“共栖”状态的过渡;在具体事态上,主要可见于中间阶层(middle class)即金钱精英与权力精英之间奇妙的共生依存关系和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超级村庄”(super village)这种两义性、中间性空间的出现。而中间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生存于权钱交易的网络之中,其自我防卫本能决定了它的相对保守性,所以不会成为构建西方意义的自主、自治性“市民社会”的承担者,而是与市民社会理论的观察相反,它是国家体制的依附性存在。大致说来,菱田雅晴的研究体现了揭示中国历史独特性和现实复杂性的学术方向感,也为考察中国特色腐败问题的病理特征提供了一种着眼于“结构变动”的社会史学分析路径。
如果说菱田雅晴和毛里和子的研究反映了作者敏锐的“结构变动”意识的话,那么天儿慧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变迁”的研究则对“历史的连续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令人更有一种历史的“结构感”。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国观的反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般的中国认识是体现了“历史不连续论”的“新中国”观;但这种认识在“文化大革命”的“虚像”被打破之后受到反省,“历史的连续性”意识在学术界逐渐成为主流。但天儿慧并没有偏执于一端,而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体制三者之间“连续与不连续”的问题意识支配下尝试一种比较历史分析。显然,这种“结构变动”研究会造成一种更具有实证性和系统性的效果。
在天儿慧的理论框架中,执政党(有无)、国家统治体制、社会统治体制和制度化是四个核心概念,而中国古代形成的传统国家体制被要约为“无执政党·皇帝——官僚型人治(非制度)·二元性统治体制”,即没有全国规模的执政党、皇权主义的官僚型非制度化国家统治体制和国家与社会弱联系的二元结构。中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特征与上述传统型国家既有连续性,又有不连续性。在个人集权取向、阶层性权威主义国家体制以及“官本位”所指称的官民脱离情形诸方面,“连续性”得到了反映;而在执政党的存在、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意义的现代性国家体制建构以及政治权力通过单位主义和人民公社制度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等方面,则反映了现代与传统的不连续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邓小平领导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诸如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利益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与国际社会紧密联系的信息化等等;但相对而言,政治领域比较稳定。这是因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与苏联、东欧的“重建”式改革有着根本的不同,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度集中和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弊害及改革的必要性,党政职责分开、下放权力、导入干部退休制等等政策的推行,目的在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所以作为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的一党体制在改革开放时期并没有改变。虽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了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但“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底线;而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党员数量、对领导干部人事权的掌握、对国家机关领导的制度化保障以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政体制的基础。
尽管天儿慧认为社会整体的结构变动还没有达到政治体制变革的深度,但他还注意到,改革开放时期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较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相应地,政治领域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从政治体制内部来考察,可以总结为三点:(1)中央权力向功能部门和地方下放,由政策决定机构一元性功能集中型向多元性功能分散型转变;(2)超法规的个人专断型领导体制向规则、手续遵守型的集体领导体制转变;(3)重视意识形态、追求理念的牵引车型权力向脱意识形态、重视实际利益的调整型权力转变。从政治体制的外部来看,有两个重要现象:(1)由于开放政策的推进强化了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传统的信息完全控制已不可能;(2)传统的社会控制机构解体,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在逐渐扩大。在这些梳理的基础上,天儿慧预测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自我变革方式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第一是经济、社会、国际化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地方领导者的考量与行动会造成“政治变革的不均衡发展”。第二是尽管政治的制度化进展困难,但只要党内制度化到较高的水平,其他领域便具备了制度化的条件,这是政治制度化初级阶段的“政治不均衡发展”特征。第三是制度化初级阶段对民主化发展有很大制约,所以党内民主是对考虑中国政治民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四是由于采取稳定优先的渐进主义改革,集权与分权所属不明确的灰色区(gray zone)将长期存在;但构成灰色区的政治体制已经不是中央权威在全国均质化的一元体制,而是在大的框架下接受中央权威的同时各地方权威发挥功能的形态,可称为“阶式串联(cascade)型权威主义体制”。总的来说,天儿慧对中国的稳定持有基调性的估计,认为无论如何,从政治体制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但平静中底流的动向仍在他的视野之中。
三
通过以上对《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首卷《重估作为大国的中国》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日本学者在世纪之交、从外部世界探索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过程与心得。当然,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凭借身处其中的文化优势、资料便利、地主地位以及常胜的辩证逻辑,或许可以指出他们的一些错误;但我们也必须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的工作也有批评,如菱田雅晴的论文当中就涉及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一代代的日本学者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以自我否定的问题意识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其中固然有服务于“日本如何认识中国”、“日本怎样与中国相处”的民族利益的一面,但中国学者也应该会受到某些促动进而强化推动本土学术创新的意识,以经得起批评和辩论的学术提高我们民族对自身问题的认识能力和思想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了国外学术研究的比照,我们可能在检视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许还会追问务虚层次的敬业精神、工作伦理问题。
[收稿日期]2001-02-23
标签:问题意识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