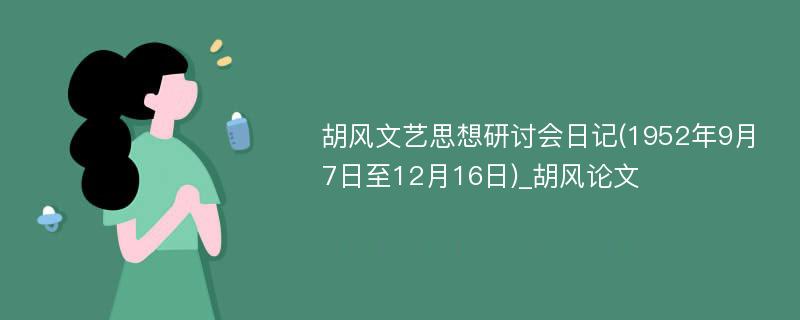
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日记抄(1952年9月7日—12月16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座谈会论文,文艺论文,思想论文,日记论文,胡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广西省委宣传部转知南宁市委宣传部长袁家柯同志,云中央宣传部有电,要我即到北京,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通知送到时,已是七日之晨,当天下午,市委宣传部即复一电,云我正参加试点学校思想改造,需带头检讨,问可否迟两周再启行。十一日,中宣部复电同意。廿五日,即至两周之期,本当即行,然运动方紧张,又迟两日。至廿七日,市委宣传部又致电中宣部,问是否必须我到,意思就是不想让我走。九月二日,中宣部以长途电话来通知,促立即动身,愈快愈好。于是,三日夜十一时五十五分搭夜车北上,次日中午十时半过柳州,下午四时半过桂林,五日上午五时过衡阳,晚十二时抵武汉;六日上午九时三十六分自汉启程,七日下午四时二十六分抵京。
以下,就是到京之日起的日记。
要特别说明,日记里所记各人的发言,都没有经过本人审阅,只是这些发言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而已。
九月七日(星期日)
下午四时二十六分抵京。出前门车站,首先见一新气象,即三轮车有售票处,乘客先按定价购票,然后上车,无讲价争价之麻烦。自前门车站至东总布胡同,价三千元。到文协后,有李秘书招待,与陈企霞一见,他有客在,即未再谈。房子已准备好,还不错。据李秘书说,讨论座谈会是中宣部文艺处组织专门小组,直接主持,文协方面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天,故无甚接洽,估计明日当开始谈话。究竟如何,须待谈后才见分晓。
九月九日(星期二)
①现实主义,②五四传统,③主观战斗精神,④深入生活,⑤民族形式,⑥鲁迅,⑦宗派主义:这以上,是上午林默涵和严文井来谈时所讲的批判胡风思想应该注意的几个中心问题。他们告诉我,我此来的具体工作,一是全面研究一下胡风的文艺理论,特别是《希望》杂志时代的理论,写一篇正式批评,同时结合自我检讨;另一个是,参加会议。
他们给我看了周总理给周扬和胡风的信,在给周扬的信上,指示此次批判应耐心帮助,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内部不行则公开批评,空言无补则让胡风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总之,争取爱护之情溢于言表;在给胡风的信上,劝他和周扬、丁玲多谈谈,好好的解决思想问题,信末特别说“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找来看了两遍,希望你多看它几遍”。由此可见,周总理对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关心的。默涵说,此次批评,内部与公开的,将同时进行。要把我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最近一期文艺报上发表。
十月十五日(星期三)
下午,林默涵来,谈了如下几点:
① 此次对胡风批评,以帮助他自己解决思想问题为主,教育读者则是次要的,因其影响今已不大,并非当前文艺运动之主要障碍;
② 因此在方式上,也就以内部谈谈为主,不拟展开大规模的公开批评;
③ 希望内部谈一两次可以解决问题,最后由胡风自己公开检讨,别人就不必多作批评;
④ 即使不能全部解决问题,也希望能解决几个根本问题;
⑤ 实在谈不通,也无法可想,只好遵照总理的指示,让他到群众生活实际斗争中慢慢求解决去;
⑥ 胡风近来已不能说舒芜不错误,于是特别强调当时他与我并不相同,我与路翎并不相同,意思是舒芜的错误是舒芜的错误,与胡风路翎无涉;
⑦ 因此,领导上特别希望我写一篇通过检讨自己来批评胡风的文章,证明相同之点。默涵说,我在此次批评中已起了积极作用,希望更进一步在这方面起作用;
⑧ 对路翎,如果他仍固执不改,那是要展开批评的;
⑨ 下周内可望开会。
晚,写长信复绿原,又给沅芷和袁部长各一封。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等了这么久,今天终于开会了。
晚饭前还是一直看书。晚饭后,在办公室楼上开会,到有周扬,胡绳,邵荃麟,冯雪峰,林默涵,严文井,王朝闻,艾青,葛琴,王淑明,周立波,陈企霞,胡风,路翎和我共十六人(萧殷早退)。
先由胡风报告,前面一大段只是重读旧文,后面检讨,说来说去,还是“本来对,不过话未说清”这样的意思。
然后我将“向错误告别”摘要说了一些。周扬指出,他还是将小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人阶级混为一谈,又未提到民族传统问题,特别是对问题不严肃,对别人意见毫不考虑,等等。
据说下次的会在下星期三开。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
上午看书。午后与张天翼谈,他对我的“向错误告别”提出几点意见:
① 关于胡风虽不赞成我的“个人主义”之名,而他自己仍是个人主义,未说清楚。
② 关于胡风为什么是借文艺问题的特殊性做掩护,为什么此特殊并不能取消思想改造的一段规律,未说清楚。
③ 关于主观作用就是具体感觉,而此具体感觉实含一定思想,反对一定思想,并非纯然客观,未说清楚。
④ 关于胡风所谓“实践”,所谓“具体行动”,实处处与“立场”对立起来提,未说清楚。
⑤ 关于胡风所谓把精神当作熔炉,重塑现实,还要多加一点解释。
晚七时半,开第二次座谈会。到会的人,除上次的十六个人而外,又加上张天翼,何其芳,田间,杨思仲,阳翰笙,合共二十一人。发言的是默涵,雪峰,何其芳。他们三人讲完,已至十一时,就吃了点心水果,宣告休会。周扬宣布,本星期内设法再开第三次会。
记录他们发言要点如下:
林默涵的意见
首先要肯定,胡风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是起过一定作用的;胡风的理论当中有些论点也是正确的,并非一概要不得。但他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错误的。
第一,错误的根源。
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阶级观点,不从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问题。
他对于五四文学革命,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认为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文化的范畴。这种看法,本来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而且现在他自己也作了检讨,所以性质还不严重。但是,他在这样认识同时,却又把五四传统看作完全好的,从来就与人民结合的,我们应该无条件继承的。这就是自相矛盾,充分暴露阶级观点的缺乏。既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又怎么能无条件的肯定呢?实际上,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其基本队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因此就有许多缺点,须要改造。最大的缺点,就是未与人民密切结合;并不像胡风所说,早就与人民结合了。
今天,胡风检讨了过去的错误,承认五四当时的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而不属于资产阶级。但是,他因此就说鲁迅当时已经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了。这又是违反阶级观点的看法。事实上,尽管鲁迅在1918年就向十月革命发出了欢呼,尽管他当时思想已经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论的,但整个的说来,他当时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胡风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也表现了阶级观点的缺乏。在他,旧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新现实主义,是混淆不分的。旧现实主义,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其大多数作家是不发生什么立场问题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但今天的新的现实主义,由于无产阶级长期被剥夺了文化,事实上不能不由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来参加队伍。在这里,立场问题,改造问题,世界观问题,就有头等的决定作用。但在胡风,恰恰从来就轻视或抹煞这些根本问题。他只是一贯地强调着“强烈的主观精神”、“忠于艺术”之类,把这些当作根本的东西。这样一来,就与资产阶级的旧现实主义看不出任何区别。
第二,关于主观战斗精神。
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作家熟悉工农大众的问题,是如何取得民族形式的问题;而这些根本问题的总的解决关键,就在于作家的思想改造。
但在胡风,却认为根本问题是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是所谓“主观与客观的脱节”;他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向作家要求所谓“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从他看来,作家的立场是已经不成什么问题的。所以他一贯强调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和人民结合,而且公然主张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缺点,顶多也只是有点所谓“游离性”,轻描淡写地提一提。所以,他就认为当时的问题,不是要改造立场,而是要“加强立场”。而所谓“加强立场”的具体办法,就是他之所谓“发扬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
“主观战斗精神”本身,并不是一个根本不能用的名词。无产阶级当然也有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而且这也是很须要的。问题是在胡风离开了立场来谈它。这样,它就是只能成为从天而降的东西,只能使那种理论成为唯心论。
胡风说:“存在决定意识,难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我都不懂吗?”不能这样说的。简单的并不简单。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很简单的真理,可是苏联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在这上面犯了错误。
胡风竭力声明,说当时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就是指的无产阶级立场。实在不是。在他所写的论文“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逆流的日子)里面,检讨了许多当时国统区文艺界的他所谓坏倾向,而他把根源一概归于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上面去。那么,难道能说他们原来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立场,而这立场后来又会“衰落”的么?
他又说,当时只有少数作家还保存着“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这里面大概包括了路翎在内。那么,难道又可以说,只有路翎等少数作家,一开始不用改造就具备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后来还一直“强烈”的么?
总之,可见这所谓“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出来是超阶级的,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它实在是一种狂热的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要用它来改造世界。舒芜的“逃集体”,是这种狂热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路翎的小说,一贯的歌颂个人的自发的反抗。
不错,人民当中是存在着自发的斗争,当然也有它的意义。但是,一个作家专门去描写它,歌颂它,而且是在解放前夜的那种条件之下,那究竟是什么意义呢?胡风引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来为路翎辩护。那实在是断章取义,歪曲了原意。那前面正是说的要写自觉的斗争,不应该限于自发的水平,他就没有引出来。而且,译文中所谓“痉挛性的”,按瞿秋白的译文,应该是“紧张的”。
路翎说,他写了自发斗争的失败,这就批判了它,也有教育意义。这也是不对的。列宁之所以那样高度评价高尔基的《母亲》,就因为它的巨大的教育意义,在于第一次写出了工人阶级的自觉的斗争,不像以前许多写斗争的只停留在自发的水平之上。《母亲》之所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正在于此。
而且,路翎所写的自发斗争,也是不真实的。他着重写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是可以的。过去乔冠华把写内心与写社会斗争对立起来,那是不对的。但写内心不能写成变态,那就是违反现实了。路翎的人物都是心理与行动分裂的,梦游病似的。难道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就是这样的吗?胡风说,人民多数都被逼疯了。难道我们的革命就是疯人的革命吗?
总之,“主观战斗精神”这种理论,当时提出来实在只引起了混乱。对于所指摘的作家,使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问题之所在;对于所赞扬的作家,使他们自满自足,阻碍了他们的改造。
第三,关于理论与生活。
理论,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从胡风看来,只是一种冷冰冰的教条。一遇到理论,他就特别强调生活实践。他不知道,生活实践是必须在理论指导之下的。舒芜的《论主观》那样的公然抹煞理论作用的文章,胡风发表出来,不加任何批评。现在他说他虽发表了这文章而自己并不赞成,这是不可能令人相信的。
但是,可不可以认为胡风真是十分重视生活呢?他遇到理论,强调生活;遇到生活,却又强调到处有人民,有生活,有斗争。这实际上是使作家沉醉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面。“文艺报”读者来信以亲身受害的经验指摘了这一点,胡风却说是曲解,是投机。不能这样说的。为什么要曲解?又有什么机可投呢?
而且,胡风还强调作家早就与生活结合,问题只在没有能吸收生活。他引了东平给他的信,说什么码头工人多得很,但并非个个成了高尔基。还说东平这个主张与毛主席不约而同。实在东平的话是错误的。码头工人固然不能(也不须要)个个成为高尔基,但高尔基之所以成为高尔基,是和他的码头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劳动生活)完全分不开的。
所以,在胡风,实际上是既取消了理论领导,又取消了生活实践。
第四,关于民族形式。
因为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所以胡风把封建时代的民间文艺,和封建文艺直接等同起来,结果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只有封建文艺而没有任何人民性的文艺。这是和列宁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直接违反的。他认为,民族形式是连应用一下都不应该的。但又不好完全抹煞,所以又说可以研究一下,目的是了解中国人民过去的“生活样相”等等。既然是封建性的文艺,为什么又能反映人民的“生活样相”等等呢?他不能自圆其说,陷于无可解决的矛盾。
他非常简单非常片面地理解“内容决定形式”。他的理论是,内容就是社会生活,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不同于封建中国的社会生活,所以不能从民族形式继承什么,只能从其他民族社会生活类似的地方借取“新”形式。这实在是弗里契的理论的翻版,尤金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中已有很好的驳斥。这种理论,严格地说,是一种世界主义。
第五,关于态度。
胡风始终自命是正确的,是现实主义的唯一的代表人,现在还是如此。他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当然是和党站在一起的。但在文艺思想上,确实是不尊重党的领导的。舒芜提出这一点来,我起初还踌躇,可不可以这样说。但回想在重庆的那些事,以及他公开宣称当时国统区文艺活动只依靠一些小单位的话,终于确认这是事实。
冯雪峰的意见
胡风的文艺思想。立场是小资产阶级的,基本上是唯心论的(当然,那里面某些马列主义的影响,某些唯物论的因素,也还是有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散播,实际上表现了唯心论对唯物论的阻碍和拒抗,是与党的方向相反的。他的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事实上是主观唯心论,是盲动论,是直接违反“实践论”的。这种理论在当时产生了极坏的效果,使作家和青年们不学习,不生活,自高自大,狂妄,使好作品与坏作品不能分辨。他把唯物论漫画化,变成教条。
但是,胡风今天努力引用毛主席和鲁迅的话,加以曲解,而目的仍是在于加强自己的理论。这是不对的。同则同,异则异;是则是,非则非。明明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反,就应该坦白地讲出来:“我不赞成这个,即使是毛主席的话,也可以讨论。”这才能解决问题,弄清问题。胡风在整个政治上是和我们一起的,这一点可以不必再说明了。但在文艺思想上,确实是反对党的路线的。这个原则性的区别,应该不容许有丝毫的混淆。
附带说到路翎。我相信,对他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前期的罗曼·罗兰和陀思陀耶夫斯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到“克里思多夫”,其实唯物论因素已经很少。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也有他的好处,但其思想显然是反动的。胡风不承认他自己对路翎的影响,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上,胡风的文艺思想,决定性的影响着路翎;而路翎的作品,后来也就成为仅有的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支持者。路翎有很好的才能,只要能回过头来,可以写出很好的作品。
何其芳的意见
胡风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接受的影响是从旧现实主义来的居多(旧现实主义其实也不是那样)。这种思想的危害性,在于它是有系统的,一贯坚持的,特别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坚持得更厉害,形成了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有意识的反对。而这也就证明了小资产阶级坚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顽强性。
胡风的现实主义,不错,正如他自己现在所强调声明,是一贯强调着生活实践的。这一类的话,他的确说过不少。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也何尝不说生活是重要的?但是,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表现了胡风文艺思想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第一个问题:对于作家,第一位的东西,究竟是生活,还是主观?
远在一九三七年,他就明白主张,第一位的是“忠实于艺术”,说这就是“追求人生”,“和人生结合”,并且居然还说什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可以补生活经验之不足”(密云期风习小记99—100页)。这很明显,就是说,生活虽然重要,但究竟是有之固好,无之也无大害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忠于艺术”的态度,其中实在早就有了一切。有了它,生活经验少也是不妨的。
这个主张,后来一直发展下来。所以有所谓“态度是创作的源泉”,“创作过程中就可以改造”,“道听途说也可以”这些错误的理论。这都明显的是从上述理论来的。
特别是刚才默涵引用过的东平的话,胡风一次把它作为“希望”的卷头语(其实是“讲话”发表两年了的时候),二次在四八年还引用来做自己的支持。东平的错误,当然由东平负责;他如果活着,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也一定能纠正这错误。但把他这话两次发表,那是要由胡风负责的(在把这话当作卷头语的那一期“希望”上,胡风反对国民党的“警察文学”,实际上把毛泽东文艺方向也带了进去,这样严重的敌我不分)。
第二个问题:对于作家,什么样的生活是最有意义的?
毛主席不但指出,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而且指出,最主要的是工农群众的生活,作家首先应该熟悉这个生活,进入这个生活,反映这个生活。
在胡风,谈到生活与主观之间的关系时,第一位是主观;谈到各种生活的意义时,是无论什么生活都一样。
因此,在他看来,作品的价值是与题材完全无关的。批评家对于作品写了什么,没有写什么,是无权批评的。说到典型,任何人都是典型。这样,写自发性当然也就大有意义了。
直到今天,他在检讨里,还是坚持要写“一切阶级”,要写“病态”和“不幸”,说是只要写得真实,就都是无产阶级的东西。
由于以上两点,所以当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指示作家无条件的都要实行改造的时候,他就替知识分子一再辩护,说他们早就与人民结合了。那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
但在表面上,他也说要改造。他之所谓改造,就是在国统区进行着反买办封建文化的斗争就可以。那实际上就是说,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照原样就可以。当然,当时国统区实行改造是有很大限制的,毛主席也说过那是不能彻底解决的,但作为一个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左翼文艺理论家,有什么权利公然取消改造的要求,向读者宣传原样就可以呢?
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根本就不了解它之所以提出的伟大意义。他认为,这问题的提出,不过是为了正确的表达内容。因此他暗暗的拿现实主义对立于民族形式,公开的又拿现实主义的要求来吞没了民族形式的要求。实际上,民族形式的提出,当然与正确的表达内容分不开,但更主要的是为了求得新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便于他们的接受。
胡风根本不了解形式本身也有它的历史,而是根据弗里契的荒谬的理论,主张形式会简单的随着基础之消灭而消灭。所以,他公然反对说,中国历史上有人民性的文艺,否认五四文学革命与民间文艺的关系,否认鲁迅与民族传统的关系。
所以,可以总起来说:以主观作为创作的源泉,主张什么生活都可以,题材与作品的价值毫无关系,作家可以无须实行改造,脱离人民群众,割断民族传统,这就是胡风的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主义”。
这样的现实主义,他自命为唯一正宗。一切他所反对的,都被他指为反现实主义。他所攻击的主观公式主义,是指郭沫若。他所攻击的客观主义,是指茅盾。而一切他的小集团之外的东西,都被他简单的派入这两类。在他的描写之中,国统区的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简直是不存在的。所谓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被他写得与反动派没有什么不同。剩下来的,就只有他所领导的小集团。但他自己也不免感到孤独,于是又在上海出版的“希望”上,引了罗丹的话做卷头语,鼓励孤独,坚持孤独,预言他的孤独不久就会消逝。但是,我要告诉胡风,你的孤独是会消逝的,但那是在你放弃而不是坚持你那一套“现实主义”的条件之下。
最后,我也和雪峰一样,希望胡风不要混淆同异,掩蔽自己的思想面貌。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
昨晚蒙头大睡,出了汗。今早又吃了发汗药。睡至午饭时起来,已觉比较好些。下午看了一些书。晚,参加第三次会议。发言的有胡绳、邵荃麟、田间、阳翰笙、艾青,最后,周扬做了总结,胡风表示了一些态度,散会已是两点钟。这次座谈会,就这样完了。发言要点如下:
胡绳的意见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可以从两个基本问题来看。
第一,是立场问题。
问题不在于当时没有从字面上写出“无产阶级立场”的字样。就拿今天胡风的检讨来看,还是很清楚地看出他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并且还要拿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混淆无产阶级立场。
当时文艺上的根本问题,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是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必须与无产阶级立场明确划分界线,使前者改造为后者的问题。但胡风今天还是说,当时作家立场已无问题,只要他们拥护无产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纲领,就等于立场问题已经解决,成问题的仅仅是态度而已。这首先就把当时作家们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掩蔽起来,把它与无产阶级立场混淆起来,否定了思想改造的根本问题。
因此,当他表面上也说要改造的时候,实际上就不能不是要以小资产阶级去改造世界。他说,当时作家们的立场虽已解决,但不够真实,就是说,还有些空洞。因此,他号召“征服现实”,使不够真实的立场变成真实的立场。这在实际上,当然就是要用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去“征服现实”,即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世界。即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既然原来的立场乃是不真实的,那么,站在那样的立场去“征服现实”,自然也只能朝着不真实的方向把现实歪曲起来。
从胡风看来,凡是反帝反封建,都等于无产阶级立场;凡是现实主义,都等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实际上,现实主义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的,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在历史上也不一定都是反现实主义的。
对于胡风这种错误,我是理解的。四三年,我和乔冠华,陈家康,也是认为当时知识分子立场已无大问题,可是问题存在还那么多,可见立场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于是也提倡什么“生活态度”。由于当时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当时我们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同情的。当时我们也是向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什么“发扬主观作用”之类,结果当然也只能发扬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作用。
这种错误,是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指为无产阶级立场,这比坚持不加掩饰的小资产阶级立场,错误更大。
第二,是方法问题。
胡风的理论,并不是完完全全不合真理。有某些在一定条件一定情况之下的部分的事实,是被他看到了的。但是,他抓住这一点,就拼命夸张扩大起来,使之成为绝对的东西,因而达到完全错误的结论。这就是主观性片面性的方法。
舒芜的方法也是这样。例如他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通,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情况之下,有些知识分子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碰了钉子,转变成集体主义的,而党的领导,也确实要重视他们,组织他们,指示他们正确的出路,这些都是事实。但乃是小部分的事实。更多的倒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终于发展到极其反动的路上去。而当时舒芜的理论,却是抓住这一小部分事实夸大起来,说成凡集体主义都必从个人主义发展出来,否则就不好,这就是由于主观片面的方法,达到极其错误的结论了。
胡风强调小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不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之下,小资产阶级只要是革命的,当然不可免的要趋向于无产阶级领导,因为从别的地方找不到出路。但这也只是一面。另一面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为体系来看仍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那思想如果不加改造,发展下去,一定发展到趋向资产阶级领导,对抗无产阶级领导。因此,党对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一面是欢迎他们,组织他们,另一面是把他们的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严格划分开来,并且坦白地告诉他们应该改造,诚恳地帮助他们实行改造。而胡风却片面地抓住前一点,夸大起来,就说成小资产阶级只要革命,便与无产阶级思想无任何界限,又是达到极错误的结论。
又如,我们今天说小资产阶级作家一定要改造,但并不是说,在当时的国统区,在党的领导之下,小资产阶级作家尽管不可能彻底改造,但就那样的努力写出一些有革命性的作品来,也是不好的。事实上,当时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尽管不可能彻底改造,但毕竟在党的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战线,而且在对于国民党反动文艺战线的斗争上还是取得了优势的(至于当时党的领导够不够,强不强,那是另一个问题)。而胡风说,今天要求作家在当时的改造,就会成为取消主义和反历史主义,这又是由于主观片面的方法得出来的极错误的结论。
又如,自发性也有各种各样,有真正工农群众的自发性,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发性,也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自发性,还有其他很不相同的许多种自发性。即使不谈当时国统区事实上存在着的,而且是作为主要的东西的自觉斗争,单单就自发性来谈,也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有的是有一定意义的,有的并没有意义,有的甚至于是反动的。胡风和路翎,却完全不加分析,对于国统区的斗争,笼统的只看到一个自发性,认为全是大有意义的,认为应该成为当时文艺的中心主题,这又是主观片面的方法的结果。
又如,胡风所谓创作过程中的主观作用,其实就是感情。但我们认为,一方面,作家固然不应该冷冰冰的没有感情,另一方面这感情却只是创造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并非关键。胡风却又把它夸大成根本关键,认为它才能够解决立场问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又如,写内心生活,当然也是要的。在香港时,乔冠华把写内心生活与写社会斗争对立起来,当然也是不对的。但胡风又把这一点夸大起来,结果就成为,写精神状态愈是复杂分裂,愈是脱离现实社会关系,就愈是把握现实的深处,这又成为极端荒谬的结论。
总之,我认为胡风之所以在错误中愈陷愈深,把一切都弄得混乱不堪,现实主义成了反现实主义,思想改造成了不要改造,无产阶级立场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其原因是在上述两个根本问题上。希望他的检讨要从上面检讨,才可以解决问题。
邵荃麟的意见
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一方面对于旧的现实主义是继承的,另一方面又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按照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它与旧现实主义相区别的特点,就是要把对现实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的描写,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社会主义精神,就是旧现实主义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因此,毛主席正确地指出,基本问题是立场问题。这也就是列宁的党性的区别。
但在胡风,却认为基本上是态度问题,而且认为态度决定立场,即所谓有了爱爱仇仇的态度立场才是真实立场,这就与毛主席的立场决定态度的指示相反。
对于旧现实主义的作家来说,例如初期的罗曼·罗兰,以这态度来要求,以这态度来作为衡量的标准,那是对的,因为对他们本来不能以无产阶级立场作为要求和标准。但对于今天的我们,就一定首先把立场问题讲清楚,然后才谈得到态度问题。这是原则性之所在,非坚持不可。
当时国统区文艺界的情况,在一定的意义上,确如胡风所认识,是所谓“在混乱里面”。这混乱的根源,正在于上述原则性的问题,即作家的立场问题未曾解决。而胡风当时却认为只要拥护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立场便已不成问题;他认为,根本问题是在于所谓爱爱仇仇的态度。其实,如果没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即使有爱爱仇仇的态度,仍然是不中用的。
例如路翎,是很有才能的,其创作态度确乎也是认真严肃的,也就是说,他是有他的爱爱仇仇的态度的。他有些小说,我也至今还有印象。但是,能不能说他是正确地反映了现实?能不能说他是正确地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呢?不能。他的小说,把自发性的斗争当作当时国统区的典型的东西,加以歌颂。事实上,当时国统区当然有自发性的斗争,但更重要的,也就是更典型的,乃是党的地下工作所直接或间接领导的自觉斗争。像路翎那样以那种自发性的斗争当作典型,这就歪曲了当时的真实。这就是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证明,如果不是首先解决立场问题,光有爱爱仇仇的态度是没有用的。(周扬:延安文艺整风,也就整过爱爱仇仇。)
立场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深入群众斗争。可是胡风就强调到处有人民,到处有斗争,起点就在脚下。这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把屁股移过来,恰好是相反的。方然解释所谓发扬主观作用,就是“立定脚跟,挺起背脊”,这也就是起点在脚下的意思。这些显然都是反马列主义的思想,然而却以马列主义的面貌出现,就把一切都弄糊涂了。
必须强调,马列主义的观点,首先是立场问题。事实上,我们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直到今天,主要的还是在讲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有了无产阶级立场,就一定能定出好的作品;但是,我们肯定地说,要写出好的作品,首先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立场。
还有关于民族传统的问题,这也是一定要讲清楚的。刚才说过,把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混淆于旧现实主义,是不对的;但把它从历史优良传统分割开来,也是不对的。在胡风,认为我们的进步文艺传统,仅仅是从五四开始。解放后,他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从源头到洪流”,所谓“源头”还是指的五四。这样,自然就联系到接受遗产问题。按照胡风的观点,是必然要取消接受遗产的任务的。
最后,关于胡风和党的关系。在政治上,胡风是和党一致的。党对于他,向来也看作一个非常的布尔什维克。有些党的会议,也要他参加。但在文艺思想上,他确乎是不接受党的领导的。他自己总说是理解水平的限制,我看不能这样说。难道说,延安参加文艺整风的那些同志,个个都比胡风的理解水平高吗?拿我自己来说,当时虽然没有写过文章,但对胡风的理论是有同情的,后来还是转过来了。我相信,我就并不比胡风的理解水平高。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
田间的意见
胡风过去对我有过不少帮助,他是第一个在批评界鼓励我的人,这些我是并没有忘记的。因此,我也很希望今天能对他有所帮助。
我觉得,他今天检讨自己,应该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但是,他并没有。他还是发挥自己的一套,还是说当时国统区没有自觉的斗争,不是强调主观作用,特别还说他之强调主观作用是为了肯定实践,令人不知问题之所在,对自己的脱离实践及其影响也没有深刻批评。
我希望胡风能下决心。他过去做了不少工作。今后,如不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是一点工作也不能做的。
阳翰笙的意见
胡风是我们从左联以来的老战友、老同志,政治上我们是一致的。
但是,正如舒芜所指出,他在文艺上是形成了宗派主义的。他自己说是自由主义,我看这自由主义已发展成了宗派主义。而宗派主义就一定有它的思想基础。从立场问题,现实主义问题,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民族遗产问题,一直到对于国统区文艺战线的估计,他都自有一套,一根线贯穿下来,总觉得只有他和他几个同道的人对,别人统统不对,这样,就自然的和必然的形成了宗派活动。但他对于这一点,至今还没有认识。
我认为,他的文艺思想,不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在国统区有孤独之感,一方面国民党迫害他,可是另一方面,共产党的文艺路线,对于他又格格不入。说一句不大妥当的话,简直有些“夹攻中的奋斗”的样子。所以,他这个人,整个的说,当然是小资产阶级加革命的,但他的文艺思想却是发展到资产阶级的范畴了。
我和胡风是很老的朋友,当年他从日本被驱逐回国,就是我被左联派去欢迎的,所以我讲得更直率一点。
艾青的意见
胡风因为抹煞民族遗产,所以他的文章也是普遍的令人不懂。他自己说是国民党压迫下的“奴隶的语言”。但这种“奴隶的语言”如果不仅对敌人蒙蔽了真相,而且也使自己人都不懂,那就完全失去意义。
我们之间,本来有些问题,例如诗的形式问题,也与上述问题有关,是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好好地交谈的。但是,好些时候以来,我们见面就只能开开玩笑,谈不上正经问题。这一点,丁玲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我希望还是可以好好地谈一谈。
周扬的结论
这不是结论,真正的结论,要由胡风自己来做。
第一,我想说一说这次讨论的意义。
我认为,这是一个路线之争,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之争,是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与反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之争。胡风不承认他代表一个路线,这是不符事实的。问题的本质,不应该模糊,而应该明确地揭露出来。
当然,并不是说曾经批评过胡风的人,全部意见都是正确的,但他们的基本方向是马列主义的;也不是说胡风全部都是错的,但他的基本方向是反马列主义的。
对于胡风的批评,应该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时间开始;更具体地说,应该拿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作为典型的代表。这是他在四八年写的,五一年还重版了而没有任何修正的。这里面,有他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完整纲领。作为一个文艺上的派别集团,这个纲领是与毛泽东文艺路线针锋相对的。
当然,要研究胡风的整个文艺思想,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文章也是要研究的。但是,那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拿我来说,比较起在座的同志,恐怕我和胡风也是最老的朋友,大概和阳翰笙同志差不多。当时在上海,我们都做文艺工作,胡风做的比我还要多一些。后来我们之间有了一些争论,今天看来,当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但有许多的确是无原则的。我的错误,也许比胡风还多。后来在延安整风,发现自己是三风不正,样样俱全。特别因为我是党员,应负的责任当然比胡风更大。再拿当时和雪峰同志的关系来说,当时他是领导我的,我们发生争论,现在看来,他的理论正确的比我多。这和他当时在思想上接近鲁迅是有关系的。至于我,当时完全不认识鲁迅,满脑子只是一些日本转运过来的洋教条,如吉尔波丁之类,自以为差不多了。那种幼稚,错误,后来回想起来,只觉得难过。所以,总之,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是没有标准的。当然也不是根本没有,鲁迅就是。但一则大家不了解他,二则他的标准究竟不像党的标准那样完整明确。
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当然也不是说大家都很好了,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有了一个尺度,总归好办了。例如我在整风当中,总想不透自己有什么宗派主义。毛主席一句话就解决了:“脱离群众就是宗派主义。”是的,只有用这个尺度;否则,从张三骂了李四,或李四骂了张三那样的去想,永远想不清楚的。
那样,你说我宗派,我也可以说你宗派。问题不是张三和李四的问题,而是大家同样的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谁脱离了群众,谁就一定只能陷进宗派的小圈子里去。宗派主义并不是反对革命的,如果是,那就是反动集团,不能称为宗派主义了。既是革命的,那就只有与群众结合的义务,而没有任何与群众脱离的权利。
所以,胡风的问题,主要的是座谈会以后的问题。那时,在国统区,郭沫若和茅盾,对于这个工农兵方向是拥护的;尽管他们拥护得很肤浅,但乃是出于真心的。而胡风却反对这个方向,直到党已经提出意见以后,甚至和他一向比较接近的党员作家(雪峰、荃麟)都提出意见以后,甚至直到今天,他还是坚持反对的。他主观上是否反对,我看这是很难估计的。根据他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认识。而这也就是马列主义估计问题的方法。
当然,并不是说胡风在政治态度上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但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和文艺思想上反对他的思想,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总之,从座谈会以来,问题积累得很久了。党,通过它的负责同志,通过党员作家,也早就提出很多意见了。到今天,是应该做出结论的时候了。这个结论只有两种,或是胡风对而党错了,或是党对而胡风错了。
今天,胡风的影响并不大。不是不批评胡风,我们的文艺运动就不能前进;但是,批评了胡风,可以帮助我们前进。这是因为,胡风理论的直接影响今天虽是小的,但产生这种理论的基础今天还是相当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欢喜很革命很漂亮的名词,但只愿意付出最小的代价。这就是产生胡风的理论的基础。光未然不一定直接受过胡风的影响,但产生了同样错误的理论,就是由于同样的基础。如果不批评胡风,可能不久又会产生这样的理论,甚至我们自己也会搞出来。如果经过批评,群众受过这一次锻炼,将来即使再有同样错误理论产生出来,群众也就容易辨别。
再有一点,胡风一向的确抓到了我们文艺运动中的真的弱点,就是公式化概念化。这个倾向,从左联到现在,一直纠缠不清。胡风要克服这个倾向,但乃是沿着他的错误的道路去克服。群众已经对这公式化概念化不满,我们如不揭露胡风的错误,胡风就可能更以其错误的道路去影响群众。所以,今天一方面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正因此,就要同时在另一方面,反对胡风的错误路线。
胡风直到今天,还是坚持着他的错误路线。我说的是实质上,是根本上。至于他的态度,也还是有了一些进步的。今春我和默涵到上海去看他,那时他对于“文艺报”发表的批评他的读者来信和编者按语,非常生气,认为完全是胡闹,他没有一点错。当时我就告诉他,读者提意见是好的,编者按语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看起来是写得对的。后来,他写了一篇纪念“讲话”十周年的文章,那里面仍然没有丝毫检讨自己。再后来,他写了那篇“关于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无论如何是开始检讨了,可是只把一切归到他和别人关系搞不好上面去。其实我在上海和他谈的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提醒他注意一个事实,就是他在他最长最完整的两篇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里面,所批评的恰恰一概都是党员作家。这当然不是说党员作家就不能批评,也不是说这就是根本关键之所在。我的意思只是,像这样一贯的系统的而且绝对否定性的批评,都是对着党员作家,可以从这现象上考虑一下自己在文艺战线上和党的关系,可以回想一下自己为什么这样不愿意考虑党员作家的意见。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们也都看到,他在态度上又有了一些进步,表现在这回他总算开始检讨思想了,尽管所检讨的还只限于枝枝节节的小问题。对于这一些进步,我们当然还是承认的,但是,仍然要指出,他对于他的错误路线,在实质上,在根本上,今天还是在坚持的。
第二,我说一说根本分歧点之所在。
首先要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充分表现了小资产阶级两面性。在对于国民党反动文艺的斗争上,表现了进步的一面,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当它的锋芒主要的已是向着党的文艺路线,向着党员作家的时候,那就很难说是进步性的表现,说反动性当然也不完全恰当,应该说是倒退性吧。
就整个胡风来说,就他的整个政治态度来说,那是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但就他的文艺思想来说,特别是发展到座谈会以后,那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面已成为主要的一面,那就不能说是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原因很简单,小资产阶级在任何一方面不是拥护而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时候,在那一方面就没有丝毫革命性,只有倒退性。所以,胡风的整个的政治态度和他的文艺思想,他的文艺思想在座谈会以前和以后,这些都要具体地分析,不能混淆起来。
那么,根本分歧之点究竟在哪里呢?就是对人民的态度问题,尊重还是不尊重人民的问题。很明显,胡风是完全不尊重人民的。
当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人民中最大多数是工农兵,其次才是小资产阶级,因此文艺第一是为工农兵,第二才是为小资产阶级的时候,胡风提出完全相反的答案。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面,他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证明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据他说,仅仅除了产业工人和雇农在外,其他无论小到怎样可怜,仍然是小资产阶级。他对于劳动人民的绝大多数,就像这样的不是主要的看他们劳动的一面,而是主要的看他们小有产的一面。从他这个看法出发,方向当然也就正好相反,第一应该是为小资产阶级了。
而且,同时,他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乃是脑力劳动者。这样对照起来,当然就不但不要向群众学习改造自己,而且本来比那些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还要好些。
如果说这就是毛泽东文艺路线,我想每一个毛泽东的同志都要出来抗议的。
胡风根本看不起人民,可是偏要强调什么“爱爱仇仇”,做出一种无限爱人民的姿态。实际上,他在人民身上,只看到“精神奴役的创伤”,只看到“封建主义的统治”。他告诉读者,人民只有两种精神状态,或者就是所谓“亚细亚的麻木”,或者就是所谓“痉挛性”、“疯狂”。把人民糟蹋成什么样子!实在令人伤心。可是他偏偏赞美的就是这个,好像他爱人民爱的就是这个。人民实在受不了!应该说,这是资产阶级对于人民的贵族式的态度。
不但如此,据他说,这“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还成了“屠刀”。人民在三十年来革命斗争中流的血,据说不是反动派给流的,而却是这“屠刀”给流的。这就是说,不是革命克服人民身上的落后因素,而是这些落后因素妨碍了革命。这就是说,人民不能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解放自己和改造自己。应该说,这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观点,是历史悲观主义。
因此,胡风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恰好相反,不是在革命的发展中看现实,而是在停滞中看现实,结果就只看到人民的“麻木”;不是在革命的发展中看现实,而是在病态的动乱中看现实,结果就只看到人民的“痉挛性”和“疯狂”。不错,毛主席也指示过,对于人民身上落后的东西也应该批评。但用什么来批评呢?应该用人民当中的先进英雄的形象,而不是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精神。但在胡风,凡遇到表现人民的先进英雄形象的文艺作品,一概都指为主观公式主义。这样一来,对于凡是追求人民中的先进典型的就加以嘲笑,而对于拼命发掘人民身上落后的东西的则大大赞扬,就这成了胡风的“现实主义”的特征。
正因为胡风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所以他完全抹煞民族遗产,乃是必然的。今天的人民,他都认为非麻木即疯狂,那么,封建社会中的人民所留下来的文学遗产,在他看来,当然更只是集“精神奴役的创伤”之大成了。他自己和我说过,说是民主这个东西,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有的东西。这是直接违反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指示,民主不由人民群众当中产生,成了无产阶级专利的东西了。实际上,任何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不可能不产生民主。资产阶级比封建地主是要民主一点,但那仅仅是在它和劳动人民还有某一些共同利害的时候。民主,永远是属于人民群众的。
胡风这样的文艺思想,脱离人民,脱离阶级斗争,而还要来指导文艺运动;直接对抗无产阶级的领导,而还要自命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这是最为危险的。我在关于“武训传”的文章中说过,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或是与群众结合,取得支持,或是从个人主义找支持。我自己觉得还是一点心得。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没有和群众结合的时候,总是表现脆弱的。在革命形势前进或后退的关头,他们都时常要发生彷徨的感觉,他们意识到自己和时代与人民的距离而感到寂寞孤独,他们抱怨别人不理解自己,仿佛自己心中不知有多少委屈,甚至觉得革命是只有傻子才干的事情。他们在感到自己脆弱的时候,就须要有一种力量来支持。或者是,从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中,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汲取力量,这个力量是无穷的;或者是,从个人主义的哲学和个人的奋斗中去寻找救助和鼓励,这就将引导人们走上脱离群众反对群众的道路。对于这个根本的危险,胡风至今还未认识。
今天也并不是说文艺上的小集团一概不应该存在。事实上也是有的,例如巴金他们就是。但不能与党对立,另搞一套,而且还要自命为无产阶级的东西,还要用来指导运动。那是办不通的。
最后,我说一说对胡风的希望。
我的希望是,检讨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打退一切关于过去成绩的回忆,推翻架子,脱下裤子,离开自己,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矛盾统一的。有了彻底的自我批评,可以把批评统一在里面。如果不能自我批评,或做得很不彻底,那就一定要有批评来帮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