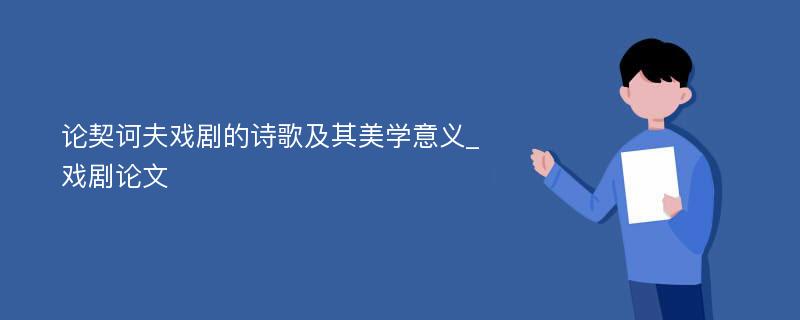
至味于淡泊——论契诃夫剧作的诗化及其美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论文,的诗论文,美学论文,意义论文,契诃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把古希腊戏剧看着是戏剧艺术的滥觞,那么,戏剧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有了近二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二千年里,戏剧作为最直观的艺术之一,其叙事性、外在的动作性,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被视为戏剧艺术的生命。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在他的美学著作《诗学》中,给“悲剧”下定义时就曾指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p.19)他这里所说的“行动”,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事件”或“故事”。戏剧离不开叙事这一美学观念,在这里被表述得十分清楚。正因为如此,戏剧艺术偏重叙事的倾向在戏剧舞台上得以长期流行,其间虽有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有意、无意地偏离了这一倾向,但毕竟没有能够走得太远,充其量不过是抒情因素在剧作中得以一定程度的增加,抒情因素与叙事因素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平衡而已(如莎士比亚的部分作品)。戏剧的抒情性,无论是从个别作品来看,还是从戏剧艺术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远没有对其叙事性构成否定。然而戏剧的这一创作倾向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契诃夫时代,却有了大的改观。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叙事因素、外在的动作性被大大地削弱了,抒情因素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抒情因素在剧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戏剧艺术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诗的特质。在契诃夫抒情魅力的诱惑下,世界剧坛上一大批剧作家开始了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抒发人物内在情感为主的心理剧的创作,并逐渐形成潮流,对传统的戏剧舞台产生了强烈冲击。下面试就这一问题作一阐述。
一
契诃夫之前创作传统戏剧的剧作家们囿于对戏剧性的片面认识,多少年来一直以为戏剧性只存在于叙事之中。因此,在创作时他们特别重视作品的叙事性,重视对作品叙事性的发掘与表现。他们热衷于在舞台上展现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或是讲述带有神秘色彩、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热衷于展示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命运之间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并擅长通过设置悬念,制造一个又一个高潮,以及“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式出人意料的结局来吸引观众。他们普遍认为,只有那些充满巧合、出人意料、令人震惊的事件才是具有戏剧性的;只有那些悬念不断,高潮叠出的作品才能获得剧场效果。这几乎已成为契诃夫之前从事戏剧创作的艺术家们的共识。
传统剧作家们在取材、情节上费尽心机的同时,还在整部剧的结构安排上煞费苦心,务求作品表现出的故事情节更加集中、紧凑,一气呵成,从而使坐在剧场里观众的注意力能够自始至终一刻不停地集中在舞台上。为此,他们创造出了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回顾式”戏剧结构,[2](p.222)即以“过去的情节”与“现在的情节”相融合,通过对“过去的情节”的发现来改变舞台上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加深、激化其矛盾冲突,从而推动“现在的情节”迅速向前发展。这种戏剧结构由于能够使故事情节变得更加集中、紧凑、紧张、激烈,特别是能够制造出令观众产生强烈兴趣的悬念,以及使剧情产生跌宕起伏的效果,因此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结构方式(尽管它并不是唯一的结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把这种结构称为“纯戏剧式结构”。[3](pp.5 —14)这种戏剧结构发展到后来便成为充斥更多偶然巧合、故事性更强的法国“佳构情节剧”的主要结构方式。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契诃夫之前,戏剧艺术的创作一直是沿着重叙事,重情节故事、重外部冲突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戏剧在重叙事、重情节、重冲突、重对人物性格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重结构的纤细、精巧等方面完全可以和小说相媲美,就其故事情节的紧张、集中、紧凑而言,它甚至超过了小说。戏剧小说化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戏剧创作总的趋势。
二
与传统作家完全不同的是,契诃夫认为戏剧性不只是存在于那些罕见的、天翻地覆的历史事变中,不只是存在于那些充满巧合、带有神秘色彩、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中。换言之,不只是存在于外部冲突中,而且还存在于抒情、存在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及人物内在情感的抒发中。美国著名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纯粹激烈的动作——纯粹的宏伟壮观是不足取的……我不需要情节,有人物就够了”。[4](pp.42—43)这句话移用于契诃夫的创作也同样适合。契诃夫正是这样一位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以刻画人物形象,尤其是刻画人物心理见长的剧作家。在契诃夫剧作中,就其情节而言,所表现的都是一些诸如“吃饭”、“喝茶”、“闲聊”之类的生活琐事,人物也只是遍布那个时代俄国大街小巷的所谓教授、作家、演员、小学教师、中小地主和下级军官。所以高尔基称契诃夫的剧作为“生活琐事的悲剧”。
和“生活琐事的悲剧”相一致,契诃夫剧作的剧情大多平淡无奇,没有悬念、没有曲折、没有“发现”和“突转”。对于被传统剧作家视为戏剧生命的戏剧冲突,契诃夫也不是刻意地加以表现。他往往把那些非表现不可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或是加以淡化,或是干脆放到幕后进行斯拉夫斯基式的暗场处理。例如:在他的代表作《三姊妹》中存在着一个姑嫂相争的故事,可是由于三姊妹只让不争,并且这一故事被分得很散,零零碎碎地表现出来,因此,冲突被弱化了。同样,在他的另一名剧《樱桃园》中,面对越缠越紧的债务,女地主柳鲍芙·安德列耶夫娜,不是积极地寻找对策,而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从而使本应存在的贯穿全剧始终的冲突被淡化到了几乎没有。另外,对那些剧中出现有可能引起观众强烈情感反应的事件,如自杀、决斗等,契诃夫则把它们统统推到幕后——观众只能听到隐约的枪响,却看不见人物激烈的行动。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契诃夫彻底摒弃了占据戏剧舞台主导地位的集中、紧凑的“回顾式”戏剧结构,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散文诗式松散的戏剧结构。契诃夫打破了古典戏剧创作中所要求的“三一律”中最根本的一条,即所谓的“动作的一致”。在他的剧作中没有一贯到底、完整、突出的中心事件,也没有众所拱卫的中心人物,故事情节及人物具有很强的离心倾向。剧情进展也十分缓慢,没有明显的标志。剧中人物在很多场合都是整幕整幕地坐在那儿,喝着茶,聊着天,剧情仿佛凝固了一般。无怪乎有人称契诃夫剧作为“静剧”。在戏剧发展史上,除后来的荒诞派戏剧外,像契诃夫剧作这样进展缓慢的剧情确实是不多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契诃夫剧作一开始给人的印象似乎过于平淡,甚至有些枯燥、难以引起观众的兴趣。
然而,契诃夫剧作并非一杯毫无滋味的白开水。契诃夫剧作在削弱戏剧外部动作力量、淡化叙事性的同时,对于深藏在生活表面激流下的潜波暗流,对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则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契诃夫在谈到他的剧作《万尼亚舅舅》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全部意义,他的全部悲剧是在内心,而不在外部表现。”[5](p.23)由此可见, 他对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所重视的程度。
契诃夫善于捕捉人物内心深处细微的情感变化,并把这种变化真实、细致的表现出来。为此,他在创作中大量地使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他剧中人物的语言宛如现实生活中的一样,往往是吞吞吐吐、断断续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也常常是答非所问、缺乏逻辑和互不相关,“某甲问的是某甲自己的事,某乙回答的又是某乙自己的事。”[6] (pp.423—424 )然而就在这许许多多看似杂乱无章的话语中却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隐藏着人物大量潜在的思想意识和隐秘的行为动机。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各种向往、欲求都得到了充分的流露。
在契诃夫的剧作中,人物内在的心态不仅是通过“有声的对话”,而且,还大量地通过人物“无声的语言”,即“静止动作”表现出来。如前所述,契诃夫剧作很少激烈的外部行动,很少“张牙舞爪的穿插”,有的只是“一次口哨,一次无声的哭泣,一次未说完又吞回去的话,一次沉默无言,一次停顿……”。在这些静止动作中,用的最多的莫过于对话中的“停顿”,这种“停顿”,有时一个剧本竟达一百多处。关于这种“停顿”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方面所起的作用,契诃夫剧作的中文译者焦菊隐先生曾有一段很精彩的讲话,他说,“现实生活中最有力的东西,便是‘停顿’。它既表现刚刚经历过的一种内心纷扰的完结,同时又表现一种正要降临的情绪的爆发,或者某种内心的期待。它又表现内心活动的最澎湃、最热烈、最紧张的刹那。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内在律动,都要靠‘停顿’来表现的——这是一种最响亮的无声台词。所以,契诃夫的‘停顿’不是沉默,不是空白,不是死了的心情,相反地,是内心生活中最复杂、最紧张的状态所必然产生的现象。”焦先生的这段讲话深刻地揭示了契诃夫剧作中所谓的静止动作,其实只是表现现象,死水微澜下面暗藏着的是洪波巨流,契诃夫剧作的戏剧性正是以这样一种深沉、内在的形式出现的,它充分地体现了作为跨世纪作家的契诃夫独特的创作个性。
契诃夫剧作还具有一种浓郁的象征意味。无论是《海鸥》中被打死的海鸥,还是《樱桃园》中被拍卖、被砍伐的樱桃园,或者是《三姊妹》中三姊妹口里常常念叨的“到莫斯科去!”,无不具有浓重的象征色彩。除此以外,契诃夫还擅长在舞台上营造种种“情调”,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种象征意味。什么是情调?焦菊隐先生认为:“契诃夫剧本里每一种声音,无论是小鸟的唧噪,或是芦笛的微声;无论是春熙的阳光,或是散布着悲哀的吉它琴;都在充分地发挥着人们的内心形态。这些外在的事物便是情调。”[6](pp.423—424)在这里,焦先生是侧重于作品中的音响而言的。其实,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构成情调的远远不止于音响,还有布景、灯光、人物的动作、表情、说话的节奏等等,这些外在的事物和人物内心的情绪相互交织、融合,便构成了情调,具有了象征意味。的确,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我们随处可以听到人物的叹息声、吹口哨声和吞吞吐吐的话语,听到更夫凄凉的打更声、天边传来的琴弦绷断声;还可以看到蔚蓝的湖水、清冷的月光,感受到秋天的寒意……而这一切在契诃夫剧作中都不是孤立地出现的,它总是恰到好处地烘托出剧中人物的种种情绪:或是忧伤、或是孤独、或是无奈……
正是因为契诃夫在进行戏剧创作时,有意淡化作品的故事情节及外部冲突,着力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主观感受,并且大量地使用所谓“无声的语言”,因而使其剧作显得含蓄、深沉、耐人寻味,具有了诗一般深邃意境。另外,由于作者充分调动了声、光、布景,并巧妙地将它们与剧中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相互交融,营造出了所谓“契诃夫式的情调”,因此,剧作更增添了浓郁的抒情色彩。此外,再加上剧作中洗炼的语言、丰富的潜台词,从而使得契诃夫剧作诗化的成分大大增加。契诃夫剧作无论是从内容上看,还是从艺术形式上看,都迥异于传统剧作。它给人总的感受是偏离“写实”而趋于“空灵”,偏离小说化而趋于诗歌化。的确,如果我们以传统的戏剧观念来看待契诃夫剧作,就会感到不可思议,难以接受。然而如果我们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全新的观念来欣赏契诃夫剧作,就会体会到它的妙处,体会到契诃夫为戏剧艺术发展所作的开拓性贡献。
三
由于契诃夫剧作是在一种全新的戏剧观念指导下创作出来的,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传统戏剧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它带给观众的审美感受也必然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统剧作重叙事、重情节、重外部的矛盾冲突。它主要是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及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诉诸观众的感官,以取悦观众,因此,显得比较外在、比较表面化。而契诃夫剧作则由于重抒情、重表现人物内心微妙的心理变化,通过这种变化诉诸观众的心灵来感染观众,拨动观众的心弦,因此,显得比较内在、比较含蓄、深沉和隽永。
其次,传统剧作的剧情经过剧作家所谓的典型化后,往往比现实生活更加的集中、紧凑、紧张、激烈,它因此给观众提供了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全新体验,有利于吸引观众。然而,由于有了人为的加工,难免有雕琢、斧凿痕迹,因此,常常给人以不自然、虚假的感受。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在谈《雷雨》的创作时,就认为《雷雨》“不好”、“做作”、“太像戏”。而《雷雨》正是在借鉴了传统戏剧的创作,特别是古希腊戏剧和易卜生戏剧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由此,传统戏剧创作中存在的缺陷可见一斑。而契诃夫剧作其创作题材似乎是从现实生活中信手拈来,在表现时遵循近乎自然主义的创作准则,结构也不事雕琢,采用散文化方式,整部剧作没有故弄玄虚,没有铺陈渲染,没有“张牙舞爪的穿插”,因此,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本色感受。
第三,根据西方戏剧理论中所谓“三S原则”, 观众在欣赏传统戏剧时,经历了这样一个审美过程,“悬念(suspension)”——“惊奇(surprise)”——“满足(satisfaction)”。观众由“悬念”而产生兴趣,随着剧情的发展,“悬念”逐渐化解,伴随“发现”而来的是人和命运的巨变,即所谓的“陡转”。这种“陡转”往往是剧中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遭到毁灭或他们的义举遭受巨大挫折,即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它给观众带来的是心灵上的强烈震撼和精神上的强烈冲击,观众由此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可见,传统戏剧主要是通过扣人心弦、令人震惊的故事情节,通过人物命运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跌宕起伏,给观众以精神上强刺激,使观众产生满足感的。这种因“惊奇”或“震惊”而产生的快感,往往是一种崇高、悲壮的感觉。
而契诃夫剧作由于缺乏大起大落、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缺少激烈的矛盾冲突,它不可能给观众带来“惊奇”或“震惊”。它主要是通过剧中人物心理上的微妙变化及弥漫全剧的“契诃夫式情调”来感染观众,以引起观众感情上的共鸣。曹禺在谈到他读了《三姊妹》后的感受时说:“读毕《三姊妹》,我阖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Masha)、哀林娜(Irina)、阿尔加(Olgu)那三个有很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处奏着欢乐的进行曲,那充满欢欣的、生命的、愉快的音乐,渐远渐微,也消失在空虚里。静默中,仿佛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喃喃地低述他们生活的抑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曹禺先生的这一段讲话再准确不过地揭示了契诃夫剧作这种陶醉人的作用。观众在欣赏契诃夫剧作时,得到的美感不是崇高之感、壮美之感,而是一种春风化雨、透彻心田的阴柔之美,一种秀美。如果说传统戏剧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大江东去”、“惊涛裂岸”,契诃夫剧作给人的审美感受则是“杏花春雨江南”、“润物细无声”。诚然,我们在欣赏契诃夫剧作时,就像是在品尝一杯上等的清茶,初品时似乎淡而无味,然而越品越觉得回味无穷,齿颊含香,正所谓至味于淡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