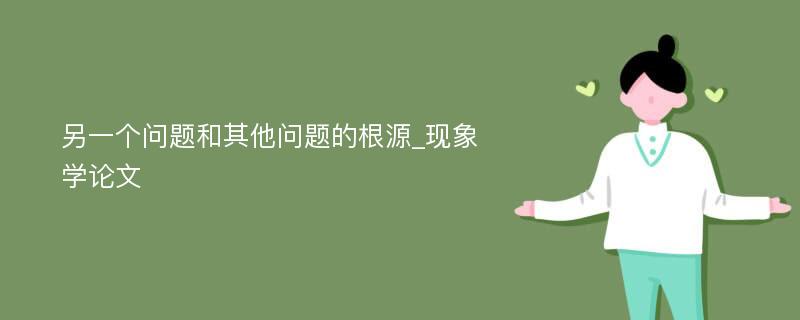
他者与他性———个问题的谱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与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分析哲学与他人之心的认知问题
英美分析哲学主要关心的是他人之心的认知问题,简称他心问题,也就是我们怎样知道除我们自己之外存在着具有思想、感情和其他心理属性的人的问题。在人工语言哲学家(如罗素、卡尔纳普等)那里,这一问题表现为以类比论证来确定他心认识的可能性与途径,在日常语言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等)那里,则转变为他心认知的语言表述问题。我们可以从罗素和维特斯坦的有关论证中窥见到这一问题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及其转换。
许多人工语言哲学家对于他心问题都有不少论述,基本上是从传统意义、认识论意义上进行探讨。罗素在多部著作中反复谈到这一主题,他和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基本倾向大致一样:一个以我的身体行为与别的身体行为间的关系来类比我心与他心间的关系,一个以此来类推我的意识与他人意识间的关系。早在其新实在论后期,罗素就以肯定物质的存在开始,以肯定他人的身体为中介,最后推论出他心的存在,“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肯定客体的独立存在,我们也便不能肯定别人身体的独立存在,因此便更不能肯定别人心灵的存在了;因为除了凭借观察他们的身体而得到的那些根据外,我们再没有别的根据可以相信他们也有心灵。这样,倘使我们不能肯定客体的独立存在,那么我们就会孤零零地失落在一片沙漠里。”(注:罗素:《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页。)从这一引文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他人身体是认知他人之心的媒介,就象卡尔纳普说过的,“不与任何身体相联系的他人之心是根本不可知的”(注: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2页。)。这就预设了类比论证。其次,罗素显然是为了避免陷入唯我论,才承认了他人心灵的存在。这两点与胡塞尔的相关论点没有根本的不同。
在后来的著作中,罗素更明确地提出了类比论证。问题源自于心理和物理现象的差异,“我们在我们自身中发现了记忆、推理、感到愉快和感到痛苦这样的事情。我们认为棍子和石头不会有这些经验,但其他人却有。”对他心的认定显然不同于对物理事实的认定,这要求一种有别于物理学解释的假定。于是我们诉诸于类比,“其他人的行为在许多方式上类似于我们自己的,于是我们假定一定有类似的原因”(注:Rosenthal编:《心之性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他人按我们同样的方式行为,因此在我们感到愉快(或不愉快)时,他人会同样感到愉快(或不愉快)。也就是说,身体行为上的相似不应该仅仅由物理上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也应该可以推出思想和感情上的相似。
罗素这样来表述这一类比论证,“抽象的表述看来是这样的:我们由观察我们自己知道一种‘A引起B’形式的因果规律,其中A是一种‘思想’,而B是一个物理事件。我们有时观察到某种B却不能观察到任何A,我们于是推断出一个A”(注:Rosenthal编:《心之性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比如,我知道我常常是因为我渴了我才说“我渴了”,当我不渴而听到“我渴了”这个句子时,我就断言一定是其他人渴了。于是就可以提出这一基本的假定:“如果每当我们能够观察A和B是出现还是不出现时,我们发现B的每一种情形有一个A作为其在先的原因,那么多数B可能有A作为其先在的原因,即使在观察使我们不能够知道A出现还是不出现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注:Rosenthal编:《心之性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不管罗素在其他地方还有什么说法,也不管别的哲学家还有什么别的表述,单从以上引文就足以使我们明白类比论证的全部意味了。
但是,在分析哲学的后来发展中,有关他心问题的这种类比论证遇到了严重挑战。大多数日常语言哲学家都认为,传统的类比论证对问题的解决是不充分的,甚至是完全的失败。比如,马尔科姆在“他心的知识”一文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我认为他心存在的类比论证仍然享有着它不应该享有的信誉,我在这篇论文中的第一目标是证明它走向的失败”(注:Rosenthal编:《心之性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这些哲学家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类比论证的出发点是为了消除唯我论,但它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罗素自己曾经表示不能严格地证明唯我论是虚妄的(注:罗素:《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页。)。卡尔纳普实际上承认他人心理以及他人身体都只不过是我的心灵的一种构造(注: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2页。)。按马尔科姆的看法,类比论证是以自己的情形推测他人心理,因此始终无法消除唯我论困境。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它让人们明白他心问题只不过是一个伪问题。他并没有直接地探讨他心问题,而是通过反私人语言论证而间接地涉及之。严格地说,他通过消解类比论证而使他心问题被消解。按照艾耶尔的看法,维特根斯坦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界定私人语言的:“试图用这种私人方式使用语言的人不仅不能把他的意义交流给他人,而且甚至也没有意义可交流给他自身;他根本不会成功地说任何事情”(注: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75页。)。显然,私人语言是绝对非沟通性的。
然而,在私人语言的非沟通性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按照库克的表述,私人语言的哲学概念得自于下述论证:没有人能知道另一个人疼痛或头晕,或者他有其他的什么感觉,因为在没有人能感觉到(经验到、亲知到)另一个人的感觉的意义上,感觉具有私人性质。而由于感觉的私人性,我们无法把感觉名称教给任何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独立于其他人和其他人对这些感觉语词的使用而给予它们以意义。这样一来,任何对自己的感觉有所述说的人所说的东西都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注: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87页。)。也就是说,私人语言旨在表达私人经验。于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否认私人语言,进而否认私人感觉与私人经验,并最终肯定主体间交流和共同经验。
我们在《哲学研究》中找到这样一个段落:“然而我们是否也能想象这样一种语言,一个人可以用这种语言写下或者说出他的内在经验——他的感情、情绪以及其它——以供他个人使用?…这种语言的单个的词所指的应该是只有说话的人知道的东西,是他的直接的私人感觉。因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懂得这种语言的”(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英国Blackwell出版公司1997年英德对照版,第88-89页§243。)。从这里可以看出,私人语言背后的私人感觉和私人经验更为根本。探讨私人语言实际上是要探讨私人感觉和私人经验的性质及其认识的可能性,如果套用他心问题的表述就是:我心能否知道他心,或者我心能否被他心所知道。
维特根斯坦下面三段话是值得注意的:“在什么意义上说我的感觉是私人的?——是啊,只有我能知道我是否真的疼痛;其他人对之只能加以推测。——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错误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是无意思的。如果我们按通常的用法来使用‘知道’这个词(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用法呢?),那么当我疼痛时,其他人通常都是知道的。——是的,但尽管如此,总不象我自己知道那样地确定无疑。对于我根本不能说我知道我疼痛(除非比如说,开一个玩笑)。这句话除了意指例如我疼痛之外还能意指什么?”“我们不能说其他人仅仅是从我的行为来获知我的感觉的,——因为对于我,并不能说我获知了我的感觉。我有我的感觉。”“下面的说法是对的:说其他人怀疑我是否疼痛,那是有意思的;说我自己怀疑就没有意思”(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英国Blackwell出版公司1997年英德对照版,第89页§246。)。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将存在着不为别人所知的私人感觉这样的说法要么看作是错误的,要么看作是无意义的。简单地说,这种说法是违背常识的,如果我们按照日常语言使用“知道”一词,我们就明白任何经验都是公共的,不存在唯我的经验。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能以我心推他心,也不能以他心推我心,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无意义的,这也是类比推理总是以己度人、从而摆脱不了唯我论的原因。事实上,他人不是通过我的身体行为来获知我的经验,而是通过参与到语言游戏中而找到了经验沟通的途径。
我们总是按照我们的语言游戏的约定来使用“疼”、“愉快”、“悲伤”之类词,这就说明私人感觉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以我们用E这一记号在日历上记下某种重复出现的感觉为例,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真正私人的语言,“我们有什么理由把'E'称为一种感觉的记号?因为‘感觉’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中的词,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懂的语言中的词。所以这个词的使用需要有一种人人都懂的辩白”(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英国Blackwell出版公司1997年英德对照版,第93页§261。)。我们实际上是在按照语言游戏规则使用表达感觉的词。由于强调游戏规则,于是就否定了语言和感觉的私人性质,他人的存在以及我与他的对话因此就不成其为问题,也就不需要寻找认识他人之心的途径。
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没有人能知道另一个人是否疼痛”这一假设或者是假的,或者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我在疼痛”和“他在疼痛”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也不能说:如果我不能经验到他人的疼痛,“他在疼痛”这样的说法就是无意义的。应该放弃这种认为个人经验是疼痛的唯一来源的假定。既然不存在着私人语言,也就不存在只有我自己理解、知道的心灵实体、精神状态与过程。“知道”、“感觉”是公共语言,它们所表达的东西是可比较的。显然,维特根斯坦不是以身体间性,而是以语言表述的公共性来证明了他人无可争议的存在,从而批判了他心问题上的怀疑论和唯我论。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无法进入他心,检验他的经验是否在性质上与我的经验相同,然而这并不排除一种谈论心理现象的公共语言。这样一来,从人工语言哲学的他心认识问题转变为日常语言哲学的语言表述问题,并因此使问题不是获得解决,而是被作为伪问题而予以消解。
二、现象学与他人意识的存在问题
在分析哲学中,他心问题从一种单纯的认识论问题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相互沟通问题。在现象学传统中,他人问题经历了类似的阶段和转换:简单地说,最初涉及的是他人意识的认识问题,然后是他人意识的存在问题。但严格地说,他人问题两阶段涉及到的都是他人的存在问题:在胡塞尔那里要问的是他人何在(在我的意识中,还是在之外)?在萨特和梅洛-庞蒂那里涉及的是他人的此在在世存在(要么与我冲突,要么与我共在)。
胡塞尔的先验还原在其现象学方法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一还原要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它最初面对着是主客关系问题,而由于他人的出现,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他人意识问题逐渐突出起来。他人问题要解决的是他人意识的认识论地位问题:他人意识属于认识活动中的主体还是属于客体,如果属于主体,他人意识如何向我的先验意识呈现出来,如果他人意识属于客体范畴,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就后一情况而言,由于意识活动的对象由意识活动构成,作为客体的他人意识就只不过是我的意识活动的构成物,这显然走向了唯我论。胡塞尔不愿意把自己归属到这一营垒中,所以就只有前一种情况。简单地说,他明确地肯定他人意识的独立存在,而不是把他人看作是意识活动的构成物。既然如此,我们就得说明同样作为内在性的他人意识如何向我的意识呈现,或者说我们如何形成对他人意识的认识。胡塞尔以身体为媒介,以类比和共现来解决难题(胡塞尔的论证较罗素的论证更复杂一些,但基本的思路一致的,故不再重复这一论证)。
我们知道,胡塞尔是在晚期作品中才着手探讨他人问题的,这与他开始关注生活世界和历史理解等问题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由纯粹意识领域转向历史和实践领域。严格地说,在他的思想中并不存在所谓的转向,他只不过是在寻找回到先验主观性的更可靠途径。对于海德格尔以及后来的现象学家来说,他们倒希望这是一次真正的转向。胡塞尔顽固地抓牢先验主观性或纯粹意识这一支撑点,显然没有满足许多弟子的愿望。就他人问题而言,先验意识只是为了保证意识对象的客观性才求助于别的意识,他人只不过是构成世界的一个补充范畴,他人作为世界之外一个正存在着的真实存在没有也始终无法获得论证。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唯我论,胡塞尔没有把他人看作是由我的意识构成的。但是,他人只不过是我的认识对象被构成的一种辅助条件,其本己的存在根本没有被提及。所以有人指出,“他的动机不是去证明别的自我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相反,胡塞尔打算强调主体间性问题对于客观真理的要求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注:Mohanty等编:《胡塞尔现象学教程》,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年版,第318页。)。萨特、梅洛-庞蒂和列维纳斯等胡塞尔弟子力图通过某种努力由他们自己来实现这种转变。当然,除了否定胡塞尔的认识论姿态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外,这些弟子之间的立场也各各不同。
萨特明确否定胡塞尔的他人问题上的认识论立场,他和海德格尔一样从生存论-存在论出发。海德格尔抛弃了胡塞尔的意识概念,他把他人与“我们”的非本真状态的日常在世的存在形式联系在一起,他人就是“常人”。萨特认为,这种他人实际上是康德意义上的普遍主体的异化形式,并没有考虑到在我的存在之外的真正意义上的他人的存在。于是在萨特那里,目标仍然是胡塞尔意义上的作为纯粹意识的他人,但探索的角度不再是认识论而是生存论-存在论。人的实在既包括自为(纯粹意识,无化)的一面,也包括自在(对象意识,物化)的一面。萨特从他人对我的实在的自在方面的构成性意义角度提出了他人概念,“他人不只是向我揭示了我是什么:他还在一种可以支撑一些新的定性的新的存在类型上构成了我”(注:萨特:《存在与虚无》,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43年版,第260页。)。简单地说,没有他人意识,我就不会有自在的存在,就只有纯粹而完全的目为。
萨特以羞耻为例。我之所以对自己感到羞耻,是因为我承认我就是别人注视着的那个“什么”(对象):“羞耻按其原始结构是在某人面前的羞耻”(注:萨特:《存在与虚无》,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43年版,第259页。)。这表明:首先,我必须承认我与某个对象具有一种存在关系,他人的存在足以使我“是其所是”。其次,我之所以对我自己感到羞耻,是因为我向他人显现,从而他人是存在着的。我在他人的注视中成为一个对象,一个客体,这既表明了我的存在的自在方面,也表明了他人意识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内在性的他人意识通过这一注视(或别的身体行为)向我的意识间接地呈现了出来。与胡塞尔用他人来保证认识的客观性不同,萨特引出他人以证明人的实在的自在方面的起源。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他人的存在,一是我与他人的存在的存在关系。萨特没有对第一个问题花费太多笔墨,差不多是直接断言了他人的存在,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则着力进行描述。其基本立场是:他人跟我一样作为具有否定特征的纯粹意识而存在;他是一个生存主体而不是认识对象;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限制对方的自由,却又恰恰意味着彼此都是自由的这种微妙关系。意识间关系的本质不是共在,而是冲突。
显然,萨特与胡塞尔的他人问题解决方案都是有问题的。他们都把人的实在看作是纯粹意识,而且意识又是完全内在的,所以不管是认识他人还是确认他人的存在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都借助身体行为间的关系类推意识间的关系,然而,他们又都自己封闭了身体和意识间的通道。这是因为,身体是外在存在,意识是内在存在,两者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进一步说,萨特把意识与绝对自由划等号,而争夺自由导致互相将对方对象化,胡塞尔在认识论中遇到的唯我论问题换一个方式又在存在论中出现了。
梅洛-庞蒂的整个思想的灵感源泉是胡塞尔晚期提出的“先验的主观性就是主体间性”这一思想。但是,由于强调海德格尔的“在世”概念,他克服了胡塞尔和萨特对内在意识的迷恋,他从根本上就否认内在意识与外在身体之间的严格区分。而且,一种新的身体概念居于其学说的核心地位。身体被看作是“感觉着的事物”,是“主体-客体”。我的身体如此,别的身体亦然,“我们既不将他人置于自在之中,也不将之置于自为之中”(注: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69年版,第190页。)。人的身体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揭示人的身体就是揭示人的存在。于是我与他人的关系变成为身体间关系,而不是意识间关系。
这意味着,我的身体器官间的关系可以推广到身体间去。于是,我的右手握着左手与我的手握着别人的手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我的手在握别人的手时,如果我有着它在那里存在的明证,这是因为它替换了我的左手,是因为我的身体在它矛盾地成为处所的‘这种想法’中与别人的身体合并在一起。我的双手‘共现’或者‘并存’,因为它们是同一身体的两只手:他人作为这一共现的延伸而出现,他和我就象是唯一的身体间性的器官”(注:梅洛-庞蒂:《哲学赞词及其他论文》,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53与1960年版,第214页。)。这种表述实际上是胡塞尔的类比论证的翻版。当然,通过身体的灵化,他简化了这一类比,并且避免了由外在身体如何向内在意识过渡这一难题。在针对别人认为类比论证不能解决由身体向精神过渡这一问题时,他这样来为老师圆场:在胡塞尔那里,“不存在为了一个精神构造一个精神,而是为了一个人构造一个人”(注:梅洛-庞蒂:《哲学赞词及其他论文》,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53与1960年版,第215-216页。)。也即,不应该只瞄准单纯的精神,身体作为一种具有感受性的东西,应该是精神与物质的整体,他人身体的呈现就代表着他人的全体呈现。
胡塞尔为了克服唯我论而求助于他人来保障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在梅洛-庞蒂这里,由于将身体灵化,仍然存在着唯我论问题,“相对于我的身体而言的事物,乃是‘唯我论’的事物,这还不是事物本身。”这明显承认与我的身体相关的事物都有“为我”性质,于是为了保证事物的真正存在,还应该求助于别的身体,“只有当我懂得:这些事物也为其他人看到,它们被推定对于所有的目击者都是可见的,我的身体所知觉到事物才是真正的存在”(注:梅洛-庞蒂:《哲学赞词及其他论文》,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53与1960年版,第213-214页。)。他进而将这种灵化的身体看作是世界的实质:身体间性之所以成立,是由于世界本身是既作为被感觉者、又作为感觉者的具有灵性的“肉”。我的两只手、两只眼睛彼此协同地面对同一个世界,我的身体与别的身体也同样协同地面对一个共同世界,原因就在于身体属于世界之肉。他的结论是“不存在着关于别的自我的难题”,这是因为,“不是我在看,也不是他在看,而是一种无名的可见性停留在我们两者全体,某种一般视觉按照原始性质隶属于肉,在此地此时向四处延伸,既是个体,同时也是尺度和普遍”(注:梅洛-庞蒂:《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64年版,第187-188页。)。
梅洛-庞蒂同意萨特的看法,对他人问题的在世理解使我们回归生存,而不是处在认识之维。但是他否认萨特提出的在注视中他人和我彼此将对方置于客体地位、彼此否定对方的自由的看法。他认为,注视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可能的沟通,即便拒绝沟通也是一种沟通形式(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45年版,第414页。)。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孤独和沟通看作是两难选择,而应当将它们看作是在世现象的两个方面,在世的实质是共在。他人在萨特和梅洛-庞蒂各自体系中的地位也是有差别的,这是由他们分别关注不同时期的胡塞尔思想造成的。诚如施皮格柏格所说:“在萨特看来,《观念》一书是胡塞尔的主要著作。而梅洛-庞蒂则认为,胡塞尔思想的最重要阶段是他的晚期阶段,特别是他死后发表的著作中所表述的那些思想”(注:施皮格柏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39页。)。萨特和胡塞尔一样关注内在意识和先验主观性,这使得他人只具有次要地位,是为了解决中心问题不得不引入的一个概念。而梅洛-庞蒂一开始就批判内在意识先验主观性,直接从主体间性出发,因此他人一开始就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三、后现代哲学与绝对他性问题
前面论及的有关思想,尽管不无分歧,但都是力图转换他性。虽然他人获得承认,但被认为是别的“意识”,别的“自我”,因此与我还是“同类”,我怎么样,他实际上也就怎么样。因此,不管是所谓的类比论证、“冲突”与“共在”学说,还是对私人语言与私人感觉的否定,无不认可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说法。但他性问题在后现代哲学中出现了转折。一方面,范围更为广泛,不仅涉及他人的他性,还探讨文化的他性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绝对他性的认可成为根本的出发点。列维纳斯作为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集中探讨了他人的绝对他性问题,而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通过批判反思现代性而揭示了理性的各种他者的命运(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罗蒂、杰姆逊等人也多有论述,赛义德等人在有关后殖民主义的学说中则把福柯等人的思想用于批判西方中心论,进而为非西方文化的绝对他性作辨护)。不管是他人的他性还是文化的他性,都表现为对趋同化、向心性倾向的突破,并且力主向多样化、异质性开放。
同梅洛-庞蒂一样,列维纳斯从胡塞尔晚期思想和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学说出发,但他最终超越了现象学。他提出的所谓的“他人的人道主义”把他人看作是绝对的他者。他主张自己的思想既是对现象学认识论又是对现象学存在论的超越,是一种伦理学或形而上学。列维纳斯的许多作品都直接涉及他人问题,他人的地位、他人的命运是他的哲学的唯一主题。他人是上帝或无限的象征,这就否定了“我思”包纳一切的整体性,他人始终处于我的自我中心的同化之外,他处于绝对外在或超越之中。
列维纳斯主张超越现象学认识论。在他看来,大凡认识总是意味着将认识对象纳入到认识的整体中,成为为我之物,不管是身边之物还是遥远的星辰概莫能外。但他人不同于这些认识对象,他是不可能被整合到我的认识之中的、不能被纳入到整体中的无限。他用“面孔”一词来具体描述他人。有人将他的这种思想概括为一种“面孔的现象学”。他就此这样评论道,“我不知道人们可否说面孔的‘现象学’,因为现象学描述呈现的东西。同样,我要问人们能否谈论朝向他人的注视,因为注视是认识,是知觉。我的想法是对面孔的触及一开始就是伦理的……与面孔的关系或许可能为知觉所控制,但那特别的面孔,是那不能还原到知觉的面孔”(注:列维纳斯:《伦理与无限》,法国Fata Morgana出版社1982年版,第89-90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他人问题上,他要求超越胡塞尔的认识论立场,而萨特的注视说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理论也被作为变相的认识论予以扬弃。
列维纳斯更为强烈地主张超越现象学存在论。与海德格尔的从存在者回归存在的要求不同,他主张从存在走向存在者。他认为,是存在者在存在着,而不是存在托负着存在者,“存在者主宰着存在,就象主体主宰着属性一样”(注: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法国J.Vrin哲学书店1990年版,第16页。)。这种从存在到存在者的还原摧毁了孤独自我的生存关怀的基础。自我生存始终是排斥外在性、异质性、他性和他人的。超越“存在”意味着不再有惊醒的、失眠的孤独自我,我处于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之中。面孔实际上是作为弱者的他人的象征。他人柔弱、赤贫,他人面孔没有防范地向我们直接展示,它最容易受到伤害。与此同时,它警示我们不要伤害别人。这实际上是说,不要把他人看作是我们的生存竞争对手,我们不能因为自我生存而剥夺他人的生存。相反,由于他人是弱者,我们应该对他人负有完全的责任。列维纳斯要求走出海德格尔的中性的、没有道德的存在论。
在否定的基础上进入肯定,列维纳斯要求建构一种伦理学。存在意味着实现自己的本质,实际上是追求个人利益。伦理学要求走出存在,超越本质,相反要求公正。列维纳斯用连字号将“公正”分解为三个词的组合,以便强调其走出存在的含义——即“走出-内在-存在”。超越自己的存在和本质,就意味着由对自己负责转向对别人负责。我对他人负责而不期待相互关系,就象祈祷上帝而不指望回报一样,这乃是伦理关系中的非齐一性。上帝或无限并不自我呈现,只有对他人负责的主体才始终在见证着上帝与无限。他人问题于是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它探讨的是超越和他性问题,而不象存在论那样探讨内在和同一问题。列维纳斯显然将他人问题推进到了极端的程度:他人是外在的,是绝对的超越,我们应该以伦理的姿态走出自我的封闭圈。
福柯曾经受到现象学的广泛影响,后来则在现象学批判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思路。他立足于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旨在揭示各种非理性因素作为理性的他者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在近代以前,西方理性文化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内部异质因素也采取了宽容的姿态。在中世纪,理性甚至沦落为非理性(主要是信仰)的他者之地位。只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理性才开始摆脱这种从属状态,重新开始在西方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在十七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中,西方文化逐步演变为理性成份尤其是科学理性高歌猛进、单一膨胀的过程,越来越走向一种唯理性主义、唯科学主义。在这一理性进程中,人自然归属于普遍理性主体范畴,不会存在什么他人,也不容许具有他性的他人成为西方文化的载体之一。所以近代哲学文献中充斥的都是大写的“我”。一些哲学家(例如卢梭、康德、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已经对这种单向文化发展提出了批评与限制。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中坚人物,福柯对现代性之谱系的清理最为典型地代表着西方哲学家对于西方文化内部异质性因素之命运的关注。
从表面上看,福柯探讨的对象各异,写作的风格不尽相同,而就其实质,他的全部工作都旨在探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力图揭示现代性进程中理性对于作为他者的各类非理性的种种控制策略。也就是说,对他者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理性中心论形态中的命运进行深刻的剖析,借以表明:西方文化的理性化进程或专断或狡诈地将非理性置于无声境地,改造和转化非理性因素变成为理性权力之成效的集中体现。有些时候,理性以真理和求知的名义压制别的声音,“倾向于对其他话语形式实施一种压制,充当控制权”(注:福柯:《话语的秩序》,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71年版,第20页。)。另一些时候,则实施一些较为温和的控制技巧,即对异质的力量实施一种规训技巧,将之改造为有用而服从的力量,“规训……是权力的个体化技巧。规训在我看来就是如何监视某人,如何控制他的举止、他的行为、他的态度,如何强化他的成绩、墙加他的能力,如何将他安置在他最有用之地”(注:福柯:《言与文》第4卷,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福柯发现,理性实际上具有难以克服的自身弱点。现代性意味着理性以不同的方式向各个领域渗透,意味着理性力图确立自己对他者的全面控制。但是,理性侵入这些领域,其目的并不仅仅是压制和排斥他者。人的认知意志把疯癫、疾病、犯罪、性错乱之类消极方面,把人的生命、劳动和语言等积极方面纳入到认识领域,以便人能够更好地更完整地道出自身的真相。认识他者实际上就是认识自身的某一方面。从根本上说,现代性就意味着人对自己的有限性和反常方面的认识;要么发现自己的有限存在(有生命之物,生产的工具,语言的载体),要么发现自己的反常存在(病态主体,犯罪主体,性错乱者)。这实际上意味着理性自身是有限的,人受制于这些作为他者的因素。这就表明,理性并不是人的全部,理性并不是文化的全部。非理性的因素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不应该消除和同化这种他性与异质性。
当然,福柯并不准备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理性,民主、科学的旗号下实际上干了许多荒唐的事情,结果为此付出了或将要付出许多惨痛的代价。想想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他们批判神学、批判专制,为理性、为自由争地盘,然而,理性战胜了神学,自由战胜了专制吗?情况或许相反,理性现在是高高在上,利用神学同样的手段来排斥异己。人们开始迷信理性,理性自己变成了神学。福柯实际上是站在多元论立场上,他希望听到多种声音,希望西方社会丰富多彩,而不是处在某一中心权力的阴影之下。福柯是各种沉默无言的他者的代言人,是这些异质成份的他性的维护者。后来的一些思想家发挥这一理论,力主非西方文化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应该承认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而不再向西方这一所谓的中心或主流靠拢,这就真正承认了别的文化自身具有的难以消除的他性。
